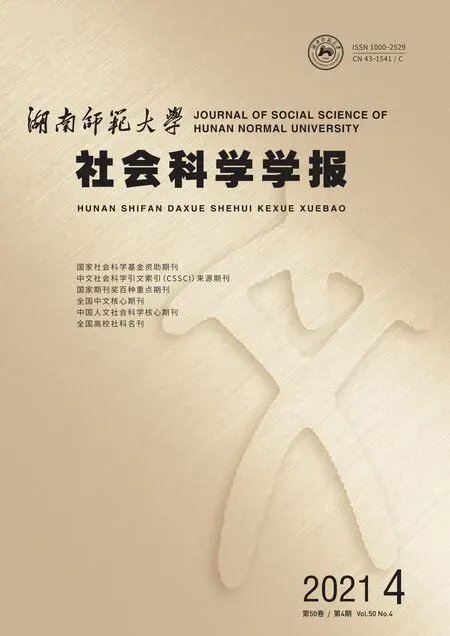論列寧黨內斗爭思想及其時代價值
丁 敏,李包庚
當前,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錯綜復雜的國際環境和艱巨的國內改革發展穩定任務,使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能力面臨嚴峻考驗。黨內一些同志思想不純、組織不純、作風不純等現象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存在,離“把黨建設成為始終走在時代前列、人民衷心擁護、勇于自我革命、經得起各種風浪考驗、朝氣蓬勃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的目標還有較大差距,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凝心聚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要求還有較大差距[1]。因此,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發展階段,如何開展黨內斗爭、加強黨的自身建設,是保持黨的先進性、革命性、戰斗力和凝聚力的關鍵所在。列寧高度重視黨內斗爭①,明確黨內斗爭本質上是思想斗爭,并在與民粹派、經濟派、調和派、托洛茨基派等錯誤思潮博弈的過程中,逐步形成了黨內斗爭思想。這一思想是蘇共革命和建設時期解決黨內矛盾沖突的理論指導,也是維護黨的團結和黨的建設的行動指南。列寧關于黨內斗爭的思想,對當下馬克思主義政黨而言,依然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一、列寧的“黨內斗爭”概念及其本質
自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無產階級政黨以來,黨內斗爭問題始終是黨建學說的重要內容。馬克思、恩格斯在談及無產階級政黨建設時指出,政黨產生的社會歷史條件要求政黨必須在其內部斗爭中實現自我發展。恩格斯早在1889年就已洞見,黨的發展“通常伴隨著黨內溫和派和極端派的發展和相互斗爭”[2]。列寧作為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忠實踐行者,在布爾什維克黨的建設過程中也提出進行黨內斗爭是有必要的,他認為“公開的、直接的斗爭是恢復統一的一個必要條件”[3]。
列寧認為,黨內斗爭的本質是思想斗爭。無產階級政黨伴隨工人運動而產生,黨內不同派別伴隨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運動相結合的過程而產生。列寧指出,黨之所以在革命中會產生各種派別,歸根結底,是因為他們思想上的轉變與差異,“思想斗爭是理解俄國革命的重要內容”。在《工人運動中的思想斗爭》一文中,列寧對1895至1914年布爾什維克黨與歪曲工人運動的孟什維克之間的斗爭進行了總結,指出俄國這20年的斗爭本質上是馬克思主義運動中不同派別之間的思想斗爭:“也就在這個時候開始了馬克思主義運動中的兩個派別的思想斗爭。”[4]列寧在《進一步,退兩步》《社會主義和宗教》《國家杜馬和社會民主黨的策略》《怎么辦》等一系列文章中表達了俄國黨內斗爭的本質是思想領域內的斗爭的觀點,這些斗爭產生的積極影響是,第一次牢固形成“真正馬克思主義政黨的真正無產階級基礎”,“走上了先進階級為實現人類的先進歷史任務而斗爭的正確道路”[4]。正是在不斷解決黨內思想斗爭中,布爾什維克黨才逐漸走向成熟,工人運動也才在由馬克思主義闡明的爭取解放的道路上越走越堅定。
思想斗爭以組織原則、革命和建設策略為外在表現。列寧對黨內斗爭的論述主要圍繞黨內各派別偏離或放棄馬克思主義、造成黨內分裂的問題展開。在建黨之初,黨內斗爭集中于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之間關于組織原則的斗爭。列寧把組織原則的斗爭歸結為思想斗爭的低級形式,稱“沒有思想上的統一,組織上的統一是沒有意義的”[5]。1905年,俄國資產階級革命爆發,黨內斗爭主要圍繞革命領導權問題展開。列寧認為,無產階級政黨不僅要在革命中起到領導作用,還要在思想上形成統一的力量。所以,他通過黨的代表大會、黨刊等來批評孟什維克的小資產階級局限性,指出黨不僅要掌握資產階級革命的領導權,還要進行教育和集體鼓動,在思想上達到統一,為社會主義革命準備條件。在革命失敗后,黨內“取消派”和“召回派”散布不相信革命會取得勝利的言論。列寧對這兩個派別進行批評,指出他們內部存在的資產階級思想是其對革命事業走向失去正確判斷的重要因素,布爾什維克黨與他們的斗爭是資產階級自由派思想與馬克思主義之間的理論斗爭。在由革命轉向建設時期,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在黨內挑起了關于工會問題的爭論,列寧在《黨內危機》中指出,布哈林關于工會的提綱完全背離了共產主義道路而走向了工團主義,而這種背叛是“思想瓦解達到頂點的表現”[6]。所以,總體觀之,雖然黨內斗爭在俄國革命中有不同的表現形式,但它本質上還是屬于思想上的差異與分歧。
黨內斗爭的目的是維護黨內團結。從表面上看,斗爭與團結相互對立,二者不可調和。列寧從唯物辯證法出發,看到了斗爭與團結之間的辯證關系,指出黨內斗爭不僅要看到差別和矛盾,還要看到黨內斗爭向其對立面轉化這個“重要的東西”。一方面,黨內斗爭和黨內團結相互依賴,雙方共處在一個矛盾統一體之中。黨內團結通過斗爭來實現,而團結不能浮于外在形式,要敢于承認黨內實際存在的問題和矛盾,敢于“為我們認為正確的策略”與問題和矛盾進行“公開的、直接的、堅決的、徹底的思想斗爭”[7]。因為“保存力量要靠統一協調的、在原則上一致的組織,而不是靠不同類東西的黏合。這種徒勞的黏合不會保存力量,而會消耗力量”[8]。同時,黨內斗爭也是無產階級組織統一的前提:“不這樣,群眾就會渙散;不這樣,就不會有共同的決定,因而也就不可能有統一的行動;不這樣,那些‘能識別問題的實質’的工人的馬克思主義組織就會瓦解。”[9]另一方面,二者還相互貫通,在一定條件下可以相互轉化,而這種轉化的標志或界限則表現為矛盾的一方在數量上是否達到了矛盾轉化的臨界點。列寧認為,把握這種從量變到質變轉化的臨界點就是把握革命勝利的規律:“在決定性時機和決定性地點在力量上占壓倒優勢……特別是在殘酷的、激烈的、稱為革命的階級戰爭中取得政治勝利的規律。”[10]盡管黨內斗爭會向其對立面轉化,但是這種轉化必須保持在一定的限度內。如果斗爭超出了一定限度,就會引發政治斗爭,而如果黨內不允許任何形式的斗爭,那么就無法發揮或增強無產階級政黨自我凈化的獨特優勢。同時,黨內存在的問題得不到解決,并隨著矛盾的加劇,黨仍面臨執政風險。只有在一定的限度內開展黨內斗爭,才能有的放矢,既給予黨員空間,解決矛盾,又對其嚴格約束,防止出現黨內分裂。因此,允許黨內存在斗爭并不是說完全放任黨內矛盾的發展,而是要求把矛盾保持在一定限度之內,既保證黨員實現“思想自由,行動一致”,又保證黨能充分發揮自我凈化的獨特優勢。
二、列寧解決黨內斗爭的基本思路
黨內斗爭是實現黨內團結的必然要求,是唯物辯證法思想在黨建領域的生動體現,恰如毛澤東所言:“黨內如果沒有矛盾和解決矛盾的思想斗爭,黨的生命就停止了。”[11]在俄國革命和建設過程中,無產階級政黨起著領導核心作用,但黨內斗爭會影響革命運動的展開和推進。從整體上把握黨內斗爭的表現形式,能夠更全面了解列寧黨內斗爭思想的主要內容。面對思想上哲學無黨性的沖擊、政治上“左”右傾錯誤的影響、作風上批評與自我批評受限以及組織上黨員質量帶來執政危機等問題,列寧堅持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為指導,對不同歷史階段的實踐經驗進行總結,形成了一系列關于黨內斗爭的重要理論和方法,豐富了馬克思主義政黨學說,也為其他國家的政黨建設提供有益借鑒。
(一)堅持哲學的黨性是解決黨內斗爭的理論前提
馬克思主義哲學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核心部分,是無產階級政黨的立黨之本。所謂哲學的黨性,就是要求哲學理論保持其鮮明的階級立場。馬克思主義哲學毫不掩蓋自己的階級立場,它的目的就是指導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完成“改造世界”的政治革命。針對德國小資產階級口中的“真正的社會主義”,恩格斯對其進行了批評,認為這種社會主義的“理論沒有黨性”,無法使“德國走向革命,推動無產階級并促使群眾去思考和行動”[12]!無產階級作為最先進最革命的階級,只有保持哲學理論的正確性,才能把這些理論上升為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發揮無產階級政黨凝聚群眾的力量。列寧在黨內斗爭中重提“哲學有黨性”的任務,強調要弄清楚唯物和唯心的區別及其所反映的階級屬性的差異,把政治行動、黨性教育與黨性立場結合起來,既克服黨內馬赫主義的攻擊,又確保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穩步前進。
“哲學有黨性”強調思想理論的階級屬性。列寧關于“哲學有黨性”的觀點是針對馬赫哲學的“非黨性”提出來的,它強調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分別代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思想體系,反對政黨內部的資產階級立場或中立立場,“因為在為資產階級社會的自由而進行斗爭的人們當中,沒有政黨就意味著沒有反對這個資產階級社會本身的新的斗爭”[7]。無產階級政黨從階級斗爭中產生,黨性反映著政黨的階級性,所以,作為黨性的外在表現形式——無產階級政黨,要在理論上堅持唯物主義,才能成為反對資產階級的先鋒隊。而馬赫主義的中立立場表現為“默默支持強者”,其實質是掩飾自己所代表的資產階級利益。列寧以一個比喻生動說明了馬赫主義的立場:“對一小塊面包‘冷淡和漠不關心’,并不是說這個人不需要面包,而是說這個人從來不愁面包,從未缺少面包,是說他牢牢地依附于飽食者的‘政黨’。”[7]這樣,哲學的黨性立場與非黨性立場就構成了俄國黨內斗爭的思想根源。當黨內的波格丹諾夫等人試圖用馬赫主義指導俄國革命實踐時,革命形勢自然就走向危機。在這一背景下,列寧力挽狂瀾,在理論上詳細闡述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科學性和先進性,夯實了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基礎,在實踐上扭轉了革命走向,使之朝正確的方向前進。
“哲學有黨性”要求將思想理論外化為政治行動。“哲學有黨性”不僅要求理論本身有黨性,還要求將黨性貫徹于革命實踐之中。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黨性不僅僅停留在廓清階級界限上去“解釋世界”,更要在把握革命規律的基礎上“改變世界”,“我們必須力求注意使黨性不僅僅停留在口頭上,而能見諸行動”[13]。受馬赫唯心主義哲學的影響,俄國黨內“召回派”和“取消派”在理論上攻擊馬克思主義哲學,妄言馬克思主義已經過時;在實踐上忽視革命具體形勢,主觀制訂革命策略,盲目擴張革命范圍或放棄革命。列寧嚴厲批評兩派的錯誤主張,提出了黨在革命低潮時期的任務和斗爭策略,認為黨要根據當前階段的革命情況和規律來決定是采取公開斗爭還是秘密斗爭的革命策略。列寧不僅要求黨員在行動上體現黨性,還要求在行動中錘煉黨性。在黨群關系上,他主張參加國家杜馬,反對調和主義,利用一切宣傳鼓動手段來爭取群眾走向革命隊伍;在宗教問題上,他采取辯證的態度吸收信教群眾入黨,把黨變成一個具有凝聚群眾力量的組織。他還把黨性教育作為反對小組習氣斗爭、維護“哲學有黨性”的重要途徑,黨性教育要在加強紀律和依托黨報之上與小組習氣進行斗爭,“黨報與其他文學事業必須站在黨性的立場上來,并依托黨報與小組習氣進行斗爭”[7]。
(二)“兩條戰線斗爭”是處理黨內斗爭的基本原則
“兩條戰線斗爭”指“左”傾、右傾之間的斗爭。“戰線斗爭”不同于“路線斗爭”,二者的區別需通過“傾向”來把握。列寧從“傾向”出發,闡述了“戰線斗爭”的特征。傾向指可以糾正的、未定型的認識論狀態,錯誤的傾向是可以通過批評、爭論等方式解決的:“傾向是一種可以糾正的東西。一些人已經有些走入歧途或者開始走入歧途,但還是可以糾正的。”[14]列寧在黨內開展反“左”傾和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斗爭的過程中,第一次把這種傾向斗爭明確概括為“兩條戰線的斗爭”。這類斗爭是圍繞正確路線而展開的“左”傾和右傾的斗爭,它們可以通過內部批評來糾正的。但列寧并沒有論述過“路線斗爭”,它最早派生于王明1930年寫成的《兩條路線》一文,主要指錯誤路線和正確路線之爭,即馬克思主義與非馬克思主義路線之間的斗爭。這類斗爭只能通過生死搏斗來解決。在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史上,曾多次出現過將黨內斗爭粗暴地歸結為“路線斗爭”的狀況,直到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后,“路線斗爭”的界限問題才真正解決:“黨內斗爭是什么性質就說是什么性質,犯了什么錯誤就說是什么錯誤,講它的內容原則上不再用路線斗爭的提法。”[15]總而言之,“戰線斗爭”針對的是黨內錯誤傾向,在革命實踐中體現為黨內“左”傾、右傾斗爭,而“路線斗爭”則是圍繞思想體系展開的生死搏斗,二者之間的關系體現為:“戰線斗爭”是“路線斗爭”在黨內的具體表現形式。
處理“戰線斗爭”要堅持兩點論的實踐方法。黨內斗爭是事關革命事業全局的重要問題,它是由許多矛盾相互鏈接而形成的整體。因此,在處理矛盾時要注意把握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既要解決主要矛盾,又要兼顧次要矛盾。1905年俄國革命失敗后,社會民主黨黨內出現了機會主義“取消派”和“左”傾召回派兩個派別。列寧在《我們的取消派》《關于鞏固黨和黨的統一的決議草案》《論目前思想混亂的某些根源》《論統一》《政論家札記》等文章中對兩個派別都進行了批評和斗爭,并指出:“反對召回主義和取消主義的斗爭在我們黨內的真正馬克思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分子的任務中,自然是占首要地位的。”[13]在推進政黨建設的主要矛盾中,列寧既看到“取消派”又看到“召回派”對無產階級革命進程的影響,“取消派”在思想和組織上都是“要毀壞無產階級的階級獨立性,用資產階級思想來敗壞無產階級的意識”,而“召回派”事實上妨礙黨聚集力量去迎接新的革命高潮[9]。經過斗爭,“召回派”和“取消派”相繼在1909年和1912年被清除出黨。
處理“戰線斗爭”要堅持重點論的實踐方針。列寧指出,政治形式是錯綜復雜的,要把握整體性“就必須抓住主要環節。不能你想抓哪個環節就挑哪個環節”[16]。十月革命勝利后,列寧把黨內斗爭的重點放在與“左派”在政治和經濟路線方面的斗爭上。針對俄國要不要簽訂布列斯特和約來創造和平的國內環境這一問題,列寧準確把握俄國形勢,提出簽訂布列斯特和約的建議,但遭“左派”反對。列寧揭露“左派”只是帝國主義進行挑釁的工具,提出要“打倒裝腔作勢的作風!認真進行整頓紀律、加強組織的工作!”[17]在列寧的斗爭下,1918年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通過了其主張,并與德國簽訂了條約,為蘇維埃政權爭取到喘息時間。此后,“左派”針對列寧要把國內主要矛盾轉移到提高生產率的問題上來,以《關于目前形勢的提綱》公開反對其主張,并指責列寧是在利用資本主義發展經濟、背叛社會主義,認為蘇聯在“‘右派布爾什維克的傾向’的影響之下有‘演變到國家資本主義去’的危險”[18]。對此,列寧專門寫了《論“左派”幼稚性和小資產階級性》揭露“左派”的小資產階級特性,指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的最充分的物質準備,是社會主義的前階”[18]。不經歷國家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共同的東西——計算和監督,是把握不了俄國的經濟狀況的,像“左派”那樣用“向國家資本主義方向演變”只是在理論上自己嚇唬自己,在實踐中倒向小資產階級。
(三)批評和自我批評是處理黨內斗爭的有效途徑
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是衡量政黨能否“真正履行對本階級和勞動群眾所負義務”的重要標準。批評和自我批評與黨的生存發展密切相關,馬克思主義政黨之所以充滿活力,就在于它敢于批評和自我批評:“我們應該有勇氣揭開我們的膿瘡,以便老老實實地進行診斷,對癥下藥地加以治療。”[19]列寧認為批評和自我批評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建設的內在要求,意味著批評是黨員的權利和義務。也因如此,在面對丘德諾夫斯基對人民委員的尖銳批評時,列寧坦誠道:“這里根本談不上能不能冒昧地進行尖銳的批評,進行尖銳的批評是革命者的責任,人民委員并不認為自己絕對沒有過錯。”[17]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清除腐朽的、落后的東西的目的是維護人民群眾利益,帶領人民群眾創造美好生活:“先鋒隊要不怕進行自我教育,自我改正……要用行動、實踐和經驗向農民證明,我們在學習并且一定能學會幫助他們,率領他們前進。”[16]
開展黨內批評要堅持把“批評自由”與“行動一致”相結合。“批評自由”與“行動一致”思想是列寧思考黨內要通過什么途徑來開展思想斗爭的問題而形成的。1906年5月,列寧在《批評自由和行動一致》中批評了孟什維克只允許批評在黨的會議上進行的觀點,并闡明了“批評自由”與“行動一致”相統一的限度和條件。以批評與選舉為例,批評選舉要保持一定原則,在選舉未舉行前,黨員可以就選舉提出批評意見,而在選舉期間,批評選舉的行為是不允許的。也就是說,黨員有批評自由,但是批評要遵循一定原則:要在黨章規定的范圍內進行。同年11月,在《同立憲民主黨化的社會民主黨人的斗爭和黨的紀律》一文中,他又把“批評自由”與“行動一致”統一起來,“行動一致”是“批評自由”的前提,沒有組織和行動的統一,批評自由是無法實現的。同樣,沒有“批評自由”,“行動一致”也無法達成。同時,他還把它視作黨的紀律建設的重要內容,“行動一致,討論和批評自由”才是“先進階級民主主義政黨所應有的紀律”[20]。
開展黨內批評要堅持“批評有內容”。“批評有內容”是列寧在《關于選舉莫斯科委員會的講話》中提出的,其目的是,在革命結束后解決黨內日益激烈的思想斗爭。“批評有內容”就是要實事求是,既要肯定其功勞,又要批評其存在的問題,“每一個黨的工作人員在工作中都有缺點,但是在批評缺點或向黨的各個中央機構分析這些缺點時,應當慎重,注意分寸,否則就成為搬弄是非”[21]。“批評有內容”不僅要求批評時要做到恰如其分,還要保證批評的目的是為黨和人民的利益服務,“使黨能夠領導蘇維埃的經濟建設,取得實際的成就”,讓人民群眾相信無產階級政黨是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政黨,是人民利益的維護者[6]。“批評自由”與“批評有內容”相結合,推動著黨內斗爭的解決,促進國內經濟的發展。
(四)“清黨”是解決黨內斗爭的必要補充
列寧“清黨”工作不同于斯大林的“大清洗”,它以維護黨的團結、純潔黨的隊伍、加強黨自身建設為目的。在《怎么辦》的題記中,列寧引用了拉薩爾的話——“黨內斗爭給黨以力量和生氣,而黨本身的模糊不清、界限不明,則是黨的軟弱的最大明證;黨是靠清洗自己而鞏固的”——來表明黨自身的建設是其獲得戰斗力和凝聚力的內因[22]。十月革命后,黨能否繼續代表人民群眾的利益,能否繼續保持共產主義理想信念,守住執政地位,是俄共(布)面臨的重要挑戰。基于此,列寧分別于1919年和1921年開展“清黨”工作,雖然在“清黨”過程中“也犯了相當多的局部性的錯誤”,但不可否認的是,這一工作不僅提高了黨員質量,還對嚴肅黨內政治生態、純潔黨的隊伍以及鞏固黨的執政基礎起到重要作用。
“清黨”是要解決黨內成分復雜、思想守舊的派別組織。列寧從與孟什維克的分歧中深刻了解到,黨內成分復雜必然導致黨派斗爭。革命勝利之后,列寧敏銳地觀察到,黨內舊社會殘余思想、各種資產階級思想仍侵蝕黨內不堅定分子,以及部分黨員居功自傲、喪失共產主義信念等問題,嚴重影響黨的隊伍建設和黨內團結。為克服這一問題,他提出要清除黨內敵人的口號:第一,清除黨內過去的孟什維克。孟什維克作為資產階級的代言人,其反動性始終存在,因此必須把“改頭換面但內心里依然故我的孟什維克從黨內清除出去”[12]。第二,除了清除孟什維克,還要清除黨內一切自私自利分子和派別組織。列寧尖銳地指出,那些只開會不做實事的官員以及那些忘記黨的性質、以權謀私的官僚主義作風,往往只會帶來革命的失敗和執政黨的衰落,真正的人民政黨要保證“我們的黨就會從事實際工作,就會像了解軍事工作那樣了解這個工作”[16]。列寧還針對黨內新出現的派別活動苗頭指出,要注意派別活動引發黨的分裂和反革命情況,“派別活動事實上也必然會削弱齊心協力的工作,使混進執政黨內來的敵人不斷加緊活動來加深黨的分裂,并利用這種分裂來達到反革命的目的”,因此要堅定地予以清除[14]。
“清黨”要把整治官僚主義、打擊腐敗行為作為長期性工作。列寧早在建黨初期就注意到提高黨員思想素養對防止官僚主義滋生和黨的隊伍建設有重要意義。1903年,在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他就對提高黨員自身素質作出要求,強調要把提高實際業務能力和理論素養作為考量黨員的重要標準,“寧可十個實際工作者不白稱黨員也不讓一個空談家有權力和有機會作一個黨員”[32]。革命勝利后,為適應新經濟發展,增強黨的戰斗力,黨內展開了防止官僚主義滋生成長的“清黨”工作。在全面考察黨員具體情況的基礎上,列寧改變了過去那種認為官僚主義產生于舊職員的看法,認識到官僚主義還存在于共產黨員身上,具體表現為不忠誠、不堅定、以權謀私等。他還注意到黨內政治生活中出現的新問題,如黨內有些干部只知道開會、談話,不從事實際工作或者專注于貪圖享樂。對此,列寧提出要建立黨內監督機制,主張把工農檢察院和中央監察委員會結合起來,吸收真正的黨員任職。當然,黨內官僚主義根深蒂固,并隨著經濟發展而不斷滋生,不可能馬上得到解決。所以,“清黨”工作需要被當作一項長期性的工作來對待,“這不是幾個月的事情,也不是一年的事情,而是好幾年的事情”[16]。
“清黨”要注重培養和擴大黨的群眾基礎。“清黨”要把“破”和“立”相結合,把“革舊”和“迎新”相結合。在黨的建設中,列寧特別重視培養黨的新生力量。他把“清黨”與創造共產主義條件的生產勞動相聯系,強調在勞動中培養和選拔真正的黨員。“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就成為吸收具有共產主義覺悟的人民群眾進入黨組織的重要標準。一方面,“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作為一種實踐活動,能把支持蘇維埃政權的人民群眾團結起來,在勞動中創造社會主義建設的條件,實現自身解放的價值。同時,這一活動也可以把意志不堅定、不愿參與社會主義建設的人排除在黨外。另一方面,“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有利于鞏固工農聯盟。“星期六義務勞動”解決了俄國經濟困難的狀況,使農民認同無產階級政權,“鞏固農民對無產階級國家的尊敬和愛戴”[23]。列寧兩次“清黨”工作提高了黨員質量,純潔了黨員隊伍,提升了黨的戰斗力,鞏固了無產階級執政黨的地位。
三、列寧黨內斗爭思想的時代價值
列寧黨內斗爭思想的深厚理論底蘊和豐富實踐形式不僅對俄國革命和俄共(布)建設事業的開展起著重要指導作用,還對中國共產黨的建設起著借鑒作用。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的歷史發展階段,黨肩負著進行偉大斗爭、推進偉大事業和實現偉大夢想的重任,需要把自己建設成為一個堅強有力的執政黨。列寧黨內斗爭思想在加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嚴肅黨內政治生活以及創新斗爭方式等方面留下了豐富的智慧,對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起著重要借鑒作用。
(一)有利于牢固樹立“兩個維護”的政治自覺
列寧黨內斗爭思想有利于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加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和樹立“兩個維護”的政治自覺。維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是無產階級政黨建設的主要內容。自社會民主黨建立以來,列寧就表達了“戰斗的無產階級最親密無間的團結”和“統一的領導中心”對實現黨的真正統一的重要性。蘇聯共產黨從統一走向組織渙散、亡黨亡國的歷程就足以證明,確立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核心至關重要,特別是對中國這樣的大國大黨來說,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尤為重要。任何時候,維護黨的權威和集中領導的立場都不能改變。新的時代條件下,習近平用“堅定不移維護黨中央權威,堅持以‘兩個維護’引領全黨團結統一”,深刻總結十八大以來黨的政治建設重大成就,深刻闡明了樹立“兩個維護”的政治自覺的重要意義。
樹立“兩個維護”的政治自覺要堅定政治信仰,補足精神上的“鈣”。列寧從俄國革命和建設中總結道:“沿著馬克思的道路前進,我們將愈來愈接近客觀真理”[24]。他進一步指出,“在這個堅如磐石的理論基礎上產生的布爾什維主義”還創造了舉世無比的豐富經驗[25]。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是俄國取得革命勝利的理論向導,而十月革命結束后,黨內派別斗爭是黨員喪失馬克思主義信仰和革命信念的表現。有信仰才知敬畏,當今中國日益走進世界舞臺中央,我們越發展,遇到的阻力就越大,面臨的風險就越多,同時,黨員隊伍中也不同程度地出現了信仰缺失、精神空虛、信奉金錢至上的傾向。面對黨內黨外的嚴峻挑戰,習近平強調用理想信念武裝共產黨人的重要性,他把理想信念比作人精神上的營養物“鈣”,精神缺鈣就會得“軟骨病”。黨員干部有政治信仰才能正確把握政治方向,才能牢固樹立“兩個維護”的政治自覺。堅定政治信仰,要堅持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武裝頭腦,牢記初心和使命,筑牢共產黨人的政治靈魂。
樹立“兩個維護”的政治自覺要堅持斗爭精神。列寧在揭露社會民主黨黨內“取消派”的反動本質時指出,黨內斗爭是實現黨內團結的有效途徑,“布爾什維克派也確實在堅持不懈地進行這個斗爭,從而鍛煉和團結了一切真正忠于黨的、真正忠于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民主主義分子”[13]。回顧歷史,中華民族的崛起、中國共產黨發展的歷史都是一部部斗爭史。一百年前,在中華民族遭遇最危險的時刻,是共產黨帶領人民經過頑強斗爭保衛了民族獨立。當前,中華民族正處于偉大復興的關鍵時刻,中國共產黨更要帶領廣大人民群眾抵御重大風險,克服艱難險阻,進行具有許多新特點的偉大斗爭。2019年9月,習近平在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青年干部培訓班開班式上就強調,廣大干部要發揚斗爭精神,增強斗爭本領。斗爭精神是樹立“兩個維護”的政治自覺的銳利武器,黨員干部要在辨別政治是非、保持政治定力、駕馭政治局面、防范政治風險等方面進行自我革命,真正做到思想上清醒、政治上明白、工作上實在、生活上干凈。
(二)有利于嚴肅黨內政治生活
嚴肅黨內政治生活有助于黨內矛盾的解決。俄國革命時期,黨內在思想、組織、作風建設等方面還處于不完善階段,黨內斗爭必然會出現。列寧時期,通過嚴肅黨內政治生活,反對黨內“左”右傾和反對民主擴大化等的斗爭都取得了成功,并制定了相應的政策和策略,實現了黨的思想統一,為革命勝利奠定了基礎。在社會主義建設的關鍵時期,嚴肅黨內政治生活,也要堅持民主集中制和嚴明黨的政治紀律、政治規矩,堅持全面從嚴治黨。習近平強調:“黨要管黨,首先要從黨內政治生活管起;從嚴治黨,首先要從黨內政治生活嚴起。我們要加強和規范黨內政治生活,嚴肅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增強黨內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時代性、原則性、戰斗性,全面凈化黨內政治生態。”[26]
堅持民主集中制組織原則,為嚴肅黨內政治生活提供制度保障。“嚴肅黨內生活,最根本的是認真執行黨的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開展黨內政治生活的重要制度,主要解決黨內權力集中或者極端民主化的問題[27]。列寧在與盧森堡和托洛茨基就建立什么樣的革命政黨的爭論中形成了以“民主集中制”來建立無產階級政黨的原則。這一創新性原則強調,政黨組織要以集中組織為前提和武器對抗敵對分子和保存革命成果,并在組織一致的情況下保證民主權利,就如列寧所說:“要穩妥可靠地保持革命的一切實際成果,只有看無產階級的組織程度如何。”[8]也正是堅持了這一原則,黨內斗爭才能得到有效解決。習近平在談到民主集中制時也表示,要發揮其“既可以最大限度激發全黨創造活力,又可以統一全黨思想和行動,有效防止和克服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的分散主義,是科學合理而又有效率的制度”的制度優勢[28]。但面對黨內實際生活時,理論與實踐仍存在差距,一些黨員干部仍不能處理或把握好民主與集中的關系,或重視民主輕集中,或輕民主重集中,這兩種傾向都會給黨帶來危害。因此,堅持黨內民主集中制,要做到把“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相結合。具體來說,一方面,集中的民主要充分發揚黨內民主,要以斯大林時期不允許黨內有異議的情況為教訓,最大限度激發黨的活力。另一方面,民主的集中要避免極端民主化和民粹主義,把各種意見集中起來,依據符合廣大人民群眾的意見做出正確決策,從而保證黨的行動一致。
樹立嚴格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為嚴肅黨內政治生活提供重要保證。十月革命后,黨內爭論擴大化導致派別組織林立,使列寧認識到要把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建設放在重要位置。對此,他明確提出要用嚴格的紀律來解決黨內派別斗爭的問題,“為了在黨內和整個蘇維埃工作中執行嚴格的紀律,并取締一切派別活動以求得最大程度的統一……可以采取黨內一切處分辦法,直到開除出黨”[14]。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也很重視黨內分裂帶來黨內政治生活扭曲異化的問題,他說:“黨內絕不允許搞團團伙伙、結黨營私、拉幫結派,搞了就是違反政治紀律。”[29]所謂“朋黨興,政事亂”,團團伙伙、拉幫結派與“立黨為公”是相悖的,它嚴重破壞黨的形象,導致組織混亂、削弱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嚴重扭曲黨內政治生活。為此,黨員干部要在方向、立場、言論和行為幾個方面保持清醒的頭腦;要嚴肅對待黨內生活,在自由的前提下,保持言論有原則和底線;要嚴格執行“四個服從”;要用法律手段規范和約束權力,提高黨內生活制度化和科學化水平。
(三)有利于創新凈化黨內政治生態
黨內政治生活是政治生態的基礎,政治生態的狀況取決于黨內政治生活,一旦政治生態形成便會對政治生活產生影響,正如習近平所說:“政治生態同自然生態一樣,稍不注意就容易受到污染,一旦出現問題再想恢復就要付出很大代價。”[30]列寧時期,嚴肅黨內政治生活,消除黨內錯誤思想,從而凝聚力量進行革命和建設的經驗在于,根據具體歷史情況創新處理黨內斗爭的形式。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黨內斗爭會以新的形式出現,就需要以新的方式來凈化黨內政治生態。
開展反官僚主義斗爭是清除政治生態“污染源”的有效方法。官僚主義是破壞政治生態的突出表現形式,列寧在清除黨內官僚主義作風的過程中指出,只有堅持清洗、治療,十次百次地治療和清洗才可能消除官僚主義作風。所以,營造良好的政治生態要把反官僚主義作風放在重要位置。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高度重視反官僚主義問題,指出官僚主義反黨、反人民,“是我們黨的大敵、人民的大敵”[31]。執政黨的前途命運取決于人心向背,黨內官僚主義脫離群眾、高高在上,割裂自己與群眾之間的聯系,使黨失去群眾基礎,還損害人民利益。在《習近平關于力戒形式主義官僚主義重要論述選編》中,習近平對官僚主義的新形式和產生的危害進行了全面闡述,并提出了實事求是的有效方法。他提出,領導干部要發揮“頭雁效應”,以身作則;思想上要堅定理想信念,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理論成果武裝自己,強化黨員宗旨意識和黨性意識,培育良好政治生態的土壤;另外,他還提出要加強黨內黨外監督,要全方位地構建監督網絡,把權力關進制度“籠子”,從制度上保證黨內政治生態的凈化。
堅持群眾路線是重塑黨內政治生態的重要途徑。政治生態受到污染,其主要原因在于黨員在思想上背離群眾觀點,在行動中脫離群眾路線。黨員只有堅持群眾路線,才不會發生角色錯位,只有堅持群眾路線,才能保證馬克思主義政黨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列寧曾說過:“把千百萬勞動群眾組織起來,這是革命最有利的條件,這是革命取得勝利的最深的泉源。”[32]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興衰成敗的力量源泉在人民群眾。習近平無數次強調要重視人民群眾的力量,要把群眾路線貫穿到治國理政的全過程,“把黨的群眾路線貫徹到治國理政全部活動之中,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斗目標,依靠人民創造歷史偉業”[33]。堅持群眾路線,就要求黨員在行動中做到關心群眾、尊重群眾、向群眾學習,逐漸克服脫離群眾的危險;堅持群眾路線,還要求黨員把人民群眾作為閱卷人,把符合人民群眾的利益和需求作為工作的尺度,從而實現黨內政治生態的重塑。
結語
列寧黨內斗爭思想為新時代條件下進行黨內思想斗爭和自我革命提供實踐指導。承認黨內斗爭不是搞階級斗爭,而是自覺進行黨的自我革命。毛澤東曾多次對黨內思想斗爭進行闡述,強調黨內思想斗爭之于黨自身的重要意義:“我們主張積極的思想斗爭,因為它是達到黨內和革命團體內的團結使之利于戰斗的武器。每個共產黨員和革命分子,應該拿起這個武器。”[34]當前,在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向縱深發展的新階段,面對黨內思想、組織、作風等方面存在的問題,面對實踐中存在的新矛盾和新挑戰,黨唯有不斷進行自我革命,才能提升執政能力和水平,才能確保長期執政地位,因為“保持革命性依然是中國共產黨在長期執政的歷史方位上必須堅守的政治底線”[35]。生于憂患,死于安樂。回顧一百年來的奮斗歷程,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砥礪奮進,創造一個個奇跡,正是在于全黨上下從不放松黨內斗爭,堅持不懈推進自我革命,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與全體人民同心同德、同甘共苦、同舟共濟,才得到廣大人民持續的支持與擁護,凝聚起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磅礴力量。
注釋:
① 學界關于黨內斗爭思想的研究成果并不豐富,代表性成果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在黨內斗爭的研究中,學者主要闡述黨內斗爭的具體斗爭手段。劉新華(2017年)認為新時期黨內還存在矛盾和斗爭,提出“團結-批評-團結”是解決黨內斗爭的基本方針;仇麗萍(2017年)從全面治黨的角度談黨內斗爭問題,強調開展黨內斗爭要從思想、自身本領、黨性監督機制以及運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等方面把握;曹宗枝(2016年)強調批評和自我批評是黨內生活優質化的武器;王玉堂(2018年)認為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是加強和規范黨內政治生活的重要手段。第二,對歷史人物關于黨內斗爭的觀點進行史學研究。馮夏根、胡旭華(2010年)對劉少奇關于黨內斗爭問題進行研究,闡述了黨內斗爭應遵循的原則和注意的方法;吳昊(2010年)對恩格斯的黨內斗爭思想的研究,闡述了在堅持革命原則、用好批評和討論的方法的基礎上開展斗爭,以保證黨內團結的實踐;江泰然(2016年)闡述了朱德堅持民主集中制原則基礎上的黨內斗爭思想,“搞好黨的建設,必須堅持民主集中制原則,正確開展黨內斗爭”。第三,少數學者將黨內斗爭歸結為黨內批評的一種。王乃俊(1990年)認為黨內的批評是多種多樣的,決不能單單理解為你死我活的斗爭;柯士炎(1980年)對列寧的黨內斗爭進行了理論層面的分析,主張“堅持用一分為二的觀點,全面地歷史地評價黨員和干部,反對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朱永剛(2017年)對黨內斗爭的具體方法——批評和自我批評——進行了學理分析,認為“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為正確看待批評和自我批評提供了理論工具”,“辯證的否定觀為準確理解批評和自我批評提供了又一學理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