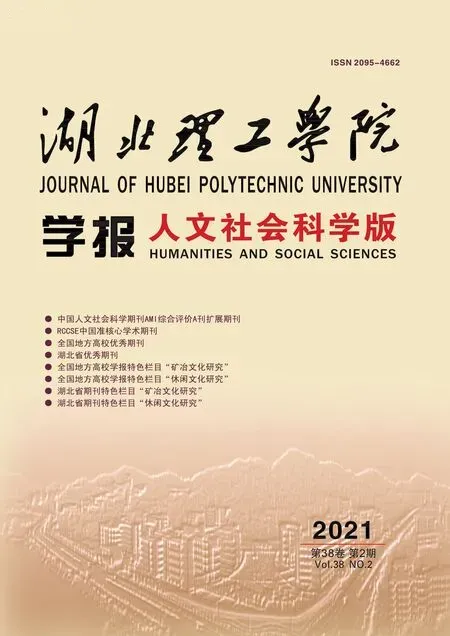“傳奇”與“文化”的有機融合
——從《穗兒紅》《潘七爺》《垢壺》管窺胡金洲小小說藝術之魅
張治國
(湖北文理學院 文學與傳媒學院,湖北 襄陽 441053)
胡金洲,男,筆名金鼎,1945年出生,湖北武漢人,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中國微型小說學會理事,2013年入選《中國小說家大辭典》。迄今已在全國知名報刊發(fā)表小小說500余篇,出版《絕活》《唱棋》《打蝴蝶結的紅皮鞋》等小說集多部。其作品多篇入選《小小說選刊》《中國微型小說選刊》《中國當代微型小說精萃》《名家精品小小說選》等選刊選集,多次入選中國年度小小說排行榜;多篇作品入選全國或地方中學語文教材;榮獲全國小小說大獎賽優(yōu)秀獎、中國當代小說獎、湖北省“五個一工程”獎等多項大獎;其作品在海外也有一定影響,多篇小小說隨選集入藏美國、加拿大國家圖書館。經(jīng)過近四十年的深耕細作,胡金洲先生已然成為全國小小說領域的領軍者之一。
2020年2月14日,其原創(chuàng)新作《穗兒紅》及昔日佳構《潘七爺》《垢壺》等三篇作品,以“集束”方式呈現(xiàn)于當下大陸最具人氣和文壇影響力的原創(chuàng)小小說網(wǎng)絡傳播平臺《活字紀》“重磅推介”欄目,讓受眾對這位年逾七旬老作家的獨到審美眼光和深厚藝術功力有了更為真切的感知。這三篇作品,題材相異,敘述的聚焦點也各不相同:《潘七爺》重在寫人,《穗兒紅》重在敘事,《垢壺》重在狀物,但藝術風格比較接近,宜作整體觀。在筆者看來,這組小說集中體現(xiàn)了胡金洲小小說的創(chuàng)作個性與藝術魅力:富有傳奇性的敘述建構,對鮮活的民族文化形態(tài)的生動呈現(xiàn),以及“傳奇”與“文化”的有機融合,帶給受眾極具張力的審美體驗,圓滿實現(xiàn)了小小說咫尺之間涵納萬里之象、以小博大的美學意圖,開啟了文化審美的新路徑。
一、富有傳奇性的敘述構建
(一)精彩的傳奇故事
三篇小說都講述了頗有傳奇色彩的故事,這是作者小小說藝術性的一個顯著標志,也是其作品引人入勝的魅力所在。
《穗兒紅》講述了抗戰(zhàn)時期鄂西北小鎮(zhèn)陶藝匠人智斗侵華日酋的傳奇故事:屈旺生于制陶世家,練就了一手燒制“穗兒紅”泥壺的絕技,遠近聞名。最讓他引以為傲的是家中珍藏著一套祖?zhèn)鲗氊悾喝珖氁环莸?“像俄羅斯套娃一樣”制作精美、功能奇絕的泥茶套壺“九套壺”①。生逢亂世的屈旺憑著處事的機敏與警覺,很快就識破了假扮哈爾濱商人、侵華日軍駐南漳谷城先遣隊大佐石川的身份,虛與委蛇,將計就計,利用本地山重水復的地理特點,巧設迷魂陣,挫敗了日軍進犯鄂西北保康、恩施,打通進川通道的陰謀。接著,又施出“貍貓換太子”之計,讓九套壺免落日寇之手,為保護中華民族的陶藝文化瑰寶立下了不朽之勛。小說還寫了游擊隊抗擊日軍的事跡,進一步增強了故事的可讀性和傳奇色彩。
較之《穗兒紅》,《潘七爺》情節(jié)更為曲折跌宕,傳奇色彩也更加濃烈。小說講述了清末巫山船夫潘大爺與王爺之女婉云格格的愛情傳奇:潘大爺是川江有名的駕船高手,被譽為“捉船之魁”。某日,他在險灘龍頭灘撿回了隨父離京逃難進川、遭遇水難失怙的十六七歲的小兄弟,認作兄弟,因在潘家六兄弟中排行老七,人稱“潘七爺”。三年來,潘大爺對潘七爺護愛有加,潘七爺也隨潘大爺練就了一身戲水捉船的硬功夫。辛亥革命爆發(fā)后,潘大爺?shù)拇牫袚诉\輸軍用輜重、裝備響應武昌起義川軍的重任。潘七爺不顧潘大爺?shù)倪沉R,執(zhí)意上船、拉纖,隨船隊一同趕路。為避免船隊重蹈三年前其父船毀人亡的覆轍,當天夜里,潘七爺獨自一人到龍頭灘探查水情。返回后警示哥哥們:水情有變,屆時一定改左道行船。但潘大爺卻固執(zhí)己見,不聽勸告,為悲劇埋下了隱患。翌日一大早,船隊重新出發(fā),潘七爺改變潘大爺?shù)陌才牛瑢⒆约厚{駛的尾船變?yōu)榈诙l船,為的是“萬一有變”,第二條船能代替首船,擔負旗船的指揮之責。經(jīng)過岸上纖夫和船上船工們的戮力配合,船隊艱難地逆流而上,終于,潘大爺駕駛的第一條船順利闖過龍頭灘,駛?cè)胨鎸掗煹挠医馈U斉舜鬆敻吲e手旗向后面的五條船發(fā)出繼續(xù)前行“旗語”之時,突然,江上沖出一團排天巨浪,“托起船頭猛地將船回拋到龍頭灘上”②,一瞬間,潘大爺?shù)拇氵B人帶物被巨浪吞噬。目睹慘劇的潘七爺悲痛不已,但他冷靜地制止了六爺跳江救兄、自尋死路的莽撞行為,迅速向身后四船發(fā)出旗語,引導船隊駛?cè)胱蠼溃詈笃桨驳竭_目的地。當天,得到軍火資助的四川宣告脫離清政府。卸罷輜重,潘家五弟兄就要返程尋找潘大爺,卻不見了七爺人影。這時,六爺接到了岸上店家送來的七爺?shù)囊环鈺牛诺弥喟槿甑男⌒值軈s是女兒身。原來,潘七爺是滿清王爺?shù)呐畠和裨聘窀瘢蚋赣H同情變法被朝廷追殺、流落至此。信中婉云真摯地表達了對六兄弟撫養(yǎng)與厚愛自己的感謝之意,以及對潘大爺生死相依的深情。后來,潘氏五兄弟在龍頭灘頭找到了投江殉情的婉云格格的尸體,并將七弟與失蹤大哥的衣冠合葬于龍頭灘左岸之上,“碑文以兄長與七弟夫妻合塋而書之”。
整篇小說情節(jié)生動,人物性格鮮明,且始終蘊含著巨大的情感力量:它既是一首以潘大爺為代表的粗獷無畏、充滿血性的勞動者與兇險大自然英勇搏斗的壯美生命贊歌,也是一曲純潔、樸素、真摯、熾烈、感人肺腑的愛情頌歌。
如果說《穗兒紅》是由“九套壺”勾連的抗戰(zhàn)傳奇,《潘七爺》是人與自然搏擊的生命傳奇、川江船夫與王爺格格的愛情傳奇,那么《垢壺》就是一段關于紫砂壺的傳奇。故事發(fā)生在當下,以第一人稱講述:父親有一把祖?zhèn)髯仙皦兀白宰嫔习淹娲藟刂螅壹抑两窈脦状藦膩砦辞逑催^茶垢”③,以至于傳到父親手上時,該壺茶垢成團,成為行家眼中的“垢壺”。為把它變成價值連城的“極垢壺”,父親堅持每天養(yǎng)垢,從不懈怠,樂此不疲。后來,一位大名鼎鼎的陶藝大師慕名前來賞壺,在親口品嘗父親用垢壺沏泡的茶湯之后,贊嘆不已,認定“此壺在中國陶藝史上值得大書特書一筆”,令父親十分得意。然而,出人意料的是,當父親送走大師返回客廳后卻驚訝地看到,原本放在桌上自己視為心肝寶貝的垢壺,轉(zhuǎn)眼已變成 “一把毫無垢跡、鮮亮如新的泥壺”——原來,是“我”老婆乘父親送客的空檔,擦拭了茶壺表面的浮塵,清理了經(jīng)年的茶垢,改變了茶壺的命運,讓它褪去了漫漫歲月和癡迷于養(yǎng)垢的主人賦予的沉重“華表”,回歸本真,回歸自我。突如其來的變故,讓父親痛心疾首、老淚縱橫:全家?guī)状司酿B(yǎng)垢的珍貴成果不僅毀于一旦,且原本指望將它賣個大價錢而一夜暴富的美夢也成了泡影。
(二)傳奇性的敘述建構
傳奇性故事所產(chǎn)生的好看、耐讀的審美效果,得益于作家對敘事藝術、修辭策略的嫻熟運用與恰當調(diào)度。富有藝術張力的小小說所采用的敘事藝術和修辭策略,落實到具體的藝術手段,就是“省略”和“暗示”:省略是敘事的空缺藝術,而暗示則隱藏在字里行間,將無法省略的重要信息用隱蔽的方式點到為止,當省略和暗示有機地協(xié)調(diào)之后,小說的藝術韻味自然就會流露出來[1]。
在《穗兒紅》中,存在著兩條敘事線索:屈旺智斗日酋、保護“穗兒紅”九套壺是主線,寫得詳細、完整;游擊隊抗擊日軍是副線,則采用了只寫結果、“省略”過程的藝術處理。如游擊隊在猴頭山伏擊日軍,重創(chuàng)敵人,只用了兩句話:“忽然一日,屈旺隱隱約約聽見槍聲從深山里傳來。隔了半天時辰,一群日本兵死的死傷的傷出現(xiàn)在小鎮(zhèn)上。”而游擊隊襲擊日軍則僅用一句敘事性文字來表現(xiàn):“日本鬼子的兵營響起一陣接一陣的爆炸聲。”省略處理,造成了事件過程的空缺,為讀者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間,同時也有利于突出主線。兩條線索又借助主人公屈旺的敘事視角相互交織,形成一體,并據(jù)此揭示了軍民團結、同仇御敵的宏大主題,也顯示出作者以談笑從容態(tài)度描摹風云變幻的浪漫主義風格。
與《穗兒紅》的藝術技法有所不同,《潘七爺》的著力點在于把控敘事節(jié)奏,營造情節(jié)的張弛效果;采用暗示手法,為事件結果或故事結局埋下伏筆。作品開頭用平穩(wěn)的靜態(tài)敘事交代故事背景、地點,引出潘大爺、潘七爺兩個主要人物,分別介紹其身份、功夫與來歷,為情節(jié)展開蓄勢;在潘家三年,七爺強壯起來,并跟隨大哥練就了一身駕船的過硬本領,但六爺不服,欲與老七比試——這成為情節(jié)啟動的觸發(fā)點。比試項目為兩人各駕一船夜走瞿塘峽。作者用“月黑風高,水流馬奔”渲染環(huán)境的惡劣與江流的兇險,用“搶過瞿塘峽”的“搶”字突出了行船的驚險,從而構建了第一個情節(jié)波瀾。接著,作者放緩敘事節(jié)奏,回敘七爺三年的生活,表現(xiàn)潘大爺對七爺?shù)恼疹櫯c厚愛,既是對文末七爺書信內(nèi)容的巧妙暗示,也使之成為高潮前的緩沖和過渡。潘大爺率領運送援川軍用輜重的船隊逆水經(jīng)過龍頭灘,是情節(jié)發(fā)展的高潮,對其過程的描寫也成為小說最精彩的片段。首先,作者用“早三坨晚三坨,龍頭揚起冇得活”的當?shù)孛裰V來突出龍頭灘的兇險;接著,用潘七爺“明天有你們好哭的”一句讖語預示結果的悲劇性。待船隊接近龍頭灘時,作品寫道:
七弟兄上岸拉纖。潘大爺大聲吆喝:龍王爺!保佑啰!潘家兄弟闖灘啰!眾人呵嗨嗨!呵嗨嗨!扯開喉嚨,吼起川江號子:舉義旗,應武昌,剪長辮,得解放……嗨呦,嗨呦!高亢之音在江面上回蕩播揚。一群銀色江雞前后相隨,上下翻飛,翙翙其羽,久久不去。
過了龍頭灘,潘大爺重新上船復行右江道,右江道水面寬闊。潘大爺高舉手旗,發(fā)出旗語:繼續(xù)前行。突然間,江上一個回流窩出,接著水柱趵突,似巨擘出水,托起船頭猛地將船回拋到龍頭灘上……隨之,連人帶物吞噬腹中,如龍激流翻滾著席卷而去……
第一段為場景描寫,展現(xiàn)的場面十分壯觀,潘大爺?shù)倪汉嚷暋⒈娙顺渡ず鹌鸬拇ń栕勇暋⑻炜战u上下翻飛的“翙翙”振翅聲連成一片,匯成了一首氣勢磅礴、壯美激越的生命交響曲;第二段為環(huán)境描寫,將大自然狂野、乖戾的毀滅性力量渲染得波瀾壯闊、驚心動魄。
《潘七爺》的暗示手法,主要見于對潘七爺?shù)目坍嬌希灿兴奶帯5谝惶幨切は衩鑼懀骸捌郀攤€小,白凈,細眉大眼,像個女娃”;第二處是“自被收留的那日起,一直獨處一室,從不與六位哥哥同居”;第三處是“潘七爺來潘家三年卻從沒赤著腳板趟過一次刀一般的石灘,肩膀依然白皮細肉一堆”;第四處是潘七爺查探過龍頭灘水情后向正熟睡的六兄弟報警,六個人“個個赤身而起”,潘七爺則“側(cè)過臉”與他們說話。小說結尾通過一封書信解開了潘七爺原是女兒身的性別之謎,產(chǎn)生了出人意外的藝術效果。而這些暗示性文字則為“意外”提供了合情合理的邏輯依據(jù),顯示了作家構思的新奇巧妙。總之,省略與暗示手法的運用,賦予了《潘七爺》故事情節(jié)的傳奇色彩,給予讀者強烈的感情沖擊和獨特的審美體驗,增強了文本的藝術張力。
《垢壺》在敘事藝術上,對暗示與省略技巧的運用也十分熟稔得當。暗示部分體現(xiàn)在對“我”老婆職業(yè)的介紹和與家人關系的展現(xiàn)。她“是某大醫(yī)院的護士”,不難想象,醫(yī)務工作者的職業(yè)敏感決定了她比一般人更注重健康的生活方式,更看重家人的個人衛(wèi)生和身體健康。事實正是這樣,在她的影響下,“我”和父親戒了煙、酒。不僅如此,“她見父親手指甲內(nèi)窩有甲垢,拿起小剪刀,抓起他的一雙手剪了起來……感動得父親當時差點落下淚來”。這處細節(jié)描寫,從塑造人物的角度看,為的是突出她孝順老人的家庭美德;而從小說修辭角度看,則顯然是為了強化其職業(yè)身份、為其后來的“毀貨”行為提供令人信服的邏輯支持,即出于敘事技術與藝術效果的考慮。而省略的運用則體現(xiàn)在,當父親發(fā)現(xiàn)垢壺變成普通泥壺,氣急敗壞地質(zhì)問“這是誰干的”之時,“我”老婆“爸,是我。不干凈嗎”的一句“嬌嗔”回答。這里,作者明確交代了“我”老婆是“肇事”者,卻懸置了人物的施事心理和行為過程。省略,造成了敘事空白,給讀者留下了充足的想象空間。而讀者完全可以憑借個人的生活常識,依據(jù)人物性格發(fā)展邏輯,結合小說暗示性敘述,做出相應的推測,從而實現(xiàn)對人物心理動機和行為過程的合理還原:如前所述,“我”老婆是醫(yī)務工作者,講衛(wèi)生、重健康是她的“職業(yè)病”,也是她的生活方式。因此,她無法接受父親指甲的污垢,所以才主動地為他剪去垢甲。她也無法認同父親“垢越厚實,茶垢越發(fā)香甜”的理論——在她的職業(yè)認知中,積滿茶垢的茶壺易生細菌,用垢壺飲茶有害健康,用干凈茶壺飲茶才延年益壽。她才不管什么“極垢壺”價值連城的壺道說辭,她才不顧“家有‘極垢’,黃金為垢”的所謂“祖上遺訓”呢,干凈、健康才是硬道理!因此,她一定會尋找機會去清理垢壺的茶垢。更何況,父親的“甲垢是養(yǎng)壺垢留下來的”,她必須將垢壺的茶垢清除而后快,以消除污染源。然而,要完成此事談何容易!父親是壺癡,“愛此壺如親生兒郎”。平時對垢壺更是嚴管死守,“從來不準別人碰摸一下”。每次養(yǎng)垢之后,總是“嚴嚴鎖進柜內(nèi)。鑰匙只有他一個人掖著” 。這次,大師來家賞壺,“我”老婆終于有了千載難逢的下手機會。于是,乘著父親出門送客的須臾,她迅速沖進客廳,三下五除二地清除了垢壺里外的污垢,把它變成了“一把毫無垢跡、鮮亮如新的泥壺”,然后,從容退出,站在父親面前,“一副春風拂面的樣子”。由此可見,作者的“省略”手法有著重要的敘事意義,增強了小說的藝術張力。同時,人物的“毀貨”行為,不僅改變了這把紫砂壺的命運,具有某種傳奇意味,也造成了情節(jié)的陡轉(zhuǎn),導致父親由“興沖沖”到“氣急敗壞”的情緒失控,具有喜劇色彩。這種審美效果,充分驗證了“歐·亨利式結尾”敘事策略的藝術表現(xiàn)力。
二、 鮮活民族文化的生動呈現(xiàn)
胡金洲先生的這三篇小小說具有豐富的民族文化意蘊。作者對絢麗多彩的民族文化中那些極具地域性、歷史感的鮮活民間文化形態(tài)進行了生動描寫和藝術觀照,既展示了文化之韻、文化之趣、文化之美,也對文化之莠、文化之弊進行了理性反思,對傳承、弘揚和優(yōu)化民族文化具有重要的文學價值和現(xiàn)實意義。
(一)雄壯瑰麗的川江船夫文化
《潘七爺》借助回腸蕩氣的生命傳奇、愛情傳奇,生動呈現(xiàn)了瑰麗雄偉的川江船夫文化。
船夫文化與特定河流的水道狀貌與航運歷史、運載工具與操控技藝、物資流通與文化交流相關,航道、船筏、船夫與船歌是其構成要素[2]。受小小說篇幅所限,作者并未對川江船夫文化的構成要素予以全面展示,而是精選了與時代背景、自然環(huán)境、人物生活密切相關,有利于演繹情節(jié)、塑造性格、表達情感、揭示主題的某些因素,即把航道、船夫、船歌三要素作為觀照對象,以實現(xiàn)以少勝多、以一斑窺全豹的美學目標。
川江航運歷史悠久,但水運條件十分惡劣。自古以來,千里川江,航道彎曲狹窄,明礁暗石林立,急流險灘無數(shù)。小說中引用的當?shù)孛裰V“早三坨晚三坨,龍頭揚起冇得活”,表現(xiàn)的就是龍頭灘“三坨石”早晚水情變化無常、“極為藏險”的情況。潘七爺之父船撞龍頭灘的船毀人亡事件,六爺與七爺比試駕船功夫“搶過瞿塘峽”的情節(jié),都是對川江航道兇險惡劣的具體化表現(xiàn)。而文中對川江兇險特征的最具現(xiàn)場感和震撼力的呈現(xiàn),則是對潘大爺被巨浪吞噬的描寫:“突然間,江上一個回流窩出,接著水柱趵突,似巨擘出水,托起船頭猛地將船回拋到龍頭灘上……隨之,連人帶物吞噬腹中,如龍激流翻滾著席卷而去……”
川江船夫靠行船拉貨為生,在民間被喻為“血盆里抓飯吃”。為避禍自保,船夫們需要在勞動實踐中傳承先輩的生存智慧,練就過硬的駕船本領。對此,小說篇首通過介紹“捉船之魁”潘大爺,對駕船高手的駕船技術要領做了形象解說:“捉船之關鍵在于把舵,憑眼手腿三種功夫。眼看,看江上急湍緩湍還是左湍右湍,把舵的手便視此而著勁,一雙腿始終如船樁一般穩(wěn)立不動。”
由于航道水情復雜,川江行船絕非一兩個功夫高手即可駕馭,而是需要眾多船夫的通力配合、分工協(xié)作,尤其在逆水行船或航道狹窄的激流險灘之處。通常的情況是,在水中船上,站立船頭者為諳熟水情的駕長(船老大),負責行船的組織指揮和領唱號子;處于船尾者為經(jīng)驗豐富的艄公(舵手),負責掌控船只行駛方向;船兩邊為橈槳船工,負責劃槳。在岸上,則為纖夫,負責合力拽船。為聚神凝氣,相互配合動作,船上的船工和岸上的纖夫常會在駕長的組織引領下吼唱高亢粗獷的川江號子,場面十分壯觀。對此,作品有細膩生動的描寫。
值得一提的是,文中所寫的川江號子,成為表現(xiàn)川江文化的一大亮點。川江號子是川江船工們?yōu)榻y(tǒng)一動作和節(jié)奏,由號工領唱,眾船工幫腔、合唱的一種一領眾和式的民間歌唱形式。是船工們與險灘惡水搏斗時用熱血和汗水凝鑄而成的生命之歌,被譽為川江文化的“活化石”。川江號子歌詞內(nèi)容極為豐富,多以沿江地名、物產(chǎn)、歷史、人文景觀、船夫生活為題材,盡顯川渝風情[3]。文中所寫船夫們在船過龍頭灘時所唱川江號子“舉義旗,應武昌,剪長辮,得解放”,其簡短的組織形式和口語化的語言風格,與傳統(tǒng)的川江號子相一致,但內(nèi)容卻是表現(xiàn)辛亥革命的政治事件,以及民眾覺悟、盼望翻身解放的政治訴求,充分表現(xiàn)了川江號子的時代性,是對既有文學作品表現(xiàn)川江文化的一種創(chuàng)新。
川江船夫整日與船筏為伍、與江水為伴,生活習性與陸地百姓大相徑庭。為減輕累贅和保護衣物,船夫撐船劃槳、攀爬峭壁和涉水泅渡盡量少著衣服[4]。尤其是下船纖夫,“因為所行纖道坎坷崎嶇,或在山腰僅容人彎腰通行的小道、或在亂石灘衣服不被石頭弄破,加之纖道多在人跡罕至的區(qū)域,纖夫們的常見打扮就是赤身,在腰間搭一塊白帕子,無論春夏秋冬”[3]。對此,作品巧妙地借潘大爺?shù)囊痪湓挕按蠹倚韪耐粘嗌砹晳T,穿鞋抿褲披坎肩”,反映了船夫們常年赤身的生活習性及其異常艱苦的生活狀況。
總之,作品對川江船夫文化的描寫,不僅展現(xiàn)了具有鮮明地域性、行業(yè)性特征文化形態(tài)的藝術魅力,拓展了文本內(nèi)容,也為整篇故事和人物形象涂抹了一道神奇瑰麗的文化色彩。
(二)詩意雋永的陶藝文化
同樣是表現(xiàn)民族文化,但與《潘七爺》觀照的具有地域行業(yè)性、江湖色彩較濃的川江船夫文化不同,《穗兒紅》《垢壺》呈現(xiàn)的是更具工藝性、文人氣的非遺文化中的一大品類陶文化,分別表現(xiàn)陶文化中的兩個分支:泥壺文化,紫砂壺文化。
陶文化是我國傳統(tǒng)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歷史十分悠久,其文化構成通常有原材料、胎體顏色、器型、做工、裝飾圖案等要素。陶器制品是中國古代勞動人民智慧的結晶。而陶器中的精品即陶制工藝品,不僅具有實用價值,還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和收藏價值。文學作品將陶制工藝品作為觀照對象的美學意義,除了其敘事功能,還在于其文化價值。1984年,鄧友梅在《收獲》發(fā)表中篇小說《煙壺》,一時間在文壇引起巨大轟動。究其原因,在小說中,“煙壺”固然是演繹主人公人生遭際和悲喜命運不可或缺的道具,更重要的它是表征“古月軒”高超民族傳統(tǒng)工藝的文化符號。因而,《煙壺》在展示烏世保和聶小軒的生活道路時,從鼻煙壺到煙壺藝術再到古月軒的燒制過程的介紹,“都內(nèi)蘊著豐富的文物工藝知識和民俗掌故”。因而,該作品的成就,“不僅限于展現(xiàn)破落貴族子弟的生活道路,而且還在于這些生活經(jīng)歷所引帶出來的市井風俗和在這市井風俗中而蘊含的歷史文化情致和美學意蘊”[5]。由此可見,煙壺雖是小容器、小物件,卻蘊藏著歷史文化的大乾坤。正如鄧友梅所言:“煙壺雖小,卻滲透著一個民族的文化傳統(tǒng)、心理特征、審美習尚、技藝水平和時代風貌。”[6]
胡金洲小小說《穗兒紅》中的“穗兒紅”,是當?shù)厝藢Ρ镜厮a(chǎn)的一種具有獨特顏色泥茶壺的俗稱,也是對所有泥壺的統(tǒng)稱、代稱。以“穗兒紅”作小說篇名,體現(xiàn)了作者既以泥茶壺為情節(jié)紐帶講述傳奇故事,又將其作為文化觀照載體的巧妙構思。該作對泥壺文化的描寫,側(cè)重于以下方面。一是泥料:質(zhì)地“膩而不滑,黏而不潤”;二是顏色獨特:“壺腹上都有一嘟嘟兒被紫黑兩色圍繞的紅點兒,比大米穗兒小,比小米穗兒大,恰似開鐮季節(jié)風中搖擺的高粱穗兒”;三是款式:“壺中套壺,像俄羅斯套娃一樣,可各自分開,亦可集中在一起。多的據(jù)說套了九把壺。壺中最小的一把能左右旋轉(zhuǎn)。小壺盛上水,壺嘴插入外壺,茶水從最外層大壺嘴里流出,滴水不漏”,把陶壺的精巧結構和實用功能表現(xiàn)得十分神奇;四是藝術價值:“上檔次的茶壺尿壺每把都刻有圖案與文字,或山水草蟲,或經(jīng)文詩詞。屈旺祖父那把尿壺就有兩句詩:文秀玉璧夜夜?jié)M,壺落珠璣時時香。他給自己也燒了一把,上面刻著:夜闌春深通今古,半月如水落玉壺”。精細的描寫,詩詞的運用,把本來用于盛裝人的腌臜排泄物的尿壺的文化韻味及其所承載的文人的詩意情懷表現(xiàn)得極為傳神。而九套壺壺腹上鐫刻的跋文與詩句,則進一步表現(xiàn)了中國人的家國情懷和高雅的審美追求。
紫砂壺的文化構成要素與上述陶文化基本相同。《垢壺》對紫砂壺文化的審美觀照,盡管也有對其基本文化元素項的展示,如小說開頭的一段精細描寫:
父親有一把紫砂壺。祖上傳下來的。兩個并起來的拳頭大小,井籃狀。壺上有印章三款,壺蓋、壺底、壺把各一,喻意天地人和。壺系上等泥料燒制,硬如鐵滑如緞。壺口籠在燈下,通體透亮,一團赭紅。
但其表現(xiàn)的重點卻是養(yǎng)壺文化,即茶垢文化,或曰垢壺文化,以及由紫砂壺文化衍生而來的茶道文化,避免了與《穗兒紅》的雷同,別開生面。
小說中垢壺文化的堅定維護者和傳承者是“我”父親。他頑固堅守著“家有‘極垢’,黃金為垢”的祖上遺訓,信奉“垢越厚實,茶垢越發(fā)香甜”的壺道說辭,一心想著如何把壺中“俗稱玉花”的成團狀茶垢變成“海綿體”,讓自己的垢壺變成“價值連城”的“極垢壺”。為此,他堅持天天為茶壺“養(yǎng)垢”,還總結了一套聽起來似乎頗有道理的養(yǎng)垢理論(或曰“心經(jīng)”):“養(yǎng)垢看季節(jié),所謂春垢為金,秋垢為銀,夏垢為玉,冬垢為石。春秋養(yǎng)的是垢花,夏冬養(yǎng)的是垢莖。無論春夏秋冬,須一日三養(yǎng),分早、午、晚三次。但養(yǎng)垢次數(shù)不能過頻,否則垢花就要枯萎凋零”,云云。以至于沉迷其中,不能自拔,手指甲里積滿污垢。小說的精彩之處在于,通過迂腐的父親形象,展示了可笑甚至病態(tài)的“養(yǎng)垢文化”,并借助富有戲劇性和喜劇性的“我”老婆的“除垢”舉動,含蓄地否定了有害健康的“垢壺文化”,隱含著作者對民族文化中的糟粕的理性批判。
小說對茶道文化的描寫也十分精細:
十分鮮亮的茶具早已擺放在古色古香的四方桌中央。四個比酒盅大一圈的赭紅色小茶碗兩廂落定,茶鉗、茶棒、茶盒、茶巾一應俱全。
大師坐在上首,父親坐下首。兩人寒暄一番之后,他打開柜門,小心翼翼取出垢壺。啟壺蓋,開茶盒,茶鉗夾出一小撮銀毫,沏沸水,茶巾拭去壺口周邊水珠……
茶具齊備、精美,奉茶者禮節(jié)周到,泡茶程序講究。富有詩意地展現(xiàn)了中國茶道文化的典雅氣質(zhì)和雋永韻味。
綜上所述,胡金洲先生的小小說,以精湛的敘事藝術和精當?shù)男揶o策略,將傳奇故事和民族文化有機融合:傳奇為“形”,文化為“神”,“形”“神”兼?zhèn)洌瑥亩鴪A滿實現(xiàn)了小小說咫尺之間涵納萬里之象、以小博大的美學意圖。此類“文化傳奇”作品,既開啟了文學創(chuàng)作上文化審美化的新路徑,也打開了文學接受中品鑒傳統(tǒng)文化的新窗口,在小小說領域尚不多見,其價值意義值得肯定。
注 釋
① 胡金洲《穗兒紅》,載于《活字紀》,2020年2月14日。網(wǎng)址:https://www.sohu.com/a/373066922_699210。凡本文引自該文文字,不再標明出處。
② 胡金洲《潘七爺》,載于《襄陽晚報》,2013年5月17日,第4版。凡本文引自該文文字,不再標明出處。
③ 胡金洲《垢壺》,載于《百花園》,2013年第7期。凡本文引自該文文字,不再標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