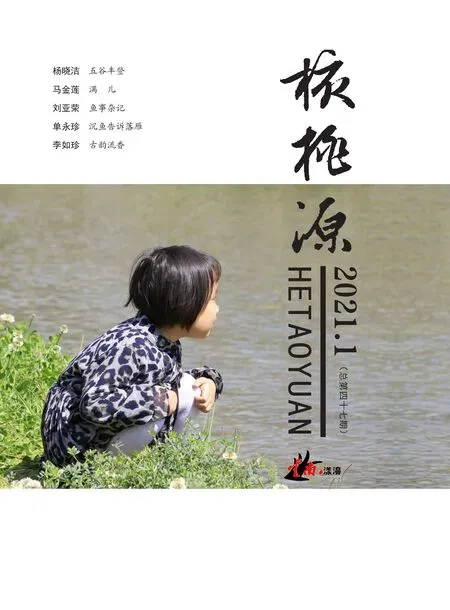蜜蜂飛翔(外一篇)
蜜蜂一般飛翔在鄉下,鄉下多花。
蜜蜂一生戀花,為花生,為花死。除了蜂房,蜜蜂更多去處就是盛開的花朵了。花朵有花蜜,有花粉,那是蜜蜂能唯一短暫棲居的詩意客棧,也是蜜蜂一時能陶醉的世外桃源。
這種資源昆蟲的飛翔,嗡嗡有聲,每座村莊皆為此變得鮮活。
我曾用荒廢一年兩茬莊稼的代價,靜觀蜜蜂的飛翔。雖然落得個懶漢的罵名,卻也使蜜蜂真正飛進了我的心庭,令我的心潮澎湃不已。
讓田地荒蕪,那是作賤。要頂住多少的壓力和謾罵,你無法想象。在我的世界里,便充斥滿不解、不屑、冷眼、熱語。要是沒有磐石般的定力,或者說油鹽不進的護繭,那株崇尚自然的心苗早被寒風吹折,那份想要探個究竟的好奇心智也已摔得支離破碎。
正因一份執著,一份堅守,讓我看清了蜜蜂的飛翔,還有飛翔后面隱藏的那些神奇秘結。
那一年,油菜花正忘情地開放,一片田野與金子攀上了親戚,滿眼都是土豪色。我靠在田埂上,仿佛一個不諳世事的嬰兒臥在花籃中,又宛若一頭容易知足的昏驢,幸福地躺在三月明媚的春光里。
我看到天空甚為湛藍,十分干凈。飄來的幾朵白云,神似嬌羞的少女走過,正應了李清照“和羞走,倚門回首,卻把青梅嗅”的絕美意境。日光暖洋洋的灑下來,沒有著色,只是亮著,但充滿了力度。油菜葉配著黃花,沒有因配的不是紅花而懊惱或沮喪,倒是使勁地綠著。由于葉綠得干脆,綠得毫無怨言,油菜花黃得更純粹了。
這一天,就藍白綠黃四個顏色,竟顛覆了我以往對美的偏執。繁花錦簇是美,色彩斑斕是美,原來,自然也是美,簡單也是美,且美得更坦蕩,更明了。
剩下的事情就是仔細觀察蜜蜂采蜜了,我沒有忘記來時的初衷。
我對蜜蜂是懷著敬畏之情的。這時,我躺著,花朵剛好在上方,蜜蜂來了,我得仰視,正好滿滿地表達了我的心意。
蜜蜂飛翔是有聲的,它翅膀振動的頻率剛好在人的聽力范圍內。蝴蝶飛翔就不同了,沒有聲音,蝴蝶一生不像蜜蜂一樣采花蜜花粉是為了筑巢釀蜜,它僅僅是為自己的美麗填飽一時的肚子,比起蜜蜂的勤勞,或許它也覺得有些羞愧,就刻意壓低翅膀振動的頻率,故意讓人聽不見。在昆蟲界,蝴蝶算識趣且有修養的了,蚊子和蒼蠅最討人嫌,屬蠢蟲那一類。蚊子飛來,張揚跋扈,吸人血還明目張膽地告示我來了。蒼蠅更可惡,越臟的地方越歇得了腳,然后哼著令人惡心的曲調,六只臟爪又不安分地往人吃的食物上去沾染。當然,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很多蚊蠅活不到老便過早夭折,那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這時,閉目靜心,側耳傾聽,遍野都是蜜蜂的嗡嗡聲。聲音無形,但具有穿透力,渲染著我的耳膜,極為美妙。其魅力在于,它是辛勤勞作的號角,也是對甜美生活的一種禮贊。
感覺中,有蜜蜂正飛到我的上方。睜眼一看,真的正有一只蜜蜂落到花朵上。那是一只完美的工蜂,平生有幸第一次這么有興致近距離地與蜜蜂親密接觸。
那只工蜂一會兒鉆到花朵里采蜜,一會兒又退出來,忽隱忽現,仰視已不利于全面觀察,我只得立起身,便于仔細端詳。
只見那只工蜂身色灰褐,頭、胸、背上生滿細絨毛,呈灰黃色,濃密的體毛,既是防寒御冷之用,也在隱約彰顯著工蜂這種特有的雌性之美。
三角形的腦顱上,長有一虎視眈眈的嚼吸式口器,并鑲嵌復眼一雙、單眼三只,滿是花粉、花蜜再狡猾也無處可躲的架勢。一對觸角高聳而立,它不僅僅是為了長著好看,主要是有嗅覺和觸覺的功能,比如說這里有一片油菜花花海,就是由某一只偵察蜂憑嗅覺發現后,回去告訴其他的蜜蜂,還有辨認敵友用的也是嗅覺。觸覺則在蜜蜂飛行時能感知到風速、風力和氣壓,進而換好擋位,控制好油門,以調整飛行的速度和姿勢。
工蜂生有六只爪,與蚊蠅一樣,不過用途卻截然相反,蚊子逃不脫吸取人血的罪惡,蒼蠅則盡往臟處飛,滿爪污垢,遭人唾棄,蜜蜂在股節、脛節及跗節處設有采集花粉的構造,定位很準確,對象是花朵。
兩對羽翼,仿佛正副油箱,正的受損,副的跟上,沒有回不了家的懸念。
尾翼最為獨特,它在幼蟲時期,僅有最初幾天可食用蜂王漿,之后則只能食一般的蜂蜜了,生殖能力的發育便頹廢,生殖器官最后生化成尾端的螯刺,且附上毒腺,以作保護自己或攻擊他人的武器,這在動物界也屬少有的了。可想而知,生為雌性難為母,仿佛枉為上等好地卻怎么也長不出莊稼,內心定是一腔悲愴。工蜂一生忘我地辛勤勞作,抑或它正是在調整和轉移自己的情緒。
工蜂的腰出奇地細,宛若楚女再世,楚王愛蜂腰的朝代已漸行漸遠,歷史的遺跡卻在蜂身上一直褪不去,落英飄紅般地纏繞,讓人的思緒見蜂便情不自禁地穿越回楚地。
再說每枝油菜花上端的花朵是一簇一簇地開放,下端早先已開過花的卻長出了長條形果角,有的莢內都已結籽。盛開的每朵油菜花共生四瓣,工蜂飛來能準確地落在花朵上,且一瓣花瓣便足夠了,工蜂落上去,花瓣微微一顫,但工蜂已緊緊抓住,不會摔下。
工蜂是嗅準了有花粉和花蜜才有的放矢地落下的,它剛落下,便亟不可待往花朵深處鉆去。我聽懂蜜蜂習性的人講過,工蜂采蜜靠的就是那嚼吸式的口器。口器的下唇伸長,和下顎、舌組成細長的小管,中間有一條長槽,能吸吮,把那小管深入花朵中,便可吸取花朵中的蜜汁。采完花蜜,工蜂又去采長在花蕊上的花粉。工蜂的后腳叫攜粉足,跗節外側有一條凹槽,周圍長絨毛,稱花粉籃,當毛茸茸的腳沾滿花粉,跗節上的花粉梳就將花粉梳到花粉籃中,再用蜜將花粉固定成球狀。工蜂回歸時,像極了載滿彈藥的戰斗機,飛行軌跡中,還不忘劃一道道優美的弧線,在炫耀自己的機動性和靈活性哩。
工蜂尋蜜,最求效率,它一般只往盛開的鮮花上飛。年輕的花朵,太水靈,可能下不去手,當然主要是花蜜還少。工蜂還是完美的勞作者,抵得上德國的工匠,過程絲毫不攙假,我發現工蜂采完一朵花的花蜜后,本來可以慵懶地爬到另外一朵花上,但工蜂絕對不會這么做,它要飛起來,定位好另一朵花,才準確地落下去。
天色漸晚,一撥撥的工蜂往回飛。心想,我也該回了,便踏著暮色往家走去。這天,我看到一只只工蜂們都收獲頗豐,蜂房里的蜜糖一定缽滿盆溢。別看我空手回來,我也受益匪淺,只不過我的收獲是在心里。
我看似有點不務正業,不過定下來要做的事卻從來沒有荒廢過。接下來,我探究的目標便是往蜂房里進發。
好在我家就養了兩窩蜜蜂。要不然求別人家去看,人家未必愿意,還有啥事不干,成天蹲在蜂箱口,有人問起來,我得費多少的口舌去解釋,別人還不一定聽明白,反而會認為我的腦袋肯定不小心被驢踢了,并且是踢得不輕的那一種。沒求得他人同意就去吧,需靠近蜂箱,還得打開箱蓋,若被主人看見,豈不有了非偷即盜的嫌疑,我家從祖上一直到我這代,都從沒有過那方面的愛好,一部家族史可清白著呢。
我家養蜂用的是蜂桶,也就是鋸一段內心朽了的樹,將樹心掏空,兩邊再砍兩個圓形的蜂桶木門分別封上,門與桶之間留兩眼供蜜蜂進出的洞即成。
我去的時候,正有工蜂紛紛離去或歸來。出去的工蜂,先是鉆出蜂洞,然后在洞沿口選好位置,腿一蹬,颼地一聲飛往既定的方向,瞬間就沒了蹤影。若是航空母艦上戰機的話,工蜂不是滑躍起飛,也不是垂直起飛,而是彈射出去。回來的工蜂不需滑翔,雖然身上荷滿蜜和粉,一樣能輕松準確地降落在洞沿口,再爬進蜂桶。我在想,工蜂與戰機有許多相似之處,不同的是,戰時的飛機出發時全副武裝,歸來一身輕松,制造的是一幕幕人間的悲劇與創傷;工蜂則空手而出,滿載而歸,釀造的是生活的溫馨與甜蜜。
轉到蜂桶的另一邊,蜂洞口同樣有工蜂不停地進出。而這一邊飛出去的工蜂飛往的是不同的方向,顯然這邊的工蜂繞一個彎與那一邊的工蜂同向飛,就會增加撞機的可能性。工蜂一定是事先就用蜂語作了分工和交待,且沒有違反規矩的工蜂,要不也沒看見有警察、保安一類的蜜蜂在維持秩序,工蜂們千軍萬馬在行動,卻絲毫不亂,一切井井有條,這一點人類都難做到。
也倒是這一季節,不僅僅油菜花、桃花、梨花、櫻花、杜鵑花均次第開放,工蜂采蜜是不必吊死在一棵樹上的。四面八方的鮮花都給工蜂源源不斷地提供著花蜜和花粉,即便工蜂一時半刻飛暈了一下頭,說不準正好跌落到花朵里,只需將口器里的吸管伸一下,就探進蜜源,分分鐘吸飽蜜囊,稍喘口息,待神清氣定,縮腳,蹬腿,照樣彈射回蜂房。
當我打開一邊的蜂桶蓋時,只見數萬只蜜蜂將蜂餅擁得嚴嚴實實,簇成一團,這一蜜蜂王朝,正值鼎盛時期。在蜜蜂眼里,我的到來,肯定屬肆無忌憚,而我針對自己的唐突,在內心里也表達了深深的歉意。面對不速之客的光臨,蜜蜂自然按下守護家園的按鈕,身居外圍的蜜蜂很齊整地一下又一下扇動翅膀,并間歇性發出嗚嗚嗚的震動聲,很明顯是在對我發出警告。
幾分鐘后,見我這異族并無掠奪的跡象,蜜蜂非但沒有啟動攻擊程序,還取消了紅色預警,不扇翅膀了。只是靠近我這邊的工蜂不再外出,戒備心理還未徹底解除,采蜜歸來的蜜蜂到蜂桶前先是一陣猶豫,然后徑直往蜂窩里飛去,根本無視我這大活人的存在,心里竟無端泛起一絲絲的酸楚。
蜜蜂最早出現于早第三紀古新世時期,比人類要晚一些。這種由黃蜂進化而來的益蟲,完完全全過的是母系氏族社會,蜂窩里的蜂王是母的。這也不必少見多怪,人類由女性當政的比比皆是,中國歷史上有武則天,當代世界歷史上有默克爾、英拉、樸槿惠、羅塞夫等一長串女領袖,只是人類首領一般男女交替,蜜蜂當王則雌性永恒。其實,蜂王的誕生只是一個簡單的過程,當一窩蜜蜂過盛,擁擠不堪,不便于管理,一部分蜜蜂需分群另起爐灶時,或者蜂王年歲已高,老態龍鐘,神志模糊的時候,只要對幼蟲期的雌蜂一直喂蜂王漿,新的蜂王便閃耀登場了。前期喂蜂王漿、后期喂蜜的雌蜂,則成工蜂。蜂王與工蜂的差別僅一步之遙,照理說,只是時運不濟,要不然每一只工蜂都有條件成為蜂王。
蜜蜂過的是群居生活,蜂群中有蜂王一只,少部分的雄蜂,數量最多的是工蜂。蜂王身藏蜂群的中間,很難視其廬山真面目,我都是掏蜂蜜的時候看到過一次,體格最大,雄蜂次之,工蜂最小。
要說蜂王,除了統治這個大家族外,它憑著超強的生殖能力,還要肩負繁衍生息的重要使命。蜂王與雄蜂交配后,可將雄蜂的精子儲存在體內數年,再自由選擇產受精卵或未受精卵,產出的受精卵發育成工蜂或蜂王,未受精卵發育成雄蜂。
工蜂的生命很短暫,夏季出生的只能活四到六周,冬季出生的能活超三個月,命長的頂多能熬到半年。可謂人生苦短,本來命就不長,蜂群里的所有臟活累活卻全部安排它們完成,且沒有假期,沒有周末。剛出生八天左右的工蜂,正值玩耍的幼年期,就成為保溫、扇風、清理巢房、調制蜜粉的打雜工。飼喂小幼蟲和蜂王、筑巢釀蜜、夯實花粉、守衛蜂巢,則由青年蜂完成。壯年蜂主要負責采蜜、采粉和采水。老年蜂雖然老了,但也不準像人一樣可居功自傲、倚老賣老,蜂王是要花盡你的力、榨干你的油的,在淫威面前,也只好乖乖地去搜尋蜜源,回來的時候也不得空身,必須順帶采點水。蜂巢里死蜂并不多,或許主要原因是眾多的老年蜂在半路上一口氣上不來,就一命嗚呼了。
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盡管工蜂的生殖器官已被變異,無法與雄蜂交配了,但卻可產下未受精卵。有些工蜂就對蜂王進行欺騙,偷偷地產下卵子,使蜂王的權力失控。畢竟蜂王是母性,還算保留著幾分仁慈,非但不處罰違紀違規的工蜂,還給它們放產假。這樣,繁殖的工蜂就不需去從事采蜜采粉般的危險工作,大大降低了勞動強度,延長壽命達三倍以上,能與蜂王齊壽了。不過,工蜂產下的卵就沒有這么好運了,蜂王為確保自己的統治地位,總是把那些卵子吃進肚里。當然也有一些逃過厄運的卵子,發育成雄蜂,但個頭較小。
先前,我是討厭雄蜂的。長著大個子,卻啥活也不干,就知吃喝,是典型的懶漢,偶爾爬出蜂洞,在蜂桶周邊溜達幾圈又飛回去,飛翔的聲音還像足了大綠蒼蠅,挺煩心。后來才知道,沒了雄蜂還不行。再有能耐的蜂王,沒與雄蜂交配,也產不出受精卵,也就預示著沒了工蜂,無蜂干活的蜂群必定在饑餓中消亡。雄蜂的存在只是專司交配,似乎可活得醉生夢死,逍遙自在,不過你也別羨慕,想象與現實是大相徑庭的,雄蜂的交配十分悲壯,精盡便蜂亡,它是以生命做籌碼換取一時的快樂,當然體現的也是一生的價值。更凄慘的是,摔死在蜂桶底部的雄蜂,身體尚有余溫,就早被負責清掃蜂房的青年工蜂抬出去,扔到荒野里。
我在蜂桶前正看著,重溫著我對蜜蜂的了解,一只工蜂遠道而回,歸蜂群后不停地擺動身體,還扇著翅膀,跟跳搖擺舞一模一樣的。我知道它是一只年邁的偵察蜂,它在向同伴們告知自己發現了蜜源,在什么地方、有多遠呢。在往常,得到信息的外勤蜂就會立即大批量地飛向蜜源地,開始忙碌而緊張地采集工作。而有我這活物的干擾,工蜂們竟不動了。我意識到不能無休止地耽擱它們的勞作,要不缺德也缺得有點過分了。于是,我急忙將蜂桶蓋鑲上,還蜜蜂一個安寧。
人在生產生活中,對蜜蜂的依賴還不可小覷。許多農作物和果樹的花,未經授粉是結不出果實來的,至少產量要大打折扣。這一繁雜的過程,大部分是工蜂給代勞了。我想也不是說工蜂的思想境界有多高,只是它們在采蜜采粉時無意地幫了人的大忙。愛因斯坦預言過,如果蜜蜂消失,人類將只能存活四年,有些危言聳聽,但不可避免的是人們的生活確實要大受影響。
說來也巧,我們村第二年就出現了類似的情況,全村的蜜蜂集體玩起了失蹤,蜂巢空了,油菜、果樹的花朵照舊盛開,只是沒了蜜蜂的身影。我看問題不輕,就對村里人奔走相告,今年的小春作物要減產了。南方農作物種植分大小季,也稱大小春,大春種稻谷、玉米、高粱、大豆,小春種蠶豆、豌豆、油菜、麥子。令我失望的是我的苦口婆心,竟沒有人理我,有的甚至還給我瞪了白眼,看他們的表情,我走后肯定又在后邊冷語這人是不是瘋了。結果不出意外,真的依我所料,農作物歉收了,果樹結出的果子也七歪八扭,看相極丑。
村民們一下子意識到我是有點文化的人,便開始信我,一茬一茬的人跑來與我取經。我告訴了他們歉收的緣由,歸根結底還是打農藥惹的禍。村民們說,我們打農藥是毒害蟲,壓根沒有針對蜜蜂,我反問蜜蜂不是蟲嗎,村民們若有所悟,紛紛表示不再用農藥了。
村民們信守了自己的承諾,大春這一季真的沒有一家再打農藥了,并認真清掃好空著的蜂桶。沒過幾個月,成批的蜜蜂又飛回來了。
又一年的初春,油菜田恢復了當年的熱鬧。想不到我這一村民們眼中的懶漢,還給大家辦了一件大好事。看著自由騰飛的工蜂,我心存萬分的感激,是它們,至少替我贏回了在村民面前的一絲尊嚴。
鄉下,多花,只要不加以人為的侵害,就一定有蜜蜂的詩意飛翔。
人與畜
我們罵那些不聽人話的牲畜不通人性,說不準牲畜也正罵你畜生不如。
人和畜在一個村子里生活著,早不見晚見,相互依存,誰也不要得罪誰太深,兔子急了會咬人,狗急了還跳墻。
你認為村子那么大,牲畜那么多,你不大識誰是誰家的牲畜,牲畜也不識你是誰,不過你錯了。
前些年,你去張家借錢,張家的大黃狗也知道你去借錢似的,咬得特別兇,眼看你身體的某部分就要與狗牙親密接觸,情急之下你給了大黃狗一悶棍,打狗還要看主人,張家的人肯定不悅,自然沒借到錢。多少年過去了,你對人還耿耿于懷,狗的事卻忘得一干二凈。可大黃狗還惦記著你哩,它不會忘記你下手之狠毒,幾乎斷了它的七情六欲。到現在,大黃狗見到你就會瞪起雙眼,別以為它不出聲就是對你友好,它正伺機逮一坨你小腿的肉呢。
又一年,李家的一群黃牛溜到你家地里偷食麥苗。你想都沒想,憤怒地拾起碗大的一塊石頭就掄過去,你的手準得出奇,那頭大公牛的一只角頃刻被打飛了一大截,大公牛強忍疼痛,領著牛妻牛子落荒而逃。隨后,李家大開罵戒,說有本事拿人開刀,拿牲畜出氣,跟畜生計較的人還是人嗎?你把有理的事辦成無理,自知理虧,又不想站出來承認,只得悶聲不出氣,心里卻五味雜陳,比挨了一刀還難受。
時間長了,人與人的事算躲過去了,但人與牛的事還沒完。那大公牛一直以一對高聳的牛角為傲,面對再牛氣沖天的母牛也自信滿滿。自從斷了角后,威風凜凜的大旗轟然倒下,開初一看到其他的公牛還是當頭迎上,決一雌雄的氣勢絲毫不減,但獨角難敵雙刃,每次都只得夾起尾巴逃跑認輸。十分尷尬的是母牛風光無限的時節,大公牛一時忘了自己已破相,和往常一樣,仍然心雄得一抱粗,尾巴翹得幾乎頂著天,但母牛們卻刻意躲閃。有力使不出的窘況,抹殺著獨角牛的尊嚴,也摧毀著它的意志。
慢慢地,獨角牛認命了,不再與同類爭斗,也懶得再去搭理那些翻臉不認人的母牛。不過,它卻每天用那只獨角見合適的土坎就挑,見粗糙的樹樁便擦,把那只角磨得犀利無比。獨角牛在牛界東山再起已無望,卻又不停地折騰自己,唯一合理的詮釋只有:它在蓄勢待發,要對某個人復仇。
那一天,你家的那只大母雞剛下完蛋,“個大,個大”地叫個不停,關鍵時候那該死的老公雞卻不知去了何處,要不然老公雞附和著安慰上幾聲,老母雞也便不叫了。偏偏老公雞這時不在,要是你學上幾聲公雞叫,雖然叫聲不如公雞好聽,也許就了事。其實老母雞也只是想邀一下功,或像人一樣撒撒嬌。可你卻非但不學公雞叫,還嫌老母雞叫聲嘈雜,讓人心煩,于是又拿出你擅長的伎倆,撿起一土塊就扔過去,老母雞嚇跑了。接下來的日子,本來每天給你產一個蛋的老母雞,三天兩頭才給你一次動靜。老母雞的異常舉動,或許是在表達它對你的意見很大。
看來人這一輩子,即使你低調做人,時時處處小心翼翼,就算人這關過了,但難免在不經意間卻得罪了畜。得罪了人,只要誠心認錯,悉心溝通,還有和解的機會。牲畜就不同了,它不懂迂回,只會認死理地和你糾纏到底。
靜下來仔細思忖,如果我們肯把自己當作一頭驢,或者是一條狗,未見得就是一件壞事。站在驢的角度想想,立于狗的立場看看,就會發現做牲畜也不容易。
過去,村里人不食驢肉,驢再苦再累,還得壽終正寢,主人一般選擇一條土溝埋了,能保住全尸。如今,隨著交通的改善,毛驢們變得清閑了,看似毛驢就要退出山村的舞臺,想不到的是竟有越來越多的村民養起了驢。都是那“天上龍肉,地下驢肉”的說法在作祟,市面上流行起了吃驢肉的時尚,請客者以吃驢肉宴為體面,食客們則筷箸你來我往,爭先恐后,吃得口門難合、嘴角流油。吃到高潮處,借著酒興,雅致大增,用充斥滿驢肉味的話語,高談古今中外,大論坊間雜聞。遺憾的是毛驢們幾乎難以再體會到老的滋味了,都是英年早逝,且均命斷于血腥的屠宰中。毛驢,以往用體力換來主人一家豐裕的生活,現今用生命博得食客瞬間一笑。
毛驢為驢,可謂仁至義盡,但卻未落得好名聲。人們把那些辦不成正事的人稱為蠢驢,將見著有點姿色的女人就要豎起尾巴的好色男人稱作老毛驢,這也有點屎盆子往毛驢頭上扣之嫌。人做茍且之事,是人的骯臟,毛驢沒合伙,沒沾邊,未貪著半點便宜,卻要生拉活扯地與毛驢扯上關系,這是人的齷齪。
狗是最護主、最通情達理的動物。主人回家時,豬雞牛羊貓頂多看你一眼,毛驢更多時候是在斜瞅,在嗔怪你沒照顧好它的草料呢。只有狗,使勁甩起尾巴,上躥下跳,激情萬丈地與你親昵。人們待狗也好過其他的家畜家禽,每條狗都有一個屬于自己的名字,黃狗叫阿黃或大黃,黑狗叫阿黑或老黑,花狗叫阿花或花花。名字土些,但狗識自己的名,只要一喚,就會立即跑過來。城里的狗名則洋氣多了,都是叮當、旺財、寶寶、貝貝的一類,甚至有哈利、仙蒂等洋名。城市狗也比鄉村狗享福,穿衣戴帽,美容梳妝,甚至被寵得勝過主人的子女,因為有的子女未必就像狗一樣肯聽話。
鄉村狗就沒有這個福分了,狗是山村的門鈴,門縫則是貓眼。來了外人,門鈴必須響得到位,否則門鈴要遭罪了。門鈴一響,一般主人不會 “來啦”或“誰呀”地應聲,而是躡手躡腳地來到大門前,往門縫里朝外看,若來者是期待的人,就急忙打開門閂,滿臉堆笑地迎客人進屋,且對狗怒斥幾聲不識相。若是不愿待見的人,主人則會縮回屋里,默不作聲,假裝沒人在家。來人在大門外徘徊一久,仍未見動靜,憤憤地罵幾句臟話,走了。
在山村,人人都要習武,來不了幾套打狗功,就別想出門。去他人家辦事,有大門的人家頂多吃個閉門羹,沒大門的人家,你就要首先與狗過招,沒點功夫的人,等主人出來時,說不定你已躺在地上。
狗的盡責,并未贏得人們的稱頌,更多的是反唇相譏。大家把那些有不雅不齒行為的人,都與狗對上親戚,如瘋狗,癩皮狗,哈巴狗,看門狗,落水狗,喪家狗。我們在貶人的同時,實質是在貶狗。我們這樣待狗,也不知狗又如何看人。肯定的是,如果狗看懂了人的心思,會將我們攆得滿世界找躲處。
我們每每聽說,某家的狗連主人都咬了。我們也不要僅僅責怪狗的不是,難說那便是先知先覺起來的一撥狗,它在發出警告呢。
人與畜斗,勝之不武,也未必占據上風,我們會經常看到有的人灰頭土臉地敗下陣來。畜與人斗,屬不自量力,即便偶爾隨了意,下場一定很難看。不如人畜友好相處,互相擔待,給山村一隅平靜和安寧,給鄉間一分融洽與和諧。
畜在圈中下得小崽,人在屋里喜添新丁,畜崽歡,小孩哭。這時一地陽光,微風習習,滿院勃勃生機,展示的是人間其樂融融的絕美境界。只是孩兒未大,畜卻老了,但也不必惦念太多,畢竟我們一同出生過,當我們進入耋耄之年,那些老掉牙的重孫輩牲畜又伴在左右,且算也一起老過。
我們在年輕力壯的時候,趕著或騾或馬或驢,人只需跟著,牲畜識路,到叉路口吆喝一下,比一個手勢,它便不會走錯方向。走到前不著村、后不挨寨的地方,除了馬蹄的踢踏聲,萬籟俱寂,你會自不而然地哼起男歡女愛的小調,在村中萬不能隨意唱,會被人在暗地里喚作老毛驢或大叫驢的。你的小調唱得清脆悠揚,竟和馬蹄聲十分合拍,這踢踏聲定是許多山歌創作時所采用的節拍。四季更替,我們總與騾馬在院門進進出出,不同的是出門時馱的是理想和希望,回家時馱的是收獲與幸福。
年少和年邁時,我們更多只能從事放牧的活計。年少時,我們無法駕馭牲畜勞作,年老了便體力不支,那畜生欺人老呢,他不聽你使喚了。放牧也不是件輕松的事,那些畜生長了一張吃嘴,宛若吃著碗里卻看著鍋里,都是揪幾嘴草換一個地方,特別是水冷草枯的季節,要跑經幾山幾洼,稍不留神還躥到別人家的地里糟蹋莊稼。若讓莊稼主人發現,牲畜每每都要被石塊打通了頭或破了身。傷口雖能痊愈,疤痕上卻不再長毛,饞嘴的牲畜,身上就那么東缺一塊西缺一片的。那牲畜到死時也一定在愧疚,為了愛貪口竟不能給主人留下一塊完美的皮張。放牧雖累,倒也是人畜平心交流的好時候。讓它干活時,它心里恨著呢,誰愿聽你嘮叨。放牧時,你與它講話,它肯定聽不懂,但會立起耳朵作聽狀,目光也很友好。牧歸了,牲畜已飽,會溫順地往家走。這時,村里的炊煙正裊裊升起,輕風一拂,迷蒙了晚歸的人和畜。
我們在白晝里與畜為伍,在夢里還與畜相遇。也許是牲畜平日里無法與我們交流,到夢中給我們作提示。有時圈門沒關緊,牲畜竟跑到屋里窺探,抑或它當夠了畜,想做一回人呢。看人看多了,難說牲畜的心里對世事比人還明了,所以在牲畜面前盡量不能提別人的不是,更不能講他人的壞話,萬一自家的牲畜講與那家的牲畜聽,而恰巧那家的主人懂畜語,人會來找你評理,牲畜則會見到你就進行群毆。
好好想想,我們不必是人就高高在上,不妨放下架子,如果不想像城里的大老板一樣養一群人差遣,就養好一群畜使喚吧,只要多給它們一些關愛,回報一定不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