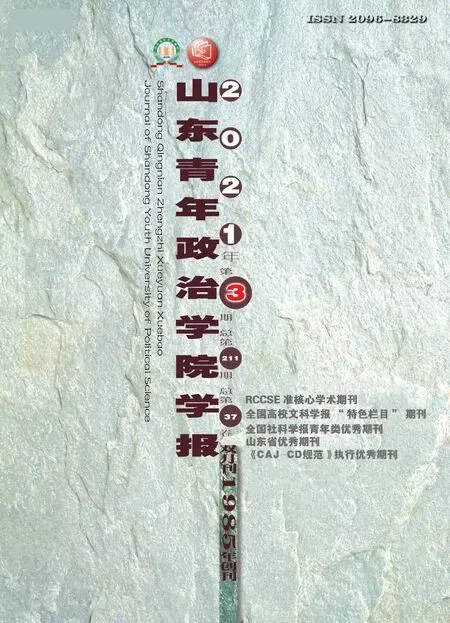從“誠意格物”到“致良知”:王陽明工夫論的困境與突破
田雨可,文碧方
(武漢大學 哲學學院,武漢 430072)
正德三年,王陽明悟道于貴州龍場,在此之后,其論學宗旨又幾經變更,最終定宗于“致良知”。陽明嘗言:“吾良知二字,自龍場以后,便已不出此意。只是點此二字不出。于學者言,費卻多少辭說。”[1]按陽明的這種說法,在龍場悟道后,他的基本思想就未發生過變化,“致良知”的提出僅是改變了他教人時思想的表達形式,這一看法亦被學界廣泛接受。但在正德十五年,陽明揭示“致良知”時曾說:“若不靠著這些真機(良知),如何去格物?我亦近年體貼出來如此分明”[2]173,這表明他的龍場悟道是不足的。且在“致良知”提出后,陽明的體用觀和知行觀等都發生了明顯變化。因此,把“致良知”的提出僅視為陽明思想表達形式的變化是不太妥當的,“致良知”學說究竟對陽明整體思想產生了何種影響值得深入探討。
一、陷入循環:王陽明早期工夫論思想之困境
錢德洪曾指出,王陽明在龍場悟道后的教人宗旨有“三變”:“居貴陽時,首與學者為‘知行合一’之說;自滁陽后,多教學者靜坐;江右以來,始單提‘致良知’三字,直指本體,令學者言下有悟:是教亦三變也。”[3]但據陳來先生研究,錢德洪的這種說法并不合理。陳先生認為:“陽明自龍場之后,學問宗旨主要是‘誠意格物’,在正德庚午(1508)至正德己卯(1519)近十年間,雖然他也根據具體對象及具體情況的差別對某一方面有所強調,如辰州、滁陽教人靜坐,南都南贛教人存理去欲,其實都是誠意格物的準備階段或具體方式。庚辰辛巳(1520-1521)致良知宗旨的提出,標志著陽明學問進入了一個新的境界,才真正構成了一個與‘誠意格物’不同的階段。”[4]在陳先生看來,陽明龍場悟道后的學問宗旨經歷了“誠意格物”與“致良知”兩個階段。
在“致良知”提出前,王陽明將《大學》中的“誠意”視為工夫的頭腦、核心,以“誠意”來統率,他說:“《大學》‘明明德’之功,只是個誠意。誠意之功,只是個格物。”[2]21對于“誠意”,陽明解釋道:“為學工夫有淺深。初時若不著實用意去好善惡惡,如何能為善去惡?這著實用意,便是誠意。”[2]84在這里,陽明將“誠意”視為“著實用意(去好善惡惡)”。“誠意”工夫顯然是針對意念的,而“意”一定要指向事物,因此“誠意”工夫也要落實在具體的事物上,這就是“格物”。[2]167如此則陽明所理解的“格物”就不是朱子所認為的“求理”工夫了,他以“正”訓“格”,格物成了正“意念”的工夫,他說:“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于正也。”[2]65又說:“但意念所在,即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2]23。可見,“誠意”與“格物”的側重點雖然略有不同,但表示的是針對意念的同一種工夫。
而對意念做工夫,首先要能區分意念的善惡,否則就談不上為善去惡(或者說好善惡惡、存善去惡),那么,意念的善惡如何區分呢?
善念發而知之,而充之。惡念發而知之,而遏之。知與充與遏者,志也。天聰明也。圣人只有此。學者當存此。[2]59
曰:“正恐這些私意認不真?”曰:“總是志未切。志切,目視耳聽皆在此。安有認不真的道理?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假外求。講求亦只是體當自心所見。不成去心外別有個見。”[2]69
陽明認為心有一種辨別意念善惡的能力,他將之稱為“志”“天聰明”“是非之心”,但陽明對此沒有進行更深入的解釋,且問題也非如此簡單。
康德指出,善和惡的概念必須根據道德法則的概念來規定,若非如此的話,善和惡就失去了絕對性。對于儒家來說,道德法則便是天理,因此,首先要識得天理,據此才能區分意念的善惡,即合于天理的為善,與天理不合的為惡。而如何才能識得天理呢
(陸澄)曰:“澄于中字之義尚未明。”(陽明)曰:“此須自心體認出來,非言語所能喻。中只是天理。”曰:“何者為天理?”曰:“去得人欲,便識天理。”[2]62
(薛侃)曰:“嘗聞先生教,學是學存天理。心之本體,即是天理。體認天理,只要自心地無私意。”[2]69
陽明將“中”視為天理,天理不能依靠旁人的言語告知,只能從自己心上體認出來,而體認天理,就須去除人欲,使得心地無私意,這又是為何呢?
王陽明主張義理內在于心性,而心性之理不能作為一個靜態的對象去觀察,只能通過心的發動呈現出來,心的發動即是意念,但對于常人來說,私意(私欲)是不可避免的,是以陽明認為:
人性皆善。中和是人人原有的。豈可謂無?但常人之心既有所昏蔽,則其本體雖亦時時發見,終是暫明暫滅,非其全體大用矣……須是平日好色好利好名等項一應私心,掃除蕩滌,無復纖毫留滯。而此心全體廓然,純是天理。方可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方是天下之大本。[2]61-62
人性是善的,“中和”之德也是人人本具的,但由于普通人的心總為私欲所遮蔽,其心之本體雖然能時時顯露,但其狀態終究是有明有滅,并非“全體大用”。只有將私欲全部掃除,不留一毫,從而使得此心全體空寂澄明,粹然全是天理,如此才是“中”,才是“天下之大本”。就是說,在私欲未去除之前,常人只能體認到一時之善端,卻不能體認到心體(天理)之全體大用。
更關鍵的是,若私欲沒有掃除,心之發動(“意”)就不一定是“理”的呈現,而也可能是私欲,“意”是理欲混雜、有善有惡的,此時體認天理就有認“欲”作“理”的危險,故一定要徹底去除私欲,才能體認天理。如此一來,陽明思想就不可避免地走入了一個死循環:他此時以誠意格物為學問宗旨,誠意格物是針對意念的工夫,而對意念用功必須先分清意念的善惡,否則便無法存善念去惡(私)念?要分清善惡,就要先體認天理,否則善惡就失去了絕對性;要體認天理,還須先去除私欲,否則就可能認欲為理。要去除私欲,又須先分清意念的善惡,否則便無法去惡(私),如此反復,互為前提。
二、原因檢討:以朱子工夫論為觀照
王陽明的思想是在與朱子的對話中形成的,對朱子相關思想的探討,有助于進一步揭示在“致良知”提出前陽明思想中存在的問題。
朱子也認為,心之理欲是很難分辨的。他說:
夫外物之誘人,莫甚于飲食男女之欲,然推其本,則固亦莫非人之所當有而不能無者也。但于其間自有天理人欲之辨,而不可以毫厘差耳。惟其徒有是物,而不能察于吾之所以行乎其間者,孰為天理,孰為人欲,是以無以致其克復之功,而物之誘于外者,得以奪乎天理之本然也。[5]
外物對人的引誘,莫過于飲食男女之欲,不過飲食男女本身也是人所當有的,只是這其間自有天理人欲之辨。若不能對天理人欲進行察識分別,就無法克除私欲,外物對人的引誘便得以奪卻天理之本然。故在朱子的工夫論中,“求理”工夫是居于首位的,“求理”即是格物致知,格物雖然是針對事物的,但在朱子看來,事物之理與心之理是同一的,并無內外之分,所謂“物我一理,才明彼即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6]因此探求事物之理也就是窮究心之理。而心之神明“人莫不有,而或不能使其表里洞然,無所不盡,則隱微之間,真妄錯雜,雖欲勉強以誠之,亦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其意者,必先有以致其知”。[7]通過即物窮理并做到極致,心之神明內外通透明了,誠意工夫也就得以展開,否則心之所發之“意”,真妄交錯,不得而“誠”。
陽明早年曾按朱子“格物”學說格竹,但“日夜不得其理”,以至于“勞思致疾”。從龍場悟道直至去世,陽明便始終堅定反對朱子的“格物”觀,他認為從事物所求之理并不具有與心之理的同一性:“且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如何去格?縱格得草木來,如何反來誠得自家意?”[2]220,并且,從事物求理還會將心與理分為二,成了告子的“義外”之說[2]101-102。
可見,朱子與“致良知”提出前的陽明都認為心的發動會有理欲混雜的風險,因此在去除私欲之前,不可直接從心上體認天理。但朱子的工夫論以“即物窮理”為先,所識認的天理就為誠意工夫提供了指導。陽明則否認了從事物求理的可行性與正當性,天理便難以呈現,誠意工夫便會由于“意”的真罔錯雜、善惡難辨而無法進行,如此的話,私欲也就難以克除,心之理的呈現更變得遙遙無期。
進一步看,由于天理無法呈現,陽明思想還面臨著更大的困難。自二程體貼出“天理”二字之后,“天理”便成為儒家判別于諸子百家的最高宗旨,能否皈依儒門就取決于是否認同天理,并且只有認同天理,才能夠在天理的召喚下“去私欲,存天理”,立身成圣。陽明認為需克除私欲方能識得天理,而未將對天理的體認放在第一位,這就可能會使學者流入異學而不自知。對于這一點,陽明的好友湛甘泉也已經指出。湛甘泉曾撰《答陽明王都憲論格物書》,對陽明“格物”說提出了四條批評,其中第三條言道:
兄之格物訓云正念頭也,則念頭之正否亦未可據,如釋老之虛無,則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無諸相無根塵,亦自以為正矣。楊墨之時皆以為圣矣,豈自以為不正而安之!以其無學問之功而不知其所謂正者乃邪而不自知也。其所自謂圣,乃流于禽獸也。夷惠伊尹,孟子亦以為圣矣,而流于隘與不恭,而異于孔子者,以其無講學之功,無始終條理之實,無智巧之妙也,則吾兄之訓徒正念頭,其不可者三也。[8]
湛甘泉認為,陽明舍棄求理工夫,將“格物”直接解釋為“正念頭”,可是佛老之虛無、楊氏之為我、墨氏之兼愛皆自以為正,如果沒有學問求理之功,將無從辨別正邪,縱使作為圣賢的夷惠伊尹,也因無講學之功,流入了狹隘和不恭。
綜上,在龍場悟道后到“致良知”提出前,陽明無法解決天理呈現的問題,這不僅會使“誠意格物”工夫由于缺乏判斷原則而無法進行,而且會使學者流入異學而不自知。可見,此時陽明的工夫論思想尚不圓熟,“致良知”的提出成為他思想發展的必然要求。
三、困境突破:“致良知”的提出
在“致良知”提出后,陽明認為自己之前“點此(良知)二字不出”[2]236,不過在“致良知”提出前,陽明卻是提及過“良知”與“致知”的:
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發,更無私意障礙。即所謂“充其惻隱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然在常人不能無私意障礙。所以須用致知格物之功,勝私復理。即心之良知更無障礙,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知致則意誠。[2]23
惟乾問:“知如何是心之本體?”先生曰:“知是理之靈處。就其主宰處說便謂之心,就其稟賦處說便謂之性。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無不知敬其兄。只是這個靈能不為私欲遮隔,充拓得盡,便完完是他本體。便與天地合德。自圣人以下,不能無蔽。故須格物以致其知。”[2]83
在這里,王陽明將良知視為知孝知悌知惻隱等,可見他是以意念中的善念來理解良知的。由于常人必然會有私欲的障礙,其意念是善惡(良知私欲)混雜的,所以要通過做工夫,去除私欲的遮蔽,使得良知本體得以充塞流行,此即“致知”,這與其前期思想“去得人欲,便識天理”若合符節,它無助于解決天理呈現的問題,王陽明所揭示的“致良知”學說也一定與此不同。
經“宸濠之亂”和“忠、泰之變”后,陽明終于在百死千難中悟得“致良知”之旨,《年譜》對此的記載值得玩味:“先生自南都以來,凡示學者,皆令存天理去人欲以為本。有問所謂,則令自求之,未嘗指天理為何如也……今經變后,始有良知之說。”[9]這里特別提到,陽明從前只是教人“存天理去人欲,”,又不說“天理”的內涵為何,只是叫人自己去體悟,這種情況直到提出“良知之說”后才改變。可見,《年譜》編撰者(應為羅念庵)也意識到“致良知”的提出與天理呈現的問題有關。
不過,《年譜》記載“致良知”提出的時間為正德十六年辛巳,這是不恰當的,據陳來先生考證,陽明揭示“致良知”的時間當為正德十五年庚辰,[10]這一年陳九川往虔州見陽明,《傳習錄》下卷記載了他們關于“致良知”的多次談話:
爾那一點良知,是爾自家底準則。爾意念著處,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瞞他一些不得。爾只不要欺他,實實落落依著他做去。善便存,惡便去。他這里何等穩當快樂!此便是格物的真訣,致知的實功。若不靠著這些真機,如何去格物?我亦近年體貼出來如此分明,初猶疑只依他恐有不足,精細看無些小欠闕。[2]173
虔州將歸,有詩別先生云:“良知何事系多聞?妙合當時已種根。好惡從之為圣學,將迎無處是乾元。”先生曰:“若未來講此學,不知說好惡從之從個什么?”[2]177
在第一條語錄中,陽明將良知稱為“真機”,并認為如果不靠它將無法格物。在第二條語錄中,陳九川臨別作詩贈陽明,詩中表達了好惡當從良知的看法,陽明也表示,如果九川未來此講學,還不知好惡從之是從個什么。無法“格物”“好惡無所從”這些說法都表明陽明認識到自己之前的工夫論缺乏判斷原則,直到此時他才解決了這個困境。
具體來看陽明在這個時期對“良知”的理解。根據第一條語錄,良知是自家的準則,自己意念的是非,良知都能知得,致知便是實實落落依著良知去做。可以看出,此時的良知概念與早期相比已經完全不同了,陽明在早期將良知視為知孝知悌知惻隱等意念中的善念,但此時他不再將良知看作意念,而是將之視為“知得意之是非者”。陽明更明確地說道:“意與良知當分別明白。凡應物起念處,皆謂之意。意則有是有非,能知得意之是與非者,則謂之良知。依得良知,即無有不是矣”[11]。“意”是人與事物相接時心中所起之“念”,有是非之別,而“良知”能夠知曉判別意念的是非,依順“良知”則有是無非。良知與意念截然區分開來,這樣的話,良知的呈現就是純粹的,不會再有與私意混雜的風險。
陽明進一步認為,良知對意念的照察是永不缺席的。他說:“(陸原靜)來書云:良知亦有起處,云云。此或聽之未審。良知者,心之本體,即前所謂恒照者也。心之本體,無起無不起。雖妄念之發,而良知未嘗不在……若謂真知亦有起處,則是有時而不在也,非其本體之謂矣。”[2]127-128陸原靜認為良知亦有發端,但陽明反對這種說法。在陽明看來,良知是心之本體,它是無限恒在的。即便產生妄念,良知同樣在場。如果良知也有發端,它就有限的,就可能有時而不在,那它也就不是本體了。
而純粹且恒常呈現的良知就是天理的明覺發見,他說:“蓋良知只是一個天理自然明覺發見處”[2]161;“良知是天理之昭明靈覺處”[2]143。可見,此時陽明所認為的心之理是始終即存有即活動的,并非克除私欲后方能呈現。且良知(天理)的呈現不會與私欲混雜,也就不會有認欲作理的風險。這樣的話,良知就可以為誠意工夫提供判斷原則,《大學問》言:
凡其發一念而善也,好之真如好好色,發一念而惡也,惡之真如惡惡臭:則意無不誠,而心可正矣。然意之所發有善有惡,不有以明其善惡之分,亦將真妄錯雜,雖欲誠之,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其意者,必在于致知焉。良知者,孟子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慮而知,不待學而能,是故謂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體自然良知明覺者也。凡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無有不自知者。其善歟,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其不善歟,亦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是皆無所與于他人者也……今于良知所知之善惡者,無不誠好而誠惡之,則不自欺其良知而意可誠也已。[12]
誠意就是要好善念惡惡念,但如果不明意念之善惡,就會由于真罔錯雜,意不得而誠,故誠意必在于致知。良知作為是非之心,乃天命之性,心體(天理)的自然明覺。意念的善與不善,良知無不自知,致良知便是將良知所自知的善念與惡念誠好而誠惡之。
由此可見,“致良知”并非不同于“誠意”的另一種工夫,而是對“誠意”的深化。并且,良知(天理)能夠純粹且恒常的呈現,以此指點人,自然也就不會有讓學者流入異學的風險了。如此,陽明前期思想的困境便得到了解決。
但是,陽明將良知視為“常精常明”的,對意念之善惡是無所不知的,這畢竟過于絕對了,現實中很多人是難以做到的。陽明高弟王龍溪曾言:“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皆指工夫而言也。人知未嘗復行為難,不知未嘗不知為尤難。顏子心如明鏡止水,纖塵微波,才動即覺,才覺即化,不待遠而后復,所謂庶幾也。”[13]龍溪認為,人們都知道做到自覺有不善且不再犯錯很難,但不知道做到對“不善”的時時覺察更難,只有像顏回這樣“心如明鏡止水”的賢者方能做到。聶雙江也有言:“往予巡閩,嘗語諸生,有云:‘圣人過多,賢人過少,愚人無過’。眾皆異之。蓋過必學而后見也,若愚則困而弗學者矣。冥行妄作,安以為常,其不復知己之有過也。”[14]聶雙江認為,對于己身的過失必須經過有意識地學習省察才會自覺,愚人由于不學,因此很難覺察到自己的過失,不過是盲目行事且“安以為常”罷了。
王陽明同樣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在其弟子提出“據人心所知,多有認欲作理,認賊作子處。何處乃見良知?”這一問題時,王陽明一方面肯定了弟子以“心安”貞定“良知”,一方面又補充強調說“固是,但要省察,恐有非所安而安者”。[2]235理得才能心安,順天理則心安,不順天理則心不安,但只講“心安”則可能出現非所安而安的情況,即將惡念錯認成了善念。這表明良知本體的具足并不意味著良知的當下朗現,必須以省察作為保證,然而省察意識必以本心之覺醒為先決條件。顯然這里依然存在一種循環:發明本心、致良知之心學進路要避免師心自用、認欲作理,必須訴諸省察,而要省察則又須以本心挺立、良知自覺為先覺條件。[15]但與前期不同的是,良知天理的呈現是在先的,不會產生由于無法認識并去除私欲而造成天理不能呈現的問題,也就不會重新陷入工夫論困境了。
還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良知是對意念的知,故它是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者:“所謂人雖不知而己所獨知者,此正是吾心良知處。”[2]220而“獨知”的說法也經常被朱子提及,如《大學章句》言:“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16]《朱子語類》也記載:“昨聞先生云‘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處,自然見得愈是分曉,如做得是時,別人未見得是,自家先見得是。做得不是時,別人未見得非,自家先見得非,如此說時,覺得又親切。’曰:‘事之是與非,眾人皆未見得,自家自是先見得分明。’ ”[17]朱子認為在己所獨知處,能見得自家是非,這與陽明的良知學說看似非常相近。正由于此,陳來先生認為陽明思想繼承并發展了朱子學中的“獨知”觀念,并與良知結合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