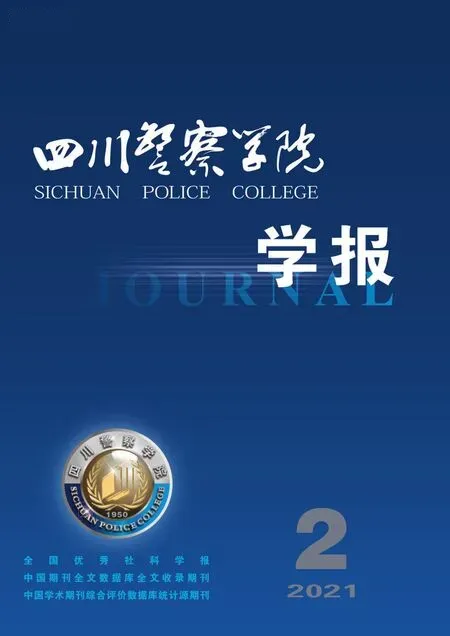問題與完善:公安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的法律條文銜接
彭凱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湖北武漢 430073)
一、問題的提出與研究的緣起
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的銜接既是一個理論問題,又是一個實踐問題,亟需學界進行法理層面的回應。
就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的法理以及語義變化而言,我國官方層面的標準表述范式先后經歷了“行政執法與刑事執法的銜接”和“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的銜接”的發展與轉變。在2006 年以前,我國官方層面就以“行政執法與刑事執法的銜接”為標準的表述范式。然而,于2006 年出臺的《最高人民檢察院、全國整頓和規范市場經濟秩序領導小組辦公室、公安部、監察部關于在行政執法中及時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意見》(高檢會〔2006〕2 號)①下發以后,我國官方的標準的表述范式便統一為“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的銜接”[1]。此外,上述標準表述范式的發展與轉變從一些期刊的論文標題也可以察覺一二。在中國知網數據庫中進行檢索,可知2006年以前發表的期刊論文標題幾乎都是以“行政執法與刑事執法的銜接”為標準的表述范式②。
然而,就公安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的理論研究而言,截至到2020 年5 月23 日,無論是以“公安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的法律條文銜接”為主題、篇名還是摘要,在中國知網數據庫中檢索,結果無文獻呈現。我國學界對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的銜接問題已有一定的研究,其中也不乏具有一定可讀性和可取性的學術成果③。,呈現日趨成熟的態勢,但還缺乏對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具體法律之間銜接問題的關注和研究,這方面的研究還需要加以拓展。
就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研究重點與難點而言,或許,最本質化、最內核化但又未妥善解決的問題即是公安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的銜接。這一問題的客觀存在以及現實變化嚴重束縛了公安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理論與實踐的健康發展、動態完善,并將影響到公安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的有序運轉、良性解決。因此,尤其需要對公安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問題作深入研究。而目前,我國學者對公安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這一問題的研究,大多數的切入點與著眼點是程序法(Procedural law),但實際上較少關注實體法(Substantive law)上的有關問題。程序法固然重要并有獨立的價值,但程序法的重要作用之一仍是保障實體法的良好施行。基于此,從實體法條文角度出發,研討公安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這一問題具有現實緊迫性。其不僅涉及到行政法學,還涉及到刑法學甚至涉及到立法學的理論。在某種程度上講,從實體法條文角度探析公安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可以成為我國法學界系統探討的學科增長點之一[2]。
二、銜接公安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的法律條文存在一定的模糊性
進入21 世紀以來,中央一直高度重視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工作,先后出臺了一系列重要文件來規范有關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程序,并提出完善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工作機制的一些具體要求[3]。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清楚提及了“完善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機制”。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系列問題的提出、梳理、分析、論證和解決成為了學界關注的話題,引起了學界的一些反響與探索。2014年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明確指出了“健全行政執法和刑事司法銜接機制……實現行政處罰和刑事處罰無縫對接。”2015 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法治政府建設實施綱要(2015—2020 年)》又再次強調了“健全行政執法和刑事司法銜接機制”。在上述極其重要的中央文件的明確指引下,健全行政執法和刑事司法的銜接機制已經上升到了頂層設計的高度。
健全和完善公安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工作的意義明顯。其不僅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還是維護國家法制統一以及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的應有之義[4]。而我國公安機關及其人民警察作為法律規范與調控的重要對象,在全面建設法治中國的過程中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不論是從理論的角度出發,還是就實踐的立場來看,我國公安機關及其人民警察都承擔與肩負著依法打擊、懲治行政違法和刑事犯罪等多重職責。依照我國《人民警察法》的第6條④以及第7條⑤之規定,公安機關是我國廣大公民“從搖籃到墳墓”都不可避免要接觸到的國家機關。而公安人民警察作為行使公安諸項權力的工作人員也常常同廣大公民發生密切的法律關系。僅僅從廣大公民的角度與立場出發,我國公安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工作直接關乎到他們合法權益的保障。當下,我國廣大公民對公安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工作所抱有的態度具有明顯的“雙面性”;一方面,廣大公民寄希望于公安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工作的精細化、準確化、合理化和人本化來積極捍衛他們自身的合法權益;另一方面,廣大公民又會擔心公安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的碎片化、錯位、缺位和人性化不足會侵犯到自己的合法權益。因此,該如何銜接好公安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的有關法律條文⑥是我國法治建設現實層面的一個重要問題。
以我國現行的具體的法律條文為著眼點與切入點,不難發現公安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的銜接有明顯、直接的法律依據。其中主要包括我國《行政處罰法》與《刑法》⑦。除上述引用的《行政處罰法》與《刑法》有關法律條文以外,《治安管理處罰法》與《刑法》有關法律條文的銜接亦是不可忽視的研究素材與分析樣本。在我國,《治安管理處罰法》就是為公安機關及其人民警察開展行政執法而“量身打造”或者“量身定做”的一部法律。《治安管理處罰法》與《刑法》有關法律條文的銜接的內容主要包在《治安管理處罰法》第2 條規定之中⑧。梳理《刑法》《行政處罰法》以及《治安管理處罰法》的有關法律條文,能夠發現涉及公安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的內容主要存在以下兩種截然不同的表述范式。其一是“抽象籠統式”。“抽象籠統式”的主要或者典型的表述范式為——“違反本法規定,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抑或“發現違法行為涉嫌犯罪的,應當依法移送司法機關處理。”其實,我國大多數法律都廣泛采取的是“籠統抽象式”的表述范式。其二是“具體細化式”。“具體細化式”的主要表述范式為——“依據刑法第XX 條之規定或以XX 罪追究刑事責任”。跟“抽象籠統式”相比較而言,采用“具體細化式”的法律條文數量要少一些。但“具體細化式”自身的長處與優勢則突出表現在法律實踐的可行性、可操作性較強等方面。
下面以我國《治安管理處罰法》與《刑法》的銜接為例展開探索。我國《治安管理處罰法》與《刑法》分別作為公安適用的重要而又典型的行政法規范與刑法規范,它們對包括但不僅限于危害公共安全、擾亂公共秩序、妨害社會管理、侵犯人身權利、侵犯財產權利的違法和犯罪行為一般可以從所侵害的法益的性質、情節的輕重、數額的大小、后果的大小、主觀的態度等方面加以區分[5]。一般而言,違反了我國刑法的行為也往往違反了我國行政法。而刑法作為最終的制裁武器不間斷地保護著有關主體的法益。我國公安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從規范意義上來講,值得橫向對比的法律條文數量相對比較充裕。這里舉一例,我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第43 條與《刑法》第234 條主要以“損傷程度是否達到輕傷以上”加以適用上的甄別⑨。但是,從《治安管理處罰法》與《刑法》的部分法律條文銜接情況可以發現公安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的法律條文之間存在一定的內在張力。這些內在張力給我國公安機關及其人民警察明確、及時、有效地評價某一行為是違法行為抑或犯罪行為、是適用行政法還是刑法、是采取行政強制措施還是刑事強制措施等后續系列工作帶來了一定的現實困擾。申言之,公安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的法律條文之間存在內在張力帶來的現實困擾主要如下:
(一)《治安管理處罰法》與《刑法》就同一行為可能分別評價為違法與犯罪
逐一對比《治安管理處罰法》與《刑法》法律條文可發現,實際上兩者仍然存在一定的內在張力。在這里簡單地舉三個例子。例如,《治安管理處罰法》第67 條與《刑法》第359 條⑩。以上兩個法律條文對“引誘、容留、介紹他人賣淫”的行為表述范式完全一致,沒有明顯的“質”與“量”的嚴格界分,但與之相對應的處罰卻迥然不同、差別很大。又如,《治安管理處罰法》第69 條和《刑法》第364 條第2 款?。上述兩個法律條文的實質性表述相同但處罰卻截然不同。再如,《治安管理處罰法》第73條與《刑法》第353條第1款?。上面的兩個法律條文都涉及“教唆、引誘、欺騙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行為而處罰的法律依據大有差別。
(二)《治安管理處罰法》與《刑法》對特定法律術語的規定不夠明晰
任何法律術語的使用需要科學、準確,確保無歧義。但《治安管理處罰法》與《刑法》這兩部法律對有些比較接近、相似的法律術語沒有予以確當的區分。比如,一方面,《治安管理處罰法》第32條?對“非法攜帶槍支”的行為評價成行政違法。而《刑法》第128條第1款?則對“非法持有槍支”的行為評價為刑事犯罪。從法律術語的角度出發,“非法攜帶槍支”與“非法持有槍支”的法理意涵和法解釋比較接近,但在法律實踐中卻難以及時界分、甄別,進而難以及時判斷是適用《治安管理處罰法》還是適用《刑法》。另一方面,《治安管理處罰法》第51 條?對“冒充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或以其他虛假身份招搖撞騙”的行為按照行政違法論處。而《刑法》第279 條?則只是對“冒充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招搖撞騙”的行為按照刑事犯罪論處。
而值得關注的是,我國的法律條文通常使用“情節較輕”“情節嚴重”“情節特別惡劣”“數額較大”“數額巨大”“嚴重后果”等標準、尺度來區分一般違法行為與刑事犯罪,但“情節較輕”“情節嚴重”“情節特別惡劣”“數額較大”“數額巨大”“嚴重后果”等標準、尺度自身就具有一定的抽象性與不確定性,從而使得一般違法行為與刑事犯罪之間的界限存在某種模糊性。而我國《刑法》第13 條規定了犯罪定義且末尾有但書規定:“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這里的但書不僅是我國界定犯罪概念時所謂的定性+定量的模式,還是我國刑法條文中存在很多“情節嚴重”“數額較大”“嚴重后果”等“量化要素”的重要原因[6]。以此為背景,《治安管理處罰法》第51條規定的“情節較輕”與《刑法》第279 條規定的“情節嚴重”的區分標準也有待進一步明晰。顯然,哪種情況屬于“情節較輕”,而哪種情況屬于“情節嚴重”直接關乎具體處罰的力度大小。以上不同的例子均是《治安管理處罰法》和《刑法》這兩部法律的條文銜接不夠完善、存在間隙、出現張力的突出典型表現。這會導致我國公安在開展行政執法和刑事司法銜接工作時面臨困頓不安、逡巡不前的不利處境。
三、消除銜接公安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的法律條文模糊性的主要路徑
明晰行政違法與行政犯罪之間的界限是完善公安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的法律條文銜接的主要路徑。在當下,行政犯罪的法律含義相對比較明晰,即行政犯罪是指嚴重違反行政管理活動被刑法規定為犯罪的行為。我國刑法分則第三章、第六章集中規定了不少的行政犯罪。行政違法與行政犯罪的首要、根本的區別在于二者危害程度的不同,即行政違法的社會危害程度要比行政犯罪的危害程度小。行政違法行為符合一定的量、超過一定的度就會“升格”成行政犯罪。此外,行政違法與行政犯罪的不同之處還體現在二者的法律后果上,即行政違法的法律后果是行政處罰,而行政犯罪的法律后果則是行政刑罰[7]。對此,我們既要針對有關法律條文之間的內在張力進行研究,也要對于現有行政違法與行政犯罪之間的界限進行系統檢視,重新劃清二者之間的界限,推動該銜接機制的健全以及完善[8]。為此,必須有的放矢,對癥下藥,從《治安管理處罰法》和《刑法》等具體法律條文切入,以盡快實現突破。
在缺乏明晰的法律條文來消除行政違法與行政犯罪銜接存在的內在張力時,我們需要緊密結合公安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的法律實踐,找到支撐公安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的法律條文銜接的一個“阿基米德支點”(Archimedes fulcrum)。為此,既要嚴格禁止“以罰代刑”,又要嚴格禁止“以刑代罰”,即:一方面,應當禁止將已經構成行政犯罪的行為按照行政違法來懲處;另一方面,應當禁止將尚未構成行政犯罪的行為以行政犯罪論處。這樣可避免人為擴大公安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的實體范疇,繼而在源頭上有效防止公安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的法律條文出現某些異化與錯位,有助于公安全面維護國家安全、有效維持社會秩序與不斷捍衛公民合法權益。綜上所言,明晰與劃清行政違法與行政犯罪之間的界限要密切關注并著力解決以下四個層面的問題。
首先,科學合理地界定行政違法與行政犯罪的規范含義,進而保證行政違法與行政犯罪在法律條文上的有效銜接。應當以違法行為的性質、種類、情節輕重、后果輕重以及危害大小等作為衡量行政違法與行政犯罪的規范因素,既要防止“升格處罰”又要防止“降格處罰”,并確保行政違法與行政犯罪之間的規范涵義具有平衡性、協調性與妥當性。
其次,及時有效地設定行政違法與行政犯罪的制裁方式,繼而保障行政違法與行政犯罪在責任形式上的有效銜接,并保障行政處罰與刑事刑罰在責任形式上的有效銜接。在具體的法律實踐中,怎樣在諸如人身自由罰與自由刑、罰款與罰金、沒收違法所得(沒收非法財物)與沒收財產刑等制裁方式中找到一個“阿基米德支點”直接關乎公安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工作的順利進行。
再次,嚴格確定行政違法與行政犯罪的適用原則,進而保證行政違法與行政犯罪在法律實踐中的有效銜接。在學理上,當同一違法行為既違反行政法又違反刑法而發生行政處罰與刑罰的競合之際,應當堅持行政處罰與刑罰的合并適用[9]。在具體法律實踐中,合并適用直接牽涉到行政處罰與刑事處罰孰先孰后的現實問題。有學者指出,就某種程度而言,國家機關在對行政犯罪進行雙重處罰的時候,理應遵守“刑事優先”的原則[10]。
最后,解決行政違法與行政犯罪兩種法律條文的內在張力問題,可分兩部完成:先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出臺法律解釋加以解決待條件成熟時,再出臺法律修正案解決。
[注釋]:
①《最高人民檢察院、全國整頓和規范市場經濟秩序領導小組辦公室、公安部、監察部關于在行政執法中及時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意見》規定:“為了完善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相銜接工作機制,加大對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犯罪、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犯罪以及其他犯罪的打擊力度,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國務院《行政執法機關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規定》等有關規定,現就在行政執法中及時移送涉嫌犯罪案件提出如下意見……”
②在中國知網數據庫進行檢索,查找到:李和仁:《形成打擊經濟犯罪的合力——建立行政執法與刑事執法相銜接工作機制座談會述要》,載《人民檢察》2003年第12期;周騰:《行政執法與刑事執法相銜接工作機制初探》,載《廣西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5年第2期,等文獻。
③例如,以練育強為代表的學者對“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有過數量可觀的系統研究。其有關研究成果主要有:《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困境與出路》,載《政治與法律》2015 第11 期;《“兩法”銜接視野下的刑事優先原則反思》,載《探索與爭鳴》2015第11 期;《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制度重構之理論基礎》,載《學術月刊》2015 第11 期;《行刑銜接中的行政執法邊界研究》,載《中國法學》2016第2期;《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制度沿革分析》,載《政法論壇》2017年第5期,等等。
④《人民警察法》第6條規定:“公安機關的人民警察按照職責分工,依法履行下列職責:(一)預防、制止和偵查違法犯罪活動;(二)維護社會治安秩序,制止危害社會治安秩序的行為;(三)維護交通安全和交通秩序,處理交通事故;(四)組織、實施消防工作,實行消防監督;(五)管理槍支彈藥、管制刀具和易燃易爆、劇毒、放射性等危險物品;(六)對法律、法規規定的特種行業進行管理;(七)警衛國家規定的特定人員,守衛重要的場所和設施;(八)管理集會、游行、示威活動;(九)管理戶政、國籍、入境出境事務和外國人在中國境內居留、旅行的有關事務;(十)維護國(邊)境地區的治安秩序;(十一)對被判處拘役、剝奪政治權利的罪犯執行刑罰;(十二)監督管理計算機信息系統的安全保護工作;(十三)指導和監督國家機關、社會團體、企業事業組織和重點建設工程的治安保衛工作,指導治安保衛委員會等群眾性組織的治安防范工作;(十四)法律、法規規定的其他職責。”
⑤《人民警察法》第7條規定:“公安機關的人民警察對違反治安管理或者其他公安行政管理法律、法規的個人或者組織,依法可以實施行政強制措施、行政處罰。”
⑥本文所言的法律均是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的法律。
⑦一方面,我國《行政處罰法》第7 條第2 款規定:“違法行為構成犯罪,應當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不得以行政處罰代替刑事處罰。”另一方面,我國《刑法》第37條規定:“對于犯罪情節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的,可以免予刑事處罰,但是可以根據案件的不同情況,予以訓誡或者責令具結悔過、賠禮道歉、賠償損失,或者由主管部門予以行政處罰或者行政處分……”以及我國《刑法》第402條規定:“行政執法人員徇私舞弊,對依法應當移交司法機關追究刑事責任的不移交,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嚴重后果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⑧《治安管理處罰法》第2條規定:“擾亂公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權利、財產權利,妨害社會管理,具有社會危害性,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規定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尚不夠刑事處罰的,由公安機關依照本法給予治安管理處罰。”以及《治安管理處罰法》第3條規定:“治安管理處罰的程序,適用本法的規定;本法沒有規定的,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的有關規定。”
⑨一方面,《治安管理處罰法》第43條規定:“毆打他人的,或者故意傷害他人身體的,處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處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處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罰款:(一)結伙毆打、傷害他人的……”另一方面,《刑法》第234 條規定:“故意傷害他人身體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犯前款罪,致人重傷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重傷造成嚴重殘疾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本法另有規定的,依照規定……”
⑩一方面,《治安管理處罰法》第67條規定:“引誘、容留、介紹他人賣淫的,處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處五千元以下罰款;情節較輕的,處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罰款。”另一方面,《刑法》第359條規定:“引誘、容留、介紹他人賣淫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罰金;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罰金……”
?一方面,《治安管理處罰法》第69條規定:“有下列行為之一的,處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處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罰款:(一)組織播放淫穢音像的……”另一方面,《刑法》第364 條第2 款規定:“組織播放淫穢的電影、錄像等音像制品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罰金;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
?一方面,《治安管理處罰法》第73 條規定:“教唆、引誘、欺騙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處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處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罰款。”另一方面,《刑法》第353條第1款規定:“引誘、教唆、欺騙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罰金;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
?《治安管理處罰法》第32 條規定:“非法攜帶槍支、彈藥或者弩、匕首等國家規定的管制器具的,處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處五百元以下罰款;情節較輕的,處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罰款。非法攜帶槍支、彈藥或者弩、匕首等國家規定的管制器具進入公共場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的,處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處五百元以下罰款。”
?《刑法》第128條第1款規定:“違反槍支管理規定,非法持有、私藏槍支、彈藥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治安管理處罰法》第51 條規定:“冒充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或者以其他虛假身份招搖撞騙的,處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處五百元以下罰款;情節較輕的,處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罰款。冒充軍警人員招搖撞騙的,從重處罰。”
?《刑法》第279條規定:“冒充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招搖撞騙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冒充人民警察招搖撞騙的,依照前款的規定從重處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