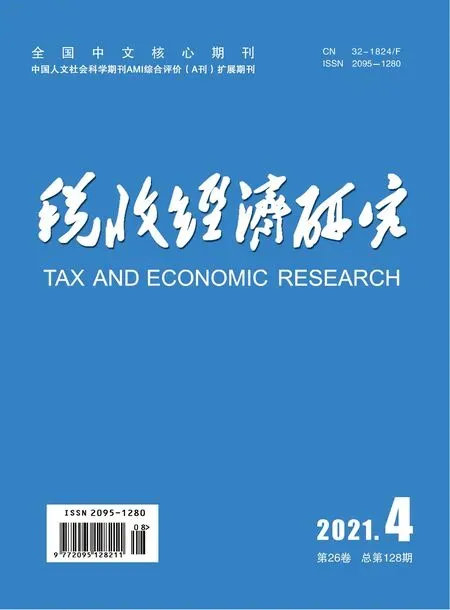混合銷售“從主納稅”制度的實然分析、應然分析及完善建議
◆王自榮
內容提要:我國混合銷售“從主(業)納稅”的制度實踐已有20多年之久,存在的不足主要有:制度安排法律效力位階過低;混合銷售的概念界定不夠準確、具體;“從主(業)納稅”缺乏對稅收公平價值的周詳考量,甚至導致稅負畸重或畸輕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增值稅法(征求意見稿)》第二十七條尚不足以克服上述后兩點缺陷。唯有在稅率法定、稅收公平和稅政效率均衡兼顧的立法價值目標約束下,設計一個例外于“分別納稅”,但又能與“分別納稅”相得益彰的“從主(項)納稅”法律規則,才是對既有混合銷售納稅制度進行增值稅立法揚棄的應然之道。為此,應樹立“從主(項)納稅”理念,借鑒域外相關立法與政策經驗,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增值稅法(征求意見稿)》第二十七條進行更為明確、具體的制度刻畫,使其更具針對性和可執行性。
為解決具有增值稅和營業稅(以下稱“兩稅”)雙重應稅特征的一項銷售行為如何納稅的難題,我國在1994年稅制改革時創設了混合銷售納稅制度。這一制度作為一種“稅法擬制性規范”,在提高征納效率、克服“兩稅”重復征收、堵塞稅收漏洞等方面有其積極作用,但在稅收公平和稅收(稅率)法定原則的貫徹上存有先天不足(葉金育,2016)。隨著全面“營改增”和國地稅征管機關合并改革的完成,造成“一項銷售”“兩稅”征納難題的舊稅制和征管體制已不復存在,混合銷售納稅制度似乎沒有“兩稅”并存時期那么重要了。但同時,我國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融合發展戰略不斷推進,服務要素在企業投入和產出中的比重不斷增加,諸如“‘產品+服務’組合包”“一體化解決方案”“混合產品”等具有混合銷售特征的交易安排,成了企業為市場競勝而創新發展商業模式的重要思維范式,這又使混合銷售納稅制度比以前顯得更加重要(郭燕和陳之昶,2020;羅建強和姜平靜,2020)。慮及上述諸因素的重疊影響,如何發揮混合銷售納稅制度的長處,規避其先天不足,又成了當前我國增值稅法律制度建設的一道難題。
一、混合銷售“從主納稅”制度的實然分析
(一)“從主(業)納稅”制度的初創樣式及首次政策調校
最早由“兩稅細則(1993)”第五條①《中華人民共和國增值稅暫行條例實施細則》(財法字〔1993〕038號)第五條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營業稅暫行條例實施細則》(財法〔1993〕040號)第五條。分別對混合銷售納稅制度作了表述不同的兩套規定,但它們的內容實質是一致的,可簡并為:混合銷售的概念界定——既涉及貨物又涉及營業稅勞務的一項銷售行為,混合銷售的納稅辦法——經營貨物或以此為主業的納稅人的混合銷售視為銷售貨物征收增值稅,其他稅納稅人的混合銷售視為提供營業稅勞務征收營業稅。由于這一辦法根據納稅人主營業務確定混合銷售征收哪種稅,所以人們在理論觀念上將它總結為“按主業征稅”(王建湘和彭彥彪,2012)。這從納稅人的角度講,即是“從主(業)納稅”。在“兩稅細則(1993)”施行后的很長一段時間內,凡發生混合銷售均應“從主(業)納稅”。為解決建筑安裝混合銷售的稅負偏重問題,《國家稅務總局關于納稅人銷售自產貨物提供增值稅勞務并同時提供建筑業勞務征收流轉稅問題的通知》(國稅發〔2002〕117號)第一條規定:“……銷售自產貨物、提供增值稅應稅勞務并同時提供建筑業勞務的,對銷售自產貨物和提供增值稅應稅勞務取得的收入征收增值稅,提供建筑業勞務收入征收營業稅。”這是我國對“從主(業)納稅”所致稅負不公問題的首次調校,也是混合銷售“分別納稅”制度的政策源頭。“兩稅細則(2008)”①《中華人民共和國增值稅暫行條例實施細則》(財政部 國家稅務總局令第50號)第六條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營業稅暫行條例實施細則》(財政部 國家稅務總局令第50號)第七條。吸收了“國稅發〔2002〕117號”文件精神,對混合銷售“分別納稅”制度做了更為明確完整的規定。自此至全面“營改增”前,混合銷售一般都應“從主(業)納稅”,但銷售自產貨物同時提供建筑業勞務等國家明確規定的“特殊混合銷售”應“分別納稅”。
(二)“從主(業)納稅”制度的全面“營改增”及再次政策調校
隨著全面“營改增”的推開,《營業稅改征增值稅試點實施辦法》(財稅〔2016〕36號印發)第四十條將混合銷售的概念修改為:既涉及服務又涉及貨物的一項銷售;將其納稅辦法修改為:經營貨物及以此等營業為主的納稅人的混合銷售按銷售貨物繳納增值稅,其他納稅人的混合銷售按銷售服務繳納增值稅;但對“兩稅細則(2008)”有關“特殊混合銷售”分別納稅的規定,《營業稅改征增值稅試點實施辦法》沒有做出任何承繼性的制度安排。此后,《關于進一步明確營改增有關征管問題的公告》(國家稅務總局公告2017年第11號)第一條進一步規定:“……銷售活動板房……等自產貨物的同時提供建筑、安裝服務,不屬于《營業稅改征增值稅試點實施辦法》……第四十條規定的混合銷售,應分別核算貨物和建筑服務的銷售額,分別適用不同的稅率或者征收率。”這既把“兩稅細則(2008)”有關“特殊混合銷售”的規定進行了“營改增”整合,又把“特殊混合銷售”剔除出了“混合銷售”陣營。與此相應,“分別納稅”也就與混合銷售無關了,凡發生混合銷售都應“從主(業)納稅”。這就是混合銷售納稅制度的全面“營改增”政策成果。由此,對諸如“運輸+貨物”“建筑+貨物”等所涉貨物與服務稅率相同的一項銷售而言,“從主納稅”規則也就無用武之地;只有那些涉及不同稅率貨物與服務的一項銷售,才是需要“從主(業)納稅”的混合銷售。這是全面“營改增”給混合銷售納稅制度帶來的最大變化。
但在全面“營改增”完成暨營業稅廢止后不久,《關于明確中外合作辦學等若干增值稅征管問題的公告》(國家稅務總局公告2018年第42號印發)第六條第二款規定:“……銷售外購機器設備的同時提供安裝服務,如果已經按照兼營的有關規定,分別核算機器設備和安裝服務的銷售額,安裝服務可以按照甲供工程選擇適用簡易計稅方法計稅。”這使得“銷售外購機器設備同時提供安裝服務”(簡稱A交易)實際上具有了和“銷售自產機器設備同時提供安裝服務”(簡稱B交易)同樣的稅收待遇。而按上述混合銷售“營改增”政策規定,A交易又屬于混合銷售,應當按“從主(業)納稅”處理。所以,上述第六條第二款和“國稅發〔2002〕117號”有著類似的政策調校功用,它使得A交易成了一種可享受更優惠“分別納稅”待遇的“特殊混合銷售”。這就是說,在現行混合銷售納稅制度下,除國家明確規定可“分別納稅”的情形(A交易)外,其他混合銷售都應“從主(業)納稅”。
二、混合銷售“從主納稅”制度的應然分析
(一)“從主(業)納稅”的先天不足
“兩稅”并存時期,銷售了貨物就應依率計征增值稅,提供了營業稅勞務就應依率計征營業稅,這是“兩稅暫行條例(1993)”的基本規定①《中華人民共和國增值稅稅暫行條例》(國務院令第134號)第一條、第二條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營業稅暫行條例》(國務院令第136號)第一條、第二條。。而混合銷售雖是一項銷售行為,但它兼具“兩稅”應稅事實特征,理應對其所涉貨物和營業稅勞務分別計征“兩稅”②就拿商場為客戶“免費送貨”來說,雖然沒有向客戶單獨結算運費,但“免費送貨”也是有對價的。因為商場只給購買自己貨物的客戶免費送貨,它不可能為購買別人貨物的買主免費送貨的。“免費送貨”是商場依約或慣例為取得貨物銷售對價而應履行的履約義務。從理論上講,只有分別核算混合銷售所涉貨物和勞務銷售額,才是對混合銷售“兩稅”計稅依據的如實反映。,可“從主(業)納稅”卻將混合銷售應征的稅率差別很大的“兩稅”視作其中之一而征收。這種為追求稅政效率價值而僭越上位階法律文本基本法旨的辦法,既缺乏對稅收法定主義價值的尊奉,又未對混合銷售應稅事實特征給予精細關照,也就難免存有稅收不公平的先天不足。具體而言,由于“兩稅”稅率差甚大,對以經營貨物為主業的納稅人的混合銷售都征收增值稅,等于對其中的營業稅勞務從高適用了稅率(增值稅稅率),造成該行為整體稅負偏重;而且所涉營業稅勞務價值比重越高(但低于貨物價值),稅負偏重越明顯。尤其是,對于以經營貨物為主業的納稅人而言,當其發生所涉營業稅勞務價值比重高于貨物價值的混合銷售的時候,也就是說,當混合銷售本身的主要經濟性質與納稅人主業(貨物銷售)不一致的時候,該等混合銷售“從主(業)納稅”的稅負畸重,形同于對該等混合銷售“錯征”了增值稅。對于主業不是貨物經營的其他納稅人而言,則恰好相反,“從主(業)納稅”會造成混合銷售稅負偏輕,甚至畸輕問題。在全面“營改增”完成暨營業稅廢止后,上述混合銷售稅負不公問題依然存在,但成因就演化成了“從主(業)納稅”與現行增值稅差別稅率制度的矛盾。在現行增值稅法律制度體系中,《中華人民共和國增值稅暫行條例》為法律效力位階最高的法律文本,其中第二條為貨物、服務、不動產、無形資產等不同課稅項目規定了相應的稅率。按這種分別不同課稅項目而確定稅率的立法意旨,只要納稅人發生涉及不同稅率應稅項目的應稅行為,就應當“分別納稅”——分別不同課稅項目(銷售額)依率計算納稅,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增值稅暫行條例》(2017)第二條自身內涵的稅率適用基本要求,更是稅率法定原則在增值稅差別稅率制度適用層面上的具體貫徹。在這個意義上,諸如“從主(業)納稅”、與“分別納稅”相左的、法律效力位階較低的稅率適用制度安排,都構成對增值稅差別稅率制度法定意旨的背離。這種背離在增值稅稅率差作用下,如果致使混合銷售稅負偏重,于納稅人不利;如果恰好相反,形同于國家稅款流失。當征納實踐中出現稅負明顯偏重或偏輕的混合銷售,就會導致“從主(業)納稅”與增值稅差別稅率制度之間矛盾的加劇。在這種矛盾沖突中,偏于追求稅政效率價值的“從主(業)納稅”辦法,就會因背離稅率法定原則且致使稅負明顯不公而喪失其必備的稅法正義;此時,國家就不得不通過政策調校,使那些因“從主(業)納稅”而稅負明顯不公的混合銷售回歸到“分別納稅”。這種調校和回歸在我國混合銷售納稅制度演進過程中的反復出現,正是增值稅差別稅率制度對“從主(業)納稅”的調校力在制度運行中反復作用的結果。
(二)“從主(項)納稅”優于“從主(業)納稅”
誠然,依據增值稅差別稅率制度所內含的稅率適用法則,納稅人發生混合銷售都理應分別納稅。但現實經濟活動中確實存在一些混合銷售,若對它們采取在整體上按其所涉主要項目納稅的辦法(“從主(項)納稅”),會取得稅政效率和稅收公平兼顧雙贏的效果。比如,在電商營銷中頻繁發生、大量存在的“購貨免運費”式銷售,它們所涉貨物和服務依約定或商業慣例須一起提供給客戶,且具有經濟上的主輔關系——一項(比如運輸服務)是為輔助、促進另一項(比如貨物)的銷售得以更好實現,一項的單獨售價明顯小于另一項,甚至從納稅人(銷售方)的角度都可以不計較(比如免費),故而往往以單一對價結算。對于這樣的混合銷售,“從主(項)納稅”與“分別納稅”的稅負相差無幾,至少無明顯差別;對它們采用“從主(項)納稅”辦法,不會因背離增值稅差別稅率制度而產生稅負偏輕或偏重問題,至少不會出現混合銷售自身主要經濟性質與納稅人主業不一致時的那種稅負畸重或畸輕問題,這對納稅人權益和國家稅收都不失公平,且可明顯節約納稅成本①對“購貨免運費”這樣的應稅行為,“分別納稅”在實務操作上要比“從主項納稅”復雜,比如要進行對價分攤、分別計算納稅等會增加納稅核算成本,再者對價分攤很容易引發納稅人對低稅率計稅依據的操縱,這又需要更多的稽征成本。,也有利于防杜納稅人“把高稅率應稅項目銷售額往低稅率應稅項目轉移”的逃稅、避稅行為。同理,對于不符合現行混合銷售概念規定的其他類似應稅行為,比如涉及不同稅率貨物的一項銷售,只要它們所涉不同稅率貨物在經濟上具有主輔關系,對其按“從主(項)納稅”處理,也可節約征納成本而不減損稅收公平價值。可見,在稅收公平和稅政效率兼顧均衡的價值目標約束之下,不管是現行制度規定的混合銷售,還是其他涉及不同稅率課稅項目的一項銷售(以下稱“類混合銷售行為”),所涉課稅項目存在經濟上的主輔關系,是它們能成為“‘從主(項)納稅’應稅行為”的必備經濟事實特征。比如,加拿大有關“‘從主(項)納稅’應稅行為”的規定為:“為單一對價和特定貨物或服務一起提供且附助于特定貨物或服務的任何其他貨物或服務,應視作所供應特定貨物或服務的構成部分。”②加拿大司法部:《消費稅法(合訂本)》。澳大利亞把“‘從主(項)納稅’應稅行為”稱為“復合供應”(Composite Supply),即“主要供應部分和其所需要的、所附帶的或附助于主要供應部分的東西,一起構成一項供應”。③澳大利亞稅收辦公室:《貨物和服務稅規則2001/8》。歐盟法院在CPP(Card Protection Plan)一案的裁定中指出,把主要項目與其輔助項目一起提供給客戶構成單項供應,其中的輔助項目本身不是客戶需求的目標,只是客戶利用主項供應的助益手段。④英國海關稅務署:《VAT供應和對價》。與上述澳大利亞增值稅政策、歐盟判例裁定相比,加拿大的規定強調了“單一對價”條件,這等于說,購銷雙方為不同應稅項目分別約定了對價的一項銷售無需“從主(項)納稅”。所以,加拿大“‘從主(項)納稅’應稅行為”的范圍相對更小一些,在制度運行過程中出現稅負明顯不公問題的可能性也就更低一些。在這一點上,加拿大的做法更值得借鑒。相較而言,我國對混合銷售概念的定義(“既涉及服務又涉及貨物的一項銷售”)確實不盡如人意。一是,對混合銷售的種差規定不準確、不完整。“既涉及貨物又涉及服務”這一定語,僅是說明了貨物和服務有某種關聯關系,并未明確這種關聯關系應是經濟上的主輔關系,這會使一些應“分別納稅”的混合銷售反而要“從主納稅”,形同于不恰當地拓寬了混合銷售的應有外延,上述兩次政策調校便是例子;此外,沒有考慮“類混合銷售行為”發生的可能性,未能將一些適合“從主納稅”的應稅行為包涵在混合銷售應有外延之中,比如售賣書包附贈小畫冊等。二是,把“一項銷售”作為混合銷售的屬概念,但“一項銷售”本身是個內涵和外延都具有伸縮性的商業用語,混合銷售也就成了一個自身歸屬都含混不清的概念。比如,同一客戶在同一超市支付一筆款項同時購買了圖書和啤酒,這也能說是“一項銷售”,但這要作為兩項(圖書和啤酒)銷售、“分別納稅”的兼營行為。鑒于混合銷售概念內涵和外延界定上的缺陷,若再延續現行混合銷售概念界定的既有思維,不但不能反映“‘從主(項)納稅’應稅行為”內涵和外延的應然,而且必會引起“從主(項)納稅”適用上的錯亂和爭議。在這一方面,我國稅收理論與實務界關于混合銷售與兼營行為的辨析與討論就一直沒有停止過(譚偉等,2019)。
三、混合銷售“從主納稅”制度的完善建議
“為鞏固‘營改增’成果,延續‘混合銷售’從主納稅的理念,明確混合銷售應從主適用稅率或者征收率”⑤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增值稅法(征求意見稿)>的說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增值稅法(征求意見稿)》(以下稱《征求意見稿》)第二十七條(簡稱“第二十七條”)規定,“納稅人一項應稅交易涉及兩個以上稅率或者征收率的,從主適用稅率或者征收率”。這將混合銷售稅率適用問題上升到了法律層面,革除了以往混合銷售納稅制度法律效力位階低于增值稅稅率制度的弊端。另外,第二十七條所說“一項應稅交易涉及兩個以上稅率或者征收率的”情形,其實就指涉及不同稅率應稅項目的一項銷售。這不僅包涵了涉及不同稅率貨物和勞務的一項銷售,還將上文所說“類混合銷售行為”納入其中,從而擴大了“從主納稅”的適用范圍,克服了現行混合銷售概念外延不完整的弊端。但第二十七條沒有完整揭示出“‘從主適用稅率…’納稅”應稅行為(應稅交易)的必備應稅事實特征,也沒有對“一項應稅交易”(一項銷售)的主要特征做出應有描述。這使得第二十七條后半句話在語言邏輯上缺乏說明“從主”的“主”應是什么的足夠事實條件。第二十七條本當明確“從主”的“主”應為交易“主項”,卻未能明確(李旭紅,2020)。所以,第二十七條雖然鞏固和拓展了混合銷售納稅制度的“營改增”成果,但尚未完全脫離現行混合銷售納稅制度的窠臼。若付諸實踐,不但不能實現稅收公平與效率兼顧的立法價值目標,而且會放大“從主(業)納稅”先天不足的影響范圍,與此相關的稅負不公問題會增多,從而導致《征求意見稿》第十三條和第二十七條之間張力的增強,與上文所說政策調校性質類似的修法問題就在所難免,第二十七條立法的穩定性、預期性和權威性也就難以保障。
通觀“營改增”前后的增值稅稅率制度和《征求意見稿》第四章規定,除增值稅征收率外,國家確定增值稅差別稅率的基本依據是課稅項目的不同。這既沒有考慮納稅人經營方式是否兼營的影響,也沒有考慮納稅人應稅行為方式是否混合銷售的影響。所以,不管《征求意見稿》第二十六條所說“適用不同稅率或者征收率的應稅交易”(“兼營行為”),還是第二十七條所說“涉及兩個以上稅率或者征收率的”“一項應稅交易”(“混合銷售”),在《征求意見稿》第四章中,它們都是涉及不同稅率課稅項目的應稅交易,都應當“分別納稅”。這是國家確定增值稅差別稅率制度的基本立法意圖。像“從主納稅”這樣的與“分別納稅”相左的稅率適用制度安排,確實可增進稅政效率價值,但可能會因背離增值稅差別稅率制度意旨而引發稅負明顯不公問題,傷及納稅人權益或國家稅收利益。在這個意義上,唯有以稅收(稅率)法定、稅收公平和稅政效率均衡兼顧為制度質量基準,設計一個例外于“分別納稅”,但又能與“分別納稅”相得益彰的“從主(項)納稅”法律規則,當是我國混合銷售納稅制度建設的應然之道。其中最為關鍵的是,對適合于“‘從主(項)納稅’應稅行為”必備經濟事實特征的制度刻畫,這要力求“明確、具體,具有針對性和可執行性”。為此,筆者建議,放棄“從主(業)納稅”理念,樹立“從主(項)納稅”理念,在正式立法時,可考慮將《征求意見稿》第二十七條改為:“納稅人為單一對價將在經濟上具有主輔關系的不同稅率或征收率應稅項目一起銷售的,從其主項適用稅率或者征收率,依法計算納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