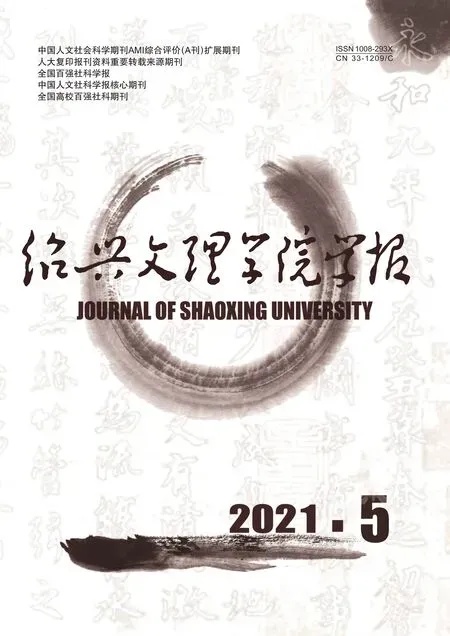論明清之際華夏道統的承續危機與屈大均對屈氏宗族精神的建構
王富鵬
(廣州大典研究中心,廣州大學 廣府文化研究中心,廣州 510623)
屈大均將自己的血統上溯至屈原,梳理出沙亭屈氏大致的世系,并特別強調沙亭屈氏對屈原忠騷精神的繼承,表現出強烈的追尋家族之根和建構家風宗訓的意識。這一行為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尋根問祖,更不是簡單地攀附高貴血統。明末清初天崩地解之時,屈原是一個具有特殊意義的精神符號。歸莊《九日過普濟寺養疴》詩云:“《離騷》讀罷鐘初歇,支枕長吟夢不成。”[1]歸莊是曾經秘密抗清的志士遺民。閻爾梅為了抗清也是奔走流離,詩云:“痛飲讀騷門閉住,西園花下即深山”[2]460;又云“走到君家須痛醉,雞鳴猶自唱《離騷》”[2]462。屈大均《樊義士墓志銘》云:布衣樊潔“每遇霜黃木落,風雨晦冥之候,人未嘗不聞其哭泣。朗月之夕,或歌《蓼莪》,或誦《離騷》《山鬼》。其聲悲酸凄楚,斷續于幽林激瀨之中,嗚嗚不止”[3]368。由這幾個例子即可大體知其一二了,此不贅述。
因此,在這一時期,屈大均將自己的血統上溯至屈原,并表現出強烈的對家族之根的追尋和家風宗訓的建構意識,就具有了特別的意義。他梳理出了沙亭屈氏大致的世系,并著《閭史》一書,特別強調沙亭屈氏對屈原忠騷精神的繼承。這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尋根問祖,更不是簡單地攀附高貴的血統,其中包含著基于時代巨變的深刻的文化意義。
一、明末清初遺民的亡天下之憂
明末天崩地解的巨變對當時士人的心理產生了巨大震撼。在當時看來,明亡清興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朝代更迭、一姓王朝的亡國。明祚移易,是華夏治統的喪失,繼之而失的可能是華夏道統和學統。如此,明末天崩地解導致的是天下之亡,而非一國之亡。
清軍入主中原,華夏民族走到了亡天下的關鍵時刻。華夏道統、學統乃至華夏文脈的存續確實面臨著嚴峻的考驗。當時士人中的優秀者清醒地意識到了這一問題,所以顧炎武驚呼“亡國與亡天下”有辨(1)顧炎武《日知錄》卷十三《正始》云:“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于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梁啟超將其概括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屈大均說:“南昌王猷定有言,古帝王相傳之天下至宋而亡。存宋者,逸民也……今之天下,視有宋有以異乎?一二士大夫其不與之俱亡者,舍逸民不為,其亦何所可為乎?”[3]394在當時有這種意識的豈止顧、屈等人。其他人雖然沒有明確說出,但不少人的心中也隱約地存在著這樣的意識。孔孟“以夷變華”(2)《孟子·滕文公上》“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于夷者”,《論語·憲問》“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都傳達了“以夷變華”的擔憂。之憂,當時稍有知識的人都應該知道,這也許就是明末遺民為數眾多的原因之一。他們堅守的并非僅僅不仕二姓的君臣觀念,他們堅守的更是華夏民族的道統和文脈。
在普通人眼中,身處草野的遺民近于至輕至賤的匹夫,豈足以承擔如此大任?屈大均曰:
嗟夫,逸民者,一布衣之人,曷能存宋?蓋以其所持者道,道存則天下與存,而以黃老雜之,則亦方術之微耳,烏足以系天下之重輕哉!……世之蚩蚩者,方以一二逸民伏處草茅,無關于天下之重輕,徒知其身之貧且賤,而不知其道之博厚高明,與天地同其體用,與日月同其周流,自存其道,乃所以存古帝王相傳之天下于無窮也哉。嗟夫,今之世,吾不患夫天下之亡,而患夫逸民之道不存。[3]394
這段話為當時的遺民找到了超出傳統不仕二姓的新的理論支點,宣明了許多遺民隱微的心理,對遺民存在的意義作出了關乎天下興亡的價值判斷。
這些遺民身伏草野,似乎微不足道,但也正是這些遺民一定意義上在特殊的時代肩負起了保存華夏文化、華夏文脈的重任。“天以布衣存日月,海濱山閣著藏書”[4]430,屈大均就是這樣一位自覺肩負起保存華夏正統文化的遺民。
屈大均等相信“道存則天下與存”,所以“夫使天下之人,盡紀忠臣孝子之事于心,而圣人之道行矣……故其言曰,大宋以有疆土而存,不以無疆土而亡……嗟乎,君子處亂世,所患者無心耳。心存則天下存,天下存則春秋亦因而存。不得見于今,必將見于后世”[3]320。他所謂的道是指代表華夏正統文化的儒學。“其所持者道,道存則天下與存,而以黃老雜之,則亦方術之微耳,烏足以系天下之重輕哉!”[3]394在他看來,黃老之學乃方術之微,不足以系天下之重,佛學更為外夷之學,并對明末清初佛教的極度興盛表示不滿。屈大均《歸儒說》:“予二十有二學禪,既又學玄。年三十而始知其非,乃盡棄之,復從事于吾儒。蓋以吾儒能兼二氏,而二氏不能兼吾儒。”[3]123他認為儒學乃華夏文化的精髓,“若逐二氏而棄儒”,則華夏文化將失其傳承,“亡天下”的悲劇將不可避免。
屈大均早年為避難一度為僧,三十歲后不避人們非議而逃禪歸儒,正是基于他的這一思想。“予弱冠以國變托跡為僧,歷數年,乃棄緇服而歸。”[3]174他不但逃禪歸儒,而且還潛心研究儒學;不但精研《周易》,寫成了《翁山易外》,還與何磻一起撰作了《四書補注》和《四書考》。朱希祖云:“屈、何二公考證《四書》之作,不事空言。”[5]屈大均之所以要考注“四書”,精研《周易》,不僅僅是出于對學術研究的興趣,應該還緣于以上所述“圣人之道”與華夏治統的關系。
二、屈原忠騷與華夏道統和學統
屈大均字“泠君”,號“華夫”。“華夫”二字,其意比較直白,華夏偉丈夫之意;“泠君”二字,則是為了音諧屈原“靈均”之號。他在《自字泠君說》一文中說:
其音與靈均相似,予為三閭之子姓,學其人,又學其文,以大均為名者,思光大其能兼風雅之辭,與爭光日月之志也。又以泠君為字,使靈均之音長在于耳,人一稱之不惟使予不忘靈均,亦使天下之人不忘靈均,斯予之所以為慈孫之心也。昔司馬長卿辭賦最盛,乃三閭之高弟子,然其名不以三閭而以藺相如,徒學三閭之文,不學其人,吾嘗以為大憾。吾三閭之子姓也,文可以不如三閭,并可以不如長卿,而為人則不可以不如三閭,而如長卿。噫嘻!自今以往,其益以修能為事,以無負茲內美,斯于高陽苗裔有光也哉![3]127
屈大均取字“泠君”,號“華夫”,是否有意義上的關聯呢?二者之間的關聯屈大均在作品中有所闡述,此不贅。
《三閭書院倡和集序》云:“《離騷》二十有五篇,中多言學,與圣人之旨相合。其有功《風》《雅》,視《卜序》《毛箋》為最。惜孟氏與之同時,知《詩》亡而《春秋》作,不知《詩》亡而《離騷》作。一鄒一楚,彼此竟未同堂講論也。”[3]284又曰:
《離騷》二十有五篇,中多言學,與圣人之旨相合。其曰:“壹氣孔神,于中夜存,虛以待之,無為之先。”又曰:“超無為以至清,與太初而為鄰。”此非孟氏養氣之說耶?不與大《易》保合太和,窮神知化為一貫耶?司馬遷采《懷沙》之篇以入列傳,豈非以“人生有命,各有所錯,死不可讓,愿勿愛兮”數語,又有當于《易》所謂“盡性以至命者”耶?朱子箋注六經四子,即為《離騷》作傳,亦以其學之正,有非莊老所及,而豈徒愛其文辭能兼《風》《雅》與其志爭光日月耶?……孫文介云,《離騷》首稱帝嚳,次堯舜,又次湯武,諄諄祗敬之意,至述死生之際,廓然世外,清凈溘居,非大有道術者不能發。嗟夫,此皆求三閭于道,而不徒求之于忠愛纏綿,哀怨悱惻之中者也。按《史記》,“帝嚳溉執中而遍天下”,夫中之象,天以《河圖》垂。伏羲以八卦則,而后神農、黃帝演之,以至于帝嚳。而堯以允執之而命舜,則堯之學,得之于帝嚳矣。三閭能溯厥淵源,推明授受之所自,則三閭亦得統于帝嚳,無墜其精一之道者。今徒以其善于騷些,驚采絕麗,為可直繼《風》《雅》,抑何得末而遺其本也哉!大抵古之圣賢,多以詩言道,見于三百五篇者,不一而足。《離騷》雖出忠憤,而所言皆至道閫奧,往往極乎廣大,盡乎精微,發三百五篇之所未發。故漢代詞人尊之為經,以與六藝并行于天壤,而獨憾仲尼未及見,不得取而刪定之,以補楚國之《風》也。今學士大夫,讀《離騷》者,而忠者得其忠,文者得其文,蓋自宋玉、景差、唐勒以至今茲,大抵皆三閭之弟子矣。然而師其文當師其學,師其學焉,而以之事父事君,知天知人,同死生,盡性至命,非即所以學夫《詩》耶?予之為三閭書院也,與二三同志,稱《詩》說《易》于其中。惟日孜孜,不敢負其家學,在三閭末胄,分當云爾。[3]282-283
屈大均認為屈原“能溯厥淵源,推明授受之所自”,得統于三皇五帝等華夏上古圣賢之學,是傳承華夏道統學統的偉大詩人。由此可以看出,屈大均視屈原為自己血緣和精神上的祖先,除了因為其本姓為屈和屈原的忠騷精神之外,還在于屈原之學與華夏上古文化、華夏道統學統的一脈相傳。
其他相近的說法還有不少。“天地之文在日月,人之文在《離騷》,六經而下,文至于《離騷》止矣。”[3]47“三閭其亦儒之醇者與!司馬遷作傳,獨采《懷沙》一篇,又以‘知死不可讓,愿勿愛’數言,誠《離騷》之正終,儒者之極致,與《易》之所謂盡性以至命一道者也。”[3]189屈大均認為孔子之后,華夏道統學統的繼承者,屈原可與孟子并稱。他的這些表述把屈原在華夏道統上的地位提升到了一個空前的高度。其《孟屈二子論》云:
孟子生戰國時,所言必稱堯、舜,屈子亦然。孟子精于《詩》《書》《春秋》,所言必稱三經,屈子亦然。《離騷》諸篇,忠厚悱惻,兼《風》《雅》而有之。《風》《雅》,經也;《離騷》,傳也,亦經也。其有功于三百篇。視卜氏《序》,端木氏《說》為優。惜孟子與之同時,知《詩》亡而《春秋》作,不知《詩》亡而《離騷》作。[3]120
由以上所述可知,在屈大均看來,屈原不但承續了華夏道統和學統,而且是那個時代可與孟子并稱的大儒,屈原忠騷是華夏道統學統的最純正的一部分,輝耀著當時和后世。
三、忠騷傳統與屈氏宗族精神
后人常以“忠愛”或“忠騷”概括屈原的精神。“忠愛”比較容易被普通人理解和接受,也更容易把抽象的精神上升到行為的層面。在屈大均看來,“忠愛”“忠騷”精神屬于華夏道統學統的一部分,這種精神也為其屈氏宗族所長期秉持。
朱明一代,沙亭屈氏曾一度輝煌;滿清至今,沙亭屈氏已大不如昔,其“屈氏大宗祠”已經變得空空蕩蕩,沒有片言只語與其宗風族訓有關。盡管如此,我們也不能否認其宗風族訓的存在。屈大均的著作不但多處談到有關內容,而且還透露出建構其宗風族訓的意圖。屈大均涉及屈氏家族的很多文章都或隱或顯地突顯了屈氏族人的作為與屈原忠騷精神的關聯,而屈原忠騷似乎也成了貫穿屈氏族人千余年的最主要的精神。不管其家族歷史如何,屈大均在文章中事實上已經表現出了試圖以屈原忠騷為核心構建屈氏宗風的努力。
屈大均在試圖建構其宗風族訓的時候,也在努力勾畫著沙亭屈氏的世系。屈大均勾勒的沙亭屈氏的譜系雖然與其兄士煌所述還存在個別齟齬之處,但大體上已形成了一個較為清晰的輪廓。就保存至今的文字而言,在屈大均之前,沙亭屈氏沒有哪一個人比他懷有更強烈的構建沙亭屈氏譜系的愿望。追溯宗族的來源,構建宗族的譜系,這固然源自于人們尋根的內在需要,但屈大均這一強烈的表現卻是個值得探討的問題。這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即是上文所論時代巨變所導致的亡天下之憂。
屈大均對原來的屈氏族譜進行了整理,易名為《閭史》,且又“采古之屈氏知名者,自春秋至明千余年,凡得五十余人,各為列傳,系以論贊”3[46]。《閭史》雖已失傳,但通過《閭史自序》一文,大體可以看出他所勾勒的沙亭屈氏的源流:
考屈氏之先,出自楚武王子瑕,瑕受屈為卿,因以為氏,瑕者屈氏之始祖也。自瑕而下,屈氏之知名者,見于《左傳》、《國語》、《國策》、諸子,凡若而人,而三閭大夫作《離騷》,僅述其皇考伯庸,而不及其祖,僅稱其姊女媭,而不及其兄弟子姓,至今考求屈氏人物者,輒以為憾。然以三閭大夫之忠,未必無后,安知漢高帝所遷屈、景、昭、懷四族于關中者,無三閭大夫之子孫在其中耶?吾番禺屈氏,當宋南渡時,有祖迪功郎諱禹勤者,實從關中來,始居沙亭,今至予十有八世,不知迪功郎之祖何人,或即三閭大夫之后未可知,要之皆楚之同姓,帝高陽之苗裔云爾。沙亭之屈故有譜,以迪功郎為始祖,自始祖至予曾從孫,凡二十一世。其譜曰《南宗屈氏家乘》,吾易其名曰《閭史》,而采古之屈氏知名者,自春秋至明千余年,凡得五十余人,各為列傳,系以論贊,以冠《閭史》之首,并為古今屈氏世系,俾吾家子姓有所考焉。[3]46-47
可以看出他實際上并沒有真正考出始祖至其本人確切連續的世系,他所勾勒的世系只是一個大體輪廓。因屈原子孫無考,不能肯定屈大均與屈原之間是否存在直接的血緣聯系。然而,正因無考,更不能排除他們之間有直接血緣關系的可能。屈大均在其他文章中也同樣表達了這樣的意思,同樣突出了屈原在屈氏血統上的崇高地位。屈大均突出屈原在屈氏血統上的地位,并非僅僅出于血統攀附,更重要的還在于他試圖以此來達成他與屈原之間在道統學統和文統上的鏈接。如果論地位,屈氏始祖楚武王子瑕的地位要遠遠高于屈原,而屈原只是懷王手下一個被排擠打擊的失敗的政治人物。
如上所論,屈原承繼了自三皇五帝以來的華夏道統和學統。屈大均所說的這種道統和學統在屈氏后世子孫中,是否得以延續呢?可惜的是屈大均整理的《閭史》及其五十余人的列傳和論贊我們不能看到了,可以相信屈大均撰寫的《閭史》以及五十多人的列傳和論贊一定會有比較明確的關于宗風族訓的表述。雖然看不到《閭史》中明確的世系圖表和對五十余人的敘述和論贊,但通過屈大均的其他文章,我們還是可以大體梳理出屈氏的宗族世系和屈氏人物對屈原忠騷精神的繼承。
現在能夠見到的屈大均筆下的屈氏族人,屈原之后,即是唐代的屈政,再后即是沙亭屈氏始祖迪功郎屈禹勤。其《西屈族祖姑韓安人遺詩序》云:
考吾屈自漢高帝遷之關中,于是關中多屈氏與昭、景、懷三貴族及齊諸田,皆猶稱王孫。傳至有唐,吾屈有節度使諱政者,自關中來,始居梅嶺之南。南宋時,其孫迪功郎誠齋又遷于番禺沙亭,今子姓千有余人,輒稱三閭大夫之裔,復號為南屈,以別于關中之西屈。[3]82-83
按照此文的說法,唐代屈政已經自關中遷至“梅嶺之南”。雖然看不到屈政秉承屈原忠騷精神的有關敘述,但他官至節度使,保一方安定,我們姑且可以假定他是忠于朝廷的封疆大吏,進而說他秉承了屈原的忠愛精神。
之后其孫迪功郎屈禹勤遷至番禺沙亭。“沙亭在番禺茭塘都,吾始祖迪功郎誠齋當宋徽宗時,來居于此。其地濱扶胥江,多細沙。又念先大夫懷沙而死,因名鄉曰沙亭。”[3]472屈士煌也說“先世翰林誠齋公卜居沙亭”[6]7。屈大均《存耕堂稿序》曰:“祖翰林誠齋公,當宋南渡時,公從祥符珠璣巷來,止南雄,其巷亦名珠璣,已而復遷沙亭。”[3]67屈禹勤既為翰林,又官居迪功郎,二者并不矛盾,其身份可以是重疊的。南遷的具體時間,雖然幾處文獻有一定的出入,如:“宋徽宗時”“當宋南渡時”“蓋宋紹興間”和“南宋”等,但綜合之后,還是可以大體得出一個比較合理說法:被視為南屈之祖的屈禹勤在兩宋之交遷至番禺沙亭。雖然屈禹勤在“梅嶺”“祥符”“珠璣巷”之間如何往復,最后遷至“沙亭”時的具體細節我們不得而知,但屈禹勤在宋室南渡這一大背景之下,隨王室而南遷,再遷至番禺沙亭本身,就一定程度上可以確認他對朝廷的忠誠。因“念先大夫懷沙而死”,而名遷入地為“沙亭”,更可見出他對屈原忠騷精神的刻意繼承。
有明一代,沙亭屈氏真正成了當地的一大豪族,且與南海神廟關系非常密切。屈大均《廣東新語·神語》“南海神”條記載:
南海神廟,在波羅江上,建自隋開皇年。大門內有宋太宗碑,明太祖高皇帝碑……廟向無祭田,宣德間,吾從祖蘿壁、秋泉、南窗三公,始施田六頃六十八畝,在波羅海心沙東馬廊、西馬廊、深井、金鼎、石魚塘,田乃潮田,歲一熟,淤泥所積,子母相生,今又增數頃矣。廟中有道士一房,僧二房,收其租谷,歲仲春十二、十三日,有事于廟,蘿壁子孫主道士,秋泉、南窗子孫主于僧,予從兄士煌有碑志其事。而吾鄉沙亭與廟僅隔一江,一舸隨潮,瞬息可至,以有祭田之供,輒視之為家廟焉。而沙亭亦有南海離宮,高曾之所俎豆,靈怪之所憑依,世修其祀罔或懈。蓋生乎南海之上者,祠南海;生乎南巖之下者,祠南岳,亦庶民之禮也,非僭也。[4]186-187
仲兄屈士煌對此事的記述更為詳細:
先是,明宣廟中,吾十世祖名原裔號蘿壁、十一世名鑒號秋泉、十二世名懷義號南窗同謁神,歸而相告,語曰:“神之赫濯甚矣。祀典隆鉅,固無以加,然有祠千余年,而竟乏一石之租、三畝之稅。朝廷禋祀而外,歲中四時薦享、牲腯蕭脂之費何出?奉祀事、司灑掃、代嘏祝者衣食奚資?即四方賓旅游觀者饔飧酒茗胡給?”于是各蠲田若波羅海心沙、東馬廊、西馬廊、北山田共五頃六十余畝以供祀事。以廟之羽士司其籍,列田形、稅畝、冊籍、條約,勒石于左廡下。蓋宣德四年己酉二月庚子也……吾族自三祖施田以來,神日降庥,于(應為“子”,形近而誤)弟多能沐詩書之澤,翱翔顯于世。自鼎革后,兵燹頻仍,舊碑苔蘚,其田亦多蕪沒不治。于是族之紳耆文學請于當事,俾浮屠黃冠交司,其租稅之出入,雖吾子姓毋得越俎焉,示公也。嗚呼!巢許讓天下,而市道細人至于較銖錙!今有人割不訾之膏壤,以薦馨于神,乃有耽耽逐逐,竊神脂以自潤,寧不愧于心歟!茲者田以漸治,祀以益修,僧道交司之說,久而不變可也。其田廣長短狹詳見《廟志》……雖然祖宗之基業,保持之責在賢子孫,而神則猶眾人之父母也。然則斯田興替,凡在廟中者皆與責焉,豈吾屈氏私言哉。”[6]7
崔弼云:“屈公祠在廟門內東北,祀番禺沙亭鄉屈原裔、族子屈鑒、族孫屈懷義,皆舍田以供祀事者。”[7]屈大均以蘿壁、秋泉、南窗三人為己之從祖,而其仲兄士煌認為蘿壁(屈原裔)為十世祖、秋泉(屈鑒)為十一世祖、南窗(屈懷義)為十二世祖。有人認為“屈大均筆下元末明初的十世祖野藪翁、十一世祖聽泉翁、十二世祖滄州翁所指即屈士煌《南海廟施田記》中宣德間的十世祖蘿壁公、十一世祖秋泉公、十二世祖南窗公”(3)見林勰宇《番禺沙亭屈氏家族南海廟施田考》,《中國地方志》2016年第12期。按:屈大均筆下其直系第十、十一、十二世祖分別是野藪公(諱璲)、聽泉公(諱鈺)、滄洲公(諱渶)。相對應者,號不同,名諱亦相不同,故林氏之說可能有誤。沙亭屈氏族人屈巨賢告訴筆者秋泉與聽泉為同輩兄弟。。不管兄弟二人誰的記載發生了錯位,都不影響這一事件的真實性和后人的論述。屈大均《南海神祠碑》又云:
南海神祠在吾鄉沙亭之東。國朝洪武初,吾十世祖埜藪公諱璲之所建,以南海神主祠在扶胥北岸,而吾鄉在南岸,大江相隔不能朝夕常至,故作此祝融行宮,與室廬咫尺,可以勤勤肅謁焉。三百年來,子姓世修其祀,祈年則以為先嗇,請子則以為高禖……祠向無碑,歲甲辰之吉,族人某某者,撤而新之,以光神明之德,以昭祖考之誠。[3]339
修建或捐錢給寺廟,在現代人看來也許只是出于個人祈福于神的行為,但在古人看來卻不大一樣。屈氏家族傾巨額家產給南海神廟,且修建神祠,雖然會有私人計慮的可能,但就當時普通百姓的信仰來說,也許可以稱得上是遂民之愿、造福民眾的功德。正如翁山所云“生乎南海之上者,祠南海;生乎南巖之下者,祠南岳,亦庶民之禮也”[4]187。如果這樣的推論合理的話,明代屈氏族人的作為也可以說沒有背離屈原的忠愛精神。因為屈原的忠愛不僅愛君,也應包括愛民在內。
屈大均的筆下,屈氏其他族人同樣也秉承了屈原的忠騷忠愛精神。屈大均《懷沙亭銘有序》一文云:
吾之鄉名曰沙亭,先祖迪功郎誠齋之所命也。往陳白沙先生嘗至沙亭,主于吾從祖博翁之家,博翁之子青野師事之。先生以博翁為三閭同姓,每舉《遠游》之篇,“壹氣孔神,于中夜存,虛以待之,無為之先”。四語為博翁言,而先生亦嘗有得真于“亥子之間,求中于未發之前,致虛以立其本”之語,辭旨與三閭一致,蓋白沙之學得于三閭,三閭其亦儒之醇者與!司馬遷作傳,獨采《懷沙》一篇,又以“知死不可讓,愿勿愛”數言,誠《離騷》之正終,儒者之極致,與《易》之所謂盡性以至命一道者也。予今為學,即以三閭之言為師。師三閭所以學夫白沙,其淵源殊不二也。聞昔有汪提舉者,嘗筑亭海北,名曰懷沙,蓋懷夫白沙也。吾今竊取其意,亦筑懷沙之亭,一以不忘吾鄉,以不忘吾祖;一以不忘白沙,以不忘三閭。[3]189
陳獻章有得于屈原之文,又以之教授屈氏族人。屈大均《廣東新語·人語》“吾祖多壽人”條云:
吾先世人多壽考,有聽泉翁者,年八十余,以耆儒為鄉黨師。梁文康公儲銘其墓曰:“剛毅正大由天成,縝純溫潤鍛煉精,考槃在澗王侯輕。”……子滄洲翁,諱渶,年八十余,有嬰兒之慕;孫梅侶翁,亦年八十余,皆以齒德,屢舉鄉飲不赴,此吾之高曾也。[4]210
屈大均通過陳白沙這一中介把屈氏族人與屈原之學乃至華夏道統和學統勾連在了一起。文中的幾位屈氏先祖皆是道德純粹的賢者形象。
到了明末清初,在屈大均筆下,屈氏家族更涌現出一些可歌可泣的人物。對屈氏兄弟來說,似乎重現了其遠祖屈原一樣的時代變局。屈士燝、屈士煌、屈士泰、屈大均等屈氏兄弟面對這一天崩地解的變局,秉承著其遠祖屈原的忠騷忠愛精神,追隨南明,至死不悔。自幼,父親的教誨就已經深植屈大均心中了。《先考澹足公處士四松阡表》云:
先考諱宜遇……幼遭家多難,寄養于南海之邵氏,嘗以魏恭簡公本姓李氏冒莊渠魏氏,歷三世而不能復,以為不孝之大。故公年四十有八,以不孝孤大均初補諸生,即攜歸沙亭謁廟,復姓屈氏……有暇,輒飲酒鼓琴,讀醫書,與經史百家相間。課大均至嚴,日誦不問何書,必以數千言為率,親為講解,弗以諉之塾師也。家貧,每得金,必以購書,謂大均曰:“吾以書為田,將以遺汝。吾家可無田,不可無書。汝能多讀書,是則厥父播,厥子耘耔,而有秋可期矣。”比隆武二年丙戌十有二月,廣州陷,公攜吾母夫人黃及大均兩弟兩妹返沙亭,則曰:“自今以后,汝其以田為書,日事耦耕,無所庸其弦誦也。吾為荷篠丈人,汝為丈人之二子。昔之時,不仕無義。今之時,龍荒之有,神夏之亡,有甚于春秋之世者,仕則無義。潔其身,所以存大倫也,小子勉之。”比永明王即真梧州,乃喜曰:“復有君矣!汝其出而獻策,或邀一命以為榮,可也。”大均既赴肇慶行在,上《中興六大典書》。[3]137-138
父子之間可記述的事情很多,父親對子女的教誨也一定不少,但這篇文章記述的卻主要是其父對他讀書和忠君的教導,而這些教導所體現的也恰恰是屈原的忠騷忠愛精神。從其記述的有意選擇,可以看出屈大均刻意強調的是父子相承的品質和建構其家族傳統和家風的意識。
屈大均一生的出處選擇,真正踐履了其父的教誨。屈大均自認為是華夏道統學統的繼承者,屢言“吾儒”,又屢言自己是屈原的精神后裔,推崇儒學,精研儒學經典,視儒學和屈騷為其家學。“師其文當師其學,師其學焉,而以之事父事君,知天知人,同死生,盡性至命,非即所以學夫《詩》耶?予之為三閭書院也,與二三同志,稱《詩》說《易》于其中。惟日孜孜,不敢負其家學,在三閭末胄,分當云爾。”[3]283順治四年(1647)他從師起兵抗清;順治六年春奉父命赴肇慶向永歷皇帝上《中興六大典書》;翌年,清兵再陷廣州,為避難削發為僧;之后多次北上,聯絡志士抗清;康熙十二年,吳三桂反清,大均上書言攻取之策,授以廣西按察司副司,監軍桂林,督安遠大將軍孫延齡軍;吳三桂陰圖稱帝,大均托病歸家,隱居番禺沙亭,從事著述。“予少遭變亂,溝壑之志,積之四十余年,濡忍至今,未得其所,徒以有老母在焉耳。”[3]313
屈大均始終以屈原忠騷砥礪自己。他一再強調自己“魂來自汩羅”“家學元騷賦,依依忠愛情”[8]。屈大均時刻提醒自己莫忘舊君,數十年佩帶永歷銅錢一枚。“以黃錦囊貯之,黃絲系之,或在左肘,或在右肱,愿與之同永其命”[3]130。可以說屈大均一生都在踐履著屈原的忠騷忠愛精神。
屈大均還常常以屈原忠騷勉勵同宗族人,不但應學其文,更要學其人。“吾宗本荊楚人,文雅之士,固宜以《離騷》為家學,學其忠,復學其文,以無愧大夫之宗族,無負《離騷》之一書……祠既成,將使吾宗操觚之士,皆以祠為歸,凡有所作,合之為《三閭家言》,附于《楚辭》之后,豈非大夫之所樂得于其苗裔者哉!”[4]419
以左徒之忠而文郁為騷賦之圣,凡屬屈之子孫,皆宜以之為大宗,繼其爭光日月之志,述其上兼《風》《雅》之事,而為湘累一家之學,此乃吾楚之同姓,高陽之苗裔所尤宜,非惟天下之人當祖述而已也……自庚寅廣州城破,予返沙亭,即以屈沱名此溪,蓋吾屈之姓之美以大夫,而沱之名之美亦以大夫,則為屈氏之子也者,毋負其姓之美;居屈沱之上也者,毋負其名之美,而有以光大于大夫。是則大均之所以自期,亦以期于合宗之人也夫![3]314
大夫之姓為屈,自有大夫,而天下之姓遂以屈之姓為天下人之姓之至高至美者,蓋大夫之姓,以大夫而重,大夫之忠,又以《離騷》而益重。為大夫之同姓者,不能學大夫之文,寧不能學大夫之忠?忠出于人,文出于天,天不可為也,人則可為,吾愿與吾宗子姓交勉之。”[3]47
屈大均所期待的是“合宗之人”“凡屬屈之子孫,皆宜以之為大宗,繼其爭光日月之志”“以《離騷》為家學”,以屈原忠騷作為屈氏家族之傳統。
明末清初天崩地解之時,屈氏族人遠紹屈原忠騷確有不俗的表現。“吾宗自喪亂以來,二三士大夫,亦頗能蟬蛻垢氛,含忠履正,三閭之遺風,其猶未泯也。”[4]419其《伯兄白園先生墓表》一文云:
伯兄生而聰敏,幼即能文,未弱冠舉隆武乙酉科鄉試。明年丙戌,丁父憂。其冬以廣州失守,益哀痛不欲生存。會永明王立以丁亥,為永歷元年。明年戊子三月,惠國公李成棟反正,伯兄亟走梧州迎蹕,上《時務》一疏。官授中書舍人,奉命還娶。先是元年春,義師四起,伯兄盡破家產以從,與仲兄泰士衰绖行軍。初入羅浮,糾合十三營壯士,得數千人,與赴文烈侯張公家玉之師……再上疏請執殳,先死封疆,弗許。四年庚寅春,南雄失守,車駕復幸梧州。伯兄遂拜表辭朝,與仲兄遄歸,聯絡山海義旗,亟援省會。拮據數月,始辦一蒼頭異軍以出……八年甲午,西寧王李定國統帥王師下高、雷、廉三府,伯兄移家羅浮,與仲兄間道赴軍……叛臣洪承疇將委二兄某官,二兄不可,謂人臣之義,君為社稷亡則亡之,吾不能亡之于緬甸,豈可不亡之于番禺?是時,延平王賜姓成功,方擁樓船數千,一戰瓜洲,遂抵白下。南都城勢且降拔,二兄亦欲浮牂牁大洋往從之,故還番禺取道。比抵家,母子相持痛哭,旋聞大行皇帝與皇太子遇難。伯兄憤惋過傷,遂得吞酸翻胃之病……乙卯正月二十有九日,遂爾不起。[3]139-141
沙亭之鄉吾之宗,凡數百人而與予雁行,在兄則為汝伯兄白園、仲兄鐵井,在弟則五郎汝,蓋道同志同,予之所朝夕相依以為性命者也……人謂汝二兄“忠貞并篤”,蓋善學其祖靈均也者。夫吾家為三閭大宗子姓之秀,固宜以靈均為師,忠以致身,文以流藻,以求無負先大夫所以垂光來葉至意。汝之二兄,大節皎然,蟬蛻垢氛,既善學其左徒先祖矣。吾與五郎繼之,復將善學其兄,豈非吾宗之盛事乎哉?嗟夫,賢人君子,道同志合,可以為死生之友,世不多得,萃之一國難矣,況萃之一家。吾沙亭當炎州,窮處煙管之峰,扶胥之水,靈秀之所孕鐘,有汝二兄為之兄,復有汝為之弟,一家而三美合,不惟人妒之,天且妒之……南屈之不幸,其遂至于此極耶![3]217-218
不管事實上番禺屈氏族人如何,屈大均筆下的沙亭屈氏族人大都能做到“以靈均為師”。而“以靈均為師,忠以致身,文以流藻”云云,也正是屈大均所建構的屈氏宗風的總綱。他在寫給同宗族人澹翁的《存耕堂稿序》中說:“翁之方寸,今所留與而子孫者,自此以往,無論肥磽,其使之種粳秫者十之三,種蘭荃者十之七,以繼先大夫之孤芳,其亦庶乎家風有光也哉。”[3]67顯然,在他筆下,屈原忠騷正是其家風宗訓的核心。
屈大均筆下的沙亭屈氏雖然沒有連續不斷的完整世系,但他的敘述已經大體上為屈氏族人勾畫出了比較清晰的世系輪廓,而且這一屈氏世系也一直秉承著屈原的忠愛和忠騷精神,秉持著包括忠愛在內的華夏道統和學統。
屈大均跨越時空以自己和沙亭屈氏接續屈原,不但是血統上的認同,更是精神的認同,是對自己家族傳統、家族意識、宗族精神的建構行為。屈大均于天崩地解之時,把屈原忠騷與華夏道統和學統的對接,對屈氏宗風族訓傳統的建構,也在理論上把自己和當時士人的出處選擇放在了巨大的華夏道統學統之承續的框架之中。在這一理論框架之中,士人此時的出處選擇,其意義不可等閑視之,它關乎著華夏道統和學統,乃至治統的存續。道統學統存,則疆土雖失而天下不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