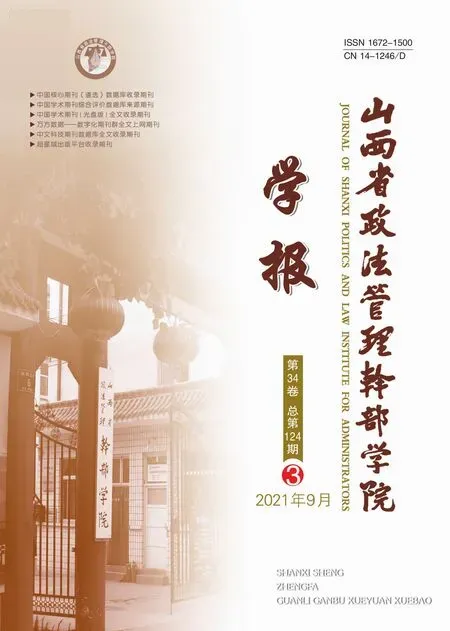妨害傳染病防治罪與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適用區分
李金珂
(云南大學 法學院,云南 昆明650091)
一、問題的提出
2020年2月12日,《北京晚報》登載了最高人民檢察院于前一日發布的首批十個妨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犯罪的典型案例,其中三起都屬于妨害傳染病防治類案件。這些案件在情節和后果上具有高度相似性:從疫區返鄉的行為人拒不配合當地衛生部門制定的疫情防控措施,或不接受隔離,或隔離期未滿便擅自出入公共場合、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最終造成大量與其有過直接或間接接觸者被采取隔離措施。上述隱瞞疫區旅行史并造成多人被隔離觀察的情況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治過程中并非個例。妨害傳染病防治的行為嚴重阻礙防控工作的順利開展,對國家機關和衛生部門控制疫情形勢的努力帶來巨大的破壞,因此是法律的重點打擊對象。然而在司法實踐中,對上述行為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或妨害傳染病防治罪立案偵查的皆而有之。為更好的打擊妨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違法犯罪行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于2020年2月10日發布《關于依法懲治妨害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違法犯罪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對妨害傳染病防控行為的法律認定予以了明確,但實務界對到底適用何罪依然存在一定疑惑。為了對妨害傳染病防治工作的行為給與精準的法律打擊,有必要深入討論該罪名的適用問題,減少司法實踐中的理念分歧,為保障疫情防控工作的成效提供堅實的法律支持。
二、厘清妨害傳染病防治罪與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之界限
妨害傳染病防治罪與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司法適用中容易產生取舍困難,歸根結底是因為二者的構成要件存在局部重合。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以下簡稱《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條以及第三百三十條第一款第四項的規定來看,如果排除主體和罪名類型,那么拒不配合隔離或隔離期未滿便擅自進入公共區域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以及因作出上述舉動而引發新冠肺炎病毒傳播的,都屬于拒不配合醫療衛生機構防控措施的行為。但我國刑法理論認為,無論是過失犯罪還是故意犯罪,都是以行為引發的后果為評判依據,而非行為本身。換言之,故意做出的行為也不能排除過失犯罪成立。明確了這一點,辨清二者的核心問題就是罪過類型與構成要件。
(一)罪過類型之辨
妨害傳染病防治罪與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二者間罪過類型的主要區別在于犯罪心態。根據刑法理論,對任何罪名的判定都必須以主客觀統一為前提,就算行為人做出的客觀行為符合某罪的構成要件,只要缺乏確鑿證據,不能證明行為人有實施該犯罪行為的主觀故意,就不能以該罪論處。那么如何證明行為人對犯罪行為具有主觀故意?對此,可通過行為人的行為方式以及行為引發的后果來判斷。在司法實踐中,妨害傳染病防治罪的犯罪主體在犯罪時持何種心態是有爭議的,爭議的焦點在于“妨害”二字。單從字面上看,“妨害”行為具有積極主動性,加上拒不配合醫療衛生部門提出的疫情防控措施的行為同樣具有積極主動性,因此理應認定犯罪行為人在心態上具有主觀故意。然而事實與現狀是,妨害傳染病防治罪目前基本一致被認定為過失犯罪,就算行為人存在故意心態,但對行為引發的后果主觀上仍然屬于過失。當然,妨害傳染病防治罪的“過失”應當為過于自信的過失,這是因為在疫情暴發后,國家幾乎“無死角”宣傳和防控的情況下,行為人對自己行為的潛在危害性不可能毫無知覺,而是在有知覺的同時自信可以掌控和避免。如,廣西壯族自治區韋某在從武漢返鄉后不配合當地衛生部門提出的居家隔離要求,仍走親訪友,到菜場買菜,致使與其有密切接觸的8人確診、122人被集中隔離。此類案件在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后屢見不鮮,幾乎每日都見諸媒體。上述情形下的行為人雖然在客觀上存在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行為,也引發了該罪伴隨的危害性后果,然而并不滿足主觀要件的要求,因此不能認定為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但如果行為人明知自己是疑似病人而還做出上述行為,則應當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論處。
(二)構成要件之辨
以上兩種罪名都屬于妨害和對抗疫情防控措施類犯罪,但適用條件有別。《關于依法懲治妨害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違法犯罪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對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所做的描述與規定為:已確診的、疑似的新冠肺炎病人或新冠病毒病原攜帶者,拒不配合衛生防疫機構依法制定的隔離措施,或者在隔離期未滿前擅自解除隔離并出入公共場所、使用公共交通工具,造成新冠病毒傳播的,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與此同時,《意見》對妨害傳染病防治罪所做的描述與規定是:其他拒絕配合衛生防疫機構按照傳染病防治法制定的防控措施并引發新冠病毒傳播或造成嚴重傳播危害者,構成妨害傳染病防治罪。
在構成要件方面,《意見》劃定了較為明確的主體范圍,但在具體案件中判定行為主體是否在該范圍之內時則需要排除行為人的身份要素,不能光憑行為人是否來自武漢等疫情嚴重地區、是否存在新冠肺炎疫情癥狀等就做出判定,而需要嚴格依照《傳染病防治法》第七十八條的規定來衡量,同時還要隨著人類對新冠肺炎病毒科學研究的漸次加深而做出更新。另外,《意見》還依不同的主體對其相應的犯罪成立要件做出規定,比如對于確診病人和病毒攜帶者來說,只要其在客觀上做出拒不配合隔離治療或隔離期未滿便擅自進入公共場合或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的行為,就可認定為妨害傳染病防治罪。如果行為人的上述行為引發了嚴重后果,則在客觀上加重了妨害傳染病防治罪的構成要件,可認定為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而對于疑似病人來說,則既要在客觀上做出以上行為,又要引發新冠肺炎病毒傳播的后果才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三、新冠肺炎疫情相關刑事案件對妨害傳染病防治罪的合理適用
在適用妨害傳染病防治罪時,司法部門需要依照《刑法》及《意見》中的相關規定,堅持罪刑法定原則,明確構成要件。具體需把握以下幾方面的重點:
(一)對犯罪主體范圍的認定
妨害傳染病防治罪為一般主體,在司法實踐中,需要注意厘清以下幾種情況:
第一,若確診和疑似新冠肺炎病人、新冠病毒病原攜帶者(以下簡稱“三類人”)拒不配合隔離要求,或者隔離期未滿便擅自離開隔離場所,但并未隨意出入公共場所或使用公共交通工具,也不存在主觀上故意傳播病毒的意圖,即使客觀上造成新冠肺炎病毒傳播,仍然認定為妨害傳染病防治罪。如果“三類人”雖未出入公共場所或使用公共交通工具,但做出危害公共安全的行為(比如將唾液涂抹在電梯按鍵上),則應當以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原因在于此行為既違反國家的衛生防疫要求,又存在危害公共安全的主觀故意,且不屬于《意見》規定的妨害傳染病防治罪的情形。
第二,若行為人在做出違反國家疫情防控要求的行為時未得到權威醫療機構的診斷,即該主體并不知曉自己是“三類人”,但事后檢驗證實其屬于“三類人”。那么該情況并不屬于《意見》所描述和規定的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情形,不構成該罪,而應認定為妨害傳染病防治罪。
第三,《意見》對妨害傳染病防治罪的主體規定采用的是排除法,即“三類人”范圍之外的人員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那么依照《刑法》第三百三十條之規定,判定其構成妨害傳染病防治罪。換言之,未得到確診的病人、無癥狀感染者、有過疫區旅居史等人員若拒不配合國家防疫防控工作要求并引發新冠肺炎病毒傳播,可認定為妨害傳染病防治罪。
(二)對衛生防疫機構依法制定的防控措施的認定
根據《意見》之規定,觸犯和違反衛生防疫機構依法制定的疫情防控措施及規定的行為,按妨害傳染病防治罪論處,但是何為違反衛生防疫機構依法制定的疫情防控措施的行為,這一點《意見》并未作進一步的說明。在舉國對抗新冠肺炎疫情的實踐中,各地采取的防控措施不盡相同,社區、衛生防疫機構等制定了形形色色的防控辦法,因此難以就“疫情防控措施”達成統一標準。筆者認為,應當依照《意見》以及《傳染病防治法》中的規定,將違反政府衛生防疫機構依法制定的防控要求的行為,作為適用妨害傳染病防治罪的要件。如果行為人的行為僅違反非政府衛生防疫機構或者非依法作出的防控要求,則不宜按照妨害傳染病防治罪論處。值得注意的是,地方政府部門或地方衛生防疫機構在組織本地的疫情防控工作時,根據《傳染病防治法》以及《突發事件應對法》中所做的規定,只要不與上位法存在沖突,就應當視為“衛生防疫機構依法制定的防控措施”。
(三)造成新冠病毒傳播或引發嚴重后果的因果關系認定
對妨害傳染病防治罪進行認定的重要條件之一,就是行為人的行為在客觀上引起新冠病毒傳播或造成嚴重危害。根據最新一版《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診療方案》對新冠肺炎病毒傳播途徑所做的說明,該病毒存在多渠道傳播路徑,多元的傳播方式加上較強的傳播力,意味著如果同一場合出現多名確診或潛在的新冠肺炎感染者,那么對行為人的行為與新冠肺炎病毒傳播以及造成的嚴重危害之間的因果關系將很難進行認定。認定某行為人的行為是造成新冠肺炎病毒傳播的原因需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在辦理妨害傳染病防治的案件時,司法機關的工作重點是分析研判行為人自身是否知曉自己是確診新冠肺炎病人、疑似新冠肺炎病人、攜帶新冠肺炎病毒的無癥狀感染者、是否拒不配合衛生防疫機構的防控工作、是否存在瞞報疫情接觸史或疫區旅居史的情況、是否在客觀上造成新冠肺炎病毒傳播等情況。若根據行為人的客觀行為事實難以判斷其行為與新冠肺炎病毒傳播存在因果關系,則不滿足構成妨害傳染病防治罪的要件,不能以該罪名定罪。
(四)對犯罪競合情形的處理
在行為人拒不配合衛生防疫機構依法制定的防控要求并造成病毒傳播或產生嚴重后果時,該行為同時構成妨害傳染病防治罪和妨害公務罪。對此類行為應以何種方式進行處罰?筆者認為,在疫情防控的嚴峻形勢下,宜擇重處罰。同時,新冠肺炎疫情屬于《傳染病防治法》所規定的乙類傳染病,根據《國境衛生檢疫法》以及《意見》之規定,若入中國國境者拒不配合我國衛生檢疫機構依法制定的防控要求,并引發病毒傳播或造成嚴重后果,既妨害國境衛生檢疫,又妨害傳染病防治。對此情形應當如何處理,《刑法》和《意見》都沒有做出明確的規定。考慮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嚴重性,以及妨害傳染病防治罪比妨害國境衛生檢疫罪的罪刑更重,根據擇一重處斷原則,應當以妨害傳染病防治罪論處。
結語
新冠肺炎疫情在國內暴發后,“兩高兩部”迅速出臺《意見》,用以指導妨害疫情防控九類犯罪行為的司法實踐,對規制妨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不法行為提供了堅實的法律依據。在司法實踐中,對妨害傳染病防治罪的適用需要秉持嚴謹審慎的態度,既要著重考量該罪的適用條件,又要順應刑事政策導向,凸顯司法之公平公正,全面分析研判行為人的主觀態度、客觀行為、以及其行為與新冠肺炎病毒傳播之間的因果關系。同時,司法機關在對此類行為進行依法懲處時,需要堅持刑法謙抑原則,不重判輕罪,也不輕判重罪,切實避免刑罰處罰擴大化的不當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