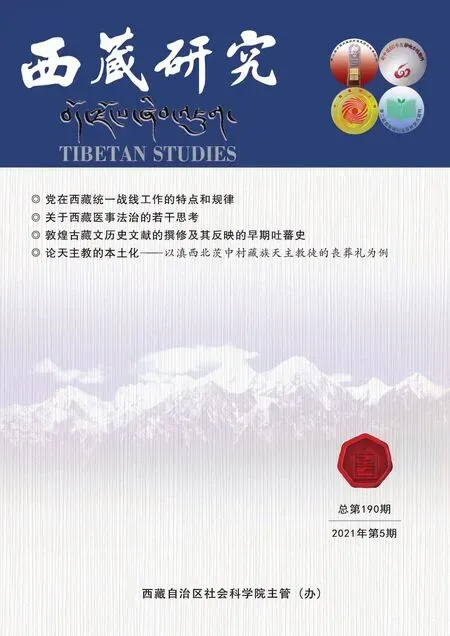明代對藏冊封問題研究
陳武強
(西藏民族大學民族研究院,陜西 咸陽 712082)
一、引 言
冊封,也稱“冊立”“冊命”“策命”等,始于周代,后世沿承。其內涵有多種,一為中國古代皇帝封立太子、皇后、王侯、公主、郡主等,并舉行儀式,宣讀冊授圣旨。二為宗主國對藩屬國的冊封,由此形成一種冊封體制。冊封體制源于商周分封制,“冊封體制也可以稱為朝貢關系,是以宗主國和屬國兩方面構成的相互關系制度”[1]。三為中原王朝對邊疆民族首領的冊官封爵,所謂“加以侯王之號,申之封拜之寵,備物典冊以極其名”[2],以定“君臣”之位。如唐朝試圖通過冊封,“來確定其對邊疆民族的統治地位”,而接受唐王朝冊封的民族政權,也就意味著“其承認唐王朝的最高統治”[3]。
明朝時期,中央對藩屬國或邊疆民族地區首領進行了大量冊封。一方面,冊封是確立明朝地位最重要的表現和環節,如明朝對朝鮮、日本、琉球等東亞諸國都曾進行過冊封。另一方面,冊封也是羈縻邊疆民族首領、維護“華夷安危之道”的重要手段,如明朝中央政府對西藏和其他藏族聚居區政教首領的冊封、對蒙古首領的冊封等。承擔冊封使命的大臣,稱為冊封使者(簡稱“冊封使”)。
對明代冊封問題已有大量研究成果(1)參見米慶余《明代中琉之間的冊封關系》、于默穎《明代蒙古順義王的冊封與嗣封》、侯甬堅《由滄水入黑水——明代冊封船往返琉球國的海上經歷》、趙連賞《明代賜赴琉球冊封使及賜琉球國王禮服辨析》、朱淑媛《新發現的明代冊封琉球國王詔書原件》、連晨曦《明代冊封琉球使臣的福州行跡》、陳沛杉《明朝對西藏地方政教首領的冊封及其演變》等成果。另有劉月《明清兩代冊封琉球使及其從客海洋詩研究》、鄭毅《明代閩籍冊封琉球使及其作考證》等學位論文,也從不同角度對明代冊封問題作了討論和研究。,但主要是針對冊封藩屬國王、國君的研究,對于邊疆首領的冊封雖有一定的探討,但研究成果并不多。關于明朝中央政府冊封西藏和其他藏族聚居區政教首領問題,如冊封方式、過程、作用、冊封使的派遣諸問題,目前尚缺乏專文進行研究。本文擬就此問題進行全面系統的梳理和考證,以期說明其在西藏與祖國關系中發揮的歷史作用。
二、來京冊封范式與“限封”主張
綜觀明代冊封西藏和其他藏族聚居區首領,主要有兩種方式:(一)對朝貢來京或迎請的政教首領、頭目、番僧等直接冊封;(二)朝廷派出使者前往西藏和其他藏族聚居區奉敕冊封。兩種冊封方式中,第一種即明朝對來朝的首領、頭目、僧侶等人直接冊封者最多,且冊封時間、地點、形式等靈活多樣。
按明朝中央政府冊封西藏和其他藏族聚居區政教首領的數量,永樂年間是明代冊封比較頻繁的一個時期。從1402年到1424年的22年間,明成祖朱棣先后冊封吉剌思巴監藏卜、著思巴兒監藏、釋迦也失等人為政教王、法王、大國師、禪師等大小不等封號封爵,“番僧之號凡數等,最貴曰大慈法王,曰西天佛子,次曰大國師,曰國師,曰禪師,曰都綱,曰剌麻。”[4]卷27:684其數量,僅永樂一朝,計有“西天佛子者二,灌頂大國師者九,灌頂國師十有八,其他禪師、僧官不可悉數。”[5]8577其冊封方式極其靈活,而最重要的冊封是藏族五大政教王和兩大法王。
西藏五大政教王的冊封是在永樂四年(1406)至永樂十一年(1413)間完成的。其中,闡化王為永樂四年敕封帕木竹巴第四任教主吉剌思巴監藏卜的爵號[6];贊善王者,“靈藏僧也,其地在四川徼外,視烏斯藏為近。成祖踐阼,命僧智光往使。永樂四年,其僧著思巴兒監藏遣使入貢,命為灌頂國師。明年封贊善王,國師如故,賜金印、誥命。”[5]8582護教王者,“名宗巴斡即南哥巴藏卜,館覺僧也。成祖初,僧智光使其地。永樂四年遣使入貢,詔授灌頂國師,賜之誥。明年遣使入謝,封為護教王,賜金印、誥命,國師如故。”[5]8583闡教王者,“必力工瓦僧也,成祖初,僧智光赍敕入番,其國師端竹監藏遣使入貢。永樂元年至京,帝喜,宴賚遣還。四年又貢,帝優賜,并賜其國師大板的達、律師鎖南藏卜衣幣。十一年乃加號灌頂慈慧凈戒大國師,又封其僧領真巴兒吉監藏為闡教王,賜印誥、彩幣。”[5]8584輔教王,“思達藏僧也,其地視烏斯藏尤遠。成祖即位,命僧智光持詔招諭,賜以銀幣。永樂十一年封其僧南渴烈思巴為輔教王,賜誥印、彩幣,數通貢使。”[5]8585
兩大法王中,大寶法王哈立麻(即卻貝桑波)為永樂四年十二月抵達南京后次年(1407)封,“(其間)卻貝桑波為皇家講經、灌頂并為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資福。皇帝所賜禮品無數。皇帝親賜卻貝桑波以‘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封號。”[7]210大乘法王昆澤思巴(即貢噶扎西),為永樂十一年二月來南京后被封(2)1425年,大乘法王貢噶扎西貝桑布在薩迦大殿去世,大乘法王一職由薩迦昆氏家族成員世襲。參見達倉宗巴·班覺桑布:《漢藏史集》,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2頁。。永樂十三年(1415)二月,明成祖還敕封格魯派宗喀巴的首席弟子釋迦也失(又譯作釋迦益西)為西天佛子大國師。次年,釋迦也失返藏,明朝賜予他金銀、綢緞、佛像等大量財物。《新紅史》稱:“燕王皇帝掌政二十二年。此皇帝最初也曾派人迎請宗喀巴,但是未去。因此,迎請了噶瑪巴法王卻貝桑波、薩迦巴袞嘎扎西及塞熱哇釋益西等三人。遂后他們依次被賜以封號:如來大寶法王、大乘法王及大慈法王。此皇帝又向尊者佛像獻了衣服供物等(之豐)不可思議。”[7]50-51顯然,較之洪武時期,永樂年間在西藏和其他藏族聚居區的冊封規模更大、數量更多、體制更加完善。五大政教王、兩大法王的封授,是明初邊疆治理史上一件重大的事件,明人鄭曉的《今言》道:外夷封王者,只有琉球三王、北虜四王、西域二王,而西番七人:“正覺大乘法王、如來大寶法王、闡化王、闡教王、輔教王、贊善王、贊化王”[8],足見西番封王最多、地位極高,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西藏事務在明朝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
繼永樂朝之后,宣德九年(1434)宗喀巴弟子釋迦也失來京覲見明宣宗皇帝,被封為“大慈法王”。明宣宗敕封大慈法王一事,《新紅史》中說:宣德九年,釋迦也失再次抵達北京,明宣宗封“萬行妙明真如上勝清凈般若弘昭(照)普慧輔國顯教至善大慈法王西天正覺如來自在大圓通佛”,即大慈法王[7]51。《明史·大慈法王傳》記載:“大慈法王,名釋迦也失,亦烏斯藏僧稱為尚師者也。永樂中,既封二法王,其徒爭欲見天子邀恩寵,于是來者趾相接……宣德九年入朝,帝留之京師,命成國公朱勇、禮部尚書胡濙持節,冊封為萬行妙明真如上勝清凈般若弘照普慧輔國顯教至善大慈法王西天正覺如來自在大圓通佛。”[5]8577《萬歷野獲編》亦載:“宣德九年六月,遣禮部尚書胡濙同成國公朱勇,持節封釋迦巴(也)失為萬行妙明真如上勝清凈般若宏(弘)照普應(慧)輔國顯教至善大慈法王、西天正覺如來自在大圓通佛。”[4]補遺卷4:914各文獻中記載基本相同,即釋迦也失來京覲見宣宗朱瞻基后被封為“大慈法王”。至宣德年間“大慈法王”冊封完成,明代共計封授了西藏五大政教王、三大法王,他們在當地地位最高、最受尊崇。研究者認為,明朝冊封三大法王和五大政教王的過程有所不同,“封授五王僅用了10年時間就告完成,而大法王的封授過程頗為復雜曲折,直至宣德九年才最終完成,歷時幾達30年。”[9]47除五大政教王、三大法王之外,明朝還對西藏和其他藏族聚居區僧俗首領封以大國師、國師、禪師等封號以及大大小小的僧官,“不可勝紀”[8]8578。
由此可見,明朝前期,中央政府適時冊封西藏地方政教首領,根本目的是要達到所授官員“統束各番”、確保地方統治。因此,得到明朝冊封者,或者是當地有勢力者,或者是在當地具有威信者,特別是高德大僧,“我朝洪武六年,因其故俗,以攝帝師喃加巴藏卜為熾盛佛寶國師……后分封為大寶、大乘、贊化、闡化、闡教、輔教等六王,皆僧也。”[10]
明代中期,中央政府對西藏和其他藏族聚居區政教首領的冊封制度照例進行。景泰三年(1452)十月,明代宗封西天佛子大國師班丹札釋為大智法王,賜以誥命。景泰七年(1456)六月,明代宗聽從禮部尚書胡濙的奏請,敕封答蒼地面王子喃噶堅粲巴藏卜襲為輔教王,賜誥敕、金印、彩幣、僧帽、袈裟、法器等物,并敕封番僧葛藏為灌頂廣善慈濟國師、烈藏為靜覺持正國師、領占巴丹為靜覺佑善國師、班卓兒堅參為戒行禪師、桑結遠丹為慈化禪師、羅竹聰密為翊善禪師、堅參烈為妙覺禪師、遠丹綽為靜范禪師、領占三竹為清修禪師、羅竹札失為崇善禪師,“各賜印及誥命。”[11]卷267:5672同年七月,明代宗冊封西番凈修弘智灌頂大國師鎖南捨剌為凈修弘智灌頂大國師西天佛子、廣通精修妙慧闡教西天佛子大國師沙加為廣通精修妙慧闡教弘慈大善法王、剌麻占巴失念為崇修善道國師、加弘善妙濟國師捨剌巴為灌頂弘善妙智國師[11]卷268:5683。十月,明代宗封番僧札失尾則兒、班竹兒星吉俱為左覺義,桑兒結巴為右覺義,鎖南班卓兒、鎖南堅粲、鎖南捨剌、遠丹羅竹、鎖南札、南葛藏卜俱為都綱,給印并誥敕,一年之內敕封的僧官達二三十人。
然而,自明代中期以來,朝廷對西藏和其他藏族聚居區政教首領的冊封已不再節制,“尤其是對寺院番僧的無限制地封賜,導致了進京冒貢人數劇增。”[12]明憲宗時,朝廷對烏思藏僧俗首領“分封賞賜泛濫”[13],帶來了一系列邊疆和社會治理新問題。于是,朝廷內部出現了限制冊封的聲音。六科給事中魏元、十三道監察御史康永韶、翰林院編修陳音等人分別向明憲宗提出在冊封問題上的建議。盡管建議的具體內容不盡相同,但都認為朝廷應當限制冊封,減少負擔,從根本上解決朝貢無度帶來的財政危機狀況。如魏元在成化四年(1468)九月提出:“革去番僧法王、國師等名號”[14]卷58:1176,發回西藏,追回賞賜,以賑饑民。同年,康永韶也指出:“今朝廷寵遇番僧,有佛子、國師、法王名號,儀衛過于王侯,服玩擬于供御,錦衣玉食”[14]卷58:1176,應當對此進行甄別查審,遣回本地。陳音在成化六年(1470)三月提出:“當今號佛子、法王、真人者,無片善寸長可采,名位尊隆,賞與濫謚。伏愿降其位號,杜其恩賞。”[14]卷77:1482對于朝廷內外各種反對冊封的奏疏甚至批評,明憲宗搪塞說,“此事累有人言,俱已處置矣。”[14]卷77:1482此后,經過一段時間的搖擺不定,明憲宗最終以“祖宗舊制”[14]卷77:1482、不能輒變為理由否決了封建士大夫們的限封主張。故明憲宗統治時期,冊封事宜照舊實行。在巨大的政治和經濟利益趨動下,西藏和其他藏族聚居區僧俗首領不時違制朝貢[15],進京朝貢人數更多、次數更頻,故冊封數量更多,“冒貢”“濫貢”“濫賞”“濫封”已經成為普遍現象。
明孝宗朱祐堂即位后,一改憲宗時期的政策,對邊疆少數民族政教首領冊封制度有了較大的轉變。明孝宗是成化二十三年(1467)九月即位的,十月丁卯(1487年10月17日),禮部即頒定一項冊封番僧法案:自法王、佛子、國師、禪師各降職一級,自講經以下革職為僧,“各遣回本土、本寺或邊境居住,仍追奪誥敕、印信、儀仗,并應還官物件。”[16]經明孝宗改革,弘治時期對藏冊封數量大為縮減,冊封得以控制,“雖然明孝宗對于番僧的態度在弘治中后期略有變化,但在整個弘治時期,中央王朝對西藏地方的冊封數量仍得到有效限制。”[17]
明武宗時期,雖有太監劉允進藏迎請活佛之舉,但明朝朝野上下對西藏和其他藏族聚居區僧俗首領冊封一事反對者甚眾,“中央王朝對西藏地方的限封和降封已經逐漸成為全朝野的共識”[17]。到了嘉靖時,明世宗即位后詔令:“正德元年以來,傳升、乞升法王、佛子、國師、禪師等項,禮部盡行查革,各牢固枷釘,押發兩廣煙瘴地面衛分充軍,遇赦不宥。”[18]卷1:10此詔以最嚴厲的法律從理論上宣告了明朝初期以來實行的對藏冊封制度的全面停止。
明臣反對對藏冊封的根本原因,皆因明代中后期的濫封無度偏離了冊封制度的初衷,給國家治理造成了危害。適時停止已經具有消極影響的無限制冊封,“因時而易”地治理邊疆民族地區,真正維護西藏和其他藏族聚居區安定應該是明智之舉,也是與時俱進之策。當然,明朝的一些封建官僚、士大夫們強調冊封“無益于治道”[14]卷58:1176,即它對于國家治理邊疆沒有任何好處,這也難免有些偏頗。因為從特點和效果上看,明朝對藏冊封,前期與后期并不相同。總體而言,前期冊封少而精,后期冊封雜而亂,因此它們對邊疆治理的作用和意義是不相同的,并不是所有階段的冊封都“無益于治道”,要理性地分析。值得肯定的是,明代前期的冊封在政治上無疑意義重大,只不過中后期的濫賞濫封才使其大打折扣。
三、遣使冊封“舊例”與成、嘉時期改革
明朝對藏冊封是確保中央政府對西藏和其他藏族聚居區有效統治的有力保障,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為了加強中央政府與地方之間的聯系,確保治藏政策的順利落實,對影響較大的寺院高僧或勢力較大的世俗地方官員,朝廷均主動派遣京城寺僧為使者前往冊封,這是從明初直至嘉靖四十二年(1563)之前實行的冊封“舊例”,即對藏冊封的基本制度。
此外,當明朝所封藏族政教首領年老不能處理政教事務時,即奏請中央政府由其子侄、徒弟襲職,中央得到奏請便會派出使者前往冊封新首領。如天順元年(1457)九月,烏思藏輔教王喃葛列思巴羅竹堅粲巴藏卜奏陳:自己已年老不能理事,請其子襲職。明英宗詔命灌頂國師葛藏為正使、右覺義桑加巴為副使,率使團到烏思藏封其子答蒼喃葛堅粲巴藏卜襲職輔教王[11]卷282:6064。如果藏族聚居地方報告所封頭目已死,朝廷便遣使吊祭,同時冊封新的首領。弘治十年(1498)十二月,烏思藏闡化王死,其子班阿吉汪束札巴乞襲封,明孝宗立即詔令番僧剌麻參曼答實哩為正使,鎖南窩資爾為副使,前往西藏封其子班阿吉汪束札巴襲職闡化王。
考終明一世,派遣到西藏和其他藏族聚居區的冊封使,見于文獻確切記載者如下:

表1:明代對藏冊封使
表1中永樂四年(1406)至正德二年(1507)間出使使者有:宣德五年,沈羽;宣德九年,劉浩、朱勇、胡濙;正統五年,葛藏、昆令;正統十年,鎖南藏卜、札什班丹、斡些兒藏卜;天順元年,葛藏、桑加巴等;弘治十年,參曼答實哩、鎖南窩資爾、札失堅參等18人;正德二年,札巴也失、鎖南短竹。這些冊封使中,國師、禪師、剌麻等僧職使者人數達到68.7%。
由于冊封對中央政府統轄西藏和其他藏族聚居區具有極其重要的政治意義,所以朝廷在派遣冊封使時充分考慮其地域性、民族性及能力、官職大小等身份因素,使派遣的冊封使能夠代表朝廷、具有話語權,并能處理好與地方之間的關系。而漢番僧人在西藏和其他藏族聚居區社會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且有語言、身份之便利,所以,以漢番僧職人員充任冊封使者最多。這是其一。
其二,此表中的使者身份是指出使時的身份。使者出使任務完成后,因功升職的情況很常見,所以身份發生變化者多。從表1中所列冊封使的身份考察,明朝中央政府派遣的冊封使者中,官職最大的是成國公朱勇和禮部尚書胡濙,使者官職為正二品大員甚至王公親往,無疑反映了明朝對西藏和其他藏族聚居區僧俗首領冊封的高度重視。
其三,上表所列并非全部遣藏冊封使,考察明清時期文獻,還有諸多無姓名使者。《明太宗實錄》卷52:
(永樂四年三月壬辰),遣使赍詔封烏思藏巴里藏卜為灌頂國師闡化王,賜螭紐王印、誥命,仍賜白金五百兩、綺衣三襲、錦綺五十匹、彩絹百匹,茶二百斤。其所隸頭目并必力工瓦國師大板的達律師鎖南藏卜,頒賜彩幣、衣服有差。[19]775-776
(永樂四年三月壬寅),遣使命靈藏著思巴兒監藏為靈藏灌頂國師,授札思木頭目撒力加監藏為朵甘衛行都司都指揮使,切祿奔、薛兒加俱為都指揮同知,各賜誥命、襲衣、錦綺。命館覺宗巴斡即南哥巴藏卜為館覺灌頂國師,隴答頭目結失古加之子巴魯為隴答衛指揮使,賜誥命、銀、幣。[19]780-781
此二例史料,除了冊封使是何人并不知曉外,其他冊封時間、地點、目的等皆十分清晰。
像這種無姓名記錄的冊封使者還有許多。《明實錄》載:明朝中央政府于永樂四年三月、正統三年正月、正統五年三月、正統十二年二月、景泰三年十月、景泰七年六月、景泰七年七月、成化四年四月等分別遣使冊封西藏和其他藏族聚居區首領,但使者名未記載。如永樂四年三月,明成祖“遣使赍詔封烏思藏巴里藏卜為灌頂國師闡化王”[19]775;正統十二年(1447)二月,明英宗“遣官赍誥敕封故安定王亦班丹子領占斡些兒襲安定王,賜織金、衣服、彩幣、表里。”[11]卷150:2947景泰七年六月,明代宗“遣官封答蒼地面王子喃噶堅粲巴藏卜襲為輔教王,賜誥敕、金印、彩幣、僧帽、袈裟、法器等物。命番僧葛藏為灌頂廣善慈濟國師,烈藏為靜覺持正國師,領占巴丹為靜覺佑善國師等。”[11]卷267:5672他們之中,可能仍然以國師、禪師、剌麻、都綱等僧職人員作為冊封使主要成員。
景泰之后,中央冊封西藏和其他藏族聚居區首領的次數和頻率明顯下降。成化三年(1467)七月,明憲宗朱見深詔命靈藏僧塔兒巴堅粲襲封為贊善王。按照明代“舊例”:
番僧封王者,賜誥敕并錦綺、衣帽諸物甚備,又遣官護送至彼給授。禮部以今西事未寧,事宜從省。乞降敕一道,惟賜袈裟、禪衣、僧帽各一,順付來朝番僧赍回靈藏給授。從之。[14]卷44:918
這條史料明確反映了一個重要信息:按明朝規定,凡是番僧封王,不論是新冊立還是襲職,中央政府必須派遣使者到當地給授。可是,景泰、成化年間,大批蒙古部落開始進入青海一帶活動,西寧邊事變得異常復雜,故禮部建議簡化對藏冊封形式,暫停遣使冊封舊規。明憲宗認為,禮部所奏合理合情,遂降敕一道:“順付來朝番僧赍回靈藏給授。”[14]卷44:918此敕表明,這次冊封西藏贊善王,朝廷不再遣使前往而是交于西藏地方來京貢使返藏后給授。此敕也預示著遣使冊封正在悄然出現變通。
成化三年冊封方式的變通,為以后冊封制度的改變留下了伏筆。嘉靖四十二年十月,烏思藏闡化等王請封,明世宗朱厚熜和禮部的回應是:
上以故事,遣番僧遠丹班麻等二十二人為正、副使,以通事序班朱廷對監之。比至中途,班麻等肆為騷擾,不受廷對約束。廷對還白其狀。禮部因請自后對藏請封,即以誥敕付來人赍還,罷番僧勿遣。無已,則下附近藩司,選近邊僧人賚賜之。上以為然,令著為例。[18]卷526:8576
從禮部的處置可以看出,禮部是要把原來遣使冊封制度進行改革,即廢除“封諸藏遣京寺番僧例”。對此,明世宗表示贊同,批準頒行,這就是嘉靖四十二年的《封諸藏不遣京寺番僧例》。新“例”明確規定:自今后西藏和其他藏族聚居區首領請封,即以誥敕交于貢使返藏時給授。不久,又調整為由臨近這些地方政府派遣邊地僧人赍敕給授,并“著為例”[18]卷526:8576。
關于此例,《典故紀聞》卷17亦有載:“舊例,烏思藏請封,皆遣番僧為正副使,而以通事監之。嘉靖四十二年,遣番僧遠丹班麻等封闡化等王,比至中途,肆為騷擾,不受通事約束。禮部因請:自后請封,即以誥敕付來人赍還,罷番僧勿遣。封諸藏之不遣京寺番僧,自此始。”[20]也就是說,自嘉靖四十二年起,明朝冊封西藏和其他藏族聚居區首領,不再派遣中央使者前往。
綜上,明代遣使冊封西藏和其他藏族聚居區首領經歷了三大階段:第一階段是洪武至景泰年間,遣使冊封比較頻繁;第二階段是成化年間的變通,第三階段是嘉靖年間《封諸藏不遣京寺番僧例》的頒行,遣京寺使者冊封停止。第二、第三階段,即成化、嘉靖時期,明朝中央政府對其冊封制度進行了改革。對于來京冊封,依然執行過去的舊政策。成化四年四月,明憲宗冊封西僧札巴堅參為萬行莊嚴功德最勝智慧圓明能仁感應顯國光教弘妙大悟法王、西天至善金剛普濟大智慧佛;札實巴為清修正覺妙慈普濟護國衍教灌頂弘善西天佛子大國師;鎖南堅參為靜修弘善國師、端竹也失為凈慈普濟國師。俱賜誥命。但對于遣使冊封,朝廷探索實行“領封”政策,依照新的《封諸藏不遣京寺番僧例》實施。新“例”的頒行,標志著嘉靖四十二年之后中央遣使冊封停止。
需要說明的是,新“例”的實施只是停止了派遣京城寺僧冊封的慣例,并不是說對這些地區首領的冊封完全停止了。實際上,在此“例”頒行前后,盡管朝野內部“冊”與“廢”的爭論激烈,但明朝官方對藏族頭目來京或遣使來京請職、請襲等要求依然予以應允,并基本按其要求封授:
如新“例”頒布前,西番剌旺藏卜于成化四年四月遣使入貢求請(職),“升西番剌旺藏卜為都指揮僉事。”[14]卷53:1077正德十年(1377)二月,“番僧完卜鎖南堅參巴爾藏卜遣人朝貢,乞襲封大乘法王,許之。”[21]卷121:2434正德十一年(1378)四月,“西番僧短竹叫等四人、桑呆叫等十人來貢方物,請襲國師、禪師職,從之。”[21]卷136:2690當然,對藏族首領的請職,朝廷有時也會酌情考慮。如成化十五年(1479)十二月,烏思藏闡化王遣剌麻鎖南領占請求升(鎖南領占)為國師,“命升為禪師,不為例。”[14]卷198:3478必須說明的是,藏族頭目請職,有時朝廷需要派出考察官員前往考察實情,方可授予。成化四年十月,管民萬戶舍人阿哈來朝貢方物,請襲職。“自稱其祖合丹思叭所轄地方十七,其印猶元至正間所授。乞換印襲職,開設衙門。”事下禮部會議認為,“宜移文四川鎮守等官,遣官出境,勘其端由”[14]卷59:1205,之后方可冊封,體現了明朝中央對邊地冊封的謹慎態度。
新“例”頒布后,烏思藏闡化王南札釋藏卜于萬歷六年(1578)二月“差番僧來西海,見其師(番)僧活佛在西海與順義王子孫等說法,勸化眾達子為善,因托順義王俺答代貢方物,請敕封。”[22]1558經禮部復議,明神宗“各授大覺禪師及都綱等職,賜僧帽、袈裟及表里、食茶、彩段有差。”[22]1558可見,即使是嘉靖朝頒行了新的《封諸藏不遣京寺番僧例》,但中央政府的對藏冊封制度并未完全停止。當然,此時的對藏冊封已與過去的無序冊封大相徑庭,并在某種情形下發揮著其特殊的歷史作用。
四、對藏冊封之評價
明朝中央冊封西藏和其他藏族聚居區政教首領,根本目的是為了加強和鞏固明朝在藏族聚居地區的統治。因此,冊封在國家治藏治邊中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
第一,基于中央政府“多封眾建,因俗以治”的治藏方略,一方面朝廷對于藏族聚居地方來京覲見或朝貢的政教頭目、大小僧人等均予以冊封;另一方面,對居于西藏和其他藏族聚居區政教領袖遣使赍敕冊封,使其在各自轄區合法行使管理權,撫治民眾、忠勤朝廷。換句話說,正如明太祖“授端竹監藏信武將軍加麻世襲萬戶府萬戶的制誥”中如是說:“今授爾信武將軍,加麻萬戶府萬戶,俾爾子孫世襲。爾其招徠遠人,綏端邊疆,永為捍御之臣。”[23]
第二,明代對藏冊封有一整套嚴密的制度,包括冊封儀式、受封者的爵號、對受封者詔書的宣讀及印璽的授給等方面,“舉行儀式時,由天子派遣相應的大臣為使者,向受封者及有關人等宣讀冊文,并授以印璽,受封者的地位由此即得到承認。”[24]凡是明朝中央政府冊封地方政教王、法王、國師等大小官員,均有冊封誥敕文書。《松窗夢語》卷3:經明初封官授職,于是西番番僧各有封號,“凡諸王嗣封,皆有賜誥。”[25]封誥文書還十分講究詔書、詔敕、詔誥等不同類型和不同金銀絲織質地,以此顯示這些高僧的不同地位及其中央政府對他們的尊崇。《南村輟耕錄》卷2《詔西番》曰:“累朝皇帝于踐祚之始,必布告天下,使咸知之。惟詔西番者,以粉書詔文于青繪,而繡以白絨,網以真珠,至御寶處,則用珊瑚,遣使赍至,張于帝師所居處。”[26]茲錄“明太祖賜噶瑪噶舉教派楚布寺”誥敕文書之內容如下:
敕書:明太祖賜噶瑪噶舉教派楚布寺(3)楚布寺,在今拉薩市西堆龍德慶縣境。明太祖洪武八年(1375)正月下達宣諭詔書的時候,楚布寺的寺主為黑帽系第四世轉世活佛乳必多吉(1340—1383)。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西藏自治區社科院、中央民族學院研究所、中國第二次歷史檔案館編《西藏地方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4頁;西藏自治區文物管理委員會編《拉薩文物志》,咸陽:陜西咸陽印刷廠1985年版,第164頁。
圣旨原文:
“皇帝圣旨:中書省官我根前題奏,西安行都衛文書里呈來,說烏思藏哈爾麻剌麻卒爾普寺在那里住坐修行,諸色人等休教騷擾,說與那地面里官人每知道者。”
末行為“洪武八年正月日”[27]907
此為明洪武八年(1375)正月明太祖朱元璋頒發給楚布寺喇嘛乳必多吉的圣旨(4)乳必多吉是噶舉派的一個支系——噶瑪噶舉黑帽系的第四世活佛,時頗有名望,曾應元順帝召于1360年至1364年住元大都5年。洪武七年(1374年,藏歷第六饒迥木虎年),派貢使往返朝廷,深得明廷器重。參見西藏自治區文物管理委員會編《拉薩文物志》,咸陽:陜西咸陽印刷廠1985年版,第164—165頁。,圣旨質地為白棉紙,方形,邊長76厘米,行文88字。墨筆楷書,字體秀勁工整。文后鈐“制誥之寶”朱印一方[27]907。由于各官員的品級不同,誥命敕書封贈的范圍及絲織質地、軸數、圖案也各有不同。
誥敕、印章是明朝中央政府頒給藏族政教首領任官的主要憑證。這些憑證要么是任官時當面賜予,要么在任官后遣使賜予。一般情況下,普通政教首領在來京時頒予,或由貢使返回時轉賜。成化三年十二月,“番僧法王札巴堅參、西天佛子札實巴、國師鎖南堅參、端竹也失、禪師班竹星吉、禮奴班丹以升職奏乞誥敕、印章,與之。”[14]卷49:1001但地位至高者,必須經明朝中央政府遣使頒賜誥敕印章。
第三,事實證明,明代中央政府冊封西藏及其他藏族聚居地方首領的政策十分有效和成功,如“大慈法王”冊封后不久返藏,在西藏修建了色拉寺,并向格魯派僧眾積極宣揚明朝的形象,增加了藏族同胞的民族認同。冊封的歷代大乘法王,“都按明朝的規定定期向朝廷朝貢,為維護西藏地方的安定和加強與朝廷的聯系發揮了重要作用”[9]171。由此可見,經過冊封,明朝在西藏和其他藏族聚居區的統治得以鞏固,藏族政教領袖也獲得了中央政府頒賜的管理各自地方的合法權力。
更為重要的是,經過冊封的西藏地方政教首領,按照中央政府的規定和要求定期朝貢、積極宣揚和維護明朝的形象,必然增加了藏族同胞的民族認同意識,客觀上加強了西藏地方與祖國之間的親密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