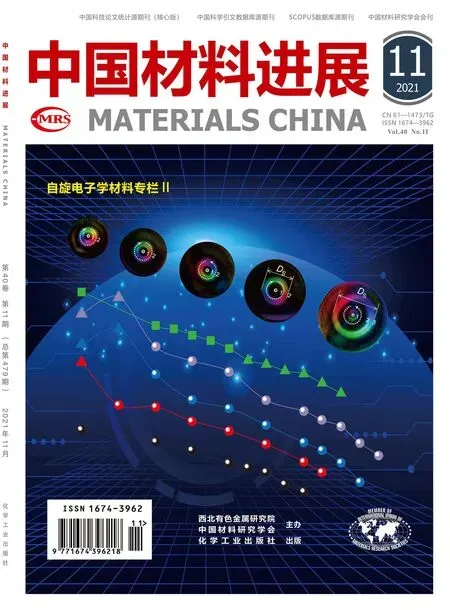細菌介導生物礦化的研究進展
王婉蓉,秦 雯,顧俊婷,鄭秀麗,唐笑怡,焦 凱,牛麗娜
(1.軍事口腔醫學國家重點實驗室 口腔疾病國家臨床醫學研究中心 陜西省口腔醫學重點實驗室第四軍醫大學口腔醫院修復科,陜西 西安 710032)( 2.中國人民解放軍聯勤保障部隊第九二○醫院(昆明醫科大學教學醫院),云南 昆明 650032)
1 前 言
生物礦化是指生物體通過蛋白質等生物大分子調控無機礦物形成的過程。在此過程中形成的具有納米級結構的生物礦物,不僅具備極佳的強度和斷裂韌性,也呈現出良好的生物相容性。迄今為止,已從生物中鑒定出60多種不同的礦物質。這些礦物對于自然界的物質循環起著重要作用[1]。細菌作為自然界最活躍的微生物之一,在生物礦物的形成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目前已經發現了大量由細菌介導生成的礦物,例如有研究發現嗜鹽菌及枝芽孢菌可以促進白云石的形成;球形芽孢桿菌有助于碳酸鈣晶體的形成[2]。
細菌介導的礦化與生命演變息息相關。在原始環境下最早出現的是原核生物礦化,這表明細菌-礦物相互作用是生命史早期的一個重要現象。這種相互作用對于古老地球環境的研究以及尋找其他行星表面生命都有著重大意義[3]。當外界環境轉變至有利于礦化發生時,細菌通常有著多種不同的應答方式,例如通過形成生物膜避免被礦化或在保存細菌活性的前提下嵌入礦物中,甚至可在礦物形成過程中控制其形態。此種現象說明細菌的進化與周圍環境的改變息息相關[4]。
相比于化學合成的方式,細菌合成礦物不僅綠色經濟環保,且操作較為方便,因此細菌介導的生物礦化在環境凈化、工業生產和醫藥研究等領域的潛在應用已成為目前研究的熱點。例如一些由微生物礦化引起的疾病有可能通過對細菌的干預進而治愈[5];由于生物礦物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因此可作為藥物載體應用在腫瘤疾病的靶向治療中[6];除此之外,可通過化學交聯和基因編輯等方式修飾細菌蛋白,使生物礦物的形態和大小根據工業需要進行合成[7]。本文綜述了細菌介導生物礦化的類型、作用機理及應用,為進一步的生物礦化研究提供參考。
2 細菌介導生物礦化的類型
2.1 鈣化
細菌介導的鈣化存在于天然礦物和生物體內。研究發現好氧菌如Salinivibrio和Virgibacillus有助于MgCa-(CO3)2的形成,而MgCa(CO3)2被認為是天然礦物白云石的前體[8]。甲殼類動物、海洋生物、植物甚至人體組織均可見由細菌介導的鈣化發生。甲殼類動物是指蝦、蟹等有堅硬外殼保護的動物,其外殼由甲殼質、結合蛋白和碳酸鈣構成,具有排泄、感知和保護的作用[9]。研究發現甲殼類動物Titanethesalbus的鈣體內存在大量細菌,且鈣體的中心存在結晶晶核[10]。海綿是一種海洋無脊椎動物,體內存在多種鈣化細菌,這些細菌可產生鈣化小球覆蓋在海綿表面,模擬外周骨骼結構,保護海綿免受外界的傷害,從而提高海綿存活率[9, 11]。細菌介導的鈣化也存在于人體組織中。有研究證實尿路結石的發生可能與假單胞菌、乳酸菌及腸桿科菌有關。細菌導致尿路結石產生的可能機制有以下3種:細菌選擇性地聚集在草酸鈣晶體上使鈣鹽增長變快;細菌釋放檸檬酸裂解酶,降低尿液中檸檬酸水平的同時提高草酸鹽濃度,從而導致尿液過飽和,致使結晶形成;細菌-晶體聚集體可與腎小管上皮結合,導致腎小管上皮或炎性細胞中結石基質蛋白的表達,從而形成結石[5]。
細菌誘導的鈣化也可發生在極端環境下。PlanococcushalocryophilusOr1在-15 ℃時可使調控碳酸鈣礦化的碳酸酐酶表達升高,導致更多的碳酸鈣沉積在細菌細胞膜中[12]。
2.2 硅化
除鈣化之外,細菌亦參與了自然界的硅化過程。據報道,在Imawarì Yeuta洞穴中發現的無定形二氧化硅是由絲狀細菌藍藻介導產生的。藍藻的代謝產物使洞穴環境pH值升高,致巖石溶解。溶解產生的二氧化硅可在細菌細胞膜上以無定形的形式重新沉淀[13],形成管狀及絲狀的巖石結構。另外,藍藻的硅化作用有助于化石在形成過程中保存完好的細胞結構,使考古學家可以獲得更多有關古生物的生命信息[14]。
2.3 鐵礦化
多種細菌都可介導產生四氧化三鐵(Fe3O4)和硫化鐵(Fe3S4、Fe1-xS、Fe9S8),其中趨磁細菌(magnetotactic bacteria, MTB)是目前研究的熱點。MTB是一種能夠沿著地球磁場運動或排列的原核生物[15]。目前已知的多數MTB屬于α-蛋白菌、δ-蛋白菌、γ-蛋白菌和硝化螺菌類[16],均為革蘭氏陰性細菌,有球形、弧形、桿形及螺旋形等多種形態。MTB中負責趨磁運動的細胞器是由細菌生物礦化合成的磁小體。磁小體由脂質雙分子膜包裹的納米級磁鐵礦晶體構成[17],是淡水沉積物中的重要天然磁性元素。這些磁性納米晶體具有粒度均一、純度高、磁性強和生物相容性良好等特點。
磁性納米顆粒在自然界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由于產生膠黃鐵礦的MTB需要硫才能合成磁小體,因此膠黃鐵礦被認為是地質歷史上停滯缺氧狀態(一種無氧狀態,由于游離H2S水平升高而呈硫化物狀態)的指標[18]。此外,在微生物的進化過程中,環境中氧氣的出現給微生物帶來了源于活性氧的毒性,而嗜熱性嗜酸菌Sulfolobussolfataricus能夠通過氧化作用將Fe2+氧化成Fe3+形成鐵礦物,這可以認為是原始生命對于氧氣環境的適應[19]。另外人體組織中的磁性納米顆粒與眾多疾病的發生發展有關。有研究在多種人體器官中均發現了磁性納米顆粒的存在,其中小腦和腦干分布較多[20]。由于這些磁性顆粒與MTB產生的晶體較為相似,因此被認為其來源為MTB。研究發現磁性氧化鐵納米顆粒在中樞神經系統細胞(尤其是星形膠質細胞)的過度積累可能導致正常的鐵代謝紊亂,這是神經退行性疾病產生的一個標志性特征,但具體的機制有待于更進一步的研究[21]。
3 細菌介導生物礦化的發生機制
自然界的生物礦化可分為生物誘導礦化和生物控制礦化。生物誘導礦化是由生物的生理代謝活動引起環境條件變化而發生的礦化,其中,生物不能直接控制沉淀物的產生位置或產生方式(圖1a)。生物控制礦化是由生物的生理活動引起的,可產生高度有序的沉淀物,且沉淀物大小、質地和方向受生物體控制(圖1b)[22]。

圖1 生物誘導礦化(a)和生物控制礦化(b)的示意圖[22]Fig.1 Schematic representation of biologically induced mineralization (a) and biologically controlled mineralization (b)[22]
根據發生位置的不同,細菌介導的礦化可分為細胞外礦化和細胞內礦化。細胞外礦化是指發生在細胞周圍基質中的礦化。細胞可通過細胞膜上的蛋白質將陽離子泵出,或通過分泌含有陽離子的囊泡,介導周圍基質的礦化。細胞內礦化則是指由細胞的代謝活動介導的胞內囊泡礦化。細胞內礦化的產物可以存在于細胞內(如MTB),也可以通過胞吐作用釋放到胞外(如硅藻)。礦化的基本化學反應過程為羧基、磷酸基團、胺基和羥基等帶負電荷的基團與金屬陽離子結合,形成礦物。以鈣化物羥基磷灰石(hydroxyapatite,HAP)為例,其基本的化學反應過程如下:
10Ca(OH)2+6H3PO4→ Ca10(PO4)6(OH)2+18H2O
3.1 細胞外礦化
3.1.1 初始礦化
細胞外礦化發生的首要條件是細菌周圍有足夠的可溶性離子。研究發現,細菌可通過多種不同機制增加可溶性離子的濃度,例如大腸桿菌在堿性磷酸酶的作用下可以釋放磷酸根離子[23],浮生細菌可以通過分泌酸(羧酸、鹽酸等)降低環境中的pH值,從而溶解無機磷酸鹽、增加可溶性離子[24]。
初始礦化階段可由經典結晶理論和非經典結晶理論來解釋(圖2)[25]。經典結晶理論認為,成核是相變的開始,這個過程是不可逆的。在細菌礦化過程中,成核位點位于胞外聚合物(extracellular polymeric substances, EPS)或細菌表面蛋白質上。EPS由細菌分泌的大分子構成,包含了多糖、蛋白質、DNA、脂類等物質。由于EPS中的大分子物質含有羧基、磷酸基團、胺基和羥基等帶負電荷的基團,EPS降解后,可與局部過飽和的陽離子相互結合引起礦物沉淀[26]。當成核位點位于細菌表面蛋白質上時,金屬陽離子如鐵離子可直接與細菌表面蛋白質中的羧基和羥基反應,通過金屬氧化反應形成金屬-蛋白質復合物[27]。

圖2 經典結晶理論及非經典結晶理論示意圖[25]Fig.2 Schematic diagram of classical nucleation theory and non-classical nucleation theory[25]
而非經典結晶理論認為晶體的形成是以粒子為媒介,由動力學控制的、與相分離無關的結晶過程。在溶液中首先形成具有彌散邊界的無定形離子簇,稱之為預成核簇(pre-nucleation clusters,PNC)。PNC是熱力學穩定的聚集體,可存在于各種不飽和或超飽和溶液中[28]。接著,PNC聚集形成無定形礦物前體,在碳酸鈣形成過程中的無定形礦化前體為無定形碳酸鈣(amorphous calcium carbonate,ACC)[29],在磷酸鈣形成過程中的無定形礦化前體為無定形磷酸鈣(amorphous calcium phosphate,ACP)[30],繼而無定形礦化前體失去結合水,經過固態轉化結晶[31]。更進一步的研究認為,這種生物礦化過程發生在由特定蛋白質形成的水凝膠環境中,其特有的內部孔隙充當“有限體積的反應容器”,可以促進無定形礦化前體的形成[32]。
3.1.2 晶體生長
晶體生長過程決定了最終晶體的大小和形態。和初始礦化相似,晶體生長也可以通過經典結晶理論和非經典結晶理論來解釋。
經典結晶理論認為,在高過飽和溶液中以成核為主,而在低過飽和溶液中晶體生長占主導地位[33]。在這一過程中依據的是奧斯瓦爾德現象,即在溶液過飽和的情況下,熱力學能量驅動單個原子或分子沉積在成核部位,使材料有序排列生長成穩定的晶體結構。溶液中不同的添加劑和物理參數會導致每個單晶面的生長速率不同,從而形成形態各異、大小不一的晶體[34]。
非經典結晶理論認為,礦化前體無定形碳酸鈣或無定形磷酸鈣通過定向附著形成介晶結構,繼而在蛋白質的引導下組裝聚集成為晶體結構。在此過程中,蛋白質發揮著重要作用。例如海膽脊椎基質蛋白SPSM50不僅可增強無定形礦化前體的穩定性,而且以介晶結構的形式誘導了晶體的定向生長[35]。
3.2 細胞內礦化
細胞內礦化是指用于細胞內礦化的離子在轉運蛋白的作用下被富集至囊泡中,繼而發生礦化[36]。細胞內礦化與細胞外礦化最大的不同在于有囊泡的參與。在此過程中,囊泡膜上的蛋白質以及囊泡內的蛋白質不僅為礦化提供成核位點,也形成了一個“有限體積”以實現蛋白質等分子的集中,稱為分子擁擠(molecular crowding)。在結晶發生前,一些分子(如聚乙二醇)會抑制礦物前體的形成和自我聚集;在結晶發生時另一些大分子(如牛血清白蛋白)則會促進礦化前體的聚集[37]。這一過程也是仿生礦化中的研究熱點。
MTB誘導的鐵礦化是細胞內礦化的典型代表。其在磁小體內產生納米級別鐵磁性顆粒的可能機制如下(圖3)[38]:首先細胞質膜(圖3a)內陷形成囊泡(圖3b),其次轉鐵蛋白將鐵離子(經細胞)轉運到囊泡中。包裹Fe2+的囊泡與細胞骨架接觸時,Fe2+氧化成為Fe3+,膜上的蛋白質啟動成核,并且調控囊泡內礦化形成磁鐵礦晶體(圖3c),稱之為磁小體。磁小體膜上的蛋白質可與肌動蛋白相互作用,使磁小體成鏈狀排列(圖3d)。隨后,在細胞分裂過程中細胞壁通過彎曲磁小體鏈減少磁力,促進磁小體均勻地分離到子細胞中(圖3e和3f)。研究表明,MTB基因組上有一段特殊的區域,稱為磁小體島(圖3g),該基因島與磁小體的形成密切相關。相關基因如mms及mam家族可調控鐵磁性顆粒的形狀和大小[39]。另有研究發現,磁小體內鐵磁性顆粒的形態可能與MTB的來源有一定的關聯。例如來自α-蛋白菌和γ-蛋白菌菌屬的MTB常產生各向同性生長的八面體棱柱形的鐵磁礦,而硝化螺菌菌屬的MTB常產生各向異性生長的子彈型鐵磁礦[40]。

圖3 磁小體的形成過程[38]Fig.3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magnetosomes[38]
4 細菌介導生物礦化的應用
4.1 環境應用
隨著工業化的快速發展,大量的有毒金屬及放射性核素被排放至環境中,對人類健康造成了極大的威脅。如何快速有效地回收環境中的污染物是學者們亟需解決的問題。隨著細菌介導礦化研究的進一步深入,有學者提出可通過耐重金屬細菌誘導有毒金屬礦化來回收環境中的鍶、鎳、鉻、鉛、鈾、鎘等有毒金屬,改善環境質量[41]。雖然高濃度的金屬離子可導致多數細菌核酸紊亂及滲透壓失衡,但對于這些損傷,細菌已進化出了精妙的抗重金屬機制,如金屬離子的跨膜運輸、形成胞內外沉淀、與胞內金屬硫蛋白的螯合作用等均可將有毒金屬離子轉化為無毒或毒性較小的物質(圖4)[42]。由于細菌的大部分抗重金屬基因位于質粒上,因此可通過基因操作得到基因編輯細菌,從而用于生物修復[43]。例如,研究發現趨磁細菌UPB-MAG05菌株對重金屬鎘具有高度耐受性,可介導污染水源中鎘的礦化沉積,繼而在外界磁場的作用下通過磁分離去除,從而凈化水質[44]。磷酸鹽增溶芽孢桿菌可分解含磷酸鹽的有機化合物,在其細胞表面產生磷酸鹽基團,并與鉛離子沉淀為穩定的Pb3(PO4)2,從而達到清除鉛離子的目的[45]。相較于傳統的物理化學修復方法,通過細菌礦化重金屬修復污染環境的方法具有成本低廉、后期處理簡單等優點,但細菌礦化重金屬的長期有效性尚未得到證明,已經結合的重金屬在環境變化的條件下可能重新活化,回到環境中。

圖4 細菌抗多種有毒金屬的機制[42]Fig.4 The mechanism of bacterial resistance to toxic metals[42]
4.2 工業應用
細菌介導的礦化也可以用于電化學領域的能源存儲。研究發現鐵氧化細菌Acidovorax可介導γ-FeOOH發生礦化,形成保留細菌大小和形狀的α-Fe2O3納米晶體。α-Fe2O3納米晶體組裝形成中空多孔的殼,導電性強,在與鋰反應時有更強的電化學可逆性。此種生成納米晶體的方法不僅具有生態友好性,也可實現工業上的規模化生產[46]。由電化學活性細菌Shewanellaoneidensis介導合成的高度分散的鈀金合金納米粒子可用作液體燃料電池的電催化劑[47]。研究發現,通過基因技術使大腸桿菌表面表達硅藻silaffin蛋白的重復片段,其調控合成的納米二氧化鈦銳鈦礦具有出色的鋰儲存性能,可用作鋰離子電池的陽極[48]。
混凝土是目前廣泛使用的建筑材料,但隨著時間的流逝,混凝土內部產生的裂縫會降低建筑結構的機械性能,縮短建筑物使用年限。有研究提出可在混凝土中加入能夠介導碳酸鹽沉淀的細菌,其產生的碳酸鈣可增強混凝土對氯離子和滲透水的抵抗力,提高混凝土耐久性和強度;同時碳酸鈣可填補裂縫,形成自修復混凝土,增加建筑的使用壽命(圖5)[49]。研究證實,當初始裂縫寬度不大于0.5 mm時,使用自修復混凝土時大部分裂縫可完全愈合[47]。但由于混凝土由硅酸鹽水泥制成,水化后可產生氫氧化鈣,使混凝土呈強堿性,且混凝土基質中的孔隙尺寸小于1 μm,而細菌的大小為1~4 μm,這些條件都不利于細菌存活[50]。因此如何提高細菌在混凝土基質中的生存能力是目前的研究熱點。有學者提出可使用微膠囊技術來保護細菌,使細菌在合適的環境下介導碳酸鹽沉淀[51]。

圖5 通過細菌誘導碳酸鈣沉淀修復混凝土開裂的示意圖[49]Fig.5 Schematic of bacteria induced calcium carbonate precipitation to repair concrete cracking[49]
4.3 生物醫學應用
4.3.1 醫療成像設備和診斷
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技術由于具有良好的空間分辨率和軟組織對比度,是臨床上常用的影像檢查手段之一。研究發現MTB產生的磁性納米顆粒具有較強磁性,可作為造影劑增強組織中質子共振吸收,使局部組織圖像得到增強,從而提高檢查的靈敏度和特異性[52]。
除增強成像對比度之外,功能化的磁性納米顆粒芯片還可用于食源性病原物的檢測,如大腸桿菌、霍亂弧菌、空腸彎曲菌、金黃色葡萄球菌等[53]。如圖6所示,趨磁細菌MO-1功能化之后可與金黃色葡萄球菌表面的A蛋白結合,從而實現靶向功能[54]。目前可以通過化學修飾和基因工程的方法生產功能化磁小體。

圖6 趨磁細菌靶向金黃色葡萄球菌的微機器人系統的構建[54]Fig.6 Construction of a microrobot system using magnetotactic bacteria for targeting Staphylococcus aureus[54]
化學修飾作用于磁小體中的Mam、Mms等蛋白上,有以下結合方式:① 通過磁小體膜上的氨基或羧基進行功能化修飾,例如經肽P75修飾的磁小體可與人表皮生長因子受體和上皮生長因子受體2結合[55];② 使用葡萄球菌蛋白A用作融合標簽,葡萄球菌蛋白A作為一種免疫球蛋白G結合蛋白,可與MamC、MamF以及免疫球蛋白Fc區結合,從而介導磁小體-葡萄球菌蛋白A復合物與抗體結合[56];③ 利用磁小體膜上的—NH2基團與抗體的—NH2或—SH基團之間的反應進行化學修飾;④ 用生物素/鏈霉親和素進行修飾;⑤ 利用正負電荷之間的相互作用進行修飾,磁小體膜上的磷脂帶有負電荷,可與帶正電荷的抗癌重組質粒熱激蛋白、70-polo樣激酶1短發夾RNA以及阿霉素結合[57]。
另外還可通過基因工程改造對磁小體進行功能化修飾。將表達功能蛋白的基因與mms16,mam13等膜蛋白基因融合,再將融合基因轉移到MTB中,從而可實現目標蛋白的表達。例如,將磁小體和翡翠綠色熒光蛋白(EmGFP)或生物素修飾的煙草花葉病毒(tobacco mosaic virus,TMV)共同培養,可生成表達這些蛋白的磁性納米鏈[58]。
由于化學修飾可能引入有毒物質,且在MTB中引入外來活性蛋白質的基因的操作比較復雜,因此最近的研究中提出了一種新的修飾方法。首先通過基因技術在大腸肝菌中表達與磁小體MamC蛋白融合的抗人表皮生長因子受體2(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2,HER2),然后去除磁小體膜中的磷脂雙層中的膜蛋白,以利于從大腸肝菌中提取的基因工程產物抗HER2與磁小體上的MamC蛋白結合,從而實現HER2陽性乳腺癌在磁共振成像中的檢測[59]。這種技術有望成為無創檢測腫瘤的手段,具有較大的臨床應用價值。
4.3.2 抗腫瘤方法
高溫療法可通過多種機制作用于癌細胞上使其變性壞死,但目前該療法缺乏特異性,難以區分健康細胞與癌細胞。遂有研究提出“生物靶向磁性熱療”的概念,意為在外源交變磁場的作用下加熱磁性顆粒,由于磁滯損耗或松弛損耗產生不同程度的升溫現象,可在磁性顆粒聚集的地方選擇性地抑制癌細胞增殖[60]。由MTB產生的磁小體由于磁性較強,可在交變磁場中產生較大的熱量;同時由于磁小體呈鏈狀排列,不易聚集,可使腫瘤細胞均勻升溫,有效抑制其增殖[61],因此磁小體在磁熱療領域有較大的應用前景。研究表明,聚賴氨酸包裹的磁小體具有更好的生物相容性,在膠質母細胞瘤小鼠模型的實驗性磁熱療中,可顯著抑制腫瘤細胞的生長[6]。但是到目前為止,多數關于磁小體抗腫瘤治療的研究都是使用腫瘤細胞株進行實驗的,未進行動物實驗研究或人類臨床試驗,因此磁小體的臨床抗腫瘤能力還需進一步驗證。
4.3.3 藥物輸送系統
靶向給藥是指將藥物選擇性地傳輸定位于病變位置,從而發揮藥理作用的給藥方式。在腫瘤微環境中,由于細胞的大量增殖消耗氧氣,腫瘤組織周圍氧氣缺乏。目前使用的納米藥物載體,如脂質體、膠束、聚合物納米顆粒難以到達缺氧區域,靶向率低。而MTB適合厭氧生長,故目前有研究通過MTB和磁小體構建納米機器人,在外磁場的作用下,納米機器人可聚集于病變部位,提高病變部位的藥物濃度,改善治療效果[62]。例如,將載有藥物的納米脂質體交聯至海洋趨磁細菌MC-1表面,并將其注射到實驗小鼠的腫瘤組織周圍,在外磁場的作用下,有高達55%的MC-1細胞滲透到腫瘤缺氧區[63]。
5 結 語
綜上所述,相比于物理和化學合成方法,細菌介導生成的礦物在環境、工業及生物醫學領域均發揮著重要的作用。雖然目前對細菌介導的生物礦化的研究已經取得部分進展,但仍有許多關鍵的科學問題亟待解決。由于多數細菌介導礦物生成的實驗室培養條件并不適宜工業化生產,所以如何將實驗室階段的科學成果轉化為可規模化生產的具體技術是限制其應用的關鍵瓶頸。其次,雖然納米機器人在腫瘤治療領域有較大的應用前景,但人體免疫系統對其會有如何反應目前尚不完全清楚[64]。為了實現細菌介導生物礦化的大規模應用,還需進一步地研究以解決上述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