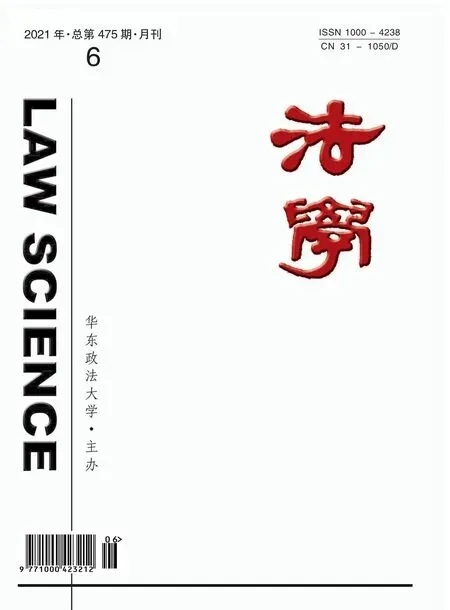我國網(wǎng)絡(luò)音樂獨家許可的運行邏輯與完善策略
●李 陶
一、研究路徑的設(shè)定與研究工具的選擇
對網(wǎng)絡(luò)音樂許可實踐中“搶奪獨家版權(quán)”“哄抬許可費價格”“惡性競爭”等亂象的規(guī)制,是近年來我國著作權(quán)法和反壟斷法領(lǐng)域共同關(guān)注的難點。對此,依《著作權(quán)法》展開的研究多強調(diào)預(yù)防與治理,通過比較法和立法論層面的闡釋,主要從新型法定許可的創(chuàng)設(shè)、競爭性集體管理模式的引入、著作權(quán)主管部門行政權(quán)力的運用等方面對相關(guān)問題進行討論。〔1〕代表性研究參見王遷:《著作權(quán)法限制音樂專有許可的正當(dāng)性》,載《法學(xué)研究》2019年第2期,第98-117頁;蔣一可:《數(shù)字音樂著作權(quán)許可模式探究——兼議法定許可的必要性及其制度構(gòu)建》,載《東方法學(xué)》2019年第1期,第147-160頁;熊琦:《中國著作權(quán)立法中的制度創(chuàng)新》,載《中國社會科學(xué)》2018年第7期,第118-138頁。基于《反壟斷法》展開的研究則多聚焦于救濟與執(zhí)法,通過經(jīng)濟學(xué)和解釋論層面的分析,主要針對網(wǎng)絡(luò)音樂服務(wù)商的經(jīng)營者集中、網(wǎng)絡(luò)音樂服務(wù)商和音樂產(chǎn)權(quán)主體間的縱向非價格壟斷協(xié)議、網(wǎng)絡(luò)音樂服務(wù)商可能存在的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等問題展開討論。〔2〕代表性研究參見寧立志、王宇:《叫停網(wǎng)絡(luò)音樂市場版權(quán)獨家交易的競爭法思考》,載《法學(xué)》2018年第8期,第169-181頁;王健、方燕、徐士英、呂明瑜:《“數(shù)字音樂版權(quán)獨家授權(quán)的競爭法問題”筆談》,載《法治研究》2018年第5期,第41-53頁。
就上述研究的結(jié)論而言,論者們雖聚訟盈庭,莫衷一是,但著眼于《著作權(quán)法》與《反壟斷法》在規(guī)制相關(guān)問題上各自的功能,通說認(rèn)為,對我國網(wǎng)絡(luò)音樂獨家許可模式的治理與優(yōu)化,應(yīng)首先考慮通過《著作權(quán)法》內(nèi)部的機制完成,如果《著作權(quán)法》不能長期、系統(tǒng)、有效地為產(chǎn)業(yè)運行提供符合其立法價值目標(biāo)的制度保障,即存在《著作權(quán)法》上的漏洞且該法律漏洞誘發(fā)了限制競爭的后果時,《反壟斷法》就應(yīng)當(dāng)承擔(dān)規(guī)制相關(guān)限制競爭行為的任務(wù)。〔3〕參見時建中:《著作權(quán)內(nèi)在利益平衡機制與反壟斷法的介入——美國錄音制品數(shù)字表演權(quán)制度的啟示》,載《法學(xué)雜志》2018年第2期,第25-33頁。對此,數(shù)字經(jīng)濟與平臺經(jīng)濟下的反壟斷問題雖是我國2021年立法、司法和執(zhí)法的重點,〔4〕參見《國務(wù)院反壟斷委員會關(guān)于平臺經(jīng)濟領(lǐng)域的反壟斷指南》,國反壟發(fā)〔2021〕1號,2021年2月7日發(fā)布。但科學(xué)、合理地化解網(wǎng)絡(luò)音樂許可實踐中不同主體間的矛盾,還有賴于《著作權(quán)法》內(nèi)部機制的完善。特別是在2020年11月11日《著作權(quán)法修正案》審議通過,相關(guān)著作權(quán)法實施條例亟待修訂之時,檢視修訂前的《著作權(quán)法》在網(wǎng)絡(luò)音樂許可問題上的治理績效,評估修訂后的《著作權(quán)法》對未來網(wǎng)絡(luò)音樂許可實踐的影響,進而指出相關(guān)配套條例在后續(xù)修訂時所應(yīng)關(guān)注的內(nèi)容不但尤為必要,而且正當(dāng)其時。
在對著作權(quán)法領(lǐng)域有關(guān)網(wǎng)絡(luò)音樂獨家許可治理的研究進行回顧后,不難發(fā)現(xiàn)既有研究在“問題意識本土化”與 “完善策略體系化”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不足。問題意識本土化之不足在討論中多表現(xiàn)為偏愛域外法上破解類似問題的具體方案,對照我國進行立法論層面的經(jīng)驗分析,即將優(yōu)化網(wǎng)絡(luò)音樂許可運行的域外法方案(例如創(chuàng)設(shè)新型法定許可、完善集體管理)認(rèn)定為我國網(wǎng)絡(luò)音樂獨家許可運行中諸多亂象的應(yīng)對之策,其意在表明倘若我國的相關(guān)制度(法定許可、集體管理)從一開始便能設(shè)計完備、運行暢達,則網(wǎng)絡(luò)音樂許可實踐中的種種亂象就根本不會出現(xiàn)。完善策略體系化之不足在討論中則表現(xiàn)為未能從《著作權(quán)法》內(nèi)部不同機制的價值與功能出發(fā),對其在誘發(fā)和解決相關(guān)問題上的作用進行體系性思考,即將我國網(wǎng)絡(luò)音樂許可的諸多問題歸因于《著作權(quán)法》在某些外在制度(法定許可、集體管理)上的漏洞,并將化解沖突的希望孤立地寄托在對制度漏洞單純的立法填補之上。換言之,不但常常忽視與其他匹配制度橫向的關(guān)聯(lián)性與協(xié)同性的考察,而且疏于對不同制度設(shè)計所蘊含內(nèi)在價值目標(biāo)的縱向的動態(tài)評估與實踐反思。
在本文看來,既有研究的這些不足或是由于我國知識產(chǎn)權(quán)法學(xué)研究在方法論運用上的慣性所致。〔5〕有學(xué)者指出:“基礎(chǔ)研究的貧弱與細節(jié)研究的繁榮,使得我們看不到知識產(chǎn)權(quán)法學(xué)的存在,只有知識產(chǎn)權(quán)法。” 李琛:《論知識產(chǎn)權(quán)法的體系化》,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5年版,第1頁。欲克服這一積弊,理當(dāng)運用批判思維,對知識產(chǎn)權(quán)法學(xué)在研究中習(xí)慣使用的研究方法進行檢視與創(chuàng)新。〔6〕參見李其瑞:《論法學(xué)研究方法的多元化趨向》,載《法律科學(xué)》2004年第4期,第16-22頁。為了彌補既有研究的上述不足,本文以法學(xué)實證研究作為分析工具。就某一社會現(xiàn)象進行法學(xué)實證層面的研究,通常可結(jié)合法的存在形態(tài),從經(jīng)驗事實、制度規(guī)范與價值取向三個方面展開。〔7〕參見朱景文:《現(xiàn)代西方法社會學(xué)》,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24-46頁;白建軍:《論法律實證分析》,載《中國法學(xué)》2000年第4期,第29-39頁。經(jīng)驗事實作為社會運行發(fā)展之表象,反映了法外在的制度規(guī)范與內(nèi)在的價值取向在特定時間和空間上的實踐表達。對經(jīng)驗事實客觀的描述、分析與總結(jié),有助于從實然角度科學(xué)地評價制度規(guī)范的運行效果,發(fā)現(xiàn)經(jīng)驗事實和制度規(guī)范兩者在實踐中的互動因果規(guī)律,動態(tài)地理解經(jīng)驗事實、制度規(guī)范和價值取向三者的運行邏輯。〔8〕參見孫笑俠:《法學(xué)的本相——兼論法科教育轉(zhuǎn)型》,載《中外法學(xué)》2008年第3期,第421-424頁。
二、經(jīng)驗事實:技術(shù)變遷背景下音樂產(chǎn)業(yè)轉(zhuǎn)型的本土策略
實證研究之要義在于通過對社會事實的考察與思辨,發(fā)現(xiàn)科學(xué)性與一般性的經(jīng)驗規(guī)律。〔9〕參見[法]奧古斯特·孔德:《論實證精神》,黃建華譯,商務(wù)印書館1996年版,第29-35頁。為貫徹本土化研究與實踐哲學(xué)所提倡的方法論自覺,〔10〕實踐哲學(xué)及其對法理學(xué)、部門法學(xué)研究的影響參見張汝倫:《作為第一哲學(xué)的實踐哲學(xué)及其實踐概念》,載《復(fù)旦學(xué)報(社會科學(xué)版)》2005年第5期,第155-163頁;葉會成:《實踐哲學(xué)視域下的法哲學(xué)研究:一個反思性評述》,載《浙江大學(xué)學(xué)報(人文社會科學(xué)版)》2017年第4期,第48-59頁。進而客觀地揭示我國《著作權(quán)法》治理某一具體現(xiàn)象所存在的制度設(shè)計與價值轉(zhuǎn)化上的元問題,〔11〕對具體命題法學(xué)及哲學(xué)研究中元問題的理解和判斷,參見劉艷紅:《人工智能法學(xué)研究的反智化批判》,載《東方法學(xué)》2019年第5期,第121-123頁;俞吾金:《再談?wù)軐W(xué)的元問題》,載《學(xué)術(shù)月刊》1995年第10期,第24-26頁。下文將從實證視角對我國網(wǎng)絡(luò)音樂獨家許可的生成與演進予以考察與分析。
(一)本土事實和域外事實的共性
20世紀(jì)末,數(shù)字技術(shù)的發(fā)展與網(wǎng)絡(luò)技術(shù)的普及,引發(fā)了全球音樂產(chǎn)業(yè)數(shù)字化和網(wǎng)絡(luò)化的轉(zhuǎn)型。〔12〕參見葉青:《網(wǎng)絡(luò)數(shù)字音樂力量與我國唱片音樂產(chǎn)業(yè)轉(zhuǎn)型》,載《音樂傳播》2012年第2期,第38-46頁。區(qū)別于此前的產(chǎn)業(yè)轉(zhuǎn)型,音樂產(chǎn)業(yè)的本次轉(zhuǎn)型顛覆了該領(lǐng)域市場主體以往的營收模式。對此,通過分析“國際唱片業(yè)協(xié)會”(簡稱IFPI,代表產(chǎn)業(yè)中的鄰接權(quán)主體)與“國際作者和作曲者協(xié)會聯(lián)合會”(簡稱CISAC,代表產(chǎn)業(yè)中的著作權(quán)主體)所公布的過去20年的動態(tài)數(shù)據(jù),可知音樂產(chǎn)業(yè)主要的營收模式正從“唱片公司發(fā)行實體唱片”向“唱片公司及其版權(quán)代理公司對網(wǎng)絡(luò)音樂平臺發(fā)放使用許可”轉(zhuǎn)變。〔13〕See IFPI, IFPI Issues Global Music Report 2021, IFPI News (Mar. 23, 2021), https://www.ifpi.org/ifpi-issues-annual-globalmusic-report-2021/; CISAC, Global Collections Report (2020), CISAC News (Oct. 28, 2020), https://www.cisac.org/Newsroom/globalcollections/global-collections-report-2020, last visit both on May 8, 2021.2021年3月IFPI公布的最新數(shù)據(jù)顯示,實體唱片發(fā)行所占的行業(yè)收入在全球已下降至19.5%;而音樂在線服務(wù)和下載服務(wù)的收入已占唱片行業(yè)總收入的67.9%。〔14〕同上注,國際唱片業(yè)協(xié)會(IFPI)報告。
在此營收模式下,作為商業(yè)使用者的網(wǎng)絡(luò)音樂服務(wù)商,若想向終端用戶提供音樂的在線收聽或下載等服務(wù),需同時從錄音制作者、表演者和詞曲作者處分別取得一首歌曲的鄰接權(quán)授權(quán)和著作權(quán)授權(quán)。在實踐中,錄音制作者和表演者的鄰接權(quán)往往由唱片公司負(fù)責(zé)鄰接權(quán)代理的機構(gòu)(部門)運營;而詞曲作者的著作權(quán)則主要由唱片公司負(fù)責(zé)著作權(quán)代理的機構(gòu)(部門)運營。〔15〕為保障詞曲作者的權(quán)益,避免弱勢詞曲作者的著作權(quán)被買斷,錄音制作者、表演者的鄰接權(quán)與詞曲作者的著作權(quán)在國際范圍內(nèi),在初始階段多采用分開代理和經(jīng)營的模式。相應(yīng)的著作權(quán)代理主體和鄰接權(quán)代理主體,要么直接向商業(yè)使用者授權(quán),要么通過集體管理組織間接向商業(yè)使用者授權(quán)。以世界三大唱片公司中的環(huán)球和華納為例,環(huán)球音樂集團旗下的詞曲作者著作權(quán)由環(huán)球音樂版權(quán)(UMPG)負(fù)責(zé)運營;環(huán)球音樂集團旗下的錄音制作者和表演者鄰接權(quán)則由環(huán)球唱片(UMG)負(fù)責(zé)運營。〔16〕二者的區(qū)別可參見其網(wǎng)站:https://www.umusicpub.com/; https://www.universalmusic.com/。對以上網(wǎng)站的訪問日期均為2021年5月15日。華納音樂集團旗下的詞曲作者著作權(quán)由華納音樂版權(quán)(WCM)負(fù)責(zé)運營;華納音樂集團旗下的錄音制作者和表演者鄰接權(quán)則由華納唱片(WMG)負(fù)責(zé)運營。〔17〕二者的區(qū)別可參見其網(wǎng)站:https://www.warnerchappell.com/; https://www.warnermusic.com.cn/。對以上網(wǎng)站的訪問日期均為2021年5月15日。易言之,如果作為網(wǎng)絡(luò)音樂服務(wù)商的騰訊音樂想在其平臺上向終端用戶提供世界三大唱片公司(環(huán)球、華納、索尼)曲庫中歌曲的在線收聽和下載等服務(wù),就需要分別與上述三家唱片公司所屬的6個版權(quán)(鄰接權(quán)、著作權(quán))代理主體商談。此外,除了像騰訊音樂一樣專門提供網(wǎng)絡(luò)音樂服務(wù)的市場主體外,但凡在經(jīng)營中使用了音樂的直播平臺、短視頻(音頻)平臺、長視頻(音頻)平臺,都需要從上游的權(quán)利(著作權(quán)、鄰接權(quán))主體處取得相應(yīng)的音樂使用許可。〔18〕參見中國音像著作權(quán)集體管理協(xié)會(以下簡稱音集協(xié)):《短視頻使用音樂應(yīng)當(dāng)取得授權(quán)》,https://www.cavca.org/newsDetail/1402,2021年5月15日訪問。上述眾多類型的網(wǎng)絡(luò)音樂服務(wù)商和不同類型的音樂產(chǎn)權(quán)主體之間復(fù)雜而多樣的權(quán)利許可交易,引發(fā)了全球網(wǎng)絡(luò)環(huán)境下數(shù)字音樂許可模式的調(diào)整與再造。圍繞其展開的著作權(quán)(許可)制度改革也成為近年來各國立法者、學(xué)者以及產(chǎn)業(yè)主體共同關(guān)注的問題。〔19〕國內(nèi)代表性研究參見熊琦:《數(shù)字音樂之道:網(wǎng)絡(luò)時代音樂著作權(quán)許可模式研究》,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5年版;域外代表性研究參見Kung-Chung Liu and Reto M. Hilty (eds.), Remuneration of Copyright Owners: Regulatory Challenges of New Business Models,Springer, 2017.
(二)本土事實和域外事實的差異
在上述技術(shù)變遷與商業(yè)模式轉(zhuǎn)變的背景下,歐盟在2014年通過了專門性的《跨境音樂著作權(quán)和鄰接權(quán)集體管理指令》(以下簡稱歐盟《音樂集體管理指令》),以創(chuàng)設(shè)新型集體管理模式、引入集體管理組織對使用者的強制締約義務(wù)、完善集體管理組織的內(nèi)部治理、強化對集體管理組織的外部監(jiān)管(特別是細化了費率標(biāo)準(zhǔn)異議的糾紛解決程序)的方式,率先開啟了全球范圍內(nèi)立法者對網(wǎng)絡(luò)音樂許可模式改造的進程。〔20〕Vgl. Reinbothe, in: Schricker/Loewenheim, 6. Aufl., 2020, Einleitung zum VGG Rdn. 29 あ.為轉(zhuǎn)化該指令,德國于2016年廢止了1965年《著作權(quán)集體管理法》,頒布了全新的《著作權(quán)和鄰接權(quán)集體管理組織法》(VGG)。〔21〕Vgl. BT-Drs. 18/8268.美國則于2018年10月通過了《音樂現(xiàn)代化法案》(MMA),以立法方式創(chuàng)設(shè)了新型法定許可,引入了法定集體管理,設(shè)立了針對網(wǎng)絡(luò)音樂許可的一站式集體管理組織,完善了對集體管理組織的內(nèi)部治理,強化了對集體管理組織的外部監(jiān)管(特別是細化了費率標(biāo)準(zhǔn)異議的糾紛解決程序)。〔22〕國內(nèi)代表性研究參見王宇:《數(shù)字環(huán)境對音樂版權(quán)制度的挑戰(zhàn)及立法應(yīng)對——以美國〈音樂現(xiàn)代化法案〉為研究樣本》,載《電子知識產(chǎn)權(quán)》2019年第11期,第4-18頁。除了歐洲和北美兩大音樂市場的立法動態(tài)外,英國和澳大利亞也在其產(chǎn)業(yè)實踐中對以往的網(wǎng)絡(luò)音樂授權(quán)模式進行了改造與創(chuàng)新。在英國,負(fù)責(zé)音樂著作權(quán)和鄰接權(quán)的集體管理組織(MCPS-PRS)和負(fù)責(zé)表演者與錄音制作者鄰接權(quán)的集體管理組織(PPL),在2018年共同組建了一個全新的音樂版權(quán)聯(lián)合清算平臺(PPL PRS Ltd),以此完成了英國境內(nèi)網(wǎng)絡(luò)音樂授權(quán)許可的一站式改造。〔23〕對三者的了解可參見其網(wǎng)站:https://www.prsformusic.com/; https://www.ppluk.com/;https://pplprs.co.uk/。對以上網(wǎng)站的訪問日期均為2021年5月15日。在澳大利亞,負(fù)責(zé)音樂詞曲作者著作權(quán)的集體管理組織(APRA, AMCOS)和負(fù)責(zé)音樂鄰接權(quán)的集體管理組織(PPCA),在2019年也共同組建了一個全新的音樂版權(quán)聯(lián)合清算平臺(One Music Australia),同樣完成了澳大利亞境內(nèi)網(wǎng)絡(luò)音樂授權(quán)許可的一站式改造。〔24〕對三者的了解可參見其網(wǎng)站:https://www.apraamcos.com.au/; http://www.ppca.com.au/; https://onemusic.com.au/。對以上網(wǎng)站的訪問日期均為2021年5月15日。
回顧我國音樂產(chǎn)業(yè)數(shù)字化和網(wǎng)絡(luò)化的轉(zhuǎn)型歷程,截至2021年5月,以網(wǎng)絡(luò)音樂服務(wù)商取得音樂使用許可的方式為標(biāo)準(zhǔn),可將音樂產(chǎn)業(yè)在我國的本次轉(zhuǎn)型劃分為以下四個階段:以“違法使用”為主要業(yè)態(tài)的轉(zhuǎn)型初期(第一階段,2015年之前);〔25〕參見于慈珂:《構(gòu)建良好的網(wǎng)絡(luò)音樂版權(quán)生態(tài) 推動我國網(wǎng)絡(luò)音樂產(chǎn)業(yè)健康發(fā)展》,載《中國出版》2015年第8期,第48頁。以“獨家許可”為主要權(quán)利取得方式的轉(zhuǎn)型過渡期(第二階段,2015-2017年);〔26〕參見張豐艷:《獨家版權(quán)是推動音樂正版化良藥》,載《光明日報》2017年5月5日,第2版。以“獨家許可加轉(zhuǎn)授權(quán)”(網(wǎng)絡(luò)音樂服務(wù)商之間的交叉授權(quán))為主要權(quán)利取得方式和權(quán)利流轉(zhuǎn)方式的轉(zhuǎn)型調(diào)試期(第三階段,2017-2020年);〔27〕參見熊文聰:《在線音樂獨家版權(quán)的困境與出路》,載《競爭政策研究》2018年第5期,第55-56頁。“以非獨家許可為主、以獨家許可為輔”的轉(zhuǎn)型再調(diào)試期(第四階段,2020年之后)。之所以將目前產(chǎn)業(yè)界所采用的“以非獨家許可為主、以獨家許可為輔”的模式認(rèn)定為轉(zhuǎn)型的再調(diào)試期,是因為著眼于我國《著作權(quán)法》的價值取向和產(chǎn)業(yè)實踐方向,該模式尚存在繼續(xù)完善的空間。劃分上述四個階段的三個標(biāo)志性事件分別為:2015年國家版權(quán)局發(fā)布《關(guān)于責(zé)令網(wǎng)絡(luò)音樂服務(wù)商停止未經(jīng)授權(quán)傳播音樂作品的通知》;〔28〕參見國家版權(quán)局:《關(guān)于責(zé)令網(wǎng)絡(luò)音樂服務(wù)商停止未經(jīng)授權(quán)傳播音樂作品的通知》,http://www.cac.gov.cn/2015-08/04/c_1116136707.htm,2021年5月15日訪問。2017年國家版權(quán)局約談國內(nèi)主要網(wǎng)絡(luò)音樂服務(wù)商、境內(nèi)外唱片公司及國際唱片業(yè)協(xié)會(IFPI);〔29〕參見國家版權(quán)局:《國家版權(quán)局約談主要網(wǎng)絡(luò)音樂服務(wù)商 要求全面授權(quán)廣泛傳播音樂作品》,http://www.ncac.gov.cn/chinacopyright/contents/518/349213.html,2021年5月15日訪問。2020年網(wǎng)易云音樂終結(jié)了此前騰訊音樂與前述世界三大唱片公司的獨家授權(quán)模式,與華納音樂版權(quán)(WCM)以及環(huán)球唱片(UMG)分別就詞曲作者著作權(quán)以及錄音制作者及表演者鄰接權(quán)簽署許可協(xié)議。〔30〕參見賀泓源:《網(wǎng)易云音樂牽手華納版權(quán):騰訊獨家到期 昂貴版權(quán)大戰(zhàn)何往?》,https://m.21jingji.com/article/20200512/herald/d98224936963f3362c8f81ea8aca6928.html;徐冰倩:《音樂版權(quán)獨家授權(quán)模式將終結(jié)?環(huán)球音樂同時授權(quán)網(wǎng)易云、騰訊音樂》,https://m.mp.oeeee.com/a/BAAFRD000020200811353654.html。對以上鏈接的訪問日期均為2021年5月15日。
(三)本土靜態(tài)事實和動態(tài)事實的因果邏輯
本文認(rèn)為,音樂產(chǎn)業(yè)在我國的網(wǎng)絡(luò)化轉(zhuǎn)型所歷經(jīng)的上述四個階段互為因果,存在引起與被引起的關(guān)系。其一,轉(zhuǎn)型初期網(wǎng)絡(luò)音樂服務(wù)商“違法使用”音樂制品(作品)行為的盛行,致使作為上游產(chǎn)權(quán)主體的音樂權(quán)利人和作為下游商業(yè)使用者的網(wǎng)絡(luò)音樂服務(wù)商合意采用“獨家許可”的方式遏制侵權(quán)。其二,“獨家許可”在運行中引發(fā)的網(wǎng)絡(luò)音樂服務(wù)商搶奪獨家版權(quán)與哄抬授權(quán)價格等現(xiàn)象,又導(dǎo)致了轉(zhuǎn)型調(diào)試期“獨家許可加轉(zhuǎn)授權(quán)”這一網(wǎng)絡(luò)音樂服務(wù)商就各自擁有的曲庫進行交叉授權(quán)模式的出現(xiàn)。其三,自2020年以來,在存在于網(wǎng)絡(luò)音樂服務(wù)商和產(chǎn)權(quán)主體間的獨家許可、存在于網(wǎng)絡(luò)音樂服務(wù)商彼此間的交叉許可合同相繼到期后,為落實著作權(quán)主管部門“促進網(wǎng)絡(luò)音樂廣泛傳播”的要求,上游產(chǎn)權(quán)主體和下游網(wǎng)絡(luò)音樂服務(wù)商在保留了極少部分獨家許可用以實現(xiàn)曲庫差異化發(fā)展的基礎(chǔ)上,對大部分音樂適用了非獨家許可的授權(quán)模式。〔31〕參見國家版權(quán)局:《國家版權(quán)局推動騰訊音樂與網(wǎng)易云音樂達成版權(quán)合作》,http://www.ncac.gov.cn/chinacopyright/contents/12227/347475.shtml,2021年5月15日訪問。至此,“以非獨家許可為主、以獨家許可為輔”的產(chǎn)業(yè)轉(zhuǎn)型再調(diào)試期也正式開啟。在應(yīng)對手段上,政府的兩次約談雖在短時間內(nèi)起到了立竿見影的效果,但在缺乏系統(tǒng)分析與統(tǒng)籌安排的情況下,著作權(quán)主管部門以行政手段調(diào)整市場主體行為,難以全面、長期、科學(xué)地實現(xiàn)《著作權(quán)法》引導(dǎo)音樂產(chǎn)業(yè)網(wǎng)絡(luò)化、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的價值目標(biāo)。有學(xué)者指出,相關(guān)部門在此問題上所采用的規(guī)制策略,將本可在著作權(quán)制度框架下解決的問題,擴大為需要競爭法介入方能有效遏制的綜合性問題。〔32〕同前注〔3〕,時建中文,第29-31頁。
通過上述考察與分析,可以總結(jié)出以下經(jīng)驗結(jié)論。第一,中國網(wǎng)絡(luò)音樂獨家許可的生成與演進,反映的是在全球技術(shù)變遷和商業(yè)模式轉(zhuǎn)變的共同背景下,音樂產(chǎn)業(yè)主體在中國轉(zhuǎn)型的一種本土性選擇。第二,音樂產(chǎn)業(yè)在他國的轉(zhuǎn)型路徑主要是圍繞著作權(quán)集體管理組織的實踐運行和對其立法層面的完善展開的;而音樂產(chǎn)業(yè)在我國的轉(zhuǎn)型路徑則主要是圍繞網(wǎng)絡(luò)音樂獨家許可的實踐運行和對其行政干預(yù)層面的完善展開的。第三,在本次產(chǎn)業(yè)轉(zhuǎn)型的過程中,他國音樂產(chǎn)業(yè)的產(chǎn)權(quán)主體(詞曲作者、錄音制作者、表演者)大多通過集體管理組織間接地向商業(yè)使用者(網(wǎng)絡(luò)音樂服務(wù)商和其他在經(jīng)營活動中使用了音樂的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授權(quán);而我國音樂產(chǎn)業(yè)的產(chǎn)權(quán)主體則大多沒有通過集體管理組織間接地向上述商業(yè)使用者授權(quán),而是通過相應(yīng)的著作權(quán)代理主體(公司內(nèi)部負(fù)責(zé)著作權(quán)運營的部門或獨立的著作權(quán)運營主體),直接與作為商業(yè)使用者的網(wǎng)絡(luò)音樂服務(wù)商商談并向其授權(quán)。
由此可見,首先,從產(chǎn)業(yè)實踐的角度看,究竟是選擇集體管理的間接授權(quán)模式,還是選擇獨家許可的直接授權(quán)模式,是產(chǎn)業(yè)主體在他國和在我國進行產(chǎn)業(yè)轉(zhuǎn)型的最大區(qū)別。其次,從政府角色的角度看,究竟是主要采用專門性立法的規(guī)制,還是主要采用靈活性行政的干預(yù),是域外立法者和我國公權(quán)力主體在助力產(chǎn)業(yè)轉(zhuǎn)型上最大的區(qū)別。接下來應(yīng)結(jié)合我國《著作權(quán)法》具體的制度規(guī)范與特定的價值取向,針對產(chǎn)業(yè)主體在域外和我國所采用的不同轉(zhuǎn)型路徑,以及政府在域外和我國所采用的不同規(guī)制策略等相關(guān)事實,思考以下兩個問題。第一,在域外,為何產(chǎn)業(yè)主體和政府會選擇通過對著作權(quán)集體管理組織及其配套機制的立法完善,助力音樂產(chǎn)業(yè)的網(wǎng)絡(luò)化和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第二,在我國,為何產(chǎn)業(yè)主體和政府會選擇通過對網(wǎng)絡(luò)音樂獨家許可模式的運用和改造,助力音樂產(chǎn)業(yè)的網(wǎng)絡(luò)化和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
三、制度規(guī)范:產(chǎn)業(yè)主體和政府策略選擇的外在體系因素
著眼于我國《著作權(quán)法》為音樂產(chǎn)權(quán)運行提供的制度框架,下文將從產(chǎn)權(quán)設(shè)計、救濟措施、運行保障、限制例外四個方面〔33〕參見吳漢東:《中國知識產(chǎn)權(quán)法律變遷的基本面向》,載《中國社會科學(xué)》2018年第8期,第109頁。考察這些著作權(quán)制度在網(wǎng)絡(luò)音樂獨家許可模式生成和演進上的動態(tài)邏輯。
第一,在產(chǎn)權(quán)設(shè)計層面,2020年修訂之前的《著作權(quán)法》的相關(guān)產(chǎn)權(quán)設(shè)計模糊。在音樂產(chǎn)業(yè)的轉(zhuǎn)型過程中,模糊的產(chǎn)權(quán)設(shè)計未能向上游產(chǎn)權(quán)主體提供產(chǎn)業(yè)轉(zhuǎn)型所需的明確而穩(wěn)定的產(chǎn)權(quán)制度保障。面對網(wǎng)絡(luò)領(lǐng)域利用著作權(quán)客體的新型商業(yè)行為,《世界知識產(chǎn)權(quán)組織版權(quán)條約》(簡稱WCT)和《世界知識產(chǎn)權(quán)組織表演和錄音制品條約》(簡稱WPPT)將著作權(quán)制度對作者、表演者及錄音制作者的保護延伸至網(wǎng)絡(luò)。〔34〕參見吳偉光:《數(shù)字技術(shù)環(huán)境下的版權(quán)法危機與對策》,知識產(chǎn)權(quán)出版社2008年版,第52-63頁。對此,我國立法者將國際公約所規(guī)定的“向公眾提供權(quán)”(WCT第8條)以“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權(quán)”(2010年《著作權(quán)法》第10條第1款第12項)進行了轉(zhuǎn)化。與歐美的立法方式相比,該轉(zhuǎn)化方式未能全面涵蓋向公眾傳播權(quán)本應(yīng)調(diào)整的所有行為。〔35〕參見王遷:《中歐網(wǎng)絡(luò)版權(quán)比較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9-11頁。在此后的實踐中,這種局部轉(zhuǎn)化的方式導(dǎo)致了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權(quán)和廣播權(quán)在法律適用層面的分歧。具體至音樂產(chǎn)業(yè)轉(zhuǎn)型的過程中,針對網(wǎng)絡(luò)音樂服務(wù)商進行的不可回放的直播,究竟應(yīng)當(dāng)納入何種權(quán)利的調(diào)整范圍,學(xué)界存在是適用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權(quán)還是廣播權(quán)的爭論。〔36〕參見劉銀良:《制度演進視角下我國廣播權(quán)的范疇》,載《法學(xué)》2018年第12期,第13-18頁。源于這一釋法分歧,法院在裁判中不但解釋標(biāo)準(zhǔn)各異,而且出現(xiàn)了向著作權(quán)制度中的一般條款逃逸的情況。〔37〕代表性判決參見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13)一中民終字第3142號民事判決書。因此,在2020年《著作權(quán)法》修訂之前,產(chǎn)業(yè)主體在我國音樂產(chǎn)業(yè)網(wǎng)絡(luò)化和數(shù)字化的轉(zhuǎn)型中未能依當(dāng)時的著作權(quán)制度獲得明確、穩(wěn)定、統(tǒng)一的產(chǎn)權(quán)制度保障。這一不清晰的產(chǎn)權(quán)設(shè)計,致使上游的產(chǎn)權(quán)主體不能針對下游網(wǎng)絡(luò)音樂服務(wù)商多樣化商業(yè)性利用音樂客體的行為主張全面而合理的報酬。而遵循私法自治展開的獨家許可卻能以商業(yè)模型和利用方式為導(dǎo)向,〔38〕關(guān)于私法中的自治問題參見易軍:《私人自治與私法品性》,載《法學(xué)研究》2012年第3期,第68-86頁;熊琦:《論著作權(quán)集體管理中的私人自治——兼評我國集體管理制度立法的謬誤》,載《法律科學(xué)》2012年第1期,第142-149頁。靈活地約定利用范圍,有效地厘定利用類型,全面地確定利用對價,以此減少因產(chǎn)權(quán)設(shè)計模糊所導(dǎo)致的下游商業(yè)使用者選擇性付費與大規(guī)模侵權(quán)的現(xiàn)象。
第二,在救濟措施層面,2020年修訂之前的《著作權(quán)法》的救濟規(guī)范不足。在音樂產(chǎn)業(yè)轉(zhuǎn)型的過程中,有限的救濟措施既沒能充分滿足上游產(chǎn)權(quán)主體在網(wǎng)絡(luò)領(lǐng)域進行權(quán)利交易的需求,也沒能充分滿足下游商業(yè)使用者利用產(chǎn)權(quán)制度展開公平競爭的訴求。與其他知識產(chǎn)權(quán)客體在救濟措施適用中存在問題一樣,我國著作權(quán)保護的救濟措施一直以來也飽受詬病。〔39〕參見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wù)院辦公廳于2019年11月25日發(fā)布的《關(guān)于強化知識產(chǎn)權(quán)保護的意見》。為克服民事救濟的不足,我國從一開始便引入了知識產(chǎn)權(quán)的行政救濟作為補充。但行政救濟在執(zhí)法對象上具有選擇性,在執(zhí)法手段上亦具有任意性。〔40〕參見謝曉堯:《著作權(quán)的行政救濟之道——反思與批判》,載《知識產(chǎn)權(quán)》2015年第11期,第6-12頁。碎片化和缺乏統(tǒng)籌安排的行政干預(yù),不但無法從根本上應(yīng)對因制度漏洞導(dǎo)致的市場失靈,反而在某些情況下會造成派生的連鎖反應(yīng)。對此,通過前文對我國網(wǎng)絡(luò)音樂獨家許可演進的靜態(tài)事實和動態(tài)事實之間因果邏輯的考察可知,著作權(quán)主管部門在缺乏對相關(guān)匹配制度作出統(tǒng)籌安排與協(xié)同推進的情況下,要求網(wǎng)絡(luò)音樂服務(wù)商全面下架未經(jīng)授權(quán)的音樂產(chǎn)品,導(dǎo)致了網(wǎng)絡(luò)音樂服務(wù)商搶奪獨家版權(quán)等現(xiàn)象。誠然,民事救濟層面的懲罰性賠償救濟和禁令救濟近年來獲得了令人稱道的發(fā)展,〔41〕參見《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審理侵害知識產(chǎn)權(quán)民事案件適用懲罰性賠償?shù)慕忉尅罚ㄡ尅?021〕4號,2021年3月2日發(fā)布。并體現(xiàn)在2020年《著作權(quán)法》的修訂之中。但在音樂產(chǎn)業(yè)轉(zhuǎn)型的初期,面對侵權(quán)行為多、維權(quán)成本高、損害賠償?shù)汀⒔罹葷鸁o的產(chǎn)業(yè)運行環(huán)境,上游的產(chǎn)權(quán)主體無法通過當(dāng)時的權(quán)利救濟措施打擊違法使用音樂作品(制品)的行為;下游的商業(yè)使用者亦不能通過當(dāng)時的權(quán)利救濟措施遏制競爭者非法使用作品的行業(yè)亂象。基于上下游市場主體合意形成的獨家許可,不但能充分保障上游音樂產(chǎn)權(quán)主體的經(jīng)濟利益,而且亦能為下游網(wǎng)絡(luò)音樂服務(wù)商提供競爭所需的排他性優(yōu)勢與交易安全。
第三,在運行保障層面,著作權(quán)集體管理組織本應(yīng)為權(quán)利運行提供保障的功能嚴(yán)重缺位。功能缺位的集體管理組織未能向上游產(chǎn)權(quán)主體及下游商業(yè)使用者提供高效、民主、透明、合理的集中許可機制。與歐美國家相比,我國學(xué)者對著作權(quán)集體管理制度的功能定位尚存分歧,〔42〕參見向波:《著作權(quán)集體管理組織:市場功能、角色安排與定價問題》,載《知識產(chǎn)權(quán)》2018年第7期,第68-76頁;熊琦:《著作權(quán)集體管理制度本土價值重塑》,載《法制與社會發(fā)展》2016年第3期,第96-108頁。立法者亦未在實定法中對集體管理組織管理權(quán)利的范圍作出任何的強制性規(guī)定。〔43〕參見李陶:《非會員作品著作權(quán)集體管理模式的選擇與重構(gòu)——以德國法為借鑒》,載《法商研究》2015年第3期,第190頁。因此,著作權(quán)集體管理組織在我國并未發(fā)揮其應(yīng)有的保護權(quán)利人權(quán)益、平衡權(quán)利人內(nèi)部利益、平衡權(quán)利人和使用人外部利益、促進文化繁榮多樣的多元制度功能。〔44〕Vgl. v. Lewinski, Funktionen von Verwertungsgesellschaften im Zusammenhang mit dem Ausgleichen von verschiedenen Interessen, in: Heker/Riesenhuber (Hrsg.), Recht und Praxis der GEMA, 3. Aufl., 2018, S. 21-36.作為著作權(quán)市場化運營的補充保障,對權(quán)利的集體管理區(qū)別于個體管理。〔45〕參見劉平:《著作權(quán)集體管理組織與權(quán)利人個體維權(quán)訴訟的區(qū)別及其解決途徑》,載《知識產(chǎn)權(quán)》2016年第9期,第88-91頁。著作權(quán)集體管理組織雖具有不可取代的制度功能,但對其內(nèi)部治理及外部監(jiān)管的完善乃是近期全球立法者共同關(guān)注的議題。〔46〕例如,在國際法層面,2018年12月生效的《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guān)系協(xié)定》(簡稱CPTPP)第一次在國際法層面(第18.70條)作出了有關(guān)著作權(quán)集體管理組織的規(guī)定;美國2018年《音樂現(xiàn)代化法案》對集體管理組織的監(jiān)督和治理之新增規(guī)定參見《美國法典》第17章第115(d)(3)(C)條。在全球音樂產(chǎn)業(yè)轉(zhuǎn)型的初期,從產(chǎn)權(quán)主體(唱片公司)在全球范圍內(nèi)運用的轉(zhuǎn)型策略看,鑒于此前集體管理組織對其需求反應(yīng)遲緩的表現(xiàn),國際大型唱片公司及其版權(quán)代理機構(gòu)等具有博弈能力的產(chǎn)權(quán)主體曾嘗試撤回其原本通過集體管理組織在互聯(lián)網(wǎng)領(lǐng)域所管理的權(quán)利。〔47〕See U. S. Court of Appeals, Second Circuit: U. S. v. Broadcast Music, Inc., December 19, 2017.為了在許可商談中謀求更大的定價優(yōu)勢,這些產(chǎn)權(quán)主體要么試圖向網(wǎng)絡(luò)音樂服務(wù)商直接授權(quán),要么通過組建新型權(quán)利集中管理機構(gòu)向網(wǎng)絡(luò)音樂服務(wù)商間接授權(quán)(歐盟)。〔48〕Vgl. V?lger, Lizenzmodelle im kollektiven Wahrnehmungsrecht, 2021, S. 231-242.于我國而言,在本輪轉(zhuǎn)型之前,國際大型音樂產(chǎn)權(quán)主體本就沒有將其互聯(lián)網(wǎng)領(lǐng)域發(fā)放使用許可的業(yè)務(wù)交給我國的音樂著作權(quán)集體管理組織(中國音樂著作權(quán)協(xié)會,以下簡稱音著協(xié);中國音像集體管理協(xié)會,以下簡稱音集協(xié))。因此,當(dāng)音樂產(chǎn)權(quán)主體在轉(zhuǎn)型中面對全球收入下行壓力時,自然也不會在我國自發(fā)地尋求本土運行績效欠佳的集體管理組織的幫助。易言之,由于我國的集體管理組織此前未能向上游產(chǎn)權(quán)主體及下游商業(yè)使用者提供高效、民主、透明、合理的集中許可機制,上游的產(chǎn)權(quán)主體就會以直接授權(quán)的方式與網(wǎng)絡(luò)音樂服務(wù)商商談,下游的商業(yè)使用者則會以“搭便車”的方式在未取得授權(quán)的情況下使用作品。而私法自治下的獨家許可,既可以滿足具有博弈能力的上游權(quán)利主體尋求高額經(jīng)濟回報的理性人需求,也可以遏制下游產(chǎn)業(yè)主體使用作品而不付費的現(xiàn)象。
第四,在限制例外層面,我國《著作權(quán)法》的權(quán)利限制例外制度價值取向單一。單一的價值取向使我國《著作權(quán)法》的權(quán)利限制例外制度并不具有調(diào)和產(chǎn)業(yè)主體間利益沖突的功能,而依私法自治開展的獨家許可卻能最大程度地服務(wù)上游產(chǎn)權(quán)主體,滿足其單向獲得高額經(jīng)濟回報的理性人需求。面對具有博弈能力的上游產(chǎn)權(quán)主體嘗試退出集體管理組織,并向下游商業(yè)使用者直接授權(quán)的策略,為防止上游產(chǎn)權(quán)主體濫用知識產(chǎn)權(quán)排他權(quán)優(yōu)勢,平衡其和商業(yè)使用者之間的利益,有國外立法者選擇從本國著作權(quán)制度中的限制例外制度入手,尋找可行的應(yīng)對方案。對此,得益于歐美版權(quán)法中限制例外制度多元的功能定位,他國立法者能夠通過修改法律,擴充實定法中限制例外的適用范圍,以此遏制具有博弈能力的音樂產(chǎn)權(quán)主體利用轉(zhuǎn)型期的制度漏洞和權(quán)利的排他性侵害下游互聯(lián)網(wǎng)產(chǎn)業(yè)利益、謀求上游產(chǎn)業(yè)不適當(dāng)收益的意圖。〔49〕See 17 U. S. C. § 115 (d)(1)(A).相較而言,我國《著作權(quán)法》的限制例外制度僅具有協(xié)調(diào)私權(quán)利益與公共利益的價值功能。〔50〕參見馮曉青:《知識產(chǎn)權(quán)法的價值構(gòu)造:知識產(chǎn)權(quán)法利益平衡機制研究》,載《中國法學(xué)》2007年第1期,第67-69頁。單一的價值取向使我國《著作權(quán)法》的限制例外制度尚未形成能夠化解產(chǎn)業(yè)主體間利益沖突的理論共識。〔51〕參見管育鷹:《我國著作權(quán)法定許可制度的反思與重構(gòu)》,載《華東政法大學(xué)學(xué)報》2015年第2期,第19-22頁;熊琦:《著作權(quán)法定許可制度溯源與移植反思》,載《法學(xué)》2015年第5期,第78-80頁。所以,當(dāng)上游的產(chǎn)權(quán)主體利用權(quán)利的排他性實現(xiàn)理性經(jīng)濟人訴求時,下游的產(chǎn)業(yè)主體囿于我國著作權(quán)限制例外制度單一的價值取向,無法通過著作權(quán)法體系內(nèi)部的限制制度覓得調(diào)和上下游產(chǎn)業(yè)主體間利益沖突的方案。
綜上所述,在音樂產(chǎn)業(yè)網(wǎng)絡(luò)化與數(shù)字化的轉(zhuǎn)型中,由于我國2020年修訂之前的《著作權(quán)法》存在產(chǎn)權(quán)設(shè)計模糊、救濟措施不足、運行保障缺位、限制例外局限等主要不足,上游產(chǎn)權(quán)主體和下游商業(yè)使用者在我國選擇遵循私法上的自治原則,合意推行獨家許可模式。該模式不但能夠有效扭轉(zhuǎn)因我國《著作權(quán)法》制度漏洞引發(fā)的市場失靈,而且亦能實現(xiàn)上游產(chǎn)權(quán)主體和下游商業(yè)使用者在產(chǎn)權(quán)交易和客體利用過程中對權(quán)利保護與公平競爭等雙向的價值追求。此外,上下游產(chǎn)業(yè)主體之所以在我國選擇以獨家許可的方式進行轉(zhuǎn)型,并非單純地源于既有研究所主張的“我國著作權(quán)集體管理組織間缺乏競爭”抑或“我國法定許可制度存在立法缺陷”等原因。〔52〕參見龍俊:《數(shù)字音樂版權(quán)獨家授權(quán)的競爭風(fēng)險及其規(guī)制方法》,載《華中科技大學(xué)學(xué)報(社會科學(xué)版)》2020年第2期,第90-92頁;同前注〔1〕,蔣一可文,第158頁。
四、價值取向:產(chǎn)業(yè)主體和政府策略選擇的內(nèi)在體系因素
音樂產(chǎn)業(yè)數(shù)字化與網(wǎng)絡(luò)化轉(zhuǎn)型的理想結(jié)果,應(yīng)是在實現(xiàn)不同產(chǎn)業(yè)主體利益訴求的同時,在音樂客體創(chuàng)作、開發(fā)、傳播、使用、消費等環(huán)節(jié)中調(diào)和產(chǎn)業(yè)主體之間的利益沖突。〔53〕參見吳漢東:《著作權(quán)合理使用制度研究》,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13年版,第13-16頁。因此,權(quán)利保護價值與利益平衡價值是在《著作權(quán)法》維度下進行價值判斷最為基本也最具共識性的標(biāo)準(zhǔn)。〔54〕同上注,第13-16頁;同前注〔50〕,馮曉青文,第67頁;同前注〔51〕,管育鷹文,第19-22頁;同前注〔51〕,熊琦文,第78-80頁。
(一)權(quán)利保護價值
首先,從實踐事實層面考察,我國音樂產(chǎn)權(quán)主體的權(quán)利保護價值自始至終都沒有得到充分而全面的實現(xiàn)。在產(chǎn)業(yè)轉(zhuǎn)型的前期,下游網(wǎng)絡(luò)音樂服務(wù)商違法使用音樂的現(xiàn)象極其嚴(yán)重,鑒于此,著作權(quán)主管部門才于2015年出臺了被業(yè)界稱為“史上最強版權(quán)令”的《關(guān)于責(zé)令網(wǎng)絡(luò)音樂服務(wù)商停止未經(jīng)授權(quán)傳播音樂作品的通知》;而即便是在產(chǎn)業(yè)轉(zhuǎn)型的過渡期、調(diào)試期及再調(diào)試期,下游的商業(yè)使用者也依舊沒有對音樂客體實現(xiàn)全面付費。在實踐中,以世界三大唱片公司(環(huán)球、華納、索尼)為代表的產(chǎn)權(quán)主體,運用直接授權(quán)的方式只能覆蓋我國互聯(lián)網(wǎng)領(lǐng)域個別(頭部)網(wǎng)絡(luò)音樂服務(wù)商的主要音樂使用場景(在線收聽、在線下載等),而對于非頭部網(wǎng)絡(luò)音樂服務(wù)商以及非直接使用音樂的場景而言,在詞曲作者和錄音制作者等權(quán)利人看來,使用音樂客體但選擇性付費或不付費的情況依然十分普遍。〔55〕參見音集協(xié):《關(guān)于要求快手APP刪除一萬部涉嫌侵權(quán)視頻的公告(第一批)》,https://www.cavca.org/newsDetail/1460,2021年5月15日訪問。此外,正是由于下游商業(yè)使用者不付費或不全面付費現(xiàn)象的普遍,以世界三大唱片公司為代表的音樂產(chǎn)權(quán)主體才會向個別商業(yè)使用者索要高額甚至遠高于音樂客體市場價值的許可使用費。唯有如此,上游的產(chǎn)權(quán)主體才能實現(xiàn)整個市場宏觀營收的績效指標(biāo)。從某種程度上說,我國本土的頭部網(wǎng)絡(luò)音樂服務(wù)商實際上正在為市場上違法使用音樂客體的其他經(jīng)營者支付本不該由其支付的不合理的許可使用對價。質(zhì)言之,單個網(wǎng)絡(luò)音樂服務(wù)商在現(xiàn)階段所支付的許可使用對價與權(quán)利保護價值在我國的整體實現(xiàn)情況成反比。故而,遏制和消除盜版侵權(quán)現(xiàn)象,即最大程度地實現(xiàn)網(wǎng)絡(luò)音樂的正版化授權(quán)與全面化付費,依舊是未來我國音樂產(chǎn)業(yè)網(wǎng)絡(luò)化轉(zhuǎn)型的首要任務(wù)。
其次,從我國《著作權(quán)法》制度規(guī)范層面考察,在音樂產(chǎn)業(yè)轉(zhuǎn)型的過程中,特別是2020年《著作權(quán)法》修訂之前,音樂產(chǎn)權(quán)主體的權(quán)利保護價值沒能系統(tǒng)而科學(xué)地在我國著作權(quán)立法中得到貫徹。其一,從權(quán)利保護價值的制度表達看,在2020年修法前,我國《著作權(quán)法》的產(chǎn)權(quán)設(shè)計、救濟措施、集體管理等能夠體現(xiàn)權(quán)利保護價值的制度存在規(guī)則設(shè)計上的漏洞;在2020年修法后,通過釋明廣播權(quán)和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權(quán)的調(diào)整范圍、引入懲罰性賠償、完善訴前救濟措施、為錄音制作者創(chuàng)設(shè)廣播與機械表演獲酬權(quán)等立法行為,之前存在于我國著作權(quán)制度規(guī)范層面的產(chǎn)權(quán)設(shè)計模糊、救濟措施局限等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完善。〔56〕參見石宏:《著作權(quán)法第三次修改的重要內(nèi)容及價值考量》,載《知識產(chǎn)權(quán)》2021年第2期,第7-14頁;王遷:《〈著作權(quán)法〉修改:關(guān)鍵條款的解讀與分析(上)》,載《知識產(chǎn)權(quán)》2021年第1期,第23-28頁。其二,從權(quán)利保護價值在國內(nèi)法對國際法制度轉(zhuǎn)化的角度看,在締結(jié)著作權(quán)領(lǐng)域的國際條約時,我國立法者充分利用了條約自身為締約國所創(chuàng)設(shè)的“保留選項”,即但凡存在可不給予某一主體以著作權(quán)立法保護的選項時,我國均選擇不對該主體給予《著作權(quán)法》上的保護。〔57〕關(guān)于我國對著作權(quán)領(lǐng)域國際公約的保留情況,參見劉勝湘、張弘揚:《略論版權(quán)公約中的保留制度及其對我國立法及司法的影響》,載《中國版權(quán)》2014年第5期,第28-29頁。上述權(quán)利保護價值的取舍在音樂產(chǎn)業(yè)所涉及的制度設(shè)計包括《視聽表演北京條約》第11條第1款和第2款(表演者對已錄制表演的廣播獲酬權(quán)/排他權(quán)和機械表演獲酬權(quán)/排他權(quán))、WPPT第15條(表演者和錄音制作者廣播與機械表演獲酬權(quán))。但在2020年我國《著作權(quán)法》修訂時,立法者在制度規(guī)范層面強化了對權(quán)利保護價值的貫徹,為錄音制作者提供了高于我國在締結(jié)相關(guān)國際公約時所承諾保護的水平,即為錄音制作者創(chuàng)設(shè)了廣播獲酬權(quán)和機械表演獲酬權(quán)。〔58〕參見王遷:《〈著作權(quán)法〉修改:關(guān)鍵條款的解讀與分析(下)》,載《知識產(chǎn)權(quán)》2021年第2期,第26-27頁。立法者接下來應(yīng)當(dāng)研究通過何種許可模式,在充分而有效地實現(xiàn)權(quán)利保護價值的同時,適當(dāng)而合理地調(diào)和上游音樂產(chǎn)權(quán)主體和下游商業(yè)使用者(廣播電臺、電視臺、網(wǎng)播平臺等主體)之間的利益,以此化解下游商業(yè)使用者對設(shè)立這兩項獲酬權(quán)的擔(dān)憂與質(zhì)疑。〔59〕參見姚嵐秋、魏高靈:《賦予錄音制作者廣播獲酬權(quán)欠缺合理性》,載《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2020年10月22日,第5版。
(二)利益平衡價值
首先,從實踐事實層面考察,音樂產(chǎn)權(quán)主體和商業(yè)使用者之間的利益平衡價值尚未在我國得到正常而合理的實現(xiàn)。目前在我國音樂產(chǎn)業(yè)運行實踐中所謂的“均衡”,乃是以下游商業(yè)使用者選擇性付費或不付費的形式存在的一種非理性“均衡”。在本文看來,該領(lǐng)域的理性均衡應(yīng)是在全面付費的基礎(chǔ)上以“合理的”或“適當(dāng)?shù)摹奔礉M足比例原則的費率標(biāo)準(zhǔn),實現(xiàn)上游產(chǎn)權(quán)主體和下游商業(yè)使用者之間的利益平衡。〔60〕有關(guān)使用費率合理性與適當(dāng)性的代表性研究參見胡開忠:《使用作品付酬標(biāo)準(zhǔn)探析》,載《法商研究》2012年第1期,第95-101頁。域外相關(guān)代表性研究參見Ohly, Die Angemessenheit von Vergütungen, Tarifen und Gesamtvertr?gen, in: Riesenhuber (Hrsg.),Die Angemessenheit im Urheberrecht, 2013, S. 169-188.反觀現(xiàn)實,其一,在選擇性付費和不付費均存在的情況下,作為理性人的上游產(chǎn)權(quán)主體會為了實現(xiàn)總體營收的增長或總體收支的平衡,以交叉補償?shù)姆绞较騻€別具有付費意愿的下游商業(yè)使用者主張不合理、不適當(dāng)?shù)氖褂迷S可費。這種不合理、不適當(dāng)?shù)馁M率標(biāo)準(zhǔn),并不利于引導(dǎo)其他尚未付費或尚未全面付費的使用者養(yǎng)成付費習(xí)慣。對此,立法者在2020年《著作權(quán)法》的修訂中添置的有關(guān)費率協(xié)商異議的集體管理規(guī)則(《著作權(quán)法》第8條第2款)雖意在深遠,〔61〕同前注〔56〕,石宏文,第15頁。但其平衡上下游產(chǎn)業(yè)主體利益的實踐績效尚需通過《著作權(quán)集體管理條例》之修訂,在細化具體概念、完善具體程序的基礎(chǔ)上方能逐漸顯現(xiàn)。其二,在選擇性付費和不付費仍然存在的情況下,作為理性人的上游產(chǎn)權(quán)主體還會為了實現(xiàn)總體營收的增長或總體收支的平衡,以“批量訴訟”“商業(yè)維權(quán)”等方式謀求不合理、不適當(dāng)?shù)氖找妗!?2〕參見易繼明、蔡元臻:《版權(quán)蟑螂現(xiàn)象的法律治理——網(wǎng)絡(luò)版權(quán)市場中的利益平衡機制》,載《法學(xué)論壇》2018年第2期,第5-18頁;陳為:《論音樂電視作品小權(quán)利人批量維權(quán)案件司法裁判標(biāo)準(zhǔn)的統(tǒng)一》,載《中國版權(quán)》2020年第3期,第26-31頁。在音樂產(chǎn)業(yè)網(wǎng)絡(luò)化、數(shù)字化的轉(zhuǎn)型實踐中,這種原本存在于線下的批量訴訟、以訴牟利的現(xiàn)象正開始向線上蔓延。〔63〕參見王瑜玲:《深層鏈接、云盤網(wǎng)傳滋生盜版,網(wǎng)絡(luò)音樂著作權(quán)糾紛廣州年收案過萬件》,載《南方都市報》2019年9月22日,第A4版。在這樣的情況下,下游具有付費意愿的商業(yè)使用者不但會逐漸負(fù)擔(dān)不起高額的使用許可費,而且困于商業(yè)維權(quán)的滋擾,也難以專注于服務(wù)的提升與商業(yè)模式的創(chuàng)新。
其次,從我國《著作權(quán)法》制度規(guī)范層面考察,音樂產(chǎn)權(quán)主體和商業(yè)使用者之間的利益平衡價值尚未在著作權(quán)立法中得到系統(tǒng)而科學(xué)的貫徹。其一,能夠?qū)崿F(xiàn)利益平衡價值的法定許可,在我國著作權(quán)法中價值取向單一,從而使得我國的法定許可只具有協(xié)調(diào)私權(quán)利益與公共利益的價值,并不具有歐美版權(quán)法上調(diào)和產(chǎn)業(yè)主體間私權(quán)利益沖突的價值。〔64〕同前注〔51〕,管育鷹文,第19-22頁;同前注〔51〕,熊琦文,第78-80頁。在制度價值理念存在根本差異的情況下,我國立法者在現(xiàn)階段是無法像歐美立法者一樣,通過創(chuàng)設(shè)能夠平衡不同產(chǎn)業(yè)主體利益的新型法定許可化解上游產(chǎn)權(quán)主體和下游網(wǎng)絡(luò)音樂服務(wù)商之間的利益分歧。其二,能夠?qū)崿F(xiàn)利益平衡價值的集體管理制度在我國存在立法設(shè)計上的不足,有限的制度設(shè)計使我國的集體管理組織尚未充分發(fā)揮其應(yīng)有的多元功能。作為連接上游產(chǎn)權(quán)主體和下游商業(yè)使用者的橋梁,盡管著作權(quán)集體管理組織具有《著作權(quán)法》上權(quán)利保護和利益平衡的多元功能,但我國立法者并未對其實現(xiàn)這些多元的功能給予必要的實定法保障。例如,與歐美版權(quán)法相比,我國《著作權(quán)法》并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強制性(法定)集體管理,權(quán)利人可依其意愿自由地選擇是否通過集體管理組織行使權(quán)利。而在這種絕對自由理念下幻化出的商業(yè)維權(quán)與牟利性訴訟,并不利于消除上游產(chǎn)權(quán)主體和下游商業(yè)使用者間的利益分歧。
五、我國網(wǎng)絡(luò)音樂獨家許可的優(yōu)化方案
本文認(rèn)為,立法者下階段應(yīng)通過《著作權(quán)集體管理條例》的修訂系統(tǒng)地完善著作權(quán)集體管理制度。對此,正是源于在音樂產(chǎn)業(yè)網(wǎng)絡(luò)化和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中,我國的著作權(quán)集體管理組織未能在此前向上游的音樂產(chǎn)權(quán)主體和下游的商業(yè)使用者提供高效、民主、透明、合理的集中許可機制,才使得上下游產(chǎn)業(yè)主體合意推行獨家許可。
(一)優(yōu)化方案的關(guān)聯(lián)性闡釋
首先,通過經(jīng)驗事實層面的分析可知,以完善集體管理制度的方式助力音樂產(chǎn)業(yè)在我國的轉(zhuǎn)型,具有在國際范圍內(nèi)產(chǎn)業(yè)轉(zhuǎn)型策略選擇的共識性。區(qū)別于美國、歐盟、英國、澳大利亞等全球其他主要音樂市場,我國的上下游音樂產(chǎn)業(yè)主體采用的是圍繞獨家許可展開的直接授權(quán)模式,而不是基于集體管理組織的間接授權(quán)模式。但圍繞獨家許可展開的直接授權(quán)模式,并不利于在上游產(chǎn)權(quán)主體和下游商業(yè)使用者之間實現(xiàn)理性而長期的價值均衡。因此,立法者應(yīng)當(dāng)完善我國的著作權(quán)集體管理制度,為上下游音樂產(chǎn)業(yè)主體在我國自主地選擇全球通行的間接授權(quán)模式創(chuàng)造必要的制度條件。
其次,通過制度規(guī)范層面的分析可知,以完善集體管理制度的方式助力音樂產(chǎn)業(yè)在我國的轉(zhuǎn)型,具有統(tǒng)籌安排規(guī)制策略、協(xié)同推進制度發(fā)展的科學(xué)性。在缺乏系統(tǒng)分析與統(tǒng)籌安排的情況下,相關(guān)部門此前以行政手段替代立法手段干預(yù)市場運行的做法,并未能全面、長期、科學(xué)地實現(xiàn)在《著作權(quán)法》調(diào)整音樂產(chǎn)業(yè)轉(zhuǎn)型過程中產(chǎn)業(yè)主體所期待的價值目標(biāo)。當(dāng)2020年修訂的《著作權(quán)法》已通過優(yōu)化產(chǎn)權(quán)設(shè)計、強化救濟措施等方式為產(chǎn)業(yè)主體提供了轉(zhuǎn)型所需的具體制度保障時,立法者接下來應(yīng)通過《著作權(quán)集體管理條例》的修訂在著作權(quán)的運行保障層面補齊短板,細化2020年修訂的《著作權(quán)法》第8條對集體管理制度所作出的頂層設(shè)計。
再次,通過價值取向?qū)用娴姆治隹芍酝晟萍w管理制度的方式助力音樂產(chǎn)業(yè)在我國的轉(zhuǎn)型,具有兼顧權(quán)利保護價值和利益平衡價值的全面性。作為連接上下游產(chǎn)業(yè)主體的橋梁,著作權(quán)集體管理組織具有兼顧權(quán)利保護價值和利益平衡價值的應(yīng)然多元功能。該多元功能決定了著作權(quán)集體管理制度就是促進網(wǎng)絡(luò)音樂的正版化使用和全面化付費,以及維持使用許可費率適當(dāng)性和曲庫穩(wěn)定性最為理想的規(guī)制工具。而該多元功能的實現(xiàn)需要必要的立法保障。
最后,對于通過創(chuàng)設(shè)新型法定許可化解網(wǎng)絡(luò)音樂獨家許可諸多負(fù)外部性的方案而言,除了前述中外法定許可存在的價值理念差異外,從政府規(guī)制策略選擇的角度看,即便不引入法定許可,也可以通過產(chǎn)權(quán)設(shè)計的細化、救濟措施的優(yōu)化、運行保障(集體管理)的強化,實現(xiàn)上游產(chǎn)權(quán)主體和下游商業(yè)使用者在網(wǎng)絡(luò)音樂許可上的價值均衡。對此,與美國法通過創(chuàng)設(shè)新型法定許可強勢干預(yù)市場運行的做法不同,歐盟立法者通過集體管理組織內(nèi)部治理以及費率標(biāo)準(zhǔn)異議的糾紛解決機制的完善等方式,較為緩和地引導(dǎo)上下游產(chǎn)業(yè)主體自發(fā)通過集體管理組織化解音樂產(chǎn)業(yè)轉(zhuǎn)型中的利益分歧。我國2020年修訂的《著作權(quán)法》已經(jīng)在產(chǎn)權(quán)設(shè)計、救濟措施層面進行了系統(tǒng)的完善。著作權(quán)集體管理組織內(nèi)部治理和外部監(jiān)管的優(yōu)化也將通過《著作權(quán)集體管理條例》的修訂實現(xiàn)。在這些制度保障日漸完備的外在條件下,應(yīng)考察市場主體是否能夠自發(fā)地借助制度的系統(tǒng)完善形成理性的價值均衡。倘若市場主體能夠借助制度保障的系統(tǒng)完善完成應(yīng)然的產(chǎn)業(yè)轉(zhuǎn)型,則立法者無需在現(xiàn)階段就通過專門的法定許可干預(yù)市場運行。
(二)完善著作權(quán)集體管理組織對權(quán)利保護價值的轉(zhuǎn)化制度
著作權(quán)集體管理組織對權(quán)利保護價值的轉(zhuǎn)化主要涉及其和權(quán)利人之間的法律關(guān)系。在我國,著作權(quán)集體管理組織是非營利法人中的社會團體(《民法典》第87條)。作為社會團體的集體管理組織應(yīng)以社團自治為運行原則,〔65〕參見李海平:《論作為憲法權(quán)利的團體自治權(quán)》,載《吉林大學(xué)社會科學(xué)學(xué)報》2011年第6期,第141-143頁;Reichert, in: Reichert/Schimke/Dauernheim, 13. Aufl., 2015, Rdn. 394 あ.依協(xié)會章程實現(xiàn)其社員(權(quán)利人)的各種訴求(《民法典》第91條第1款)。因而,著作權(quán)集體管理組織應(yīng)當(dāng)進一步強化協(xié)會章程在社團自治運行中的統(tǒng)領(lǐng)作用,在特別強調(diào)信息公開的同時優(yōu)化其內(nèi)部的治理結(jié)構(gòu)。〔66〕參見鮑少坤:《社會組織及其法治化研究》,載《中國法學(xué)》2017年第1期,第14頁。對此,雖然協(xié)會章程的內(nèi)容、信息公開的程度以及內(nèi)部治理的結(jié)構(gòu)本質(zhì)上屬于社團自治的范疇,但為了保障社團成員利益以及公共利益,法律可對社團章程的內(nèi)容、信息公開的范圍和內(nèi)部治理的結(jié)構(gòu)作出必要的強制性規(guī)定。〔67〕參見張清、武艷:《包容性法治框架下的社會組織治理》,載《中國社會科學(xué)》2018年第6期,第92頁;祁春軼:《社團秩序模式的功能優(yōu)勢及其制度空間》,載《法學(xué)》2017年第8期,第62頁;Reichert, in: Reichert/Schimke/Dauernheim, 13. Aufl., 2015, Rdn. 399.
第一,就完善著作權(quán)集體管理組織的章程內(nèi)容而言,應(yīng)結(jié)合著作權(quán)集體管理組織的自身特點,將會員資格及其權(quán)利、義務(wù),民主的組織管理制度、執(zhí)行機構(gòu)的產(chǎn)生程序,資產(chǎn)管理和使用的原則,內(nèi)部監(jiān)督機制,應(yīng)當(dāng)由章程規(guī)定的其他事項等在法人專門性和一般性立法中已經(jīng)確立的章程內(nèi)容,〔68〕上述有關(guān)非營利法人章程的內(nèi)容分別規(guī)定在《社會團體登記管理辦法》第14條和《慈善法》第11條。在《著作權(quán)集體管理條例》第8條有關(guān)章程內(nèi)容條文的修改中加以吸收。規(guī)制慈善組織的《慈善法》(2016年頒布)和規(guī)制社會團體的《社會團體登記管理辦法》(2016年修改)是法人專門性和一般性立法。為保持非營利法人概念體系的融貫和運行規(guī)則的協(xié)調(diào),作為非營利法人中社會團體法人的著作權(quán)集體管理組織,理應(yīng)對標(biāo)法人專門性和一般性立法。然而,現(xiàn)行《著作權(quán)集體管理條例》第8條關(guān)于章程內(nèi)容的條文既未要求協(xié)會將會員資格及其權(quán)利、義務(wù)寫入章程,也未強調(diào)協(xié)會的組織機構(gòu)應(yīng)保障決策的民主,更未要求協(xié)會設(shè)立內(nèi)部監(jiān)督機制。
第二,就強化著作權(quán)集體管理組織對權(quán)利人、使用者和公眾的信息公開而言,應(yīng)要求其定期、具體、主動地向上述主體公開相關(guān)信息。集體管理組織對上述主體的信息公開規(guī)定在《著作權(quán)集體管理條例》第21條和第32條,但該信息公開的義務(wù)具有被動性,即根據(jù)該條例第21條,權(quán)利人“可以查閱有關(guān)業(yè)務(wù)材料”。這種依申請查閱信息的方式并不利于權(quán)利人在充分知悉協(xié)會運行狀況的基礎(chǔ)上行使其參與協(xié)會決策的各種會員權(quán)利,而且何為“有關(guān)業(yè)務(wù)材料”也完全取決于協(xié)會單方的解釋。根據(jù)2020年修訂后的《著作權(quán)法》第8條第3款的文義,著作權(quán)集體管理組織對權(quán)利人、使用者和公眾的信息公開義務(wù)已經(jīng)由修法前被動的義務(wù)轉(zhuǎn)變?yōu)橐环N定期、具體、主動的義務(wù)。申言之,根據(jù)《著作權(quán)法》第8條第3款的規(guī)定,集體管理組織應(yīng)當(dāng)將某些具體的事項和協(xié)會運行的總體情況定期向相關(guān)主體和公眾公布。為了體現(xiàn)這一改變,未來在《著作權(quán)集體管理條例》第21條(集體管理組織對會員權(quán)利人的信息公開)的修訂中可新增一款規(guī)定:“著作權(quán)集體管理組織應(yīng)在上一會計年度結(jié)束后的12個月內(nèi),將上一會計年度使用費的收取和分配情況報告所有權(quán)利人。報告的內(nèi)容應(yīng)至少包括:(一)著作權(quán)集體管理組織收取的使用費數(shù)額;(二)使用費收取的權(quán)利類型和使用類型;(三)管理費提取數(shù)額;(四)除管理費外,著作權(quán)集體管理組織其他費用的提取數(shù)額;(五)使用費的未分配部分?jǐn)?shù)額。”與此同時,建議將《著作權(quán)集體管理條例》第32條(集體管理組織對權(quán)利人、使用人和社會的信息公開)中“供權(quán)利人和使用者查閱”這一表述修改為“定期向社會公布”,并將“使用費的未分配部分等總體情況”添至集體管理組織定期向社會公布的事項中。
第三,就優(yōu)化協(xié)會內(nèi)部治理結(jié)構(gòu)而言,應(yīng)要求著作權(quán)集體管理組織設(shè)立監(jiān)事或監(jiān)事會。著眼于我國社會團體運行治理的最新發(fā)展,在社會團體內(nèi)部設(shè)立監(jiān)事或監(jiān)事會乃是學(xué)界和立法者的共識。首先,從國內(nèi)相關(guān)實踐和非營利法人最新立法發(fā)展的角度看,一則,《慈善法》第11條和第12條明確了慈善組織必須設(shè)立獨立的內(nèi)部監(jiān)督機構(gòu)(監(jiān)事或監(jiān)事會)。二則,民政部2020年4月公布的《全國性行業(yè)協(xié)會商會章程示范文本(試行)》明確了全國性的協(xié)會應(yīng)當(dāng)設(shè)立監(jiān)事或監(jiān)事會。三則,雖然現(xiàn)行《社會團體登記管理辦法》并沒有對社會團體設(shè)立監(jiān)事或監(jiān)事會作出強制性要求,但民政部2018年8月公布的《社會組織登記管理條例(修訂草案征求意見稿)》第40、41、47條均作出了社會團體應(yīng)當(dāng)設(shè)立監(jiān)事和監(jiān)事會的具體規(guī)定。〔69〕參見《2018年民政部關(guān)于〈社會組織登記管理條例(草案征求意見稿)〉公開征求意見的通知》, http://www.mca.gov.cn/article/xw/tzgg/201808/20180800010466.shtml,2021年5月15日訪問。其次,從域外相關(guān)立法最新發(fā)展的角度看,根據(jù)歐盟2014年《音樂集體管理指令》第9條,成員國必須以強制的方式要求集體管理組織設(shè)立監(jiān)事或監(jiān)事會。為了盡量保持原有條款編號的穩(wěn)定,可在我國《著作權(quán)集體管理條例》第18條中新增第2款規(guī)定:“著作權(quán)集體管理組織應(yīng)設(shè)立監(jiān)事。監(jiān)事有3名以上的,可以設(shè)監(jiān)事會。監(jiān)事或者監(jiān)事會對理事、常務(wù)理事執(zhí)行職務(wù)的行為進行監(jiān)督,并行使章程規(guī)定的其他職權(quán)。”
(三)完善著作權(quán)集體管理組織對利益平衡價值的轉(zhuǎn)化制度
著作權(quán)集體管理組織對利益平衡價值的轉(zhuǎn)化主要涉及其和使用者之間的法律關(guān)系。著眼于我國著作權(quán)集體管理組織在實踐中存在的問題,立法者應(yīng)當(dāng)通過《著作權(quán)集體管理條例》的修訂細化使用費率協(xié)商和異議機制的構(gòu)造,并引入針對獲酬權(quán)的強制性集體管理。
第一,細化使用費率協(xié)商和異議機制的構(gòu)造,可促進上下游產(chǎn)業(yè)主體在音樂產(chǎn)業(yè)轉(zhuǎn)型過程中權(quán)利保護價值和利益平衡價值的實現(xiàn)。一方面,隨著物價水平的波動,上游的音樂產(chǎn)權(quán)主體希望獲得與經(jīng)濟發(fā)展水平和產(chǎn)業(yè)發(fā)展貢獻相匹配的動態(tài)收益。另一方面,下游的音樂商業(yè)使用者也希望能夠參與使用費率的制定,通過協(xié)商形成與產(chǎn)業(yè)發(fā)展水平相適應(yīng)的付費標(biāo)準(zhǔn)。對此,在集體管理制度運行順暢的歐美,均存在以行政仲裁、行政裁決或司法手段保障音樂商業(yè)使用者對使用費率異議的機制。〔70〕參見歐盟《音樂集體管理指令》第34條和第35條;德國《著作權(quán)和鄰接權(quán)集體管理組織法》第98-131條;《美國法典》第17章第115(c)條、第28章第137(b)條。為了回應(yīng)上述來自上下游產(chǎn)業(yè)主體的共同訴求,2020年《著作權(quán)法》的修訂采取了國際通行做法,在第8條添置第2款,為使用者參與費率協(xié)商、提出費率異議予以必要的制度安排和程序保障。〔71〕同前注〔56〕,石宏文,第15頁。目前,使用費率標(biāo)準(zhǔn)的確立規(guī)定于《著作權(quán)集體管理條例》第13條,建議在現(xiàn)有規(guī)定的基礎(chǔ)上新增兩款,分別對“使用者代表”和“仲裁和訴訟中的提存規(guī)則”作出規(guī)定。對使用者代表的定義應(yīng)為“能夠代表具體某一使用類型中相當(dāng)比例使用者利益的團體或個人”。〔72〕參見日本《著作權(quán)等管理事業(yè)法》第23條第2款中有關(guān)“利用者代表”的定義。引入必要的許可費提存機制,可以保證在費率異議的行政裁決和訴訟中使用者不會因費率異議程序的推進而不能使用存在爭議的著作權(quán)客體。
第二,引入強制性集體管理,可促進上下游產(chǎn)業(yè)主體在音樂產(chǎn)業(yè)轉(zhuǎn)型過程中權(quán)利保護價值和利益平衡價值的實現(xiàn)。強制性集體管理是指具體的某種排他權(quán)、獲酬權(quán)或在某種商業(yè)模式中具體的某項請求權(quán),只能通過著作權(quán)集體管理組織統(tǒng)一行使。〔73〕關(guān)于強制性集體管理及相關(guān)域外制度的研究,參見前注〔43〕,李陶文,第185-190頁。與歐盟、德國和美國相比,我國尚不存在實定法上的強制性集體管理。〔74〕從歐美近年相關(guān)立法趨勢上看,強制性集體管理正越來越多地被立法者所采用。參見《美國法典》第17章第115(d)(3)(C)條和歐盟2019年《數(shù)字單一市場中的版權(quán)指令》第12條。其一,就權(quán)利保護價值的實現(xiàn)而言,通過對請求權(quán)的統(tǒng)一行使,能夠化零為整,為權(quán)利人創(chuàng)造博弈優(yōu)勢,最大程度地使集體管理組織在與使用者的商談中維護權(quán)利人利益,進而消除使用者不付費或不全面付費的情況,以此滿足權(quán)利人對獲得適當(dāng)報酬的訴求。其二,就利益平衡價值的實現(xiàn)而言,通過對請求權(quán)的統(tǒng)一行使,亦能夠化零為整,將分散的權(quán)利人、紛繁的締約過程、多樣的付費標(biāo)準(zhǔn)在肯定差異性訴求的基礎(chǔ)上相對地統(tǒng)一化,進而避免商業(yè)維權(quán)與訴訟牟利現(xiàn)象,為使用人營造良好的營商環(huán)境,并以此實現(xiàn)商業(yè)使用者和權(quán)利人對交易安全和交易效率的雙向追求。
本文認(rèn)為,對于因法定許可形成的獲酬權(quán)與法定獲酬權(quán),均應(yīng)當(dāng)適用強制性集體管理。因法定許可形成的獲酬權(quán)與法定獲酬權(quán)是兩種不同類型的權(quán)利。〔75〕相同觀點參見前注〔58〕,王遷文,第26頁。前者是指2020年修訂后的《著作權(quán)法》第25條、第35條第2款、第42條第2款、第46條第2款規(guī)定的教科書使用、報刊轉(zhuǎn)載、翻錄、廣播電臺電視臺使用他人已發(fā)表之作品所形成的基于法定許可的獲酬權(quán),其立法表述是“可以不經(jīng)許可,但應(yīng)當(dāng)按照規(guī)定(向著作權(quán)人)支付報酬”,其民事請求權(quán)行使的基礎(chǔ)是《著作權(quán)法》第52條第1款第7項。后者則僅指《著作權(quán)法》第45條規(guī)定的錄音制作者的廣播與機械表演獲酬權(quán),其立法表述是“應(yīng)當(dāng)向錄音制作者支付報酬”,其民事請求權(quán)行使的基礎(chǔ)是《著作權(quán)法》 第52條第1款第11項。對此,其一,就因法定許可形成的獲酬權(quán)而言,現(xiàn)行《著作權(quán)法實施條例》第32條與《著作權(quán)集體管理條例》第47條所規(guī)定的報酬支付方式允許使用人自行選擇向權(quán)利人直接支付或通過著作權(quán)集體管理組織進行轉(zhuǎn)付。但在實踐中,這種“二選一”的繳納方式致使大部分使用者并沒有主動繳納許可費。立法者在著作權(quán)法修訂中也承認(rèn),既有的“二選一”報酬支付方式并沒有達到原本的立法目標(biāo),使得該獲酬權(quán)在實踐中形同虛設(shè)。〔76〕參見吳漢東:《著作權(quán)法第三次修改草案的立法方案和內(nèi)容安排》,載《知識產(chǎn)權(quán)》2012年第5期,第16-17頁。因此,應(yīng)當(dāng)通過《著作權(quán)集體管理條例》第47條的修訂,明確基于法定許可所形成的獲酬權(quán)只能通過著作權(quán)集體管理組織統(tǒng)一行使。其二,就法定獲酬權(quán)而言,盡管缺乏對此類獲酬權(quán)行使的本土實踐經(jīng)驗,但總結(jié)上述基于法定許可形成的獲酬權(quán)之行使并不成功的經(jīng)驗教訓(xùn),錄音制作者的廣播與機械表演獲酬權(quán)也應(yīng)一并適用強制性集體管理,并與已有的基于法定許可的獲酬權(quán)一起,均由著作權(quán)集體管理組織統(tǒng)一行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