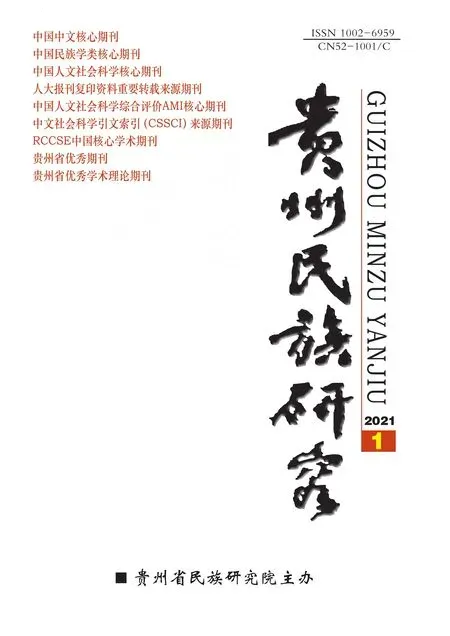以生為計:中老邊民跨界流動的認知研究
吳興幟 梁昭莉
(云南民族大學 社會學院,云南·昆明 650500)
邊民即是生活在民族國家邊界線地區的人群共同體,在民族國家形成之前,國界線兩側是一個完整的地域空間,人們根據生活與生產的需求,自由地流動;而在民族國家邊界線劃定之后,地域人群共同體歸屬于不同的政治共同體,需要遵守民族國家主權約定和邊界管理規定。但地域人群共同體的多重身份(公民、民族、邊民等) 構成了邊境地區人群的多重認同(國家認同、族群認同、地域認同),進而為此類人群在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中,根據具體的政治、經濟環境,在民族國家間的縫隙空間中,為了生活或生存而進行主動或被動的抉擇提供了機會。因為在這特殊的地理區位里,生活在邊界線兩側的人群,由于語言相通、習俗相同、族源相近、經濟互補以及歷史的沿襲,雖然民族國家的邊界線把地域分割為兩個主權國家,但邊民的跨界流動則是一種習以為常的客觀事實。
一、邊界:跨界流動與日常生活
邊界、邊民的存在是以國家為前提的,全球化使得越來越多的跨國群體出現,使得民族國家的原有民族屬性、國民屬性受到沖擊[1]。國家邊界的劃分和清晰的治理分化使得在極小的空間范圍內,因國家背景的不同,資源、教育、安全、發展等出現極大不平衡,這種空間內部出現的不均勻引力,致使邊民利用地緣、親緣、血緣和業緣,向更有利于自我生存發展的空間流動,邊疆問題變得更加復雜化。我國的邊民研究主要集中于對邊民治理和發展層面,跨國民族作為邊民常見的樣態,也成為這些年探討的重點。社會學、人類學界在研究跨國民族時將視角聚焦于宏觀和微觀兩個維度,課題涵蓋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的各個層面,具體包括跨界民族的健康狀況、居住環境、語言、收入不平等、族群沖突、學校交往中的友誼隔離、公民權利、認同問題、政治文化狀況、政治參與、宗教、結構性同化,以及對國家的威脅、跨界民族的過去發展以及未來的發展趨勢等方面[2]。同一民族卻分屬不同國家的跨境民族,交往密切且形式豐富,在全球化、現代化情境下,互為“文化備份”的跨境民族及其之間的族群互動將有助于民族傳統文化的傳承與該地文化多樣性的存續[3]。
邊民的流動包括3種形態:一是以經濟交往為主的跨界商貿活動;二是以日常生活為主的交往;三是基于民族國家內部政治生態為了生存和生計的逃離。邊境民族大規模遷移的直接原因是戰爭,而最根本的原因是生計需求。如云南瑤族因自身群體性弱勢而缺失了維系生存所需的經濟背景,被迫游走滇越邊境深山僻野,延續傳統的游耕生活[4]。邊民跨界流動背后有不同的時代背景,以及當事者群體或個體的選擇,從不同側面也映射出邊民與國家的互動關系。邊民的離散意味著去國離鄉,而回歸又意味著重回故里,有著“利”“害”判斷“去”“留”選擇及其因果邏輯[5];邊民回歸的不僅僅是簡單的物理空間的轉換過程,更重要的是物理空間之上的政治場域,以及社會文化的變化[6]。邊民的離散和回歸,是各民族根據自身的需求和實際的情況,在不同國家的“拉—推”合力中做出的優化流動決策,是邊民對自身空間特殊性的獨特運用。
邊民概念表述的關鍵在于“邊”,民族國家的“邊”是一個特殊的社會空間,既是邊民生活于其中的社會場所,又是邊民可以利用的工具;既是民族國家主權的符號表達,又是民族國家發展社會的資源。邊民以時空為經緯,在與國家相互依存的關系中,以地方的安全為基礎,享受著空間的自由。現有的研究成果,多是以邊民社會客觀的社會事實為基礎,討論地方社會與民族國家的關系,闡述邊疆地區的社會治理與發展,跨國民族間的日常交往與文化交流等,其核心是邊民應該在民族國家的主權框架下,利用沿邊的社會屬性,實現社會的和諧發展;但這些研究成果卻對“長時段”的社會歷程中,邊民基于空間屬性的離散與回歸認知則缺乏深入的討論。
二、縫隙:跨界邊民的彈性空間
空間作為物質存在的基本形態,經歷了與時間類似的發展歷程,主要表現為方位、位置、場所,發展出空間的等級與秩序、象征與意義以及權力、資源、價值等情況。空間研究以自然空間、文化空間、社會空間為研究對象,以空間屬性、空間秩序、空間生產、空間邊界為研究主題,并由此關注空間的結構、關系、秩序、權力、等級、資源以及人類的社會實踐[7]。社會科學關于時間、空間的研究經歷了從社會事實、關系秩序到資本的演化,時間成為資本時,具有兩重意義,一是時間的商品性問題,時間成為衡量價值的度量;二是時間的工具性,關鍵性的時間節點,成為人們可以利用的資本。民族國家的邊境地區,是集自然空間、政治空間、社會空間為一體化的多重空間結構。自然空間是人們生存的基礎,屬于客觀存在的場所;政治空間是民族國家主權的表達,是一種“無縫隙”“非彈性”的空間;社會空間是日常生活、生產的地方,是一種“流動性”“交互性”“縫隙化”的空間。對于特定人群共同體來說,邊境是由時間與空間編織的社會經緯。在民族國家形成之前,其生活在同一個地方,可以自由、安全地進行流動,在文化身份上疊加的是地域人群共同體身份;而在民族國家形成之后,其隸屬于民族國家的政治身份,要求其行為要符合國家主權的約定和國家利益的維護,“邊界線”成為規約地方人群空間移動的屏障。
安德森認為,人口調查、地圖和博物館相互關聯,共同闡明了晚期殖民地政府思考其統治領地的方式[8],而這3種方式,某種意義上講也是民族國家彰顯其統治的方式,地圖宣示著國家的疆域與邊界,人口成為生活在地圖邊界內的主體,而博物館則成為民族國家歷史記憶的載體與現實狀態的證據。邊民對民族國家的模塑不是被動的、僵硬的接受,而是以一種主動的態度、策略性的智慧加以轉化。這種智慧表現在邊民的生計策略中,就是他們運用多重身份,實現資源的最大化掘取[9]。邊民的生計策略之所以能夠實現,關鍵在于邊民社會特殊的社會空間,為其在社會發展階段的某一時刻,作出有利于自我生存與生活的行動提供了可能性。從“地圖”的角度看,民族國家間的空間是無縫的、線型的,但從文化、地方的角度看,民族國家間的空間在邊境地區是有縫的、交互的,從而形成了“縫隙空間”“特定的社會群體運用獨特的方法,利用、挪用本不屬于自己的各種縫隙和角落,使之成為某種‘縫隙空間’……(從而) 獲得了完全不同于純粹空間縫隙的新意義”[10]。他們一方面通過對“中心”的確認,來實現對自身“邊緣”位置和“有限空間”的認識;另一方面,通過對“縫隙空間”的挪用來編寫自身的空間敘事[11]。對于邊民來說,縫隙空間敘事與其生計緊密相連,人們借助于縫隙空間的交互性,在民族國家發展的“長時段”歷史進程中,主動或被動地選擇流動的方向。
在國內形勢不利于邊民生活與生存時,邊民選擇流向與之相鄰的同源的族群居住地,從而獲得生存的資本;當遷居地國家的政策對其不利,或者國內形勢有好轉,邊民又開始回歸,開啟新的生活。超越邊界的流動,成為邊民的生計策略,人們在邊界線兩側行走之所以有可能,關鍵在于民族國家間的邊界線建立于邊民社會的社會空間之中,邊民之間族源的親緣性、歷史習慣的沿襲性、文化習俗的相似性以及經濟生活的互補性等都為邊民提供了一種策略性的選擇,離散還是回歸均是其以生為計的理性抉擇。邊民在長時段的社會歷史周期中循環式的流動過程,都基于邊民的生存、生活需求,是以活下去、生活好為訴求的理性抉擇,社會空間與政治空間成了流動的關鍵區位,社會時間與鐘表時間則成了流動的關鍵節點。中老邊境地區由于歷史的積淀性、跨國民族的親緣性、經濟資源的互補性等特性,邊民對于國界線兩側的地方社會相當熟悉,使得王朝時代社會空間特性嵌入到民族國家的政治空間之中,加之跨國民族的文化空間,從而形成一個集政治、社會、文化為一體的多維空間,使邊民源于王朝時代的“資源性移動”在民族國家中轉化為生存藝術。
三、邊民:跨界流動的生計抉擇
在民族國家形成之前,邊民社會無所謂邊界意識,人們根據生活的需求,自發地尋求生活資源;但隨著民族國家的確立,邊民的首要身份是隸屬于“國家”的公民;邊疆地區也由最初的生計空間疊加了政治空間,空間內的人群則需要遵守民族國家主權原則進行有約束性的行為。而邊界線兩側的邊民由于歷史的沿襲性、生活的互補性、習俗的同源性、語言的相通性等歷史、文化以及經濟的原因,超越邊界的流動行為一直未曾中斷。邊界區域處于民族國家的邊緣,遠離政治中心,雖然現代民族國家的權力以基層行政單位的模式滲入邊境地區,但此空間仍然是一種“彈性空間”。邊民以地方性知識體系為智慧,在民族國家內部社會發展歷程、以及毗鄰國家之間的關系演化進程之中,以“生計”為目標,以離散與回歸為表征,策略性地選擇生存空間。中國與老撾的國界線是以內陸山地為主,跨境民族的親緣性、地域空間的熟悉性、跨界流動的無障礙性,讓這部分人群在民族國家發展過程中,遇到危及自身生存的歷史時刻,能夠在“縫隙空間”中自主地離散或回歸。
勐臘縣位于云南省西雙版納州的東部,東、南、西南與老撾毗鄰,西與緬甸隔江相望。國境線長740.8公里,其中,中老段677.8公里,中緬段63 公里,是云南省國境線最長的縣[12]。按照我國的民族劃分,目前居住在中老邊境的跨境民族主要有漢族、傣族、哈尼族、苗瑤、瑤族、布朗族、壯族等。根據勐臘年鑒統計,2016年,全縣常住人口28.97萬人,其中少數民族人口18.3萬人,其中傣族6.21萬人,哈尼族6.18萬人,彝族2.54萬人,瑤族1.89萬人[13]。從1895年到1992近百年的歷史進程中,中國社會的發展經歷了清王朝的覆滅,中華民國的30年治理,新中國的成立與各項社會運動,尤其是人民公社與大躍進(1958—1960年)、文化大革命(1966—1976 年) 與改革開放(1978 年至今);老撾則是經歷了法國屬地(1893—1940 年)、日本占領(1940—1945年)、法國重新占領(1946—1954年)、美國的新殖民(1954—1975 年) 和最終的老撾人民民主共和國的成立(1975年12月)。邊民社會的“小人物”無法逃避受民族國家“大事件”的影響,邊民經歷了“有邊無界”的自由行動,到“有界無邊”的策略性、選擇性行動,尤其是在邊民所在國家內部發生劇烈的社會運動期間。邊民跨界流動是邊民群體中的個體因為某種社會、政治等原因離開中國邊界到相鄰的國家居住、生活一段時間,再回到邊境線內繼續生活的人群,其跨國流動的目的不是為了現代意義的商貿、務工等經濟行為,而是為了生存。勐臘縣沿邊界線一帶的每個村莊,由于政治、經濟、歷史等原因,或多或少地都有人曾經到老撾去生活了一段時間,又返回中國沿邊地區生活,而這一歷史事實在當代演繹成了邊民的流動,即擁有邊民證的地方人群,合法或“非法”地行走邊界兩岸,進行貿易、務工等商業活動,從而提升自我的生活水平。
中老邊境地區是處于中國、老撾兩個民族國家的政治邊緣,但從國際交往的視角來看,無論是以民族國家為單位,還是以邊民社會為行為體,都是處于對外經濟交往的中心,相毗鄰的地域空間造就了人們相互經濟交往的便利性。邊民的交往集合了地方性日常生活的自發式和民族國家主導的自覺式兩種形態。自發式的邊民跨界生計模式主要表現為中國邊民過界到老撾租種田地、林地;老撾邊民過界到中國進行短期的、生產性的務工行為。自覺性的邊民交往則是以口岸、互市區域為主要空間,在民族國家間的貿易交往中,集中體現了邊民社會是如何在民族國家和地方社會之間,實現自我生存發展的道路抉擇。磨憨鎮位于勐臘縣最南端,與老撾接境,國境線長174千米,境內磨憨口岸為國家級口岸。全鎮轄有磨憨、尚勇、尚岡、曼莊、龍門、磨龍6個村委會,有56 個自然村,5個村辦場,5個茶農隊,是一個以傣族為主,漢、哈尼、苗、瑤、拉祜(苦聰人)、布朗(克木人)等多民族聚居的邊境鄉鎮,2016年全鎮常住人口2.4萬人,少數民族人口2.08萬人,占86.7%[14]。磨憨村位于勐臘縣的最南部,距磨憨鎮3 公里,勐臘縣48公里,東與老撾國家勐賽省磨頂村接壤,南與老撾國家磨丁口岸相連,西鄰磨龍村,北毗尚勇村,轄區面積共有38平方公里。磨憨村是一個多民族雜居的村,轄區內有14個小組,居住著漢(茶一隊、茶二隊、三公里、渡槽、村辦茶隊、磨憨、磨本小組)、傣(磨整、南嘎、磨龍小組)、苗(納龍小組)、瑤(新民、回金立小組)、哈尼(南列) 等民族。主要經濟收入是通過種植茶葉、橡膠、水稻、冬季蔬菜等作物來獲取(2018年磨憨村委會村支書提供)。
新民村位于“新民通道”路邊,是中國通往老撾的傳統道路,屬瑤族村寨,全村共65戶284人。2018 年課題組在新民村調查了解到,新民村邊民的跨界流動呈現出以家庭為單位,圍繞生存而進行抉擇。村民ZJS本人沒有去老撾,ZJS的堂哥一家6口人(堂哥以及堂哥的岳父、岳母、老婆、小媳婦和一個孩子) 則是于1968年遷徙到老撾。因為自己的第一個老婆不會生孩子,就帶著一個孩子(領養) 和老婆上門到了小媳婦家。小媳婦的父母會打鐵的手藝,專門給傣族人打刀,所以家里經濟條件稍微好一些。當時正趕上國家劃分階級,堂哥不想自己辛辛苦苦賺的錢交給合作社,所以就帶著一家人跑到老撾南塔的一個瑤族聚居的地方,那里沒有什么水田,靠開山種地。堂哥在老撾生了3個姑娘,一直沒有生兒子,于是抱養了一個。據ZJS回憶,堂哥一家搬到老撾以后,于1975 年跑到了泰國,后來又去了美國(1990年侄女和她的老公回來探親,講述了他們家從老撾、泰國,最后去了美國),再也沒有回來了。ZJS 堂兄一家人屬于邊民離散中漸行漸遠式流動,起因在于當時國內的社會環境,不利于家人的生存,從老撾到泰國則也是因為老撾內戰,最終歸途無期。
中老邊境地區的民族國家邊界線是20世紀90年代才真正確立的,在這之前,邊民社會群體對于邊界線沒有明確的量化意識。人們在面對社會動蕩時,策略性地在熟悉的空間里流動,以求自保。新民村PYF家是1958年父母帶著哥哥和姐姐去了老撾。當時中國和老撾的國界線沒有明顯確定,也沒有建邊防站,去老撾很容易,自己的父親經常會去老撾,買一些東西或是串親戚,但是當時這種行為就會被認為是特務向老撾匯報機密。再加之當時因為國內劃階級,打擊富農,自己的父親由于受不了這樣的批斗,就跑去了老撾。1959政府又去做工作,把這些逃去老撾的人領回來。1970 年,國家清理階級,搞政策邊防,因為家里的經濟條件稍微好一些,又聽聞其他寨子有被批斗的情況,十分擔心,就準備逃亡老撾。當晚自己的母親就被抓去批斗,當時批斗得十分嚴重,每晚都會有民兵在門外看守。后來母親逃了出來,跑到了老撾,父親和哥哥、姐姐、姐姐的孩子也跑去了老撾,自己當時14歲,沒有跟著一起出去。1982年老撾謠言要抓人,不承認這部分人是老撾人,一聽要抓人,哥哥帶著父母和姐姐回到了現在新民村所在的寨子,回來的當晚發現是謠言,就又返回老撾了,只有哥哥留下來。哥哥在中國呆了1年以后,覺得父母都在老撾,一個人在這邊也沒有什么意思,就又返回老撾再也沒有回來過。
納龍村是磨憨村委會轄區內唯一的苗族村寨,全村共79戶403人。現在的納龍村是從“十七公里”(即十七公里國界線) 處的老苗寨搬遷過來。據老村長講,當年在國界線那里老是被飛機炸,1968 年搬到了南嘎,1977搬到現在的納龍。納龍村的TZ家是1958年從中國跑到老撾去的,當時她爺爺、奶奶經濟條件相對好一些,為躲避批斗,搬到了老撾有苗族人居住的毛草寨。1964年一家人回到中國,是因為聽說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好,她爺爺在老撾的時候就經常說,等以后中國政策好了,就帶你們一起回去。想著自己老了以后,沒有力氣干勞動,總是靠砍山也不是長久之計,當時同十來個親戚一起約好,晚上點著火把,從國境線上就回來了。據TZ說,回來之后就再沒有去老撾了,因為他們知道中國共產黨好,不像老撾的兵,老撾政府不關心老百姓,還會搶老百姓種的東西。TZ的二兒子娶了一個老撾媳婦,他們是在磨憨打工的時候認識的。現在寨子里的姑娘都不愿意嫁給寨子里的小伙子,她們在外面呆久了,就看不上寨子里的小伙子,都愿意嫁給外地人。所以寨子里的小伙子大多數都是娶老撾姑娘。一般都是找老撾的苗族,這樣語言相通,可以交流。因為相對中國來說,老撾那邊的生活條件更苦、更差一些,所以老撾的姑娘都愿意來中國。老撾姑娘也都很勤快、很能吃苦,她們在中國很知足。納龍村的苗族,原來居住在“十四公里”國界線處的山上,以“刀耕火種”的方式進行生產,遷徙流動性大。加之國界線兩側的國家政策和國家形勢變化的影響,跨國流動成為正常的“逃避藝術”,人們根據生存環境,理性抉擇居住的空間。
在整個調查的過程中,所有的被訪談人被問及為何遷徙到老撾又為何回歸的時候,課題組得到的一組關鍵詞是:人民公社、大躍進、文化大革命、批斗、生存、戰爭等。縱觀中老邊界100多年的邊民遷徙歷程,其涉及到民族國家邊界線的確定、國內社會形勢的變遷、老撾國內政治形勢的發展、以及邊民自我生存的需求。中老邊民出現大規模的離散現象主要集中在1958年和文化大革命開始的階段。當地人說“外逃”的主要原因:一是當時的政策不好,正好也遇見劃分階級的時候,怕被批斗;二是勞動太苦,又不自由,干什么都要介紹信,去哪都需要報備,聽說當時老撾自由,就想著去那邊;三是一些不法分子以訛傳訛,抹黑共產黨的政策,讓大家對共產黨的看法產生了陰影;四是大躍進時期,合作社時候生活太困難了,吃飽都成問題,又苦又累,就不想在中國了,去老撾想干就干,自由些。由此可見,邊民的流動是以生存訴求為第一目標,無論是基于傳統的生產方式還是因為社會運動,都是邊民的理性抉擇。
四、生計:中老邊民流動的原動力
邊民是一個集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為一體的,生活在現代民族國家邊界線一帶的人群共同體。“邊”主要相對于“內”而言,即遠離內地而與其他國家接壤之地。從民族國家主權的視角,“邊”是一個“無縫空間”,因為主權范疇的邊界是“線性”的;從社會角度看,“邊”是一個“縫隙空間”,因為社會范疇的邊界是“彈性”的。因此,在民族國家邊境地區形成了以主權符號(界碑、界河、界線等) 為標志的線性區隔和以生計活動為目的的縫性場所的多重空間,這為邊民的離散與回歸提供了客觀條件上的可能性。民族國家對“地方”的線性分割,在保障了地方人群的“安全”的同時,也形成了一個他者的“空間”以及地方人群對于空間自由的想象,造成了邊疆地區聚集了地方安全感和空間自由感為一體的場所。地方所提供的“安全感”是地方人群基于客觀社會事實而產生的價值判斷,也就是說地方對于特定人群來說,需要提供人群生存與延續的基本物質資源與保障。邊民的離散基本上是其“安全感”逐步減弱過程中而出現的被迫式理性抉擇。他國的陌生感、危險性對于邊民來說,是可以部分忽略的因素,因為邊民歷史交往的慣性、文化的共性、族源的相同等,為其塑造了一個超越民族國家的、熟悉的地方感,給予其在特殊時期為了生存與生活而進行抉擇的機會。相對于內地居民,邊民借助于多重空間的彈性,在民族國家發展的進程中,根據國內形勢和生存發展的需要,進行理性的抉擇,即離散或回歸。
中老邊境地區是集政治、社會、文化為一體的多維空間。政治空間關涉主權、社會空間關乎生產、文化空間關乎生活,當三者交織在民族國家邊境地區的時候,邊民形成了一個以生存為宗旨的經驗性抉擇。在段義孚看來,“地方意味著安全,空間意味著自由”[15]。當邊民社會在發展歷程中,遇到重大的社會變革,原有的地方安全感逐漸消失的時候,人們就開始向更自由的空間離散,而作為邊界線外側的“他者”世界就成為流動的方向;當國內地方安全感恢復后,“他者”空間的自由沒有達到預期的目標時,人們便選擇回歸地方,追求有意義、有秩序的生活。所以,在國內政治空間邊界內的組織、制度、意識形態的權威危及到個體生存時,個體會利用邊民地方性社會空間內的資源,突破政治空間的邊界而進行流動。改革開放之前,中老沿邊一帶的邊民由于中國內部的戰爭、剿匪、鎮壓反革命、土地改革、民主改革、“極左路線”、文化大革命等出現群體性的邊民離散;同時,隨著國內形勢的好轉與經濟社會的發展,以及老撾國內形勢的緊張,離散的邊民則又開始回歸。改革開放之后,邊民的離散與回歸更多的屬于個體行為,邊民到相鄰國家進行經貿活動,以期獲得更多、更好的社會資源。由此可見,國內的政治局勢、社會生態只是邊民離散與回歸的推動力,而非根本性的原動力,作為個體的人,生存與發展是其作出抉擇的原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