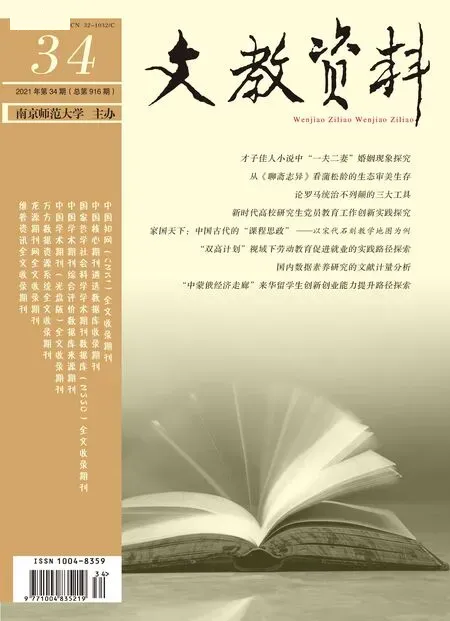從《聊齋志異》看蒲松齡的生態審美生存
陳春鳳
(中南大學 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湖南 長沙 410000)
一、蒲松齡與生態審美生存問題的提出
面對“現代性”極度擴張導致的人的生存狀態的逼仄,以大衛·雷·格里芬(David Ray Griffin)為代表的后現代哲學家提出以“生態論的存在觀”取代認識論的現代范式,試圖從建構性思想出發來改善人的生存狀態。在這一背景下,生態美學關注自然和人的存在,強調人與世界的交融,“以‘人在世界中存在’的本真生存升華為審美體驗的方式”[1]。在這種審美體驗中,自然不再是人的視域所挾持之物,而得以從對象性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它不來源于什么,也不為了什么,它自身就是自身的緣由和目的”[2]。而人自身也在不斷消解現實世界各種欲望和功利目的的束縛,以及由此所造成的生存坎坷和生存困境,從而擺脫物與欲對人的挾持,自由地生活在自然世界中,自然和人相互解放又各自回歸本身。
作為一種前沿的理論形態,生態美立足當下人們的生存狀態而面向美好的人類命運暢想。生活在明末清初的蒲松齡似乎和生態美學并無直接的聯系,但在《聊齋志異》中,蒲松齡通過融入自然世界,擺脫了現實生存的磨難和欲求對自身的束縛。毋庸置疑,這是蒲松齡生態審美生存的表現之一。然而在整個20世紀,學界大多研究者僅關注《聊齋志異》中的社會生活內容,忽視其中的自然書寫以及自然與人的關系的表現。進入21 世紀后,著名蒲學家馬瑞芳和美學家葉朗先后都注意到了《聊齋志異》中的自然,并對其進行了相關闡釋。在2020 年,曾繁仁的生態美學研究高度關注了《聊齋志異》中的自然書寫[3],這使我們以更開闊的生態學眼光看待文本中自然與人的關系,并從中窺探作者的審美方式和生存方式。而蒲松齡之所以會選擇生態審美的生存方式,和他的個人遭遇息息相關。
蒲松齡從19 歲(清順治十五年)應童子試以縣、府、道三試第一補博士弟子員之后,到72 歲時才最終得一虛銜—歲貢生。蒲松齡對科考抱著極高的熱忱卻屢試不第。其中既有清代科考標準極其嚴格、蒲松齡生活期間山東進士錄取名額銳減、教育條件較差等客觀原因,但最主要原因還在于蒲松齡個人“制藝”不符合清代科舉考試八股文的錄取標準。清代劉熙載如此總結八股文寫作的擇優標準:“文不外理、法、辭、氣。理取正而精,法取密而通,辭取雅而切,氣取清而厚。”[4]理、法、辭、氣四個方面是科舉考官評卷的衡文標準。所謂“理”即四書五經之學,“法”指文體格式,“辭”即表達和文采,“氣”則指作者的涵養。而據學者對《聊齋全集》卷十《聊齋制藝》收錄的23 篇八股文的分析來看[5],蒲松齡所作的八股文:一是喜好小說筆法,不滿足“辭”所要求的“真”與“正”;二是“學理不深,對圣賢之言體悟不透”[6],又不滿足科考文“理”的標準;三是制藝格式不規范,不符合“法”的要求,最顯著的例子如康熙二十六年(1687 年)鄉試蒲松齡因越幅被黜。概言之,蒲松齡“雅愛搜神;情類黃州,喜人談鬼”[7]的小說家氣質和科舉考試的要求有根本上的不同,但由于科舉是古代文人唯一的出路,他只能一次次通過參加科舉來改變自身命運。個人愛好與現實之間的對抗落在蒲松齡身上似乎成為不可調和的矛盾。
屢試不第的痛苦遭遇之外,蒲松齡身上另一塊“壘愁”是情愛上的壓抑。蒲松齡自26 歲(康熙四年)起在外坐館執教至70 歲(康熙四十八年)才撤帳回家,其妻劉氏又溫謹樸訥寡言,“出逢入者,則避扉后,俟入之乃出”[8]。聚少離多,妻子恪守閨訓到古板,又兼貧困潦倒,種種生活境遇使得蒲松齡的心理欲求備受壓抑,再加上科考場上的受挫,蒲松齡便將目光轉向了鄉野世界。通過創作《聊齋志異》,蒲松齡與各類植物和動物建立起了親密的關系,在敘寫這些動植物和人的故事時不斷超越現實欲望對自身生存的鉗制,進入人與自然、意與境、情與境圓融共舞的審美世界中,體驗生命存在的價值與意義,走向生態審美生存。
二、《聊齋志異》中的自然:人類的親密伙伴
促進人與自然的雙向解放、和諧共存是生態審美生存的核心問題。因此,一個人的生態審美生存就表現在他是如何看待自然、與自然建立了什么樣的關系以及自然于其而言是何種存在等方面。在中國古代審美文化中,儒家把自然物象和社會生活相聯系,借自然進行倫理比附,“比德”觀就是儒家自然美學思想中的重要內容。如《論語·子罕》篇:“子曰:歲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9]朱熹對此注言:“小人之在治世, 或與君子無異, 惟臨利害,遇事變, 然后君子之所守可見也。”[10]這里用松樹和柏樹經歷寒冬而不改其蒼翠來比喻君子堅韌不屈的氣節。再如《論語·雍也》篇:“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11]自然物象在此喻指美德,進而指稱不同的性格。儒家思想體現了中國古代自然審美經驗,但這種對自然物象的把握還算不上真正的生態審美。從根本上來說,這些自然物象總是和社會倫理相關,是一個民族在特定時代倫理觀念的特殊表達。正如薛富興在反思先秦“比德”觀時所指出的,“‘比德—比興—借景抒情’便是中國古代自然審美傳統下‘不適當’自然審美的典型代表”[12]。
在道家文化中,莊子特別親近自然。在《莊子·逍遙游》篇,惠子與莊子討論一棵皮粗質劣、長著木瘤盤結的喬木。惠子以此樹不中繩墨和規矩、不為木匠理睬來反駁莊子此前對“用”的否定。對此,莊子如此回應:“今子有大樹, 患其無用, 何不樹之于無何有之鄉, 廣莫之野, 彷徨乎無為其側, 逍遙乎寢臥其下。”[13]與惠子不同,莊子通過逍遙者與喬木的關系來表明他對自然物的態度:將大樹樹于“無何有之鄉”的廣漠曠野,而人自由地臥在大樹下。在逍遙者與樹所構成的生存關系中,大樹生長在自然之野中,不為人之“用”所縛而回歸到了其自身和自然世界。與此相對,悠閑臥坐在大樹旁的逍遙者也擺脫了人欲,與大樹一樣回到人本身,自由地游于自然與人的本性中。如此,物與人各得其所,在存在的家園中自由地棲居。莊子筆下逍遙者對大樹的態度正是一種生態審美的態度,逍遙者實現了一種生態審美生存的方式。
歷經千年發展與傳承,儒道文化綜合作用,深刻地影響著歷代文人士子。這從《聊齋志異》多種文化現象混融的局面就可見得,蒲松齡一方面繼承了儒家人格,表現出了極強的入仕精神;另一方面繼承了莊子的自由人格,在仕途坎坷、不得志之時寄情自然,通過悠游于自然中而不斷消解現實遭遇帶來的束縛與苦難。在《聊齋志異》近五百篇短篇小說中,蒲松齡提及了多種自然物象,涉及動物的篇章就有1 / 3 以上,種類數以百計,其中的主角有狐、蛇、黿等;涉及的植物不勝枚舉,有如黃瓜、西瓜、橘樹等常見種類,還有耐冬、檞、槚等稀見品種。可以說,蒲松齡筆下出現了一個萬物同處,狐妖神怪“多具人情,和易可親”[14]的生動世界。
在《聊齋志異》眾多篇目中,不乏以自然物為主角的,《橘樹》篇正是如此。此篇語言精簡凝練,敘述了清代興化縣令劉公之女與一棵橘樹之間的深厚情誼。《橘樹》中的小橘并沒有通過任何幻化或變形的方式增加與劉女的交集,它始終按照自己的方式生長著,隨著時間的推移變成一棵“十圍”大橘樹。第一次看到小橘樹時,劉女“不勝愛悅。置諸閨闥,朝夕護之惟恐傷”[15],由衷生發出對小橘樹的喜愛與驚嘆。劉縣令任滿時,由于橘樹已“盈把大”,不方便簡裝束行,就將橘樹留在了興化縣。面對與心愛之物的分別,劉女“抱樹嬌啼”。巧妙的是,十余年后劉女丈夫一入仕即為興化縣令,劉女亦隨之前往興化縣生活。劉女本以為橘樹已不復存在,但沒想到橘樹正結初果且“實累累以千計”。劉女丈夫任期內橘樹“繁實不懈”,至其解任時才“憔悴無少華”。《橘樹》篇雖簡短但對橘樹與劉女之間的感情描寫集中且富有起伏:初見之歡、分別之啼、重聚之喜,到最終永別之憔悴無華。橘樹雖然沒有辦法像劉女一樣直接表達自己的情緒,但通過“繁實不懈”與“憔悴無少華”,同樣呈現出了它對劉女的喜愛與不舍。
在我國文學史上,寫橘的詩詞曲賦不少。屈原的《橘頌》到漢末三國曹植、晉代潘岳、南朝梁吳均等人同題的《橘賦》,都從不同的側面描繪和歌頌橘樹。張九齡的《感遇十二首·其七》、孟浩然的《庭橘》以及杜甫的十幾首詩中則以橘樹來抒懷。這些詩句詠物以抒情,前半部分寫景,后半部分緣物抒情。正如薛富興所言,這種“以物興情”的詩歌傳統在本質上其實還是上述儒家“比德”觀的演化,同樣也具有上述“比德”觀在自然審美上遇到的“不適當”問題。與歷代文人的《橘賦》相比,《聊齋志異·橘樹》篇極具特色,重點關注了人與物的關系,在這一點上此篇和上述《莊子·逍遙游》有相似的地方,都通過人與樹的關系來闡明內心的理想世界。但與《莊子·逍遙游》中的逍遙者和大喬木的關系不同,《橘樹》中的人與物并非互不相干,相反,物與人有非常緊密的聯系—橘樹的生長直接和主人公的命運相關,并且,無關利益,劉女并不知道橘樹在自己人生得志之時會果實累累,從而護愛有加,她只是出于對橘樹的“愛悅”而將橘樹“置諸閨闥,朝夕護之惟恐傷”。更為特別的是,不僅人對物充滿喜愛與驚嘆,物對人也產生了至深情誼。橘樹似乎充滿靈性,能感知到劉女的關愛及其命運起伏。
文章中劉女對橘樹的深厚感情體現了人對自然物象由衷的喜愛。她對橘樹的欣賞并不是英國美學家布德(Malcolm Budd)提出的“環境形式主義”式的欣賞—人欣賞自然環境時更多的是欣賞自然中那些細小的自然物的形式與框架。劉女不執著于橘樹的外觀,而是參與了橘樹的生長過程,觀察它從“細裁如指”到“盈把大”再到“樹十圍”,從“繁實不懈”到“憔悴無少華”,在自然的光影交錯和生長磨滅中感受自然的魅力及自身命運的不斷變遷。而橘樹也并不是一個孤立簡單的蕓香科常綠灌木,它根植于大地之中,矗立于天空之下。“它每一個枝條、每一片葉脈都舒張著生命的活力,并有著自己的歷史。”[16]表面上劉女是站在橘樹對面的人,但實際上她們的生命早已融為一體,時間的推移共同作用于二者,她們的每一步生長變化都保持著相同的節奏。這種步調幾乎一致的變化突顯了人作為自然生態一部分的本質,劉女的生命與橘樹的生長相摩相蕩,自然的生機與情感的交互體認統為一體,達到了人與物、物與人圓融共舞的美好畫面。
在《聊齋志異》中,自然物象擁有了與人同樣的主體地位,人和自然建立起親密且和諧的關系。有些篇章雖然著重體現人與自然之間的沖突,但往往以人類受懲罰為結果,如《放蝶》《豬龍婆》《蝎客》等。這從另一個側面突出了作者的觀點:人與自然應和諧相處,自然是人的親密伙伴。當然,僅從尊重自然的態度出發還不足以體現一個人的生存具有生態審美趨向。在書中,蒲松齡還通過自然物象的幻化來消解心中的名與利的欲望,將生態審美生存更加強烈地表達了出來。
三、《聊齋志異》中的欲望書寫:從自然本能性存在到生態審美生存
《聊齋志異》近五百篇短篇小說中,以情愛為主題的作品數量最多,這些愛情故事多以落魄書生、浪子與花妖狐魅為主角。在他們身上,欲望在自由地舒展、涌現。如《毛狐》和《瞳人語》篇中的桑間濮上之欲:“顧四野無人,戲挑之。婦亦微納。欲與野合”[17];《嬌娜》和《蓮花公主》的色相之欲:“得此良友,時一談宴,則‘色授魂與’,尤勝于‘顛倒衣裳矣’”[18];《伍秋月》和《荷花三娘子》篇的交合之欲:“宗近身啟衣,膚膩如脂。于是挼莎上下幾遍”[19]。這些書寫不禁令人發問:作者為何要反復書寫男女欲望?為什么書中男性欲望下的對象絕大部分都由自然物幻化而來?解決了這些問題,我們才能更好地挖掘出《聊齋志異》欲望書寫背后的原因及其對作者的意義所在,而非單純地將這些文本現象歸結為男權社會的產物。[20]
傳統儒家文化認為,美應符合善的規定,一種美的感情應“發乎情,止乎禮義”[21]。至于兩性之情—性愛,儒家文化承認其是“人之大欲”,但同時也把兩性性愛納入倫理的規范中。《禮記》有言:“昏姻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后世也,故君子重之。”[22]這句話清晰地體現出儒家文化對男女結合的定位:孝事宗廟、繁衍教養后輩。男女之間的情愛在儒家文化的禮制之下變成了孝事尊長、延繼后世的倫理責任和義務。但到明代中葉,隨著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萌芽,商品經濟在東南沿海地帶發展起來,一批市民階層開始崛起。在思想界表現為以王陽明心學以及以李贄為代表的泰州學派從理學禁欲桎梏中覺醒,肯定人們追求物質欲望的合理性,宣揚個性解放、真情至上。到了清初,統治者為安定社會,順治帝親政不久就頒布了一系列思想文化政策,意圖扭轉明末的人心散漫放蕩之風。但由于清初男女比例失衡,男多女少,“婦女生活的自由度相對較大,平日常男女相雜,交往不避嫌,桑間濮上之風時有所聞,‘見其守貞者鮮矣’”[23]。在下層民間,男女相處之風還相對開放。在此社會思潮和民間風俗的氛圍中,蒲松齡肯定人情、人性及人欲。如《書癡》篇彭城郎玉柱言:“天倫之樂,人所皆有,何諱焉?”[24]又因常年坐館在外,與妻子聚少離多,蒲松齡對于異性和人欲的憂思只能寄諸搜神談鬼的創作之上。
在搜神談鬼的創作中,蒲松齡所描繪出的由自然物象所幻化而來的女性常帶有一種病態美,人物所處的自然環境也常伴隨昏暗陰森的氛圍。例如由老鼠幻化而來的阿纖“年十六七,窈窕秀弱,風致嫣然”[25];蜜蜂幻化而來的綠衣女“腰細殆不盈掬……聲細如蠅,裁可辨認”[26];白鱘精幻化而來的白秋練更是嬌顫文弱:“移燈視女,則病態含嬌,秋波自流”[27];仙女云蘿公主則“輕如抱嬰”,“四肢嬌惰,足股屈伸,似無所著”[28],世俗衣物著于其身“幾于壓骨成勞”[29]。這些女性構成了具有病態審美特征的意象群體:身體輕小,年齡稚嫩,體態嬌嗔羸弱。這種病態的審美傾向使得蒲松齡在塑造女性形象時總是把她們和小而優美的自然物象聯系在一起,如蜜蜂、菊花、鸚鵡、蓮花等。又或者說,在這種病態審美傾向下,蒲松齡總是不自覺地將體型較小的動物身上的友善美好與女性形象結合。這是因為在傳統男權社會中,女性與動植物都處于從屬和附庸的地位,經歷過多次科考不得志又常年獨居坐館在外的蒲松齡很容易便能在這些柔弱的女性和動物身上找到共同感。通過創作,蒲松齡將坎坷遭遇所導致的內心深層欲望的壓抑和科考不得志的哀傷投射在了具有同等柔弱性質的對象身上。
蒲松齡在《聊齋志異》中塑造女性形象時帶有的病態審美傾向雖然與明清時期“美人一根釘”的主流女性審美標準傾向有關,但對其影響更大的是其自身的坎坷遭遇。科考及情感雙雙失意的坎坷遭遇在蒲松齡內心積郁的深厚的哀愁與志不得酬的酸澀通過對女性與自然的病態建構。《聊齋志異》將蒲松齡內心中對女性情愛的渴望表達了出來,從而消解了現實生存中的欲望性和占有性的功利性存在意識對自身生存造成的擠壓。這種消解方式實際上是一種對人的自然肉體生存方式的改善,蒲松齡內心雖然渴求、迷戀異性知己,但他所受的儒家傳統教育及其自身的倫理道德理念約束著他,蒲松齡在外坐館期間并未游走青樓,在其一生中也并未納妾。內心對人欲的肯定和情愛的渴望與道德倫理的約束在蒲松齡思想中是一對無法解決的矛盾,因而他只能通過創作《聊齋志異》來調和心靈深處的沖突。在這種創作中,欲望“不是黑暗本身, 而是一個被揭示了的黑暗, 也就是被思考和言說了的黑暗”;在文學作品中,這些欲望既“通過技藝鏡子般的反映來揭示自身, 而且要在大道的指引下實現自身”。[30]《聊齋志異》正是通過自然的幻化變形,既呈現了欲望,又使得欲望的出現和描寫不過于暴露及粗俗,符合蒲松齡自身的倫理道德要求。通過對女性和自然的病態審美,《聊齋志異》更多呈現的是女性和自然的柔弱品質及男性對女性的欣賞和渴望,而不是單純的男女交歡淫亂。這種方式使得人的肉身所產生的自然欲望帶有一種文化品性,克服了肉身生存中的所產生的占有性功利意識。
人的本原性自然肉體生存是人最根本的生存狀態,但隨著人不斷地融入文化社會,社會性的規范與束縛會在潛移默化中解構人的自然性生存。蒲松齡在本能性欲望與社會倫理規范的沖突中做到了以自然本能生命為根基,以自身的文化修養為內在超越機制,為其生命注入了新的生機與活力。這種超越性機制并不是對自然本能和自然物象的全盤否定,而是將自然物象的生活習性和生命特質與其所幻化成的人物在身份、處境和生存等方面貼合為一體,從而塑造出美好的人物形象。例如《阿纖》一文,老鼠習性和特質成為其所幻化的人物的美好品格。阿纖由老鼠幻化而成,鼠本性好儲糧,阿纖之母正是用儲糧兌換成現錢替阿纖準備嫁妝。嫁為人婦的阿纖“寡言少怒,或與語,但有微笑,晝夜績織,無停晷”,這與老鼠來去無蹤、不喜與人打照面的本性相似。當阿纖與三郎重遇,三郎正愁沒有足夠的錢交付房租時,阿纖領三郎到倉房,“約粟三十余石”,“償還有余”。蒲松齡對老鼠的本性作了巧妙地提取,避開了老鼠一向為人詬病的骯臟一面,將其喜積糧食、悄無聲息之性轉為了阿纖勤儉持家、賢惠溫順的美好人格。
四、結語
蒲松齡在《聊齋志異》中通過幻化將自然物象與人合為一體,編織了許多大團圓式的愛情故事,從而克服了肉身之欲對他的挾持,超越了欲望性和占有性主導的功利意識。從這點來看,蒲松齡的創作邏輯無疑帶有審美性質。《聊齋志異》對人欲和自然物象與人結合的書寫,是蒲松齡對人與自然物象生命本性的思考與把握,在人與自然物象的融通化寫作中解放自身。正基于此,我們說蒲松齡是以一種生態審美式的生存方式棲居于《聊齋志異》世界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