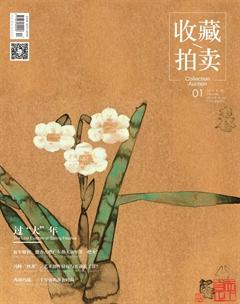馮峰“抄襲”,藝術創作侵權與否誰說了算?
馮善書
1月15日,廣州美術學院教授、實驗藝術系主任馮峰的展覽作品《鴨兔元旦》,被網友公開指責抄襲荷蘭畫家迪克布魯納的Miffy米菲兔經典卡通系列原創作品,從而引發了一場席卷整個網絡的輿情事件。
通過對比分析發現,馮峰的作品在造型、構圖、線條等方面均與米菲免系列有較高的相似度,其中一個顯著區別是,馮峰作品給米菲兔加了個鴨嘴巴。面對輿論,馮峰1月16日在微博上解釋,“鴨兔”其實是在心理學和哲學領域很早就有的一個典型圖例,其《鴨兔元旦》只是圍繞公共知識和信息開展的一種藝術創作。與此同時,個別自稱馮峰學生的網友亦出來為老師站臺,認為這是一種正常的藝術創作行為。然而,從網絡上的評論來說,大部分的名人和吃瓜群眾顯然對馮峰一方的“合理化解釋和描述”并不買賬。
2019年的“葉永青抄襲事件”。面對同樣的輿情危機,馮峰的處理手法與葉永青如出一轍,均否認抄襲并不予道歉,同時把爭議裁判權推向了法律的一端。把這兩件爭議放在一起來分析,可以引向兩個公共話題。其一是,藝術家創作的自由權利邊界到底在哪里?其二是,發生在藝術圈的所有爭議糾紛都要交給法律來解決嗎?如果法律解決不了的怎么辦?
對于第一個問題,最近幾十年來,國內的藝術家一直在一邊模仿、一邊摸索自己的當代藝術發展之路。不管是葉永青的涂鴉系列,還是馮峰的鴨兔系列,都可以理解成是在這個大背景下的一種探索和嘗試。但從實踐情況來看,他們的探索和嘗試無疑都觸及了他人的權利邊界。若說沒有觸及,別人也不會跳出來指責他們。至于這種觸及是合理的,還是不合理的,甚至有沒有引起對原有權利秩序的沖擊和打亂?在葉永青和馮峰看來,最終需要法律來認定。
由此可見,當代藝術雖然天生就想著挑戰和打破原有的話語權和秩序,但作為一種新的文化運動和藝術語言,它在解構的同時,事實上承擔著重構新思想和新秩序的任務。譬如,在創作過程中,挪用、拼貼、解構的對象必須是屬于公共領域的知識信息,創作的目的要形成新的思想主張。何謂公共知識和信息?我們拿到著作權保護的范疇來理解,應該是那些依法不受保護或已經過了保護期的著作。譬如,公共名人的肖像照片,作者過世已經超過五十年的美術作品等。透過這個新秩序,我們也可以明顯看到當代藝術創作的邊界:不管你如何標新立異和嘩眾取寵,都不能侵犯他人的合法權益。
對于第二個問題,由于藝術并非法外之地,把藝術界存在的權利關系和權利糾紛納入法律調整范圍,并無不當。只不過,司法機關處理民事爭議,歷來奉行的是“不告不理”的基本原則。因此,即便藝術家故意、非法侵犯了他人的著作權,只要權益受害人沒有到法院起訴,法院是不會主動介入到事件當中去為當事人定紛止爭的。與葉永青一開始就受到被侵權人指控有所不同的是,馮峰涉嫌抄襲的行為是由吃瓜群眾在微博上指出來的,代表權利方的Miffy米菲中國官微雖然事后發表了一則聲明,但這則聲明并沒有明確表示要借助法律手段來維權。因而,目前馮峰還算不上惹上了法律糾紛。但是,馮峰在事后聲明中,不僅不承認侵犯,反而引導大家去相信法律,潛臺詞當然是,他的行為到底屬不屬于侵權,由法律說了算。
問題的關鍵在于,法律充其量不過是最低水平的道德要求。對于像馮峰這樣一位在社會和行業上均有一定名望的教授級藝術家,對公共事務的參與權利和機會本身就比一般的社會大眾要多很多,難道不應該比一般的社會人具有更強的自律意識和更高的道德水平以及社會責任感嗎?從司法制度上講,程序正義優于實體正義。就算納入到法院審理判決的民事糾紛,也不一定最終百分之百就能得到代表實體權利公正的判決。
回到葉永青事件和馮峰抄襲風波來說,藝術家只是把別人的指責視為一般法律糾紛是不合適、不妥當的,而更應該看成是一起有可能嚴重影響到個人職業生涯和社會聲譽的輿情危機事件。盡管對于大部分的當代藝術家來說,他們的投資者和收藏者非常小眾和固定,但也不要因此就輕視公眾的影響力。社會輿論不一定會影響某些收藏家和企業家的投資行為,但過多的社會負面評價,一定會損害藝術家的個人聲譽和公共形象。但也有人認為,搞當代藝術創作的畫家,哪一個不是在各種社會敏感話題和輿論的風口浪尖上跳舞的好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