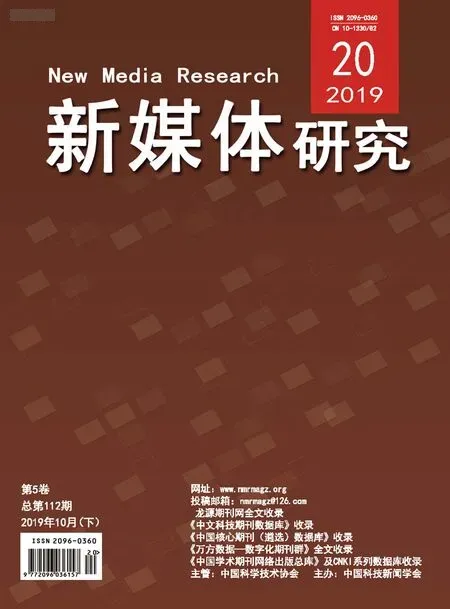智媒時代身體的表現與影響
張玉 崔悅
摘 要 在智媒時代,媒介的具身性促使在主流傳播研究中被遮蔽的身體重新顯現,“身體—技術”實踐成為智媒時代人與媒介關系的表征。在“身體—技術”實踐中,身體表現出了多元的形式,并由此對個體的認知方式、存在狀態與傳統的人—媒關系產生了影響。身體的多元形式及影響從側面印證了身體在傳播實踐中的重要地位,啟示我們應全面認知身體對傳播實踐的形塑作用。
關鍵詞 身體;媒介;賽博格;數據化身體
中圖分類號 G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2096-0360(2021)20-0093-03
在當下的社會生活中,以算法、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為依托的智能傳播實踐成為了人們日常生活實踐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媒介環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個體對外界的感知與行動。在這一過程中,媒介技術與人們的日常生活的聯系日益緊密,人類經驗越來越依賴技術媒介與世界發生關系,媒介的物質形式和信息內容構成了人類社會活動的背景和前景[1]7。與此同時,由于智能技術的具身性,被遮蔽的身體開始逐漸顯現,媒介技術與身體的聯系日益緊密。新媒介技術的出現改變了技術具身于人的方式,身體在媒介技術的介入下具有了多種表現形式,由此產生了一系列影響。
媒介與身體的關系問題是傳播研究中的重要議題,特別是近年隨著傳播研究“物質性”轉向的興起及媒介技術的進一步發展,媒介技術與身體的關系日益凸顯。從生理層面來說,身體是一切傳播實踐得以開展的物質前提,從口語傳播到當下的智能傳播,每一種新媒介技術的出現都會改變個體的感知模式與認知方式,媒介技術以身體為中介對現實世界施加影響。身體所感知的世界并不是純粹客觀的世界,而是經由技術所中介的世界,這也就決定了身體和技術不可分割的狀態。
離身與具身是認知媒介與身體關系的兩個主要維度。在西方主流的思想認知中,經由身體感知而形成的認知被認為是主觀的和不可靠的,身體被認為是被壓制和超越的,由此造成了近代去身性的哲學困境。在笛卡爾身心二元論的影響下,形成了離身認知(disembodied cognition)的范式,離身認知著重強調認知在功能上是能夠脫離人的身體而獨立存在的[2],在離身認知的范式下,身體的地位被進一步擠壓。而具身指的是在投入到某種活動時,人的身、心、物以及環境自然而然地融為一體,以致力于該活動的操持,具身性既是我們的身體向周圍世界的“外化”,也是周圍世界向我們身體的“內化”[1]10。媒介與身體的關系是具身還是離身,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媒介的物質特征決定的。構成媒介的物質如果必須依賴身體,那么媒介很可能就是具身的,如果相反,那么媒介技術或媒介很可能就是離身的。從人類傳播史來看,在口語傳播時代,信息通過聲音得以表征,聲音必須依托身體的物理特性決定了語言與身體的不可分割;而在大眾傳播階段與互聯網的發展的早期階段,文字、書籍與電子媒介完全可以脫離身體而獨立存在,信息能夠以文字、圖像的形式被表征,身體在傳播中變得“隱而不見”,造就了傳播研究的“去身體化”傾向。長久以來,身體在傳播研究中一直處于被遮蔽的狀態,這既是主流傳播學重內容、重效果產生的弊端之一,也是理性主義對感性認知壓制的結果。
在智能傳播時代,“傳播技術的發展,突出并加劇了技術的具身性趨勢,當前的新傳播技術的鮮明特點就是,技術越來越透明化,越來越深地嵌入人類的身體,越來越全方位地融入我們的身體經驗”[3]。智媒時代媒介的物質構成,如作為基礎設備的移動智能手機,其體積小、可移動的物理特征使其可以嵌入到個人的身體經驗之中。隨著傳播技術具身性的增強,身體與技術耦合所形成的唐·伊德所言的“技術身體”,成為勾連個體內部經驗與外部經驗的中介,“身體—技術”實踐成為智能傳播時代人與媒介關系的主要表征。在這一實踐中,身體表現出了多元形式,由此對個人的認知方式、存在狀態與人—媒關系產生了一系列影響。
在智能傳播時代,技術與物質性的身體的耦合,使得身體的形式正在走向多元化。首先,媒介對主體的全面入侵使得身體成為媒介的延伸。其次,技術與身體耦合所催生的新型主體“賽博格”成為傳播實踐中的主體,哈拉維在20世界80年代提出的賽博格的相關概念如今正在成為現實。再者,大數據、算法依托身體在各種平臺中所留下的痕跡,生成了數據化的身體,身體不僅以肉身的形式存在著,而且以也以數據的形式的存在著。
2.1 作為媒介延伸的身體
麥克盧漢的著名論斷——媒介是人的延伸,啟發了眾多學者從感官或身體的角度認知媒介,但媒介是人的延伸只說明了媒介與人類身體感官的關系,但對于身體在媒介技術系統中所扮演的角色與所發揮的作用卻被忽略了。實際上,在媒介成為身體延伸的同時,身體也在影響并塑造了媒介技術系統。在智能傳播時代,由于智能手機等媒介的具身性,身體成為媒介技術系統的一部分,媒介不再僅僅充當人的工具和手段。與現代技術完美結合的媒介不僅擺脫了人,反過來以“座架”的方式規制人,塑造人,控制著人和人的生活方式,人成為媒介的延伸[4]。物質性的身體一旦進入到傳播網絡之中,就成為其中的一個節點,與其他的技術物相互形塑,并在具體的媒介實踐過程中受制于技術的邏輯。在這一過程中,身成為媒介技術系統的“義肢”,從這種意義上來說,人成為媒介的延伸。
2.2 賽博格主體的誕生
在智能傳播時代,新媒介技術持續地將機器、網絡的邏輯與有機體人類的邏輯雜糅,經由媒介技人與環境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融合,主客體的邊界正在逐漸消失[5],促使了新興人類主體——賽博格的誕生。賽博格可以簡單的理解為有機體與媒介技術之間相互融合、不可分割的狀態而形成的新型主體,它是有機體和機器集合的新型主體。這里的賽博人不是指電子機器融入于物質性的身體,而更多的是指身體與媒介技術不可分割的狀態,智能傳播時代的媒介使用已經成為了個體的日常生活實踐,在這種情況下,媒介與身體始終處在緊密連接的狀態,人與技術處在一種不可分割的狀態,這意味著智媒時代的身體不只是純粹的生理意義上的身體,而始終處在被技術所穿透的狀態中,賽博格成為了一種常態化存在的新型主體。
2.3 數據化的身體
在智媒時代,身體浸潤在媒介技術所建構的環境中,“數字資本和平臺資本利用我們行為生產的數據實現了數字繪像,形成了比我們還了解我們自己的數字身份”[6]。所謂數據化的身體,可以簡單理解為物質性的身體在與媒介交互的過程中,在網絡世界留下的痕跡而形成的,算法、大數據與人工智能技術使得身體以數據的形式被表征。與有機物和機器或機器集合而形成的賽博格主體不同,數據化的身體雖然以現實生活中的物質性的身體為依托,但它是虛擬的,它并非物質性的實體存在。在多數情況下,介入到傳播實踐中的身體,并不是以實體性的身體的形式出現的,而是以數據的形式呈現的。在我們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各類平臺中,平臺向個體所推送的內容,或者說平臺對于個體的反饋,就是以身體在平臺上的操作所留下的數據為依據的,人們的各類媒介實踐行為都會在網絡上留下痕跡,在這一過程中,身體是以數據的形式在平臺上得以表征的。
3.1 重塑了個體的認知方式
人對現實經驗的感受和認知受到技術中介的暗藏的轉化,技術并不會“像對象一樣的東西”,而是“融入到”人的身體經驗中[7],從而改變人的認知方式。如前所述,每一種新媒介技術的出現都會改變個體的感知模式與認知方式,進而影響到個體對世界的認知。印刷媒介的出現使得視覺超越其他感覺而處在認知的中心地位,造就了認知的視覺中心主義傾向,人類其他的感官經驗反而被遮蔽了,而后來作為中樞神經系統延伸的電子媒介的出現,使人又重新回到“視聽平衡”的狀態。與上述媒介技術不同的是,智能傳播時代的技術具身并不是對身體某一感官的強化,而是從整體上改變了個體認知世界的方式。
無論是作媒介延伸的身體,還是與技術相融而誕生賽博格主體,都是“為技術所穿透”的身體,“技術—身體”實踐重塑了個體的認知經驗。當身體是媒介的延伸時,這時身體的行為方式受媒介技術邏輯的影響,如個體在使用微信等各種傳播平臺時,這時身體就成為了傳播平臺上的一個節點,個體的行為邏輯就要受到平臺性質的限制,人對事物的認知與平臺的信息呈現方式和運作模式息息相關。也就是說,平臺整體上影響了人的認知方式,而不是通過增強個體的某一感官來形成對事物的認知。當賽博格作為傳播主體時,其遵循的也是相似的邏輯,與身體相融的技術之特性塑造了人對世界的認知方式,技術融入到了個人的身體經驗中,比如智能手機就融入到了身體經驗之中,個體通過智能手機來中介外部世界,形成具體的認知,在這一過程中,我們將媒介的呈現內容與方式視為我們自己的感知。智能手機作為各種媒介的集合,從整體上塑造了個體感知外部世界的方式。在當下,技術與身體的融合使得“傳播的主體已經從掌握工具的自然人轉變為技術嵌入身體的賽博人”[8]。當然,上述兩種情況并不是各自獨立的,在更多的情況下兩者是相融的狀態,人既是媒介的延伸,也是賽博格主體,賽博格本來就是有機物與無機物相融的產物。
3.2 改變了個體的存在狀態
首先,身體的數據化使監視資本主義逐漸興起。由于平臺或者機構與用戶之間不平等的權力關系,平臺在多數情況下無視個人隱私,任意收集用戶的相關數據,人們的一切行為都轉變成了透明的、可以被監視與預測的數據。個人被卷入進大數據時代的生產關系,身體或人的行為被抽象為簡單的數據與符號,數據成為了衡量一切的標準。“刷臉”“指紋識別”使得人的生理信息也轉被轉化為數據,成為數據監控系統中的一部分。個人行為信息與生理信息的數據化形成了個人的數據身份,而數據身份的建立,意味著政治之外的肉體的消亡,被數據化意味著所有的生物性個體變成了人口,他們不再是可以逃逸的生命體,而是在現代生命政治治理技術之下的身份,唯有當我們可以被數據和身份識別時,我們才存在,才具有公民的地位[9]。這使得個體之間豐富差異性被抹除,人成了數據化的符號,個體以數據的形式存在著。
其次,身體的數據化也使人更容易受到媒介技術的“反向規訓”,以算法推薦為核心的抖音的普及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它通過物質性的身體在網絡或平臺上留下的痕跡,可以輕而易舉的了解到個體的興趣偏好,情感偏向等,從而推送個體在潛意識中感興趣的內容。我們越來越依賴媒介不僅是以為媒介與日常生活實踐的不可分割,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媒介越來越“了解”我們,再者,身體的數據化實現了從肉身在場到虛擬性涉身在場的轉變。“缺席的在場”就是這一現象的典型例證。身體的數據化使得身體能夠以數據的形式突破時空與距離的限制,通過終端的連接實現虛擬性涉身在場,網絡會議、視頻通話都是身體的虛擬性涉身在場。
3.3 挑戰了傳統的人—媒關系
長久以來,在現代功能主義的范疇下,媒介被視為信息傳遞過程中中介化的工具。它秉持的是海德格爾概括的技術流行觀念:“技術是合目的的手段,是人的行為”,預設了人先于技術的主體性存在,遵循的是主客二元對立范式,即把人視為傳播實踐中的主體,把媒介(技術)視為滿足人的需要而存在的客體。把媒介視為傳播傳播實踐中客體化的工具,造就了傳播研究的“傳遞觀”取向,即把傳播視為意識主體之間信息流動的過程,在這一取向下,媒介成為了傳播實踐中透明的、純粹的渠道,而身體成為了傳播研究中必須要克服的障礙,這一“去身體化”致使身體長期處于被遮蔽的狀態。
而在智媒時代,人與媒介的主客體預設遭遇了挑戰。如前所述,“身體—技術”實踐成為了智媒時代人—媒關系的主要表征,而在“身體—技術”實踐中形成的賽博格主體與成為媒介“義肢”的身體,說明了人與媒介的關系并不是簡單的二元對立的關系,而是人與媒介相互依存,共同形塑著傳播實踐,這意味著應當超越主客體范式,去認知人與媒介的關系。行動者網絡理論為超越主客范式、認知人—媒關系提供了思考方向,在行動者網絡理論中,所有組成事物的要素都是行動者,行動者之間并沒有主客體之分,行動者經由轉譯連接構成了事物的狀態。以此觀照人—媒關系也就意味著,人與媒介都只是傳播實踐中的行動者,并無主體與客體的區別,它們都是傳播實踐得以進行的必要條件。因此,對人—媒關系的認知應有主客體對立轉移到行動者連接上來,關注傳播實踐中的人與媒介的交互。
在智媒時代,媒介技術的具身性使得在主流傳播研究中被遮蔽的身體重現顯現,“技術身體”成為了勾連個體內部經驗與外部世界的中介。智媒傳播中的“身體—技術”實踐促使身體的形式走向多元化,作為媒介延伸的身體、賽博格主體及數據化的身體既體現了“身體—技術”實踐的豐富性,也體現了身體在傳播研究中的復雜性。身體形式的多元化重塑了個體的認知方式,改變了個體的存在狀態,并挑戰了傳統的人—媒關系。智媒時代身體的多元形式及其影響從側面印證了身體在傳播實踐中的重要性,這啟示我們應當超越傳播研究的“去身體化”預設,全面認知身體對傳播實踐的形塑。
參考文獻
[1]芮必峰,孫爽.從離身到具身:媒介技術的生存論轉向[J].國際新聞界,2020(5):7,10.
[2]於春.傳播中的離身與具身:人工智能新聞主播的認知交互[J].國際新聞界,2020(5):37.
[3]孫瑋.交流者的身體:傳播與在場:意識主體、身體-主體、智能主體的演變[J].國際新聞界,2018(12):87.
[4]姜紅,魯曼.重塑“媒介”:行動者網絡中的新聞“算法”[J].新聞記者,2017(4):26.
[5]孫瑋.媒介化生存:文明轉型與新型人類的誕生[J].探索與爭鳴,2020(6):17.
[6]藍江.外主體的誕生:數字時代下主體形態的流變[J].求索,2021(3):37.
[7]唐·伊德.讓事物“說話”:后現象學與技術科學[M].韓連慶,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56.
[8]孫瑋.賽博人:后人類時代的媒介融合[J].新聞記者,2018(6):5.
[9]藍江.生物識別、數字身份與神人類:走向數字時代的生命政治[J].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21(4):199.
30765019082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