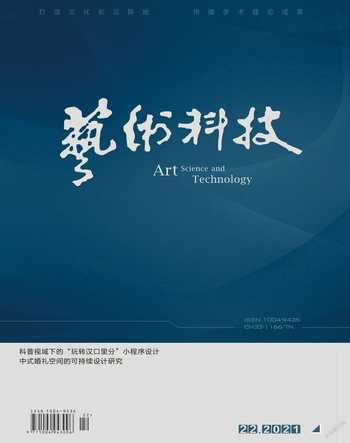貴州黔東南苗族聚落及民居建筑特征研究
摘要:黔東南苗族人口眾多,具有悠久的歷史,特殊的地域環境孕育出了適合其生存的聚落文化,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苗族形成了獨特的風俗習慣,影響著其建筑與居住形式。因為歷史記憶與民族文化的傳承,黔東南苗族在聚落及民居特征上存在一定的規律。文章從聚落與民居兩個層面分析黔東南苗族建筑的具體特征,對其平面、功能及形態進行解析。
關鍵詞:黔東南;苗族;建筑;聚落
中圖分類號:TU25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9436(2021)22-0-03
黔東南位于貴州東南部,總面積約三萬平方千米,以山地為主,東部和南部為海拔較低的丘陵和盆地,南北西三面高而東部低。境內河谷縱橫,山巒延綿,自然資源豐富。境內河流眾多,河網呈樹枝狀展布于各地。地質地貌的特殊性對于苗民聚落選址、民居布局及建筑風貌有很大的影響。
歷史上苗族由于戰爭經歷了數次遷徙,主要沿長江流域的上游支流沅江和清水江溯江而上,輾轉至黔地。遷徙促使苗族區域形成與分化,苗族歷史遷徙影響著聚落的形成與發展,聚落作為土壤孕育了苗族文化,建筑特征也因自然環境因素和軍事戰略不同而存在差異。苗族同胞由長江中下游挺進黔東南后,在此地繁衍生息,選擇聚族而居,半山居住的方式能夠更好地生存與延續。
1 黔東南苗族聚落特征
1.1 聚落選址
黔東南苗族主要分布在清水江以南的多山地區,雷公山一帶最為密集,主要聚居在雷山、麻江、臺江等地。苗寨聚落多分布在山腰或山頂,選址受到自然生態環境、歷史遷徙以及宗教信仰等因素的影響。
選址特點表現為依山而寨,擇險而居。苗族大多選擇在地勢險要的高山地區聚居,這是因為其在長期的封建王朝進剿和壓迫中形成了防衛意識。由于歷史因素動蕩不定,苗民為了獲得安定的居住環境,增強村落防御能力,往往選擇隱秘性較強的深山密林居住,以便更有效地保護族人。苗族也特別重視風水,將山與水視為大自然中的神靈。通常會讓巫師探察風水,在選址上他們普遍認為背山面水可以“藏風閉氣”,因此在選址時會綜合考慮山勢、日照、水流等因素[1]。
水源以及耕地是生產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也是村落選址中極為重要的因素。鄰近水源便于日常生活以及農耕灌溉,也利于消防。由于地勢高峻,山巒連綿,平坦之地較少,為節省出更多的耕地,聚落常修建于山勢較為陡峭之處,將平緩之地留作農田。若地形條件不滿足,還會采用梯田的形式。梯田一般始自山腳,在宜開墾的坡地上拾級而上,直至山腰或山肩。黔東南苗族的梯田文化具有獨特的文化遺產價值,是苗族人民寶貴的經驗積累和智慧結晶。
1.2 聚落布局特征
苗族聚落根據村寨規模以及地形條件靈活布局,建筑群體較為松散。位于山頂的聚落多選擇地形相對平坦的臺地,布局較規則,呈分團式布局;有些聚落則根據山坡地形的變化成片式分布于山間,與山體融合較好;在低山河谷區,聚落多選擇水邊臺地或山腰坡地,成條式布局;規模較大的聚落或并列或散落分布于山腰坡地,呈現群集式布局[2]。
黔東南苗族聚落布局特征可以概括為因勢利導,布局靈活,借助自然地貌組織聚落空間,大體可分為均質式空間布局與團聚式空間布局。
均質式空間布局受地形條件影響較大,建筑疏密不一,多沿等高線分布,平面形狀不規則,較為松散。聚落外部與自然植被、河流溪水、山田坡地相結合,形成了較為自然的邊界過渡。因崇拜自然,聚落附近的自然環境被較好地保護了起來。團聚式空間布局即村寨在內部布局和形態上呈內聚圍合的特征,存在于部分苗族聚落。主要以蘆笙坪或銅鼓坪為中心向四周延伸,空間秩序較明顯。順應自然地形的變化,民居沿山勢起伏層疊而上,表現出空間結構上的秩序感。
1.3 聚落公共空間特征
黔東南苗族聚落的公共空間與本民族的歷史、風俗、宗教有著密切的關系。苗族人民居住環境相對閉塞,分散在大山之中,因此在聚落人口較少、生產力水平不高的原始階段,族群居民需要經常交流感情,相互團結,凝聚力量。而聚落中的交往儀式及公共空間則維系著整個聚落的人際關系,自然也是節日聚會、處理糾紛、議事商討的主要場所,具有一定的象征意義。
銅鼓坪或蘆笙坪是苗寨主要的公共交往場所,也是苗寨的中心空間。一般為面積較大的平地,通常表面用鵝卵石或條石按照太陽紋的圖案鋪設,表達對太陽的崇拜之情。中心為一圓形巨石,上插有銅鼓柱,銅鼓柱呈牛角形,用來懸掛銅鼓,圓形場地周圍設有一圈長廊作為遮光避雨的休息場地。每逢重大的節慶或祭祀活動,人們都會聚集起來表演銅鼓舞、花鼓舞等節目,演奏古樸悠揚的樂曲[3]。
除了交往空間外,還有生產類型空間、交通類型空間,與人們日常使用需求息息相關。生產空間主要作用是存儲糧食,包括禾晾、谷倉群等獨具特色的倉儲設施。禾晾是晾曬禾把的木結構建筑,而谷倉則通常修建在離住居較遠的寨邊或路口,方便農忙運輸。交通空間則主要起到日常通行、連通過渡的功能,包括巷道、寨門和風雨橋等。寨門作為村寨入口,在早期為了御敵防衛常設在地勢險要之處,寨門多采用石塊筑成,且選址上兼顧村寨的風水。風雨橋一般建在村頭的溪水河畔,是一種廊樓與橋合一的橋梁建筑。作為一種重要的公共空間,其代表的文化在苗族有著諸多含義,苗民建橋、祭橋、過橋等儀式是一種生殖崇拜的體現,寄托著子嗣興旺的愿景。
公共空間建構起寨內與寨外以及寨內各類空間之間的相互關系,支撐起聚落內部各物質要素的結構網絡。
2 黔東南苗族民居建筑特征
2.1 建筑形式及材料
黔東南吊腳樓在建筑形式上可分為單吊式、雙吊式、四合水式以及平地起吊式。單吊式即“L”形房屋布局,主樓為平地,一側廂房懸空;雙吊式即“U”形房屋布局,兩側廂房懸空,類似于三合院;四合水形式較為少見,部分大型苗族公共建筑會采用此種類似四合院的建筑形式;平地起吊式即民居總體懸空,為全干欄式結構。
苗族受到漢族社會“天人合一”思想的影響,在建筑形制上尊重自然,順應地形地勢,與生態環境相協調。
民居以單吊式與雙吊式為主,也存在部分平居建筑,平居建筑多為二層且帶院壩。中間為堂屋,主屋旁邊分布有外部的披廈,具有廚房、糧倉、衛生間等多種功能空間,并與主體建筑組成院落式空間。平地式民居將正屋前的水泥平地作為自己的院落,且一般無圍墻,院落面積有大有小,其廂房屋頂多采用歇山頂的形式。在黔東南雷山、臺江等地,由于坡崖山地的復雜地形以及山間多雨潮濕的氣候因素,半干欄式吊腳樓的建筑形式更能滿足當地苗族人民的生活需求。苗民以數根木柱為建筑底部的支撐,讓建筑一部分懸挑出來,架空于坡地之上,建筑后部置于石砌的臺基上。
2.2 建筑材料
由于地域文化的不同,建筑材料的選擇也各具特色。黔東南苗族民居具有鮮明的鄉土特色。早期苗族建筑多為木架結構的茅屋形式,后來隨著社會的進步,聚落出現了以青瓦鋪蓋屋頂的瓦屋。結構形式與茅草屋差不多,有木架結構的,也有石頭、土墻混合的。聚落逐漸發展壯大后,由于地形的限制以及干欄式建筑文化的影響,黔東南苗族現存民居建筑以干欄式為主,分布區域主要在黔東南的雷山臺江等地,民居保存完整,工藝精巧。
建筑材料方面,考慮到使用要求及經濟要求,建筑基本上以木結構為主體,木材多使用堅固耐用的杉木,次為松、楓、樟等。雖然材料種類與城市建筑相比并不算豐富,但在建構時會通過色彩、質感表現建筑的美感,本地材料的運用也增強了與自然環境的聯系及和諧性。另外,因黔東南地區出產細長竹,故常編竹編墻,內外用膏灰抹面,堅固耐用。石材資源較為豐富,青石板使用較多,主要用于砌筑房屋堡坎,鋪裝路面。隨著社會的發展,一些建筑開始使用磚砌,或者將外立面改造為磚砌結構,屋頂則還是以小青瓦或杉樹皮為主,少數采用石棉瓦[4]。
材料的使用往往反映了當地的價值觀念及審美取向,石材、木頭、青瓦片組合而成的建筑往往表現出一種質樸的歲月感,黔東南吊腳樓將房屋的筑臺與崖壁或石質堡坎融為一體,與環境相協調,材料的天然性也體現在了建筑之上,反映出了苗民尊重自然、敬畏自然的民族文化。
2.3 建筑功能布局
在黔東南民居布局方面,正屋多為三或五間,中心一間為明間堂屋,左右為次間。一般火塘設置在堂屋的地面層,如今大多數苗居內的火塘則從中堂移至右邊次間,主要在家庭成員聚集時起到取暖的作用,伴隨居住舒適性需求的增加,火塘漸漸被移動式火盆取代。隨著社會的發展,民居功能更加多樣,在正屋基礎上向水平各方向增設附屬部分,主要添加廚房、牲畜圈養、交通等空間。黔東南苗族民居的多樣性就體現在對交通空間的組織上,如建筑主體四周常常采用披廈、偏棚等方式搭建樓梯間,三間住居多采用獨立外設樓梯連通二層,若超過三間則將面闊較小的某間設為室內樓梯間。
吊腳樓下部堡坎多用鵝卵石或毛石砌成,以三層居多。民居中的底層多做牛欄、豬圈、雞舍或廁所用,中間層分為堂屋、臥室、火塘間、過廊等空間[5],旁邊有木梯連接上下空間,是生活起居、接待外客的主要活動區域。堂屋空間位于首層入口處,是建筑的功能核心,也是居所的主體空間,主屋兩側為灶房儲藏空間以及臥室。上層堆放糧食和雜物,中間層旁邊還配搭一間偏棚作廚房。
干欄式民居在平面組織上更注重交通空間的處理與聯系,基于苗族信仰祭祀的精神需求,以及受漢族住居模式的影響,民居空間構成豐富多樣。
2.4 民居構造特征
黔東南苗族民居的穿斗式木構架營建技術歷史悠久,因其具有獨立性強、堅實穩固、形式多樣的特點,一直傳承至今。建筑的整體屋架形式較靈活,通常較為普遍的有四架三間或六架五間,屋架大體由地腳枋、穿枋、中柱、檐柱、中梁、斜梁等木質構件組成。
穿斗式民居的一大特點是柱子承接屋頂,梁作為穿枋連接立柱,不直接承重。為增強民居的穩固性以及保證室內空間通透寬敞,屋基立柱較多,柱子數量有三柱四瓜、五柱四瓜或七柱六瓜,立柱之間的間距約為1米。穿枋作為支撐瓜柱和挑檐的結構一般為四至五枋,建筑高度可以通過不同的穿枋數量來調整,樓層凈高一般為2.7米,屋頂高度略高于樓面,可作閣樓使用。建筑進深與其屋架的柱瓜數量有著密切關系。
與現代混凝土結構的模數不同,穿斗式建筑在建造過程中將步架作為基本的模數,木匠師傅可通過改變兩檁間的水平與垂直距離控制建筑尺度,現實建設中會根據實際需要調整。一般正屋面寬4.6米,廂房面寬4.3米。屋架完成后內部的建筑空間由不同柱位進行功能劃分,尺度上通常取13.2~14.4平方米為主居室面積,取6.6~7.2平方米作為次居室面積[6]。
2.5 建筑營造風俗文化
苗族人民普遍認為居室是生者與先祖共居的場所,他們相信萬物有靈,視居所環境中的生命萬物為精靈,與先祖一道以不同方式庇佑生者的現世生活。因此從村寨擇址到房屋落成的建造環節中,均有已成體系的“原始形態巫術”殘留,以及在某些居住環節中,苗人一直對某些房屋部位持續性地賦予巫術的象征意義,從而成為民族空間的一種表征。
民居建造過程首先是給中柱發墨,接著工匠制作其他柱子、枋、檁,動土儀式主要包括平屋基、挖基腳與砌屋基。風俗上也有講究,巫師擇選吉日,通神禱告以求土地神庇佑,與漢人、侗族、土家族的儀式較為接近。中柱就地取材,以楓木居多,高度取與“八”有關的數字以求吉利平安。立房前要將地腳枋架好,用木樁竹條固定,準備撐架等工具,工匠會殺只雞繞地腳枋滴一圈雞血,認為這樣可使房屋更牢固。在天未亮時就要祭祀建筑保護神“嘎西”或敬魯班先師,反映出黔東南苗族人民希望通過獻祭而尋求諸事平安的世俗信仰。在祭神誦讀儀式后就是立屋架了,黔東南地區立屋架一般在早上七八點,將扇架立穩,用穿枋、斗枋連接扇架并加固,木栓打好,保證柱腳都落在石質基礎上。最后的上梁儀式很重要,必須保證在一天之內完成,尋梁砍梁都有祭祀儀式,敬過魯班后方可上梁,用繩子將梁兩端捆住,吊起拉至中柱榫口,用酒肉祭過后就可以擺席慶祝新屋建成了。
3 結語
獨特的自然環境和民族歷史造就了苗族獨特的民居文化,聚落中的建筑除了居住生活功能外,還能夠體現出一個民族的文化特質,如社會制度、生產方式、民俗風情、組織形態等。作為地域民族建筑的代表,黔東南苗族建筑傳統營造技法獨特,文化特色鮮明,凝聚了本族長期積累下來的生活智慧與美學意識。隨著現代社會的經濟發展與演變,應更加關注對黔東南當地傳統民居風貌的保護,使苗族建筑文化在繼承的過程中不斷完善和發展。
參考文獻:
[1] 吳巍.黔東南苗族傳統建筑文化的當代設計表達研究[D].廣州:華南理工大學,2018.
[2] 龍玉杰.黔東南苗侗村寨傳統民居建筑之比較[J].安徽農業科學,2012,40(3):1602.
[3] 紀文.貴州黔東南苗族傳統聚落建筑藝術的審美探析[J].重慶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22):137-138.
[4] 蔣維波.貴州黔東南地區苗族村寨空間形態研究[D].北京:中央美術學院,2013.
[5] 周政旭,孫甜,錢云.貴州黔東南苗族聚落儀式與公共空間研究[J].貴州民族研究,2020,41(1):75-80.
[6] 劉賀瑋,楊逸舟.黔東南苗族傳統民居營建技藝與禮俗[J].民藝,2018(5):22-26.
作者簡介:唐光磊(1996—),男,河南濮陽人,碩士在讀,研究方向:城市規劃與設計。
3540501908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