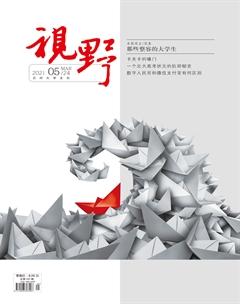在我閉起眼睛的世界里

呂三三
我從很小就跟著奶奶了。
聽姐姐說,從弟弟出生,那時候我剛滿一歲。大姐比二姐大一歲,二姐比我大兩歲,她們也是這樣一個個歸到了奶奶的懷里。媽媽忙里忙外,奶奶就負(fù)責(zé)照看我們?nèi)齻€。
再大一點,倆姐姐一起另住,只有我仍舊跟著奶奶,住在偏屋。同一間屋子同一張床。我在奶奶腳頭睡著,抱著她裹得并不成功略微變形的大腳,聽著如山雷一樣的呼嚕聲,被子上壓著她的大筒子棉褲。奶奶睡得早,我看完電視上床的時候,總要細(xì)細(xì)聽一會她此起彼伏的呼嚕聲:每一聲呼嚕聲由小到大,像一點點吹響起來的嗩吶,氣息漸上,隨著一聲短促有力、直擊耳膜的“哼”到達(dá)最高點,而后稍稍停頓,才終于長長地吐出那口氣。
每天早上,天剛蒙蒙亮,奶奶就起床了,到院子里趕雞罵狗,大嗓門攪拌著我們清晨的酣眠,加上雞鳴犬吠,想睡懶覺的我們總是無比懊惱。其實,她給雞撒點食,把羊牽到門口喂上草就會出門溜達(dá)了。沒多大一會兒的。然而每次都這樣驚天動地的,我們真是不勝其擾。
奶奶嗓門亮,最大的好處就是叫人起床。奶奶叫人起床很執(zhí)著,我們每個人都見識過。
從小學(xué)到初中一直跟著奶奶住一張床,每天早上都是她叫我。每次迷迷糊糊中聽她急急地喊我,我就驚慌不已。如果多賴一會兒,奶奶就開始用腳蹬我。也是急急地連環(huán)蹬。沒辦法躲,我只能馬上起來。初中后我常常十一二點才睡,有時候怎么上床的都記不清。盡管如此,我仍是同行的幾個孩子里最早起床的那個,起來后站在家門口,朝著她們家的方向挨個喊她們起來上學(xué)。冬天的時候門外一片烏黑,我常常要猶豫好一會兒才敢出去。
周末或者假期的時候,媽媽總想讓我們多睡一會兒。如果她要出去干活,會把飯菜留在鍋里,坐到封好口的煤火上。保證我們無論何時起床飯菜都是熱的。奶奶不然。如果她早飯后出門遛彎回來,發(fā)現(xiàn)鍋里有飯,就知道我們還在睡。于是,奶奶就走到院子里,對著窗戶,開始連聲地喊。叫不應(yīng)的話就走近窗戶,趴在窗前,用一只手罩在額上往里瞅,看到我們沒動靜就繼續(xù)喊,一聲比一聲急、一聲比一聲亮。好歹還隔著窗戶呢,困意頗濃的我們并不為之所動。奶奶也不罷休,拄著拐杖顫顫地走進(jìn)房間,一邊拍著我們一邊喊……特別執(zhí)著,特別氣人!
許多年后我才意識到,奶奶的觀念里,睡覺不能耽誤了吃飯,三餐要準(zhǔn)時吃才對,不然身體就壞了。
從我記事起,奶奶就那么老了吧。天天藥不離身;吃飯也麻煩,所有的東西都要煮得稀爛,無論是米湯還是面條。全家人的飯盛出來后要把奶奶的留在鍋里,再煮上一會兒。奶奶忌口,辣的、腥的、涼的、硬的從來不碰,蘋果梨子要煮,連西瓜都要放墻頭上正午的太陽曬一曬才吃。三十多歲就大口大口吐血的奶奶,因為嚴(yán)格忌口,雖然隔三差五的就要看醫(yī)生,依然活到了90歲。
奶奶膽子小,一點小事就帶哭腔,動不動就喧喧得讓人頭皮發(fā)麻。每當(dāng)家里有人晚歸,明明天一黑就上床的她,總喜歡躺在床上大聲喊我們的名字,喊不應(yīng)這個換那個,喊我們到跟前打聽消息……或者,干脆再重新穿上衣服,拄著拐棍,到堂屋里坐著等。有次,父親在臘月廿九出去買羊,下著雪的天,晚上八九點還沒回來,媽媽去尋。奶奶在家坐立難安。下著雪也一定要拄著拐杖,站在院子里等。臉苦皺著,隨時要哭出來的樣子,嘴里不停地念叨:“我嘞主啊,我嘞主啊……”。過一會兒頓一下拐杖,仿佛在宣泄自己深入骨髓的恐懼。
我高考前放假回家,家里只有奶奶弟弟我們?nèi)齻€人。晚上雷陣雨停電,我們仨點著蠟燭圍著方桌聊天。家里的貓躥上桌子,我拍了它一下,沒想到它轉(zhuǎn)身咬住了我的手指頭。左手食指被咬出了血。奶奶看到后頓時喧翻了起來。到現(xiàn)在我都記得電閃雷鳴的夜,奶奶的聲音尖利高亢,仿佛能把人的神經(jīng)刺破,依舊帶著哭腔,本來并不慌亂的我心里漸漸爬上了大難臨頭的恐懼……晚上沒地方打針,奶奶嚇得好像我已經(jīng)得了狂犬病,依舊是一連串“我嘞主哎”、“我嘞主哎”就再也說不出別的話,使勁地頓著拐杖,不知道是在自責(zé)她養(yǎng)了那只貓,還是怪我多事拍了它。
小時候,奶奶還經(jīng)常把自己的零食藏起來。糖啊花生啊果丹皮啊山楂糕啊,都是姑姑們來的時候給她買的。等她出了門,我們就去翻,無非是衣服堆下面,或者褥子下面、貼著墻壁的那一側(cè)。當(dāng)然是糖、果丹皮、山楂糕最容易遭殃。果丹皮是一長條,有塑料薄膜單獨包著,偷一條慢慢吃,可以吃上好一會兒。最可憐是山楂糕,一塊巴掌大的方方的山楂糕,總是被啃得半半拉拉的。偷吃的時候不敢讓其他人知道。但是后來發(fā)現(xiàn)我們每個人都偷吃了奶奶同一樣?xùn)|西。發(fā)現(xiàn)彼此的秘密后,我們開始互相推卸誰吃的多,又知道誰都脫不了干系,于是每個人都佯裝鎮(zhèn)定,不安地等著奶奶回來發(fā)落。其實,即使奶奶發(fā)現(xiàn)了也無非是吵吵兩句,根本不會怎樣。有一回,我真的很小心吃了一小口,但是山楂糕酸酸甜甜的,真的太好吃了,我過一會兒去吃一小口,過一會去吃一小口,后來只剩下一條窄窄的邊……這次沒有人與我一起承擔(dān),心里忐忑極了,估摸著奶奶快回來的時候我趕緊溜出家,到小伙伴家里去玩了。晚上回家奶奶竟然問都沒問這事。就這么混過去了。
要說奶奶最厲害的還是搟餃子皮,揉中饃(蒙古包似的饅頭)。奶奶雙手推著搟面杖把一個小小的面劑子打著旋兒搟,不一會兒一張中心厚邊緣薄的圓圓的餃子皮就出來了,就像一個花骨朵一點點在她手下盛開,均勻細(xì)致,光滑圓潤,神奇極了;做中饃,一手一個面劑子,同時推揉,然后放下一個,抓起一個兩手一團(tuán)溜,圓圓的的饃就成型了,立著放一邊,再去揉另一個,旋即而成。不一會兒案板上就擺滿了。
我記憶里的奶奶是永遠(yuǎn)都在過冬天的奶奶:帶著帽子,圍著圍巾,穿著厚厚的深色暗花棉衣、黑棉褲,褲腿用長長的寬寬的黑帶子綁住,生怕灌了風(fēng)進(jìn)去。我們幾個還小的時候,奶奶的手在冬天總是很暖和。她要么在鍋底門口燒火,不做事的話就一直把手揣在袖筒子里。每當(dāng)放學(xué)回家,聽到我們回家的動靜,她和媽媽就起身走出廚屋門口,接住我們凍得幾乎沒有知覺的手,緊緊捂在手心里,心疼地搓來搓去。后來我們越來越大,奶奶冬天要穿兩個棉襖,手卻越來越冷了。每次手冷的時候我總是習(xí)慣性去找奶奶暖手,卻發(fā)現(xiàn)她沒有“火力”了。我很失望,并且一直不明白,為什么她衣服越穿越多,手卻反倒越來越冷了。
這些年,想奶奶時我總是習(xí)慣性地閉起眼睛。在我閉起眼睛的世界里,奶奶一如往常:穿上了薄夾襖,厚棉襖,外面還要再披上一件。戴著暗紫色帽子,邊緣的白發(fā)兀自露著。臉上的皺紋深淺交錯,臉色也一年比一年焦黃,手上皮膚干干的,大大的手掌,嶙峋的骨節(jié)分明。我靠著她,或攙扶著 或面對她站著,用手指沿著她臉上縱橫的皺紋游走,不時碰到帽子外面的白發(fā);撫摸她松垂的眼皮,輕輕捏下她大大的鼻子,或者不停的在她干枯的手背上來回摩挲……這些都是最后幾年,我每次回去常做的事情。一邊跟奶奶有一句沒一句的聊著,一邊在她臉上畫來畫去,并且故意不叫奶奶,喊她:“老婆兒……”她聽到也不生氣,哈哈哈地大笑著罵我:七(音)孫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