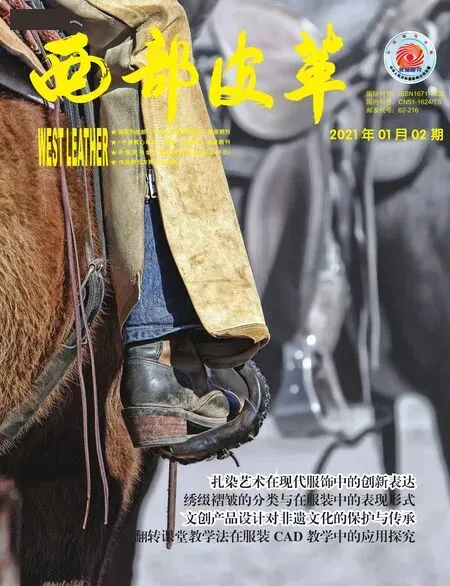頻閃效應在繪畫中的運用
——主要以立體畫派和未來畫派作品為例
羅菲
(南寧師范大學師園學院,廣西 南寧 530012)
1 關于頻閃效應
通常我們所指的頻閃是指人眼看到發光物后在視網膜留下的象,通過視覺神經傳入大腦視皮層形成的視覺形象并未立即消失而是短暫保留,這種視覺暫留現象造成連貫或閃爍。夜色中規律排列變換閃亮的led燈,實際上它們并未發生物理運動,卻讓人產生位移的感覺。根據格式塔心理學家的研究,這是人的視知覺引起的錯覺現象。德國心理學家韋太默在頻閃運動的視覺心理學研究中,處于黑暗并保持一定距離的兩個閃光點,按照一定的規律相繼閃動,在視網膜上先后收到刺激并傳輸到大腦視皮層產生某種生理短路,繼而使我們心理上認為是同一個光點的位移,從而我們“看到”這一運動。
人的視知覺具有一致性和連續性,能彌補時空上的鴻溝。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常常存在這種現象,許久未見的朋友突然出現在我們面前,我們一眼就能判斷他長胖了;在大城市中呆了一段時間回到小縣城,會覺得馬路上的車流變慢了。這是記憶痕跡和眼前知覺對象造成的頻閃效應。
在美術史中,頻閃效應也有廣泛的體現,例如史前壁畫上反復重疊的動物形象,例如佛教藝術中舞蹈的千手觀音,都能產生出與led燈規律變換閃亮的動感效果。最具代表性的是20世紀的立體畫派和未來畫派。在當時背景下應運而生的頻閃攝影,即攝影中借助連閃攝影技術電子燈光的連續閃動,拍攝出一系列動態連續的圖像,讓人得以看到一連串快速連貫動作的微妙變化。未來畫派直接把頻閃攝影挪用到繪畫當中,成為頻閃效應在繪畫中運用的典型代表。本文主要以立體畫派和未來畫派作品為例,通過具體案例分析頻閃效應在繪畫中的形式特征和藝術效果。
2 繪畫中頻閃效應的表現特點
2.1 以圖式為特征的頻閃效應
根據格式塔心理學魯道夫阿恩海姆著作《藝術與視知覺》中闡述,“在整個視域中,各個視覺對象的相貌和功能基本一致,但他們的某些知覺特征——位置、大小、或形狀——又不一定要相同”,即符合“由形象的相似性和變化的連續性所產生出來的,是一個活動起來的知覺整體,這一知覺整體的活動性,又因各個片段的互相重疊而得到大大加強”,這種視覺圖式就會產生頻閃效應。立體畫派的作品,不再是依照看到的自然作畫,他們的畫面普遍呈現幾何化,傳統繪畫所追求的明暗、光線、空氣、氛圍等,全部讓位于直線、曲線構成的輪廓、塊面堆積交錯形成的趣味。幾何化后的物象,形成了許多相似性的形狀,這些相似的形狀,就體現著頻閃的圖式特征。
早期的立體畫派被稱為“解析型”的立體主義繪畫,呈現出來的畫面效果往往讓人感覺仿佛在嘗試解讀照相機鏡頭或分析圖像被人眼捕捉以及圖像在人腦被處理成視覺印象的過程。布萊克的《手持吉他的人》是分析立體主義階段的典型代表。畫面是一個正在彈奏樂器的人,整幅畫面似乎被割裂成許多塊狀透明平面,二維和三維互相交織在一起,如畫面上部,用一連串交疊分割的平面營造出一定的體量感,呈現出復雜的重影式樣,讓人產生混亂不定的感覺,但是這種不穩定卻與畫家要表現彈奏的動感主旨是相吻合的,看這幅畫我們仿佛能感受到這個吉他手正在興致昂揚地彈奏樂器,身體和琴都隨著歡快的旋律搖擺晃動起來。在格里斯的《畢加索肖像》中,畫面人物形象相對清晰,雖然畫家并未著意表現人物的運動,但由于幾何形化后重影的效果,使人物形象給人不安分的感覺。類似的作品還有雅克·維雍的《前行中的士兵》、梅贊熱的《浴者》。
運用重影的圖式體現運動,在未來畫派作品中得到進一步發展。受立體主義的藝術形式所影響,未來主義繪畫也采用分解的平面,同一圖像重復交疊來描繪時間和空間的變化移動,他們不僅追求“動感有力”,甚至要求直接表現運動本身,頻閃效應起到了事半功倍的作用。擅長運用頻閃效應來營造畫面的有巴拉、波喬尼、卡拉、賽韋里、杜尚。
巴拉的《一只拴著鏈子的狗》,畫面中心是一只拴著鏈子的小狗,看得出來這只活潑的小狗正在拽著主人快步前進,因為狗的四肢、尾巴、鏈子、女主人的鞋子和裙擺都出現了重影。因為人眼看到的形象會滯留在視網膜上,運動中的物體就是多重的變形的,因此一只快速奔跑的狗不再是四條腿,而是數不清的腿。在靜止的畫面中,通過重復形狀營造重影效果從而獲得這種凝固運動本身的感覺,是頻閃效應在視知覺中起到的作用。巴拉的另一幅作品《陽臺上奔跑的女孩》,是巴拉對速度客觀精到的解析,女孩跑過的所有痕跡都沒有散去,運動被分解凝固在畫面里。杜尚的《下樓梯的女人2號》描繪的是一個女人在連續的時間里走下樓梯的機械動態。
觀看靜態的畫面感受到運動,這本身是一種視錯覺,頻閃效應本質就是一種視錯現象,所以在以上談到的畫作中,靜態畫面與運動本身悖論這一充滿意味的主題,用同一視覺形象頻閃的圖式來表現是最合適不過的。在這些作品中,營造出頻閃效應的圖式是相似的輪廓、塊面、形狀、等有秩序地重復疊加組合,甚至直接是頻閃攝影的圖解式樣。
2.2 以思維方式為特征的頻閃效應
如上所述,在表現運動的主題繪畫中頻閃效應直接依靠相同或相似圖式來營造,這些相同的圖式,造成視覺后象從而起到暗示動態持續的作用,這是一種純粹依賴圖式本身產生的頻閃效應。還有一種情況是,在我們觀看作品時在思維上發生的頻閃效應,輔助我們去解讀畫面。相對于傳統繪畫這也是一種繪畫理念的轉變,表現在畫面的結果是畫家直接將思維的跳躍頻閃展現出來,如果說前者是在同一視點空間下,以相同圖式暗示動態的連續為特征,那后者則是以視點轉移、空間轉移為特征,將不同時空置于同一畫面產生頻閃效應這樣一種畫面表達方式。
當畫家在同一畫面上同時呈現了不同的視點圖像,這些圖像相繼刺激視網膜然后投射到大腦視皮層發生暫留現象,最終使得這些跳躍的圖像串連成一個完整的線索,從而觀者讀懂這幅畫。埃及繪畫的正面律,就是一種視點轉移的效果。這與中國畫的散點透視有異曲同工之妙,中國畫因散點透視,畫家不受視域局限,作畫表達更自由。視點轉移產生頻閃效應,還有一個別具一格的案例,即以契理科、埃舍爾、馬格利特為代表的超現實主義繪畫。與正面律、立體主義和中國散點透視法不同,超現實主義尤其是契理科的形而上繪畫,他們的視點轉移是建立在傳統的空間表現上,是在正確地運用焦點透視基礎上,并置了多個焦點透視制造空間的頻閃,利用多個空間矛盾來表現主題。恰恰是現實主義焦點透視的“真實穩定”,與畫面中多空間并置頻閃的沖擊,將矛盾最大化,從而營造畫面的神秘、荒誕氛圍,以表達藝術家的深邃哲思。
在立體主義最賦盛名的畫家畢加索的作品中,多次運用了視點轉移產生頻閃效應去表現主題。例如《鏡子前面的少女》,畫面中同時出現少女側面和正面兩個形象。我們可以明顯區分這兩個形象,先是少女柔美的側面輪廓,當把側面輪廓與左半部分結合起來看時,又成為一張少女的正面臉龐。這兩個角度的形象相互混淆,在觀看這幅畫時,需要觀者在腦海中切換不同的角度,兩個視點形象在腦海發生頻閃,最終似乎看到少女照鏡子左右擺動臉龐這一充滿意趣的過程。畢加索還有很多類似的肖像畫,選取對象的不同的角度攫取各部分的典型成分,最終讓整體形象特征得到完整的呈現,這是視點轉移描繪的優越性,也是頻閃效應在繪畫中起到的特殊效果。這種繪畫理念,顯然不是完全建立在視覺經驗和感性認識的基礎上的,還要依靠理性觀念和思維重構,在解讀這類作品時同樣需要我們思維迅速轉換,即畫家運用頻閃的理念去表現作品,我們觀看的同時也發生了頻閃效應。
3 頻閃效應對繪畫表達的啟發
從以上分析來看,頻閃的手法不僅是一種可操作性強的繪畫技巧,同時它本身所具有的開放性思維,也能讓我們得到啟發。在某些特定的題材,如運動、時間的行進,營造頻閃效應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只要將描繪的物象進行重復排列制造模糊重影的效果,就可以產生運動感;在畫面的構成上,運用相同或相似元素布局,就可以形成節奏的動感,視覺的一致性和連貫性也有利于畫面的整合。這些相似的元素不單指具體形象一只狗局部的腿,還包括繪畫基本要素點、線、面、形、色彩、筆觸等形式語言,例如梵高整幅畫統一的筆觸,例如用同類色去平衡畫面取得和諧。僅僅依靠點、線、面去營造畫面的頻閃效應是可行的,從歐普光效繪畫的作品中就可以得到證明。在歐普光效繪畫中,幾乎所有的作品都是運用直線、曲線、及簡單幾何圖形的重復,漸變構成的,在觀看這類作品時,畫面上大量相同元素的頻閃會對眼睛造成過度的信息負荷,再加上視覺的連貫性和觀者的預測傾向帶來的干擾,就使得作品出現了閃爍的運動感或眼花繚亂的感覺,歐普光效繪畫是把頻閃效應運用到極致的繪畫。
除了追求動感、表現運動和時空的主題非常合適運用頻閃效應來體現,一些敘事性繪畫主題也可以借鑒這種方法。連環畫的形式實際上就是采用一種頻閃的思維,多個畫面有次序地敘述故事。最初電影的發明,就是利用多幅靜態畫面在眼前快速而過產生頻閃效應的原理。克里姆特的作品《女人的三個階段》,畫家用強烈的裝飾風格展現一個天真可愛的幼兒,一個成熟美麗的成年女子一個衰敗憔悴的老年女人三個狀態。一個女人人生三個階段的身形在觀者腦海里對比閃現,生與死的更古主題以及身為女性的美麗與悲哀,讓人感慨和悲嘆。高更作品《我們從哪里來我們是誰我們到哪里去》也是不同時空的線索并置來表現主題。頻閃手法不受傳統繪畫法則束縛的自由形式,可根據畫家的需要將不同時空的事物并置同一畫面,對作品敘事性的表達有著極其便利之處甚至可以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這是一種蒙太奇式的思維,當破壞視覺的一致性,畫面是令人匪夷所思的場景時,就是超現實主義的荒誕;當強化視覺的一致性,畫面是具體對象碎片化的重構拼接時,就是立體主義的立體呈現。
當下,蒙太奇式的頻閃手法運用形式更是多樣的。我們還可以把它作為一種創作的形式或者說最終呈現給觀者的形式,就像連環畫一樣,需要看完整體才能獲知完整的故事。荷蘭畫家菲利普·阿克曼,他從學畫開始就一直堅持畫自畫像而且只畫自畫像,他賦予自己這幾千幅自畫像更深一層的含義,聲稱自己畫的是全人類,當所有肖像一齊呈現出來,那時才達到他的意圖。杜馬斯的作品《對面的模樣》也是這樣的形式,多幅頭像組合成一幅畫。徐唯新的《歷史的眾生相》當把同一個時代的人物肖像并置閃現,就能喚起觀眾對這個時代的記憶共鳴。并置閃現的人物是同一張臉的復制時,就會產生不一樣的效果,如安迪·沃霍爾的夢露頭像復制,然而卻很符合畫家所要表達的對這個消費社會的價值觀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