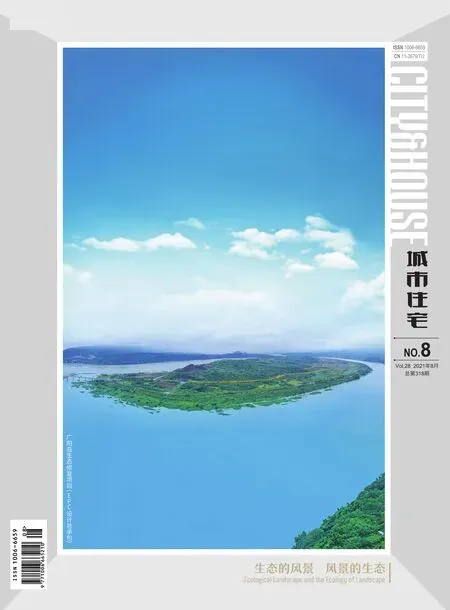理性功能主義的演化及其對城市規劃的影響
張 虎
(北京中建恒基工程設計有限公司蘭州分公司,甘肅 蘭州 730050)
0 引言
社會發展是一個不斷延續、變化的過程,通過不斷探索、梳理、思考,總能從歷史軌跡中得到啟示、警示、感受和感悟。人類需要不斷地自我審視,需要更清醒地認識到自身的處境和如何去選擇理性。現在想來,任何一個今日的城市都是歷史城市的延續,不了解城市的過去,就無法認識城市的現在,當然也就不可能有效規劃城市的未來。說到底,不充分認識規劃思想在規劃史中的地位,就不能理清規劃何去何從。近現代以來,人們對城市的探索從未停止,探索城市規劃思想也從未止步。理性功能主義特征最早出現在建筑中,后來逐漸應用在城市規劃中。在規劃語境下,歷史中理性功能主義的探討從思考到實踐、從思想到理論的過程伴隨著城市規劃學科的不斷深入和完善,并對我們產生重大影響。
1 理性功能主義的歷史演繹
1.1 早期功能主義的探索
在早期探索中,雖然并未有完全意義的功能分區,但這種思想有一定的體現。在西方米麗都城城市規劃中,十字路的空間布局和公共建筑耦合成為城市的中心,而居住和宮殿等具有使用功能的區段散布在其周圍。而在我國早期的城市規劃中,《管子》的“匠人營國……市朝一夫”思想和禮制思想的交流與融合,“前朝后寢、左祖右社”等布局一定程度上滿足了管理階層對城市管理的功能要求。可以說,東西方管理階層都在追求對底層階層的管理,而這種思想正是對城市功能布局的追捧,以實現管理階層的夙愿。至近現代,最典型的是由塞納區行政長官歐斯曼主持的巴黎改造。巴黎改造在滿足現代城市設計要求的前提下,設計中也有政治的目的,包括拓寬大道,疏導城市交通,消滅便于革命者進行街壘戰斗的狹窄街巷,把便于炮隊和馬隊通行的大道連通起來,有利于統治者調動騎兵炮兵,發揮火器作用,以鎮壓起義者。這種功能主導的城市規劃,一定意義上來講是統治者的城市,而非人民的城市。
1.2 對功能主義的過度追捧
真正的城市規劃開始于工業革命之后。工業革命以后,由于技術革新給城市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變化,也給人類的生活帶來史無前例的便捷,此時的城市在經濟社會中的地位尤為突出。正如20世紀50年代末唐納德·伯格在“推-拉理論”中將“推”理解為“是一種促使人口遷移的力量,即有利于人口遷移的正面積極因素”。這種因素來自城市里面更多的就業機會、更加完善的基礎服務設施、更高效和發達的通信和交通、高質量的居住環境、更加客觀的經濟收入等。因此,可以認為工業化為城市發展創造了條件,也為人口集聚創造了條件,但工業化同時也給城市帶來了負面影響,給人類帶來了諸多麻煩,人類正在被因工業化而引發的社會、經濟、環境衛生等問題困擾。最具代表性的是以柯布西耶主導的思想和城市規劃。面對前人多次的規劃實踐,柯布西耶認為要實現城市因集聚而帶來的多種城市問題,需要從功能入手,即城市的基本功能為居住、游憩、交通和工作。因此城市的布局也應該從屬這種功能要求。在昌迪加爾規劃設計中,這種從功能角度出發的城市設計是精英主義者的作品,象征的設計元素充斥其中,也可以理解為是一件藝術品。而在巴西利亞的城市設計中將這種思想延展到城市形態中去表達一種對美好生活的愿景。這種過度的功能主義追捧必然是脫離經濟、社會、交往的內在發展規律。
正是由于缺乏對城市發展、社會發展的全面認識,才會引起精英主義對功能主義的過度追捧。此外,面對城市的進一步集聚,因為它固有的局限性而對城市空間發展的考慮較少,短暫的輝煌之后便是思考和檢討。但仔細甄別也不難發現,正是由于人們認識世界的局限性,才會導致對功能主義的過度追捧。
1.3 理性功能主義的最后選擇
這種機械式的規劃思想完全追尋城市規劃的秩序和空間,在一定程度上放大規劃師、管理機構的設計意向,卻脫離了人的參與,擺脫了人的能動性。這種認識伴隨著社會發展、科技進步,是社會整體環境氛圍中的產物和人們的普遍共識。本質上來講,功能主義是現代工業社會追求效率和成本的“嫁衣”。可見,功能主義的發展是結合了歷史維度下的社會、科技、經濟和文化的共同作用,逐漸趨向于理性功能主義。這種理性功能主義的選擇實際上是認識到了城市本就不是簡單的機械組合,而是多種功能之間相互連接、相互依存的。與此同時,這種選擇也見證了底層人民日趨成為社會主體,進一步放大和激發了人的主動性和能動性。一方面,這種理性功能主義的選擇依賴于人們對多元化社會的認可;另一方面,更是人們對世界的一種唯理態度。由此可以進一步得出理性功能主義是遵循普遍的科學客觀規律,尊重理性的合乎邏輯的做法,并將這種認識作用于規劃設計和規劃實踐中。也可以認為城市在促進物質、文化繁榮和社會進步方面發揮的作用是不可磨滅的。
2 理性功能主義對城市規劃的影響
2.1 城市規劃理論
人們逐漸認識到城市并不是某種功能或是多種功能的簡單組合,而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城市內部的各個功能區之間相互連接、相互作用、相互成就。這實際上揭示了城市規劃的實質就是進行系統的分析和系統的控制。這個階段普遍被認為是理性主義的最高峰。城市系統規劃思想視為一個多種流動、相互關聯、由經濟和社會活動所組成的大系統,運用系統方法研究各要素的現狀、發展變化與構成關系,相對于過去單純的物質形態規劃思想,無疑是一個極大的提高。這也進一步表明了《馬丘比丘憲章》中眾多先進的規劃思想的出處。當然,也看到了后期城市規劃思想從社會學、經濟學和地理學等多學科的角度進一步思考城市、認識城市。最具代表性的是區域規劃思想和人文主義的崛起,從理性的角度延展到各類城市規劃理論中,進一步引導著人們追尋對城市的理性認識。
2.2 城市規劃管理
規劃實踐和規劃理論是高度的統一體,我們探索的所有規劃理論都將應用于規劃實踐中,兩者之間緊密相連。一定程度上來講,規劃理論是人們在探索城市發展規律過程中的理性認識,這種認識不僅僅只是理論層面,也是指導和引領規劃實踐的“金鑰匙”。毋庸置疑,在規劃實踐中的城市規劃管理是落實和發展的基本工具和媒介。比如城市規模管控,霍華德在田園城市理論中提出在城市周圍要有永久性的農田,不能另作他用,當城市規模達到規劃人口時,再修建一座田園城市。但是,人們依然發現城市一直外延式發展,或通過綠帶、綠楔予以限制,但終究還是不能有效限制城市規模。可見,人們對于城市的認識是在理論和管理(實踐)之間相互不斷認識,所以必須選擇理性地看待城市問題。此外,在具體的城市管理中我們也認識到一些城市法規、規章也都遵循一種理性態度,并不是一種“一刀切”的思維。誠然,我們也看到在未來城市規劃中更加傾向于“彈性”“留白”,這也是長期實踐中得來的一種規劃理性。
3 啟示
至此,我們探討了理性功能主義在歷史維度下的演繹,并進一步指出理性功能主義的歷史演繹對規劃理論和規劃管理兩方面的重要作用。當然,這些重要的規劃思想一定程度上還是圍繞西方的規劃思想史進行探討。相較而言,我國在這方面的探討還處于一定的空白。實際上,采用理性功能主義的核心內容,有利于我們進一步探討這些思想對當下中國社會和城市問題的啟發。眾所周知,改革開放以后,我國城市化在經濟增長的驅動之下進一步提高,人民生活質量顯著提升。但是,在粗放式的發展下依然面對諸多城市問題。特別是近幾年來人們愈發普遍認為,在追逐城市化和經濟效率下城市化質量面臨嚴峻挑戰。有專家認為,在新時代更應該為中國城市化松一松油門,更應該從生態、可持續的理念去認識城市化。從頂層設計角度而言,不能用統一的視角單一判定區域城市化,主要是因為區域內的城市化是區域結構、經濟結構進一步交叉和融合的階段,也是區域內城鎮間的交往更趨于一種固化的方式交流與協作。可以說,我國的城市化發展受多種影響。因此,我國在城市化發展的道路上更應該從理性的角度去辨識和梳理。
4 結語
本文按照歷史維度的邏輯梳理了功能主義演化的階段即早期功能主義的探索,對功能主義的過度追捧和理性功能主義的最后選擇3個階段。理性功能主義的演化是我們認識社會、經濟、環境等要素的完整階段,是城市發展過程的一個縮影。而這種認識也是促進城市規劃理論方法和城市管理思想不斷成熟的過程,這種認識也起著一定的規劃作用。這有益于進一步思考我們的城市將何去何從。同時,探討理性功能主義對城市規劃的影響,對我國城市化道路選擇進行梳理,認為我國城市化發展受到多種影響,更應從理性的角度出發,積極辨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