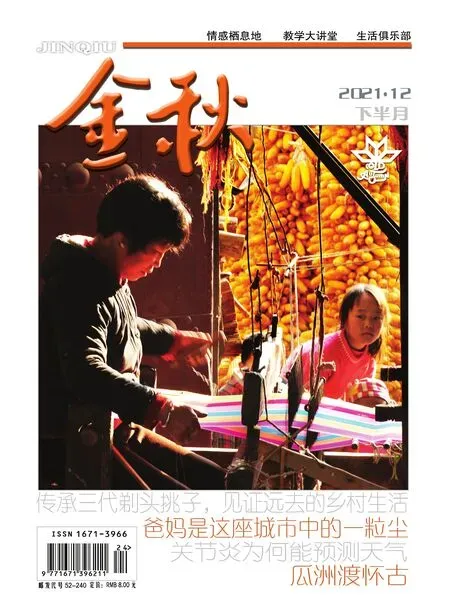一場等不及的生死之約
◎文/林友僑

2006年8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家里電話響了。我拿起電話,是一個女人的聲音,自稱是我的同學傅木龍的妻子,說木龍有事找我。我一聽覺得奇怪,也預感不妙,接著傳來木龍低沉的聲音。他告訴我,他得了肝癌,已是晚期,時日不多了。
這簡直是晴天霹靂!我連連問:“怎么回事,怎么一直沒聽你說起,有沒有去醫院治療……”木龍有氣無力地說:“治不好的,怕同學們擔心,就都沒說了。”木龍說,他走了,最放心不下的是兩個女兒,大的十二歲,小的才八歲。他說,友僑你在報社當記者,認識的人多,社會接觸面廣,將來孩子讀書、就業有什么困難和需要,希望你能看顧。我含淚答應。這是臨終托孤啊,我能說什么呢?
木龍接著問我,能不能抽空回家鄉見一面,他很想見見我。我說好,今天是星期五,我明天有一個重要采訪,已安排好的不能不去,我們就約定下周六,也就是八天后在紅湖中學見面,如何?木龍欣喜地說,好,我在母校等你。
然而,就在我和木龍通電話兩天后的晚上,木龍駕鶴西去。家中電話再次響起時,一個男子的聲音,自稱是木龍的哥哥含悲說:“木龍走了。走前,家人要接他回老家祖屋住,也好葉落歸根,魂歸故里,但木龍一直不肯,堅持要在學校等你回來,說約好在學校見面的,說回了村里怕你回來找不到他。最后到了彌留狀態,家人哄他說,友僑來過咱村,能找到的,才勉強同意回村去住。回村當晚就走了,撐不下去了……”
聽到這里,我已忍悲失聲,淚流如注!木龍,我的老同學,我們不是已經約好了嗎?就差這么幾天,你怎么就撐不下去了呢?你才三十九歲,正值壯年啊!
坐在回家鄉奔喪的客車上,八百里路路漫漫,五個小時時恍惚,我的心中、眼中、腦海里,全是木龍的音容笑貌和與他相識、相知的點點滴滴。
我初中一年級第一學期是在西陂小學臨時寄讀的,第二學期轉學到了紅湖農場中學,成了初一(1)班的插班生。班主任叫曾婉珠,是個教育有方的女老師,教數學。不知出于什么考慮,她安排我與班中成績最好的兩個同學同桌。那時學校的課桌由兩桌相連,同桌的同學是四人,而不是兩人。我的左右同桌,一個是班長魏少文,一個是學習委員傅木龍。少文不但學習成績好,還打得一手好乒乓球。對于一個沒見過乒乓球的農村學生來說,少文的球技簡直神乎其神,讓我佩服得很。木龍則比較深沉,不愛說話,銳利的眼睛,虎虎的腦袋,給人一種威武感,讓人一時難以親近。他學習很用功,有一股不服輸的狠勁,尤其作文寫得好,這恰好是我的弱項。
我們就這樣慢慢地熟悉,漸漸地了解,放下彼此的戒備,交流開始多了起來。我因大兄在農場公路邊開了一間店鋪,放學的時間都用來幫大兄看鋪、做買賣,還要自己做飯,常常上學遲到,完不成作業,就常找他們問這問那。我數學有點天分,讀書時幾乎沒有我解不了的數學題,他們遇到難題,也常與我商量。有一次,木龍開玩笑說,你快成我們班的小陳景潤了。
一年之后,我就申請轉學回到了所在鎮的中學繼續讀初二的第二學期。此舉本意是想離開成為“生意仔”的環境,專心讀書,補回一年來落下的學業。沒想到幾個月后,星期天放學回家,我為了改善伙食,冒雨下河捕蝦,受涼得了一場急病,不得不休學在家調理。從此離開校園,早早結束了求學生涯。
再次與木龍聯系,是在我經歷了打工、流浪,離家出走想闖少林寺學武,碰得頭破血流,差點客死他鄉之后。聯想自己家境如此貧寒,拜師學武是不成了,一支筆、一張白紙總還買得起,于是打定主意,決心以文為生。其時我才十七歲,正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年齡,文學創作的道路有多艱難,根本不知道,更沒去考慮。
木龍聽了我的決定,二話不說,送給我一本厚厚的《寫作基礎知識》。他這時已考上了縣師范學校,而且是學校文學社社長,對寫作之難,該是有體會的吧。但他沒給我潑冷水,而是以實際行動予我無聲的鼓勵。他所贈的這本書,是我系統讀過的第一本寫作知識書。可以說,是這本書指引了我的文學之路。
后來,帶著不滅的文學夢,我應征入伍遠赴海南,在椰風陣陣、海浪聲聲中,目睹了海南立省建特區,十萬人才過海“沖浪”的盛況。在陌生的環境和滾滾熱浪中,我的閱歷多了,視野開闊了,業余寫作歷經六七年的彷徨,終于有所突破,開始在《海南日報》《海口晚報》《海南農墾報》等報刊發表作品。
每次發稿后,我都會第一時間寄樣報給木龍,他也會第一時間回信,表示祝賀,并暢談自己的讀后感受。他曾這樣坦率地對我說:“你是我們同學中文學天分很普通的一個,也是同學中在文學創作上走得最遠的一個,這是你勤奮和堅持的結果。很多有天分的人因為沒有長期堅持,所以半途而廢,嘗不到成功的果實。”我認同他的分析,雖然我并沒走多遠,更談不上成功。
到了2004年,也就是木龍走的前兩年,我將陸續發表的散文隨筆結集出版。木龍得知后很高興,叫我多帶幾本回去送給他,他要推薦給他的學生讀,他要留給他的女兒看,他要在縣教育系統的語文同行中介紹我。他是那樣有想法,那樣的熱心。他熱愛學生,熱愛漢語教育,熱情地推介我這個老同學,真誠地以同學的進步為傲。就這么年輕有為的一個人,老天爺卻把他帶走了,毫無商量的余地,是天妒英才呢,還是天上正缺他這樣古道熱腸的人?蒼天啊,你能告訴我嗎?
葬禮上,哀樂嗚咽,淚如雨灑,說不盡的悲傷。而我,在傷感之余,更有一種徹骨的心痛。我心痛木龍,責怪自己,為什么沒有早點回來看望木龍,而要一個病入膏肓的人苦苦等待,望穿秋水,終未得見,抱憾而去,把一場同學約會,變成了生死之約,從此陰陽相隔,生死兩茫茫。
木龍沒等到約定時間就走了,是木龍失約,“有負”于我;我沒即行赴約,釀成了終生遺憾和永遠的痛,是我之過。這個沉痛的教訓讓我明白:人這一生,有些事,不能等,有些約,等不了也等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