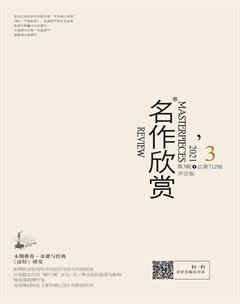貧困鑄就的犬儒主義者
夏肇蔓 王芳
摘 要:《巴黎圣母院》中的甘果瓦是一個貧困鑄就的犬儒主義者,他的身上影射出了巴黎底層民眾的生存困境,不幸流浪謀生的生活經歷,粉碎了他的詩化理想,導致了極端的現實主義,集中表現為實用至上的價值觀,同時懷疑一切的虛無理念,消解了價值與崇高,使甘果瓦成為不折不扣的利己主義者。
關鍵詞:巴黎圣母院 甘果瓦 犬儒主義 實用主義 利己主義
犬儒主義最初緣起于古希臘時期,早期的基本思想是堅持內在的德性與價值,鄙視外在的世俗與功利。后期,其思想內涵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犬儒一詞成了它的反面。《巴黎圣母院》是雨果的一部著名長篇小說,其中的比埃爾·甘果瓦是一個典型的聯結人物,與莎士比亞《亨利四世》中的福斯塔夫有著異曲同工之妙。通過他的活動,雨果展現了上至皇室、教會,下至酒館、圣跡區等廣闊的社會場景。而甘果瓦的犬儒哲學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種世界觀,他看似理想主義者,實則沒有恒定的追求與信仰,看似愛好幻想,實則極端現實,虛無主義的理念,更是顛覆了道德與義理,但是歷來對《巴黎圣母院》的研究高度集中于男女主人公,對甘果瓦的分析常常一筆帶過,很不深入,故此,本文擬對甘果瓦的形象做一個初步的分析。
一、 窮酸卑微的流浪文人
甘果瓦是《巴黎圣母院》主要人物中出場最早的,“這家伙長得高大,瘦削,面色蒼白”,“身穿破舊的黑嗶嘰衣服”,一副窮酸瘦弱的形象。他是一個孤兒,居無定所,“二十年前,在巴黎圍城期間,我父親被勃艮第人絞死,我母親被庇卡底人剖腹殺死了。因此我六歲就成了孤兒……” a幼小的甘果瓦成了親情隔絕的孤立體,也喪失了寄身圈和物質來源,只能靠著接濟強以度日。后來因緣際會,得到副主教克洛德·弗羅洛的指點,學了點拉丁文,在小說開篇,他正打算用一個圣跡劇賀婚,以求得到一點賞賜。圣跡劇演出失敗后,他已經窮得一文不名,不敢回到租住的寓所,只能流浪街頭:“哲學正是他獨一無二的藏身之處,反正他不知道往哪兒投宿……他不敢回到他在干草港對面水上樓街所住的那個客棧里去了。”(巴 ,50)
甘果瓦身上有著流浪者的精神共相,他們都被剝奪、被遺棄以及被蔑視。以圣跡劇場景為例,當時的甘果瓦身份卑微,幾乎不被人認可與賞識,當吉斯蓋特問甘果瓦圣跡劇是否好看時,他毫不猶豫地肯定了它的價值與魅力,自豪地表明了自己劇作者的身份,但這個作者身份并沒有贏得看熱鬧的姑娘吉斯蓋特的尊重,她對同伴說“他并不是什么學者,他是個普通人,不用稱大師,就稱先生得了”(巴,19)。在看熱鬧的群眾等得不耐煩哄鬧的時候,甘果瓦以他一貫的審時度勢的機敏,自作主張提前開演圣跡劇,暫時平息了風暴,但不幸的是,群眾的注意力很快就被陸續到場的紅衣主教等達官貴人吸引過去了,他的努力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和期待中的效果。圣跡劇失敗后,甘果瓦流浪街頭,連露宿街頭的心愿也無法實現,后又因被愛斯梅拉爾達吸引而誤入黑話王國,差點被乞丐國王克洛潘絞死;在倍爾那丹街上,他又差點淪為替罪羊,幾近于死;乞丐王國為救愛斯梅拉爾達發動暴動之際,甘果瓦被錯逮,又差點被法國國王路易十一絞死。流浪途中,危機迭起,他吃盡了苦頭。所有這一切,他都以一種近乎麻木的卑微與順應姿態,讓自己一次次化險為夷。
在故事結束后仍然活著的甘果瓦,又嘗試過多種職業,他當過兵,做過修士,也曾在失望之下,跟隨過木匠當學徒。孤兒、職業的不穩定性、瘦弱的體貌特征,以及窮酸拮據的經濟狀況,為讀者勾畫出了甘果瓦的大致形象。他的求職欲與職業觀,彰顯了他對流浪身份的認同與適應,頻繁的變更與求索則影射著他獨有的流浪氣質。
甘果瓦因貧困而四處流浪,既沒有生活上的安定,精神家園也無從尋覓。在求生欲的驅動下,流浪成了他的基本生存模式。甘果瓦的地理流浪是他精神流亡的載體,漫長的流浪生涯,使甘果瓦缺少了堅定的信念和目標,他變得實用化和世俗化,失去了神圣與崇高,只剩下了動物性的生存本能。甘果瓦這個不乏美好幻想卻以實用指導人生實踐的人物,是讓人同情的,在15世紀路易十一統治下的巴黎,社會生產力極端落后,資本主義尚在萌芽狀態,宗教勢力雖趨于式微卻仍暴露出邪惡與黑暗的面目,封建制度的殘酷性也相當程度上扼殺了人的天性。在這種壓抑扭曲的社會空間中,甘果瓦般的生存哲學,對于底層人民而言,恐怕是無奈而唯一的生存選擇,他也因此成為中世紀流浪文人的代表。
二、 不折不扣的實用主義者
作為一個現代犬儒主義者,甘果瓦忙于生存,外在的世俗的利益,吞噬了內在的美德與良善,這種犬儒主義帶有實用至上的“工具性”。關于實用主義,美國哲學家威廉·詹姆斯認為“有用即是真理”。同時,實用主義把理論行動主義化和功利主義化:強調生活、行動和效果,經驗和實在歸結為行動的效果,知識歸結為行動的工具。在這方面,甘果瓦也是實用主義者的典型,在《巴黎圣母院》中,他的價值判斷與選擇均以實用主義價值論為根本依據。
從甘果瓦的職業選擇與藝術態度看,他說:“十六歲上我想找個職業,我不斷嘗試去做各種事情……我發現自己缺少干任何事情的才干,看到自己做什么都不行,我就決定去當一個詩人,一個韻文作者……”(巴,95)可見對于甘果瓦來說,詩人和韻文作者作為職業是用來獲取生活來源的。這是一種對自我的理性認知與實用性的價值判斷,而非源于精神需要的滿足或是藝術審美性的追求。小說中還有不少細節也可以佐證他功利化的人生態度,如他為總督大人寫賀婚詩是為了換取六個月的房租,圣跡劇的演出也是趨利的,他甚至認為最好的亞歷山大體詩歌,對于嘴巴還不如一片布西奶酪值錢等。
在圣跡區中,愛斯梅拉爾達出于善心救下了甘果瓦,這使他誤以為自己是一個勝利的愛神。而對愛情的希望首次受挫時,他并沒有陷入絕望的境地,反而將失意的情感變成了食欲的滿足。在坦露和彰顯了自己的身世經歷和才華學識后,再次遭拒,他也沒有表現出絲毫的悲傷,反因能有一張床鋪得以棲身而感到欣慰。名義夫妻所帶來的生存利益足以彌補他愛情上的創傷。這種典型的實用觀,是甘果瓦一貫遵循的人生哲學。
從他對責任勇氣與生存利益的取舍看,甘果瓦在看見波希米亞姑娘遭遇劫持時,他有責任上前阻攔并營救,可當他看見伽西莫多那張可憎的臉后,畏而不敢上前。當得知碎罐締婚的伴侶藏在圣母院時,他為了擺脫替罪羊的命運而為副主教獻計,根本不打算報答愛斯梅拉達的救命之恩,騙出愛斯梅拉爾達后,更是登岸即溜走,把愛斯梅拉爾達留給不懷好意的副主教,一系列無視道德的行為也是出于對生存利益的權衡與考量。此后攻打圣母院時的半途逃離以及被捕后展現出的虛與委蛇,均反映出他對生存的強烈渴望與不擇手段。責任勇氣對于甘果瓦而言是虛無縹緲的,不具有客觀實在性與實踐價值,生存利益的第一性,是他融于血脈的價值認同。
實用主義滲透在甘果瓦的職業、愛情、道德選擇等方面,是一種獨立的思想意識。通過甘果瓦的活動,小說的主要人物被串聯在了一起,并且,甘果瓦的實用主義與愛斯梅拉爾達的神性、伽西莫多的奴性以及克洛德的復雜性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使小說的情節更富于戲劇性,表現的社會思想更加多元立體。
三、折中調和的利己主義者
甘果瓦自詡為懷疑派哲學家,對客觀世界、上帝、知識的確定性都表示懷疑,信仰的缺失使他對外界保持一種不反抗的清醒和一種不認同的接受。折中調和是他在幻想與現實間得以切換自如的生存法寶,也是利己的重要手段。
我們不妨將作品劃分為數個場景,在圣跡劇場景中,圣跡劇的提前開演,得益于甘果瓦的調和與權變。一邊是群眾的暴動與發難,一邊是主教等勢力的威壓,得罪哪邊都難逃絞死的命運,甘果瓦的機動性與平衡執中的態度是他生存的資本。
在跟蹤場景中,甘果瓦覺得沒什么比跟蹤一個美女更有助于幻想,于是聽任那奇特的獨立自由的意識去跟蹤愛絲梅拉爾達,自己的投宿問題卻拋置一邊,沉浸于溫甜朦朧的幻境。正如齊澤克所說:“雖然犬儒主義對于意識快樂面具和社會現實之間的距離心知肚明,但它依舊堅守著面具。” 直到被伽西莫多揍暈在陰溝中,寒意與垢污給了他感官上的強暴,才迫使他清醒。他說赤足小野人慌亂中留下的草席是自己的救濟床,“不論是好床,還是好火,總之草席是天賜的呀”(巴,70),這是一種帶有玩世不恭色彩的隨遇而安,也是一種折中調和的精神勝利法。
在圣跡區場景中,甘果瓦誤入圣跡區,他起初漂浮于自己可怕的文學想象中,將畸形、擁擠、奇特的圣跡區幻想成群魔殿。他在為自己辯護時則繾綣于詩的世界,自稱為詩人、劇作者以及哲學家,企圖獲取赦免。直到聽到絞死的警告與最后通牒時,他才如夢初醒,為了謀取生存利益,他選擇無原則地妥協與服從。這種委曲求全、接受現實的做法,正是犬儒的表現。在獻計場景中,甘果瓦說:“起先我愛過女人,后來我愛禽獸,現在我愛石頭。”(巴,354)這種不乏自嘲的語言中,表現了甘果瓦重視自我保存的特性,愛情追求不過是鏡花水月,這自然不等于他無欲無求,只不過是流浪過程中的慘痛教訓使他對現實世界有了更清晰的認知,使他更懂得放下。適度的折中與妥協,也是另一種方式上的利己。
在替罪羊情節中,副主教企圖說服甘果瓦作替罪羊,起初甘果瓦出于自身利益的權衡果斷拒絕了,但當副主教再次以道德名義綁架他時,他猶疑了并陷入哲學家的幻想中去了,他不僅大言不慚地說道“死又算得了什么?”且憧憬死后或許能見到像荷馬、埃加德斯和奧蘭普等偉大人物。不切實際的意識流是他保持心理平衡的內在需要,而幻想中的哲人之死與現實中的個體存在終歸是對立的。甘果瓦作為一個絕對的利己主義者,面具之下的理性,使他走上了損人利己的邪路。
桑德斯曾經指出:“利己主義是認為每個人在任何時候都應該最大限度地追求自己利益而不應該犧牲自己利益的學說。”費爾巴哈更是將利己主義劃分為兩種:一種是利人利己,一種是損人利己。在甘果瓦身上,不論是對爭執糾紛事件的調和,還是對自我幻想與外在現實的調和,都很好地彰顯了他的利己主義本色。而個人利益的至高無上,為了生存超越道德底線,又讓他染上了庸俗、滑稽,甚至邪惡的色彩。
綜合觀之,作為流浪文人的甘果瓦,負載著厚重的歷史文化內涵,聚焦了底層民眾共時性的生存困境與精神危機;作為實用主義者的甘果瓦,則是充分地演繹了人的異化歷程與信仰的泛俗化;作為利己主義者的甘果瓦,在虛妄幻想與客觀世界中切換自如,緊握著折中調和的生存法寶。概言之,甘果瓦是貧困鑄就的犬儒,是《巴黎圣母院》中的不可缺少的聯結人物,值得我們給予更多的關注與思考。
a 〔法〕雨果:《巴黎圣母院》,陳敬容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94頁。以下出自《巴黎圣母院》的引文均出自這個譯本,為了行文簡潔,后面不再一一做注,只在正文標注頁碼。
參考文獻:
[1] 雨果.巴黎圣母院[M].陳敬容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
[2] 齊澤克.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
[3] 威廉·詹姆斯.實用主義[M].陳羽綸,孫瑞禾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897.
[4]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Ethics . Printed by Braun Brumfield Inc U. C 1995. 250.
作 者: 夏肇蔓,紹興文理學院人文學院漢語言師范本科在讀;王芳,紹興文理學院人文學院教授,當代文學評論家,研究方向:世界文學與比較文學。
編 輯: 趙紅玉 E-mail: zhaohongyu6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