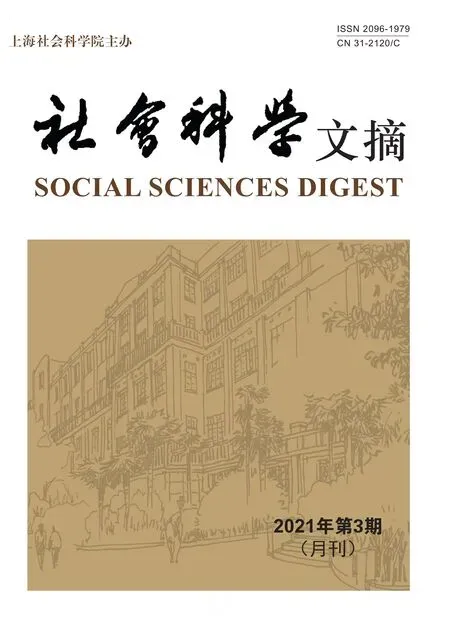基督教與社會服務的契合、沖突與重構
引言
基督教慈善團體作為現代社會服務的載體之一,廣泛參與社會福利傳輸,在為弱勢群體提供服務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基督教慈善活動與現代社會服務的共通性“偶然性聯結”如何體現、二者存在哪些沖突、這些沖突在現代福利背景下如何化解等問題,是當代社會服務研究需要厘清的問題。本文通過對基督教服務行動的歷史分析和對基督教與社會服務關系內涵的闡釋,來解讀基督教對社會服務的構造意義,并嘗試分析基督教服務與專業社會服務如何實現雙向整合。對基督教與社會服務的契合性及其關系重構的分析有利于促進二者進一步耦合,更好發揮基督教的社會福利功能,實現服務資源多元化。
基督教與社會服務的親緣性
宗教組織作為一種重要的組織形態,與社會服務有天然的契合性。社會服務脫胎于基督教的濟貧實距,被視為基督教世俗化的余緒和變體。
(一)基督教價值與社會服務實距
基督教濟貧以教會為單元進行組織,在社會服務資金募集、服務對象管理、志愿者培訓等方面均發揮了先驅作用。從資金來源來看,國家只是強調政府在反貧困中的責任和義務,沒有專門的資金劃撥,福利救助采取由教區牧師向富人征收濟貧稅的方式進行。資金來源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教會神職人員募集資金的能力,依賴于教會中信教人士的“十分獻一”奉獻資金。從濟貧管理來看,救助資格以教區居留權利作為接受救助的必要條件,《濟貧法》規定“治安法官有權以教區為單位管理濟貧事宜、征收濟貧稅及核發濟貧費,每一教區設立平民濟貧監察員進行監督”。實際上,濟貧由教區教會負責組織實施,教會是濟貧的實質性責任主體;教區神職人員作為濟貧的主要管理人員,管理救助資金的使用以及調動教區內的人力資源。從志愿者層面來看,濟貧法實施之后,教區內出現了以教區牧師為首的具有基督教信仰的“友善訪問員”,這些友善訪問員是最早的社會服務個案工作者雛形,是社會服務工作者和志愿者的前身。
在后期的睦鄰運動中,教會神圣性分享的團體活動與世俗的社會救濟方法逐漸整合,借由國家公共福利責任的擴張而發展,教會牧師是主要實距者。這一階段如成人教育、幼兒園、鄰里會議等活動均采取團體為導向的方法,運用的是通過團體改變個人的理念,并積極探索使用團體契約、團體記錄的方式來協助個別成員的成長。這被視為宗教慈善衍生與裂變專業團體工作方法的重要開端。
(二)基督教倫理與社會服務職業觀
一方面,“天職觀”在職業與社會結構之間建立了理性的聯結,解決了“為什么要服務他人”的問題。基督教正是通過超自然的象征性的約束體系將天啟與俗世生活聯結在一起,通過理性教義結構強化超驗性質從而規范基督徒現世生活的道德秩序。宗教改革之前,教會內部存在貶抑財富的傾向,視貧窮為榮耀,認為職業與工作是贖罪的過程。宗教改革之后,勤勉工作被賦予美德的內涵,被認為是“上帝選民”身份的佐證。新教所表露的職業倫理體現了人與社會的互構關系,化解了神圣與世俗之間的矛盾,通過宗教“準則”的邏輯將宗教目的、國家目標和合作的社會秩序密切整合在一起,實現了基督教道德與社會合作的二元一致性,成為社會工作職業觀念的宗教源頭,為社會服務“利他主義”的職業操守提供了合理性的解釋。從事社會服務職業不僅是一種謀生的工具,也是一種職責和公民義務,這使得服務他人具有了道德正當性,回應了“為什么要服務他人”的問題。工作倫理重新詮釋了社會的本質,重組了集體生活的原則,職業不僅是個體的責任,職業活動需要通過上帝賦予的“天職”與更廣闊的社會結構聯系在一起,與整個社會的經濟行為準則相適應,從而構建法律準則與社會秩序。
另一方面,基督教價值孕育了西方社會服務職業的核心價值,嘗試解決“如何服務他人”的問題。宗教改革在救贖、財富和職業之間建立了一種微妙的平衡機制,通過基督徒與上帝之間締結的契約來規范基督徒的俗世行為。基督教教義的“天職觀”和“預定論”要求信徒以榮耀上帝為使命,從而達到靈魂的操練與救贖。通過本職工作來改善不完備的社會福利供給,兢兢業業、忠于職守做好本職工作,這為社會服務職業價值觀和職業倫理體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礎。新教倫理削弱了理性倫理的心理基礎,使慈善救助工作出現了重視工作倫理和體系化的新趨勢。新教倫理通過榮耀上帝的使命將神圣的宗教原則與世俗領域的生活建立了根本性聯系,使社會生活具有了宗教意義,這為社會服務職業觀的建構提供了天然的養料。基督教價值認可“人在上帝面前平等”,人有與生俱來的尊嚴,從這一教義出發,逐漸發展出社會服務中“尊重服務對象”“案主自決”“保密”等職業倫理。雖然現代社會服務的職業倫理體系日益成熟和完善,對從業者的職業觀和道德操守要求越來越細化,“堅毅”“正義”“廉潔”“公共參與和政治行動”等操守遠遠超出了基督教倫理道德規范的范疇,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天職觀”為社會服務“助人自助”“忠于職守”“權利”“尊重”等核心職業觀的形成提供了重要基礎。
基督教慈善與社會服務的沖突
工業革命加劇了社會矛盾,基督教的道德和方法論無法應對工業化對社會結構的破壞,宗教式的濟貧方式在應對人文脫序和社會弊病問題上表露出無力感。在這種情況下,科學慈善運動應運而生,基督教濟貧實距受到來自科學慈善服務的批評與詬病。基督教與科學慈善服務的沖突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社會性不足
對服務對象的選擇性是基督教慈善飽受爭議的重要原因之一。很多教堂在提供服務時,只針對本教堂的信徒。由于服務資源的有限性,往往會對服務對象的選擇作出一定限制,傾向于選擇信仰一致的服務對象,具有小共同體本位的特點,缺乏資格廣泛性與對象參與的社會性。同時,基督教服務多為附屬于教會團體活動的行為,其組織為教會團體的內部行政管理機構,其服務規則、服務管理和監督均遵循教會內部的運作管理思路,缺少社會服務的社會取向和公共價值觀念。科學慈善具有趨于均等性和普惠性的特征,尤其是法定社會服務和世俗非營利組織的服務提供通常注重公平性和社會性。基督教服務實距的局部共同體本位特征與公平性相沖突,不能適應工業化之后社會福利的運作邏輯。
(二)公共性不足
基督教慈善活動的公共性不足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其社會服務具有強烈的福音目的性導向,不符合社會服務的公共性特征。按照專業慈善組織理念,公益慈善工作要進行專業分工與協作,去除私人化的功利性與目的性。基督教慈善將服務傳遞作為傳遞福音的途徑,很多基督教慈善團體將口傳福音和布道作為服務過程中不可或缺的行動,以凸顯信仰為主,服務為輔,社會服務只是作為傳遞福音的連帶行為。另一方面,基督教提供的社會服務多為短期的、個體化的、應急性的慈善行動,本質上是心靈的功利主義,這種服務形式不能從宏觀的高度考慮受助者的需求是否得到滿足,服務行為是否契合服務對象的需要。且局部性、松散的服務缺乏組織性與深入性,“授人以魚”的慈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社會問題,但無法從源頭上根治社會弊病。
基督教慈善與現代社會服務的重構
福利國家出現危機之后,宗教慈善組織再次成為政府福利供給的重要合作伙伴。同時,社會服務組織的管理出現了規范化和專門化態勢,很多國家建立了專門的機構,管理與支持有宗教背景的團體參與社會服務。基于后福利國家的發展現狀,基督教調整自身的服務行為,其參與社會服務的模式出現了新的轉變,這種轉變具體體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從法人類型而言,依托獨立的非營利組織開展公益服務成為重要的社會參與路徑。雖然教會仍然在直接提供零散的、應急的、不定期的社會服務方面發揮一定作用,但是,由于其專業性的缺失,服務水平、服務規模和服務層次非常有限,很難滿足社會福利對于社會性和公共性的要求。教會直接辦社會服務已經成為基督教參與社會服務的非主流形態,主流的模式則為教會通過獨立注冊慈善機構輸送社會服務。總體而言,在組織管理方面,治理結構從依附于宗教實體的內設機構、附屬機構轉型為與宗教弱關聯的獨立法人機構,治理呈現出與社會規則和制度較高程度的契合性。在人員配置方面,從決策依賴于教會神職人員轉向理事會成員選擇社會化,大部分機構在理事會成員中仍會保留一定的信徒比例,服務人員的選擇從宗教性考量向世俗性考量轉變,不再以信仰一致或信仰優先作為選擇員工的唯一標準,而是更側重于員工的能力素養。
第二,從專業類型而言,許多基督教背景的服務機構或團體通過專業化途徑實現了從“宗教慈善”到“社會公益”的轉型。服務供給出現職業化、專業(學科)化,服務方法走向標準化,以過程管理和質量證據為導向,注重管理和服務人員的專業資質(執照)而非信仰歸屬;服務供給與信仰傳播相分離,不再以口傳福音為唯一目標,更多兼顧世俗性的專業方法。基督教參與社會服務跨宗派趨勢增強,服務理念更加開放,其服務不僅呈現出跨教派特征,也出現了與世俗服務機構合作的特征。基督教服務方法逐漸超越不同教派、跨越不同宗教,甚至出現了宗教與非宗教世俗方法的融合,催生了靈性社會工作的出現,在絕癥護理、臨終關懷、戒毒、苦難疏導、災后心理輔導等領域發揮特殊作用。
宗教慈善與社會服務關系重構需要建立于兩個基本的考量之上:縱向的歷史動態發展維度和現實的各國基督教參與社會服務的異質性維度。歷史的縱向維度前文已經加以闡述。在現實的異質性維度方面,根據當今歐美國家的基督教參與社會服務的組織類型、服務遞送和服務人員選擇,結合宗教慈善服務的特點與方法,本文梳理出以下基督教與社會服務的整合模式及形態特征。(見表1)

表1 基督教與社會服務的整合模式及形態特征
基督教慈善與社會服務關系重構的要旨
(一)入世性——關系重構的重要前提
西方宗教慈善的入世特征是關系重構賴以立論的依據之一,基督教主動積極參與濟貧扶弱的現世行為,是基督教慈善與現代社會服務重構關系的重要前提。基督教與社會服務之間存在著選擇性契合關系,這種近親關系發端于宗教倫理與價值的母體。宗教慈善行為從未被擠出社會福利領域,而是作為一種有效抵制政治權力和經濟財富支配性影響的力量存在于社群之中。宗教實存的歷史性結構表明了其參與社會服務的適應性與主動性,能夠根據時代與環境的變革而重塑自身,參與道德和社會秩序重建,在變化的環境中能夠找到與社會文化的結合點,不斷調整自身適應現世生活,在經驗層面實現世俗化。正是宗教的可塑性與世俗化特性使其成為社會服務主體的“候補者”,積極尋找社會福利的社會空間,通過調整自身行為努力適應現代社會服務的邏輯規則,廣泛嵌入社會規范、福利制度與權力安排。宗教團體所具有的志愿人力資本、免費場地、強大募捐能力與動員能力等資源作為社會服務的儲備性物資,為社會實距的開展提供潛在物質性支持。
(二)宗教性——關系重構的焦點變量
基督教慈善組織的宗教性格決定了社會服務產品中必然有宗教元素的體現,最低層次在服務宗旨表達上體現基督教價值。允許宗教屬性的適度表達是基督教參與社會服務過程中的重要問題,基督教核心價值的存留和符號表達是基督教與社會服務關系重構的關鍵。宗教的泛普化使宗教改變了原初樣式,彌散于世俗制度之中,基督教主流觀點肯定了服侍善工(“手傳”)是福音傳遞的基本條件之一。即社會服務不必以口傳福音作為附帶條件,但是服務中的必要宗教性表達是基督教社會服務的內在訴求,這種訴求體現在管理哲學中的宗教文化納入,體現于宗教標志的外在顯現,體現于服務項目中宗教方法的運用。適當宗教儀式性的表達不應該成為宗教與社會服務關系重構中的屏蔽“要素”,而應該作為優勢因素加以延續,作為關系重構的焦點變量加以考量,遵循求同存異原則和優勢互補原則。在基督教文化底蘊深厚的歐美國家,政府逐漸意識到宗教性表達對于宗教性社會服務機構的重要性,部分制度為宗教性表達提供了一定的彈性空間。比如,允許宗教標志和符號的外在運用;宗教團體自籌資源的服務項目可以傳教,購買政府項目的服務中禁止使用公共資金傳教;允許在對服務對象進行嚴格的需求評估基礎上運用靈性方法;宗教性方法的使用需要同時具有可替代的、可及性的世俗方法供選擇;等等。
(三)互嵌性——關系重構的共通途徑
現代基督教參與社會服務合作不是中心主義的支配與被支配思路,而是需要秉持去中心化的雙向合作、求同存異的態度,同時需要以公共福利為合作契合點作出雙向的行動調整。基督教團體與社會服務的關系重構具有雙向促進效能,基督教組織參與社會服務有利于抑制社會福利中的過度專業化現象。同時,社會服務行為為宗教團體操練靈命、榮耀上帝提供了現世的平臺和空間。西方基督教倫理作為價值規范與道德準則的延伸,在世俗實距中形成制約經濟關系準則和個體職業行為的約束性力量,通過契約神學塑造了現世工作的職業道德。在現代社會服務過于倚重科學主義的工具取向之時,需要借鑒基督教的社會關懷倫理,糾正服務中人文主義不足、彌補價值缺失的缺陷,重申國家社會服務的道德目的,為重新審視社會服務的本質提供出發點和基礎。反之,基督教參與社會服務需要借鑒專業社會服務的系統化、專業化和職業化要素,引入社會服務的視角和方法克服慈善低效,提高專業性,將促進人類福祉的慈善行為提升到更廣闊的道德維度,上升到現代公益的高度,促進施舍型服務價值向制度型福利觀轉變,將社會小共同體本位的服務推向更寬廣的公益范疇,將零散的、善意的教友互助轉變為建基于國家與市場基礎之上的慈善社會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