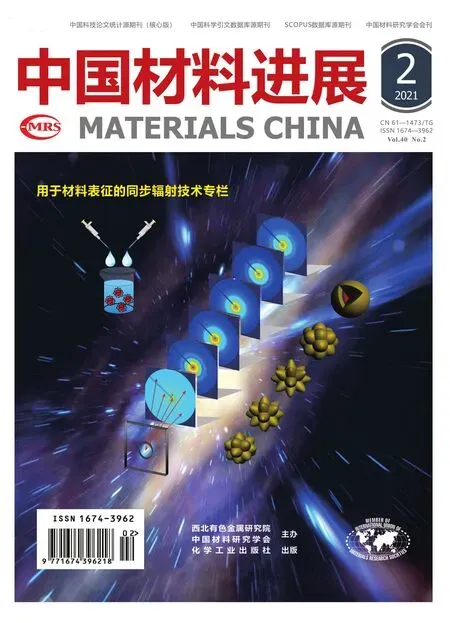三維X射線衍射技術與工程材料研究
王樂耘,朱高明
(上海交通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院 輕合金精密成型國家工程研究中心,上海 200240)
1 前 言
工程材料,例如金屬和陶瓷,構成了現代制造業的基礎。這些材料的物理、化學和機械性能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它們在晶粒尺度上的微結構及其相互作用。因此,對材料晶粒尺度微結構的表征成為了聯系材料設計與服役評價的關鍵橋梁。傳統的基于電子顯微學的表征方法(如電子背散射衍射)只能用于探測材料表面的晶粒,無法研究材料內部的絕大多數晶粒及它們之間的晶界。此外,電鏡表征需要在真空環境下對樣品進行操作,限制了各種原位實驗的可能性。因此,迫切需要發展一種方法來實現材料內部晶粒的三維、無損、定量乃至動態的微結構表征[1, 2]。
同步輻射是近年來迅速發展的一種新型材料表征手段,尤其在近20年里,隨著第三代同步輻射裝置的興起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同步輻射裝置利用加速器使電子以接近光速的速度在周長為數百米的儲能環里作圓周運動,在沿儲能環分布的磁場作用下這些電子失去部分能量,以X射線的形式釋放,通常被稱為同步輻射X射線。與常規實驗室X射線相比,同步輻射X射線有許多優點,包括高能量、高亮度、高準直性等[3, 4]。高能量的X射線可以穿透數百微米乃至毫米級別厚度的宏觀樣品,其開放的實驗環境為各種原位實驗提供了極大的空間。
目前,同步輻射X射線衍射是研究晶體材料的重要手段,但普通的多晶衍射方法只能得到材料內部所有晶粒的平均信息[5]。使用白光勞厄微束衍射,例如差分孔徑X射線成像(differential aperture X-ray microscopy, DAXM)能夠表征單個晶粒,但掃描成像速度較慢[1]。近年來,歐美的一些學者提出了一種三維X射線衍射(3DXRD)技術,可以實現對塊體材料內部單個晶粒的解析。該技術首先由丹麥Ris?國家實驗室提出[6, 7]。3DXRD的核心思路是從不同角度采集樣品的衍射信息,然后綜合分析所有的衍射譜,解析出材料內部的晶粒結構信息。3DXRD的工作原理與X射線斷層掃描(XCT)類似,但前者采集的是衍射信號,而后者采集的是X射線吸收譜。3DXRD可以與各種原位實驗配合,來研究工程材料內部晶粒的演化[8, 9]。由于3DXRD實驗往往需要使用能夠穿透毫米厚度樣品的高能X射線,因此3DXRD又被稱為高能X射線衍射成像(high energy diffraction microscopy, HEDM)。與DAXM相比,HEDM的空間分辨率要低一些,但實驗速度會快很多,便于開展各種原位實驗。
3DXRD技術在歐洲的ESRF光源、美國APS光源、日本SPring-8光源以及德國的DESY光源的幾條線站已經實現并面向用戶開放。
2 三維X射線衍射基本原理
圖1展示了3DXRD的技術原理[10]。由扁平狀狹縫匯聚的高能X射線以透射方式與樣品作用,在另一端以高分辨二維探測器記錄衍射信號。實驗過程中,樣品繞Z軸以步進方式旋轉(步長為1°或更小),在每個旋轉角度分別記錄樣品產生的二維衍射譜。3DXRD技術采用單色X射線,因此這些衍射圖譜上的衍射斑會分布在若干個同心圓環(德拜環)上。由于樣品的旋轉,樣品中的每一個晶粒的各個{hkl}晶面都有機會在不同轉動角度下產生衍射信號。由于同步輻射產生的高能X射線可以穿透毫米級的各種金屬(如鎂、鈦、鋼、鎳等)[11-14],所以可以對絕大多數工程材料塊材進行分析。
在獲得不同旋轉角度(ω)下的二維衍射圖譜后,利用專用算法及軟件,例如FABLE[15]、MIDAS[16]等對這些二維衍射譜進行尋峰、幾何變換、衍射峰逆向標定等操作,可以分離出每個晶粒所對應的衍射峰,進而根據衍射峰的位置及旋轉角度ω來分析這些晶粒的晶體取向、空間位置、晶內局部應力張量等信息。
3DXRD實驗可與原位拉伸實驗結合。實驗中,對樣品以步進方式沿圖1中的Z軸進行拉伸;在每一拉伸步后暫停引伸計,然后進行3DXRD的數據采集(繞Z軸旋轉并采集衍射信號);之后進行下一步的拉伸及3DXRD數據采集,直到實驗結束。通過對不同應變下的3DXRD數據分析,可以得到晶粒的晶體取向和晶內局部應力隨加載過程的演變。

圖1 原位3DXRD技術裝置示意圖[10]Fig.1 Schematic of the in-situ 3DXRD experiment[10]
利用3DXRD方法可以方便地對材料的宏觀和微觀織構進行分析。圖2為通過3DXRD得到的Ti-7Al樣品中某一截面內的晶粒取向及位置信息(X射線能量:65 keV,束斑尺寸:2 mm×1.7 μm),該截面體積為1.5 mm(x)×1.5 mm(y)×0.56 mm(z),其中z軸為拉伸方向[17]。該材料為六方晶體結構,晶粒尺寸約為100 μm。通過對樣品z軸和晶粒的c軸夾角θzc的計算,發現大部分晶粒θzc較大,即這些晶粒的c軸與拉伸方向近于垂直,符合鈦合金擠壓棒材織構的特點。

圖2 3DXRD實驗獲得的Ti-7Al多晶樣品的晶粒取向與位置[17]Fig.2 Grain orientations and positions of a polycrystalline Ti-7Al sample characterized by 3DXRD experiment, the hexagonal unit cells represent the grain orientations, which are colored according to the angle between the grain and the sample z-direction[17]
圖1所示的是遠場(far field) 3DXRD模式,探測器距離樣品在300~1500 mm范圍內,也是較為常用的模式。另外一種被稱為近場(near field) 3DXRD模式,探測器被放置在離樣品只有幾毫米的位置。近場3DXRD可以重構得出晶粒的三維形貌信息,其空間分辨率可低至1.5 μm[18, 19]。近場3DXRD主要應用于高分辨三維晶粒形貌、晶體取向等研究。
3 3DX RD在工程材料研究中的應用
3.1 晶體取向的演化
工程材料在變形時通常伴隨著晶粒的晶體取向變化,3DXRD原位實驗是理想的研究手段。Poulsen等采用3DXRD技術研究了AA1050多晶純鋁的塑性變形過程[20, 21]。圖3a中展示了其中一個晶粒的某個{hkl}晶面的衍射斑變化(X射線能量:55 keV,束斑尺寸:5 μm×5 μm,角分辨率:0.2 mrad),在不同的應變下(0%~6%),衍射斑質心在ω和η方向上發生了位移。通過分析所有衍射斑的位置改變,可以計算晶粒晶體取向隨應變的旋轉。該研究分析了95個晶粒在拉伸過程中的晶體取向變化。在圖3b的反極圖(IPF)中,圓點代表每個晶粒的最終取向,短線另一端代表晶粒在塑性變形前的初始取向。所有晶粒在反極圖中的位置可分為4個區域(①~④)。他們比較了實驗測得的晶粒晶體取向旋轉方向和用經典的Sachs模型計算得到的晶粒晶體取向理論旋轉方向(圖3c),結果表明,僅區域①中的晶粒晶體取向沿模型預測方向旋轉,而其他3個區域中的晶體取向旋轉方向與模型有較大差異。該工作表明,多晶材料在晶粒尺度上的變形十分復雜,一些經典的力學模型只是一種簡單的近似,無法完全擬合材料內部的實際演變。

圖3 通過原位3DXRD對AA1050鈍鋁中晶粒的晶體取向演化的表征[21]:(a)不同應變量下某個衍射斑的變化,(b)拉伸過程中各晶粒晶體取向在反極圖中的演化,(c)實驗及Sachs模擬得到的晶體取向旋轉的對比Fig.3 Monitoring the grain orientation rotation in AA1050 pure aluminum by in-situ 3DXRD[21]:(a) position and shape change of a diffraction peak at different strain, (b) grain orientation rotation during tensile deformation shown in an inverse pole figure (IPF), (c) comparison of grain orientation rotation between the experimental result and the Sachs model simulation
3.2 晶粒尺度應力測量
工程材料變形時,不同晶粒內的實際應力狀態往往與根據外部載荷除以樣品截面尺寸計算得到的宏觀應力有較大出入。這是由于,不同晶粒的晶體取向、晶粒尺寸以及相鄰晶粒的相互作用等均會對該晶粒的變形方式產生影響,進而改變各晶粒內的局部應力。
通過3DXRD實驗,可以在加載條件下對樣品中不同晶粒的應力狀態進行計算。作者等借助美國APS光源1-ID線站的3DXRD實驗裝置表征了純鈦在原位拉伸時不同晶粒的應力狀態的演變[22],樣品的橫截面為1 mm×1 mm。圖4a為拉伸變形前通過近場3DXRD得到的某個截面上的晶粒分布圖,顯示該材料由晶粒尺寸約為100 μm的等軸晶組成。該截面上的晶粒的晶體取向如圖4b中的{0001}極圖所示。圖4c和4d顯示的是在變形前和拉伸應變為0.31%時,通過遠場3DXRD分析得到的該截面上的晶粒的質心位置及Mises應力分布。遠場3DXRD使用的X射線能量為65.4 keV,束斑尺寸為100 μm×1.5 mm,在樣品繞z軸旋轉時,整個橫截面始終在束斑照射下,有利于對處在樣品表面的晶粒的標定。樣品繞z軸以1°的步長旋轉140°,在每1°記錄一張衍射譜,從而獲得遠場3DXRD數據并得到晶粒的晶體取向、質心位置及應力信息。結果顯示,樣品在變形前,其中晶粒的應力分布已經有所差異,不同晶粒的Mises應力約在50~200 MPa,明顯大于預加載的宏觀應力的數值(19 MPa)。這表明該樣品在初始狀態下就存在殘余應力,可能是由于熱加工后冷卻時鈦的熱膨脹系數的各向異性引起的。拉伸應變為0.31%時,這些晶粒中的Mises應力普遍增大(如圖4d所示),并且不同晶粒之間的差異進一步變大。晶粒間的應力差異與每個晶粒內部的變形過程有關。
運用類似方法,一些學者研究了其它鈦合金在加載-卸載[17]以及室溫蠕變[23]后的殘余應力分布,發現不同晶粒中的殘余應力也往往有較大差異。

圖4 通過3DXRD分析多晶純鈦拉伸時不同晶粒的Mises應力演化[22]:(a)通過近場3DXRD得到的樣品某個截面上的晶粒形貌照片;(b)截面上晶粒的晶體取向以{0001}極圖表示;通過遠場3DXRD得到的樣品變形前(c)和拉伸應變為0.31%時(d)不同晶粒的質心位置及Mises應力分布圖,每個晶粒旁的數字代表Mises應力值Fig.4 Analyzing the von Mises stress (σVM) evolution in a polycrystalline pure titanium from the 3DXRD data[22]:(a) Reconstructed grain map from a near-field 3DXRD scan; (b) {0001} pole figure generated from the grain orientations; Measured σVM in different grains before deformation (c) and at the microscopic strain of 0.31% (d) from far-field 3DXRD
遠場3DXRD能夠測量每個晶粒的平均應力(即typeⅡ應力)。從上面例子中可以看出,在相同的宏觀應力(typeⅠ應力)下,不同晶粒的平均應力可以有很大不同。然而,在很多情況下,在每個晶粒內部也存在應力分布的不均勻,即所謂的typeⅢ應力。普通的遠場3DXRD方法無法分辨typeⅢ應力。在近期一項研究中,日本豐田實驗室與SPring-8光源的BL33XU線站合作,發展了一種掃描3DXRD技術 (scanning 3DXRD)[24]。圖5展示了該實驗的裝置與結果。他們采用了能量為50 keV、束斑尺寸為1 μm×1 μm的X射線微束照射一塊低碳鋼樣品。微束每次照射在一個1.2 μm×1.2 μm×1.2 μm的體素上。在每個位置,樣品繞z軸以0.6°的步長旋轉180°并記錄衍射譜。運用3DXRD分析軟件可以測量該體素的晶體取向和應力張量。接下來,讓樣品臺在y方向和z方向分別進行步進掃描,在每一個掃描點進行上述3DXRD數據采集,就可以得到掃描區域內所有體素的晶體取向與應力信息,綜合后就可以獲得晶粒形貌及內部的應力分布。圖5d~5i所示的是在宏觀應變5.1%下,晶粒內部的typeⅡ應力,圖5j~5o所示的是晶粒內部的type Ⅲ應力。可以看到,一些晶粒內部存在較大的應力分布不均勻性。在某個晶粒中,其σzz分量為280 MPa,而其內部的體素的σzz分量在20~470 MPa的寬闊范圍分布。這個例子表明,晶粒內部的type Ⅲ應力是不可被忽略的。
3.3 六方晶系材料變形機制研究

測量六方晶系材料滑移及孿晶啟動CRSS的一種方法是用聚焦離子束(FIB)加工出微米或納米尺度的單晶樣品,然后利用特殊裝置對這些微納樣品進行壓縮或其它加載[25, 26],從表面滑移帶或孿晶區域的產生判定滑移或孿晶的啟動,同時從實時應力上計算得到對應變形機制的CRSS值。但該方法的樣品制備復雜、實驗周期長、每次只能測一個晶體取向內的滑移或孿晶。
原位3DXRD實驗提供了測量六方晶系材料滑移和孿晶啟動的CRSS的另一條途徑。作者等通過原位3DXRD分析了純鈦在拉伸過程中材料內部晶粒中的孿晶形核[10]。實驗中選取的初始拉伸樣品的橫截面為1 mm×1 mm,晶粒為尺寸約100 μm的退火等軸晶。在APS 1-ID線站測量了樣品從0到3.0%應變下的遠場3DXRD數據,確定了截面上所有晶粒的位置、晶體取向和應力張量。由于應變量較小,大部分晶粒的位置、晶體取向變化不大。如圖6a所示,在拉伸應變達到1.6%時,在{0001}極圖上發現了一個新的晶體取向,通過與其他晶粒的位置和取向差對比后,確定其為1#晶粒中產生的孿晶,因為兩者位置接近,取向差約為85°。根據1#晶粒在孿晶形核前一刻的應力張量(圖6b),計算得到孿晶形核的CRSS約為225 MPa。在孿晶形核后,繼續追蹤了1#晶粒和孿晶的應力張量(圖6b),發現孿晶中的應力始終比母晶粒低。這表明孿晶界兩側存在顯著應力差,這個現象在其他孿晶中也被觀察到[27]。

圖6 通過原位3DXRD研究多晶純鈦中的孿晶形核[10]:(a)不同應變量下,探測區域內的晶粒{0001}的極圖以及晶粒位置圖;(b)4個晶粒以及孿晶的σzz應力分量隨宏觀拉伸的演化Fig.6 Study of a twin nucleation event in a polycrystalline pure titanium using in-situ 3DXRD[10]:(a) {0001} pole figures and grain positions at different strains in the probed volume; (b) Evolution of the σzz stress component in four grains and the twin
原位3DXRD實驗也可以測量位錯啟動的CRSS,可分為間接測量法和直接測量法。間接測量法是將3DXRD測得的數百個晶粒的應力張量在各個滑移系上作投影,以此作為每個滑移系的“強度”,根據所有晶粒中各滑移系“強度”的平均值演化,再結合晶體塑性模型,可以對各滑移系的CRSS值作出估計[28, 29]。
作者等[22, 30, 31]發展了通過觀察晶粒的晶體取向變化判定滑移系啟動的方法,根據應力張量在啟動滑移系上的投影可直接測量CRSS。室溫下鎂合金的變形主要由基面滑移實現,而柱面滑移及錐面滑移的CRSS數值一般為基面滑移的數十倍,這嚴重降低了材料的塑性變形能力。在鎂合金中添加少量固溶稀土元素往往能夠顯著提高材料的強度與塑性,其中一個重要機制是固溶稀土元素改變了鎂基體中的滑移系及孿晶系的CRSS。作者等[31]采用3DXRD技術直接測量了Mg-3%Y(質量分數)合金基面滑移、柱面滑移和錐面滑移的CRSS。實驗采用的拉伸樣品來自于軋制板材,晶粒尺寸約為50 μm,拉伸軸沿著材料的軋制方向(RD)。在APS 1-ID線站,試樣被逐步加載至3%應變,在每個加載步下,通過遠場3DXRD分析在1 mm×1 mm×0.1 mm體積中近1000個晶粒的晶體取向、空間位置和應力張量。對每個晶粒,將其在任一應變下的取向與變形開始前的取向作比較,可以求得取向差(disorientation)以及c軸轉角(c-axis misalignment),如圖7a所示。


圖7 通過原位3DXRD測量Mg-3%Y(質量分數)合金中不同滑移系的CRSS[31]:(a)晶體取向旋轉中的取向差(disorientation)和c軸轉角(c-axis misalignment)的定義;(b)3個晶粒中的晶體取向旋轉及Mises應力的演化,3個晶粒分別發生了柱面滑移、基面滑移及錐面滑移;(c)3個晶粒中各滑移系的分切應力的演變Fig.7 Measuring the critical resolved shear stress (CRSS) of a Mg-3wt%Y alloy using in-situ 3DXRD[31]:(a) Definition of disorientaion and c-axis misalignment; (b) Evolution of the disorientation, c-axis misalignment, and von Mises stress values in three grains that show the slip activity of prismatic slip, basal slip and pyramidal slip, respectively; (c) Evolution of resolved shear stress values on different slip systems in the three grains
3.4 材料失效過程研究
理解工程材料的失效過程對于預計其服役壽命以及改進設計具有重要意義。傳統的研究手段,如斷口分析、電鏡表征等,無法清晰認識材料內部的裂紋產生過程,尤其對裂紋產生的晶體學與局部力學條件。3DXRD結合X射線斷層掃描技術(XCT)是研究材料失效過程的一種新手段,尤其適合各種原位實驗條件。
氫脆是許多高強度工程材料失效的一種重要機制,在石化、核電、儲氫等工業領域尤其普遍。經過長期研究,人們認識到氫脆是由氫原子與材料中的各種缺陷,如位錯、點缺陷、晶界的交互作用所導致,是一個復雜的物理過程。目前仍不清楚哪些晶界容易成為氫脆的發源地。Hanson等[32]將一根直徑為1 mm的鎳基725合金在充入氫氣后拉伸至斷裂,通過XCT技術在斷口附近找到了位于材料內部的若干條微裂紋。之后,他們對相關區域進行了近場3DXRD表征(取向分辨率:0.1°,空間分辨率:1.5 μm),獲得了這些微裂紋附近的晶粒形貌和晶體取向信息。著重分析了哪些晶界會更有效地阻擋裂紋擴展,即圖8a中所示的裂紋阻擋晶界(crack-resistant grain boundary plane)。對10處裂紋阻擋晶界進行晶體學分析(圖8b),發現當晶界兩側晶粒中至少有一側對應的是低指數晶面時,晶界對裂紋擴展的阻擋能力會較高。

圖8 氫脆裂紋擴展的3DXRD研究[32]:(a)裂紋轉向過程示意圖,(b)10處裂紋阻擋晶界(crack-resistant grain boundary plane)的晶體學分析Fig.8 Study of hydrogen embrittlement by 3DXRD[32]:(a) schematic of crack deflection event (CDE), (b) orientation of plane normal directions for each pair of grains meeting at the un-cracked grain boundary in a CDE
疲勞是工程材料失效的另一種主要機制。疲勞壽命的短裂紋(small fatigue crack)擴展階段特別受關注,因為短裂紋擴展階段占到部件疲勞壽命的90%以上。目前,對于疲勞短裂紋擴展的晶體學和局部力學條件的認識不充分。Naragani等[33]研究了含有氧化鋁顆粒的鎳基超合金RR1000的疲勞短裂紋的擴展。實驗所采用的RR1000合金是由粉末冶金法制備的,晶粒尺寸約為23~32 μm,具有隨機織構,樣品橫截面為1 mm×1 mm。實驗采用循環應力載荷,應力變化范圍為0~600 MPa (60%的屈服應力)。在10 000次循環后,通過XCT在氧化鋁顆粒與基體的界面處觀察到了一條裂紋。繼續到20 000次循環后,他們用近場3DXRD(取向分辨率:0.1°,空間分辨率:1.5 μm)首先表征了裂紋附近的50個晶粒的形貌和晶體取向。接下來,對經20 000,21 000,23 000,26 000,30 000,36 000,38 000,41 000,45 000,52 000次循環載荷后的樣品,分別用遠場3DXRD表征了這些晶粒的應力狀態。圖9a展示了不同次數循環后樣品的裂紋形貌變化以及裂紋附近晶粒的應力變化,包括Mises應力、等靜應力以及應力三軸比。可以看到,在裂紋的上、中、下3個區域,晶粒的應力狀態有較大差異,此外,循環次數從30 000到41 000時,晶粒的Mises應力下降,而等靜應力與應力三軸比均上升。他們還研究了其中457#晶粒的裂紋生長方向及長度與{111}<110>滑移系上的最大切應力的關系,如圖9b所示。他們發現,疲勞短裂紋往往沿著具有最大切應力的滑移系的滑移面上生長,且裂紋生長速率與該滑移系上的切應力數值有直接關系。

圖9 原位3DXRD研究鎳基合金中的疲勞裂紋擴展[33]:(a)不同循環次數后的裂紋形貌變化以及裂紋附近晶粒的應力變化,包括Mises應力、等靜應力以及應力三軸比;(b)457#晶粒的{111}<110>滑移系上的最大切應力與裂紋生長方向及長度的關系Fig.9 Study of the fatigue crack growth in Ni-based alloy by in-situ 3DXRD measurement[33]:(a) Crack propagation and the stress state change in the surrounding grains, including the von Mises stress, hydrostatic stress, and stress triaxiality; (b)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maximum resolved shear stress on the {111}<110> slip systems in grain 457 and the crack propagation direction and length
3.5 晶體塑性有限元模型的驗證
晶體塑性有限元(crystal plasticity finite element, CPFE)模型是模擬多晶材料塑性變形行為的一種數學抽象,它充分考慮了每個晶粒中由位錯滑移或孿晶導致的局部塑性應變以及晶粒與晶粒之間的交互作用[34]。在以往研究中,CPFE模型的驗證一般是將模擬結果與材料的實驗拉伸曲線以及織構演變進行比對。然而,在晶粒尺度上的比較相對較少。此外,CPFE模型一般采用的是根據材料宏觀織構生成的虛擬晶粒結構[35],或者是根據材料表面晶粒形貌與取向(一般由EBSD測定)生成的柱狀晶結構[36],無法真實反映材料內部的結構信息。
3DXRD為CPFE模型的驗證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豐富的實驗信息[37]。一方面,3DXRD對材料初始狀態的表征結果(晶粒位置、形貌、取向)可以作為CPFE模型的輸入晶粒結構。另一方面,通過原位3DXRD獲得的晶粒取向與應力演變信息可以用來驗證模型在模擬晶粒尺度變形上的有效性。
Kapoor等[38]利用3DXRD測得的Ti-7Al晶粒形貌與取向信息建立CPFE模型(圖10a),該模型能較好地重復樣品的應力-應變曲線(圖10b)。對于0.5%應變下不同晶粒中的σyy值,CPFE模型的模擬結果與實驗值有一定程度的不同(圖10c);當用晶粒的初始殘余應力對模型修正后,模擬結果的準確度有所提升(圖10d)。
Abdolvand等[39, 40]對純Zr樣品拉伸1.2%后卸載,通過原位3DXRD測量了晶粒中的殘余應力,并與CPFE模型作了對比,同樣發現CPFE模型對于晶粒的內應力的模擬結果與實驗結果有一定差異。
上述研究表明,現有的CPFE模型盡管在模擬材料宏觀拉伸行為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準確率,但在準確描述每個晶粒的變形行為上仍然存在提升空間。

圖10 原位3DXRD測量和晶體塑性有限元(crystal plasticity finite element, CPFE)模擬結合對Ti-7Al的研究[38]:(a)將3DXRD測得的Ti-7Al合金的晶粒形貌與取向信息代入CPFE模型;(b)樣品的實驗及模擬應力-應變曲線;(c)在0.5%應變下CPFE模擬的和3DXRD測得的晶粒σyy應力對比;(d)在考慮了晶粒初始應力之后,晶粒中σyy應力的CPFE模擬值與實驗值更為接近Fig.10 The combination of in-situ 3DXRD measurement and CPFE simulation for Ti-7Al[38]:(a) The grain morphology and crystal orientation information from 3DXRD are used for CPFE model input; (b) Simulated and experimental stress-strain curves; (c) Comparison of σyy stress component between CPFE simulation and 3DXRD measurement at 0.5% strain; (d) The CPFE model becomes more accurate in capturing the stress state in the grains after taking the initial residual stress into consideration
4 結 語
本文通過多個應用案例展示了3DXRD技術在工程材料研究中的巨大潛力,這主要得益于該技術對于材料內部晶粒晶體取向、形貌、位置以及局部應力的無損快速表征。
當前,對3DXRD技術還需在以下幾個方面加強研究:① 技術普及性:盡管目前大多數同步輻射光源都具備中能或高能X射線衍射線站,但能開展3DXRD實驗的寥寥無幾。這是由于3DXRD對X射線光束均勻性有很高的要求,需要特殊的聚光鏡系統。目前,我國尚不完全具備相關硬件的自主開發能力。② 數據通用性:目前,3DXRD的數據格式和分析方法主要由國際上各相關線站及部分用戶開發,缺乏統一的標準,數據與分析軟件的兼容性不足,例如線站A采集的數據往往無法用線站B開發的分析軟件來分析。解決這個問題需要全球范圍內的協作,開發統一的數據格式及分析軟件。③ 專業人員培養:3DXRD不同于普通的XRD實驗,其數據采集與分析需要專業的線站科學家和有經驗的用戶共同完成,我國將來擬在一些高能同步輻射裝置上配置3DXRD技術,不但要加強相關硬件的自主研發,也需盡快培養專門的線站科學家,建立長效的人才任用機制,這對于相關學科和技術的高質量發展至關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