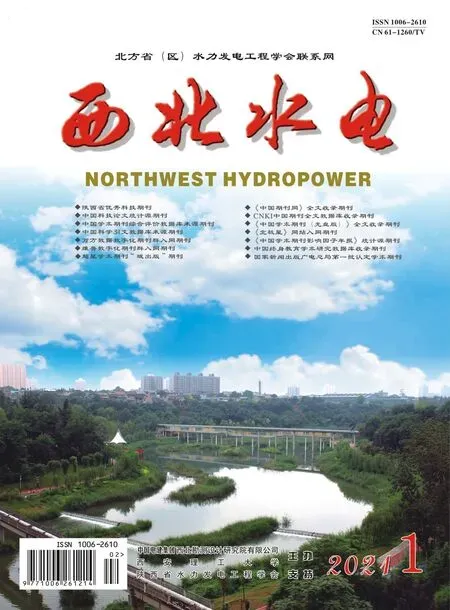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戰略解讀及頂層設計思考
任 葦
(中國電建集團西北勘測設計研究院有限公司,西安 710065)
0 前 言
2019年9月1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鄭州主持召開了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第1次將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上升為國家重大戰略[1]。如何把握這一重大戰略決策的理論背景,做到系統策劃、有的放矢、重點突出,本文通過解讀習近平總書記這一戰略的頂層設計思路,提出部分策略建議,以期有所幫助。
1 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戰略解讀
習總書記的科學戰略,可以概括為“一套理念、一個方法論、一個實踐論”,一套理念就是“堅持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堅持生態優先、綠色發展”,這兩個堅持核心是一致的,“生態優先”就是“綠水青山”的要求,“綠色發展”是發展“金山銀山”的約束條件,就是要追求人類社會與自然的和諧共生。
“以水而定、量水而行”提出了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的方法,筆者認為就是要通過科學分析人類對水的物質、精神不同需求以及人水和諧的高度,從水量、水質兩個方面的矛盾出發,解決汛期水量太多的洪澇問題、總體水資源短缺的量少問題,以及水質污染、水文化挖掘不足、生態環境惡化等問題,“量水”就是要分析水的各個方面,做到研究、決策,達到“知行合一”。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戰略方法論見圖1。

圖1 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戰略方法論圖
實踐論分別從空間和時間兩個方面提出了在戰略實施中應該注意的問題,“因地制宜、分類施策”和“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統籌謀劃”分別從區域和流域兩個角度提出空間實施原則;時間軸上,要求近期“共同抓好大保護,協同推進大治理”,遠期要“著力加強生態保護治理、保障黃河長治久安”,滿足“促進全流域高質量發展、改善人民群眾生活”的物質需求和“保護傳承弘揚黃河文化”的精神需求,最終讓黃河成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戰略實踐論見圖2。

圖2 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戰略實踐論圖
2 戰略頂層設計中的幾點思考
2.1 開展河長領導、多部委協同的頂層設計
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戰略作為重點國家戰略,需要開展系統的頂層設計。總體來講,人類對黃河流域水的物質性需求分為水量、水質兩個方面,水量不足時產生水資源時空短缺問題,水量過大即洪澇災害問題,由于人類活動造成了流域水質污染問題;而從精神需求來看,目前黃河流域水文化普遍存在千景一面、碎片開發的問題。其次,自然環境、物種生存進一步提出了“人水和諧”的要求。
從我國黃河流域管理體制來看,水量調度管理職能在水利部下屬黃河水利委員會,黃河水利委員會專門成立了黃河流城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研究中心和工程技術中心,依托多年來在黃河流域水量調配、水沙調節、堤岸治理方面的技術優勢、豐富經驗,研究方向更專注水資源、水安全、水文化方面。水環境污染防治的監督管理、保護修復等工作職能屬于生態環境部黃河局,重點在分區分類水污染防治、生態保護修復、生態環境監管等方面。岸線管控等空間管控職能在自然資源部,并承擔上下游重點濕地、中游水土流失治理、土地綜合整治、地質災害防治、生態補償機制等工作。值得注意的是,為了避免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戰略陷入“五龍治水”、各自為戰的不利局面[2],必須發揮近年來提出的“河長制”的作用,把“水資源、水安全、水污染、水文化、水生態”和岸線空間管控統一在河長的領導下,建立各部位統一協調、信息共享機制, 避免各部委在制定各自目標治理措施時出現重復、矛盾的問題。同時,黃河治理開發與流域生態保護按行政區域由相關省、自治區聯合協同進行,為確保工作持續推進,必須在河長制基礎上協調好區域、流域關系,建立行之有效的省、自治區聯席會議制度[3],建立合作協調機制。另外,筆者建議注意以下問題:
(1) 發揮信息技術作用。充分依托5G、GIS信息系統、物聯網等先進平臺技術,“一張圖繪到底”。
(2) 頂層設計可持續——銜接好過去、現在、未來。重點依托黃河已建梯級,思考其在調水調沙、生態保護中的作用,如何做好魚類保護,以及如何與后續南水北調工程銜接等問題;規劃待建的黑山峽河段樞紐如何實現防洪、調水調沙、發電、魚類保護等多目標功能。
(3) 辯證分析。既要研究政策、建設工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同時應分析其不利影響,比如水土保持對于徑流的削減到底有多少,黃河泥沙減少的不利影響有哪些,如何應對,均應系統統籌。
2.2 注重利用產業高質量發展實現可持續
建國以來,黃河流域人民生活和社會發展取得了長足發展,流域內GDP占全國的14%[4],黃河上游修建了一大批水利、水電工程,水電能源最集中的龍青段開發基本完成,三盛公、青銅峽、沙坡頭等水利樞紐為沿岸灌區農業發展提供了源源不斷的活水,但從國家對黃河流域產業布局來看,黃河流域仍然以農業和基礎能源產業為主,黃河僅相當于全國河川2%徑流量的占比,卻承擔了全國15%耕地、12%人口及多座大中型城市的供水任務[5],高耗水農業約占總用水量的65%~75%,平均灌溉水利用系數只有0.49,流域內分布“鄂爾多斯盆地基地、山西基地”兩大能源基地,其煤炭、石油、天然氣資源豐富,煤炭資源占全國一半以上,高耗水、高污染問題仍然存在。可喜的是,在朱顯謨院士提出的“黃土高原國土治理28字”方針(全部降水就地入滲攔蓄、米糧下川上塬、林果下溝上岔、草灌上坡下坬[6])指導下,我國水土保持治理工作成效顯著,該方針不僅是海綿城市理念在黃土高原的最早應用,同時是把水土保持與產業發展、人民生活提高聯系在一起的成功實踐,充分說明只有以產業高質量發展為引領,才能實現黃河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戰略目標。未來應進一步推廣塬面雨洪資源村社高效管理集中收集利用技術、“高效凈化型庭院經濟式”管理利用模式、生態水箱式道路雨洪資源的綜合試點地[7],淤地壩、集雨窖、箱等多形式聯合調配,把水土保持與雨洪利用、新型農業、鄉村振興有機結合。
以黃河下游生態廊道構建研究為例,應首先推進水安全治理與沿線產業的融合,應按照黃委提出的“洪水分級設防、泥沙分區落淤、三灘分區治理”原則進行水安全治理,結合張金良提出的“高灘三帶(水、生態、防護林)生態綜合治理、二灘高效生態旅游觀光農業、嫩灘親水濕地公園”思路[8],給黃河下游生態廊道兩岸打造綠色生態基地,結合岸線保護與利用規劃、兩岸現有產業布局及土地利用規劃,發展濱河商業、生態農業、生態文化旅游業,把產業、人居生活與“山水林田湖草沙”統一在綜合治理思路上。其次,同步推進水污染治理,按照“正本清源、雨污分流”的思路,持續做好沿線城市、農村工農業、生活污水處理,重視畜牧業、礦產業水污染治理,把水污染治理納入綜合治理,開展污染源與納污能力分析,在堤岸綜合整治、濕地建設、生態綜合治理中充分考慮植物措施、微生物措施及工程措施對水污染的作用,把水污染、水安全、水文化、水產業系統統籌考量。把傳統單一水安全治理與“生態護岸、海綿開發、滯蓄并用、污染治理、確權管理、景觀文化”等措施結合,以生態防護調度為目標,在產業政策引領下建設黃河下游生態廊道。黃河下游生態廊道綜合治理概念見圖3。

圖3 黃河下游生態廊道綜合治理概念圖
2.3 黃河流域“三軸兩圈”文化格局的暢想
習總書記提出“保護傳承弘揚黃河文化”,筆者理解應該是“保護黃河流域物質文化遺產、傳承黃河流域非物質文化遺產、弘揚黃河精神”,因此應重點梳理黃河流域物質文化和非物質文化遺產、黃河精神,筆者提出“三軸兩圈”文化格局的初步構想,為保護、傳承、弘揚黃河文化提供借鑒。
如圖4所示,黃河流域沿東西軸方向,由北向南依次分布有長城、黃河、絲綢之路3條文化軸線,此“三軸”可用“萬里長城分內外、一條大河蘊精神、絲綢之路通中西”來概括。

圖4 黃河流域“三軸兩圈”文化格局圖
萬里長城分內外:長城東起山海關、西至嘉峪關,縱橫萬里,綿延黃河流域的北側,將中國劃分為塞外、中原兩個部分,長城以北為沙漠、草原,呈現“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的自然風光,與“射雕挽弓塞外奔馳”的游牧文化相互輝映;而長城以南則“九月筑場圃,十月納禾稼”、“夜來南風起,小麥覆隴黃”,是典型的中原農耕文明。長城是中華民族以農耕文明為正統的核心文化,在與外來游牧文明斗爭過程中的產物,是重要的物質文化遺產,在游牧文明與農耕文明幾千年的攻防、互鑒中,形成了中華民族的“家國”情懷,是中國民族主義意識覺醒、形成的根源,與黃河“自強不息”的抗爭精神相互呼應。
一條大河蘊精神:這個精神,是中華民族的內蘊之神,可以劃分為“自強不息”的抗爭精神、“天人合一”的和合文化精神[9]。我們現代人稱呼的黃河母親,在古代,更多以龍的形象出現,汛期恣意肆虐、一瀉汪洋,人或為魚鱉,在中國最早的大禹治水傳說中,深刻揭示了在共同抵御大自然洪水災害中,中華民族從氏族部落向國家轉型中民族精神第1次融合、統一,黃河沿線積石峽、禹門口、龍門保留了大量的傳說遺跡,“三不過家門、股無肱、脛不生毛”的治水精神為大一統奠定了文化底色;而在抗戰時期,“黃河在咆哮”的黃河精神又一次上升為抗戰精神,以及延安精神、長征精神,是黃河“自強不息”的抗爭精神在近代民族主義國家創立過程的集中體現。而平靜時的黃河確是以母親形象潤澤中原大地,孕育中華兒女,“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大河兩岸演繹了千百年的兒女情長,“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先哲在黃河邊上感悟人生,形成了“道法自然”、“利萬物而不爭”的和合文化。這兩種黃河文化共同鑄就了民族核心精神。
絲綢之路通中西:是連接中國腹地與歐洲諸地的陸上商業貿易通道,同時是一條東方與西方之間經濟、政治、文化進行交流的主要道路。2014年,中、哈、吉3國聯合申報的“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成功申報為世界文化遺產。絲綢之路既是佛教、阿拉伯數字等外來文化,番茄、葡萄等外來物種的引進之路,同時也是中國儒學文化、瓷器、絲綢等文明輸出的通道,促成了以敦煌、長安、洛陽等為中心的儒釋道多文化繁榮,不同文化風格的建筑、書畫、詩歌薈萃,形成了獨特的中國意趣。
“兩圈”分別是以西安為核心的“漢唐”文化都市圈,和洛陽、開封為中心的“河洛”、宋代文化都市圈,與以北京為中心的明清文化圈相呼應。漢唐文化圈以積極進取、大氣恢弘為特色,建筑風格達到了力與美的統一。而色調簡潔明快,屋頂舒展平遠,給人莊重、大方的印象,展現了一個民族上升時期的自由、開放的精神取向;而宋代文化都市圈以市民文化興起為代表,這一時期的建筑,注重自然美與人工美融為一體的意境,建筑物的屋脊、屋角有起翹之勢,展現了中國文化歷史中的豐盛時期詩意人生的精神取向。
黃河流域精神文化特征,呈現出與長江流域截然不同的氣象,總體來看黃河文化所代表的“蒼涼、雄渾、恢弘”成為豪邁派形成的根,與長江流域“杏花煙雨江南”的婉約形成對比,如豪放派詞:須關西大漢、銅琵琶、鐵綽板,唱“大河向東流、天上的星星參北斗”。北方的陜西刀客、關東大漢、水泊梁山都與黃河文化息息相關。實際水文化景觀塑造中,可按照“適用、經濟、綠色、美觀”的建筑方針、融人性、統一性、差異性、通達性、生態性低影響開發等六大原則,發揮黃河等水域體在景觀營造中的統一、聯系、聚焦、分割、賦韻等作用[10],充分展現、塑造中華民族的黃河魂。
3 結 語
本文通過系統解讀習總書記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戰略精神,從開展河長領導、多部委協同和注重利用產業高質量發展兩個方面,提出在頂層設計中應避免出現各部委“五龍治水”的割裂,并應重視以產業引領實現可持續的建議。同時暢想了黃河流域“三軸兩圈”文化格局,以期為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頂層設計提供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