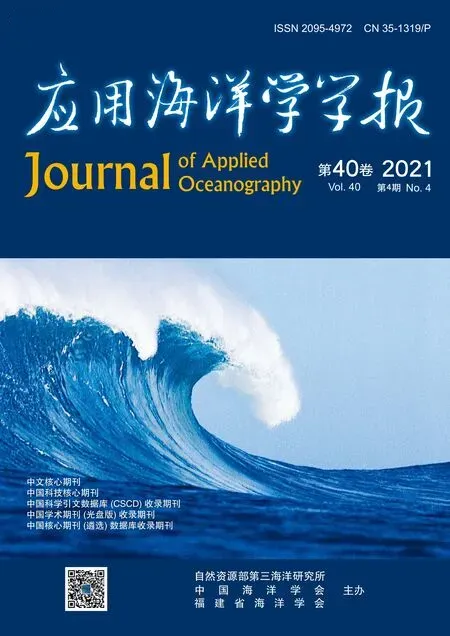我國近海大型海藻生態修復策略與典型案例
何培民,段元亮,劉 巧,劉金林,劉 煒,張建恒,3,方建光,蔣增杰,吳海龍,李信書,湯坤賢,李可俊,李娟英,3,趙 爽,常佳楠,張建琳,包炎琳,趙子滔,張梅菁
(1.上海海洋大學海洋生態與環境學院,上海 201306;2.上海海洋大學水產種質資源發掘與利用教育部重點實驗室,上海 201306;3.自然資源部大都市區國土空間生態修復工程技術創新中心,上海 200003;4.中國水產科學研究院黃海水產研究所,山東 青島 266000;5.江蘇海洋大學,江蘇 連云港 222005;6.自然資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福建 廈門 361005)
海洋生態系統(Marine Ecosystem)在維系自然界物質循環、凈化環境、緩解溫室效應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21世紀是“海洋世紀”,但人類活動對海洋不合理開發使得海洋生態環境變得更為脆弱,海水污染、資源浪費、資源枯竭等海洋環境問題日益突出。2005年,國際千年生態評估計劃報告指出,由于經濟發展和生態資源過度開發,全球超過60%的海洋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在退化,其中超過35%的紅樹林和超過20%的珊瑚礁被破壞,另有20%的珊瑚礁正逐步退化;部分地區海岸帶濕地損失已超過30%[1]。至今全世界仍然有三分之一的海岸生態系統處于嚴重退化狀態[2]。
我國近岸海域富營養化仍然比較嚴重,致使近海藻華生態災害頻繁發生。2000—2019年期間,我國近海平均每年單細胞有害藻華事件達50~80次[3],2007年起我國黃海已連續15 a大規模暴發綠潮,且近年來金潮暴發正演變為我國新型海洋生態災害。上述生態災害嚴重威脅國家海洋生態安全,近海富營養化防治已刻不容緩。
本研究針對我國近海富營養化問題,分別介紹了近海生態修復工程技術及封閉海域、半封閉海域、開放海域水體生態修復效果,旨在為我國近海富營養化海域生態治理提供參考。
1 我國近海環境現狀仍然十分嚴峻
隨著國家和各級政府不斷發力,近海生態環境整體趨好,環境惡化勢頭逐步遏制,但我國海洋生態環境現狀仍然十分嚴峻,富營養化問題依舊突出。
1.1 我國近海陸源排污和水產養殖自身污染趨勢
陸源污染物持續輸入是導致我國近海富營養化加劇的主要原因。據報道,陸源排放對近岸海域的污染貢獻占70%以上[4]。2007—2017年期間,我國每年大約有1 102~1 653萬噸化學需氧量(COD)、164~237萬噸硝態氮、15.0~60.7萬噸氨氮、5.0~7.6萬噸亞硝態氮、18.0~35.9萬噸總磷等通過河流直接排入近海。其中2010—2017年期間,直排海污染源廢水中硝態氮、亞硝態氮排放量總體不變,而氨氮、總磷、COD分別下降64.57%、42.64%、57.96%[5]。
我國近海水產養殖投喂餌料造成的污染不容忽視。由于海水網箱養殖過程中大量投飼野雜魚,餌料系數最高可達1∶7,這對附近海域造成巨大營養負荷[6-7]。徐姍楠等(2008)[8]曾對象山港網箱養殖區調查發現,網箱中心區營養狀態指數(E)超標31倍。海水網箱養殖每養成1噸魚類,向環境輸入氮、磷分別高達161 kg和32 kg[9]。挪威峽灣地區大西洋鮭(Salmosalar)網箱養殖環境監測數據顯示,每生產1噸大西洋鮭,則向環境中排放11 kg溶解無機氮和1.81 kg溶解無機磷[10]。我國是海水養殖大國且養殖產量逐年遞增,2019年我國海水養殖產量為2 065.33萬噸,其中魚類養殖產量已達160.58萬噸。如果平均按照1∶3餌料系數計算,大約使用了480萬噸餌料投喂,這相當于有320萬噸餌料直接進入海水,使近海富營養化進一步加劇。
1.2 我國近海富營養化依然嚴重,赤潮、綠潮、金潮三潮齊發
2010—2019年夏季我國近海未達到I類水質海域約為9×104~18×104km2,呈現逐年下降趨勢,這說明水質在逐漸變好。2019年夏季我國近海未達到I類水質海域面積最低,總面積為89 670 km2,其中II類、III類、IV類、劣IV類水質海域面積分別為34 330、18 440、8 560、28 340 km2。2012—2019年夏季,我國近海富營養化面積約為5×104~10×104km2,總體亦呈下降趨勢,特別是輕度富營養化面積下降更為明顯。2019年夏季我國近海富營養化海域總面積為42 710 km2,與2012年相比,下降60%左右[11],其中東海富營養化海域面積最大,為32 190 km2[5],占我國近海富營養化海域總面積75.4%,應列為重點防控區。
近年來,由微藻和大型藻類形成的有害藻華事件持續增加。2007—2019年,我國近海每年赤潮暴發數量和面積分別為35~82次、1 991~14 102 km2,總體呈下降趨勢[11]。自2007年以來,我國黃海連續每年暴發綠潮,2007—2019年間我國黃海每年綠潮暴發涉及面積為1 500~58 000 km2,最大覆蓋面積為21~2 100 km2,每年對山東、江蘇省近海生態、漁業和旅游業造成重大影響[12]。2020年自然資源部在江蘇輻射沙洲紫菜養殖筏架海區開展綠潮源頭防控試驗,防控效果顯著,黃海綠潮暴發最大面積與2019年相比約減少了60%,這為今后黃海綠潮防控與治理工作奠定了堅實基礎。此外,2012年上海海洋大學何培民教授團隊在長江口附近海域發現大規模金潮,面積超過400 km2;2017年初,金潮銅藻侵襲江蘇省輻射沙洲條斑紫菜(Neoporphyrayezoensis)養殖區,造成經濟損失約5億元[13-15]。
2 我國近海富營養化海域生態修復方法與策略
2.1 生態修復定義與主要方法
生態修復(Ecological Remediation/Restoration)是指協助受損和退化的自然生態系統進行恢復、重建和改善的過程。具體說,生態修復是在生態學原理指導下,以生物修復為基礎,結合物理修復、化學修復及工程技術措施,通過優化組合,使之達到最佳效果和最低耗費的一種綜合修復污染環境的方法[16]。國內外治理海域污染采用的方法主要有:物理方法、化學方法、生物方法等3類。其中物理方法成本較高;化學方法易造成二次污染,多應用于局部海域突發事件;而生物方法成本低、對環境友好、易規模化,被科研人員廣泛應用于多種場合[17]。
2.2 近海富營養化海域生態修復策略
我國近海海域面積遼闊,而近海環境最突出的問題是氮、磷濃度超標[17]。因此,開展海洋生態修復工作迫在眉睫。近海海域生態修復是利用生物本身的生理特性治理水體富營養化,目前主要有植物修復、動物修復、微生物修復等方式。其中,水生植物修復是治理富營養化水體氮、磷污染的重要手段,用于海域生態修復的海洋水生植物主要有紅樹、濱海鹽沼植物、海草、大型海藻、浮游植物等,其中紅樹林、濱海鹽沼植物、海草場、海藻場為降低海洋富營養化做出了重大貢獻。
大型海藻栽培已被國內外公認為近海富營養化海域生態修復的最佳途徑之一,也是現階段應用于海洋生態系統修復最多的生物[8]。開展大型海藻栽培可一舉多得[18-19]:①通過海上人工大規模栽培生產大量海藻生物質,加工為海藻健康食品或工業原料,獲得巨大經濟效益;②大型海藻栽培大量吸收海水中的無機氮、磷等物質,顯著緩解海區富營養化狀態,并抑制赤潮發生;③大型海藻通過光合作用大量吸收CO2和碳酸鹽(碳匯),并提高海水pH值,防止海洋酸化;④海藻葉片可為海洋動物提供優質隱蔽的棲息地、產卵地及繁殖地,并可提供天然餌料。2019年,我國大型海藻總產量為254萬噸[20],按照藻體中氮、磷、碳元素平均含量計算[21],我國僅大型海藻栽培產業,就直接從近海富營養化海水中移出57.6萬噸碳、11.52萬噸氮、5 760噸磷。焦念志(2021)[22]估算我國大型海藻初級生產力(固碳量)為3.52 Tg/a,其中移出碳通量0.68 Tg/a。
2.3 近海富營養化海域生態修復發展趨勢
將海洋水生植物、海洋動物修復和微生物修復方法相結合,通過生態系統和食物鏈等人工操縱手段,以期達到更好的生態修復效果。目前國內外在大型海藻規模化栽培和海藻場基礎上,構建了近海海域多營養層級綜合養殖系統(Integrated Multi-trophic Aquaculture,IMTA)、海洋牧場(Marine Ran-ching),利用“藻-貝-魚”人工生態系統凈化和修復近海生態環境,并通過海洋生物資源增殖,進一步保護和養護海洋生物棲息地,在保護生態環境前提下實現經濟效益最大化,這有望成為近海生態修復的主流模式。
3 近海海域大型海藻生態修復基本模式
近海海域大型海藻生態修復基本模式主要有大型海藻栽培、構建海藻場2種模式。
3.1 大型海藻栽培生態修復模式
我國是大型海藻栽培大國,大型海藻栽培產量一直位居世界之首。我國沿海主要栽培海帶(Saccharinajaponica)、裙帶菜(Undariapinnatifida)、羊棲菜(Hizikiafusifarme)、鼠尾藻(Sargassumthunbergii)、銅藻(Sargassumhorner)、條斑紫菜、壇紫菜(Neoporphyrahaitanensis)、龍須菜(Gracilarialemaneiformis)、真江蘺(Gracilariaverruco)、麒麟菜屬(Eucheuma)、石花菜(Gelidiumamansii)、紅毛菜(Bangiaatropurpurea)、石莼(Ulvalactuca)、礁膜屬(Monostroma)、滸苔(Ulvaprolifera)等種、屬[19]。我國已形成了山東省海帶和裙帶菜、江蘇省條斑紫菜、福建省和廣東省龍須菜等大規模人工栽培藻場,區域內每年很少發生赤潮災害[23-24],栽培期間海區水質甚至可高達I—II類[25],可見生態修復效果十分明顯。其中,桑溝灣海帶栽培海區研究表明,海帶產量以8.45萬噸計算,每年可移出2.8萬噸碳和1 538噸氮[26];江蘇省輻射沙洲條斑紫菜栽培區研究結果表明,266.6 km2條斑紫菜栽培和收獲可移除3 688.15噸氮和105.61噸磷[27]。江蘇省連云港海州灣紫菜養殖區研究顯示,2018年江蘇省海州灣2.7×108m2紫菜養殖區年產條斑紫菜1.05萬噸,可固氮量約為569.1噸[28]。半封閉海灣象山港海帶栽培海區研究表明,每年象山港可移除297噸氮和42噸磷[29];南澳深澳灣龍須菜栽培海區研究表明,15 km2的龍須菜栽培和收獲可移除2 212噸氮、174噸磷和1.33萬噸碳,并釋放氧氣3.47萬噸[24]。
3.2 海藻場生態修復模式
海藻場(Seaweed Bed,也稱海藻床)生態系統是一種以大型底棲藻類為主,輔以其他浮游生物、游泳動物、底棲動物等生物群落共同構成,位于水深20~30 m以內的硬質底質上的海洋生態系統[30-31]。該生態系統是海洋中初級生產力最高的區域之一,其初級生產力占全球海洋初級生產力的10%~30%,在海岸帶海域發揮著重要的生態功能:減緩水流、形成魚蝦貝類生息場所、吸收氮磷等營養鹽、固定CO2等[31-33]。因對海藻場保護不太重視,全球海藻場退化十分嚴重。我國海藻場研究起步相對較晚,2017—2019年上海海洋大學章守宇教授團隊對我國沿海從南到北(海南10個、廣西4個、廣東3個、福建6個、浙江8個、江蘇1個、山東10個、河北3個、遼寧7個)共52個區域的40個海藻場進行了實地調查,發現最高平均生物量可達30 kg/m2,主要優勢種為銅藻、海帶、裙帶菜、海黍子(Sargassummiyabei)、海蒿子(Sargassumpallidum)、瓦氏馬尾藻(Sargassumvachellianum)、亨氏馬尾藻(Sargassumhenslowianum)和匍枝馬尾藻(Sargassumpolycystum)等[31]。
為防止海藻場的繼續衰退,我國在山東、浙江、福建、廣東等沿海省份均實施了不同規模的海藻場修復工作[34-37]。其中,山東省長島已投入大量資金構建海藻場,通過改善水質以吸引海參和海膽等珍貴海洋動物棲息,提高漁民經濟收入。浙江省南麂列島先后開展銅藻、羊棲菜、鼠尾藻、海帶等大型海藻場建設,涉及海域面積150 hm2,核心區面積30 hm2;浙江省枸杞島銅藻場達1.5×104m2、瓦氏馬尾藻場達2×104m2,福建省平潭壇紫菜海藻場達5 000 m2[38]。此外,中國水產科學研究院南海水產研究所黃洪輝研究員團隊在深圳和惠州大亞灣分別構建了1 600 m2和8 500 m2的馬尾藻場。
4 大型海藻生態修復案例
4.1 上海市金山城市沙灘封閉海域生態修復案例
2004—2006年,上海市金山區政府在杭州灣北岸建設了封閉海域城市沙灘,面積為1.75 km2,水源取自杭州灣海域。圍隔堤壩合攏時水體為劣IV類海水,富營養化十分嚴重,浮游植物密度幾乎達到赤潮暴發臨界水平。
2006—2008年,上海海洋大學何培民教授團隊在城市沙灘圍隔海區首次使用大面積栽培大型海藻真江蘺的方法進行生態修復,發現大型海藻栽培對富營養化封閉海區具有顯著生態修復效果。2006年9月開始大規模栽培真江蘺,1個月后與非修復區相比,修復區水體活性磷幾乎檢測不出,無機氮已達到I類水質標準,修復區氨態氮、硝態氮、亞硝態氮、活性磷分別降低了92.0%~92.8%、34.7%~78.7%、46.5%~88.3%、49.8%~100.0%,高錳酸鹽指數(CODMn)、5日生化需氧量(BOD5)、葉綠素a(Chl a)含量分別降低了19.4%~28.9%、18.0%~39.4%、22.6%~70.3%,溶氧(DO)含量比對照區增加6.8%~19.4%,水體透明度增加2.7%~12.6%。修復區海水水質自2006年11月起均轉變為I~II類,其中2006年12月至2007年2月間均為I類海水。2006年10月至2007年5月間營養狀態指數均小于1。6個月后水體中已檢測不出氨態氮,透明度由原先的0.5 m提升至3.0~6.0 m。栽培真江蘺后,整個封閉海域浮游藻類密度一直控制在1×107個/m3以下。封閉海域大型海藻生態修復匹配模式估算表明,維持1.72 km2封閉海域常年處于II類均值水質,需栽培真江蘺18.0噸,維持海區常年處于I類均值水質,需栽培真江蘺21.8噸[8]。
4.2 山東省半封閉海域桑溝灣多營養層級生態養殖生態修復案例
桑溝灣是位于我國山東半島的半封閉海灣,面積約144 km2,是我國重要的規模化海水養殖海灣。該灣自20世紀50年代開始就開展了海帶筏式養殖,目前主要養殖種類為海帶、長牡蠣(Crassostreagigas)、櫛孔扇貝(Azumapectenfarreri)、刺參(Oplopanaxelatus)、皺紋盤鮑(Haliotisdiscus)等,其中海帶年產量約8萬噸(干重),長牡蠣產量6萬噸,櫛孔扇貝1.5萬噸。多年來,桑溝灣海帶養殖一直處于主體地位,隨著養殖種類多樣化,逐步實踐并發展了大型海藻、貝類、海參、魚類等多種多營養層次生態養殖模式,其中以“海帶-鮑-海參”、“海帶-牡蠣-海參”等形式的筏式多營養層級生態養殖模式,以及鰻草(Zosteramarina)床海區海珍品底播生態養殖模式的應用最為廣泛,并取得了顯著的經濟、生態、社會效益[39-41]。以“海帶-鮑-海參”多營養層級生態養殖模式為例,每個養殖單元(4條浮梗)可增加產值1.68萬元,綜合效益提高30%以上,所提供的食物供給功能服務價值遠高于鮑單養和海帶單養,價值比分別為2.06∶1和9.83∶1[42]。多營養層次生態養殖模式在提供優質蛋白、產生經濟效益的同時,還兼具水質調控、氣候調節等生態服務功能。據估算,桑溝灣海帶養殖每年可移除2.8萬噸碳和1 538噸氮[26];年際尺度的溶解無機碳收支估算結果表明,桑溝灣整體表現為“碳匯”,固碳強度達1.39×105噸/年[43]。國內外多種不同方法的研究均證實,桑溝灣規模化養殖雖已開展了30多年,但水質和沉積環境質量仍保持在Ⅰ類水平[44-45]。近些年來,以多營養層級生態養殖模式為核心的“桑溝灣模式”在世界范圍內得到了廣泛認可[46]。2016年,聯合國糧農組織(FAO)和亞太水產養殖中心網絡(NACA)將桑溝灣生態養殖模式作為亞太地區12個可持續集約化水產養殖的典型成功案例之一,并向全世界進行了推廣[47]。
4.3 江蘇省開放海域大型海藻栽培生態修復案例
江蘇沿海輻射沙洲作為世界最大的潮間帶輻射狀水下沙脊,其灘涂面積日益淤積擴大,生態系統區域特色鮮明。然而,據海洋環境質量公報顯示,陸上污染輸入耦合內源養殖污染使該海域富營養化明顯,環境質量退化嚴重。
自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輻射沙洲海域逐漸形成了以經濟紅藻條斑紫菜為主要栽培品種的海水養殖產業。隨著人類對海藻食品和產品需求的日益提高,其栽培面積和產值也不斷增加,已形成價值200億的條斑紫菜行業經濟產業鏈,且基于條斑紫菜生態修復潛力而建立的生態修復模式和牧場經濟也逐步形成。因此,對輻射沙洲海域條斑紫菜栽培牧場生態修復能力和碳匯貢獻的研究已成為在該海域建立生態修復手段和策略的重要基點。2013—2014年上海海洋大學何培民教授團隊對輻射沙洲海域開展的全年水質監測結果顯示,輻射沙洲海域條斑紫菜核心栽培區(養殖面積約133.3 km2)營養鹽濃度顯著低于非養殖區,通過栽培和采收每月可移除8.04~1 495.72噸氮和0.19~43.86噸磷,栽培季節總共移除3 688.15噸氮和105.61噸磷。栽培133.3 km2的條斑紫菜可使輻射沙洲離岸5 km至100 km海域水體氮指標達III類海水標準,磷達到II類標準。條斑紫菜栽培總產量約5.895萬噸(干重),總銷售額達65.08億元[27]。
5 結論與展望
綜上所述,大型海藻規模化栽培對富營養化海域具有十分顯著的生態修復效果。我國近海富營養化比較嚴重,頻繁引起藻華災害發生[48-49],為此,我國更需要發展大型海藻栽培產業,并通過規范有序開展規模化大型海藻栽培和收獲,有效控制和削減近海富營養化程度,最終抑制赤潮、綠潮、金潮等發生。同時,大型海藻也是一種健康海產品,具有較高的經濟價值,目前我國海藻產業已達2 000多億元,可見大型海藻栽培產業的發展不但可以治理近海富營養化環境問題,還可以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美國前藻類學會主席Charlie Yarish教授在2014年世界養殖大會上就提出應用大型海藻經營海洋污染物的理念,即通過大型海藻把海洋污染物轉化為經濟價值的產品,這與我國現在倡導的污染物資源化利用理念相一致。若我國能更好地發展多營養層次生態養殖、海洋牧場等模式,將會帶來更大的經濟效益。總之,研究人員需堅守“自然修復為主,人工修復為輔”的生態修復理念,在沿海富營養化海域治理過程中,上述生態修復工程技術有望得到廣泛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