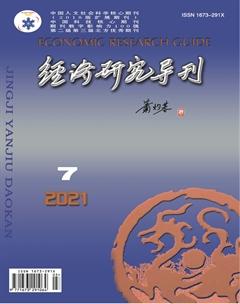知識產權保護對企業創新績效的影響
李佩澤 周敏



摘 要:基于2006—2018年我國上市公司的面板數據,運用擴展的Griliches-Jaffe知識生產函數,對知識產權保護水平與企業創新績效之間的相關關系進行實證分析。研究結果顯示,兩者之間存在顯著的倒“U”型關系,且我國當前除西藏自治區外,其余各省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均高于“最優知識產權保護水平”,進一步研究發現,第二產業的“最優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略高于第三產業。因此,建議政府在完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時,應該細化相關法律法規,針對不同行業、不同地區采取針對性的知識產權保護政策。
關鍵詞:知識產權保護指數;創新績效;個體固定效應模型
引言
隨著傳統成本優勢的漸漸喪失,我國也正在逐步轉向以技術創新為特點的經濟發展模式。創新作為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在這個新冠肺炎疫情對全球經濟沖擊以及中美貿易摩擦對我國出口抑制的大背景下,更顯得尤為重要。作為技術創新的主體,企業是我國發展成為創新強國的中堅力量,其研發創新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代表著我國的自主創新水平。而在關于企業創新影響因素的相關研究中,知識產權保護是十分重要的因素之一。我國黨中央一直非常重視知識產權保護工作,改革開放以來,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規,并一直對包括法律法規在內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進行修改、完善。近日,習近平總書記更是指出,要完善知識產權保護法律體系,大力強化相關執法,加大知識產權民事和刑事司法保護力度。知識產權保護一方面可以捍衛產權擁有者的權益,使其成果不被他人盜取、利用;另一方面,知識產權的過度保護又會使得產權擁有者獲得較長時間的壟斷權,增加他人技術創新的成本,抑制技術的傳播和推廣。那么,知識產權保護對企業的自主創新到底起到促進、抑制還是有更復雜的關系?在我國當前的國情下,制定怎樣的知識產權保護政策是最有助于企業創新發展的?
著名經濟學家Helpman通過推導得出技術進步模型在南北國家框架下的穩態均衡解,發現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水平會強化創新者的壟斷權力,提高學習成本,從而降低技術創新的利潤期望。也就是說,北方國家鞏固其自身在全球市場中所占份額是以犧牲南方國家產業發展作為代價的,這樣下去最終會導致全球技術進步速度放緩[1]。張建忠等學者基于全球價值鏈治理者控制的視角,認為嚴格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雖然可以吸引更多的全球鏈治理者,使其將技術和訂單向發展中國家轉移,但是同時也會降低發展中國家本土企業代工的機會成本,導致更多本土企業并沒有著眼于技術創新,反而加入了代工行列[2]。吳超鵬等學者基于跨省比較的視角,通過實證分析發現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的執法力度,可以通過緩解外部融資約束和減少溢出損失兩條路徑來促進企業的創新行為[3]。李俊青等學者則以企業出口技術復雜度為視角,通過博弈論的方法,解釋了在不完全契約的條件下,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可以降低供應商被制造商“敲竹杠”的風險,激勵企業投資高技術活動,從而促進社會技術水平的提高[4]。不論是積極影響,還是消極影響,前面梳理的相關研究均認為知識產權保護與技術創新之間的關系為線性關系,但在2004年,ODonoghue等學者從知識產權廣度的角度,首次提出知識產權保護與技術創新之間存在倒“U”型關系的假說[5]。中國學者劉小魯也提出,對于后發國家而言,提高知識產權保護水平會使得對本國和國外研發成果的保護同時加強,既能促進本國的技術創新活動,同時也會使得國外已有成果對本國創新活動阻礙程度加強[6]。
已有的研究主要是通過構建理論模型來推導知識產權保護與技術創新的關系,對該領域的理論研究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也有一些學者通過構建國家層面的知識產權指數,并以國家層面或省際層面的技術創新指標作為面板數據對知識產權保護與創新產出之間的關系進行實證分析,為相關研究提供實證證據,但是作為技術創新主體的企業卻少有被作為研究對象。同時,已有的研究僅僅以制造業為研究范圍,忽略了日益壯大的第三產業。所以,本文希望結合上述問題,在以下幾個方面提出建議。
第一,在知識產權保護強度的測算方面,基于對前人研究的梳理和總結,本文從立法、執法兩方面對知識產權保護水平進行測度。在立法方面,在以往研究僅對專利權保護水平進行測度的基礎上,加入了對商標權和版權保護強度的測度,更加準確全面地度量出我國實際的立法水平;在執法方面,由于我國各省雖然在立法方面水平一致,但各省因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差異,執法水平參差不齊,所以本文基于跨省比較的視角,對各省的執法水平進行測量,構建出省際知識產權保護強度指數。
第二,在研究對象方面,本文基于上市公司的數據來檢驗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對企業創新的影響,相比于選用國家層面和省級層面數據,上市公司的數據在控制變量方面更加全面,結論更具有說服性。
第三,在樣本選擇方面,本文選用了全行業的上市公司數據,并且將其分為第一、第二和第三產業,對其異質性進行分析比較,為我國的產業發展和技術創新提供更加可靠且具體的政策建議。
一、知識產權保護指數的構建
根據對以往相關文獻的梳理,國內外學者對知識產權保護強度的度量方法主要為問卷調查和構建指數兩種方法,而Ginarte和Park在1997年提出的G-P指數被大多數學者所采用,該指數通過一系列指標來測算一國的知識產權立法水平[7]。但對于我國這種司法體系還處于正在完善階段的發展中國家,由于立法水平與司法水平尚未完全同步,采用上述方法度量出的保護強度與實際情況可能并不相符,所以,許多國內學者在G-P指數的基礎上進行改良,構建更加符合我國國情的知識產權保護指數。許春明等學者在以G-P指數度量我國知識產權立法程度的基礎上,從司法保護水平、行政保護水平、經濟發展水平、社會公眾意識以及國際監督五個方面來測度我國知識產權保護的執法力度[8]。但是G-P指數僅能代表專利法的特征,而版權作品和商標的價值對經濟增長具有同樣重要的影響,G-P指數無法完整地反映知識產權立法的水平。因此本文在以往學者構建的知識產權保護強度指數的基礎上,從立法和執法兩方面對其進行改進,基于跨省比較的視角,創造性地構建能夠更準確度量我國各省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的指數。
(一)知識產權保護立法指數
本文借鑒G-P指數對專利立法水平的評價方法和標準,在其基礎上針對我國實際情況進行改良,分別計算出專利權、版權、商標權的指數,然后將三者通過熵值法確定權重,得到綜合的知識產權保護立法強度指數。
1.專利權指數。專利權指數下設5個一級指標,每個指標滿分為1分,每個指標下設n個二級指標,每滿足一個二級指標即可獲得1/n分。一級指標包括:一是保護范圍;二是國際條約成員資格,即從條約生效開始算起,對我國開始生效得1/n分,n為當時已生效條約數(下同);三是權利限制;四是執行機制;五是保護期限。由于我國對于發明專利、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三種專利的保護期限不同,所以給每一項賦予權重1/3。專利權指數的總分分數范圍在0—5分。
2.商標權指數。商標權指數下設5個一級指標,每個指標滿分為1分,每個指標下設n個二級指標,每滿足一個個二級指標即可獲得1/n分。一級指標包括:保護范圍、國際條約成員資格、權利限制、執行機制、保護期限。商標權指數的總分分數范圍在0—5分。
3.版權指數。版權指數下設6個一級指標,每個指標滿分為1分,每個指標下設n個二級指標,每滿足一個個二級指標即可獲得1/n分。一級指標包括:保護范圍、國際條約成員資格、專有權范圍、權利限制、執行機制、保護期限。版權指數的總分分數范圍在0—6分。
為使求得的知識產權保護立法強度指數更加符合我國實際情況,本文通過熵值法確定三者的權重,其中專利權占比46%,商標權占比29%,版權占比25%,立法指數的分數范圍為0—5.25。
(二)知識產權保護執法指數
本文從司法保護水平、行政保護水平、社會公眾意識和國際監督四個方面來度量我國各省知識產權保護的執法強度,每項滿分為1分,知識產權保護執法強度指數的總分分數范圍為0—4分。
1.司法保護水平。司法保護是解決知識產權糾紛的主要途徑,主要是通過提起侵權訴訟來實現的,司法保護的水平可以直接影響知識產權立法在實際中的體現。本文以“律師人數占比”,即律師人數占各省常住人口的比例來度量各省的司法保護水平。當該省“律師人數占比”不低于0.0005時,得1分,當“律師人數占比”小于0.0005時,得分為實際比例/0.0005。
2.行政保護水平。知識產權的行政保護主要是由各省知識產權局及其地方的分支機構負責的,本文以“專利未被侵權率”,即1-省知識產權局專利侵權糾紛累計立案案件數除以該省截至當年累計授權專利數,用以衡量知識產權的行政保護水平。該數值越高,表示該省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越高。
3.社會公眾意識。社會公眾意識是指公眾對知識產權保護的意識強弱,一般認為,社會公眾意識與社會公眾的受教育程度成正比例關系。因此,本文用“1-各省的文盲半文盲占15歲及以上人口的比例”的值來衡量各省份的社會公眾知識產權意識。
4.國際監督。由于世貿組織對于其成員知識產權保護的最低標準以及爭端解決機制有明確地規定,所以加入世貿組織無疑對我國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且該影響并不是在加入時突然產生從0—1的質的飛躍的。本文借鑒許春明等人的方法,假設我國從1986年復關談判開始到2005年加入世貿組織第五年,國家監督指標從0均勻地變化到1[8]。
(三)知識產權保護指數
知識產權保護指數是立法強度和執法強度的綜合結果,計算方法如下:
IPRp,t為p省在t年的知識產權保護指數,Lt為我國在t年的知識產權保護立法指數,Ep,t為p省在t年的知識產權保護執法指數,IPRi,t為i公司所在省份的知識產權保護指數。知識產權保護強度指數的總分范圍為0—21分。圖1為1990—2018年我國知識產權保護指數的趨勢圖,從圖中可以看出,我國知識產權保護水平一直在穩定上升,并且在2000年和2008年出現兩次跨越式的增長,這是由于在這兩段時間左右,我國先后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進行了較大程度的修訂和完善。由此可見,我國政府對知識產權保護體系的完善工作十分重視[9]。
二、研究設計變量說明和數據來源
(一)研究設計
本文基于Griliches-Jaffe知識生產函數的思想,認為新知識的產出由研發支出和研發人員兩大投入要素所決定,其公式如下:
式中,?滋i,t為隨機擾動項。為了檢驗知識產權保護對我國高新技術企業創新的影響,將知識產權保護指數IPR也納入式(2)中,并且考慮到在企業創新過程中,還有很多因素會對創新能力產生影響,所以將企業層面的控制變量Control和省份層面的控制變量Province也納入式(2)中。本文采用專利申請量Patent作為衡量企業創新能力的指標[10],由此可以構建擴展的知識生產函數,得到以下模型:
考慮到技術創新的延續性以及研發投入對產出的時滯性影響,在式(4)中加入滯后一期的被解釋變量,并且將研發支出和人員投入均采用滯后一期的值。這種做法不僅可以得到企業技術創新的動態特征,還可以克服遺漏變量問題,使得回歸結果更加準確。引入滯后項的動態模型為:
(二)變量說明
通過對前人關于企業技術創新影響因素的相關文獻梳理,本文選取的企業層面的控制變量有企業規模、企業年齡、企業性質、資產流動性、財務杠桿、凈資產收益率以及無形資產率,省際層面的控制變量為該省份經濟發展水平。同時,由于數據庫中研發人員數量這一數據缺失比較嚴重,本文假設研發人員占公司總員工人數比例保持穩定,用企業員工總數量來替代研發人員數量指標,具體內容如表1所示。
(三)數據來源
由于財務部在2006年2月15日發布的《企業會計準則第6號——無形資產》對原準則中關于企業研究與開發費用統一計入當期損益的會計處理做了較大修改,因此2006 年以前的研發投入數據與2006 年之后的數據不具可比性。因此,本文以2006—2018年全行業上市公司作為初始樣本,從中剔除ST、*ST、PT、退市以及公司,因為這類公司在經營和研發等數據方面存在異常,在此基礎上剔除關鍵數據缺失的樣本,最終得到2 660家公司的16 745組數據。本文中,上市公司的專利數據、研發數據來自CNRDS數據庫,財務數據和其他基礎數據均來自Wind和CSMAR數據庫。構建知識產權保護強度指數所需的省際數據來自國家統計局、《中國律師年鑒》《中國社會統計資料》《中國衛生健康統計年鑒》和各省的《統計年鑒》,各省專利數據和專利侵權糾紛數據源自CSMAR數據庫。
三、實證分析
由于各企業之間存在著除上述控制變量以外的差異,如對自主研發創新的積極性等因素,為了盡可能減少回歸結果的偏差,本文運用個體固定效應模型,模型(1)、模型(2)和模型(3)分別對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對企業創新的影響進行回歸分析,回歸結果如下頁表2所示。模型(1)為對知識產權保護與企業技術創新之間線性關系的回歸分析,可以看到,知識產權保護水平與企業創新績效之間存在著顯著的負相關關系,說明對總體而已,繼續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會抑制企業的技術創新[11]。模型(2)為對知識產權保護與企業技術創新之間非線性關系的回歸分析,可以看到,知識產權保護水平與企業創新績效之間存在著顯著的倒“U”型關系,這一結果驗證了Park提出的“最優知識產權保護假說”。計算得出,該倒“U”型的拐點為13.9,即我國的最優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為13.9。在計量樣本中,有86.6%的樣本位于拐點左右側,也就是說,在2006—2018年這13年里,知識產權保護對我國上市公司技術創新能力的作用效果絕大多數是處于隨著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的提高而減弱的區間范圍。通過對2018年我國各省知識產權保護水平與拐點的比較,僅有西藏自治區的知識產權保護指數小于13.9,即當前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強度僅對西藏自治區的企業創新有促進作用。模型(3)為考慮到技術創新的延續性以及研發投入對產出的時滯性影響后,對知識產權保護與企業技術創新之間非線性關系的回歸分析,從結果可以看出,在考慮了技術創新的延續性以及研發投入對產出的時滯性影響后,知識產權保護水平與企業創新績效之間依然存在著顯著的倒“U”型關系,此時的拐點為13.7。通過比較,就2018年各省的知識產權保護強度而言,當前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強度依舊僅對西藏自治區的企業創新有促進作用。
表2后三列為對知識產權保護對三大產業技術創新影響的異質性回歸分析,對三大產業的劃分以2012年修訂的《三次產業劃分規定》為標準。從表中可以看出,對于第一產業來說,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對其企業的技術創新并無顯著影響,原因為第一產業包括農、林、牧、漁業,該產業中企業主要從事的工作是從大自然中獲取并生產不必經過深度加工的產品,自身對技術創新的需求小,所以知識產權保護政策對其并無顯著影響。對于第二產業,知識產權保護水平與企業創新績效之間呈顯著的倒“U”型關系,計算得出其拐點為13.92,與全行業回歸結果相近,原因在于第二產業所包括的制造業等行業是我國企業技術創新的主力軍。第三產業中,知識產權保護強度與企業創新績效之間的關系也呈現出顯著的倒“U”型,計算得出其拐點為13.58,略低于第二產業的最有保護水平,但無重大差異。
四、結論與建議
本文通過構建省際知識產權保護指數測度我國各省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基于2006—2018年上市公司的面板數據,建立個體固定效應模型來對知識產權保護與企業創新績效之間的相關關系進行實證分析。回歸結果表明我國知識產權保護水平與企業創新績效之間呈顯著的倒“U”型關系,且“最優知識產權保護強度”為13.9,目前除西藏自治區以外,我國各省的知識產權保護指數均高于該“最優水平”。通過進一步對三大產業進行異質性分析發現,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對第一產業的企業創新無顯著影響,但與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企業創新績效之間呈顯著的倒“U”型關系,且第二產業的“最優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略高于第三產業。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議。第一,政府應該繼續完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的建設,但不應僅僅局限于盲目提高知識產權保護強度,而應該細化相關法律法規,針對不同行業、不同地區采取針對性的知識產權保護政策,使其發揮最佳效用。第二,政府應該在知識產權保護外的其他方面出臺政策激發企業研發動力,如稅收減免。因為從回歸結果可以看出,增加研發投入可以顯著地提高企業的專利產出。
參考文獻:
[1]? Helpman E.Innovation,Imitation,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J].Econometrica,1993,(6):1247-1280.
[2]? 張建忠,劉志彪.知識產權保護與“趕超陷阱”:基于GVC治理者控制的視角[J].中國工業經濟,2011,(6):58-68.
[3]? 吳超鵬,唐菂.知識產權保護執法力度、技術創新與企業績效——來自中國上市公司的證據[J].經濟研究,2016,(11):125-139.
[4]? 李俊青,苗二森.不完全契約條件下的知識產權保護與企業出口技術復雜度[J].中國工業經濟,2018,(12):115-133.
[5]? ODonoghue Ted,Josef Zweimuller.Patents in a Model of Endogenous Growth[J].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2004,(9):81-123.
[6]? 劉小魯.知識產權保護、自主研發比重與后發國家的技術進步[J].管理世界,2011,(10):10-19.
[7]? Ginarte J.C.,Park W.G.Determinants of patent rights:a cros-national study[J].Research Policy,1997,(26):283-301.
[8]? 許春明,單曉光.中國知識產權保護強度指標體系的構建及驗證[J].科學學研究,2008,(4):715-723.
[9]? 董雪兵,朱慧,康繼軍,宋順鋒.轉型期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增長效應研究[J].經濟研究,2012,(8):4-17.
[10]? 寇宗來,劉學悅.中國企業的專利行為:特征事實以及來自創新政策的影響[J].經濟研究,2020,(3):83-99.
[11]? 魏浩,巫俊.知識產權保護、進口貿易與創新型領軍企業創新[J].金融研究,2018,(9):91-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