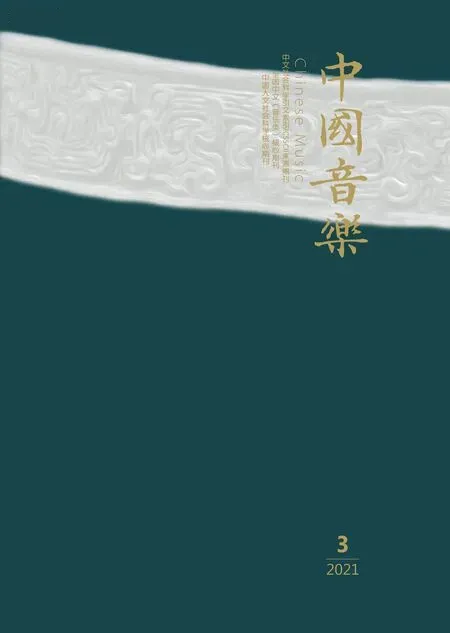欲窺堂奧 先探門徑
——讀路應昆主編《戲曲音樂入門》
○ 楊冬林
常見的戲曲音樂概論類著作大致有兩種,一種是單一的劇種音樂研究,例如,劉吉典的《京劇音樂概論》,武俊達的《昆曲唱腔研究》,黎建明的《湘劇音樂概論》等,這一類著作于某一劇種音樂甚為詳盡;另一種是綜合性的戲曲音樂著作,例如海震的《戲曲音樂史》,重在梳理聲腔的發展演進,再如蔣菁的《中國戲曲音樂》,以大的聲腔類型為綱目,介紹其音樂特點。這兩種著作互為補充,前者讓我們對某一劇種的唱腔音樂有深入了解,后者讓我們從整體上把握聲腔或劇種音樂之間的關系。但隨著戲曲音樂研究的深入,尤其是許多小劇種音樂得到學者們越來越多的關注,很多問題需要重新清理,觀點或者表述也需要重新完善,例如,小戲聲腔的體制問題,小戲聲腔與大戲聲腔的關系問題等。此外,古典戲曲曲牌曲律的研究也在不斷推進,曲牌與聲腔之間的關系也需要進一步闡釋。
由路應昆教授主編的《戲曲音樂入門》一書從 “體”和“腔”兩個維度來深入闡釋戲曲唱腔音樂,作者打破了單一的學科思維模式,運用戲曲史學、文學、音樂學等多種視角,為我們全面深刻把握戲曲唱腔音樂指明了方向。相對于此前的眾多戲曲音樂著作,該書提出了一些新的見解,關于戲曲唱腔音樂之體,在曲牌體、板腔體的基礎上提出了小曲體和上下句體;關于戲曲音樂的腔,作者探討了南北曲與高腔、昆腔之間的關系,啟發我們深入思考曲腔之間的關系。
一、提出了小曲體和上下句體
關于傳統戲曲的唱腔體制,曲牌體和板腔體的二分法是目前較為通行的分類方法,但《戲曲音樂入門》一書則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小曲體、上下句體、曲牌體和板腔體的分類法,并用圖示法標示出戲曲音樂各體之間的關系。①參見路應昆:《戲曲音樂入門》,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作者認為小曲體和上下句體是戲曲在小戲階段最為常用的體制,而曲牌體和板腔體則是戲曲發展到大戲階段使用的唱腔體制,小曲體的主要特點是在一個戲劇單元中一支小曲的單曲疊用;上下句體是由一對上下句腔反復使用構成唱段,在反復之中只有快慢的變化,而沒有板式的變化;曲牌體以曲牌的組合使用為主,同一套曲之中各個曲牌在音樂上共性較多,各套曲之間形成音樂色彩的對比;板腔體雖然也是上下句腔構成唱段,但更強調通過板式的變化來推動音樂的展開,其表現力更強。這四種體之間并不是壁壘森嚴,“不論在四種‘體’之間還是在他們與其他結構形式之間,都可以存在交混和‘過渡’的形態。”②同注①,第11;62頁。這些表述是之前的戲曲音樂論著不曾提到過的。
作者闡釋了小曲體與曲牌體的關系并明確小曲和曲牌的性質差異。在之前的戲曲音樂論著中,曲牌體和小曲體是混在一起的,例如,“屬于曲牌體唱腔的,主要是采用昆腔和高腔兩大腔系的諸劇種。此外,還有各地的部分采茶戲、花鼓戲、秧歌戲及部分地方小戲,如福建的莆仙戲,陜西的眉戶等。”③蔣菁:《中國戲曲音樂》,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95年,第37頁。這里把唱小曲、小調的采茶戲、眉戶戲都歸入曲牌體,這一方面緣于我們對曲牌一詞的使用不嚴謹,同時也表明我們對小曲小調和曲牌的性質差異沒有作深入探究。例如在我們經常看到的戲曲、文學、音樂論著中,不論是文學作品中的詞曲曲牌,如宋詞詞牌【念奴嬌】【卜算子】,還是戲曲演出中的器樂曲,如京劇中的【夜深沉】【小開門】,還是南北曲的曲牌,如【步步嬌】【皂羅袍】,都使用曲牌一詞來指稱,然而這幾種類型曲牌的性質是有明顯差異的。正是由于曲牌一詞在使用上的隨意性較大,導致很多著作把【銀紐絲】【剪靛花】之類的小曲、小調也說成是曲牌,于是,唱小曲、小調的劇種也就成了曲牌體。其實南北曲曲牌和這些小曲之間差異很大,海震在《戲曲音樂史》中說“昆腔的曲牌與一般小戲里所唱的小曲曲牌不同。我們知道,小曲,亦稱小調,較有名的有【孟姜女】【剪靛花】【鮮花調】等,它們一般都有比較固定的曲調,常常一聽就能聽出來。而昆腔的曲牌則不然,它常常沒有比較固定的曲調,在音樂上也沒有比較明顯的特點。”④海震:《戲曲音樂史》,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3年,第100頁。也就是說,我們之所以把小曲體和曲牌體混在一起,是因為沒有認識到小曲和曲牌之間的差異,而作者在《戲曲音樂入門》一書中多次提到這種差異,在第二章中作者用廣西彩調劇的【趕路腔】、小戲中的【銀紐絲】、黃梅戲中的【對花調】詳細解釋了小曲的音樂樣式,認為小曲的音樂比較凝固,其唱法屬于“定腔套唱”。在第三章第五節中作者再次提到小曲通常是“專曲專腔”,而“昆腔的曲牌一般不需要以音樂的個性色彩當作其獨有標志(曲牌主要是從詞格來區別),因此在昆腔的眾多曲牌中腔調材料通用的情形非常普遍。”⑤同注①,第11;62頁。此外,作者曾發表《小曲、曲牌辨異》一文,總結了小曲、曲牌之間四個方面的差異,“從牌調性質看,小曲是音樂性質的牌調,曲牌是文詞性質的牌調。從牌調使用形式看,小曲一般為單曲使用,曲牌主要是多牌聯用。從腔調形態看,小曲之腔固定、“板塊化”,曲牌之腔組織靈活。從不同牌調的腔調關系看,小曲之腔各自獨立,(單支)曲牌之腔不能獨立。”⑥路應昆:《小曲、曲牌辨異》,星海音樂學院學報,2012年,第4期,第57頁。作者此文不僅是論述二者的差異,同時也意在提醒大家注意學術名詞的運用,稍有不慎,便會產生歧義。
相對于小曲體和曲牌體的區分,上下句和板腔體的區分要容易得多,在第二章的第三節,作者同樣選取了廬劇、滬劇的唱段作詳細的解析。上下句體通常只是單一的上句腔、下句腔的反復,只有簡單的快慢變化,但是沒有板式的變化,通常為“起、平、落”結構,即第一句散板起唱,最后一句也常常散板收尾,中間則是大段數唱,而板腔體則是在一個上下句的旋律基礎上作各種板式變化,通常有散板、慢板、原板、流水板、快板、搖板,甚至有導板、回龍等特殊板式,慢板中還可以有慢三眼、中三眼、快三眼的區別,這是僅僅用上下句反復的唱腔體制遠遠無法比擬的。作者在第二章中論述小戲的唱腔音樂體制是小曲體和上下句體,“小戲音樂是戲曲音樂的初級形式,小曲和上下句是戲曲音樂的兩個生長‘原點’”⑦同注①,第17;24;29頁。,同時又指出“宋元時代形成的南北曲一定意義上可說是小曲的發展演變產物,南北曲的體制‘曲牌體’也可說是小曲體發展演變的產物”⑧同注①,第17;24;29頁。,“清代形成的板腔體可說是上下句體發展、提升的產物,換言之上下句體可視為板腔體的前身”⑨同注①,第17;24;29頁。,這些論斷都是作者多年潛心研究所得,并非一時臆斷,這從作者發表的《小戲唱腔之“體”略說》一文就能體會得到。該文對小戲的音樂體制進行了充分的討論,可以說是本書第二章的寫作基礎,文中說“以往的研究大都是以曲牌體涵蓋小曲體,以板腔體涵蓋上下句體,忽略了小曲體和上下句體的獨特性質,因而不能準確體現小戲音樂的結構特征。對于戲曲音樂從簡到繁、從‘小’到‘大’的發展來說,小曲體和上下句體正可說是兩個‘原點’,忽略了它們,也難以準確揭示戲曲音樂的成長和演化軌跡。”⑩路應昆:《小戲唱腔之“體”略說》,《戲曲研究》,2017年,第2期,第107頁。從這段話中不難看出《戲曲音樂入門》一書在體例編排上的用心,作者將小戲音樂放在第二章來論述,三、四章論述曲牌體音樂,五、六章論述板腔體音樂,正是體現了戲曲音樂由簡到繁,由“小”到“大”的成長演化軌跡,而第七章論述新興劇種的音樂,與第二章遙相呼應,一方面用近現代的實例說明小戲音樂逐漸成長,小戲逐漸成為大劇種的發展趨勢,另一方面也暗示了小戲雖然由于歷史記載較少,不被人們關注,但實際上一直存在的事實。誠然,關于“體”的進一步認識不代表我們把握住了種類繁多的“腔”,但總算前進了一步。
作者提出小曲體和上下句體是小戲的基本唱腔音樂體制,這確實符合實際情況,例如筆者熟悉的河南曲劇的唱腔音樂就屬于此類。河南曲劇的常用曲調中,【陽調】【慢垛】【書韻】【滿洲】等就是典型的四句頭式小曲,當然演員在演唱時往往不拘一格,喜歡在句中加垛或者加花腔,做出各種變化,但其基本格式卻是相對固定的;而【上流】【詩篇】則屬于典型的上下句,二者單獨構成唱段時,通常是起平落結構,即第一句為散板,最后一句為收尾,中間則是一對上下句反復,當然演員也可以略做變化以適應敘事的需要,但整體上看則是略有快慢變化而沒有板式的變化。當然,小戲的唱腔音樂也是發展的,受到板腔體戲劇劇種的影響,有些小戲的唱腔音樂逐漸擺脫了小曲小調或者簡單上下句的格局,已然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例如越劇的聲腔體制發展就非常典型。但是也有很多小戲的唱腔音樂仍然保留了原始的基本面貌,風格樸素而自然,同樣受到人們的歡迎,這也是戲曲唱腔音樂風格多元化的需要。
二、深入闡釋南北曲與曲腔關系
《戲曲音樂入門》一書對南北曲一雅一俗兩種不同發展路徑的闡釋是另一個有新意的地方。由于精致優雅的水磨昆腔受到歷代文人的尊崇,其文獻資料豐富,各類曲譜、曲論對其闡釋也較多,尤其昆腔是文人傳奇正宗唱法之類的表述屢見不鮮。然而南北曲除了逐漸走向“雅化”(昆腔)的路子以外,還有另一條“俗化”(高腔)的發展路徑,這是歷代文獻記錄相對較少的部分,也是研究較為薄弱的地方。之前的戲曲音樂著作并非沒有講到高腔,但只是就其聲腔音樂而談,沒有對高腔所唱的南北曲本身作充分的介紹,尤其沒有對南北曲在兩種腔體中的差別作對比,這未免有些遺憾,而這一點正是《戲曲音樂入門》一書頗為用心的地方,這些解釋對我們進一步理解“南北曲”和“曲腔關系”有重要的幫助。
作者以“南北曲俗唱”作為第四章的標題,與第三章的標題“南北曲和昆腔”相呼應,一方面意在強調南北曲有兩種不同的發展路徑,另一方面也突出了“南北曲”在兩種聲腔中的重要作用。第四章開篇就談到,“在文人傳奇中的南北曲強化格律和水磨昆腔將南曲唱法推向‘高雅’的同時,民間的南北曲卻以‘俗化’和‘自由化’為主要趨向,即各地藝人以‘土俗’之腔演唱南北曲,曲牌文詞也不守格律而有種種自由處理。”?同注①,第67;62–63頁。在討論聲腔的時候,始終圍繞南北曲來展開,其中既有對比,又符合實際情況。作者對南北曲雅俗分化的闡釋概括如下:
南北曲的雅化,主要體現在文人撰寫的傳奇劇作文辭優美,文學性強,甚至追求深刻的思想內涵;曲牌講究格律,曲牌的格式、句式、平仄、用韻皆有法度,并編制一系列曲譜作為填詞的范本;唱法上打造了細膩悠長的水磨昆腔,重視腔對字音的體現,所謂“五音以四聲為主”;唱腔語音力求雅正,以韻書為準,強調擯棄方言土語,以突破地域的限制;重視規范化,走定腔定譜的路線。
南北曲的俗化,體現在民間戲文面對底層百姓,文辭常常通俗易懂,明白如話;曲牌不重視格律,甚至完全突破格律,常在曲牌中用加滾;唱法上各地高腔以民間土俗之腔對南北曲“改調歌之”;唱腔語音為各地方言語音,地域性很強;曲牌和唱腔的傳承沒有曲譜,甚至曲牌名稱佚失較多。
這些認識也是建立在長期研究的基礎上,作者在《高腔與川劇音樂》《戲曲藝術論》《北京高腔研究》等著作中多次談到這個問題,例如在《北京高腔研究》一書中,作者指出“傳奇以高度‘雅化’為特征,與民間戲文形成一雅一俗的鮮明對照,這種差別體現在劇本文學、曲腔、場上演藝、總體風格品味等一系列方面。”?路應昆:《北京高腔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11頁。這些論述不僅僅是作為聲腔音樂分析的背景,更重要的是對曲腔關系做深入的剖析,揭示聲腔發展演變的邏輯關系,深化了我們對南北曲的理解,對我們認識南戲與傳奇的關系也有重要的參考意義。
作者還重點分析了昆腔和高腔的音樂,可以看出二者之間也有相同之處。比如二者都是以曲牌的組群化使用為特征,都有曲牌分類的現象,在曲腔關系的處理上同一曲牌都可以配唱不同的腔調。關于昆腔音樂,作者不僅分析了板拍規律、腔對字音的體現、腔調材料在曲牌中的組織規律等,還特別指出昆腔“宮譜”的出現對于曲牌定腔的影響,“在出現曲牌格律譜之前,曲牌填詞的自由度較大(有時很大),那以后曲牌的填詞則會更多‘趨同’;同理,在出現‘宮譜’之前,曲牌音樂處理的自由度會較大(有時很大),那以后的曲牌音樂處理也會更多‘趨同’。”?同注①,第67;62–63頁。這一點作者雖然沒有深度展開論述,但非常有助于我們理解昆腔曲牌音樂。關于高腔,作者指出高腔各個分支之間在曲腔關系上有共性,但在具體的腔調上卻差異很大,這是高腔在音樂上不同于其他聲腔的重要特征。作者以四川高腔為例,分析了高腔的形式特點“幫打唱”,即幫腔、打擊樂伴奏、無管弦伴奏的干唱,分析了腔對字音的體現和板式特點,并對高腔的“曲牌類”做了詳盡的闡述,以《思凡》為例介紹了曲牌類的變換所造成的音樂色彩的對比。對高腔的這些介紹可以和昆腔部分作對比,這樣就會有更深刻的理解。
這些對我們認識曲腔關系極有啟發,作者首先對南北曲的形成和發展演變做了詳細的闡述,對諸宮調、南曲戲文、北雜劇、明清傳奇中“曲”的情況作了詳細的梳理,對南北曲與唐宋大曲、唐宋詞、諸宮調的關系作了論述。其中尤為重要的是對傳奇中南北曲逐漸走向格律化做了詳盡的解釋,從中尋繹出“曲牌強化格律的傾向也蔓延到了音樂”的發展規律。從最早的文辭格律譜《舊編南九宮譜》,到有了點板的《南詞全譜》《南詞新譜》,到后來有了工尺的《九宮大成》,再到收錄單出或全劇的南北曲清唱譜《納書楹曲譜》,最后發展到舞臺演出的“戲工譜”《遏云閣曲譜》,這一發展過程的講解使我們對南北曲的文辭格式和唱腔音樂有了全面的理解。又如該書對高腔音樂的介紹,首先從南北曲的“俗化”講起,而不僅僅是談唱腔音樂;再如對南北曲其他變異形式的弦索曲的介紹,以弦索曲中的【山坡羊】為例,探討弦索曲與南北曲、小曲的復雜關系,指出弦索曲“大體屬于南北曲與小曲交融演變的產物”。?同注①,第85頁。
總之,該著在學術上取得了新進展,然作者僅稱其為“入門”,足見其謙遜的治學態度,同時也表明作者力圖為戲曲音樂研究者提供最佳的入門之徑。作為國家視頻公開課的配套教材,該著與時俱進,不僅有理論介紹和樂譜實例,還充分利用現代傳媒手段以直觀呈現,每一章節都配有二維碼,讀者通過掃描即可觀看對應的教學視頻,感受對應的唱腔音樂,學習起來極為便利,相信會有更多的有識之士能夠登堂入室,以窺堂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