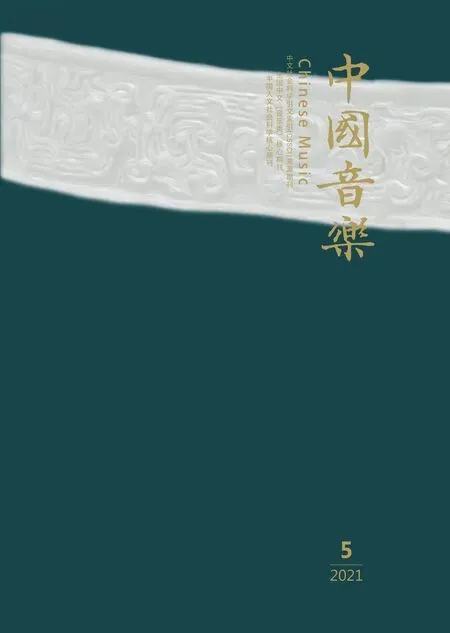西周“周樂”的文化基質(下)
○ 李方元
四、西周“周樂”的歷史與其文化特質
由上可知,“三禮”所載西周“周樂”其實就是“六樂”以及“詩樂”中的《雅》《周頌》及二《南》。這一發現表明:《雅》《周頌》和二《南》即西周“周樂”的主體。這意味著西周“周樂”是有文化根基的,而此根基即是姬周人自己的傳統和文化。本節擬對其文化特質略加概論。如果說文化圖式與其歷史有著正相關①任何事物都有其共時表征和歷時因由,即有文化與歷史的兩維,美國學者馬歇爾·薩林斯就此論說道:“歷史乃是依據事物的意義圖式并以文化的方式安排的,在不同的社會中,其情形千差萬別。但也可以倒過來說:文化的圖式也會是以歷史的方式進行安排的,因為它們在實踐展演的過程中,其意義或多或少地受到重新估價。在歷史主體,即相關的人民進行的創造行動中,這兩個對立面的綜合被展現了出來……人類學家所稱的‘結構’—文化秩序的象征關系—乃是一種歷史事物。”薩林斯:《歷史之島·導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4頁。,那么,姬周歷史脈絡的梳理當可使西周“周樂”的文化特質更為彰顯。筆者以為,西周歷史中兩大基本史事—“姬周王朝”和“禮樂制度”尤應得到關注,此乃西周“周樂”文化特質形成的兩塊基石。
(一)姬周王朝—西周“周樂”文化特質形成的歷史節點。西周“周樂”始于周朝,以此看,四個史實不可忽略:一是商周之戰。武王滅商,無論是曾同“多方”之“友邦冢君”(孔安國說此“三分二諸侯及諸戎狄”②阮元校刻:《尚書正義》卷一一《泰誓上》,第180頁。)盟誓孟津,還是后來率庸、蜀、羌、髳、微、、彭、濮人(孔說此“八國皆蠻夷戎狄”③阮元校刻:《尚書正義》卷一一《牧誓》,第183頁。)大戰牧野,可知商末社會的基本格局是族群林立,牧野之戰即是姬周人聯合眾族群友邦發起的一場針對商族的戰爭。④司馬遷撰:《史記》卷四《周本紀》裴骃集解云:“羌在西。蜀,叟。髳、微在巴蜀。、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漢之南。”又張守節正義引《括地志》云:“武王率西南夷諸州伐紂也。”第123頁。姬周人通過翦商滅紂而使姬周天子成為天下共主。可見,商周之戰,本質是族群間的戰爭,即族群之爭。二是拓殖東土。蕞爾周邦原偏居西部周原,自西伯文王始而向外拓展,曾先后劍指密須、耆、黎、邘、崇等族群⑤司馬遷撰:《史記》卷四《周本紀》:“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第118頁。,后又移師南下而德威南國,“于時三分天下有其二”⑥阮元校刻:《毛詩正義·詩譜序》:“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于是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庸、梁、荊、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第264頁。,待武王勝殷,再一舉擁有了東部眾商土與商民,到周公平亂和成王東征,拓土殖民,又獲他族裔之地,王朝疆域再度擴張,以“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之豪氣而大國天下。由此,姬周人的擴疆拓土也意味著周王朝版圖內族群的多樣化加劇,其遺民數量尤以商人最巨。如此殖民,自然引發王朝層面的文化主體之爭并導致族群間潛在和長期的博弈。三是姬姓王朝建立。周朝姬姓,周初自武王至康王,眾姬姓貴族封侯,就此摶成“以藩屏周”的王朝政治格局。如《左傳》所云:“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⑦阮元校刻:《春秋左傳正義》卷五二《昭公二十八年》,第2119頁。《荀子》也說:“(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稱偏焉。”⑧王先謙撰:《荀子集解》卷四《效儒》,第114頁。《史記》亦謂:“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⑨司馬遷撰:《史記》卷一七《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801頁。由此,周朝的姬姓周人,事實上成為了王朝的特殊族群—國族。四是周朝主體文化。根本上說,不同族群皆植根于各自的族群文化。⑩參詳拙著:《周人傳統與西周“禮樂”淵源》,《音樂研究》,2019年,第5期,第5-25頁。周公“制禮作樂”而成就的“禮樂”文化,即是以姬周文化為根基而損益打造的有周一代的王朝文化。周人本不同于商人或其他族裔,擁有自己的歷史和文化,而其中兩根支柱即所謂的“雅言”和“雅樂”,此亦周代“禮樂制度”形成的文化之根,即使是到春秋“禮崩樂壞”之際仍有人堅守。孔子就說他“吾從周”?阮元校刻:《論語注疏》卷三《八佾》,第2467頁。,還說:“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何晏集解引鄭玄云:“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后義全,故不可有所諱。”?阮元校刻:《論語注疏》卷七《述而》何晏注引鄭玄語,第2482–2483頁。可見雅言與經典的文化關系。后儒家弟子對“禮樂”和“雅”文化亦推崇備至。“雅言”“雅音”,作為西周的文化符號,實乃周王畿之言之音,本由姬周人文化根脈所生發。清人劉臺拱謂:“王都之音為最正,故以雅名……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正于王朝,達于諸侯之國,是為雅言。”?劉臺拱撰:《論語駢枝》,《續修四庫全書》,經部四書類,第154冊,第293頁。西周“王都”即西都,所以劉寶楠說:“周室西都,當以西都音為正……夫子凡讀《易》及《詩》《書》執《禮》,皆用雅言,然后辭義明達。”?劉寶楠撰:《論語正義》卷八《述而》,第270頁。今人李建國也說:“周代官方語言稱‘雅言’,雅是正的意思……王都之言最正,故稱雅言。”還說雅言基于“秦晉方言”?李建國著:《傳統語文規范及其現實意義》,《中國語文》,1996年,第1期,第45–46頁。。袁家驊等說:“周末許多部落互相并吞或聯合,許多小部落方言融合為幾個較大的部落方言。”?袁家驊等著:《漢語方言概要》,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60年,第17頁。秦處宗周故地,宗周之音即宗周地方之音,“雅”亦姬周人方言、方音的代稱。《詩》《書》等因基于“雅言”“雅樂”而升格,成為王朝“不可諱避”的文化載體,周公據此“制禮作樂”,使姬周“禮樂”更具法典地位?參見拙著:《“樂”“音”二分觀念與周代“雅鄭”問題》,《音樂研究》,2018年,第1期,第43–64頁;又拙著:《周人傳統與西周“禮樂”淵源》,《音樂研究》,2019年,第5期,第5–25頁。,并以為國家禮典不可割舍的標配和支柱。從《周禮·春官》大司樂、樂師、大師等職事看,西周“雅樂”內容豐富,涵蓋廣泛,囊括諸如樂德、樂語、樂舞、樂儀、六詩、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等整個的音樂系統?阮元校刻:《周禮注疏》卷二二《春官·大司樂》,第787–788頁。,并整體地納入到后在春秋時被普遍認可的“五禮”體系之中。故有《大戴禮·小辨》如是說:“是故循弦以觀于樂,足以辨風矣;爾雅以觀于古,足以辨言矣。”?王聘珍撰:《大戴禮記》卷一一《小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206頁。從“樂以辨風”“雅以觀古”中可知,“雅樂”和“雅言”確實為姬周王朝打造起一座新的文化基臺,并搭建起以姬周文化為根基的“禮樂”文化系統。對此,楊華《先秦禮樂文化》一書有論說云:“周王朝一統中原,賓服四方,把他們的文化形態作為標準模式向全國推進,實行文化滲透和文化統一,以西周京畿方言‘雅言’(夏言)為上,以西周京畿鄉樂‘雅樂’(夏樂)為正。雅言成為全國官話,雅樂成為國朝官樂。”?楊華著:《先秦禮樂文化》,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86頁。
以上所述表明,“姬周人”擁有天下后在為維護其族群利益而采取的諸種文化舉措中,包括了西周“周樂”在內。可見,西周“周樂”產生過程同周王朝建立過程和王朝文化再造過程同步。以此看西周“周樂”,知其要點有三:其一,西周“周樂”基于周初姬周人強烈的族群認同。這種認同產生于對新生“姬”姓王朝的維護,無論是他們自稱“西土之人”或“夏人”,都表現出與商人區分和切割的意圖和姬周“我群”意識。商周之爭的背后,“族群”之異質不可忽視。所以,姬周人不斷強化自身的“族群”特征,以凸顯我群的存在,這當是西周“周樂”文化意識之重要根源。其二,從“三禮”可知,西周“周樂”延續和保持了與姬周“族群”屬性的高度一致性。“三禮”中所見周樂“樂名”,除部分古樂(“六樂”)外,余《雅》《頌》和二《南》樂或為姬周之樂或為與姬周人有關之樂的事實表明,西周“周樂”具有清晰的姬周性質。同時也表明,作為西周早期制度之“周樂”,本止此三類,更無其他“十二國風”?筆者按:《詩經》中的《豳風》比較特殊,從《周禮·籥章》看,周初它仍處于姬周民俗內部之范圍,尚未納入到國家的“禮制”層面中。。劉臺拱指出“列國之音不盡正,故以《風》名”?劉臺拱撰:《論語駢枝》,《續修四庫全書》,經部四書類,第154冊,第293頁。,所以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返魯,只是說“然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阮元校刻:《論語注疏》卷九《子罕》,第2491頁。而未言及《風》,這反映出《雅》《頌》與《國風》早期的關系。就時間講,“十二國風”入樂當在后,出兩周之交或春秋已降“禮崩樂壞”時侯國之風土及其屬民,為非“姬周”之樂,故不在周初“周樂”之列。侯國方域之“風”(如“邶”“鄘”“鄭”“唐”等)皆辨之以“地”名?如劉臺拱《論語駢枝》所云:“先《邶》《鄘》《衛》者,殷之舊都也,次王者東都也,其余……大抵皆以聲音之遠近離合為之甄敘矣。”第154冊,第293頁。就是后來,《周南》《召南》還是被歸于《風詩》,也是因為它們本出宗周王畿以南的非姬周屬民,原非宗周本土的姬周人之音。此正如《呂氏春秋·音初》所云:南音出南土,只是后來“周公及召公取風焉,以為《周南》《召南》。”,本亦含“族群”(或民系)之區分和間離,其文化意識深隱其中。由此亦可知,“周樂”之“雅”“正”觀念,其深層依據也在此。西周“周樂”于春秋以來冠以“雅”“正”之名義,正是想正名和彰顯它原初內在的“姬周”傳統和國家性質在以往“禮樂”現實中的那種一貫之義,同它相對和對峙的則是春秋已降“禮崩樂壞”背景下的“鄭衛之音”及其非姬周的族性之義。而侯國的非姬周“風詩”則乘“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的政治僭越之機而逐漸浸淫和忝列于“周樂”。孔子因對此現狀不滿和憎惡而提出批評:“惡鄭聲之亂雅樂。”這也暗示“十二國風”原不在西周“周樂”之中。其三,《雅》《頌》和二《南》與姬周根源的文化關聯。《雅》,本出宗周王畿之地,為姬周人之樂;《頌》,亦源自姬周人的“聲歌之謠”,也是在周地姬周民人歌謠上的禮典再造。?在周代,方域與風、風詩,以及王政與樂、樂律間有著某種特別的關聯。故《管子·宙合》有“君失音則風律必流”之說。宋楊簡說周人有“辨風即辨詩也,詩即樂”之說。前者見黎翔鳳《管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211頁。后者見《先圣大訓》卷五《小辨》,明萬歷刻本。而二《南》,盡管緣起于南國“南音”,本非姬周人之樂,然因文王南國之治的歷史機緣和“周公及召公取風焉”?陳奇猷著:《呂氏春秋校釋》,卷六《音初》,第334–335頁。的積極介入而與姬周人聯系到了一起,并由此融入到姬周文化當中,也就是說,它因其聯系了姬周人及其政治傳統而受到重視;更為重要的是,二《南》是文王先周時期和周、召二公周初政治治理的經驗和遺產,在姬周人早期的南國治理和教化中做出過重大和特殊的歷史貢獻,由此也成為后來的周朝“禮樂制度”的先行先試的前奏曲。
(二)禮樂制度—西周“周樂”文化特質形成的文化基座。眾所周知,西周以“禮樂”立國,然“禮樂”又是怎樣的一種文化類型呢?從類別和性質上講,周代“禮樂”屬“操演”文化而非“文本”文化,根源于姬周人歷史上“非文字文本”的文明形態。?筆者按:姬周人在先周文王至周初武王之時,使用文字的情況遠遠落后于商人(對照殷墟和岐周的甲骨文即可知)。而“禮樂”則是基于“非文字文本”的文化系統,它又是以“身體操演”的方式在周人自文王時開始便在其南國治理中實踐的,并由此積累了大量的歷史經驗。操演,是一種文化系統,指以身體行為為基礎而建立起來的整套的行為儀軌和社會規范,并規定和指導人們的社會活動和行為方式;而文本,也是一種文化系統,指以文字書寫為基礎通過對社會行為、儀典制度及其義理和思想觀念等加以記述與解說而創立起來的一套權威,用以達到對社會的治理和對人們行為的管控。西周的“禮樂”治國,重在通過儀式規則和身體規訓來確立社會和政治的規范,而非僅以用文字記錄所形成的法規條文來管制社會。周初“制禮作樂”是禮樂治國的開端,始于周公攝政六年(前1038年?此依克商年為公元前1046年推算。見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2000年階段成果報告》(簡本),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0年,第49頁。),此時距武王滅紂和開國不足十年。姬周人選擇“禮樂”治國,即選擇了主以“操演”文化治國的方式,而暫未能像商人那樣重視以“典冊”(文本)?阮元校刻:《尚書正義》卷一六《多士》:“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典有冊,殷革夏命。”第220頁。文化來輔助治國。個中原因固然不少,但有四點不可不說:其一是周初姬周人“文字”“文本”水平不高。從20世紀下半葉西周甲骨出土最集中的陜西岐山周原鳳雛村發掘資料看,所見甲骨文僅903字?王宇信著:《西周甲骨探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第20頁。,可知在周初姬周人的文字使用不會太多。陜西周原考古隊“發掘簡報”稱,鳳雛村西周建筑遺址年代為公元前1095±90年?西周原考古隊著:《陜西岐山鳳雛村西周建筑基址發掘簡報》,《文物》,1979年,第10期,第34頁。,正好合太王、王季和文王的年代?阮元校刻:《毛詩正義》卷一六之二《大雅·緜》:“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又,漢時舊說文王與《周易》有關聯。如《史記》卷四《周本紀》:“西伯……其囚羑里,蓋益《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第119頁。《漢書》卷三〇《藝文志》:“文王……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歷三古。”第1704頁。。而此時距后來周公“制禮作樂”也就大致半個世紀,距武王伐紂僅40年。從現有周人甲骨情況看,姬周人要在短短幾十年內便可以用“文本”文化來治國,當有相當的困難。其二是周初能熟練使用文字者多殷商舊臣。周初姬周人不得不任用有文字能力的殷遺民,以幫助自身提升其文字和文本水平。《尚書·多士》載周公初往新都雒邑時,便希望商舊臣能以“典冊”服務周室:“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阮元校刻:《尚書正義》卷一六《多士》,第220頁。又據墻盤銘(節選):“(助詞)武王既殷,(微)史(使)刺且(烈祖)迺來見武王,武王則令周公舍(居處),于周卑(俾)處。”?馬承源主編:《商周青銅器銘文選》(三),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54頁。盤銘說,器作者強是周共王時史官,其先祖為殷畿微國史臣,商滅投奔武王,此后歷世皆周朝史官。?見李學勤著:《論史墻盤及其意義》,《考古學報》,1978年,第3期,第149–157頁。周室史官,其要職多商臣或商人。胡新生認為:“周王朝史官就其淵源看大多出自異姓。一些異姓家族如辛氏、尹氏、程氏、微氏等,自文武時期投靠周邦后一直世襲史職,可以說長期壟斷著周王朝的文化事業,其中辛、尹兩家的地位尤為顯要。”?胡新生著:《異姓史官與周代文化》,《歷史研究》,1994年,3期,第44頁。如辛甲,原殷臣,商末文王接納了他;?司馬遷撰:《史記》卷四《周本紀》裴骃集解引:“劉向《別錄》曰:‘辛甲,故殷之臣,事紂。蓋七十五諫而不聽,去至周,召公與語,賢之,告文王,文王親自迎之,以為公卿,封長子。’”第116頁。尹逸(佚),原亦仕商,后為周史官,歷文、武、成、康等朝。?徐元誥撰:《國語集解》第一〇《晉語四》,載胥臣對晉文公說:“(文王)諏于蔡、原,而訪于辛、尹。”韋昭注云:“辛,辛甲。尹,尹佚。”第362頁。又,武王勝殷后,在代殷受命儀式上,尹逸不僅宣讀受命文書曰:“殷末孫受,德迷先成湯之明,侮滅神祗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彰顯聞于昊天上帝,”還負責“遷九鼎三巫”之禮。參見《逸周書匯校集注》(修訂本)卷五《商誓解》,第354-355、358頁。班固撰:《漢書》卷三〇《藝文志》,自注云:“(尹佚)周臣,在成、康時也。”第1737頁。其三是姬周人自先周文王始已有“禮樂”安邦的成功經驗。周初周公“制禮作樂”之舉本身即是此經驗的延續。繼以“禮樂”操演來治理國政,對周公(包括姬周上層)來說這可謂駕輕就熟:因為他們原來就擁有文王治理南國的禮治遺產,同時還直接有周、召二公施《周南》《召南》歌樂以治周、召二地的實踐經驗。也就是說,姬周人“禮樂”實踐早始于周朝建立之前,而“禮樂”治邦也早已融進了姬周的政治文化傳統。“禮樂”作為非“文本”書寫的文化系統,特別之處在其實踐性、身體性以及操演性等,而這種主以行為的社會“履踐”方式直接導致了“周樂”的非“文本”特性。反過來,這種“非文本性”又成就了西周“周樂”特殊的社會實存性。易言之,“禮樂操演”即“禮樂政治”的社會文化形態。這種社會文化形態的基本特點是基于“行為”而非“文本”。此可以《國語·周語》中一段話窺其一斑。其曰:“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韋昭注云:“獻詩以風也。瞽,樂師。曲,樂曲也。賦,公卿列士所獻詩也。矇,主弦歌諷誦。誦,謂箴諫之語也。百工,執技以事上者也。諫者,執藝事以諫。庶人……傳以語王也。”?徐元誥撰:《國語集解》第一《周語上》,第11頁。此處歌詩、諷誦、勸諫之語、執技之事和傳語等行政方式皆屬“操演”形態。無獨有偶,《楚語》載兩周之交的衛武公執政,亦不離交戒、誦志、訓導、勸箴、瞽史之導、師工之誦等言說行為:“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于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茍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于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導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寧有官師之典,倚幾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褻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導,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蒙不失誦,以訓御之,于是乎作《懿》詩以自儆也。”?徐元誥撰:《國語集解》第一七《楚語上》,第500–502頁。而據今人王小盾研究,《周禮·春官》中“大師”所教之“六詩”—風、賦、比、興、雅、頌,也都是身體性的活動,即都是建立在身體行為之上的。?王小盾著:《詩六義原始》指出:“六詩是西周樂教的六個項目,服務于儀式上的史詩唱誦和樂舞。其中‘風’與‘賦’是用言語傳述詩的兩種方式,分別指方音誦和雅言誦;‘比’與‘興’是用歌唱傳述詩的兩種方式,分別指賡歌與和歌;‘雅’與‘頌’則是加入器樂因素來傳述詩的方式,分別指樂歌和樂舞。”載作者《中國早期藝術與宗教》,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88年,第213頁。這意味著西周早期“禮樂”活動之“六詩”,即是西周“禮樂操演”行為的典型代表。可見,周初天子執政,多種行政措施多賴“耳聞”而非“文本”,而“禮樂”作為非“文本”性活動則當是當時國家政治的基本手段。其四是周初兩類文獻(口傳與文本)之脈絡。以傳世的周初文獻看,當《詩經》和《尚書》最具代表性,就其歷史性質講,當也是口傳文獻與文本文獻的代表。下面就二者的歷史關聯和不同特點談幾點:(1)就內容看,《詩經》飽含早于武王的文王、王季、太王、公劉乃至姜原、后稷等更古老的歷史信息,而《尚書》“周書”所載歷史最早止于武王年代。(2)就文化形態看,周初《詩經》為詠歌,與非文本的“口”“耳”這種古老傳統相聯系,這要比文本形態的《尚書》早了許多,也就是說樂歌《詩經》的歷史要遠遠早于文本《尚書》的歷史。此意味著姬周人先周歷史是多由“口耳”操演的身體傳統保存下來的(尤其在詩樂傳統的脈絡中),而周初“制禮作樂”則使這一傳統發揚光大,同時也意味著周姬人建國前后文字文本水平相對低下的狀況。(3)就文本編纂看,《詩經》和《尚書》的文本形式都比它們的“口耳”形式要晚。詩文本或要到周康王時才出現,即《今本竹書記年》所載康王“三年,定樂歌”?載方詩銘、王修齡撰:《古本竹書紀年輯證》(修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48頁。。據馬銀琴研究,康王“定樂歌”活動中出現了詩文本。?馬銀琴著:《兩周詩史》,第144頁。而《尚書》最初編纂在周昭王、穆王年代。《管子·小匡》有載:“昔吾先王周昭王、穆王,世法文、武之遠跡,以成其名。合群國,比校民之有道者,設象以為民紀,式美以相應,比綴以書,原本窮末。”?黎翔鳳撰:《管子校注》卷八《小匡》,第396頁。饒龍隼認為此文“記述了昭王、穆王時一次成規模地編纂典籍的實況”,而“《書》篇最初之編纂當在其列”?饒龍隼著:《〈書〉考原》,載《揚州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集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80–86頁。。有關口傳與文字傳統的歷史關系,《莊子·大宗師》一則寓言有暗示。其說女偊聞道:“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于謳……”郭慶藩集釋:“副墨,翰墨,文字也。臨本謂之副墨,背文謂之洛誦。聶,附耳私語也。謳,歌謠也。”?郭慶藩撰:《莊子集釋》卷三上《大宗師》,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第256–257頁。這反映出“口傳”與“文字”兩類文獻的鏈條關系和歷史梯度,即歌謠(口傳)當為書寫(文字)之所宗。(4)再就《尚書》文章體式言。《尚書》為我國上古歷史的文獻匯編,其文章體式,偽孔安國《尚書序》一分為六,謂:“典、謨、訓、誥、誓、命。”?而孔穎達將《尚書》文體分為十體,其云:“檢其此體,為例有十。一曰典,二曰謨,三曰貢,四曰歌,五曰誓,六曰誥,七曰訓,八曰命,九曰征,十曰范。”見《尚書正義》卷二《堯典》,第117頁。《說文》的釋義云:“典,五帝之書也。從冊在亓上。,古文典,從竹。”?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卷五上《亓部》,第99頁。又:“謨,議謀也。從言,莫聲。《虞書》曰咎繇謨,暮,古文謨從口。”“訓,說教也。從言,川聲。”“誥,告也,從言,告聲。”“誓,約束也,從言,折聲。”?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卷三上《言部》,第51–52頁。又:“命,使也,從口,從令。”?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卷二上《口部》,第32頁。上述語文體式,就其名看,“從言”“從口”者有五種之多,這意味著謨、訓、誥、誓、命五體出言說之辭。檢視《尚書》全文,當不誤,故孔穎達有云:“自《甘誓》已下,皆多言辭。”[51]阮元校刻:《尚書正義》卷二《堯典》,第117頁。《尚書》之語錄,主以帝王(圣王、時王)或重臣。如“謨”,即謀,就是謀慮、議政、論政,即計議大事大謀。[52]阮元校刻:《爾雅》卷一《釋詁上》:“謨,謀也”邢昺疏:“謨,大謀也。”第2569頁。阮元校刻:《詩經》卷一八之一《大雅·抑》:“訏謨定命。”毛傳:“訏,大。謨,謀。”鄭箋:“大謨定命。”第554頁。又有《尚書·君牙》“文王謨”,《左傳·襄公二十一年》“圣有謨勛”和《后漢書·左雄傳》“周公謨成王之風”之文。《大禹謨》《皋陶謨》即錄大禹、伯益和舜謀政之言。“訓”,即說教、教誡之言[53]段玉裁撰:《說文解字注》第三上《言部》“詁,訓故言也”段注:“故言者,舊言也。訓詁者,順釋其故言也。”第92–93頁。陳奐撰:《詩毛氏傳疏》卷二五《大雅·烝民》“古訓是式”陳奐傳疏:“訓,說教也。”續修四庫全書,第70冊,第378頁。阮元校刻:《詩經》卷一八之一《大雅·抑》:“四方其訓之”毛傳:“訓,教。”第554頁。。孔穎達說《尚書》訓體有《伊訓》《太甲》《咸有一德》《高宗肜日》《旅獒》《無逸》諸篇,其文皆主以言說之辭。“誥”,即告,“以約勤謹戒眾”[54]阮元校刻:《爾雅》卷三《釋言》郭璞注,第2582頁。又阮元校刻《尚書》卷一七《多方》“誥告爾多方”孔穎達疏:“以言告人謂之誥”。第228頁。。《尚書》中此體最多,孔穎達說有二十篇,而又以《周書》為多。如周初“八誥”,皆周公之誥辭[55]過常寶以為《召誥》亦周公“誥殷遺民之辭”。參見過常寶《制禮作樂與西周文獻的生成》,第144–145頁。,為訓誡殷頑民及四方不服者之言辭。[56]蘇軾撰:《書傳》卷一五《周書·多方》云:“自《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八篇,雖所誥不一,然大略以殷人不心服周而作也……多方所告不止殷人,乃及四方之士,是紛紛焉,不心服者非獨殷人也。”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54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誓”,即約束、戒告,初以言約之,軍旅使用尤多。《周禮·秋官》士師以五戒輔刑罰:“一曰誓,用之于軍旅。”今《尚書》之《甘誓》《湯誓》《牧誓》《費誓》皆此。“命”,即使、令,為呼號、發號施令。《說文·卪部》:“令,發號也。從亼、卪。”[57]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卷九上《卪部》,第187頁。《口部》:“號,呼也,從號,從虎。”可見,從口、從令之“命”,初或重聲音之呼、召和告。[58]阮元校刻:《毛詩正義》卷一三之一《小雅·北山》:“或不知叫號”毛傳:“叫,呼也。號,召也。”第463頁。王念孫撰:《廣雅疏證》卷三上《釋詁》:“號,告也。”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86頁。據此可知,以上五體(謨、訓、誥、誓、命)從言、從口,皆源出有聲之言語。反倒是“六體”居首之“典”,卻為從“冊”之“書”,與音聲無關。孔穎達對此亦大惑不解云:“其堯、舜之典,多陳行事之狀,其言寡矣,《禹貢》即全非君言,準之后代,不應入《書》,此其一體之異。”[59]同注1。其實不然。如依甲骨文,“典”刻辭作“”,徐中舒說“從冊,從手,象雙手奉冊之形”[60]徐中舒主編:《甲骨文字典》卷五,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2003年,第490頁。,會祭祀之意。于省吾《釋工》說契文“工”出祭祀,即“貢典()”,“猶言獻冊告冊也”,即“書祝告之辭于典冊,祭而獻于神,故云‘貢’”[61]于省吾著:《雙劍誃殷契駢枝 雙劍誃殷契駢枝續編 雙劍誃殷契駢枝三編》,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164–166頁。。也就是說,依甲骨文,“典”也是“告辭”,本祭祀時以語以冊之祭告,會“祭祀之語辭和典冊俱奉”之義。此意味著《說文》“典”的釋義,當祭告之辭文本化后的情況,即書冊義當后出。其實,漢唐學人早有明確表示,云《尚書》六體皆“本于號令”。班固《漢書·藝文志》云:“《書》者,古之號令,號令于眾,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曉。”[62]班固撰:《漢書》卷三〇《藝文志》,第1706–1707頁。以“言”“聽”對文,知“號令”本音聲而非文字。劉知幾《史通》直接說:“蓋《書》之所主,本于號令,以宣王道之正義,發話言于臣下。故其所載,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63]張振珮《史通箋注》,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頁。由此可以認為,周代或自昭王始,即有一個先圣先王之語及議政要言陸續文本化的進程,而《尚書》文字即是該進程中口傳傳統文本化的結果。《說文》錄古文“”字,也透露出其口傳文獻形諸竹書的轉變環節。基于此,知先秦“文獻”一語,實蘊含口傳傳統和文本傳統復雜的歷史關系,劉師培對此的理解宏通而精到。他視文獻傳統為兩脈:一是“文”,即文本書寫傳統;二是“獻”,即身體操演傳統;其《文獻解》說:“儀、獻古通。故《虞書》儀獻《漢碑》作黎儀,《周書》民獻《大傳》作民儀,是文獻即文儀也。書之所載謂之文,即古人所謂典章制度也;身之所習謂之儀,即古人所謂動作威儀之則也……儀之于文,對文則異,散文則通。”[64]劉師培著:《左盦集》卷三《文獻解》,載《劉申叔遺書》,第1222–1223頁。他肯定了“動作威儀”這一“身體文獻”及其傳統的存在,而出自身體的口傳文獻則遠古老于文字記錄的文本文獻。而在文本文獻到來之際,其前身當與口傳傳統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由此可見,周初以“制禮作樂”為興國之舉,更多是基于姬周人自己的口傳身體傳統而非殷商人的文字文本傳統。除此之外,另一現象亦值得關注。即先秦文獻中“周樂”不見以符碼方式對其音聲形態進行書寫的文本(即“樂譜”)記錄,反倒是那些有關“周樂”活動之實踐性特征如儀式、儀程和身體操演的記錄頻頻見于《儀禮》的《鄉飲酒禮》《燕禮》等文獻。就這類“文本”所錄看,其特點是不主“樂音”,只錄同儀式性活動及其相生相伴的“樂儀”活動,即歸屬于“操演性”文化方面的特質。當然不可忽略的是,就音樂言,音聲物理部分之屬性自是其自然實在,無論古今皆然。于此而言,樂音載之于聲,即現即逝,來無影去無蹤,形貌皆無,其自然之象難以識見,也是古今皆然;因此之故,音樂的形貌皆隱匿于人和游離于社會。此“非文本”之特性使然。若見其形,非有“文本”書寫和符號記錄之實存不可。然西周“周樂”,因更無書寫之物質性依存(如“樂譜”),故這又為它的社會性實在再平添一層迷霧。音聲的物質性依存既是“音樂”的特殊之象,也是“音樂”鏈接人和社會的一條通道。西周周樂“音聲”之維無書寫物質之實存,正是西周“周樂”的特殊本相。那么,西周“周樂”(音聲)之實存存于何處呢?事實上,它確有所存之處。從社會角度看,其實存處有二:一是外存于“操演”;二是內在于“人心”。對“人心”和“操演”的依附即是西周“周樂”的物質之基和形見之貌。對于音聲說,它雖仍難形見,卻既可由“心”感知,亦可從身體和操演上去發見、捕獲和體認。“人心”和“操演”,彌補了“周樂”無文本性留存的空白,由此而有了不同的實存之“象”(想象和具象)。由此,對于“操演性”實踐的西周“周樂”來說,其社會性實存的特質或主要包括在依附性、身體性、操演性、社會性和族群性等屬性之中。然而,這些可以呈現于社會的諸實踐性特質卻多數難以在文本中被書寫到位,故容此對其特質再申說如后。
1.“依附性”特質。所謂“依附性”,指音樂(音聲)與其社會性實存物之關系。西周“周樂”(音聲)的物質依存非止于其“物理”自在,即非僅反映為單一的音聲之物(空氣振動)的存在,而更實存于“人心”。也就是說,古人更愿意將音聲作為一種社會現象而與人系連在一起。古代“心”字多義,或指“人心”,或指“人腦”等。如《說文·心部》:“心,人心,土藏,在身之中。”[65]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卷一〇《心部》,第217頁。《列子·湯問》:“內則肝、膽、心、肺……。”[66]楊伯峻撰:《列子集釋》卷五《湯問》,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第180頁。又如《國語·周語上》:“夫民慮之于心。”[67]徐元誥撰:《國語集解》第一《周語上》,第13頁。《孟子·告子上》:“心之官則思。”[68]焦循撰:《孟子正義》卷二三《告子上》,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792頁。可知,在古代“心”(腦)之于“音聲”,與其源出和記憶皆有關。關于“源出”,《禮記·樂記》云:“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69]阮元校刻:《禮記正義》卷三七《樂記》,第2527頁。這是說,音聲之所出同“心”相關,無“心”,難以言“樂”。關于記憶,《隋書·何妥傳》:“臣少好音律,留意管弦,年雖耆老,頗皆記憶。”[70]魏徵等撰:《隋書》卷七五《儒林傳·何妥》,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1714頁。《釋名·釋言語》:“憶,意也,恒在意中。”[71]任繼昉纂:《釋名匯校》卷四《釋言語》,濟南:齊魯書社,2006年,第202頁。《關尹子·五鑒》:“譬猶昔游再到,記憶宛然。”[72 ]《左傳·昭公元年》:“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73]阮元校刻:《春秋左傳正義》卷四一《昭公元年》,第2025頁。這是說,音聲之留存亦同記憶有關,或被記住或被遺忘,即音樂的識記與“心”(腦)記憶直接相關。由上可知,古人識音是聯系到人的,其基本認識有二:一是“音聲”生于“心”;二是“音聲”識記(即記憶)于“心”(即“腦”)。這是周初“禮樂”時代人們識記“音聲”的基本路徑—重口、耳、心。所以《毛詩序》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74]阮元校刻:《毛詩正義》卷一之一《毛詩序》,第269頁。《尚書·舜典》云:“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75]阮元校刻:《尚書正義》卷三《舜典》,第131頁。辨之音律,則更是“以耳齊其聲”。可見,周初禮樂操演文化中“音聲”對于人尤其是對“人心”的強烈依附。音聲對“人心”的這種依附,實為西周“周樂”(音聲)之社會性存留的特定方式。[76]在今天看來,音樂音聲的這種對人心的依附,主要是想象性的。但從古籍中大量的事例可知,這種想象作為一種意識確實存在于古人的“音樂”觀念之中的。有譜之樂(如書之竹帛—依附于譜),“譜”便成為“樂”的實存方式(為其依附的主要對象)。“樂”之音聲形態,稍縱即逝,而樂譜形態,則可越瞬時而駐久長。故“譜”在,即“樂”在,作樂可依譜而行。這也意味“樂”與“人”可以分離(即與“心”無關):無“人”,樂自在“譜”上。無譜之樂(源存于心—依附于人),因人之言志、緣情而發,口耳相傳,人人相授,人為“樂”聲之源。從“人”到“人”,終究不離人。這意味著“樂”與“人”不可分離(自然難離于“心”):無“人”,即無“樂”,更無所生發。在周代,“樂工”適遠即意味此樂于此地消逝。春秋末魯哀公時,就因諸太師離魯而適齊、楚、蔡、秦等地[77]阮元校刻:《論語注疏》卷一八《微子》:“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缼適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漢,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第2530頁。而出現人失樂崩的情形。“口耳相傳”是樂輾轉綿延之象,而“心心相印”則樂之實根。它表明樂本在人心且在人心間流轉和在情志間交糾。西周樂之無譜,然從“心”到“心”,則表明樂存“人心”,一旦棄離“人心”和失之“口傳”,樂自然無法自存(與今所謂音樂“本體”兩歧)。可見,“人心”即“樂”之依存物,亦“樂”之現實實在之本根。此即是《禮記·樂記》反復強調之理:“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動,故形于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又:“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78]同注 69,第1527頁。等等。據此,亦知西周“周樂”的三層意涵,即:音、心(人)、物。“音由心生”“感物心動”都離不開“心”,并表明此三者互依互存,難相割舍,存多重的關聯。音(樂)既依附于人“心”,又受制于外“物”,同時聯通、展現和儀式化“組構”于歌、樂、舞并形就社會實在之象。這一切說明,西周“周樂”之概念非指單一的音聲之物,即便不談其他社會取向,也非僅為音之“形態性”實在。《樂記》開篇即開宗明義地提示:“樂”不當止于音(五音),它同時還包括了器(樂器)和容(形貌)。如果僅用“音聲”(及其組織)來理解西周“周樂”,便窄化或誤釋了周代“禮樂”的本義。這一切當源自或離不開“非文本性”這一原點。所以,西周“周樂”作為“非文本性”實在,它絕非能由其物理性“形態”的概念所能囊括。而“形”,實為視覺之象,亦為其所感,本是對應于視覺的概念,與聽覺無關。然“音聲”,為聽覺之對象,亦為其所感,它轉瞬即逝,摸不著亦看不見,更不見于“形”,故音聲之所謂“形態”無從由來。可見在西周,“音”只能聽聞,不可形見,而“樂”則兼二者而有之,然此形(形象)非彼形(形態)也。如《詩序》所云:“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79]同注 74,第270頁。這里,“樂”之“音聲”之形故不可見,然源自“心”之生發和表象的言語、嗟嘆、永歌、手舞、足蹈之“象”皆可形見。所以所謂的“樂”(或“音樂”),當為形(象)、聲(音)、意(義)相疊加的復合概念,而此“形”則非聽覺對象之音聲之形而為視覺對象之容貌之形。《樂記》言樂一再提醒我們,對于音樂,古人更在乎其中之“意”而不僅僅是其中之“形”。“周樂”無“譜”所依,故“音”單純的所謂“形態”不復存留,古人的關注點似亦非此。先秦文獻不見(樂)“譜”的事實已是一種暗示。反倒是對“人心”“操演”和“儀式”的關注為其尋常,進而因“周樂”對“人心”和“操演”的依附而延展出來的對“人”對“族群”對“社會身份”和對“禮儀”政治的關注及其有關它們間多重關聯的事例的記述則于文獻中數不勝數[80]這種情形在專門的論樂文本《樂記》中十分常見,如《禮記正義》卷三八《樂記·樂言》篇所云:“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后心術形焉。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啴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卷三九《樂記·魏文侯》篇亦云:“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眾。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眾。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第1535、1541頁。。所以,西周“周樂”因其“非文本性”的特殊性質,不可能只有“聲音”一維的所謂的本體性存在。由此,這種“依附性”特質在理解西周“周樂”時有重要且特別的意義。
2.“身體性”“操演性”特質。西周“周樂”既是“身體”和“操演”的對象,也是“身體”和“操演”的結果,而非單純“聽覺”的對象和聽聞的結果。同“周禮”一樣,“周樂”在禮典意義上,當涵括三個部分:儀式理念、身體操演和名物制度。就“禮典”言,沈文倬以為,它包括“名物度數”和“揖讓周旋”兩個部分[81]沈文倬著:《宗周禮樂文明考論》,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5頁。,“揖讓周旋”即是“身體操演”。西周“周樂”的“身體性”和“操演性”特質源自“禮樂”文化的儀式性質,同時也成為其儀式性的構成要素以及“禮樂”活動生發的一個社會基點。作為“禮儀”之樂,西周“周樂”自然有對身體的操作和控制的要求,不僅強調樂之生發的身體性和操演性,同時也強調樂之目的的身體性和操演性。也就是說,儀式之樂,是離不開身體的儀式參與的:“樂”生發于人的身體操演(包括“心”在內),同時反過來又指向對人身體行為(也包括“心”)的規訓。故“身體”和“操演”始終是儀式之樂的核心要素。最清晰的記載見于《儀禮》諸篇,如《鄉飲酒禮》載:“設席于堂廉,東上。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二人,皆左何瑟,后首,挎越,內弦,右手相。樂正先升,立于西階東。工入,升自西階。北面坐。相者東面坐,遂授瑟,乃降。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卒歌,主人獻工。工左瑟,一人拜,不興,受爵。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祭。工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眾工則不拜,受爵,祭飲,辯有脯醢,不祭。大師,則為之洗。賓、介降,主人辭降。工不辭洗。”[82]阮元校刻:《儀禮注疏》卷九《鄉飲酒禮》,第985頁。禮儀皆一個個具體的行為聚合而成。據該“儀式”過程可知,有眡瞭相瞽矇進入儀式現場,照各種儀節、儀程以及歌樂操演行儀。其中儀節皆是通過身體行為(包括歌樂操演)來實現的。除樂工音樂操演如相瞽、授瑟、工歌、卒歌外,尚有非音樂性儀節如工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等各種身體操演行為相間其中。這些行為同儀式的儀節、儀程以及其他參與者的操演一道,共建和完成“鄉飲酒”之禮儀,而非僅為停止于紙面(文本)的禮典文字。[83]筆者按:禮儀文本如《儀禮》等所載則當是針對操演活動及其社會隱喻的文字記錄。《儀禮·燕禮》中亦載類似情形,如:“公又舉奠觶。唯公所賜。以旅于西階上,如初。卒。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主人洗,升,獻笙于西階上。一人拜,盡階,不升堂,受爵,降;主人拜送爵。階前坐祭,立卒爵,不拜既爵,升,授主人。眾笙不拜,受爵,降;坐祭,立卒爵。辯有脯醢,不祭。”[84]阮元校刻:《儀禮注疏》卷一五《燕禮》,第1021頁。等等。又,周初在“禮樂”的身體參與中,“耳”是特別的部位。《詩集傳·靈臺》注云:“古者樂師,皆以瞽者為之,以其善聽而審于音。”[85]朱熹撰:《詩集傳》卷一六《大三雅·靈臺》,第218頁。《左傳·昭公二十年》亦云:“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86]又云:“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流,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春秋左傳》卷四九《昭公二十年》,第2093–2094頁。聽“聲”可平“心”,亦可“成政”,可知古人“耳聽”傳統聯系廣泛。其實,虞舜前早有以耳“協風聽樂”之事。《國語·鄭語》云:“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韋昭注:“協,和也。言能聽知和風。”[87]徐元誥撰:《國語集解》第一六《鄭語》(修訂本),第466頁。又,《春秋左傳正義》卷四四《昭公八年》:“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杜預注:“幕,舜之先。”第2053頁。司馬遷《史記》卷三六《陳杞世家》裴骃集解:“鄭眾曰:‘幕,舜之先也。’”司馬貞索隱:“按:賈逵以幕為虞思,非也。《左傳》言自幕而至瞽瞍,知幕在瞽瞍之前,非虞思明矣。”第1581頁。后又有禹“聲為律,身為度”之說。史記司馬貞索隱云:“禹聲音應鐘律。”裴骃集解云:“聲與身為律度,則權衡亦出于其身。”[88]司馬遷撰:《史記》卷二《夏本紀》,第51頁。而《藝文類聚·人部·圣》引《風俗通》說:“圣者,聲也,通也。言其聞聲知情,通于天地,條暢萬物也。”[89]歐陽詢撰:《藝文類聚》卷二〇《人部四·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358頁。后至周代,樂人多瞽矇,亦只以耳聽而未有目視。《史記·律書》稱:“武王伐紂,吹律聽聲。”[90]司馬遷撰:《史記》卷二五《律書》,第1240頁。《國語·周語》亦謂:“瞽告有協風至。”韋昭注云:“瞽,樂太師,知風聲者也。”[91]徐元誥撰:《國語集解》第一《周語上》,第17頁。《晉語》有“瞽瞍循聲”而“不可使視”[92]徐元誥撰:《國語集解》第一〇《晉語四》,第360、363頁。和《楚語》有“師工之誦”與“矇不失誦”之語,韋昭注云:“師,樂師也。工,瞽矇也。”[93]徐元誥撰:《國語集解》第一七《楚語上》,第501頁。由此可知,無論古之神瞽、圣王,還是后世的太師、瞽矇,候氣聽八方之音,辨音律,定歷法,都難離“耳”與“聽”,且系之于制度。“耳”“聽”二字,早見于殷墟甲骨文,郭沫若以為“古聽(聽)、聲(聲)、圣(聖)乃一字”[94]郭沫若著:《卜辭通纂》北京:科學出版社,1983年,第489(137)頁。,當歸屬“耳聽”傳統一脈。而該傳統周初又為“禮樂制度”所承繼。《周禮·大師》云:“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兇。”[95]阮元校刻:《周禮注疏》卷二三《春官·大師》鄭玄注云:“《兵書》曰:‘王者行師出軍之日,授將弓矢,士卒振旅,將張弓大呼,大師吹律合音。’”孔穎達疏云:“釋曰:《兵書》者,武王出兵之書。”第796頁。至春秋其遺緒猶存,如晉國師曠仍“吹律聽聲”:“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96]阮元校刻:《春秋左傳》卷三三《襄公十八年》杜預注云:“歌者,吹律以詠八風。南風音微,故曰‘不競’也。師曠唯歌南北風者,聽晉楚之強弱。”第1966頁。周代主以操演并聯系政治的“禮樂”傳統,對身體(耳聽、言語)有高度的依賴。《左傳·文公六年》有載:“古之王者……并建圣哲,樹之風聲,分之采物,著之話言,為之律度,陳之藝極,引之表儀,予之法制,告之訓典……”[97]阮元校刻:《春秋左傳正義》卷一九上《文公六年》,第1844頁。這里的“話言”“訓典”,即是古王遺制中先于文本存在的“口”“耳”傳統。《說文·言部》云:“言,直言曰言。從口,聲。”“話言”即“善言遺戒”,“訓典”則“取其言以語之”[98]阮元校刻:《春秋左傳正義》卷一九上《文公六年》杜預注及孔穎達疏,第1844頁。,它們皆為書錄之淵藪。另見《國語·周語》單穆公答周景王之問政云:“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故必聽和而視正。聽和則聰,視正則明。聰則言聽,明則德昭。聽言昭德,則能思慮純固。以言德于民,民歆而德之,則歸心焉。”[99]徐元誥撰:《國語集解》第三《周語下》,第109頁。這里“耳聽”等身體行為被反復強調表明,“禮樂”文化與早期的身體傳統(即“非文本”性)有著直接淵源關系。同時,西周禮儀活動,因其主體是人及各種的身體行為(而非“文本”),所以它也并非只是單一的音樂操演行為,更不是抽離了人(包括儀式)的單一的“音聲”本身,也就是說,“禮樂”是不可簡單化約之“樂”,自然也絕非能為“音樂”的形式所包含。從現有文獻看,西周“周樂”最被關注和強調的是它社會性的儀式操演,而絕非物理性的聲音實體。從這里可知,作為“非文本”之樂的儀式實踐,西周“周樂”展示和呈現的是儀式中人的“身體”和“操演”以及“樂”之音聲和容貌的總體,并通過儀式整全的儀節和儀程來加以實現。這充分表明,禮儀活動,其意義并非只由音聲單元來展示和完成,而是綜合各種儀式要素尤其是人的整個身體行為來展示和完成的,而“樂”也并非是剔除了聽覺對象以外的其他儀式形態的單一的“音聲”現象。所謂儀式之樂,從《儀禮》文本看,重點即在儀式活動的總體行為,盡管它總是以記錄儀式的單個行為為基礎,但也并非僅局限于其中的音樂部分或音樂中的音聲。由此可見,儀式之樂是不可能同儀式整體和身體操演相分離的,也就是說音樂的音聲部分還不能構成儀式和儀式音樂的全部。這有同鄭玄所寫《詩譜》一樣,非僅著眼于“詩樂”辭章本身,而更是包含了社會和文化的多重網絡。與此同時,儀式行為的“身體性”和“操演性”還指向了對參與者身體的規訓以及這種規訓的社會效應。所以當參與者將自己身體投入到儀式之中后,所有的身體行為都必須遵循其儀程和儀節之規則,并實現音樂操演和身體規訓同總體儀式間的互動共生。文獻中這類事例不少。如《周禮·樂師》:“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車亦如之,環拜以鐘鼓為節。凡射,王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蘩》為節。”[100]阮元校刻:《周禮注疏》卷二三《春官·樂師》,第793頁。鄭玄以為:“人君行步,以《肆夏》為節。趨疾于步,則以《采薺》為節。”又謂:“行者,謂于大寢之中;趨,謂于朝廷。”[101]阮元校刻:《周禮注疏》卷二三《春官·樂師》,第793頁。《禮記·射義》:“《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繁》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為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為節,卿、大夫以循法為節,士以不失職為節。”[102]阮元校刻:《禮記正義》卷六二《射義》,第1686–1687頁。《大戴禮·投壺》:“降揖,其阼階及樂事,皆與射同節。”[103]王聘珍撰:《大戴禮記》卷一二《投壺》,第243頁。等等。可見,凡儀式活動,無論上至國君,還是下至士人,其身體和行為皆受制于儀式和儀式之“樂”。經籍中“以……為節”之句式,則清晰地傳達了“樂”本身的儀式性和對儀式參與者身體行為規訓的明確指向。這也正是《禮記·樂記》所反復強調的:“先王之制禮樂,人為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至則不爭,禮至則無怨”。[104]阮元校刻:《禮記正義》卷三七《樂記》,第1529頁。可見,西周“周樂”之禮儀及其社會意義的獲得即是通過參與者的“身體”及其儀式過程的“操演”來實現的,而絕非簡單地以聆聽和靜思來面對其音樂形態。故簡單以音聲形態為目的的系統的認知理論,在先秦音樂知識系統中是沒有現實和實踐的基礎的。
3.“社會性”“族群性”特質。在現有文獻中,周代“周樂”的文本取向亦可被關注。一個顯在的文本事實是:周人對周代音樂的認知,甚多質性的社會“認知”,而幾無形式性的音樂“分析”。也就是說,周人的專注點在音樂的社會屬性方面,而并不在意或刻意于其“形式”或“形態”問題。從文本看,音樂認知的文本焦點,主要集中于社會、政治、倫理、地域和族群等方面。此例甚多,不勝枚舉,茲各取數例列于后。如《周易·豫》載:“先王作樂以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105]阮元校刻:《周易正義》卷二《豫》,第31頁。《禮記·禮器》載:“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以節事;修樂,以道志。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也。”[106]阮元校刻:《禮記正義》卷二四《禮器》,第1441頁。于此關注的,乃“樂”之社會屬性。又,《禮記·樂記》載:“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又載:“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107]同注 104,第1527–1528;1528頁。于此強調的,乃“樂”之政治屬性。再如《尚書·舜典》載:“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孔安國注云:“倫,理也。”[108]阮元校刻:《尚書正義》卷三《舜典》,第131頁。《禮記·樂記》載:“樂者,通倫理者也。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眾庶是也。唯君子為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109]同注 104,第1527–1528;1528頁。于此確認的,乃“樂”之倫理屬性。另,《儀禮·鄉飲酒禮》載:“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鄭玄注云:“鄉樂者,風也。”[110]阮元校刻:《儀禮注疏》卷九《鄉飲酒禮》,第986頁。《呂氏春秋·音初》說“音”有東、南、西、北之分:孔甲《破斧之歌》為東音,涂山女妾“候人兮猗”為南音,殷整甲徙宅“西河”而有西音,有娀氏二女“燕燕往飛”為北音。[111]陳奇猷著:《呂氏春秋校釋》卷六《音初》,第334–335頁。《左傳·成公九年》云:“問其族,對曰:‘伶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杜預注:“南音,楚聲。”[112]阮元校刻:《春秋左傳正義》卷二六《成公九年》,第1905頁。于此留意的,乃“樂”之方域屬性。又如《禮記·明堂位》載:“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拊搏、玉磬、揩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鄭玄注云:“四代,虞、夏、殷、周也。”又:“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垂之和鐘,叔之離磬,女媧之笙簧。”[113]阮元校刻:《禮記正義》卷三一《明堂位》,第1491頁。以及《詩經》“風雅頌”三分所暗含的人群(或民系)分剖等。于此凸顯的,乃“樂”之族群屬性。也就是說,西周的“周樂”,因其社會性取向和依附于人的族群性質等,故很難拔離它最深層的文化根由。由此可見,先秦典籍所載“樂”之理論認知,無論是社會的、政治的、倫理的、地域的,還是族群的,本質上都是質性的社會認知,故針對“樂”之社會屬性及人文性質者甚多,如《莊子》所云“詩以道志”,“樂以道和”,[114]郭慶藩撰:《莊子集釋》卷一〇下《天下》,第1067頁。《荀子》所云“詩言是其志也”,“樂言是其和也”,[115]王先謙撰:《荀子集解》卷四《效儒》,第133頁。《春秋繁露》所云“詩道志故長于質,樂詠德故長于風”,“禮之所重者在其志,志敬而節具,君子予之知禮,志和而音雅,則君子予之知樂……重志之謂也”[116]蘇輿著:《春秋繁露義證》卷一《玉杯》,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第36、27頁。等等。而那種單純以“樂”之形態為對象的形式認知者則少之又少,幾無所見[117]如《國語·周語下》所載:“王弗聽,問之伶州鳩。對曰:‘臣之守官弗及也。臣聞之,琴瑟尚宮,鐘尚羽,石尚角,匏竹利制,大不逾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圣人保樂而愛財,財以備器,樂以殖財,故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絲尚宮,匏、竹尚議,革、木一聲。’”徐元誥撰:《國語集解》第三《周語下》,第110–111頁。。這充分說明,西周“周樂”之“質”在“志”在“和”,而非在“形”在“聲”。由于這種文本認知取向的存在,故音樂“形態”難有機會在周人的文獻記錄中成為主導。當然,不可不見涉及音樂“形態”的零散記述,如《周禮》中提到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及十二律律名等[118]阮元校刻:《周禮注疏》卷二二《春官·大司樂》,第788–789頁。,《國語·周語》伶州鳩對景王問中也見七律、十二律名和音名[119]如《國語·周語》所云:“王將鑄無射,問律于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鐘,百官軌儀,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于十二,天之道也,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鐘,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由是第之:二曰太蔟,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三曰姑洗,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也。四曰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為之六間,以揚沈伏,而黜散越也。元間大呂,助宣物也。二間夾鐘,出四隙之細也。三間仲呂,宣中氣也。四間林鐘,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五間南呂,贊陽秀物也。六間應鐘,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徐元誥撰:《國語集解》第三《周語下》,第113–121頁。,《左傳》中另有清濁、大小、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等樂語的記載[120]阮元校刻:《春秋左傳正義》卷四九《昭公二十年》,第2094頁。。不過,恰恰是零星、散見和不集中記載本身,已將“周樂”的樂音形態與其文本書寫間的疏離狀況表露無疑,倒是有關“鐘律”的文字資料和音樂考古的音律資料,潛藏更多有價值的歷史信息。如蔡邕《樂令章句》說:“古之為鐘律者,以耳齊其聲。后(人)不能,則假數以正其度,度數正則音亦正矣。”[121]司馬彪:《后漢書》志第一《律歷志上》劉昭注引,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3016頁。此中所透露的重要信息有二:一是古之“鐘律”有兩個階段;二是其分野在于“耳聽”與“數度”。這里,與鐘律有關的歷史信息值得注意。就殷甲骨文看,商代無“鐘”字,惟以“庸”字稱銅制合瓦形擊奏之器,與鐘相類。而“鐘”之字形,始見于金文。這意味著,“鐘”字始自周代,周人徑稱合瓦形青銅擊奏樂器為鐘。“鐘律”自當周人命名,為周制。而據出土西周編鐘測音,西周“鐘律”主羽—宮—角—徵四聲,無商聲。[122]子初著:《巡禮周公—音樂考古與西周史》,《中國音樂學》,2019年,第3期,第52-54頁。此音律當出姬周人實踐為先的周初“禮樂”,亦屬鐘律之第一階段,即源出于“耳聽”[123]筆者按:周初“周樂”音律無“商音”從“操演”文化角度好理解,因為在“耳聽”標準中,“人”是其出發點,人的社會存在又具其先在性,社會層面出發的意識或優先于“度數”上的邏輯推導。。也就是說,周初,作為“禮樂制度”之“周樂”依據的是身體實踐,即屬“以耳齊其聲”的“操演”文化系統。春秋已降,鐘律的“耳聽”傳統仍有延續。周景王二十三年,單穆公仍舊說“夫鐘聲以為耳也,耳所不及非鐘聲也”,“耳之察和也,在清濁之間”。[124]徐元誥撰:《國語集解》第三《周語下》,第108頁。戰國初的曾侯乙鐘律,黃翔鵬說也是“一種實踐的體系”。[125]黃翔鵬著:《釋“楚商”》,《文藝研究》,1979年,第2期,第75頁。“以耳察律”之實踐當屬“操演”體系,而恰恰是因“操演”實踐性的存在,才是音樂“形態”難見于文本記載的主因。也正因為此,史籍只是在有關音樂制度(如《周禮》)和有關音樂操演者言談(如《國語》伶州鳩)的記錄中才能稍多地見到一些有關音樂“形態”的信息。當然,這并不能說周代周人對音樂“形態”一無所知或不屑一顧,而只是因為周初“周樂”屬于與身體相關的“耳手”操演系統而非屬于與文字相關的“文本”書寫系統而已。也就是說,“禮樂”操演之聲音記敘主要不在文本系統之列。所以,今人難以從文本中全面地了解和把握“周樂”的音樂形態。在周代歷史中,西周“周樂”的“文本化”有一個漸進的過程,盡管緩慢長久,但影響卻不可小覷。現有資料表明,“文本”系統中的西周“周樂”,其音樂形態幾近被忽視、壓抑或排斥(或者說也是難以被記錄的),而它們仍主要保存在相對狹小的伶人專門群體及他們的操演傳統和言說話語中,惟有一些他們對音律的言說的記載還保留在文本之中。對照史官的制度性書寫(如《周禮》)和伶人(韋昭注:司樂官)言樂(如《國語》中州鳩所言)的區別和差異便知其一二。從歷史文獻看,直到春秋中葉,文本系統中才有了較集中的有關音律(也屬“形態”)的專門記載出現,而特點是“音律”以“度數”方式通過“文字”呈現于“文本”,此即《管子》中“三分損益”的記載[126]黎翔鳳撰:《管子校注》卷一九《地員篇》云:“凡將起五音,凡首,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以是生黃鐘小素之首,以成宮。三分而益之以一,為百有八,為徵。不無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有三分而復于其所,以是成羽。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成角。”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1080頁。。可以認為這是“鐘律”第二個階段—“后人不能,則假數以正其度”一個標志性的時間節點。與第一階段的身體和感性前提(“以耳齊其聲”)不同的是,此理性前提之“數”和“度”成為了第二階段“鐘律”的基礎。“度”托之以“數”,而又以“數”字形見于“文本”,“數”“度”通過“文本”共謀和助力于相關制度的形成和威權的出現。如《國語·周語》州鳩答景王問所云:“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鐘,百官軌儀。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于十二,天之道也。”[127]同注 124,第110–111頁。《史記·律書》亦云:“神生于無,形成于有,形然后數,形而成聲。”[128]司馬遷撰:《史記》卷二五《律書》,第1252–1253頁。西漢劉歆《鐘律書》對此總結稱,其大率有五:“一曰備數,一、十、百、千、萬也;二曰和聲,宮、商、角、徵、羽也;三曰審度,分、寸、尺、丈、引也;四曰嘉量,籥、合、升、斗、斛也;五曰權衡,銖、兩、斤、鈞、石也。”[129]參見房玄齡等撰《晉書》卷一六《律歷志》,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474頁。又《漢書》卷二一上《律歷志》云:“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所以算數事物,順性命之理也,本起于黃鐘之數。聲者,宮、商、角、徵、羽也。所以作樂者,諧八音,蕩滌人之邪意,全其正性,移風易俗也。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鐘之長。量者,龠、合、升、斗、斛也,以為量多少也,本起于黃鐘之龠,用度數審其容。衡權者:衡,平也,權,重也;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于黃鐘之重。”第956–969頁。在這里,“數”居首位,統領“聲”“度”“量”“衡”及其余,四者皆以“數”釋之,并皆形之于“數”。此“假數以正其度”正是“鐘律”第二階段的寫照。可見,《鐘律書》所云并非針對前一階段“以耳齊其聲”的音律實踐。明人朱載堉更有扼要概說:“上古造律,其次聽律,其后算律。”[130]朱載堉撰,馮文慈點校:《律學新說》卷一《約率律度相求第二》,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86年,第12頁。又云:“《虞書》《周禮》有聽律之官,無算律之法。典同所謂數度,為樂器言之。至于律同合聲,陽左旋而陰右轉,觀其次序,不以算法論矣。算法之起殆因律管有長短,此算家因律以命術,非律命于算也。”同 129,第12頁。這種以“數”字來辨識事物和記錄音聲的特殊方式,可以讓無形之“音聲”現身,并將人的目光引向“音聲”的一種具有穩定可見性的符碼實像,使不可見之“音聲”之物進入到可見之文字與書寫場域,由是,“文本”文化給“音樂”音聲帶來一種理性的視覺直觀,并成為促成其視覺轉向的重要媒介,而此時耳之聽覺感性則被撇在了一邊。然反過來看,它又成為了削弱甚至消解“禮樂”之操演原根性的潛在推力。以“度量”之“數字”觀照音樂,雖可使人獲得其原理上的認知,及數理直觀和想象,然卻難取代音樂獨特的感性和操演品性,甚或還可能丟失人們對音樂音聲的社會直觀、感受和文化體認。“度”“數”之文本化,是中國音樂歷史進程中一次影響深遠的變故,它開啟了音樂“形態”進入文本系統的文化之旅[131]當然,此還非“樂譜”,但可以認為此已是聲音通過語言符號而進入文本之先聲的預示。,也使得音樂在音聲的“操演”之外又多了一種“文本”化的文化樣態。[132]這也當是日后“樂譜”文化產生的重要契機和前提之一。“音樂文本”在周代的出現,一方面使音樂形式的理論表達有了可能并使其成為現實,另一方面也給“禮樂文化”以巨大沖擊,使原先基于操演文化的“周樂”經歷了一次被迫的轉型—從單純的“操演”文化向“操演”文化和“文本”文化混合的文化形態轉型。在“禮樂文化”層面上,它更是加速了“禮”(目標)“樂”(手段)分離、“禮”(意涵)“儀”(形式)分離和“意義”(理論)和“操演”(實踐)分離的步伐。在“國家治理”層面上,也使周初通過“操演”文化建立起來的“禮樂制度”權威受到挑戰,并因此而由盛而衰、日漸式微;相反,以“文本”文化助力的對“禮樂制度”的系統書寫和闡釋的社會影響力卻與日俱增,其中文本和理論闡釋的社會意義與其價值在諸多方面也嶄露頭角,并逐漸取代了原有的操作性實踐及其體驗和隱喻。“三禮”中有關音樂的文字記述尤其是《禮記·樂記》書寫文本的出現即可視為是這一過程的遺留物和印記。由此看,西周“周樂”鮮明的“社會性”“族群性”特質正是通過“文本”的文化方式而得到更為充分的彰顯和體現,而與此同時,西周“周樂”的操演目標及其社會意義在其文本系統中也有了更徑直和清晰的表達與傳遞。
總之,西周禮樂制度和社會文化與西周“周樂”的關系是全面關聯的:一方面西周的時代政治對西周“周樂”的社會性質產生重大影響,另一方面姬周人的歷史文化對西周“周樂”的特征如非文本性、身體性、操演性、社會性和族群性等也有深度的根本性浸染;而同時,西周“周樂”的歷史存在所造就和型塑的西周“禮樂制度”的文化表征及其社會實在,又使得西周社會沿著禮樂文化的特定方向不斷地伸延和推展,終而形成整個周代“周樂”的基本文化類型。
結 語
綜上,可知西周“周樂”同西周歷史情境有密切的關聯和互動,它既受西周的歷史現實影響,同時其自身也成為了歷史的具體情境之一;而更深一層則是它聯系著一個基本然而也是關鍵的社會因素—姬周族群。從文獻記載角度看,這種歷史情境伴隨著西周“周樂”的整個歷史過程,或產生,或延續,或寖微,或被時代強化,或被時代弱化,而它本身作為一種歷史現象也成為了不同歷史時段中最為鮮活的部分。故這樣的事實不當被無視或視之不見。透過文獻中周人言樂諸資料,尤可注意西周“周樂”的五個基本事實:一、人們言“樂”,前提是周王朝“禮樂”文化和“姬周”文化,而非如今所謂的“藝術音樂”;二、人們言“樂”,是側重從音樂的社會性實在和意義角度來理解和“認知”的,而非作為物理范疇中的聲音形態來理解和“分析”的;三、人們言“樂”,其取向已超越了單純的“音樂”(今天藝術意義上的)而囊括了它的“社會”脈絡及其文化象征在內的諸多側面;四、人們言“樂”,是基于西周“周樂”的兩種不同的文化形態:即依托于身體和操演并以行為為主體的“周樂”,和依托于“文本”書寫并以意義為主體的“周樂”,對此不可無視而應加以區別和區分;五、從人們言“樂”可知,西周“周樂”既同“姬周”族群屬性和“禮樂”文化緊密關聯,亦同其“非文本性”實存有關,尤因“禮樂”文化的“實踐性”和“非文本性”等諸多特質而致使其音聲之跡難覓,形態難見,故而遠離了音樂的形式的分析性議題,而主以文化性議題。由此,西周“周樂”當處在兩種社會實在—自然性實在(聲音之實在)和文化性實在(非聲音之實在)之中,然于社會和文化表征上明確彰顯的卻多是后者,受時人關注和強調的也多是后者。基于西周歷史情境的這些事實,筆者以為,西周“周樂”最為凸顯的表征有四,即:以特別的方式:依附“人”和“禮儀”;以特殊的載體:依附于“人心”和“操演”;以獨特的呈現:展演于“身體”與“儀式”;以特定的社會取向:頗具“政治的”“倫理的”“地域的”“族群的”等意涵。西周“周樂”因其緣自西周社會的獨特現實之中,故很難想象它同西周歷史和姬周文化根脈無實質性的關聯。
由此,西周“周樂”的文化基質也可以四點來簡要地概括:(1)從實存方式講,它是依附于“人心”和“操演”的;(2)從表現形態講,它是“身體”和“儀式”的;(3)從歷史特征講,它是“非文本”的;(4)從文化屬性講,它是“姬周”文化的。(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