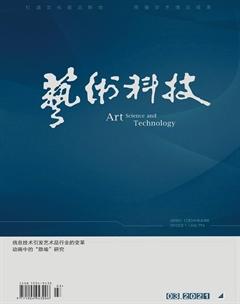泛二次元背景下虛擬偶像熱背后的原因與反思
劉源 李劍
摘要:虛擬偶像是利用信息技術構建的虛擬角色。虛擬偶像作為二次元文化的一部分,其大熱與泛二次元社區和資源共享有著密切的聯系。從2008年“初音未來”的誕生開啟虛擬偶像時代以來,虛擬偶像行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形成了龐大的粉絲群體。如今,在互聯網上存在許多虛擬歌姬或虛擬主播,虛擬偶像已從一個新媒體藝術形式轉變為具有人格化的社會存在。本文探究虛擬偶像背后的文化內涵,從中總結虛擬偶像熱潮形成的原因,并對其產生的社會影響作出反思。
關鍵詞:虛擬偶像;虛擬歌姬;虛擬主播;泛二次元文化;媒介社會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9436(2021)03-00-02
1 虛擬偶像的興起
虛擬偶像是基于計算機平臺創造的虛擬角色形象。其通過建模、動態捕捉、圖像識別等技術模擬人類的行為方式,通過網絡、數字媒體手段等使虛擬角色與觀眾互動。虛擬偶像既具有作為電子角色的“虛擬性”,也具有中之人所賦予的“真實性”,對來自現實演員“真實”的表演與來自虛擬形象“虛擬”的展示進行實時的融合。虛擬偶像既不是真實的,也不是虛假的,虛幻與真實的邊界正在慢慢消解[1]。
1.1 虛擬歌姬時代
第一世代誕生的虛擬偶像被稱為“虛擬歌姬”。2007年,音像制作公司CRYPTON使用雅馬哈VOCALOID2制作了一個音樂合成軟件“初音ミク”,也被稱為“初音未來”,象征著“未來音樂的可能性”。KEI為初音設計了一個經典的形象,綠色雙馬尾、銀色背心、黑色長筒襪。全世界最著名的虛擬歌姬MIKU就這樣誕生了。初音的流行速度堪稱“病毒式”,在產品發售4天后,《甩蔥歌》誕生了,從此,初音未來在互聯網上一炮而紅,從日本傳播到了中國,最后蔓延到了全球網絡。時至今日,初音已是世界上最知名的虛擬形象,是世界上最具商業價值的IP之一,無數知名作曲家與演唱者為初音創作了單曲,其已成為21世紀的一個數字符號。
1.2 虛擬主播時代
虛擬主播是在網絡技術高速發展、智能設備迅速普及、直播行業壯大的背景下應運而生的。2016年,一個名叫“絆愛”的虛擬主播在YouTube平臺上開設了自己的頻道。相較于虛擬歌姬完美的形象設定,虛擬主播在角色設定上更加平易近人,絆愛被設定為一個人工智能(AI),因此被故意設計了一些“人格”上的缺陷。但這些缺點的存在反而使其“虛擬”的形象更加“真實”,人們更愿意接受這樣一個活潑可愛、充滿元氣又時常吃癟的角色。虛擬主播通過直播的形式與粉絲互動。相較于虛擬歌姬宏大的live現場,直播對于運營企業的負擔要小得多,而且隨著二次元彈幕文化的發展,彈幕交互具有更強的臨場感與及時性,實現了粉絲與虛擬主播的直接互動。
2 虛擬偶像與傳統偶像的區別
2.1 泛二次元生態下的“同人”共筑
初音的成功得益于互聯網與信息技術的高速發展,還得益于第一代數字“二次元”群體的迅速崛起,同人創作模式的流行使二次元IP可以極大地擴展受眾,角色消費模式使其市場得到保障。這些崛起的二次元群體需要一個可以代表自身特點的符號,而初音恰逢其時誕生,成為新世代“御宅族”的精神符號。初音自己并不會寫歌,也不會演唱,她的一切作品都來自音樂制作者和粉絲,這賦予了創作者無限的可能性。與傳統偶像高高在上的形象不同,初音不屬于你,不屬于我,甚至也不屬于開發公司,作為偶像來說,初音未來是“大家的偶像”。虛擬偶像的出現,使粉絲從“偶像做什么我都支持”轉變為“偶像做什么由我來決定”,粉絲群體可以參與到偶像形象的二次創作中,共同塑造偶像的性格特點[2]。
同人創作是虛擬偶像最具代表性的特點,也是其與傳統偶像最大的區別之一。同人作品中,普通人可以使用已有的動漫作品進行二次創作或改編,同人文化是二次元文化的一個重要標簽。計算機技術與網絡技術大發展的背景下,人人都可以被稱為藝術的參與者與創作者,這是后現代社會的特點。可以說同人創作就是一種后現代藝術行為,一個虛擬偶像誕生時,其只有簡單的基本設定,粉絲通過音庫軟件與繪圖賦予偶像聲音與形象,通過粉絲的“二次設定”,偶像的性格特征逐漸豐滿起來,一個虛擬偶像正是在海量的同人作品中被堆砌起來的,虛擬偶像是由所有同人創作者共同創作的。
2.2 MMD——所有人的舞臺
MikumikuDance簡稱MMD,原本只是為初音未來的3D模型設計舞蹈的動畫軟件。2008年MMD免費公開以來,帶動了一系列3D動畫產業鏈,也成為大眾參與虛擬偶像創作的重要工具,目前是使用用戶最多的3D軟件之一。MMD使用簡單,未曾學習過3D技術的普通人也可以輕松上手。MMD完全打破了3D動畫制作的專業壁壘,為日后虛擬偶像大量的3D同人創作提供了基礎。
MMD軟件本身也是“泛二”同人文化影響下的產物。MikumikuDance的創作者是樋口優。樋口優不是3D行業相關人員出身,在初音未來出道大火的背景下,樋口優想利用初音的開源3D模型進行動畫同人創作,隨后他自學數學與程序設計,制作了一款簡易的3D動畫軟件MikumikuDance。MMD設計之初十分簡陋,功能也并不完善。早期MMD用戶大多是初音的粉絲群體,在大家共同使用下,許多粉絲為MMD制作了配套插件,更新了版本,無償將舞蹈動作數據分享歸類,MMD在所有粉絲的共同努力下完成了最終的升級。樋口優解釋這一現象為“因為興趣”,所有的粉絲都是在共同的“興趣”與對初音的熱愛驅動下共同行動。正如粉絲們共同打造了初音一樣,粉絲們也共同打造了MMD這個所有人的舞臺。2008年后,互聯網自媒體平臺大量出現,“視頻投稿”成為一種流行的創作方式,然而大部分人沒有跳舞、畫畫、解說的天賦,打開他們創作大門的正是簡單便利的MMD,虛擬角色代替使用者進行表演,觀眾則被這些虛擬角色與背后創作者的創意所吸引,現實的壁壘被打破,“二次元”世界變得更加真實,并與現實不斷融合。MMD的出現,使一群熱愛虛擬偶像與同人創作的人有了可以盡情創作的空間。MMD免費與共享的特性降低了3D動畫領域的門檻,大多虛擬角色都會公布自己的免費3D模型,粉絲通過MMD 進行舞曲、服裝創作,粉絲的同人作品也相應擴大了虛擬角色的宣傳效力。圍繞著虛擬偶像與MMD軟件誕生的MMD文化有值得期待的前途,MMD文化領域內,模型、效果器、插件、數據伴隨著新虛擬角色的誕生全部公開使用,以此建立了一個龐大的共享社區,節省了大量的開發時間。“興趣”“熱愛”“共享”是MMD文化的組成部分,也是泛二次元同人文化數十年發展的結果。
3 虛擬偶像的社會價值
鮑德里亞認為仿真模型形成的幻象可以作為真實世界的替代,它無所不在,以致無法分辨真實和幻象。仿真的世界對鮑德里亞來說恰如一個沒有深度、來源和指涉物的后現代符號世界。
虛擬偶像就是后現代世界中一個類群的數字外衣。數字符號正在代替我們的“現實”,人的種種社會活動都是在這些符號的驅動下進行的,我們獲取符號信息,進行符號化的工作,我們想變成符號的樣子。我們在現實中經歷的時間僅僅是一場虛擬的“媒介之戰”,我們從媒介上獲取的信息都是被包裝加工、被注以主觀傾向的符號。我們所在的現實正在慢慢消散,一種電子存在正在占據更多的社會比重,電子符號的作用力已經超出所有人的想象。虛擬偶像誕生之前,很難相信一個“紙片人”可以產生如此大的社會影響以至于形成一種亞文化。21世紀是數字信息時代,我們的生存方式已不知不覺被數字技術改變,數字媒介打破了電視的“規則”,分布傳播的特點決定了數字媒介無法形成共同價值觀的傳播形式,其更傾向于以生活方式、教育水平、歷史文化等組成“部落”,進行“再部落化”[3]的文化重組。二次元文化作為青年文化的一部分,成為青年群體的一種符號代表和身份認同[4],以此組成了媒介部落。在成年人的價值觀下,“生產者—內容—消費者”是一種普遍存在的形式,而數字媒介的出現打破了這種常規的認知體系,人既是“內容”的消費者,也是創造者。
虛擬偶像的存在是人類自我量化的一個進程。數字技術可以讓人們將理想的形式投射到虛擬世界中。人們共同創造虛擬偶像,對虛擬偶像的設計構建即是自我意識在其之上的投射,形成人自我的一種量化。不論是VOCALOID還是MMD,使用這些技術生成的虛擬形象都是人自我的一種延伸,粉絲群體與偶像的關系不再是傳統的追隨關系,而是數字復制背景下的創造關系。
4 對虛擬偶像的反思
商業化運作下的虛擬偶像行業屬于ACG(動畫、漫畫、游戲的總稱)產業的一部分,虛擬偶像的IP往往可以在ACG市場內進行轉化,通過動畫聯動、同人劇場、衍生品開發等實現更大的商業價值。這也造成了運營公司過于追求商業利益而忽視虛擬偶像的核心要素——共同創作下粉絲群體的聯結紐帶。VOCALOID在開發初音未來后又開發了多個虛擬偶像,如鏡音雙子、巡音等,通過虛擬偶像團隊擴大經濟效益,運營者明白對于虛擬偶像來說粉絲的參與度才是最重要的,因此新偶像出道立即開發MMD模型與音庫,VOCALOID家族迅速吸引眾多粉絲。隨后在多平臺推出相關游戲與影像作品,并與其他品牌聯動,擴大宣傳效益。2012年,初音未來擔任了谷歌形象大使,初音形象在全世界擴散,以至于初音成為在海外銷售單曲最多的日本偶像。
但虛擬主播和虛擬歌姬的管理運營有很大的區別,在虛擬主播行業內有很多運營失誤事件。虛擬主播往往由個人或小團體運營,其對緊急情況的應對能力不足,再加上虛擬主播通過實時的直播與粉絲互動,這種直接的高強度的互動方式使粉絲對主播行為的反應也更加情緒化。2018年,運營商Activ 8 宣布對絆愛的“中之人”進行替換,并設立“4個絆愛”計劃。此舉惹怒了粉絲群體,運營商缺乏與粉絲群體的溝通,對粉絲需求不夠了解,對粉絲而言,替換中之人相當于使絆愛變成披著絆愛皮的另一個虛擬主播。事態發酵后,運營商沒有聽取粉絲意見,反而制作了對粉絲的侮辱性視頻,并且爆出了運營商對原中之人的不公行為,此事件出現后導致絆愛A.I.Channel頻道訂閱量銳減,粉絲紛紛取關以表達對原中之人的支持。自此之后,雖然運營商采取了補救措施,但也無法挽回絆愛的粉絲,曾經最具熱度的虛擬偶像就這樣落幕。虛擬主播作為二次元文化連接現實世界的交點,人設是其核心,對虛擬形象必須有應有的尊重。粉絲們并不介意絆愛的人設分化,也并不介意“愛醬”的商業化。但絆愛不是提線木偶,不是盈利機器,而是陪伴粉絲度過歡樂時光的二次元朋友。Vtuber的從業公司也應該重新認真思考虛擬IP與粉絲的關系。
5 結語
虛擬偶像是在青年文化與泛二次元文化流行的背景下誕生的。信息技術與數字媒體的發展為虛擬偶像提供了平臺,而后現代藝術大眾傳媒作為虛擬偶像被賦予了文化內涵。虛擬偶像不僅僅是數字技術的應用,更多的是受眾群體的集體創作。虛擬偶像不是運營者設計出來的,而是粉絲共同設計的結果,粉絲群體通過同人作品參與到偶像活動中,虛擬偶像形象、單曲作品、舞蹈、角色性格等都是從龐大的同人設定中凝練而出的。可以說,虛擬偶像的存在就是媒介社會下“媒介化生存”的產物,一種新的媒介環境正在改變我們的生活,虛擬和現實的邊界越來越模糊,虛擬偶像從電子世界走出來,卻對我們的現實作用重大,但我們也應當警惕這種后消費主義的消極影響,過于沉溺媒介帶來的娛樂性,會讓我們漸漸從客觀的現實脫離,讓我們混淆虛擬與現實的社會定位。
參考文獻:
[1] 張依.虛擬偶像直播熱現象探究[J].新媒體研究,2019(17):72-74.
[2] 王霜奉.虛擬偶像為何受追捧?[J].上海信息化,2019(10):75-77.
[3] 胡泳.理解麥克盧漢[J].國際新聞界,2019(1):81-98.
[4][丹]施蒂格·夏瓦.文化與社會的媒介化[M].劉君,譯.復旦大學出版社,2018:67-68.
作者簡介:劉源(1995—),男,山東青島人,碩士在讀,研究方向:數字媒體。
李劍(1981—),男,江蘇南通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電影學、數字媒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