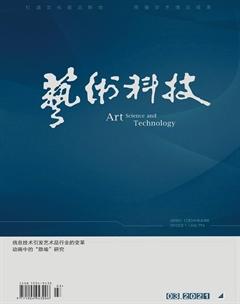北魏龍門造像題記所反映的書法平民化


摘要:北魏龍門造像題記是一種特殊的書法形式,與北魏邙山元氏墓志(皇室及貴族銘石書)共同形成了北魏書法的兩種形態。以“龍門二十品”為代表的龍門造像題記書法,以獨特的藝術風格體現了特殊的審美價值,使之后的書法實踐進入了藝術創作的新階段,開辟了書法創作的新道路,這正是造像記書法審美價值的真正體現。拋開外在歷史局限對龍門石窟造像記書法風格的自覺滲入,參與營造者群體帶來的非自覺的影響是不能忽視的。
關鍵詞:北魏龍門造像題記;書法;平民化
中圖分類號:J29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9436(2021)03-0-02
1 龍門造像開鑿背景概述
1.1 佛教興盛
北魏時期盛行佛教,孝文帝將都城遷到洛陽后,佛教更是在民間廣為傳播。在《洛陽伽藍記》中有這樣一段記載:“王侯貴族,棄象馬如脫屣,庶士豪家,會資財若遺跡。”足見上至顯貴、下至普通百姓對佛教癡迷的程度。隨之而來的便是大規模地開鑿石窟,建寺造像。佛道兩教在中國的蓬勃發展,引發了宗教藝術的興盛,于是寺院郁起,造像迭生,其中典型的案例就是各種石窟。龍門石窟大量造像題記應運而生,北魏政權遷都洛陽后,龍門石窟繁榮與衰頹并存。北朝承漢遺風,碑版、墓志流傳廣泛,加之北朝佛教興盛,以建造寺塔和鑿造石窟造像為功德,因此造像題記、摩崖刻石、石經、石柱等石刻書法遺存豐富,自北魏至北周,數以千萬計。這些品種繁多的石刻書法爭奇斗艷、絢麗多彩,這一時期成為自漢以來石刻書法的第二個高峰。龍門石窟的開鑿年代最早在北魏太和七年(483年),經過北魏至清代康熙年間的鑿造,至今仍留有窟垅2100多個,造像10萬余尊,造像題記3600余品,當屬全國各地石窟造像題記之最。
1.2 社會動蕩
動蕩多變的社會形勢、胡漢雜糅的文化現實、非漢民族對中原的統治、佛教等外來文化的風行,不可避免地影響社會,并深刻地表現在社會文化的各個方面。具體到文字,就是北魏造像題記書風。龍門石窟中的碑刻題記,記載的是佛教信徒為了某種愿望而出資開龕造像的事跡。造像記雖是功德性地傳播佛教的手段,書寫并不是為了藝術,但其結果卻是藝術化的。
2 龍門造像題記所反映的書法平民化現象
2.1 造像主的平民化
造像主的身份可以依據題記、題名加以區分。北魏龍門造像題記中,多刻有造像主的身份、名號等個體識別的信息。陳玉女對造像者的身份進行了分類統計,對北魏時期造像者的身份進行了考察,在她所考察的131件北魏題記中,官僚含王公貴族階層造像32件,群體造像9件,僧尼造像50件,一般信眾40件[1]。盡管參與造像活動的有皇室顯要、各級官吏等,但無階無品的平民和民間信仰群體依然是造像發愿的主流。
此外造像也并不一定是單人完成的,在北魏時期也存在大量多人一同出資造像的現象,將造像活動作為主體的佛教團體,也就是邑義。開窟造像要花費大量錢財,邑義這種組織形式可以分攤、降低費用,這樣貧苦者也能造像祈福。從民俗信佛社團的眾多和普遍看造像題記書法,可以發現,題記書法的字形、結體也都帶有通俗化、普及化的特點。題記造像書法不是高雅的貴族書法,而是地地道道的通俗書法,帶有實用性和可識讀性,突破了字學的煩瑣性和書寫的裝飾性。
2.2 書丹者的平民化
北魏時期盛行一種以傭書手為職業的群體,其存在其實與龍門造像題記的書寫相關。從整體而言,北魏龍門造像題記寫作的書法風格逐漸趨于一致,原因與刻工相關,當時出現的專職傭書手也是原因之一。在北魏時期,傭書手大多來自民間的普通家庭,因此即使他們書寫文字較為美觀,但是在寫作過程中帶著通俗的審美視角。
2.3 刊刻者的平民化
北魏造像刻石行業極其發達,從北魏立朝100多年竟留下2000多方造像記可見一斑。2000多方造像記中許多與“龍門二十品”迥異,有的與晉唐書法近似,這說明以造像刻石為業的多是漢人,且多是下層文人所作,不少石刻文字工匠參與其中又進行過二度創作。有些作品由工匠直接鑿刻而成,雖然缺少法度,卻有率真之趣。相反,北朝墨跡留傳很少,史籍中有名的書法家也遠遠少于南朝。
3 北魏龍門造像題記書法的平民化特點
龍門造像題記是一種特殊的書法,其最大的特點在于具有民間書法的體貌與精神,其民間特色主要可從三個方面分析。
3.1 廣泛的參與性
在龍門石窟中,邑子像隨處可見,參與造像的百姓非常多。正是大量平民的參與,帶動了當時楷書體的逐漸形成。許多平民一個人無法承擔造像的費用,于是一群人一起籌集資金用以造像。當時家家戶戶都存在變故,百姓們的心愿便是可以安穩健康地過日子,于是百姓們用造像的方式表現自己的祈愿。因此,在北魏時期,民間造像并不需要積極動員,百姓們就能夠主動參與。民間書法的優勢在于擁有足夠的廣泛性與普遍性,大量民眾的積極參與,也使日常書寫能夠快速完成對書法的轉換。
3.2 字形的訛化
與當時受過良好教育的士人高官相比,平民的書寫并不規范。盡管《牛橛造像記》《始平公造像記》的漢字在書寫和字形上都較為規范,別字很少,但是其他的造像記中經常出現很多別字。陸明君先生的《魏晉南北朝碑別字研究》一書明確指出,魏晉南北朝時期,出現眾多碑別字是因為當時不同字體相互交融,而社會較為動亂,當時的政權并沒有重視正字,沒有規定統一的用字標準,而當時文化程度較低的平民百姓則在好奇的心態下廣泛參與。相較于受過良好教育的士人高官,百姓的書寫更加不規范。這是由于隸楷轉化時期本身的不定型性,人們都按自身的習慣偏好來寫字,同時當時大量的平民并沒有接受很好的文化教育,不清楚漢字形成的過程與基本的漢字筆畫書寫順序,所以寫作更加隨意。從書體的演進看,形體的簡化是必然趨勢,從參與人數的廣泛性看,字形訛化也是不可避免的。很多常用的字,也訛化得讓人不知為何物。如《孫秋生造像記》中有一個“毛”字,一般出版的“龍門二十品”都釋為“毛”。其實就是一個常用的“三”字。
3.3 刊刻不計工拙講
刊刻造像與造像記的工匠大多從平成遷徙而來,工匠當時的社會地位并不高,然而工匠在審美趣味上不同于普通的平民百姓。貴族需要墓志時,工匠便謹按刀法與字法進行刊刻。面對一般的造像題記時,工匠們才更加開放,在刊刻中對字的結構與字形有所改變,增加了不少趣味,刊刻的過程實際為線條的二次創作。我國近代學者對刊刻的寫與刻非常關注,在沙孟海的學術研究中有較為代表性的觀點,他認為碑版文字通常先寫作再篆刻,因此古往今來都將書寫與篆刻分開,寫手與刻手都有其優勢與劣勢。北魏時期最盛行造像,當時產出的大量造像中,大部分都是亂寫亂刻,甚至沒有經歷先寫作的這一過程而直接篆刻,因此最終的呈現非常拙劣,不能夠將其都視為好的作品,但是當時盛產的造像中不少字跡擁有天趣,可以借鑒。
4 與同時期邙山元氏墓志的比較
4.1 “野”與“雅”
不同的學者對魏晉時期的碑體概念持有不同的觀點。學者施安昌認為,不應將其稱作魏碑體,而要叫作北邙體,統一用以表示皇室貴族的銘書文。學者叢文俊則表示,魏碑體表示北魏時期社會主流且有楷書典范樣式的刻石書法的作品類型,代表作為洛陽周圍出土的黃石規則的墓志銘。兩位學者的觀點較為相似,都是將北魏時期皇室貴族有楷書典范樣式的元姓墓志作為其含義。所謂典范樣式是指書風中士人的“雅文化氣息”[2],但其并非魏碑的所有樣式。這是由于當時龍門造像中產生的2480件作品,大多數并非貴族的作品,也不含有文雅的文化氣息,來自當時的民間,是與“雅”對立的“野”與“樸”。造像記是平民百姓表達自己美好祈愿與追求的一種方式,形式并不刻板,追求盡興達情。其字形、結體也都帶有通俗化、普及化的特點,其重要性正是一般人所忽視的。龍門造像是民間書體,書風帶有粗獷、天真的藝術特質。
題記造像書法不是高雅的貴族書法,而是地地道道的平民書法,是通俗之“俗”,而不是庸俗之“俗”,帶有實用性和可識讀性,突破了字學的煩瑣性和書寫的裝飾性。
4.2 “稚拙”與“精巧”
龍門造像題記的風貌之所以是民間的,就因為其不合主流楷法。其中多數題記刻字稚拙浪漫,以稚拙爛漫著稱,是鮮卑族的審美趣味決定的,同時當時的刻工技術也對其造成了影響。刻手在鑿刃敲刻的過程中,其運動的方式不是被動的,給貴族辦事和給平民階級鑿刻的心態是相反的,在刊刻造像題記時,刻手不一定完全遵守原作的線條精工雕琢,有自己主觀性發揮的空間。以長期存在爭議的《鄭長猷造像記》為例,該作品造型樸素,結字緊密,可以表現出刊刻人本身的性情。基于雅致的看法來評價,會認為該作品并不美,而從民間書法的視角來評判,則會認為《鄭長猷造像記》是一部骨血俊宕的作品(圖1、圖2)。
在《佛法與書法》中,田光烈對北魏時期龍門造像題記作出了評價,他認為北朝造像刊刻一定程度上可以標記為人類宗教藝術的高峰,而銘文題記書法則能夠代表中國書法藝術的高峰。其風格比正統書法更加動人,特別是北魏的造像題記,千變萬化,法無定法,使人百看不厭[3]。
4.3 “隨性”與“安排”
在章法處理上,元氏墓志大都帶有界格。這樣的安排使得每個字都有自己較為妥當的空間,不至于造成章法上的散亂和結字上的渙散,并讓結字在有限的空間里發揮無限的張力。所以,書刻版面表現得更加有秩序規整,更有章法。北魏時期大量的元姓墓志,幾乎都打磨得非常光滑,并且篆刻大量的文字,字體較小,非常規整,布局嚴謹,根據篆刻文字的數量進行排列。通過相對固定的橫豎排列達到刺激視覺的效果,搭建出一個固定的框架,塑造一種方嚴的風格。在這種格式下,章法更重視體勢,通過位置的調整配合字的造型,使其區域協調,以形成動靜平衡的視覺效果。龍門造像題記書法則不同,除少數幾品有明顯界格外,其余十六品都沒有明顯界格,通過對字形的伸縮或者夸張,營造出一種錯落有致的形式感,從而化解了整體凌亂的難題,使整幅作品在章法形式上靈活而不失穩健,字與字之間的穿插跌宕錯落有致。“隨性”還體現在書寫中對線條形態的夸張上。康有為說《慈香造像記》“其為章也,龍蟠鳳舞,縱橫相涉,闔闊相生……使轉斫折,酣縱逸宕,其結體飛揚綿密”。結體、用筆都隨意而發,這種書寫的隨意,正好是書法表現所需要的抒情特質。《慈香造像記》雖打好了界格書寫點,但書手總不按固定的空間安排他的點畫,讓字勢傾側,線條飛舞起來。若把碑刻擬人化,龍門造像題記與邙山元氏墓志是兩種完全不同性情、不同階級的人,一個斯文有致如貴家子弟,一個活潑如鄉野孩兒(圖3、圖4)。
5 結語
龍門北魏造像題記書風,是一種無意識的書法審美與文字審美的體現。這些造像題記為我們研究漢字的流變和書法藝術提供了珍貴的實物參考。我們在學習古代寫作與刊刻時,應當更多地重視其呈現于當前的現實狀態,這種狀態已然歷經無數次的再創作的過程,遭受了時間的打磨與侵蝕,成為富有豐富歷史意味的作品。這些作品的原作者是誰不具備多大的研究意義,更關鍵的是這些作品有無深厚的美學內涵,能否啟發當代的書法藝術。龍門北魏造像題記書法通過新奇的美學樣式、深厚的美學內涵,給予了當前書法藝術創作更多的藝術啟示,是不朽的書法經典之作。龍門石窟的碑刻題記是龍門文化的載體與藝術的展現,它們好似一部部承載歷史律動的古書,從歷史中穿越而來,見證歲月的滄桑,從紙墨間躍然而出,閃耀著智慧的光芒。
參考文獻:
[1] 陳玉女.龍門石窟佛教信仰圈之探討——以清陸蔚庭稿本《龍門造象目錄》為分析依據[C]//龍門石窟國際學術研討會文集.鄭州:南人民出版社,2006:251.
[2] 從文俊.揭示古典的真實[M].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245.
[3] 田光烈.佛法與書法[M].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51.
作者簡介:黃嘉瑩(1995—),女,河南濮陽人,碩士在讀,研究方向:書法美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