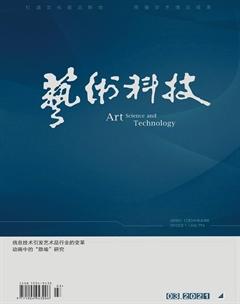農(nóng)家書屋助力鄉(xiāng)村公共文化建設(shè)與發(fā)展
摘要:農(nóng)家書屋拓展了農(nóng)村地區(qū)的文化陣地,使農(nóng)民群眾養(yǎng)成了良好的閱讀習(xí)慣,為農(nóng)村地區(qū)的文化事業(yè)發(fā)展打下了良好基礎(chǔ)。本文從農(nóng)家書屋的發(fā)展入手,通過對揚州市J區(qū)的調(diào)研,揭示其共性特征,并對其未來規(guī)劃以及與鄉(xiāng)村文化的關(guān)系進行探討。
關(guān)鍵詞:農(nóng)家書屋;鄉(xiāng)村文化;建設(shè)
中圖分類號:F32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9436(2021)03-0-02
農(nóng)家書屋在新農(nóng)村建設(shè)中發(fā)揮著至關(guān)重要的作用,它能夠?qū)⒊青l(xiāng)之間的文化網(wǎng)絡(luò)有效聯(lián)結(jié),不僅豐富了農(nóng)民的知識,提高了農(nóng)民的素養(yǎng),而且可以拓寬農(nóng)民的心胸,對于農(nóng)民的社會化起著不可估量的作用[1]。一方面,圖書是現(xiàn)代科學(xué)技術(shù)傳播的使者,可以加快農(nóng)村地區(qū)的技術(shù)轉(zhuǎn)型與升級,幫助農(nóng)民實現(xiàn)增產(chǎn)增收,是我國建設(shè)學(xué)習(xí)型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2];另一方面,農(nóng)家書屋建設(shè)擴大了農(nóng)村的公共文化空間,豐富了農(nóng)民的日常生活,有利于傳統(tǒng)文化的傳承,同時拓展了農(nóng)民的公共空間,使得農(nóng)村的文化氛圍更加濃厚。
1 當前農(nóng)家書屋發(fā)展的基本情況
在傳播生態(tài)系統(tǒng)中媒介種群所處的位置,就是所謂的傳播生態(tài)位,該位置決定著媒介種群的形態(tài)、功能、作用。對于鄉(xiāng)村而言,電視是當前最重要的媒介資源,發(fā)揮著知識傳承、環(huán)境監(jiān)督、生活娛樂的功能[3],而網(wǎng)絡(luò)的興起進一步增加了媒介的娛樂功能。電波媒介取代印刷媒介被看成進步的象征,所以在此基礎(chǔ)上容易形成一種圖像對文字的霸權(quán)[4]。實踐證明長期受到影像文化的影響,更容易形成“電子烏托邦”的思想[5]。其實,在邏輯性、深刻性、批判性等方面,圖像并不比文字優(yōu)越。基于農(nóng)村受眾的認知水平、知識結(jié)構(gòu)、生活習(xí)慣,他們更愿意接受以視聽為主的電視,而不是抽象的書籍。
隨著媒體融合,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注意到農(nóng)家書屋。起初,農(nóng)家書屋并沒有得到廣大市民的注意,一度變?yōu)榭諢o一人的城鎮(zhèn)書籍儲藏間。伴隨政府支持力度加大,農(nóng)家書屋也加快發(fā)展的步伐。為了使農(nóng)家書屋的建設(shè)環(huán)境得到改善,政府需要逐步完善相應(yīng)管理體系,加大對管理人員的培訓(xùn)力度,提高專業(yè)人員的專業(yè)能力。通常情況下,城市媒體是農(nóng)村地區(qū)人民群眾獲取信息的主要途徑[6],受強勢媒體以及市民文化的影響,農(nóng)村地區(qū)的文化傳播發(fā)展相對滯后,無法滿足農(nóng)村地區(qū)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文化方面的需求。農(nóng)民之間無法實現(xiàn)資源共享,導(dǎo)致農(nóng)民意愿無法得到及時反饋,對農(nóng)村地區(qū)溝通渠道以及輿論機制的搭建形成了阻礙,使農(nóng)村信息服務(wù)機制存在很大的漏洞[7]。農(nóng)家書屋在我國經(jīng)濟較為發(fā)達的中部和東部地區(qū)建設(shè)情況較好,在西北等經(jīng)濟相對落后的地區(qū)發(fā)展較為緩慢,由此可以看出,文化和經(jīng)濟的發(fā)展正相關(guān)。
目前,受關(guān)系、人情、面子等因素的影響,鄉(xiāng)土傳播的發(fā)展穩(wěn)定性較強,同時將民間智慧體現(xiàn)得淋漓盡致,也是農(nóng)村地區(qū)推動文化事業(yè)發(fā)展的大勢所趨[8]。除了政府的投資與建設(shè)以外,也有社會各界的愛心人士對農(nóng)家書屋進行捐贈,從資金到書籍的支持,使其加快了發(fā)展的腳步。隨著建設(shè)環(huán)境好轉(zhuǎn),宣傳力度加大,人員管理專業(yè)程度提升,市民參與度也得到提升。在周末,年輕群體會到書屋看書[9],也有家長帶兒童進入書屋進行親子閱讀,部分中老年人也會進入書屋閱讀,閱讀人數(shù)不斷增長[10]。提高城鎮(zhèn)市民文化水平,營造濃厚的文化氛圍,為市民提供讀書學(xué)習(xí)的場所,成為農(nóng)家書屋發(fā)展的首要任務(wù)。
2 揚州市J區(qū)農(nóng)家書屋的情況
揚州市J區(qū)一共有14個農(nóng)家書屋開放點,環(huán)境較好,管理正規(guī),其中丁伙鎮(zhèn)和仙女鎮(zhèn)開放點最多。該地區(qū)農(nóng)家書屋的數(shù)量基本能夠滿足鄉(xiāng)村居民的需求,并成為江蘇省模范農(nóng)家書屋。從借閱情況來看,丁伙鎮(zhèn)各個鄉(xiāng)村通借通還冊數(shù)較多,居民熱情度較高,具體數(shù)據(jù)如下:丁伙鎮(zhèn)丁南村1429冊、丁伙村1487冊、高橋村1488冊、李豐村1443冊,郭村鎮(zhèn)吉港村850冊、張倪村208冊,武堅鎮(zhèn)雙林村609冊,小紀鎮(zhèn)太平村1300冊,仙女鎮(zhèn)江橋村123冊、陳莊村119冊、三友村119冊、新河村119冊、北社區(qū)600冊、孔莊社區(qū)1200冊。但是部分鄉(xiāng)鎮(zhèn)的情況不佳,有待改善,具體問題如下:第一,分布不均衡。丁伙鎮(zhèn)和仙女鎮(zhèn)的經(jīng)濟發(fā)展相較其他區(qū)域來說更為快速,所以農(nóng)家書屋的數(shù)量多,借還數(shù)目多。由于發(fā)展不平衡,我國部分偏遠落后地區(qū)鄉(xiāng)村書屋的發(fā)展還遠遠達不到平均水平。農(nóng)村書屋在推動農(nóng)村文化傳播方面影響甚小。第二,供給不充分。J區(qū)農(nóng)家書屋因為地域分布,供給存在差異。一部分農(nóng)家書屋提供的書籍無使用價值,圖書資源相對匱乏,導(dǎo)致農(nóng)村地區(qū)人民群眾的基本需求無法得到滿足。針對留守兒童、婦女等人群的圖書資源不豐富。隨著電子時代發(fā)展的速度越來越快,農(nóng)家書屋沒有配套的電子資源,更新速度慢,導(dǎo)致大量讀者流失[11]。
雖然政府和社會各界對農(nóng)家書屋進行了資金等方面的投資,但除了政府資金以外,其余資金不能保證及時穩(wěn)定支持農(nóng)家書屋發(fā)展,對農(nóng)家書屋的發(fā)展形成阻礙。政府對于農(nóng)家書屋的法制建設(shè)不完善,存在很多問題。書籍資源的種類并不能滿足廣大市民的需求,市民閱讀熱情下降,農(nóng)家書屋的整體發(fā)展呈現(xiàn)降溫趨勢。基于這種情況,我們需要與時俱進,實現(xiàn)農(nóng)家書屋線下以及線上兩種模式融合。作為社會建構(gòu)的核心力量,網(wǎng)絡(luò)為農(nóng)村的信息傳播提供了廣闊的空間,農(nóng)民可以根據(jù)自己的需求對信息進行收集、加工和處理,并通過自組織的方式向他人或群體發(fā)布有關(guān)生產(chǎn)、生活的信息。互聯(lián)網(wǎng)與手機推動了農(nóng)民的自組織化程度提升,社會化媒體日益成為其獲取信息、生活娛樂、交流互動的主要渠道[12]。
3 農(nóng)家書屋與鄉(xiāng)村文化發(fā)展的關(guān)系
伴隨著經(jīng)濟的發(fā)展和社會的進步,地球逐步朝地球村的方向發(fā)展。搭建科學(xué)合理的關(guān)系在信息傳播過程中發(fā)揮著至關(guān)重要的作用[13]。十六屆五中全會指出,在推動我國現(xiàn)代化生態(tài)文明建設(shè)過程中,應(yīng)加大建設(shè)生活富裕、村容整潔、生產(chǎn)發(fā)展、鄉(xiāng)風(fēng)文明社會主義新農(nóng)村的力度,從而推動農(nóng)村地區(qū)社會和經(jīng)濟的發(fā)展,這也是全面建設(shè)小康社會采取的重要手段[14]。新時期的圖書館尤其是縣(市)級公共圖書館工作重點應(yīng)轉(zhuǎn)向農(nóng)村,為新農(nóng)村建設(shè)出謀劃策,農(nóng)家書屋在此舉措中扮演重要角色。
第一,促進農(nóng)村文化產(chǎn)業(yè)發(fā)展。縱觀歷史,我國在發(fā)展過程中沉淀了豐富的文化底蘊。我國在加快文明建設(shè)的同時,要通過振興文化的方式,加快鄉(xiāng)村地區(qū)文化產(chǎn)業(yè)發(fā)展的步伐。農(nóng)村書屋在加快農(nóng)村地區(qū)建設(shè)的過程中發(fā)揮著至關(guān)重要的作用。農(nóng)村地區(qū)的文化產(chǎn)業(yè)在發(fā)展過程中除了會受到政治、經(jīng)濟等方面的影響,還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文化因素的影響。
第二,助力鄉(xiāng)村文化振興。農(nóng)家書屋的建設(shè),打破了“喂食”式的文化傳播形式,營造了主動學(xué)習(xí)的氛圍[15]。很多鄉(xiāng)村人員進入城市工作,整體素質(zhì)提高,回農(nóng)村以后學(xué)習(xí)積極性變高,對文化活動的需求變大。加快建設(shè)農(nóng)家書屋的步伐,推動“送文化”向“種文化”過渡。農(nóng)家書屋在推動鄉(xiāng)村文化建設(shè)過程中發(fā)揮著至關(guān)重要的作用,有利于培養(yǎng)農(nóng)村地區(qū)人民群眾良好的閱讀習(xí)慣,與此同時,鄉(xiāng)村地區(qū)的發(fā)展與農(nóng)家書屋文化建設(shè)關(guān)聯(lián)十分緊密[16]。
第三,豐富村民文化生活。通過對現(xiàn)階段涉農(nóng)傳播系統(tǒng)發(fā)展的情況展開研究可以看出,農(nóng)村地區(qū)文化的發(fā)展在很大程度上會受到媒介生態(tài)體系建設(shè)以及政府宏觀調(diào)控的影響。不可否認的是,在一些鄉(xiāng)村地區(qū),群眾文化意識薄弱,文化氛圍不夠濃郁[17];鄉(xiāng)村生活單一,村民娛樂活動范圍窄;鄉(xiāng)村缺乏質(zhì)量高的文化傳播場所,沒有電影院、圖書館等[18]。在文化建設(shè)方面,農(nóng)村地區(qū)組織力較差,且投入相對匱乏,對農(nóng)村地區(qū)的發(fā)展形成了阻礙。
鄉(xiāng)村地區(qū)的文化資源十分豐富,政府將農(nóng)村文化建設(shè)作為首要任務(wù)是很有必要的,我國農(nóng)村有豐富的文化底蘊[19],要從根本上打破農(nóng)村空心化,農(nóng)家書屋的建設(shè)在文化上加快了鄉(xiāng)村健康發(fā)展的步伐,從根本上緩解了農(nóng)村病的嚴重程度[20]。
4 農(nóng)家書屋發(fā)展的問題及反思
農(nóng)家書屋建設(shè)有利于平衡鄉(xiāng)村媒介生態(tài)系統(tǒng),使得對農(nóng)傳播的手段和路徑更加健全。然而,開展鄉(xiāng)村公共文化建設(shè)并非一朝一夕的事,基于鄉(xiāng)村地區(qū)資金匱乏的情況,需要動員全社會共同推動文化建設(shè)發(fā)展[21],不僅需要政府的重視,還需要穩(wěn)定的資金支持,增強群眾的文化意識,管理人員積極投入工作[22]。農(nóng)家書屋的建設(shè)不能僅僅依靠政府行為,要不斷適應(yīng)新社會新形勢,就必須進行不斷的改革。我們需從自身實際出發(fā),在辦館籌資的選擇上應(yīng)該從多維度出發(fā),與農(nóng)村地區(qū)發(fā)展的實際情況相結(jié)合,在籌資方面選擇多種渠道。與此同時,還需要引導(dǎo)廣大民眾,調(diào)動他們的自主性,創(chuàng)建便民且形式多樣的文化書屋,滿足人民群眾在閱讀方面的多元化需求。伴隨著經(jīng)濟的發(fā)展和社會的進步,農(nóng)村地區(qū)應(yīng)與時代發(fā)展的真實情況相結(jié)合,加快信息化數(shù)字化建設(shè)的步伐[23],可以充分利用微信平臺,實現(xiàn)信息的傳遞和資源的共享。
5 結(jié)語
農(nóng)家書屋在創(chuàng)建農(nóng)村文化機制的過程中應(yīng)充分實現(xiàn)自身價值。通過書屋文化,縮小知識鴻溝、信息鴻溝,做到農(nóng)民有書可看、有地方可學(xué)。在建設(shè)農(nóng)家書屋的過程中,需要與自身發(fā)展的實際情況相結(jié)合,養(yǎng)成良好的閱讀習(xí)慣。我們應(yīng)該意識到農(nóng)民并非不愛學(xué)習(xí),鄉(xiāng)村也不是沒有文化,培養(yǎng)既有“志”又有“智”的農(nóng)民,需要深耕像農(nóng)家書屋這樣的農(nóng)村公共文化服務(wù)平臺。
參考文獻:
[1] 吳妍.基于知識圖譜的鄉(xiāng)村傳播研究熱點、進展與趨勢分析(1993-2019)[J].東南傳播,2020(06):38-42.
[2] 王網(wǎng)明.抖音傳統(tǒng)文化相關(guān)視頻走紅原因分析[J].戲劇之家,2019(26):214-215.
[3] 衛(wèi)欣,劉露.縣級電視臺傳播生態(tài)位面臨的挑戰(zhàn)及其應(yīng)對[J].中州學(xué)刊,2017(12):164-169.
[4] 王淑一.涉農(nóng)電視節(jié)目的內(nèi)容創(chuàng)新與發(fā)展策略研究[J].藝術(shù)科技,2020(11):111-114.
[5] 葛婷婷.綠色廣告對農(nóng)村居民消費行為影響研究——以L村為例[J].東南傳播,2020(11):50-54.
[6] 黃晨.鄉(xiāng)村健康傳播的問題及對策研究——基于信息生態(tài)系統(tǒng)平衡的視角[J].新聞知識,2019(05):71-73.
[7] 馮廣圣.互嵌與協(xié)同:社會結(jié)構(gòu)變遷語境下鄉(xiāng)村傳播結(jié)構(gòu)演變及其影響[J].南京林業(yè)大學(xué)學(xué)報(人文社會科學(xué)版),2020(02):91-101.
[8] 王俊霞.新媒體視域下鄉(xiāng)土傳播的優(yōu)化與整合研究[J].青年文學(xué)家,2018(10):186-187.
[9] 劉露,陳昱潔.網(wǎng)絡(luò)時代青年群體的審美異化研究[J].大眾文藝,2018(16):225-226.
[10] 卜嘉敏,戴蔓琳.鄉(xiāng)村振興語境下老年人的媒介使用偏好研究——基于對淮安市Y鎮(zhèn)的調(diào)查[J].東南傳播,2020(05):59-62.
[11] 袁培培.從“文史之美”跨界“體育休閑”——《周末報》“媒體+體育”的融合探索[J].今傳媒,2018(12):86-87.
[12] 衛(wèi)欣,張衛(wèi).社會化媒體視域下鄉(xiāng)村初級群體的交往行為研究[J].南京社會科學(xué),2017(09):50-57.
[13] 王全權(quán),張衛(wèi).我國生態(tài)文明的對外傳播:意義、挑戰(zhàn)與策略[J].中南民族大學(xué)學(xué)報(人文社會科學(xué)版),2018(5):149-153.
[14] 劉千萌.當代中國農(nóng)村生態(tài)文明建設(shè)研究[J].大眾文藝(學(xué)術(shù)版),2018(16):236-237.
[15] 趙雅君.快餐文化下“慢綜藝”節(jié)目的發(fā)展路徑研究[J].今傳媒,2018(12):91-93.
[16] 李惠敏.助力鄉(xiāng)村文化自信:涉農(nóng)紀錄片的當代價值研究——以記住鄉(xiāng)愁為例[J].東南傳播,2020(06):35-37.
[17] 楊藝,謝慧.融合傳播語境下鄉(xiāng)村文化振興的路徑研究——以江蘇鹽城市A鎮(zhèn)為例[J].東南傳播,2020(07):51-52.
[18] 王燦,馮廣圣.情感喚醒與鄉(xiāng)村認同:從《向往的生活》看慢綜藝熱[J].新聞知識,2020(07):62-65.
[19] 石淑敏.試論新媒體時代下非遺推廣中的新契機[J].漢字文化,2020(22):155-156+171.
[20] 莊眾顯.鄉(xiāng)村振興戰(zhàn)略背景下城鄉(xiāng)融合發(fā)展探究——以蘇北地區(qū)為例[J].中國集體經(jīng)濟,2018(32):1-3.
[21] 袁玥,馮廣圣.突發(fā)公共事件中農(nóng)村社區(qū)大喇叭強動員效果探析——以新冠肺炎疫情報道為例[J].新聞知識,2020(11):47-53.
[22] 陳相雨,丁柏銓.自媒體時代網(wǎng)民訴求方式新變化研究[J].傳媒觀察,2018(09):5-12+2.
[23] 張偉博.從熵理論解讀“新冠”疫情防控期間自媒體傳播亂象[J].東南傳播,2020(03):24-26.
作者簡介:蔡一姝(1997—),女,江蘇揚州人,碩士在讀,研究方向:廣告與新媒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