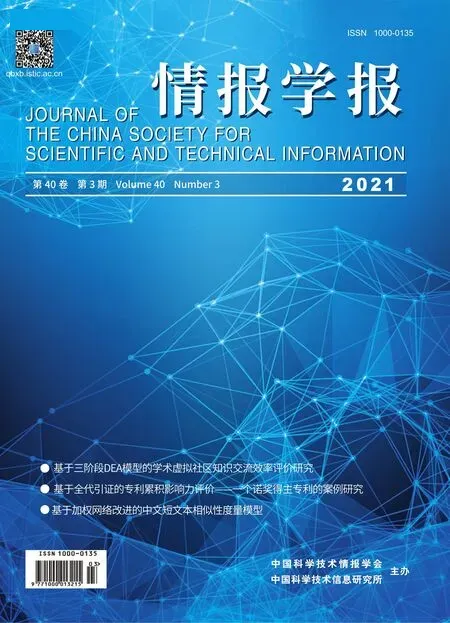基于三階段DEA模型的學術虛擬社區知識交流效率評價研究
楊瑞仙,黃書瑞,于政杰
(1.鄭州大學信息管理學院,鄭州 450001;2.鄭州市數據科學研究中心,鄭州 450001)
1 引 言
20 世紀60 年代,蘇聯學者米哈依洛夫[1]提出了科學交流模式。科學交流是科學研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分為正式交流和非正式交流。其中,正式交流主要是研究引文分析,相對比較成熟。然而,隨著社交媒體的出現,學術虛擬社區,如科學網博客、人大經濟論壇、小木蟲學術科研互動平臺(以下簡稱 “小木蟲” )和中國專業IT 社區(以下簡稱 “CSDN” )等,作為非正式知識交流的媒介逐漸受到科研人員的青睞。在學術虛擬社區中,科研人員可以通過發文、回復、點贊以及轉發等形式來發布、分享和討論與科學研究相關內容。因此,學術虛擬社區已成為傳統環境下正式知識交流的有益補充,其即時性和交互性較強,受到科研人員的青睞。隨著知識社會的到來和發展,各界的 “知識化” 趨勢愈加明顯,從起初的 “文獻交流” 到 “科學交流” ,再到現在的 “知識交流” ,知識交流的形式逐漸豐富,知識效率越來越高。然而,隨著學術虛擬社區知識交流熱度的不斷提升,如何從定量角度對學術虛擬社區知識交流效率進行測度,進一步改善社區知識交流氛圍,充分發揮非正式交流的作用,是當前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之一。
在學術虛擬社區中, “小木蟲” 擁有良好的交流氛圍及廣闊的空間,已成為最具影響力的學術虛擬社區之一。本研究以 “小木蟲” 為主要研究對象,構建學術虛擬社區知識交流效率評價指標,采用 三 階 段DEA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模型計算學術虛擬社區的知識交流效率值、分析學術虛擬社區知識交流效率的影響因素,并測算學術虛擬社區知識交流效率的真實值,以促進學術虛擬社區知識交流效率,為社區管理者提供參考信息。
2 相關研究
通過文獻調研發現,國內外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學術虛擬社區知識交流的理論、模式、作用和效率4 個方面。
(1)學術虛擬社區知識交流的理論方面。彭紅彬等[2]以國內著名論壇CSDN 為研究對象,從中抽取出知識交流網絡,采用復雜網絡的分析方法進行分析,試圖定量化地揭示學術虛擬社區中知識交流的特點。張海濤等[3]運用社會網絡分析方法,對學術虛擬社區用戶知識交流網絡結構與功能作用進行了探究。王偉軍等[4]以科學網博客為研究對象,基于PLS(partial least square)結構方程模型對學術博客持續使用意愿的影響因素進行研究。
(2)學術虛擬社區的知識交流模式方面。胥偉嵐[5]從社會網絡理論出發,構建出基于人際網絡的知識交流模式。丁敬達等[6]在學術虛擬社區用戶類型和交互關系分析的基礎上,提出基于會話、鏈接和引證關系的三種主要知識交流模式。Zheng[7]以 “Emuch 論壇” 為例,分析了知識傳播主體、知識交流項目和知識傳播途徑,并對當前學術虛擬社區的知識交流模式提供了建議。
(3)學術虛擬社區的知識交流作用方面。國外學者認為,學術虛擬社區不僅能夠增強用戶間的知識交流,亦能挖掘用戶的隱性知識,提升決策水平。Huang 等[8]發現超鏈接能夠提高知識交流效率,利用矩陣聚類技術對學術虛擬社區成員在知識創造過程中的互動演化行為和用戶創造價值的功能進行探討,以確保可以通過學術虛擬社區持續做出最佳決策。Romero Borges 等[9]以Esanum、Sermo 和Doc‐tor.net.uk 等學術虛擬社區為例,闡述其對全球醫務人員的信息交流、病例討論以及新療法和藥物的促進作用。Kindler 等[10]基于protocols.io 平臺創建了一個名為VERVENet 的病毒學學術虛擬社區,該社區能夠與更廣泛的虛擬社區建立聯系,有助于病毒學科研人員的知識交流,并且該社區的最新文獻個性化推薦功能有助于科研人員對前沿技術的動態追蹤。
(4)學術虛擬社區的知識交流效率方面。學者們主要從學術虛擬社區知識交流效率的測度和學術虛擬社區知識交流效率的影響因素兩個維度展開研究。①關于學術虛擬社區知識交流效率測度研究維度,2014 年,宗乾進等[11]最先構建了學術博客知識交流效果評價指標,采用DEA 方法對科學網博客8個學科的知識交流效果進行實證研究;2015 年,萬莉[12]借鑒宗乾進等[11]構造的評價指標,采用非參數DEA、Malmquist 指數方法,對 “小木蟲” 、人大經濟論壇8 個學科的知識交流效率以及全要素生產率進行測度;2018 年,龐建剛等[13]以 “經管之家” 經濟學論壇三區為研究對象,采用SFA (stochastic frontier approach)方法對學術虛擬社區知識交流效率進行測定,并運用Kernel 估計研究學術虛擬社區知識交流效率的動態演化;2019 年,吳佳玲[14]采用Super-SBM 對學術虛擬社區知識交流效率進行測定,建立Tobit 模型對學術虛擬社區知識交流效率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2019 年,晉升[15]以 “小木蟲” 為研究對象,在現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將 “討論時間” 和 “再回復數量” 分別作為投入指標和產出指標,構建虛擬社區知識交流投入產出評價指標。②關于學術虛擬社區知識交流效率的影響因素維度,楊瑞仙等[16]以技術接受模型為框架,構建學術虛擬社區知識交流效率影響因素集成模型,研究結果發現,科研人員的年齡、科研工作年限、受教育程度、專業技術職稱、用戶的感知易用性和感知有用性對知識交流效率具有正向影響作用,且知識交流意愿對知識交流效率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吳佳玲[14]認為,社區設立時間、社區成員質量和社區管理水平等因素對學術虛擬社區知識交流效率具有顯著正向影響作用。
相關研究表明,國內研究較多、國外較少,原因在于國外關于知識交流的研究較為微觀和具體,理論研究較少。學者在對學術虛擬社區知識交流效率測度方面,多采用傳統DEA 模型、兩階段DEA模型的方法,未剔除用戶自身因素和外部(如社會、經濟、政策等的變化)因素對學術虛擬社區知識交流效率值測定產生的干擾[14],這種干擾會降低學術虛擬社區知識交流效率值的可信度。因此,針對此問題,本文提出了基于三階段DEA 模型的學術虛擬社區知識交流效率評價方法,該方法能夠剔除環境因素(environmental effects,EE)、隨機噪聲(statistical noise,SN) 和管理無效率(managerial inefficiencies,MI)對學術虛擬社區知識交流效率的影響,進而更加真實地反映學術虛擬社區的知識交流效率的實際數值。
3 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3.1 數據來源
本研究選擇 “小木蟲” 社區中較活躍的4 個版塊作為該研究的決策單元(decision making unit,DMU),包括:有機交流、微米和納米、第一性原理和金融投資。編寫Python 爬蟲程序獲取2009—2019 年 “小木蟲” 4 個版塊的用戶數、發帖數、瀏覽數、回帖數、再回復數、用戶加入社區時長、用戶在線時長、散金數等數據。數據采集時間為2019年12 月6 日至2019 年12 月11 日。為反映學術虛擬社區知識交流效率的真實情況,本研究根據以下規則對采集到的發帖、回帖數據進行篩選:
(1)同一主題帖中,發帖人在該主題帖下反復發帖,且沒有其他用戶回應,則記為一次發帖;
(2)同一主題帖中,同一回帖人多次回帖,且沒有其他用戶回應,則記為一次回帖;
(3) 同一主題帖中,不同回帖人回復內容相同,則記為一次回帖。
3.2 研究方法
“效率” 一詞來源于經濟學領域,在微觀生產理論中,效率是指資源投入與有用產出之間的比率。經濟學領域在測度效率時主要采用DEA 法。DEA 法由運籌學家Charnes 等[17]在1978 年提出,用于DMU 間的相對效率。Fried 等[18-19]認為,傳統的DEA 模型未將EE、SN、MI 等從DMU 效率評價的影響中剔除。Fried 等[18]認為,DMU 的效率受以上三種因素的影響,因而有必要將其分離,從而更加準確地測定DMU 效率值。三階段DEA 模型由Fried等[18]于2002 年提出,是傳統一階段DEA 模型的衍生和改進,該模型能夠剔除EE、SN 和MI 等因素對效率的影響,更加真實地反映DMU 的效率水平。學術虛擬社區知識交流效率是指在相同投入下,決策單元的實際產出與生產前沿(最優產出值)的差距,差距越小,則決策單元的知識交流效率越高。目前,有關學術虛擬社區知識交流效率的研究成果,主要采用傳統DEA 模型進行學術虛擬社區知識交流效率評估。本文為準確地測算學術虛擬社區知識交流效率,采用三階段DEA 模型剔除EE、SN和MI 等因素的影響,具體包括以下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傳統DEA 模型效果評估。DEA 模型用于評價相同DMU 間的相對有效性[20]。在第一階段,本文采用2009—2019 年 “小木蟲” 4 個版塊的投入產出數據對學術虛擬社區初始知識交流效率進行評價。由于本文著重考慮產出不變的情況下投入最小化的問題,選取投入導向型的BCC(Banker-Charnes-Cooper)模型對學術虛擬社區知識交流效率進行測算。對于任意DMU,投入導向下對偶形式的規模報酬可變模型[21]可表示為


其中,i表示DMU;θ表示各個DMU 的知識交流效率值;e表示改寫的非阿基米德無窮小量;S-、S+分別表示投入、產出的松弛變量;x和y分別表示學術虛擬社區評估知識交流效率的投入產出集合;λ表示第i個DMU 權重。
在BCC 模型下,DEA 模型求解規劃后的結果主要有三種:①若θ=1,且S+=0、S-=0,則DMU 有效;②若θ=1,S+≠0 或S-≠0,則DMU 弱有效;③若θ<1,則DMU 無效。其中,BCC 模型的技術效率(TE)=純技術效率(PTE)×規模效率(SE)。
第二階段:剔除EE、SN 和MI,構建相似SFA模型。將投入變量的松弛變量分解為含有EE、SN和MI 三個自變量的函數,剔除EE、MI 和SN 的影響。相似SFA 模型的表達式為


由此可得出vmi的值,進而將SN 分離。
第三階段:將調整后的投入值x?mi作為投入,再次利用傳統的DEA 模型計算各DMU 的相對效率,此時的效率值更能反映出學術虛擬社區知識交流效率的真實情況。
4 指標構成和影響因素
4.1 指標構成
現有文獻中,關于學術虛擬社區知識交流效率投入產出指標的設置,通常是由知識交流的廣度和知識交流的深度來衡量[13]。本文依據數據的可獲得性和統計口徑一致性原則,構建學術虛擬社區知識交流效率評價指標,如表1 所示。一級指標是投入和產出,投入和產出所對應的二級指標均是知識交流廣度和知識交流深度。其中,①投入指標的知識交流廣度,即用戶數,是指在知識交流過程中所涉及的進行知識交流的人員數量,人員投入是反映知識交流投入的重要評價指標。②投入指標的知識交流深度,即發帖數,知識交流的知識源于用戶貢獻的知識,發帖是用戶知識貢獻的主要形式,發帖量反映知識貢獻的知識源投入,是評價知識源投入的重要指標。③產出指標的知識交流廣度,即瀏覽數,是指學術虛擬社區4 個版塊自發帖到統計時間內的瀏覽總次數,反映知識交流產出的廣度。④產出指標的知識交流深度,即回帖數和再回復數,回帖數是用戶對知識的內化吸收程度,反映了學術虛擬社區知識交流的產出深度;再回復是指回帖者之間的交流,體現了學術虛擬社區知識交流層次的加深,反映了用戶之間知識交流的深度。
4.2 環境因素
已有研究發現,環境因素對學術虛擬社區知識交流效率的準確測定有所影響[14]。因此,本文有必要進行第二階段相似SFA 回歸剔除EE 的影響,綜合考慮數據的可獲取性及學術虛擬社區自身的特點,將影響學術虛擬社區知識交流效率的主要內部因素歸納為用戶因素和社區因素,如表2 所示。其中,用戶因素包括:用戶加入社區時長、用戶在線時長、散金數、用戶總發帖數以及用戶活躍期間發帖頻率;社區因素包括:社區規模、社區管理者參與度[14]和社區成員質量。

表1 學術虛擬社區知識交流效率評價指標構成

表2 影響學術虛擬社區知識交流效率的環境因素
5 結果分析與討論
5.1 傳統DEA模型分析
“小木蟲” 2009—2019 年投入產出指標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如表3 所示。從表3 可以看出,同一版塊、同一指標的數值差異較為明顯,且數據穩定性較差。例如,有機交流版塊投入指標的用戶數的最小值為88,最大值為8470,標準差為2861.640,這表明該版塊在2009—2019 年間不同年份用戶數的差異較大,且數據整體穩定性較差。其主要原因是 “小木蟲” 只允許訪問前200 頁的主題帖,無法爬取200 頁之后的數據,可能導致多年前的數據缺失嚴重。然而,本文主要研究學術虛擬社區知識交流的效率,反映單位投入的產出量,故可忽略不同年份數據缺失差異對本文研究結果的影響。
為消除投入產出單位差異對學術虛擬社區知識交流效率的影響,本文將所有投入產出變量進行取對數處理。為檢驗所選指標是否合理,本文對學術虛擬社區的投入產出指標進行 “同向性” 條件檢驗,如表4 所示。從表4 可以看出,2009—2019 年學術虛擬社區投入與產出指標的Pearson 相關系數均為正值,且在1%水平下顯著相關,符合模型的 “同向性” 假設。

表3 2009—2019年投入產出指標的描述性統計

表4 學術虛擬社區投入產出的相關性檢驗
本文采用Deap 2.1 軟件,對學術虛擬社區的知識交流效率的初始值進行計算,計算結果如表5 所示,學術虛擬社區知識交流效率值的變化如圖1所示。
從表5 和圖1 可以看出:
(1)學術虛擬社區整體的知識交流技術效率較低。由表5 可知,2009—2019 年學術虛擬社區知識交流技術效率在[0.946, 0.988]之間變化,4 個版塊的知識交流技術效率值均小于1,未達到DMU 有效。其中,第一性原理的知識交流技術效率最高,其次為有機交流、微米和納米,金融投資的知識交流技術效率最低。

表5 2009—2019年 “小木蟲” 4大版塊第一階段DEA知識交流效率值

圖1 2009—2019年第一階段學術虛擬社區知識交流效率值的變化
(2)學術虛擬社區4 個版塊知識交流效率的變化。由圖1 可知,學術虛擬社區知識交流的PTE 與TE 的變化趨勢基本一致,由此可知,剔除外生因素的影響前,學術虛擬社區知識交流的PTE 對TE變化的影響較大。但該結果未剔除外生因素的干擾,不能準確反映學術虛擬社區知識交流效率變化的實際情況,因而需剔除外生因素的影響,再次對學術虛擬社區知識交流效率進行測定。
(3)學術虛擬社區知識交流效率臨界值的區域劃分。為進一步研究第一階段學術虛擬社區4 個版塊知識交流效率的差異,本文參考劉偉[26]對臨界點的界定標準,將學術虛擬社區知識交流的PTE 和SE 的均值(0.975 和0.987)作為臨界值,對構成學術虛擬社區知識交流的PTE 和SE 進行劃分,可將學術虛擬社區整體知識交流效率劃分為 “雙高型” “高低型” 和 “雙低型” 三種類型,如圖2 所示。
“雙高型” ,即學術虛擬社區知識交流的PTE 和SE 均大于相應臨界值的版塊,由圖2 可知,只有第一性原理為 “雙高型” ,該版塊的知識交流效率較高,改進的空間較少,需要對PTE 和SE 進行小幅改進。 “高低型” 主要指PTE 高、SE 低或SE 高、PTE 低兩種類型,前一種類型的版塊為有機交流,后一種類型的版塊為金融投資;前一種類型的版塊主要改進SE,后一種類型的版塊主要改進PTE。 “雙低型” ,即PTE 及SE 均低于臨界點的版塊,納米和微米屬于 “雙低型” ,需要同時提高PTE 和SE。

圖2 調整前學術虛擬社區PTE均值和SE均值分類
5.2 似SFA回歸分析
本文主要依據Cobb-Douglas 型函數計算相應指標,且由于環境因素的單位影響和某些環境因素值可能為0 的情況,因此,將環境因素的原始數據增加1 后,再對其做對數化處理[27](公式(5))。
依據公式(2)設定的SFA 模型形式可得:

其中,Sit表示第一階段投入變量的松弛變量;Eikt表示環境變量,i表示 “小木蟲” 的4 個版塊,k表示環境變量,t表示年份;β0表示截距;βik表示環境變量的待估參數系數;vit表示隨機干擾;uit表示管理無效率。
本文將 “小木蟲” 4 個版塊的投入松弛變量作為被解釋變量,各環境因素作為自變量,通過Frontier 4.1 軟件進行SFA 回歸,回歸結果如表6 所示。由表6 可知,SFA 回歸的對數似然函數(log likelihood function)、似然比檢驗(LR test)均在1%水平下通過了顯著性檢驗,估計效果較好。除社區規模[14]外,其余環境因素的系數均不同程度地通過t檢驗,說明環境因素對各投入變量的松弛變量有所影響。學術虛擬社區兩個投入松弛變量的γ值均達到0.99 的水平,且在1%水平上通過t檢驗,說明MI 在學術虛擬社區知識交流效率中占主導作用。
在研究環境因素對投入變量的影響時,如果環境因素的系數為正值,則表明環境因素的提高會使松弛變量增長,即產出降低,導致對知識交流效率產生負向影響。若環境因素的系數為負值,則表明環境因素的提高會使松弛變量降低,即產出提升,使得對知識交流效率產生正向影響。

表6 第二階段似SFA回歸結果匯總
從表6 的回歸結果可知,用戶數和發帖數兩個變量的投入松弛變量相應的環境變量系數符號均一致,說明環境因素對這兩個投入冗余變量的影響趨勢相同。本文以發帖數松弛變量的似SFA 回歸結果為例進行分析,從用戶因素和社區因素兩個角度,分析環境因素對學術虛擬社區知識交流效率的影響。
(1)用戶因素。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①用戶加入社區時長與發帖數冗余正相關,與學術虛擬社區知識交流效率負相關。用戶的感知價值是社區成員滿意度和持續使用意愿的主要動力[28],用戶滿意度能夠顯著促進用戶的持續使用意愿[29]。用戶加入社區時間越長,學術虛擬社區知識交流效率越低,表明用戶對其在學術虛擬社區中的信息搜尋或知識貢獻經歷并不滿意,故加入社區時間較長的用戶參與知識交流的意愿降低。②用戶的在線時長與學術虛擬社區知識交流效率負相關。信息需求是用戶信息搜尋行為的重要驅動因素[30],持續在線的用戶信息需求降低,進而參與知識交流的意愿降低。③用戶活躍時間內發帖頻率與學術虛擬社區知識交流效率負相關。某段時間內用戶信息需求較高,當用戶信息需求得到滿足后,參與社區知識交流的動機降低,因此,社區管理者應從知識交流的內在動機和外在動機[31-32]的角度激勵老用戶積極參與知識交流。④散金數與學術虛擬社區的知識交流效率正相關。出于互惠動機,用戶的知識搜尋或使用行為得到滿足時,會激發用戶為社區貢獻知識的意圖[33],感知外在獎勵對用戶知識共享行為產生影響作用[34],用戶發放金幣會激勵更多用戶參與到社區的知識交流中,進而對學術虛擬社區知識交流效率有促進作用。⑤用戶總發帖量與學術虛擬社區知識交流效率正相關。用戶通過發帖、評論獲得更多的積分或更高的等級,從而建立社區威望,對用戶知識共享行為產生積極影響[35]。因此,社區管理者可以設立一些獎勵機制鼓勵用戶積極發帖[13]。
(2)社區因素。①社區規模系數為正,但未通過假設性檢驗,這表明盲目擴大社區規模而忽視社區發展的質量,不利于社區的發展[14]。②社區管理者參與度與學術虛擬社區知識交流效率成正比。高效合理的管理方式能夠促進學術虛擬社區內知識的轉化,營造良好的社區氛圍,進而提升用戶的知識交流體驗[14]。③社區成員質量系數為負,且絕對值遠高于其他環境變量,說明學術虛擬社區高質量用戶占比會對提升學術虛擬社區知識交流效率起到明顯作用。因此,社區管理者應提升高質量用戶占比。
5.3 調整后學術虛擬社區知識交流效率結果分析
(1)學術虛擬社區知識交流技術效率值測算。本文根據公式(3)對初始投入變量進行調整,并使用Deap 2.1 軟件對調整后的投入變量和原始產出變量進行分析,得到第三階段學術虛擬社區知識交流效率情況,如表7 所示。表7 仍基于投入導向型BCC模型測算學術虛擬社區知識交流的效率值。通過對比學術虛擬社區第一階段和第三階段知識交流效率,更易觀測到剔除EE、MI 和SN 后,學術虛擬社區4 個版塊知識交流效率的變化。從總體來看,調整后,學術虛擬社區的平均效率值由0.963 上升到0.973,但4 個版塊知識交流技術效率均值仍未達到1,處于DMU 無效狀態。調整前的TE 取值范圍為[0.946, 0.988],調整后的TE 取值范圍為[0.971,0.991],調整后各版塊的TE 差距縮小,且4 個板塊的TE 值均有所提升,其中金融投資變化最大。
(2)學術虛擬社區知識交流技術效率值調整前后的變化。學術虛擬社區4 個版塊知識交流效率的變化情況分別如表7 和圖3 所示。從圖3 可以看出,2016 年環境因素對學術虛擬社區知識交流效率值的影響最大。從時間上來看,除2011—2013 年,其余年份第三階段的TE 均高于第一階段的TE。由表7可知,調整后第一性原理的TE 值依然最高,其次為納米和微米、金融投資,最后為有機交流,各版塊知識交流技術效率值與調整前相比變化較大。圖4 表示調整后學術虛擬社區知識交流效率的變化情況,顯然,調整后學術虛擬社區的PTE 與TE 的變化趨勢仍然相似,由此可知,TE 與PTE 的變化顯著相關。

表7 2009—2019年 “小木蟲” 4個版塊第三階段DEA知識交流效率變化情況
(3)調整后學術虛擬社區知識交流效率臨界值區域的劃分。參照第一階段設定臨界值的標準,調整后以(0.970, 0.986)為臨界值,其分類結果如圖5所示,可以看出在剔除EE、MI 和SN 后沒有出現 “雙高型” 版塊。由表7 和圖5 可知,調整后除第一性原理SE 變化略微高于PTE 外,其余版塊的SE 變化均遠高于PTE 的變化幅度,因此,學術虛擬社區的環境因素主要對其規模效率產生影響。金融投資的PTE 變化幅度遠高于其他版塊,金融投資也由PTE 較低SE 較高變為PTE 較高SE 較低的 “高低型” ,社區管理者實際應小幅度提升金融投資的PTE,大幅度提升金融投資的SE。同時,由于第一性原理與金融投資在同一象限,社區管理者應小幅提升第一性原理的PTE,大幅提升第一性原理的SE。有機交流由第三象限變為第一象限,社區管理者應重點提升有機交流的PTE。微米和納米調整前后均為 “高低型” ,社區管理者應提升有機交流的PTE 和SE。

圖3 學術虛擬社區調整前后TE均值變化

圖4 2009—2019年第三階段學術虛擬社區知識交流效率變化

圖5 調整后學術虛擬社區PTE均值和SE均值分類
6 結論與建議
本文利用三階段DEA 模型,分析2009—2019年學術虛擬社區知識交流效率的變化情況。研究結果表明:①在學術虛擬社區總體效率方面。調整前學術虛擬社區的TE 均值區間為[0.946, 0.988],調整后學術虛擬社區的TE 均值區間變為[0.971, 0.991]。顯然,調整后的學術虛擬社區TE 均值的變化區間縮小,這表明EE、SN 和MI 的存在會導致學術虛擬社區TE 均值的變化幅度增大。②在學術虛擬社區4個版塊的知識交流效率方面。剔除環境因素的影響后,各版塊的TE 均值均有所提高,但仍未達到DMU 有效。在4 個版塊中,調整前后第一性原理的知識交流技術效率均最高,調整前金融投資的知識交流技術效率最低,調整后有機交流的知識交流技術效率最低。③在PTE 均值和SE 均值的臨界點分類結果方面。調整前可將學術虛擬社區劃分為三類,即 “雙高型” “高低型” 和 “雙低型” ;調整后 “雙高型” 區域消失,僅剩 “高低型” 和 “雙低型” 兩類。④在環境因素對學術虛擬社區知識交流效率的影響方面。用戶加入社區時長、用戶在線時長等因素均對學術虛擬社區的知識交流效率產生負向影響,散金數、用戶總發帖、社區管理者參與度以及社區成員質量對提升學術虛擬社區知識交流效率有促進作用。
依據學術虛擬社區知識交流效率的實證研究結果,從社區管理者的角度出發,為提高學術虛擬社區知識交流效率、擴大知識傳播范圍和促進知識創新,本研究提出以下三點建議:
(1)針對MI 的存在和TE 不高的問題,社區管理者應重點提高學術虛擬社區的資源配置水平,合理增加用戶數量、鼓勵用戶發帖,進而提高學術虛擬社區單位投入的產出量。
(2) 針對調整前后學術虛擬社區知識交流的TE 與PTE 變化趨勢一致的結果,社區管理者應加大對社區基礎設施和技術應用的投入。一方面,學術虛擬社區基礎設施和技術應用決定了社區用戶和各方資源能否有效地在社區內進行知識交流和資源共享;另一方面,社區平臺操作界面的易用性和平臺基礎設施的成熟度會影響用戶體驗,進而影響用戶再次參與知識交流的意愿。除此之外,擁有一定技術優勢的社區有助于加速信息、知識的傳輸,節約時間和成本。社區管理者應強化社區的個性化推薦功能,當學術虛擬社區推送信息與用戶知識分享意愿一致時,會引起用戶與社區的共鳴,從而進一步激發用戶的知識交流行為。
(3)針對不同環境因素對學術虛擬社區知識交流的影響結果,知識源與知識接收方在知識共享的過程中需要付出精力、時間和財富等代價,這將影響用戶參與社區交流的積極性。而物質獎勵能夠補償用戶參與知識交流過程中的成本,激發用戶的知識交流行為。社區管理者應該根據社區情況不斷調整學術虛擬社區的激勵機制,引導用戶積極參與知識交流,如設置升級任務、徽章、兌換券等,對知識貢獻者和新注冊用戶予以獎勵。社區管理者應建立完善的社區制度,營造相互信任、相互幫助的社區氛圍,以增強社區成員對社區的歸屬感和認同感。社區管理者可通過推送各類用戶共同關注的事務,拉近用戶之間的距離,加強用戶間的溝通,使用戶能夠快速融入社區。另外,社區可設置管理者淘汰機制,對出勤率較低的社區管理者進行淘汰,以提升社區的管理水平,為用戶營造更融洽的社區氛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