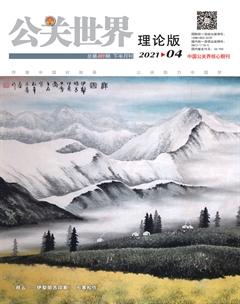降低中國刑事責任年齡界線設置的探究與創新
黃群輔
摘要:簡單降低刑事責任年齡雖不能完全匡正我國嚴重觸法青少年行為矯治的孱弱現狀,但其更多可解讀為一種信號和底線,以簡明的立法方式彰顯對未成年人采取保護或懲治的堅決態度,同時以回應國民最樸素的正義情感。
關鍵詞:刑事責任年齡 未成年人犯罪 降低刑事責任年齡
刑事責任年齡背后的基礎性理論是指,行為人在著手實施一定犯罪行為時是否享有意志自由以及這種意志自由是道德假設的作用還是心理事實的折射。當前,不少學者認為降低刑事責任年齡的實質收益甚微,單純地以數字大小孤立地劃分界線,僅僅機械性地多圈住一部分人并不能達到降低原意。
對此,筆者認為,單純以降低刑事責任年齡界線的方式應對當前嚴重觸法青少年行為的矯治,確實不能完全達到匡正孱弱現狀的目的。但其更多地可解讀為一種信號和底線,以簡明的立法方式彰顯對未成年人采取保護或懲治的堅決態度,同時能夠積極回應國民最樸素的正義情感。當前,未成年人生長發育進展以及心智成熟深度不同以往,社會大環境下的通識教育、行為影響和心理熏陶等因素,對青少年的意志自由產生的激烈沖擊,已不同于傳統認知。
一、未成年人權益保護與其刑事責任年齡界線要義的探究
我國現有刑事責任年齡設置長期未變。針對未成年人犯罪和處罰領域,我國主要由三部法律調整。其中,只有《刑法》明確了關于“刑事責任年齡”的規定。而2008年至2019年的時間里,涉及“未成年人刑事責任年齡”的條款僅被修改過一次,即2015年的《刑法修正案(九)》,但其也并未對刑事責任年齡作出實質性修改,只是對條款進行了一些細節填充。
未成年犯罪案件中多數被害人的權益保護被忽略。縱觀近年來不斷涌現的低齡惡劣犯罪案件和普通民眾要求降低刑事責任年齡的呼聲,可以明顯感覺到,問題的實質在于日益嚴重的未成年人犯罪社會現實和對受害人及社會情感的撫慰薄弱。面對這一痼疾,近年來國家對于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方面也開展了大量規制工作,但未成年人犯罪總體上仍持續增多,在數據中體現為上升趨勢持續到21世紀初,且刑事犯罪總數基數呈螺旋上升模式增多,導致司法效果從保護偶爾犯錯沒有顯著人身危險性的未成年人扭曲為縱容和沉溺惡性未成年人肆意犯罪的搖籃,甚至導致“惡性逆變”。
而目前我國刑法對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似乎陷入了一種尷尬境地,在強調加害人的人權保障權利和未成年人的特殊身份時,往往將案件中明顯更處于弱勢地位的被害人權利忽略,粗暴地理解未成年人權益保護的要義,削弱被害人在犯罪過程中所受侵害的法益、恐懼和不安,僅以未達刑事責任年齡對未成年罪犯減輕處理程度,最后不了了之,失去刑法懲罰、震懾性的本意,甚至達不到教育感化未成年人罪犯,警示被告人家屬的效果。
如轟動一時的大連13歲男孩奸殺10歲女童案近日民事訴訟開庭時,被害人家屬表示“他們的訴求主要是賠償和道歉,事發后男孩家人從未露面,也從未以任何形式向被害人及其家屬表示過歉意,這令被害人家屬感到非常氣憤。誠然,在這個典型案例中,10歲未成年被害人的權益保護與13歲被告人的權益保護完全失衡,從案件發生到民事審理過程中更是渲染出了多數被害人的“無力和易受傷害感”,也容易讓一般公眾喪失對國家公信力的信心。
二、降低中國刑事責任年齡的可行性和要義探究
未成年罪犯具備現實刑事責任能力卻不處罰。自2012年《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訂后,以“未成年人犯罪”為關鍵詞的案件數量增勢迅猛。截至2019年12月,于中國裁判文書網內檢索,08至19年十年間,以“未成年人犯罪”為案由,“未成年人”為關鍵字的相關裁判文書數目就達到3738篇。
多以侵害人身法益出現的未成年案件手段殘虐,現有措施不足以應對。從典型案例來看,未成年人案件多以“主觀惡意”的實施行為和“客觀危害”的犯罪結果體現,其中不乏14周歲以下未成年犯罪人犯罪手段殘虐,有預謀地跨過法律紅線。然而,一方面,刑事司法實務操作中,大多都會基于對“責任年齡”的優先考慮條件,以對侵害人的責任能力為標準,倒置刑事立法中明確規定的犯罪構成行為標準,有悖刑事立法的立法初衷,在不經意間發生了本末倒置的目標轉換或價值取向的轉換,有失偏頗。另一方面,即使刑事司法者在意到法益的平衡,在處置具體個案時,也會不斷在“被告與被害”之間權衡,甚至常常會被社會公眾的質疑和憤怒困擾,對其要求司法者解釋司法判斷的理由百口莫辯,難以服眾。
因此,刑事責任年齡的規定不僅僅是年齡的問題,也是社會對仍在成長的監護階段的未成年人一種寬容和仁慈的反映。但以教育為主的處置手段不同于刑法意義上的處罰,也因此決定了這種手段使用的范圍僅“限于青春期的違法行為”,而不能擴大為對所有嚴重惡性行為的“保護傘”。
僅以有待商榷片面否定當前嚴重低齡犯罪人的犯罪行為,而遺漏對其犯罪客觀事實的分析,觀察行為發生的條件、行為實現的難度、行為操作中的組織力、時間等候的控制力以及行為人要表達的情緒背景等,都嚴重偏離了刑事立法的初衷。
三、降低中國未成年人刑事責任年齡界線的新理論建構
針對嚴重侵犯人身法益罪名,下調最低未成年人刑事責任年齡界線至12周歲,同時嚴格限定適用條件。
1.通過刑事立法規定,更好地預防和懲治犯罪
首先,下調最低刑事責任年齡界線,是以國家意志作出的強制性措施,再輔之以大面積、有針對性、有深度的法制宣傳工作,能充分地向一般社會大眾尤其是未成年人群體釋放出法律、國家對于犯罪行為根本原則不會動搖的決心和態度。其次,從案件的常發性來看,低齡未成年人的犯罪主要集中在故意殺人和故意傷害方面,針對人身法益的暴力侵害比例最高,其中尋釁滋事、聚眾斗毆和綁架都可以被故意傷害包含。
借鑒14-16周歲未成年罪犯相對負刑事責任的罪名范圍,筆者認為12-14周歲年齡階段的低齡未成年罪犯可以就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死亡、搶劫、強奸行為承擔相應的刑事責任。設置此項條款有助于刑事司法人員在處理易引發社會爭議和公眾不滿的具體個案時,能清晰地做到有法可依,在解釋和應用法律時彌補“捉襟見肘”的現象,能真正做到給“被告人以及被害人”一個交代。并且,所涉及罪名均為嚴重侵害人身法益的暴力犯罪,對于被告人來說,能真正做到撫慰被害人,教育行為人的方法就是將其“繩之以法”,這不僅僅是一般人對于法律最基本和最真摯的信賴,更是法律保護民眾樸素的價值觀的充分體現。
2.突出法院角色,加強未成年人視角,引入篩選機制和獨立法庭
法院作為裁判者,在少年司法體系建構中發揮著不言而喻的作用。但目前,少年司法體系中法院作用缺失,角色參與感不強,往往因為“未達刑事責任年齡”而“一罰了之”或“不了了之”。
(1)嚴格適用條件,明確區分未成年人犯罪和成年人犯罪,建立獨立的少年司法制度
借鑒國外現行少年司法制度經驗研究,一方面,對于中國的“觸法少年”,即未滿14歲便觸犯了刑法法規的少年,除了依據下調刑事責任年齡所列罪名進行相應刑罰處罰的設置,對于其之后回歸社會的教育和矯正工作,以及未列入12-14周歲刑事責任年齡列舉罪名的低齡未成年罪犯其他刑事犯罪,設立相應的公立強制性矯治場所,從“可以由政府收容教育”轉變為“必須由政府收容教育”。另一方面,對于主觀惡性不大,犯罪情節較輕微,矯治難度一般的低齡未成年人,建立以公權力為主導,以社會福利機構為輔的組織,專門從事針對性福利事項和指導低齡未成年人認知活動,特別是針對經法院或檢察院研究決定后,做出收容教育決定或附條件不起訴決定,經強制移送過來的少年保護案件進行監護和教育,形成以教育、感化、寬宥和關愛為主的矯治柔性階段。在經相關考核和認定后,通過一定措施介入幫助其重返社會,開始新的生活。這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監護人與相關部門間相互推脫,導致未成年人及時矯治陷入僵局,也有效遏制“楊永信戒治中心”的亂象。
(2)增加未成年人犯罪的父母責任比重,完善責令監護人嚴加管教制度
父母責任并非強調父母對被害人的連帶責任,責任歸責只能治標不治本,而是規定其對罪錯子女的強制性養育責任。實踐中,為使父母成為合格的父母,具備教育孩子的能力,可以先由專家對父母進行培養。但由于未成年罪犯犯罪的根源常常來源于家庭情感缺失、父母關愛不足等問題,對此建議應由立法明確強制規定監護人的責任比重,借鑒英國在收容教養中的“養育協議”與“養育令”措施,在對未成年人罪犯采取強制教育措施后,由執行機構強制性對未成年人及其監護人進行必要的指導,凡屬少年兒童的問題,無論是社會、家庭還是自身原因、無論是先天抑或后天形成、不管是生理還是心理問題,都可以由監護人單獨或監護人與子女一起同執行機構的專業人員共同研究探討,提出矯正和防治方案并簽署“養育協議”,規定監護人在未成年人收容教養期間及重返社會后一定階段內的法定養育責任,并由執行機構相應工作人員監督實施。
四、結語
近年來,關于修改未成年人法律的討論聲正盛,而落到法律實處的改革需要立法機關和社會各界法律人士的反復推敲和討論,更需要公眾的耐心。
筆者認為,降低刑事責任年齡的舉措并不意味著對未成年人采取嚴苛的刑罰,其在一定程度上擴大對犯罪主體進行有效追責的范圍,能夠有效進一步維護社會的穩定,彰顯司法的公平和正義。立法與社會需求相契合,才能更好地推動社會法制。
項目名稱:“四川師范大學‘大學生創新創業計劃項目資助”項目編號:S201910636002
參考文獻:
[1]新浪新聞.《大連13歲男孩殺害10歲女童案民事訴訟開庭:被告缺席》[N/OL],(2020-5-9)[2020-5-9],http://news. sina.com.cn/s/2020-05-09/doc-iirczymk0667893.shtml
[2]李玫瑾.《從刑事責任年齡之爭反思刑事責任能力判斷根據——由大連少年惡性案件引發的思考》,載《中國青年社會科學》2020年第1期,第10-2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