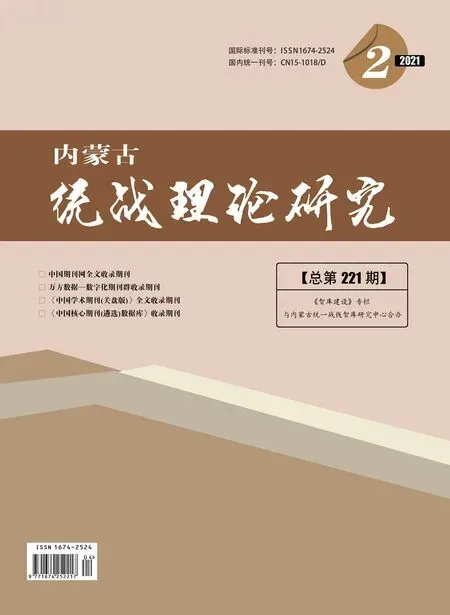歷史文化視野下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發展演變
◇ 文/西藏社會主義學院 周洪軍 李文韜

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以后,特別是黨的十九大以來,我們黨提出了“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大命題,由此與之相關的議題一度成為政治理論研究的熱點。綜觀現有研究成果,一些學者都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思想淵源歸于千百年來形成的“華夷一體”的族群觀,但對二者的相互關聯等基礎性研究卻鮮有涉獵。鑒于此,本文試對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對“華夷一體”族群觀的承繼關系做一簡要探查。
一、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源頭:“華夷一統”族群觀的形成與發展
民族共同體最初呈現為在一定族群觀指導下構建而成的族群共同體。在中華民族文明發展史上,據以構建族群共同體的“華夷一統”族群觀經歷了從“夷夏之辨”到“華夷一體”的轉變。
早在夏商之時,“華夷”之說就已出現,其中“華”或“夏”是居于中原地區的人們的自稱,而他們對居于四周且在文化上與自己不同的民族則稱為“夷”。到了西周時期,“華夷”之說又增添了“分服”意蘊,就是根據其與周王的親疏關系將全國的邦分為畿蠻夷戎狄“五服”。此時,雖有“華夷”“親疏”之分,但是這種劃分是整體內部的劃分,強調普“天下”各族群的統一性與整體性。至此,“華夷”之說羽翼漸豐。
春秋戰國時期,儒家諸派代表人物對“華夷”之說加以豐富與完善,其中最為完備的當屬孔子提出的“夷夏之辨”思想。孔子在《春秋》中以反問的方式強調:“裔不謀夏,夷不亂華,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在這里,孔子無疑是主張,在“大一統”之下明“夷夏之辨”,在對“四夷”進行“辨”的基礎上施以“以和為貴”策略。其后,“夷夏之辨”逐步得以完善與發展,厘定并包含了“夷夏有別”和“夷夏之變”兩重涵義。其中,“夷夏有別”不僅是指“夏”和“夷”之間在生活習慣、傳統風俗等方面“有別”,而且還指二者在地理空間分布上“有別”,體現為“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夷夏之變”是指傳統儒家基于對“夷夏”可變性的肯認,主張讓文化程度較高的族群與“文化低即不遵守周禮的人或族(蠻、夷、戎、狄”)深度交融,使二者相互趨同、相互促進。
秦漢時期,“華夷一體”思想在中原士大夫階層得以萌生并發展。漢昭帝時,桓寬在其編著的《鹽鐵論》中強調:“中國與邊境,猶支體與腹心也。夫肌膚寒于外,腹心疾于內,內外之相勞,非相為賜也!唇亡則齒寒,支體傷而心僭怛。故無手足則支體廢,無邊境則內國害。”在這里,將中央和邊境比作“腹心”和“支體”的關系。非僅如此,大多少數民族政權也對中央政府有著依附感和認同感,一些首領甚至認為,無論是“華”還是“夷”,只要具有較高德行,都可以成為受天命的皇帝。匈奴漢國高祖劉元海在稱帝時說:“夫帝王豈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東夷,顧惟德所授耳。”在這里,劉元海盡管是在為自己統治的合法性辯護,但是居于其思想意識深處的“華夷一體”思想還是根深蒂固且顯而易見的。
魏晉南北朝是我國歷史上民族矛盾較為突出的大分裂時期,在“大一統”觀念影響下,各族裔政權都以華夏正統文明承襲者自居。在這一時期,傳統上不被納入“正統”范疇的各少數民族政權,都紛紛賦予“正統”以新義,進而提出華夷皆正統。《魏書》堅稱:“昔黃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內列諸華,或外分荒服”“其裔始均,入仕堯世,逐女魃于弱水之北,民賴其勤,帝舜嘉之,命為田祖”。這樣,拓跋鮮卑建立的魏朝通過追述華夷共祖為自身正統地位尋求血緣上的合法性。南北政權對華夏正統地位的激烈爭奪,表明了它們對華夏傳統政治倫理和歷史文化的深刻認同,彰顯了對華夷共祖共融的“華夷一統”理念的深刻認同,從而發展出“華夷皆正統”的全新理念。在這一理念的引導下,北魏孝文帝開啟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社會改革,著力推進鮮卑貴族與漢族門閥氏族的交融與合流,使二者在政治上榮辱相共、在血統上凝為一體,不僅促進了多民族國家政權的穩固,而且極大地推進了“華夷一體”的進程。
隋唐以降的歷代封建王朝,“華夷一家”理念倍受封建王朝推崇。隋文帝楊堅強調:“溥天之下,皆曰朕臣,雖復荒遐,未識風教,朕之撫育,俱以仁孝為本。”唐太宗李世民主張:“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唐玄宗李隆基對少數民族不分“夷狄”同等接納,認為“萬邦述職,無隔華夏”,主張“王者無外,不隔遐方”。明太宗朱棣強調:“華夷無間,姓氏雖異,撫字如一。”非僅如此,“華夷一家”理念也被少數民族政權領袖接受。金熙宗完顏宣主張:“四海之內皆朕臣子,若分別待之,豈能致一。”元太宗孛兒只斤·窩闊臺認為:“圣人以四海為家,不相通好,豈一家之理哉。”清雍正帝愛新覺羅·胤禛強調:“中國而夷狄也,則夷狄之;夷狄而中國也,則中國之”“自我朝入主中土,君臨天下,并蒙古極邊,諸部落俱歸版圖,是中國之疆土開拓廣遠,乃中國臣民之大幸,何得留有華夷中外之分論哉!”到了乾隆時期,“華夷一家”理念得以進一步發展,認為天下“大一統”為“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從而將其提升到社會發展普遍規律的層面和高度。可見,隋唐以來的歷代封建統治者,不論是漢族王朝還是少數民族建立的王朝,都將“華夷一體”視為自然且必然之事。
二、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雛形:“大一統”理念的內涵
“大一統”理念涵括三重主要蘊含:“天下一統”的疆域觀、“王權一統”的政治觀和“儒家一統”的文化觀。
(一)“天下一統”的疆域觀
疆域是族群共同體存在并發展的最為重要自然基礎和空間條件。因而,族群共同體首先呈現為一種疆域共同體。在此維度上,“華夷一統”族群觀主張“天下一統”的疆域觀。
“天下一統”的疆域觀最早源于“天下一統”的“天下觀”。“天下觀”最早可追溯至夏朝建立之初。夏啟在武力消滅有扈氏后,即著手廢除當時實行的部落“禪讓制”,通過“鈞臺之享”使各族臣服于自己,確立了自己“天下”之“共主”的地位,第一個“大一統”王朝——夏朝——由此得以建立。至此,“天下觀”得以初步構建。到了商朝,指代商之朝廷的詞匯包括“中商”“大邑商”“中土”和“土中”等,而作為商之朝臣的四方諸侯則根據地理方位被稱作東土、南土、西土、北土,表明了商朝在當時整個“天下”中居于中心和核心地位,“天下觀”由此得以清晰呈現。此時,作為“天下觀”之核心概念的“天”或“天下”,意指在當時歷史條件下人們認知能力所及的整個物理世界。
西周時期,在“天下觀”的基礎上,又出現了“四方”“四海”“九州”“畿服”等概念,從而“天下一統”理念開始萌生,其核心主張為:整個“天下”范圍的所有邦國,無論其距離周遠近,無一不屬于周天子管轄范圍。在戰火紛飛的戰國時期,“大一統”地理觀念又進一步得以完善與發展,產生了“九州說”“五服說”等概念。由此可見,中國自古以來就呈現為一個“‘中心清晰,邊緣相對模糊’的政治體”。
秦漢時期,“天下”的涵蓋范圍以中原大地為中心而不斷擴大。秦王嬴政秉承著傳統上流傳下來的“天下一統”觀念,在滅六國基礎上大舉征戰四方,使帝國疆域不斷拓展,治域內族群也日漸增多,從而使“天下一統”理念得以初步實現。西漢武帝時期,帝國疆域在周遭多個方向都得到拓展:向西張騫鑿通西域通道;向北霍去病、衛青三度擊退匈奴;在東北地區設置樂浪等四郡;向南徹底征服閩越和南越并控制了海南島;向西南設置健為等七郡。東漢時期,大將竇憲攻擊匈奴致其分裂為南北兩部,又出塞三千余里追擊北匈奴至燕然,解決了長期威脅帝國北疆的匈奴問題;明帝時又在原哀牢國轄地內設置哀牢、博南二縣。至此“俾建永昌,同編億兆”。
秦漢之后,唐代秉承“天下一統”的疆域觀,不僅推進了疆域空間的拓展,而且還在新拓展的邊疆地區普遍實施羈縻制度,先后設置800多個羈縻府州,形成了“際天所覆,悉臣而屬之,薄海內外,無不州縣”的“大一統”局面,從而對疆域“大一統”作出了巨大貢獻。其后,作為第一個少數民族建立的全國性政權,元朝先后消滅了南宋、金、西夏、大理等政權,并將西藏真正納入中央政府管轄范圍,從而在空前廣闊的帝國疆域內實現了“大一統”。到清朝時期,中國這一坐落于亞洲東部的“大一統”帝國的四至基本確定下來:西起帕米爾高原,東至太平洋西岸諸島,北起廣闊的荒漠,南至浩瀚的海洋。
縱觀古代中國文明史,無論地理疆域大小,不管治理狀態如何,遼闊疆域的完整與統一是每一個中國人的普遍的、共同的、永恒的追求。正是對這種“天下一統”疆域觀的追求和踐行,“天下”之疆域不斷擴大并穩固。
(二)“王權一統”的政治觀
要維系一個特定族群共同體,最根本的是形成一個相對穩固的政治形態,以及與之相匹配的一套秩序體系。就此而言,族群共同體同時也是在特定政治理念引導下構建而成的一種政治共同體。在很大程度上,“華夷一體”族群共同體是在“王權一統”政治觀的引導下構建而成的一種政治共同體。
早在先秦時期,“華夷一體”族群觀之政治大一統意識已初步形成。《公羊傳·隱公元年》有云:“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在這里,將“正月”歸屬于周王,用以表明天下都聽命于周王的政令,這是“大一統”概念首次出現在有據可考的文獻資料中。春秋戰國時期,面對“多元多中心的格局”,各家各派先賢人物紛紛致力于尋求政治“大一統”的路徑和良方,形成了“百家爭鳴”的局面。在政治紛爭過程中,秦國通過對當時最為先進“王權一統”理念的深入踐行,尤其是采納并秉持了丞相李斯所提出的“滅諸侯,成帝業,為天下一統”的政治策略和主張,得以從萬邦之中脫穎而出,開啟了征伐天下的艱難進程,順次滅掉與其齊名甚至曾一度更為強大的其他六國,結束了長達兩個半世紀諸侯割據的分裂局面,成就了一統六國的霸業,并在幅員遼闊的治域內創立并實行了高度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秦王嬴政自任“始皇帝”,擁有不受任何制約的至高無上權力,從而實現了政治形態從“萬邦之國”向“天下一統”的歷史性轉變。
秦朝創立的一整套體現著“大一統”政治共同體理念的國家政治制度,成為其后歷代封建王朝在其治域內施政與管理的主導性策略和指導性理念。兩漢時期,在隴右、河西地區大力推行郡縣制,在西域地區推行都護府制,在西北羌族聚集區實行屬國制和護羌校尉制。自隋朝始,統治者認識到少數民族地區情況的特殊性,對于歸附和被征服的少數民族開始實行“以夷治夷”的政策,讓他們自己管理本民族的事物。唐朝貞觀四年(630年),唐太宗李世民在平定東突厥之后,開始推行羈縻府州制度,在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先后設立羈縻府、州、縣八百多個,既保留了少數民族傳統的行政管理制度,又將少數民族地區納入國家統一行政設置之中。元朝時期實行內地府州與邊疆土司制度、藩屬制度、朝貢制度等差別化治理的制度設計,并通過行省制把蒙古與西藏首次納入帝國的統治疆域,不僅真正實現了空間疆域上的“天下一體”,而且還在整個帝國治域內呈現出“王權一統”的政治局面。到了清朝,統治者大力推進邊疆——內地政治一體化進程:在東北,將三將軍轄區改建行省;在西北,廢除新疆的伯克和札薩克制度并改設行省;在北部,廢除蒙古各部的札薩克分封制,增設州縣和改設行省;在西南,提高駐藏大臣的主事權力,并在西藏各地實施與內地近似的行政管理秩序。
可見,在秦漢之后2000多年的歷史長河中,無論何種族裔逐鹿中原,最終的治理模式無一不是追求帝國政治統治的完整統一,從而使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態一直以穩定的“王權一統”為主流。
(三)“儒家一統”的文化觀
政治上的“大一統”必然要求思想文化上的“大一統”。在一定意義上,“華夷一體”族群觀所涵括的“大一統”意蘊,是在“儒家一統”理念所激發的認同機制的作用下而形成的。
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中,中國是唯一沒有發生文化斷流的國度。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最為重要而關鍵的無疑在于“大一統”意識對思想文化領域的建構和維系。前秦時期,共同體的維系主要依賴于自三皇五帝以來的道統論說,尤其是西周時期創立的禮樂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戰國時期的亂世局面正是“禮崩樂壞”的消極后果。面對這一局面,儒家創始人孔子在“百家爭鳴”的思想文化氛圍中,把實現“天下”思想文化整合作為自己畢生的理想訴求和價值追求,主張借助“文化一統”來確立并維護“天下一統”的“王道秩序”,并以“正天下之不正”“合天下之不一”之名確立了儒家思想在思想文化領域的正統與主導地位。儒家作為“百家”之一,之所以能夠勝出,在于它是當時最忠實的道統傳承者以及最堅定的“文化一統”理念踐行者。
事實上,“儒家一統”的文化觀不僅內在地要求“獨尊儒術”,而且還為秦漢以后儒家在思想文化領域主導地位的確立與穩固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大作用。西漢建立之初,盡管實現了政治上的統一,但思想文化上的紛爭遠未平息,有時甚至還達到危及政權穩固和政局穩定的程度。面對這一局面,漢武帝為了鞏固中央集權制度,下詔征求治國方略,最終采納了董仲舒的主張。董仲舒在被委以重任后不負重托,在吸取儒家思想精華的基礎上博采眾家之長,創立了以“天人感應”“三綱五常”等為核心內容的儒家思想體系,開始推行“獨尊儒術”的政治策略,使之成為此后歷代封建王朝占主導地位的核心價值體系,成為促進并鞏固“王權一統”的策略工具和有效手段。其后,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王夫之認為,“儒者之統,與帝王之統并行于天下,而互為興替。其合也,天下以道而治,道以天子而明。及其衰,而帝王之統絕,儒者保其道以孤行而無所待,以人存道,而不可亡。”在這里,王夫之將“儒家一統”置于國之為國的首要基礎重要地位。
可見,對于傳統的帝國政治秩序和政治形態而言,儒家思想文化無疑是一種絕好的思想凝聚劑和文化整合劑。無論何種族裔或政治力量入主中原,基本上都認可并推行“儒家一統”的理念和傳統,借其在思想文化領域的主導地位和統轄效應為政治統治合法性正名,為實現政治統一提供必要的思想基礎和文化論證,進而提升政治統治和社會管理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三、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完善:新時代條件下的創新與發展
近代以來,隨著民族國家的形成與發展,族群共同體逐漸發展為民族共同體。在這里,民族共同體是指在一定地域內形成的具有特殊歷史文化聯系、穩定經濟活動特征和心理素質的民族綜合體。基于這一概念,考古學家夏鼐于1962年發表的《新中國的考古學》一文,首先提出并使用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概念。1988年費孝通先生基于人類學、社會學和民族學的視角,提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以及中華民族是一個民族實體和統一體的觀點,使得中華民族共同體概念更加成熟與完善。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與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對“中華民族共同體”進行了系統闡述,從而將其納入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話語體系。2017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進一步提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加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進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這一全新概念由此產生。筆者試從上面所述及的疆域觀、政治觀、文化觀三個重要維度上,分析考察“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概念對“華夷一體”族群觀的揚棄與超越。
(一)在疆域觀維度上:從“天下一統”到領土主權完整
在傳統的疆域觀中,疆域單純指族群共同體生存于其間的地理空間。到了近代,隨著主權概念的出現,傳統的疆域或領土概念又疊加了一層主權意蘊。一般意義上,主權是指一個國家對其轄域所擁有的至高無上的、排他性的政治權力。與疆域或領土相比,主權更具有基礎性和根本性。對此,習近平在論及總體國家安全觀時,將領土完整與國家主權相提并論,強調“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全體中華兒女共同愿望,是中華民族根本利益所在。”這樣,習近平在借鑒吸收“天下一統”疆域觀的基礎上發展出了強調完整與統一的領土主權觀。這一全新觀念,在兩個層面上實現了對傳統疆域觀的揚棄和超越。
其一,承認并尊重他國領土主權。傳統的“天下一統”疆域觀是排他性的,強調“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否定并排斥除“王”之外擁有合法疆域的可能性。新時代領土主權觀繼承了傳統疆域觀對國家疆域統一性與完整性的重視與強調,主張“我們偉大祖國的每一寸領土都絕對不能也絕對不可能從中國分割出去!”然而,它不僅強調本國擁有領土主權,同時也承認并尊重其他主權國家的領土主權,主張在國際關系中堅持主權原則,強調“世界各國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侵犯、內政不容干涉”,“世界各國一律平等,不能以大壓小、以強凌弱、以富欺貧。”
其二,維護領土主權應采取和平手段。在傳統疆域觀指導下,不論是夏啟武力消滅有扈氏,還是秦王嬴政實現一統六國,甚或蒙元先后滅掉南宋、金、西夏、大理等政權,奉為圭臬的無一不是叢林法則,所采取的手段從未外乎武力征服。新時代領土主權觀固然沒有否定維護領土主權的武力手段,強調“軍隊必須把國家主權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履行好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領土完整的根本職責。”同時也給出了以和平的方式維護領土主權的選項,主張“中國將堅持同直接當事國在尊重歷史事實的基礎上,根據國際法,通過談判和協商解決有關爭議。”在這里,“有關爭議”主要是指領土主權問題上的爭議。
(二)在政治觀維度上:從“王權一統”到黨的集中統一領導
如上所述,傳統的“王權一統”政治觀強調最高統治者政治權威的至高無上和不可分割性,以實現王權治域內的政治統一與行政高效。新時代政治觀繼承了傳統政治觀對政治權威統一性的推崇與注重,強調“堅持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這是黨的領導的最高原則,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含糊、不能動搖。”在此基礎上,后者對前者又實現了揚棄與超越。
其一,握有一統政治權力的“王”從帝王轉向了人民。在傳統的“王權一統”政治觀中的“王”,指的是獨享至高無上政治權力的封建帝王,其借助手中的權力實現對治下臣民的專制統治。與封建社會存在的統治與被統治關系迥然有別,我們黨與人民群眾的關系是魚水關系。“中國共產黨從誕生那天起,從來就沒有自己的私利,而是以全心全意為人民謀福利為根本宗旨。”可見,新時代政治觀中的“王”是人民群眾中的一員;我們黨實現集中統一領導的目的不在其自身,全然在于更好地為人民謀福利。對此,習近平強調:“堅持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始終與人民群眾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
其二,政治權力的運行從王權獨尊到黨的集中統一領導。縱觀封建社會發展史,歷代帝王政治權威的獲得并維持是通過武力壓制而實現的,而且其政治權力的行使是排他的、自上而下的。在很大程度上,“華夷一體”的過程就是封建帝王對生活于不同區域不同族群推進一體化統治的過程。然而,在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視角下,由于少數民族和其他民族一樣同屬于“王權一統”之中“王”的有機組成部分,其獨有的各種生活習慣、文化傳統等被得到充分尊重,并通過“民族區域自治制度”這一制度安排予以維護和保障。對于堅持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習近平強調要做到“兩個結合”。一是“堅持統一和自治相結合”,就是要求“要在確保國家法律和政令實施的基礎上,依法保障自治地方行使自治權,給予自治地方特殊支持,解決好自治地方特殊問題。”二是“堅持民族因素和區域因素相結合”,強調“民族區域自治不是某個民族獨享的自治,民族自治地方更不是某個民族獨有的地方”,而是在維持國家政治統一基礎上的民族和地方自治。
(三)在文化觀維度上:從“儒家一統”到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主導地位
在封建社會中,長期以來尊奉的是以仁愛、正義、自強等理念為核心的儒家文化價值觀,借其思想“凝聚劑”和文化“整合劑”作用的發揮,對統合文化思想、促進社會穩定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大作用。習近平繼承了中華傳統文化中重視文化價值的思想精髓,強調它“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其所蘊含的核心價值觀“是一個民族賴以維系的精神紐帶,是一個國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礎”。他同時認為,“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精神”,因而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獨特的文化以及核心價值觀。與封建時代所秉持的儒家文化的核心價值觀不同,當代中國所推崇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對前者實現了揚棄與超越。
其一,文化價值從為封建治權辯護到為人民服務。在封建社會中,歷代統治者之所以推行“儒家一統”的文化觀,是為了借儒家核心價值觀所主張的“三綱五常”來實行愚民政策,并通過其在思想文化領域的主導地位和統轄效應為其統治的合法性辯護,從而維護自身的政治權威和獨裁統治。與之相對,新時代文化觀主張在文化建設中要發揮人民的主體作用,“堅持文化發展為了人民、文化發展依靠人民、文化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其中,“堅持文化發展為了人民”就是要堅持人民在文化建設中的價值主體地位,是與“……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主張相一致的。這樣,新時代文化觀將人民群眾置于主體地位,從而實現了對“儒家一統”文化觀之價值主體的原則性顛覆和根本性轉換。
其二,核心文化價值與非核心文化價值關系從“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到“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盡管新時代文化觀與傳統的“儒家一統”文化觀同樣強調核心文化價值觀的核心作用,但在對核心價值與非核心價值關系問題上卻走向了對立。后者堅持儒家文化這一核心價值的獨尊地位,主張“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與之相對,新時代文化觀主張,在強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文化領域核心與主導地位的基礎上,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最早是毛澤東在1957年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提出的,主張在藝術問題上“百花齊放”、在學術問題上“百家爭鳴”。習近平在繼承毛澤東文藝思想的基礎上,結合當今時代條件又賦予其時代性、創新性意蘊,強調文藝創作要“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堅持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在族群文化關系上,這一文化觀體現為對民族文化差異性與多樣性的尊重與包容,強調“各民族要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賞、相互學習、相互幫助”。
其三,對核心文化價值的遵從從文化強制到文化認同。如上所述,在封建社會實現“儒家一統”的過程中,所采取的是對“百家”之非核心文化價值予以“罷黜”的強制手段,進而確立儒家之核心文化價值的“獨尊”地位。與之相對,在新時代文化觀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之“核心”地位的確立源于人們心理層面的文化認同;而文化認同是民族團結之根。對此,習近平強調:“要把維護民族團結作為生命線,全面貫徹黨的民族政策,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大力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不斷鞏固和發展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增強各族群眾對偉大祖國、中華民族、中華文化、中國共產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同。”值得強調的是,根據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原理,要切實促進各族人民對中華文化的深刻認同,必須在經濟層面上使他們切切實實地得到實惠。鑒于此,習近平在會見貢山獨龍族怒族自治縣干部群眾代表時強調,“全面實現小康,一個民族都不能少”,意在通過實現共同富裕來強化少數民族群眾的文化認同。
可見,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不僅借鑒吸收了傳統“華夷一體”族群觀的思想精華,而且還通過政黨宗旨、時勢考量等諸多因素的融入,在疆域觀、政治觀、文化觀三重重要維度上實現了揚棄和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