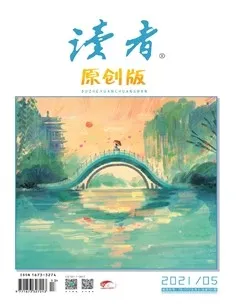粵海鐵路、蘇軾和火龍果田
樊北溟
一
剛出發就很不順利。
盡管只是4月,嶺南的陽光卻過早地炫耀起自己的威力。明晃晃的光不斷舔舐著過往行人,很快,人們的衣衫和額頭上都膩起了一層厚厚的汗。耳邊蟬鳴不斷,我感到一陣眩暈,于是趕緊回到候車大廳。
我一直上不了車,車站的大屏幕上一直顯示該趟列車“晚點待定”。急,但是沒用,只能等著。
晚點帶來的影響是持續性的,它意味著在接下來的旅程中,我們的火車需要不斷臨時停靠,為準點運行的火車讓出路來。而且這種“臨時”更像是“隨時”,我們的車會不止一次停靠在草木蔥蘢的荒野,前路漫漫,前途茫茫,心情煎熬……
“估計是趕不上了,這誰也不敢給你保證。”
列車員看了看手里的列車運行時間表,又看了看神色不定的我,滿懷同情地說。
走粵海鐵路,從廣東坐火車前往海南,一直是我的一個夢想。然而我沒能買到直達海口的車票,需要在茂名站中轉,轉車時間近一個小時。正常來說時間是充足的,可是火車已經晚點46分鐘了。我在心里反復默念著一本散文集的書名—《火車快開》。
火車快開,如果轉車順利,我乘坐的火車將在湛江的徐聞港乘船過海,再在海口港重新組裝,在新的陸地上全速前進;火車快開,由已知前往未知的旅途中,我們總在不定中求安定,在不安中祈求脆弱的平和與轉瞬即逝的安全感。
二
波折的旅途讓我想起了一個人,900多年前,他也是一路輾轉奔波,從惠州出發,沿西江而上,坐船走水路航行數百里到梧州,繼而南轉,從雷州半島渡海登島。
“責受瓊州別駕,昌化軍(今海南儋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
拿到一紙薄薄的貶謫詔令時,蘇軾在想什么?62歲了,即使前路不是天涯海角,自此一別,也終是海角天涯了!輕飄飄的一生,此時竟要由一葉孤舟送往荒涼之地。別問前方是什么,面臨多次被貶的人生,他早已無所謂出發和抵達了。
又一次不得不“在路上”的蘇軾,與我共享的,是同一輪朗日和同一方澄明的夜空。由徐聞奔赴海口,跨越千年,我們行走在相似的途中。900多年前的道路是怎樣的?沒有筆直的鐵軌延伸向無盡的遠方,沒有昏黃的路燈在站臺上留下斜斜的影子,甚至沒有路,沒有燈光,只有頭頂一輪皎潔的月亮。
這樣想著,我忽然覺得車廂里散亂的人影開始淡去,耳畔的短視頻也兀自緘默,車輪不再自鐵軌發出有節律的聲響,轆轆的車馬聲近了、更近了,奔波行旅的蘇軾遠了、更遠了……真奇妙啊,我在列車時刻表上分秒必爭,蘇軾在他的人生旅程里行行復行行,我和他的生命突然產生了神秘的連接,原來并不是萬水千山我獨往,盡管我不懂蘇軾的困厄,他卻告訴我,我其實并不孤獨。
行至梧州時,蘇軾聽聞被貶雷州半島的弟弟蘇轍正經過這里,便急忙寫下“他年誰作輿地志,海南萬里真吾鄉”的詩句,派人追上。他鄉遇故親,同為天涯淪落人的兄弟二人,相見時該是怎樣的驚喜與唏噓呀!人世滄桑,人海蒼茫,一切的經歷都融進眼前這無盡的蒼山和橫流的滄海之中了。人生哪兒能處處稱意?權且行一路、歌四方吧!
就這樣,兄弟倆在藤州見面后,相伴同行到雷州半島。然而短短的相聚過后,又是長久的分離,只是兄弟二人經此一別,竟再無緣見面,真的一揮手、一轉身,匆匆就是一生了。
“某垂老投荒,無復生還之望。春與長子邁訣,已處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當做棺,次便做墓。乃留手疏與諸子,死則葬于海外,生不契棺,死不扶柩,此亦東坡之家風也。”
在給友人的信中,蘇軾這樣寫道。抱著“后會無期”的心情,蘇軾前往海南。揮之不去的意冷心灰,如霧鎖海面,籠罩在字里行間。
火車晚點仍在繼續。我隨車廂繼續在暗夜中搖晃,感覺自己如燈、如豆,如海上行舟,如一支晃動的燭火。
未知的旅途、無望的心情,原來,千百年間,旅人的心緒,并無改變。
三
車廂人滿為患,過道里站滿了人,讓我的心情又增添了一分凝重。我打開手機地圖,不斷刷新與目的地間的距離,盤算著還有沒有可能趕上。其實即使錯過火車也沒什么要緊,我可以重新規劃旅程,可以轉簽、改乘輪渡,或者索性不去海南了,留在茂名就地游玩。
和蘇軾相比,我實在幸運太多了。
從徐聞渡到海南,兩地相距200公里,趁北風一日一夜則可到達。但這對當時的人來說,實在不是一趟容易的旅程。滄海不比江流,海面風大浪急,哪里是一葉扁舟能招架得了的?何況蘇軾已年過花甲、年老體弱,又怎能經受得了一路的奔波?但是他必須走,不能回頭。
所有人都以為這注定是一場人生的謝幕,卻萬萬沒想到,蘇軾不僅去了,而且在海南生活得很好。在儋州,他修“東坡井”、設私學,改善民生,大興教化,使當地荒蠻兇悍的環境有所改善。而他自己,也在全新的生活面貌中找到了精神寄托。在海南,蘇軾再一次完成了自我的療慰和精神的生長。
參橫斗轉欲三更,苦雨終風也解晴。
云散月明誰點綴?天容海色本澄清。
空余魯叟乘桴意,粗識軒轅奏樂聲。
九死南荒吾不恨,茲游奇絕冠平生。
蘇軾什么都沒說,他坦然接受自己的命運,奮力地生活著、書寫著;蘇軾什么都說了,穿越千載,在我心中仍然擲地有聲。
四
車窗外忽然快速閃過一連串金燦燦的燈光,把暗夜照得通亮。
“是火龍果田。”車上的當地人說,“種火龍果需要照燈,這樣可以改變生長周期,增加產量。”
望著窗外夢幻般一晃而過的火龍果田,我好像終于放下了心中的執念,突然就不著急了。人生也好,旅程也罷,本就無所謂出發和抵達的,珍重每一份經歷,珍惜每一段旅途,盡量感受和體驗,努力活得充實而豐富,自己能心領神會,其實就足夠了。
粵海鐵路、蘇軾、火龍果田,這三種原本不相干的事物匯集在一起,像三股麻線擰成的麻繩,又柔又韌,充滿力量。
“盧戈夫斯科依有真正的詩人品質,他從來不是遠遠地在一旁從事詩歌寫作。他自己用詩歌充實了周圍的世界以及其中所有的現象,無論它們是崇高的還是渺小的。”在《一把克里木的泥土》中,作者這樣寫道。這句評價其實也適合蘇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