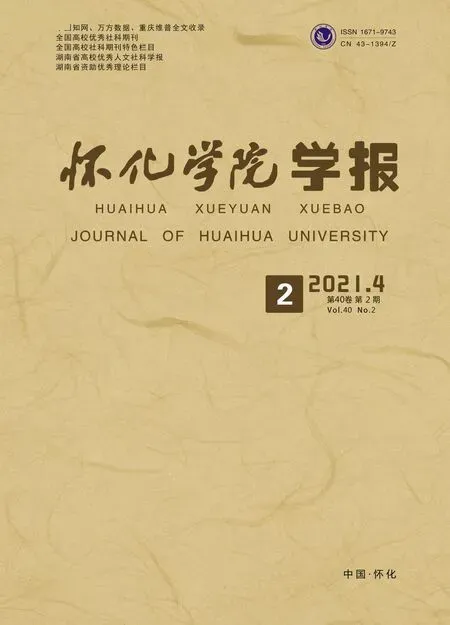西方經典瘟疫小說研究在中國
——從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談起
高 虹
(綿陽師范學院外國語學院,四川綿陽621000)
2017年,習近平總書記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的講話中對“人類命運共同體”與文學的關系進行了深刻論述,指出:人類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村”里,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文藝是世界語言,必須堅持不同文明兼容并蓄、共建共享。由此可見,一切文學作品終將回歸到一個問題:人類與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問題。文學即人學,其本質終究是探討人的命運和人生的意義,世界上絕大多數經典文學作品都涉及到人類的生存與毀滅、戰爭與和平、生態與未來等全人類普遍關注的生死攸關的共同話題。縱觀世界歷史,文學作為文明的重要載體之一,每有疫情發生,無論是民間傳說還是文人創作,都會記錄瘟疫的相關情況及嚴重后果,這便使瘟疫文學作品成為世人了解和認識瘟疫的頗為重要的知識手段。2020年,新冠病毒的全球性爆發,讓人們對瘟疫、疾病、災難、人與自然的關系、家國之愛、人類的命運與共等議題有了更為深刻的認識和反省;中國的眾多學者也對包含疾病的題材及其相關文化的西方瘟疫小說書寫關注有加,期待通過對西方經典瘟疫小說的研究對其歷史文化功能進行還原,從而提升人類對疫病的認知、使人們重拾對自然和生命的敬畏感,樹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觀念。
一、研究概況
從中國知網、北京大學圖書館及中國國家圖書館等較權威的文獻檢索信息統計結果來看:20世紀50年代至今,中國的翻譯學家和學者們一直致力于西方經典瘟疫小說的譯介、研究工作,出版的西方經典瘟疫小說譯著149部,各類期刊雜志發表相關譯文及論文443篇。具體數量分布如表1(以《瘟疫年紀事》《霍亂時期的愛情》等11部經典瘟疫小說為研究對象)。

表1 西方經典瘟疫小說譯著及相關論文情況
表1呈現的數據是按照每一種書目的名稱為主題搜索所得出的結果,是專門針對單部作品的研究。那么,對西方經典瘟疫小說系統性、全面性、綜合性的研究成果又如何呢?在中國知網、中國國家圖書館分別以“西方瘟疫文學”“西方瘟疫小說”“西方文學+疾病”為主題進行文獻檢索,結果分別為3篇、2篇和15篇;以“共生視域”“人類命運共同體”為主題進行文獻檢索,結果顯示2000—2020年間發表論文數量分別為160篇和7 000余篇,僅在2020年,關于“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的研究成果就高達1 000余篇,這足以說明國內學者對它的關注和重視。然而,再分別以“西方瘟疫小說與人類命運共同體”“西方瘟疫文學與人類命運共同體”“共生視域+西方瘟疫文學”“西方瘟疫文學+共同體”為主題進行論文檢索,結果均顯示為0。由此可見,盡管國內一直不乏對西方經典瘟疫小說的研究,但大都集中于對單部作品的研究,結合國家大政方針、實時動態的整體系統性的研究相對較少。譬如,盡管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研究成果呈持續上升趨勢,但絕大多數是從國內的經濟、政治、教育和企業發展等方面切入來探討人類命運共同體問題,鮮有對國外文學中的命運共同體思想的研究。筆者再以關鍵字作為檢索項,發現在使用頻率上以“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637次)一詞最多,“共生視域”(6次)次之,“西方瘟疫文學/小說”(0次)一詞則從未出現在關鍵字中,這就進一步說明了對西方瘟疫文學中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的研究是留白之區。
西方經典瘟疫小說的譯介工作是西方瘟疫文學研究中一項舉足輕重的任務,也能從側面反映出國內西方瘟疫文學的研究狀況和水平。西方經典瘟疫小說在中國的譯介工作起步于1958年,新文藝出版社出版了由方平、王科一翻譯的《十日談》,22年后,上海譯文出版社再次出版了該部小說,自80年代至今,方平、王科一翻譯的《十日談》歷經十次再版,足見其重要性和受歡迎程度。除了方、王二人,陳世丹、錢鴻嘉、肖天佑、王永年等的《十日談》譯本也在90年代至2020年間分別由長江文藝出版社、譯林出版社、中央編譯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等反復再版。《鼠疫》是另一部在中國頗受歡迎的瘟疫小說,80年代至今,國內《鼠疫》的主要譯者有劉方、徐和瑾、吳立靜、劉合文、郭宏安、顧方濟、徐志仁,僅2020年,該小說的譯著就高達7部,足見國內學者對當下疫情與文學之關聯的敏感度和重視度。相比這兩部著作的大量譯介,其余幾部瘟疫小說的譯著則稍顯遜色:《霍亂時期的愛情》的4部譯著均在2000年前面世;《瘟疫與人》《瘟疫年紀事》《傳染病屋》的譯本較少,其頭版分別于1998年、2005年、2007年出版,且前兩部著作的再版幾乎都出現于2010—2020年間;《屋頂上的輕騎兵》《瘟疫與霍亂》《失明癥漫記》《地球上的最后一座小鎮》譯著均只有一部,分別出版于2013年、2014年、2018年和2019年。綜上所述,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可以說我國在西方經典瘟疫小說的譯介方面,已經取得了較豐碩的成果。這些作品的大量譯介,無疑給國內的研究者提供了寶貴的資料,為他們更深、更全地研究西方瘟疫文學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我國對西方經典瘟疫小說作品的研究始于20世紀80年代,在21世紀初升溫,近十年來日趨成熟和完善。刊登有關西方經典瘟疫小說研究論文的主要刊物包括《外國語文》《外國語文研究》《外國文學》《國外文學》《電影文學》《外國文學評論》《世界文學》《當代外國文學》《外國文學評論》《世界文學評論》《外國文學研究》及各類學報。這些刊物登載與西方經典瘟疫小說有關的論文情況如表2所示:

表2 幾大主要刊物登載的西方經典瘟疫小說相關論文情況
從表2可以看出,《當代外國文學》刊載的西方經典瘟疫小說研究論文最多,包括對《傳染病屋》《地球上的最后一座小鎮》及《鼠疫》的研究,僅對《鼠疫》的研究就有4篇;其余刊物和各類學報等則零散刊載了其他一些主要的西方經典瘟疫小說論文,但數量均偏少,且前后相隔時間較長;從80年代至今,縱然對西方經典瘟疫小說的研究數量不少,但質量卻差強人意,相比于443篇的論文研究總量,能在國內幾大權威刊物上發表的相關論文卻不足30篇,足見國內學者在相關研究領域尚有努力的方向和進步的空間。
二、研究特點
對西方經典瘟疫小說的譯介工作始于20世紀50年代,而對其作品的研究源于80年代。眾多小說譯本的出現打開了國人了解、研究西方瘟疫文學的大門;對其作品的研究更有益于國人借古通今,以史為鑒,在激勵讀者思考各種疫病與人類共生共存關系的同時,給讀者帶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啟示。總體看來,從80年代至今,中國的西方經典瘟疫小說研究呈如下特點:
(一)相比于國內學者大都熱衷于僅對西方主流大國如英美等國的文學研究,對西方經典瘟疫小說的研究將關注點置于世界主流文學圈之外。《鼠疫》《霍亂時期的愛情》《十日談》分別是加繆(法國)、加西亞·馬爾克斯(哥倫比亞)、喬萬尼·薄伽丘(意大利)的作品,由前文對譯本及論文統計數據可知,此三部作品的研究成果在所有的西方經典瘟疫小說相關研究成果中,位居前三甲,大部分研究成果從2000年起集中出現,且在近十年內達到頂峰,這既說明三部作品確是曠世經典之作,又說明國內學者對西方經典文學作品研究的敏感性和包容度在與日俱增。
(二)國內對西方經典瘟疫小說的譯介和研究工作在國內外發生重大疫情和災難之際較為突出。2003年的“非典”、2008年的5.12地震、2016年的黃熱病、2020年的新冠,這些重大的“災難年”都見證了為數不少的西方經典瘟疫小說研究成果。具體情況如表3:

表3 西方經典瘟疫小說在重大“災難年”的研究成果情況
由表3可知,每遇重大疫情或災難,國內總有針對西方瘟疫小說的研究成果出現,且對某些經典瘟疫小說的研究成果較為豐碩。然而,國內學者在重大“災難年”對西方經典瘟疫小說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對《鼠疫》《十日談》的研究,無論是譯本還是論文,二者的研究成果都位居一、二;《瘟疫與人》《瘟疫時期的愛情》雖有譯本,但數量僅為一,且論文數量較少;《屋頂上的輕騎兵》《瘟疫與霍亂》《地球上的最后一座小鎮》《傳染病屋》《末世一人》不僅譯本為零,對應的論文數量更是寥寥無幾。可見,在歷經重大災難或疫情之際,對西方經典瘟疫小說的譯介工作還可加強、增多;特別是針對目前譯本較少或尚無譯本的瘟疫小說尚有豐富其論文研究成果的空間和可能。
(三)研究視角和范圍不斷拓寬。研究者采用各種批評理論對西方經典瘟疫小說進行分析研究,而不僅限于對作品主題、人物、寫作特色等的分析。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來,伴隨著后現代主義批評理論的迅速發展和廣泛傳播,國內的西方瘟疫文學研究者也在不斷拓寬研究視野,借助女性主義、后現代主義、魔幻現實主義、后殖民主義、存在主義、原型批評、精神分析法等多種理論范式對西方瘟疫小說進行多角度、深層次的理解和解讀。賈艷鋒在《〈十日談〉的女性形象分析》一文中,通過分析《十日談》中幾種不同特點的女性形象,分析其成因及意義,以彰顯薄伽丘對宗教禁欲主義的批判以及對女性的深切同情和高度贊揚;杜巧玲在《后現代主義視域下〈傳染病屋〉的敘述特征》一文中指出,《傳染病屋》中非線性的敘述、黑色幽默及結局的開放性等典型的后現代主義特征對小說主題的詮釋發揮了關鍵作用;倪楠在《〈霍亂時期的愛情〉中的烏爾比諾——以弗洛伊德的“三重人格結構理論為視角”》一文中以弗洛伊德的人格結構理論闡釋了烏爾比諾醫生人格系統中本我、自我、超我的沖突與協調,進而揭示其自身理性與非理性的矛盾統一。
1.研究者嘗試突破傳統的研究方法和手段,采用跨學科的研究方法,通過超越傳統分門別類的方式,實現對西方經典瘟疫小說的整合性研究。自2000年至今,國內學者嘗試從翻譯學、敘事學、醫學、美學、倫理學、語言學、詞匯學、哲學、社會學、文化符號學等多學科角度研究西方經典瘟疫小說。有的將文學與一門學科融合起來研究;有的將文學與幾門學科結合起來進行研究,透過跨學科、跨文化視域來豐富和完善國內對西方經典瘟疫小說的研究,以期研究成果更豐富、客觀、全面和有價值。王亭亭的《〈地球上的最后一座小鎮〉中的傳染病倫理學研究》一文揭示了當代傳染病倫理學所面臨的倫理困境。”[1]王洪智在《康德道德哲學視域下〈失明癥漫記〉的善惡譜系》一文指出:“人性和道德將在歷史的發展中不斷從‘自然法則’走向‘目的國’,從而實現至善。”[2]蔣天平在《社會建構論下〈霍亂時期的愛情〉對殖民醫學的逆寫》一文中質疑了殖民醫學的進步性、西方文明的優越性,并表明了本土醫學的有效性和文化的永恒性[3]。王尤迪在《〈霍亂時期的愛情〉的美學解讀》一文中從審美著眼的對象、審美表現的內容和審美表現的方法三個方面探討了小說的美學特征。陸洵在《法國疫病敘事:以〈屋頂上的輕騎兵〉中霍亂意象為例》一文中指出:“《屋頂上的輕騎兵》構建了‘霍亂’這一微生物的符義形象,凸顯了霍亂在表現人性、展現人與自然關系方面的文學價值。”[4]
2.從比較文學的角度對西方經典瘟疫小說進行解讀是國內西方瘟疫文學研究的另一重要特征。幾乎每一部西方經典瘟疫小說的研究成果都包含從比較文學角度進行的研究:有的文章側重于東西方不同文學、文化的對比研究;有的側重于對東西方兩位不同作家的某兩部瘟疫作品進行比較;有的側重將西方某一瘟疫小說與另一西方小說并置比較;另有研究者青睞將西方某一作家的某兩部瘟疫小說進行比較研究。趙丹丹、高超的《薩拉馬戈作品中的表現主義特色——以〈失明癥漫記〉和〈復明癥漫記〉為例》一文探析了薩拉馬戈作品中的表現主義特色,進而了解薩拉馬戈對人類精神世界的所思所見[5]。石晶的《對〈霍亂時期的愛情〉和〈包法利夫人〉中女性形象的對比分析》一文對新世紀女性面臨的困境提出了思考和建議。盧家興的《加繆與史鐵生文學創作中的生命哲學比較——以〈鼠疫〉和〈務虛筆記〉為例》一文揭示了二人的生命哲學的成因、契合點和差異之處。上述研究成果有一共性:闡明了西方經典瘟疫作品中所包含的人文主義精神,無論是對人類精神世界的反思,還是對新世紀女性面臨的困境的思考,在遭受重大災難之際,作者更加關注人的心理健康、精神狀態和生存困境,而這正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精髓所在:人類共處一個星球,同呼吸,共命運,越是遭受重創之時,越是需要求同存異,共同應對災難,實現共生共存共發展。
3.以個體研究為主,整體研究為輔。縱觀歷年來國內西方經典瘟疫小說的研究成果,絕大多數成果都是圍繞單部瘟疫小說展開的,其人物、主題、寫作技巧、藝術特色等,或進行縱向剖析,或開展橫向對比,研究者們一直在不斷地為西方經典瘟疫小說研究注入新鮮血液。除開對瘟疫小說的個體研究,整體研究的嘗試也于90年代拉開帷幕:吳錫民分別于1993年和1996年在廣西師院學報發表題名為《西方文學與疾病》和《西方文學與疾病再思索》的論文。前者“從西方文學史中文學與疾病的事實聯系出發,著重從比較文學角度和文學主體生命機理的視野,探究二者聯系之奧秘,從而悟出它們的實踐意義:文學與醫學加強合作,在經濟大潮中大有用武之地”[6]。后者聯系西方文學實際,得出公允結論:“病理因素本身不具什么創造性,但其給作家所造成的病痛則有益于作家深化對生活的洞察,對生命的體驗。”[7]吳錫民在90年代初期對西方經典瘟疫小說所做的整體性研究嘗試為2000年后研究者們對西方瘟疫小說進行更深更廣的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礎。王予霞在《西方文學中的疾病與恐懼》一文中指出,“人類面對形形色色的疾病所表現出的恐懼卻具有濃厚的社會文化屬性。在同疾病斗爭的過程中,人類不斷地在‘疾病’中注入各種文化內涵,使其呈現出隱喻特征,從而使得對頑疾的恐懼遠遠超出疾病本身,甚至成為一種集體無意識”[8]。范蕊在《西方小說中的瘟疫題材》一文中,以《十日談》《鼠疫》等西方經典瘟疫小說為研究對象,得出結論:“瘟疫與人類關系密切,不僅影響社會進程還影響人們的文化和精神狀態。”[9]僅在2020年新冠之年一年出版的相關論文就高達9篇,足見國內學者們對文學于現世重要意義的敏感度和重視度。王曉路在《疾病文化與文學表征——以歐洲中世紀鼠疫為例》一文中,提出“作為揭示人的歷史境遇、張揚生命文化的文學書寫對于疾病文化的表征,可以使人們重拾對自然的敬畏感并間接地奠定社會文化發展所需的觀念基礎”[10]。管新福在《避瘟、祛魅與隔離療法——西方近現代文學中的瘟疫書寫》一文中指出“文藝復興到19世紀的西方近現代文學,開始理性思考瘟疫沖擊下人與神、人與人、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隱喻社會失范和人性失格、悲憫人類付出的沉重代價、透顯人類對自身和瘟疫認識的不斷深化;同時告誡人類要正視人性的弱點、善待生命,實現人和自然的和諧共處”[11]。
三、結語
文學即人學,其本質終究是探討人的命運和人生的意義,“對于文學書寫本身所包含的疾病題材以及所涉及的相關文化,人們有必要加以關注,以對其歷史文化功能加以還原并提升認知”[10]。三十余年來,國內的西方經典瘟疫小說研究雖已取得一定的成績,但能結合當下時事熱點、國家大政方針的相關研究十分稀少;作品中歷史性與現代性的結合、瘟疫歷史事件對現代社會的啟示等研究成果更是屈指可數;西方瘟疫小說中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的研究也尚有深入的可能和空間。在全球化趨勢愈演愈烈的當下,任何一種疫病的爆發、流行最終都會將全人類拉進一個共同的命運漩渦之中,正如研究中世紀文化遺產的學者庫克所指出的,“鼠疫一直就在我們的周圍”[13]1。人類絕不能對其置之不理,無動于衷,那么,我們在今天,依然,甚至可以說應該借助文學的力量,通過研究古今中外人類歷史上的經典瘟疫文學作品來不斷提升對疫病的認知,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