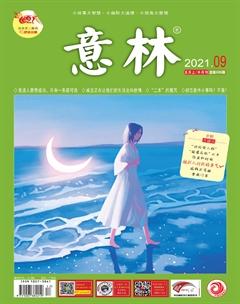“被遺忘權”之爭:大數據時代的數字化記憶與隱私邊界
所謂“被遺忘權”,即數據主體有權要求數據控制者永久刪除有關數據主體的個人數據,有權被互聯網遺忘,除非數據的保留有合法的理由。在大數據時代,數字化、廉價的存儲器、易于提取、全球性覆蓋作為數字化記憶發展的四大驅動力,改變了記憶的經濟學,使得海量的數字化記憶不僅唾手可得,甚至比選擇性刪除所耗費的成本更低。記憶和遺忘的平衡反轉,遺忘變得困難,而記憶卻成了常態。“被遺忘權”的出現,意在改變數據主體難以“被遺忘”的格局,賦予數據主體對信息進行自決控制的權利。
首先,“被遺忘權”不是消極地預御自己的隱私不受侵犯,而是主體能動地控制個人信息,并界定個人隱私的邊界,進一步說,是主體爭取主動建構個人數字化記憶與遺忘的權利,與純粹的“隱私權”不同,“被遺忘權”更是一項主動性的權利,其權利主體可自主決定是否行使該項權利對網絡上已經被公開的有關個人信息進行刪除。是數據主體對自己的個人信息所享有的排除他人非法利用的權利。
其次,在數據快速流轉且難以被遺忘的大數據時代,“被遺忘權”對調和人類記憶與遺忘的平衡具有重要的意義。如果在大數據時代不能“被遺忘”,那意味著人們容易被囚禁在數字化記憶的監獄之中,不論是個人的遺忘還是社會的遺忘,在某種程度上都是一種個人及社會修復和更新的機制,讓我們能夠從過去經驗中吸取教訓,面對現實,想象未來,而不僅僅被過去的記憶所束縛。
最后,大數據技術加速了人的主體身份的“被數據化”,人成為數據的表征,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以數據的形式被記憶。大數據所建構的主體身份會導致一種危險,即“我是”與“我喜歡”變成了“你是”與“你將會喜歡”;大數據的力量可以利用信息去推動、勸服、影響甚至限制我們的認同。也就是說,不是主體想把自身塑造成什么樣的人,而是客觀的數據來顯示主體是什么樣的人,技術過程和結果反而成為支配人、壓抑人的力量。進一步說,數字化記憶與認同背后的核心問題在于權利不由數據主體掌控,而是數據控制者選擇和建構關于我們的數字化記憶,并塑造我們的認同。適度的、合理的遺忘,是對這種數字化記憶霸權的抵抗。
(本文入選2018年高考全國卷II,文章有刪減)
袁夢倩:南京大學藝術學院副研究員,香港中文大學博士。曾榮膺江蘇省“雙創博士”,香港政府博士獎學金等,主要研究方向:媒介文化研究、文藝批評、口述歷史與社會記憶。
意林:您認為閱讀對個人成長有哪些影響?
袁夢倩:閱讀滋養我們的生命,開拓我們的思想視野。閱讀使我們能夠超越現實生命,在歷史長河中穿梭。閱讀建構我們的精神家園,讓我們的心靈在此靜謐棲居,思想在此自由徜徉。
意林:對您而言,寫作的意義在于什么?
袁夢倩:就個人意義而言,寫作可以幫助我們梳理思想和情感,理解和反思自我生命經驗,并重新賦予生活世界以意義,塑造我們的身份認同與人際關系。就社會意義而言,我們通過寫作理解和反思社會文化,觀照和探索社會文化的復雜性。寫作作為介入社會的方式,在微觀層面參與建構社會文化的敘事與話語行動。
意林:您認為好文章有什么特征?
袁夢倩:于我而言,好文章應是作者生命經驗、思想和情感的凝結與積淀,它至少有三個基本特征:一,好文章是真誠的,修辭必立其誠,寫出真情實感。二,好文章是清晰的。清晰并不意味著簡單,反而更能體現作者思維和表達的邏輯性、反思性,能把復雜的故事和思想講得深入淺出。三,好文章是令人回味的,令讀者讀完一遍仍意猶未盡,還有一些意味深長之處發人深思、激蕩心靈,使其一讀再讀、常讀常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