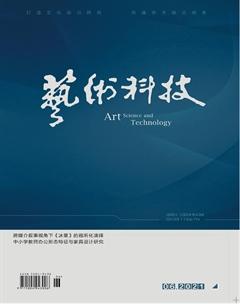交互設計在公共藝術設計中的應用
馮瀾 薛沖

摘要:交互設計在公共藝術中的應用,以大型互動裝置最為常見。公共藝術意味著公共領域,面向的是大眾群體。公共藝術可以展現一個城市的獨特風貌,體現一個城市的歷史文化底蘊,使大眾通過真實存在的作品感受城市風采。交互設計注重公眾的參與度,強調參與者與設計作品之間的互動,更加關注公眾體驗后收獲的感受。公共藝術與交互設計結合,能夠更加具體地展現兩者的優勢,從而使大眾對城市產生深刻的印象。
關鍵詞:交互設計;公共藝術;鋼琴樓梯;應用
中圖分類號:J0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9436(2021)06-0-02
1 交互的設計概念、內涵及其在公共藝術設計中的應用
交互設計中“交互”一詞的英文為“interaction”,譯為“相互影響、交互作用”[1],顧名思義,交互設計可以理解為在設計中,讓設計內容與體驗對象產生互動,其包含的內容十分廣泛,大致為讓人與人、人與物、人與環境之間相互產生聯系[2]。交互設計的內涵在于它更加貼近現實世界,使參與者在快節奏的生活中感受到片刻的放松與新鮮感。與一般的公共藝術作品不同,交互設計作品可以與大眾產生互動,從公眾的反應中直接或間接地獲得反饋[3]。公共藝術大致可以理解為“面向公眾的藝術”,它所映射的是公眾的參與情況。當公眾對藝術品產生反應,公共藝術作品才算完成[4]。不同的藝術品,其表現方式與形態不同,給人帶來的情感體驗與審美感受也就有所不同[5],從而在精神層面具有雅俗文化之分[6]。交互設計在公共藝術中的呈現大致可以分為2種:
第一,接觸式體驗。接觸式體驗就是面向欣賞交互式公共藝術作品的參觀者,讓他們通過觸摸或其他親身體驗的方式獲得深刻的感受[7]。“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實踐可以使參與者更加具體地了解一項事物,比起走馬觀花式地欣賞一件公共藝術品,近距離的接觸可以讓參觀者直接感受到作品的紋理、質感,以及一些肉眼不能收集到的內容,從而留下不一樣的記憶。
第二,沉浸式體驗。沉浸式體驗的互動方式使得人們可以調動視覺、聽覺[9]等多種感官去欣賞一件作品[8]。視覺體驗時,色彩對視覺起到了重要作用,色彩運用的手法不同,所設計出的作品便會產生不同的效果。對于五歲之前的兒童來說,他們對那些對比強烈的色彩十分敏感[10],交互裝置所形成的色彩會讓孩子產生一種身處其中的真實體驗感,這種人景交融的方式有助于激發孩子的探索欲。VR給人帶來的沉浸式體驗會使得體驗者通過集中感受形成心理沉浸感,從而產生獨特的感受[11]。
2 鋼琴樓梯的背景及設計分析
2009年,有“最長的地下藝術長廊”之稱的斯德哥爾摩地鐵站[12]將一個地鐵站的樓梯改建成了著名的公共藝術品“鋼琴樓梯”(如圖所示)。在科技發達的時代,比起樓梯,人們更愿意選擇直達電梯作為代步,就此現象,大眾汽車公司曾經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我們可以用一種有趣的方式使更多人選擇樓梯嗎?”面對這個問題,地鐵站通過將樓梯改造為鋼琴鍵的方式給出回答,并且通過考察,發現選擇鋼琴樓梯的人數占了總乘客人數的66%。
2.1 普通樓梯的短處
鋼琴樓梯之所以能夠出現,是因為普通樓梯已經不能夠滿足人們的需求,所以需要創新思維打破這個局面。與普通樓梯相比,電梯較為方便快捷,并且能夠減少乘客的運動量,因此選擇樓梯的人數一般較少。在這樣的情況下,“如何讓更多人選擇樓梯?”便成為一個關鍵的問題。
2.2 鋼琴樓梯設計考慮的因素
2.2.1 趣味性
地鐵站最初的設計理念就是讓選擇樓梯行走的群眾感受到趣味性。鋼琴是音樂領域比較常見的一種樂器,樓梯是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通行場所,這兩種看似普通且毫無關聯的事物相結合,會讓人產生一種新奇感。音樂本身具有令人身心放松的功效,當人們踏上黑白的“鋼琴鍵”,聽著優美的旋律,枯燥乏味的出行就增添了一絲趣味。鋼琴鍵雖是黑白的,但它具有色彩的動力[13]。當參與者踏上不同臺階,旋律不同的音樂便會隨著“琴鍵”上下浮動,像隨著鋼琴演奏出來一樣。該作品的趣味性正在于設計師將兩件平凡的事物結合成一件,讓大眾感受到與藝術作品互動的樂趣。
2.2.2 美觀性
相較于其他公共空間,地鐵站是一個人流量非常大的相對封閉的空間。如果使用過于復雜或者過于單調的色彩,不僅會影響人們的情緒[14]而且會使人們感到視覺疲勞[15],因此,簡約的設計風格或許更加適合這種環境。不同的色彩會給人帶來不同的心理感受[16],在地鐵站,來來往往的行人在地鐵中短暫地停留,屬于中性色的黑白雙色于琴鍵而言可以理解為一種“極簡主義”[17],從視覺上有簡潔大方之感,不會引起人們的審美疲勞。簡約不僅是一種風格,更是一種生活態度[18]。黑白相間的色彩搭配,使得節奏與韻律更加清楚地體現美感[19],在地鐵站中,也不會有浮夸的感覺。
2.2.3 創新性
對于選擇地鐵出行的人們來說,進站、轉線、出站、乘坐電梯已經成為生活中習以為常的部分。在網絡快速發展的時代,世界各地的新鮮事物緊密聯系,開闊了人們的視野,使人們擁有著更為強烈的審美情趣[20],而不僅限于外表的欣賞。老舊的事物缺乏美觀性與功能性[21],會使大眾缺乏新鮮感。
3 交互設計在當代公共藝術設計中的應用及價值判斷
服務于大眾的公共藝術作品,出現在群眾視野中,會潛移默化地對觀賞者產生一定的影響。對于身處不同領域的群眾來說,比起通過一件固定的公共藝術品來感受它所包含的內在情感,通過與藝術品進行互動更加能夠引起他們的共鳴,美術史學家沃爾夫林[22]從理性的角度解讀大量藝術作品,并且注重藝術作品文化內涵的體現,而文化內涵與情感二者之間為包含關系,由此可見文化內涵的重要性。北京地鐵6號線與地鐵8號線的換乘站南鑼鼓巷站的公共藝術作品“北京·記憶”,其通過一個個小小的琉璃塊,承載城市時代更迭中屬于自己的回憶[23]。琉璃塊中有著各式各樣、具有代表意義的小物件,從簡單的各種票據到給人帶來童年回憶的鐵皮小青蛙,無不展現著曾經美好的生活碎片。不僅如此,創作團隊通過讓行人掃描二維碼,了解每件物品背后所承載的不同故事,這種情感化敘事和二維碼互動的方式,可以讓行人從眾多信息中篩選自己感興趣的部分,從故事中感受到溫暖。在當今生活節奏快速的時代,社會經濟發展前景雖好,但人們卻逐漸忘記了最初的簡單的快樂,人們為所追求的生活奔波,沒有選擇停下腳步注意周邊生活環境的變化,而這些小物件使觀眾與藝術作品之間產生了良好的互動,慢慢將人們的思緒拉回曾經美好的時光。這種設計比起地鐵站中的其他現代科技展現、浮雕、廣告牌等,多了一絲生活氣息和人情味,容易引起人們的共鳴,增強了與群眾的互動性[24],讓群眾了解到每個看似簡單的物品背后所隱藏的意義。地鐵站能夠展現城市文化特點,具體體現一個地區的文化特色[25]。南鑼鼓巷站中那些頭戴馬聚源帽子、梳著辮子的大人,調皮的兒童等都是“老北京”所具有的典型形象,通過地鐵中的文化展示,人們能更加了具有人情味的北京。
加拿大蒙特利爾的裝置作品發光蹺蹺板,是設計師改良的作品,發光蹺蹺板通過將閃耀的光與柔和的音樂結合,吸引了人們的注意,使人們漸漸將自己的思緒帶入無盡的回憶。蹺蹺板雖然承載著人們兒時的回憶,但普通的蹺蹺板卻在繁華的都市逐漸被人們所淡忘,而發光蹺蹺板無疑成為大眾在閑暇時刻放松玩耍的絕佳選擇。
4 結語
通過將交互設計與公共藝術結合,能產生滿足大眾情感需求的作品。隨著人們生活質量的不斷提升,藝術涉及的領域會逐漸拓展,而藝術家通過兩種形式的結合以傳遞所要表現的內容,更容易引起大眾的共鳴。鋼琴樓梯不僅突出了格德斯爾摩地鐵的文化特色,而且為公眾帶來了樂趣;南鑼鼓巷站的公共藝術作品不僅體現了北京的文化內涵,而且喚醒了大眾的美好回憶。以上優秀案例給我們帶來了一定啟示:要根據當地的環境與實際存在的問題展開分析,從而達到一個滿意的效果。公共藝術的最終目的是更好地符合大眾審美,正因如此,越來越多的藝術家通過交互設計的方式讓大眾更好地感受到藝術所蘊含的魅力,感受各種藝術形式所展現出來的城市特色和文化內涵。
參考文獻:
[1] 張牧.新媒體交互設計在公共藝術中的應用研究[J].美術教育研究,2017(07):80-81.
[2] 覃京燕.大數據時代的大交互設計[J].包裝工程,2015,36(08):1-5,161.
[3] 黃亦菲.淺析數字媒體交互技術在公共藝術領域的應用[J].藝術科技,2020,33(23):172-173.
[4] 石鑫,李雪艷.基于Processing平臺的聲音可視化運用[J].藝海,2020(10):102-103.
[5] 徐雪媚,李雪艷.公共室內空間中的纖維裝置[J].大眾文藝,2019(02):135-136.
[6] 吳歆悅,李雪艷.藝術中的雅俗文化之辨析[J].美術教育研究,2020(20):52-53,57.
[7] 譚凡,史鐘穎.交互藝術在公共藝術設計中的應用[J].設計,2017(07):62-63.
[8] 吳成煒,曹磊.沉浸式設計理念及應用實踐探析[J].美術教育研究,2020(08):65-66.
[9] 高睿彤,王夕倩.基于色彩景觀的兒童戶外活動空間設計研究——以東莞萬科中天城市花園兒童“活力谷”景觀設計為例[J].美術教育研究,2020(13):94-95.
[10] 黃婕,張雨,黃瀅.兒童交互電子書視覺系統設計有效性研究——以2~5歲兒童電子書設計為例[J].大眾文藝,2019(23):120-121.
[11] 張潤楠,湯箬梅. AR/VR數字化技術下對環境空間設計的影響[J].美術教育研究,2020(12):69-70.
[12] 艾昕.斯德哥爾摩地鐵:最長的地下藝術長廊[J].中華民居,2010(10):52-57.
[13] 胡雪歌,孔德金,劉雅迪.從視知覺角度分析公共藝術帶來的動態體驗[J].美術教育研究,2019(1):51-53.
[14] 郭笑妤,黃瀅.基于色彩分析的兒童游樂空間視覺傳達設計[J].藝術科技,2020,33(13):88-91.
[15] 鄭欣宜.論地鐵公共藝術的審美性——以南京地鐵三號線壁畫為例[J].大眾文藝,2019(18):57-58.
[16] 吳馨宇,田曉冬,薩興聯.公共景觀空間雕塑情感化敘事研究[J].美術教育研究,2020(06):71-72.
[17] 管佩弦,李雪艷.論北歐家居設計和日式家居設計中的極簡主義[J].家具與室內裝飾,2018(11):28-30.
[18] 尤心培,李雪艷.梁志天設計符號的批評與評價[J].美術教育研究,2020(23):52-53.
[19] 沈慧芳,徐舒珩,曹磊.中國傳統圖案在室內設計中的運用研究[J].家具與室內裝飾,2020(11):105-106.
[20] 陸遜彪,湛磊.淺析蠟染工藝在現代藝術創作中的局限性[J].大眾文藝,2019(22):132-133.
[21] 趙哲,黃維彥.基于地域文化的書屋空間環境設計——南京老城南舊屋改造設計[J].美術教育研究,2020(13):101-102,116.
[22] 宋童恬,葉潔楠.淺析沃爾夫林的形式分析理論[J].美術教育研究,2020(06):46-47.
[23] 朱瑤,曹磊.歷史文化街區的傳承與城市形象傳播——以“老字號”集聚街區老門東為例[J].大眾文藝,2018(23):238-239.
[24] 俞沁,施愛芹.智能電視界面交互設計的易用性和用戶體驗研究[J].大眾文藝,2018(21):127-128.
[25] 甘思文,湛磊.對南京地鐵文化的現狀分析——以地鐵一號線設計為例[J].大眾文藝,2019(23):157-158.
作者簡介:馮瀾(2001—),女,內蒙古包頭人,本科在讀,研究方向:公共藝術。
薛沖(1967—),男,江蘇南京人,碩士,系本文通訊作者,研究方向:高等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