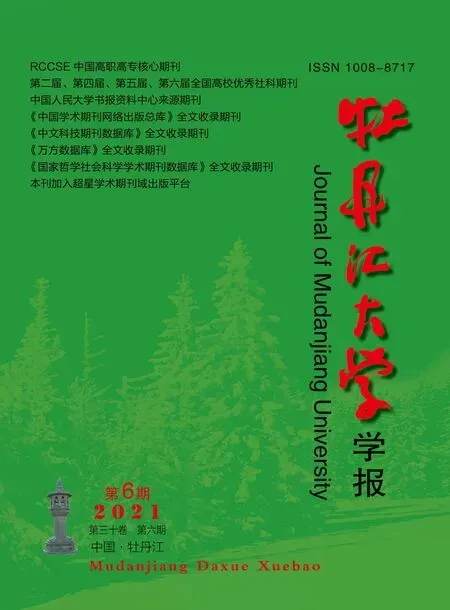玩具、武器與小鳥
——日本童謠詩的發展與特點
潮洛蒙 石 芳
(天津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天津 300222)
童謠,是以兒童為對象創作的、在兒童中間流行的歌謠或詩歌,是少年兒童認識世界、感悟生命、豐富內心的一種途徑和方式。日本的童謠在其發展過程中形成了個性鮮明的三種類型,即“童歌”“唱歌”以及“創作童謠”,三者在時間上前后承接,且各自特征鮮明。
關于日本童謠詩的研究,日本研究者更多是從童謠的內容、音樂性、作家作品解讀、教育性等視角進行研究,研究較充分且多元化。例如,高橋美帆(2003)通過將英國女詩人羅塞蒂與日本童謠詩人金子美鈴的比較研究,探究了西歐詩人及其作品對日本大正創作童謠發展的影響。若井勛夫(2008)對于童謠詩內容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做出新的闡釋,為童謠愛好者和研究者提供了新的視角。吉本篤子(2015)在《明治、大正時期的藝術教育對于人的培養——圍繞唱歌、童謠教育——》中認為,大正時期的童謠對于當時社會的兒童觀、教育觀的形成有重要的影響。對于個別的童謠詩人的研究同樣豐富,比如山內良子(2003)的《窗滿雄童謠的表達特點——以童謠集<大象>為中心——》、金井明子(2006)的《從視點的多樣性看金子美鈴的詩歌表達》、笹本正樹(2018)的《北原白秋童謠分析》等。2010年在中國湖南舉辦的第10屆亞洲兒童文學大會上和田典子發表了《作為綜合藝術的童謠集》一文,認為日本童謠集作為文字、音樂、繪畫和裝幀等的綜合藝術品,是日本孩子們以及日本社會的文化財產。總之,可以看出日本研究者對于童謠的研究時間之久,內容之豐富,重視之高度,但尚缺國外研究者視角下的不同類型童謠的對比分析和面向中國的系統介紹。
相對而言,國內對日本童謠的研究目前還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更多的是對個別的童謠詩人及其作品的研究。其中,隨著近年來金子美鈴的童謠譯本不斷推出,對于金子美鈴以及她的作品的研究成為國內對日本童謠研究領域里的熱門。比如,吳昊(2013)的《金子美鈴的詩情》、劉燦燦(2016)的《論金子美鈴詩歌的藝術成就》、秦秘蜜(2017)的《童謠詩人金子美鈴的詩法研究》等。另外,宣妍(2009)的《北原白秋的創作童謠研究》以及郭爾雅(2019)《童謠童畫童心——<竹久夢二童謠集>對中國兒童文學的借鑒意義》等,也為國內日本童謠研究增添了新的內容。除此之外,還有圍繞象征著大正時期創作童謠誕生的兒童雜志《赤鳥》的研究,如王亨良(2012)的《藝術真價值》的追求與落敗——以近代日本兒童文學雜志《赤鳥》為例”、牟鑫(2013)的《從大正時代的童謠來看日本童謠文化》等。國內的以上研究,皆是對于日本大正時期創作童謠的相關研究,而缺少對與其在教育目的、創作方法、內容等方面截然不同的傳統童歌以及明治唱歌的研究或介紹。
基于以上國內外研究現狀,本文試圖從日本童謠詩(不含曲調的文字內容部分)的產生、內容和目的等入手,對日本童謠詩發展過程中的特點進行對比和分析,以期加深對日本童謠的進一步認識和了解。
一、自然傳承的傳統童歌——隱藏在孩童游戲中的瑰寶
孩子的天性是擅長模仿和想象,日本早期童謠——童歌的形成便是兒童模仿成人歌謠,或在玩耍和游戲中發揮想象力而自我創作的結果。因此,日本早期口口相傳的童歌,大多是在孩子玩耍及日常生活中自然產生,也常稱為“傳承童謠”“自然童謠”等,大部分是作者、創作地點、傳達意圖等都不明確的童謠。同時在代代傳唱的過程中,由于地區和時代的變化,童歌的歌詞會發生一些改變,并且受方言的影響較大也是童歌的特點之一。童歌的內容以游戲、傳授知識、季節風物、動植物故事、民俗事典等為主,其吟誦的形式幾乎都是伴隨著游戲進行,比如穿插在拍手游戲、捉迷藏、丟沙包等兒童游戲里完成。例如:

這首童歌是孩童玩游戲時候唱的歌,一個孩子坐在中間閉上眼,其他孩子圍成圈,一邊唱歌一邊繞著圈走,歌曲結束時中間的孩子猜測背后的人是誰。通過最后一行“是誰呀”可以得知這是一個做類似于“猜人”的小團體游戲時候的輔助“玩具”。專業作家的作品往往是個人產物,而童歌則更像是一種群眾集體的創作,據柳田國男的《民間傳承論與鄉土生活研究法》中的觀點,童歌多是孩子們模仿成人進行宗教儀式而產生。[2]雖然后世對于這首童歌有不同的解析和闡述甚至是猜測,比如德川埋藏金子①、陰謀②等等,但正確的解讀并沒有確定下來。另外,童歌的版本一般有多個,這首童歌最早的文獻記錄是《竹堂隨筆》,由修行僧人行智編著收錄在他的童話集里,用詞和長短音節奏等都與后世版本有所不同。[1]隨著時代的發展以及在不同地區的傳唱,這首童歌被收錄于不同書籍中的版本就已達到四種——《返橋背御攝》(1813年)、《月花此友鳥》(1823年)、《幼稚游昔雛形》(1844年)以及《俚謠集拾遺》(1915年)。[3]同時,又因為絕大多數童歌是孩子們玩耍時候的助興詩歌,注重游戲性而不注重詞句意義,以及年代久遠,創作者和發祥地不明等等,大部分都很難再尋其歌詞真正的含義。
但是,童歌的價值卻是不可忽視的。作為源遠流長的口承文學,它飽含了日本民族的歷史文化、日本人民的審美意識等重要的人文素養和人文特征。如上述歌詞中提到的“鶴”和“龜”兩個素材,便是日本傳統文化中兩個極具象征性的符號,例如小學館大辭泉中的條目二記載,鶴和龜代表著長壽和吉慶,多出現在一些喜慶的物件或儀式上,比如紅包、壽宴、婚禮等。此外,童歌背后撲朔迷離的民間傳說,更是展現了日本傳統童謠詩的生動、豐滿、鮮活的一面,不僅能加深對從江戶時代前就存在的古老童謠的了解,也對了解日本民俗、風物以及人文溯源等極具魅力和價值。
總之,日本童歌歌詞雖然注重游戲效果而不注重實際含義,是個類似于“玩具”性質的存在,但在釋放兒童天性、培養孩子想象力和創造力方面有著積極的意義,以及在研究日本傳統文化和日本審美意識等方面也有著重要的價值。
二、文部省唱歌——“德行”的培養
隨著明治時期的到來,日本提倡“脫亞入歐”,日本人在諸多方面向歐美學習以求強國富民。日本的教育界也毫不例外地開始探索符合國家發展方向的教育方式和培養國家力量的道路。明治之前口口相傳、沒有鮮明的創作方向和目標的童歌,已經無法滿足日本社會發展的新需要,因而逐漸淡出人們的視線。取而代之的是將歐美音樂學科的教學模式與日本的國家需求相結合的“唱歌”。即日本文部省從明治時期到昭和時期組織編制的或得到文部省認定后編寫到小學音樂課教材中的童謠。主要以西洋曲子為基礎,配以國文學家或者教師創作或翻譯西洋歌詞的方式進行。因此,在大正時期的創作童謠運動中“唱歌”也被批判為太過西洋化而忘卻了日本固有文化和情感的童謠。正如東京高等師范學校附屬小學唱歌教員青柳善吾所說, “教育的最終目的是培養出與時代和社會需要相符合的人”[4],當時唱歌打出的口號是為了道德教育。但是只要對當時的日本文部省推送的相關唱歌集內容進行分析,就會明白這里的“教育目的”并不只是為少年兒童身心自由發展而設立的“正向目的”。

這段文字是日本文部省在1874年欲設立并推行唱歌課程時,在當年的《文部省雜志》第三號上刊登的從德文翻譯過來的短文《愛國心的教育》中的一段內容。該文論述了為了培養愛國心而設立愛國主題類兒歌課程的重要性,也正契合了當時日本文部省推出“唱歌”的目的和理念。再看19世紀80年代以此主旨和意圖推出的《小學唱歌集》系列教材,其中為了推出更“先進”、更具教化和培養力的唱歌,文部省進行了一系列對歐美音樂和詩歌的考察以及內部人員的調整和部署。以1882年(明治15年)出版發行的《小學唱歌集》第一版為例,其中的第17首“蝴蝶”中唱道:

其中第三行中暗指明治時代的“繁盛的年代(栄ゆる御代に)”的“年代(御代)”是個特殊的日語,在日文中“御代”一詞,是對天皇、皇帝、王等治世的敬語說法。這個意義特殊的詞傳達出了“文明開化的明治時期,在天皇的統治下會更加繁榮”的意思。看似描繪春天櫻花盛開一片春意盎然的寫景詩句,實則是對天皇統治的歌頌。當時的日本文部省首腦伊澤修二在命人創作此歌時,對這首唱歌做了這樣的評價:“將皇室的繁榮比擬為櫻花的燦爛,感受著圣恩、生活在國泰民安時代的人民像蝴蝶一般自由飛舞,以此讓少年兒童深切感受到國之恩惠,并激起他們為國效力的志氣。”[7]可以看出,當時日本文部省所謂的“教育目的”不過是為了借“愛國主義”之名義,宣傳和教化忠君報國思想,將一個個少年兒童培養成為對帝國和天皇甘愿盡忠的一兵一卒。作為面向少年兒童的“唱歌”,為了達到培養為帝國效忠的“國民”的目的,鼓吹“愚忠”,此類童謠不僅會影響少年兒童判斷是非黑白的能力,更會遏制少年兒童在天真爛漫的年紀抒發童心和童趣、自我探索和發現世界的天性。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的1947年,為打壓日本的軍國主義以及皇權勢力,占領日本的同盟國軍隊總司令部曾要求將帶有明顯的歌頌皇室的“在櫻花繁盛的(明治)年代”這一句歌詞刪除。于是同年文部省發行的《一年級音樂》中,對其做了改動,將第三行的“在櫻花繁盛的年代”改成了“在花叢間”。
在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時期,更是產生了不少鼓吹戰爭、煽動民心的唱歌作品。比如,明治24年(1891年)從山田美妙發表的《戰景大和魂》(1886年)節選而成的“成千上萬的敵軍”[6]這首唱歌中,“敵人雖成千上萬/但全都是烏合之眾/即使不是烏合之眾/我方是正確且有道理的/邪是壓不了正義的”來合理化侵略戰爭,以及“失敗逃走的人是國家的恥辱/前進并為國捐軀的人是榮譽之軀”這樣的歌詞來對侵略戰爭下的國民進行精神上和道德上的綁架,尤其是對于辨別能力還很弱的兒童,更是一種錯誤的意識形態的灌輸和洗腦。“勇敢的水兵”[6](1895年)中“‘還沒有沉沒/定遠號’/這句話雖然簡短/但在心心念念著國家的國民/心里永遠長存”這樣歌詞,從中可以看到甲午海戰中清政府派出的定遠號戰艦的誓死抵抗,而這首唱歌作品則是企圖通過描寫與定遠號的鏖戰,來宣揚日本士兵在前線“奮勇”前進,以此昂揚戰意、煽動民眾。當時文部省為了提高國民戰斗意識,鼓勵此類唱歌的創作,因此這類在戰爭期間誕生的戰爭主題的唱歌不僅在中小學生之間廣為傳唱,更是作為國民之歌在大眾之間流行,不僅污染少年兒童的心靈,更為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搖旗吶喊,對于兒童的健康成長來說可謂是有百害而無一利。
綜上可以看出日本唱歌帶有明顯的功利性,是為了培育符合帝國意志的兒童而誕生的童謠,是對兒童宣傳和教化忠君報國思想的工具和手段。因此,文部省推出的唱歌大多是極具軍國主義、國粹主義傾向的童謠,在精心雕琢的語言文字下面往往隱藏著別有用心的目的,借助唱歌這種無形的“思想武器”綁架和改造天真爛漫的童心,通過政府和學校合作的方式將忠君報國的思想潛移默化地灌輸給少年兒童,把他們塑造成為侵略戰爭的先鋒和武器。
三、創作童謠——豐富內心感悟生命
創作童謠誕生于日本大正時期開展的“童謠運動”中,是以反對“忘卻了日本的風土、傳統和童心”[8]的“唱歌”為目的,以創作站在孩子的立場、保留孩子純真的心靈和美好想象為創作目標的“童心主義”詩歌。當時還沒有出現真正意義上符合兒童的讀物,市面上更多的是改編或翻譯的西歐兒童文學,以及日本傳統故事,如桃太郎等,兒童讀物亟需新的發展。同時,大正時期正逢第一次世界大戰,一戰結束后整個日本社會彌漫著作為戰勝國的自滿和驕傲,明治唱歌中的軍國主義等意識形態的灌輸也愈發增強,文部省利用學校唱歌對學生的教化同當時“大正民主”運動所提倡的自由民主和個人解放相違背。另外,隨著日本近代化的進程日趨加快,西歐“兒童本位”思想也促進了日本兒童文學對于童真、童心、童趣的再次發掘。1918年(大正7年)日本著名兒童雜志《赤鳥》創刊,創始人鈴木三重吉提出了“面向孩子們創作的、具有豐富的藝術性”的新童謠創作理念。這一理念一經推出,便獲得了一批有赤子心、有責任感的文學家的支持,如北原白秋、西條八十、金子美鈴等,紛紛加入童謠詩的創作。在創作童謠的巔峰時期,類似于《赤鳥》這樣的與童謠相關的雜志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如《金色的小船》(1919年創刊)、《童話》(1920年創刊)等,甚至一度出現日本全國上下無作家不寫童謠詩的局面。北原白秋認為,“唱歌”這樣的童謠讓“日本孩子越來越無法天真無邪地歌唱出他們內心的聲音”,而“真正的童謠用的是孩子們容易理解的話語,在表達孩子的內心情感的同時,也能引起成年人深刻的感悟和理解。”[8]
正如日本廣為傳唱的創作童謠之一“紅蜻蜓”:
晚霞夕照的山上 從(姐姐的)背上看到的 難道是幻影
采摘山田的桑果 放到小籃子里 又是哪一天
十五歲的姐姐已嫁到遠方 別了故鄉 杳無音信
只有晚霞夕照中的紅蜻蜓 還停歇在那竹竿尖上[9]
詩人三木露風的這首童謠選取的雖只是一些司空見慣的自然界意象,如晚霞、桑果、竹籃、紅蜻蜓以及親人小姐姐等,但是卻營造了一種小巧溫馨的氛圍,加之詩句中對故鄉自然流露出的懷戀和親人的思念——人類共通的感情,充斥著觸動讀者內心的魔力。
人對于童年時候陪伴過自己的人總是充滿著難以割舍的感情。回想起曾經背著自己,披著晚霞的余暉,在夕陽西下的山間田地采摘桑果的小姐姐,詩人的憂傷和不舍溢滿字里行間。而故鄉,或是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園, 或是落葉歸根的夢中故土,總之故鄉是每個人內心深處不可磨滅的記憶。詩人對于親人和故鄉的懷念之情,這種質樸的感情對于兒童的美育和德育的能量是無限的。盡管兒童身上有著許多的“幼稚”,但是兒童心理渴望著“成熟”,跟兒童談親情、談故鄉等問題,將會無限豐富兒童的內心對生命的認識。[10]“動人的作品往往來自深切的感受”[11],三木露風在這首詩里所抒發的對親人的思念和故鄉的熱愛,正是人內心深處最本質的構成。這也是一直到今天,這首創作童謠不僅被日本人民喜愛,而且走出了日本,傳到中國,被收錄于人教版小學四年級音樂課本中的原因所在。那扣人心弦的曲調和優美動人的詞語,尤其是其中包含的對于故鄉、親人以及大自然的淳樸的感情,是其能夠超越時空和民族的界限照亮人們心靈的根源所在。
朝霞映紅了天邊
漁船滿載而歸嘍
大條的沙丁魚
滿載而歸嘍
海邊
像過節一樣熱鬧
海里
幾萬條
沙丁魚的葬禮
正要舉行[9]
這首廣為人知的金子美鈴的童謠“大漁”(1924年),將大人們眼中值得慶祝的漁獵大豐收的熱鬧場景,通過逆轉的視角,即透過內心豐富敏感的兒童的眼睛,描繪了一場令人悲痛的大海里的悼念會。兒童總是會將自己作為大自然萬物的一員,去感受并擅長和動植物建立“連接”,這不僅是人類作為自然界的一部分的本能的反應,更是一種作為“自然界的高級動物”的人的善良,因為他們擁有一顆對于“同類”的尊重和愛護的善良的心。孩子常常用和動物平等的視角來看世界,再如蕗谷虹兒的“松葉十字架”(1925年)和“大漁”有異曲同工之妙,通過孩子的視角傳達對動物的同情,“散落在海邊的/貝殼,大家以前都是/活的貝殼/大家以前都是/活的貝殼。銀色的細螺/櫻花貝/象牙般的/蛤蜊/大家以前都是/活的貝殼”“和父母走散了的/小貝殼/和孩子分開了的/貝殼的父母/大家一起哀悼”[9],對和父母走散了的小貝殼的不幸遭遇寄予同情,為其母親和孩子的分離而痛心。
詩人們懷著孩子般柔軟善良的心,巧妙地選擇了符合孩子內心的主題,創作出充滿真摯感情的童謠。而且,這種“萬物皆有生命”“敬畏自然”的精神在當下的現代社會也非常欠缺,因此這些創作童謠的意義不僅僅是面向兒童的童謠,更是大人的精神補給。人們總是被現代“文明”的發展速度所追趕,而遠離自然懸浮于“大地”之上,逐漸失去了生存的真實感,因此,包含著孩子們直接且近乎透明的樸素感情的創作童謠,可以說是治愈心靈的良藥。
人在年幼時期對萬事萬物總是充滿好奇,有著更為敏感的洞察力和心得,但卻也缺乏判斷是非的能力和理性的思考。因此,如明治文部省唱歌那樣說教、灌輸大于引導的形式顯然不利于兒童成長,更不必說軍國主義意識形態對社會和人類的發展的危害,因此正如鈴木三重吉所說的,“為孩子創作高質量的文學作品”來“培育孩子美好的想象力和情感”[12]非常有必要。人是一個有機的整體,身心都需要得到自由的成長,尤其是心靈的成長。那些包含著對于美好、自由、愛的追求以及樸素而美好的情感的創作童謠,正是心靈成長的養料。
承載著人的美好且樸素情感的作品往往擁有著超越個人和時代的生命力,正如創作童謠那樣能夠像一只小鳥,飛躍時空,歷經百年跨越山海來到我們身邊,唱著悅耳的歌。
四、結語
如上述分析,日本文學史上的三種童謠詩在時間上前后相繼,既有共同點也有不同點。眾所周知,在一個人成長初期對世界充滿幻想和渴望的時候,所接觸到的語言或文字以及這些語言或文字帶來的感動和留下的印象往往具有啟蒙意義,且影響深遠。因此,不論是童歌、唱歌還是創作童謠,都會在日本人年幼時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他們。另外,文學創作脫離不了母國文化,因此三種童謠都不同程度地融入了日本的文化、風土、傳統等。
而不同之處,首先在語言表達上,童歌在形式上用詞簡單,大多是便于做游戲互動時候朗誦或歌唱。“唱歌”,作為文部省帶有一定目標設置的學校學科,遣詞造句多生僻晦澀。創作童謠站在兒童角度進行創作,語言文字表達較口語化,用詞通俗易懂且優美清新。
其次體現在內容上,童歌主要是以游戲玩耍、簡單的常識、慶典活動等日常題材為內容,大多數是自然發生的口承童謠,因此更具有民風民俗的特色。而“唱歌”由于是通過大人的角度,將大人的思想和感情強壓給孩子們,具有功利性,因此不能迎合孩子們的興趣。創作童謠大多數是考慮到孩童的好奇心和興趣而創作,有利于開發孩子們的天性與想象力。
再者,體現在思想情感上,兒童階段是人格發展和形成的重要時期,培養孩童的美好的想象力和情感才能符合社會和人類發展規律。而“唱歌”更多的是為了宣傳為帝國、為天皇效忠,進行思想統一的一種工具,缺乏童歌的質樸和游戲性,更缺乏創作童謠里蘊含的兒童的童心爛漫和天真無邪。創作童謠從1918年到今天歷經百年,依舊能照亮我們的心靈,因此創作童謠更有利于兒童心靈的豐富和成長,同時更能呼喚起大人的“童心”,老少皆宜,超越時空。
注釋:
①1867年,日本江戶末年,江戶政府在實行 大正奉還之際秘密地埋藏下金子,用于幕 府復興的軍備資金。有日本民間說法指出, 本首童歌有暗指德川藏金子的地方。
②“竹網眼(かごめ)”還可以寫作日語漢字 “籠女”,指腹前懷抱籠子的女人,暗指孕 婦。“籠中鳥(かごの中の鳥)”,指腹中 孩子。民間說法為孕婦家中正在進行繼承 人之爭,其中有人對繼承人候選人增加感 到不快,因此在孕婦預產期即將到來的某個 月夜,將正要下樓梯的孕婦從背后推了下 去,因此說這首童歌是孕婦流產之后的怨 恨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