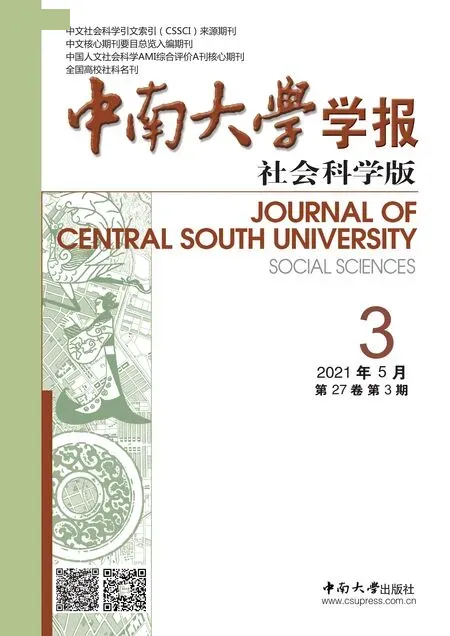福柯對西方權力“戲劇”之維的批判及其理法路徑
劉臨達
福柯對西方權力“戲劇”之維的批判及其理法路徑
劉臨達
(中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湖南長沙,410083)
西方關于權力的“戲劇”之維構建有著長久的歷史。福柯通過描述西方精神病院近代以來的相關情形,揭示和批判了醫院對精神病人的“戲劇化治療”,包括其內部隨意“設置角色和劇本”的危害,從而開辟了理解現代西方統治術形式的新途徑。福柯的批判,其話語分析蘊含著結構主義方法論要素,其歷史分析則隱含著其與馬克思權力論的傳承關系。解讀福柯對權力戲劇之維的批判,不僅有助于理解西方許多現代性問題的重要理論環節,對包括我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人民應對當代的“霸權劇本”也具有重要的現實啟發意義,如如何在跨文化交流的過程中書寫“美美與共”的崇高性敘事,如何從命運共同體的維度去書寫國際交往的政治美學,等等。
福柯;權力的戲劇之維;結構主義;歷史動態;馬克思
一、引言
西方關于權力的“戲劇”之維構建的論說有著長久的歷史。早在古希臘時期,柏拉圖在考慮建立其所謂“理想國”時,“整個政治制度就建得相當戲劇化”[1](576)。柏拉圖進一步指出:如果按照其所推崇的斯巴達式“王政”來建立理想國的話,“哲學王”就要自己制定“舞蹈、歌曲、歌舞活動的整個規劃”[1](559)。由此,城邦就能運行在相當戲劇化的古希臘式貴族政體之中。然而,柏拉圖關于權力的戲劇之維的構想,終其一生也只是停留在文本探討之中,并未付諸實踐。另外,盡管古希臘社會曾出現過“觀劇津貼”的制度安排來促進戲劇與政治的結合,但學界一般也沒有將其與柏拉圖的理論構想聯系在一起。
在柏拉圖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權力戲劇之維的構想并沒有再度引起西方學界的理論聚焦。到了20世紀,在弗雷格、羅素、維特根斯坦等學者開啟了西方哲學的“話語轉向(the linguistic turn)”之后,一部分學者出于所謂的“話語研究”的敏感性,又重新開啟了對該問題的探討。福柯和其老師阿爾都塞對此相關問題的研究也在這一時期。
話語研究是微觀研究,所以福柯和阿爾都塞兩人都不再以柏拉圖式的宏觀視野審視和討論權力與戲劇的問題,而是從一種微觀視角出發,將論述題材轉向了精神病的治療問題。兩人同時將批判的焦點指向了精神病院里的“戲劇化治療”。阿爾都塞住過醫院,所以對精神病院里醫生的“假裝治療”做出了直接且辛辣的批判。阿爾都塞將當時的圣安娜醫院稱作“基羅爾地獄”,并且認為,某些時候精神病醫生所謂的治療只是一種表演,而不是一種科學行為。這種表演之所以能夠繼續蒙混下去,是因為外界對其中的詳情并不了解——“不了解醫生有時會面臨可怕的困難,有時在突然陷入令人焦慮絕境的同時還得繼續做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樣子”[2](29)。作為阿爾都塞的學生,福柯延續了其老師關于歐洲精神病院的相關研究,并重啟了對西方權力戲劇性特征的研究。
與阿爾都塞的直接批判不同,福柯筆下的《性經驗史》《臨床醫學的誕生》《規訓與懲罰》等作品雖然都只討論了某個社會問題的某一方面,但每一部作品,都因刻畫了西方世界里的某種通用權力技術和批判影射了西方世界相關問題的普遍性而成為經典。以《規訓與懲罰》為例,該作品雖然只討論了歐洲社會的監獄問題,但是其中所描繪的“全景暢視”權力技術,卻使歐洲后工業社會的監控問題受到影射。另一部《瘋癲與文明》對社會問題批判的廣泛性意蘊也與《規訓與懲罰》異曲同工:歐洲精神病醫院對待精神病患者的某些權力技術,是歐洲特定時期某些普遍性權力技術在局部社會延伸和運作的縮影。這種以小見大的書寫方式,不僅是福柯文本的一大特點,也是福柯文本相關權力論述的價值所在。以其為學術棱鏡,能夠幫助后世更好地理解西方近代以來的現代性弊病。
二、福柯對精神病人治療中醫院權力戲劇之維的批判
用戲劇手段治療精神病人,在西方長期以來被認為是常規手段。甚至在20世紀早期,當弗洛伊德開創了精神分析理論之時,他也仍然認為戲劇手段是治療精神病人的常規手段。弗洛伊德認為,普通戲劇、普通心理劇、心理變態劇,這三者對觀眾產生的影響是有很大區別的。普通人可能會在觀看普通戲劇、普通心理劇時產生觸動,而在觀看心理變態劇時卻不明所以;精神病人則會對心理變態劇產生觸動。這是因為,普通人只會產生諸如“當英雄”之類角色的代入快感,但精神病人則會有其他的心理沖動,并期待某些特殊角色的代入快感。對于這種劇本,弗洛伊德說:“這里,快樂的前提條件是觀眾本人須是一個神經癥者,因為只有這種人才能從(心理變態)戲劇的昭示中和從被壓抑的沖動的或多或少的意識中獲取快樂,而不是反感。”[3]7所以,弗洛伊德認為,戲劇治療就是要洞悉并化解某些特殊的心理沖動和角色代入沖動。精神分析的催眠方法就是其中之一。這種治療的關鍵之處在于,治療者千萬不能被神經癥者的心理劇本所同化。否則,一旦反向的情況發生,則治療者就會忘記對方是一個病人。弗洛伊德認為,這些心理變態劇要審慎對待。因為,“看來似乎是劇作家們在誘發觀眾產生相同的疾患。”[3](8)因此,催眠、心理劇本置換,都顯得十分必要。
弗洛伊德的這些觀點在福柯的有關論述中遭到了批判。福柯的分析指出,在這種置換心理劇本的過程之中存在一種權力濫用的隱患。通過描述西方精神病院近代以來的相關情形,福柯揭示了其內部隨意設置角色和劇本的危害。并且,在“話語研究”的層面來看,西方精神病院本身可能就是一種特定時代話語所編織的“局部劇本”,且對參與者有強制性。精神病院對病人實施的強制性治療,則是其不受約束權力進一步編織的“劇中劇”。因而,所謂的“病人”一旦接受精神病院的治療,就很可能再也無法出院。對此,一種對當時狀況比較激進的批評也指出“瘋癲是社會創造的”[4]。對于精神病院的種種戲劇化強制,一種觀點認為福柯的主要價值在于批判了一種“自導自演”的不受約束的權力。在這種權力架構中,“主管的角色以及他至關重要的組織性表演,將其安置在了一個擁有兩重性的地位:既內在地和外在地主導著關于真實的表達,也承擔著這種表達對于機構和對于他自己而言的種種結果”[5]。由此福柯意在啟發我們,在治療精神病人的問題上,首先是要限制精神病院里醫生的權力,而不是把關注的焦點放在優化治療方案上。
在福柯的“瘋癲考古”中,我們還能看到精神病院里荒誕的治療方案。例如,有的瘋人認為自己是死人,因為死人是不吃東西的,所以他也不應該吃東西;也有的瘋人認為屋子里的人都死了,而自己也在這個屋子里,所以自己也應該是死了的。以當時的科學水平,精神病院治愈上述兩類病人的醫療條件并不具備,但由于精神病院里“醫生—病人”角色系統的預設不受任何質疑,精神病院的權力不受任何干預,因此病人只要被送進精神病院,就會被隨意治療。于是我們看到了十分荒誕的治療場景:醫生邀請三五好友裝扮成陰間的人物,在瘋人的床前進餐,并大談特談死人應該吃東西這個主題;瘋人院也會常常策劃“茶話會”,邀請瘋人按照院長和工作人員的暗示來扮演特定的角色。在這些角色扮演中,瘋人必須按照被指派角色的預設完成一系列言談舉止。對此,福柯批判說:“瘋人不停地扮演著這種名不符實的陌生人的角色。他人的觀察、禮節和偽裝會無聲地強加給他某種社會人格”[6](234)。
福柯認為,對待精神病人的這種戲劇化強制,應視為不合理。因為,這只是近代以來才出現的現象。這種現象的出現和很多近代以來的“話語建構”有關。在哲學經歷了“話語轉向”之后,這些現象都應再予以反思。福柯通過對“話語建構”的歷時性考察發現,在精神病院出現之前,瘋人是被放置在“人類社會—已知自然—神秘自然”的話語之中來理解的。在這種話語所構造的角色想象之中,人們往往帶著驚異的目光,把瘋人想象為一種神秘的、強大的自然力量。當時的人們認為,“瘋人不是病人。獸性使瘋人免于遭受人身上脆弱、不穩定、不健康等因素的傷害。瘋癲時的那種頑強的獸性,以及從魯莽的野獸界借來的愚鈍,使瘋人能夠忍受饑餓、高溫、寒冷和疼痛”[6](73)。所以,在那個年代,并不存在對瘋人的強制性戲劇治療。而對于更早期的情況來說,瘋人的處境則更加自由。福柯指出:“在文藝復興時期,人們允許各種無理智自由地展示于光天化日之下”[6](67)。通過這種對比,福柯意在指出:瘋人在近代以來的遭遇,是因為一種全新的權力技術向他們擴展,一種新的牢籠式話語系統開始試圖規訓他們。按福柯的理論,這種希望人人都被改造成類似黑格爾語境里“優美的靈魂”的權力意圖,往往是近代西方社會弱勢群體命運悲劇的起點。對此,福柯說:“這個靈魂是一種權力解剖學的效應和工具;這個靈魂是肉體的監獄。”[7](32)
通過福柯的“瘋癲考古”能夠看出,近代西方的現代化進程是需要反思的。尤其是在對待弱勢群體方面,許多做法都值得商榷。對精神病人的戲劇化治療就是其中的典型性問題。對這些問題的反思也正是福柯等人創造的學術價值所在——“通過對莎士比亞和福柯的解讀,在政治儀式和戲劇性的系譜學方面,開辟了很多理解現代西方統治術形式的新途徑”[8]。所以,我們很有必要對其中所蘊含的理論核心問題進行更加深入的解讀,特別是福柯是運用什么方法探觸到了長期以來并未受到質疑的事物的問題。其分析的方法論,以及其所屬的理論傳統又是什么。解答這些問題將為我們提供更多的分析類似問題的 參考。
三、福柯權力戲劇之維批判中的結構主義要素
在經歷哲學的“話語轉向”之后,不少西方哲學家開始質疑西方的政治話語和真理間的必然聯系,福柯、德里達、鮑德里亞以及詹明信等人更是把西方的政治話語當成世俗權力的技術牢籠。結構主義方法論正是西方哲學“話語轉向”潮流中的核心要素。具體地說,就是一部分理論家開始運用結構主義方法論,來分析話語的“命名”“賦名”“指位”等能指和所指間看似偶然的對應關系中所包含的權力技術。
世界上眾多的語種對物質的命名是千差萬別的。從結構主義理論來看,話語的能指和所指的對應,特別是命名,具有很強的隨機性。“語言符號是隨機的,擬像性是它的典型特征”[9]。諸如“水”“火”之類的基礎性詞項,我們在腦中反映的可能是“水”“火”的擬像,但是“水”“火”具體以怎樣的能指和所指表達,就是完全隨機的。正是由于話語的這種隨機性,它才可以成為權力運用的中介。
在近代的西方世界里,話語中的“名”“詞”“指稱”等要素并不是中性的。這是福柯在其最主要的方法論著作——《詞與物》中所要表達的核心思想:繁多的語言符號能夠通過體系化與結構化規定來實現某些權力效應。例如,一份來自中國的分類表曾引起歐洲人發笑,其原因是該分類表把動物分成“皇家的、有芬芳的、馴順的……”[10](1)。福柯曾認真地思考過當時歐洲人發笑的根源,認為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歐洲人并不知道該分類表中的相關意象在中國語境中的規定和所指。
結構主義認為,由于話語結構的形成和話語所指一樣沒有普遍性規律來遵循,它最終也呈現出了千姿百態的共時性結構。任何團體,只要擁有足夠強的公共權力,它就能擁有自己的話語結構;如果公共權力崩塌了,與之相關的話語結構就會跟著一起土崩瓦解。福柯也持此觀點。福柯進一步將不肯放棄失效話語結構的人稱為“異托邦人”。“異托邦人”使用諸多概念之所以會被認為是“奇怪的列舉”,是因為“使這種(諸多概念)相遇成為可能的那個共同基礎(權力)已經被破壞了。”[10](3)離開了權力,千種千面的共時性結構不一定都能繼續存在。
依照福柯的上述理論,可以從結構變遷的視角來重新審視瘋人問題。具體來說,在沒有“醫生—病人—家屬”這種安置瘋人的共時性結構出現之前,瘋人的社會處境是完全不一樣的。依照當時社會對角色系統的理解和安排,瘋人不會遭受悲慘際遇。福柯曾引證《李爾王》《麥克白》《哈姆雷特》等經典戲劇對此進行了前后對比。在這些劇作中,作為公開的、光明正大向社會展示并被廣大觀眾接受的瘋癲,是沒有完全被列入“他者”維度、沒有在話語位置上被“降維”的瘋癲。這是福柯通過對比得出的結論。特別是通過“考古”莎士比亞和塞萬提斯筆下的瘋癲,福柯認為,當時的社會仍然對瘋癲保留著足夠的社會容忍度,甚至認為瘋人潛在地具有說出不為人知的真相的能力。這也說明,在那個時代人們并不急于干預瘋癲。但是好景不長,如福柯“瘋癲考古”所揭示的那樣,隨著共時性結構的轉換,“瘋癲很快就告別了塞萬提斯和莎士比亞給它安排的這些終極地位”[6](33)。
在對待瘋人的問題上,話語共時性結構的權力效應體現得十分明顯。具體來看,有人認為自己是死人的這種想法,就構成了對當時話語權力的挑戰。因為,在當時歐洲社會所有角色預設系統中,沒有“死人”這一說法。相反,大家要盡心盡力地當“活人”,完成諸如為上帝服務,為領主服務等任務。但是瘋人堅持要成為自己設定的角色,并常常用看似具有自洽性的“我是死人—死人不吃東西—我也不吃東西”這一形式邏輯來和外界對抗。福柯說:“很輕易地在瘋人中發現了這些嚴格的推理形式……瘋人的這種不可思議的邏輯似乎是對邏輯學家的嘲弄,因為兩者十分相似,更確切地說,二者完全相同……我們發現了一種隱蔽的完整語言”[6](92)。所以,“治療”就不能以瘋人的邏輯展開。因此,福柯的“瘋癲考古”有這樣的記載:由于無法說服認為自己是死人的瘋人,“醫生便承認他的譫妄,讓他似乎看到一位手中持劍的白衣‘天使’。這個幻影 嚴厲地訓斥了一番,然后宣布他的罪孽得到寬恕。”[6](176)這種“療法”是為了讓“瘋人”回到“人間”,回到當時話語權力所建構的共時性結構之中。除此之外,此前提到的“茶話會療法”在本質上也是想讓瘋人忘卻最初的指涉意愿。很多時候,戲劇性的“治療”能夠起到很好的效果。因為在戲劇中,一部分所謂的“瘋人”能心領神會醫生的意圖,從而配合他們演出。但是從福柯的表述來看,他恰恰是在提醒人們,“瘋人”之所以能夠配合“演出”,是因為“瘋人”具有完整的敘事理解能力,所以他才具備表演“治療性”戲劇的基本素質。
通過以上梳理能夠看出,福柯對西方特定時期權力戲劇化特征的刻畫,在方法論層面有著濃厚的結構主義色彩。這并不是一種巧合。“瘋癲考古”最初是福柯的博士論文,而其寫作之時正是列維·施特勞斯將結構主義引入法國并造成巨大影響后不久。對此,我們只需比對一下福柯的有關論述和列維·施特勞斯關于“野性的思維”的相關論述即可看出其中的同構性。
施特勞斯曾批判說,近現代歐洲人始終盲目地認為現代思維是高度理性的、合理的;原始思維是混亂的、無規則的,其分類細致性與結構完整性都有待提高。但是施特勞斯通過細致考察原始思維發現情況并非如此。他認為,原始思維并不缺乏高度的區分功能,也不缺乏分類的細致性,它始終具有自己獨特的共時性話語結構:一種相對于研究者的“先在結構”。原始人已把能指和所指都納入自己所認可的共時性結構中。施特勞斯把原始人心中固執堅持的這種結構,比喻成修補匠預先在心中謀劃的先在設計。施特勞斯說:“修補匠可能永遠也完不成其設計,但 他總是把與他自身有關的某種東西置入設計之內”[11](22)。原始人的固執還有許多明顯的表現。例如,啄木鳥的嘴和治療牙病并不一定有關系,但是為了補全一種既定的共時性結構,這二者就會被納入一組聯系緊密的意義關系之中,“問題并不在于碰啄木鳥的嘴是否真能醫治牙病,而是在于是否能有一種觀念認為啄木鳥的嘴與人的牙齒‘相配’……在于是否能通過這類事物的組合把某種最初步的秩序引入世界”[11](10)。再比如,孕婦相信懷孕之時遇到的某些意象會和胎兒有某些聯系。由此,孕婦便在孕期意象和胎兒之間建立起固執的共時性結構聯系,水果、動物等都被拿來參與有關胎兒的相關推理——“如果找到的是鱔魚或海蛇,孩子將和它們一樣柔軟和怠惰。如果是一只寄居蟹,孩子就是暴性子的。另外,如果是蜥蜴,孩子就是溫柔可愛的”[11](73)。
孕婦臆測式的想象和瘋人的某些思維相比沒有太大區別,這表明了話語先在共時性結構的巨大效應。原始和文明的對峙、“瘋人”和精神病院的對峙,實際上都是話語共時性結構層面對峙的表現。可以說,正是在對語言隨機性和結構的強制性的強調中,福柯確實繼承了結構主義方法論的基本要素。關于結構主義與權力,法國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思潮的代表人物阿爾都塞對此也曾直言:“爭吵是不可避免的,這是結構的規律。”[2](78)法國后結構主義的代表人物鮑德里亞也曾借助涂鴉做出分析,表達了類似的思想。他指出,涂鴉之所以具有反抗意味,是因為涂鴉是對現代資本主義整個意義鏈條的拒絕。涂鴉純粹是針對結構來創造的,由此嘗試去顛覆資本主義的意義體系——“涂鴉沒有內容,沒有信息。但這種虛無就是力量,其對形式的全面攻擊伴隨著內容的衰退,這并非偶然”[12](107)。
通過比對不難發現,福柯“瘋癲考古”的結構主義元素是有源可考的。但是,我們卻并不能就此認為福柯是在結構主義方法論范圍內開展了有關研究。通常而言,學界只認為福柯是一個“唯物主義式的后結構主義者,并與德里達、利奧塔、鮑德里亞等其他后結構主義者有顯著的區別”[13]。這就是說,在理解福柯文本的時候,我們不能忽視其與一般結構主義者的區別,尤其是在研究其對某些權力的戲劇性特征的刻畫時,這一點更不能忽視。
到了20世紀70年代,這些不接受結構主義“能知假設”的學者被稱為后結構主義者。基于對“能知假設”的不同闡釋,后結構主義者們形成了多種不同的理論。在福柯的論說中,則主要是借助了結構主義方法論來批判特定的權力。
四、福柯權力戲劇之維的批判與馬克思權力觀的關聯
對于結構主義,福柯說:“結構主義算不上一種新的方法,它只不過是一種現代思維意識,具有覺醒的意蘊,但仍然是成問題的。”[14]。這種問題主要在于,如果離開了對共時性結構的發生學分析,我們到底在分析什么呢?所以,福柯筆下巨大的歷史情境性色彩以及某些意象的前后連貫性,都始終激勵著研究者從權力的發生學的角度來理解福柯的理論。這也是福柯在那個時代較為獨特的一面。因為,在后結構主義思潮興起之后,權力的發生學已不再被重視。如鮑德里亞就認為,被壓迫者之所以被壓迫,是因為接受了一種祛除了“死亡”的能指系統;勞動在西方世界里是一種戲劇動作,在祛除了“死亡”的“劇本”中上演。他認為,這從遠古時代就是如此,被處死的戰俘和成為勞動者的戰俘的區別是,兩者接受了兩種不同的生存“劇本”。所以,對于今天仍然被迫接受不公正勞動的人來說,“劇本從沒變化。勞動的人仍然是那些沒被處死的人,那些沒得到這一榮譽的人”[12](54)。對此德里達也持同樣的觀點:人生如“戲”——“技術文明里的個人精確地依賴一種對獨特自我的誤解而生存。這種個人是一種角色,或者也可以被稱作假面(masque)個人,或人格面具(persona)個人、人物(personage)個人,而不是一個人(person)”[15]。德里達對人生角色化的批判也是在拋開權力的發生學的前提下展開的。但福柯的理論沒有完全拋棄權力的發生學,這在以往關于“瘋癲考古”及相關研究之中未得到足夠發掘。在結構主義的影響之外,福柯關于歷史、生產力、暴力、階級、實踐等核心概念的闡述也需要得到重視。這些闡述體現了福柯權力論中某些方面與馬克思的相關理論間的淵源。
“考古”必然包含著發生學的元素。福柯把他的“考古”作品的方法論,稱為“知識考古學”。按福柯的解釋來看,這種方法論并不意在分析某種給定的、“原初的饋贈”的要素,“而是把它(話語變化)歸結于歷史實踐的過程”[16]。這大概可以解釋,為什么福柯對某些戲劇化權力特征的刻畫,沒有止步于結構主義論域。福柯意在指出,共時性結構的變化根源于實踐的改變。實踐的改變催生人群的分化,而新崛起的權力主體,在西方世界編織全新的共時性結構。
在描繪規訓體制的形成時,福柯認為在西方的“舊制度”下,社會各群體都或多或少地依靠“非法”行為生存。但是隨著歷史的演進、實踐的變遷,新的權力主體開始崛起。由此,舊式君權所編織的共時性結構,開始被資產階級編織的嶄新的共時性結構所置換。這種新的共時性結構表現為近代歐洲的法制體系。由此,西方君權時代對窮人僅存的“慷慨”不復存在,資產階級苛刻的法律體系開始抹殺對窮人的最后寬容。這也即福柯所謂的西方再也沒有了“并行不悖的非法行為”[7](307-308)。禁閉瘋人的行為,實際上就是這種苛刻體系的連帶效應。除歷史實踐外,福柯對生產力的重視,也十分引人注目,福柯強調:“權力隨著生產力的不斷發展而得到改變”[17](162)。對這一點,福柯在諸多問題上都做了比較統一的理論歸因。如在批判肉體規訓時,福柯說,在近代西方的工廠中,工人的生產姿勢受到嚴格規訓,目的是為了提高生產效率。“按照工業社會的一般規范制造出機械化的個人……這是在制造機器人,也是在制造無產階級。”[7](272)對于性問題,福柯指出,西方人之所以不遺余力地去規范性行為的細節,甚至矯正同性戀的性傾向,是出于保持勞動力人口體量的考慮。福柯指出:“權力技術的最大新變化就是出現了作為政治經濟問題的人口現象……還出現了旨在將夫妻的性行為轉化為一種和諧的政治、經濟行為的有計劃的運動。”[18]而至于瘋人處境的變化,福柯認為經濟因素同樣在其中發揮著關鍵作用——大規模地禁閉瘋人,是要最大限度地在西方社會消除想要躲避資本主義勞動的心理[6](48)。
除此之外,福柯關于暴力對“戲劇治療”的支撐作用,也存在很令人震撼的論述。這主要是通過“考古”“水”這一意象的變遷來揭示。“水”和瘋癲的關系最初被認為是一種凈化關系。在社會仍然對瘋癲有一定容忍度的時候,人們相信瘋癲之人經過“水”的清洗,能夠褪去不良色彩。對此,福柯記述了曾經流行一時的“愚人船”現象。瘋人被載上“愚人船”,經過航行就像是經歷了“大水”的清洗。而后,瘋人走下船,來到新的地方,當地人便會接納瘋人。這是一種“凈化”瘋人的戲劇性儀式。福柯說,“水域給這種做法添加上它本身隱秘的價值。它不僅將人帶走,而且還有另外的作用——凈化”[6](13)。但是,逐漸地,人們開始在共時性結構里懷疑這種關聯,人們不再以清洗和凈化的態度去想象“水”和瘋人的關系。于是,“愚人船”的現象也消失了。由此,“它(瘋癲)留駐了。沒有船了,有的是醫院”[6](35)。
最初,在精神病醫院里,“清洗”瘋人的思想仍在延續。“水”和瘋人在“劇本”之中仍然有緊密的聯系。在“劇本”中,還有許多其他東西被當作藥用來治療瘋人,就是根據這種古老的清洗想象。比如,“苦藥具有海水的全部澀厲特點。它能通過洗蝕來達到凈化目的”[6](156)。于是,與海水的澀厲口感相似的東西,都會被拿來用作藥物。例如服用咖啡、肥皂等,都被當作治療瘋癲的苦藥療法。尤其是肥皂,“最好是,早晨第一件事就是服用肥皂……”[6](157)隨著歷史的演進,話語結構中有關瘋人的元素繼續發生變化。在有關“水”與瘋人的想象中,一些人開始相信,“水”的真正作用并不存在于它的性質中,而是存在于它的力道之中。“水”真正能對瘋癲起治療作用,主要是“水”“發生”得足夠激烈。于是,“人們認為水產生作用的唯一性質是其強烈性。不可抵擋的水流可以沖刷掉造成瘋癲的各種不潔之物”[6](163)。由此,“水”的作用開始脫離性質而轉向力道。這是里程碑式的轉變。于是,用水流對瘋人進行強烈的噴射,就成為“水”和瘋人的主要意義聯系。這取代了此前的坐浴、盆浴、泡浴的水療思路,“淋浴法則明顯地成為一種司法手段,淋浴是瘋人院中的常設治安法庭所慣用的懲罰手段……”[6](250)也就是說,暴力開始在精神病治療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福柯說,當時人們認為,“這種暴力行為據說是為了實現洗禮后的再生。”[6](163)不難看出,這又是另一種天馬行空的想象。在前文所述的誘導瘋人進食的問題上,戲劇之下的暴力色彩也在逐漸加重:對于不肯進食的瘋人,院長會來到他的房門口,用鐵鏈腳鐐相威脅,命令他必須把湯喝掉。于是,瘋人最終將湯喝掉,不過卻要“經過這幾個小時的思想斗爭”[6](249)。在福柯語境里可以看出,在讓人啼笑皆非的戲劇背后,還有歷時性的權力 圖景。
通過以上梳理能夠發現,福柯對某些權力戲劇化特征的透視具有歷時性的發生學色彩,而這是超出結構主義論域的。因為結構主義方法論只存在于共時性研究之中,所以對于福柯某些歷時性研究而言,我們需要考察其與其他理論傳統的淵源,進而準確定位其思想史地位。由此,通過提煉其中的關鍵概念會發現,實踐、歷史、生產力、暴力,乃至階級力量崛起等實際上更加靠近馬克思所代表的理論傳統。正如馬克思所說,“物質的力量只能用物質的力量來摧毀”[19]。這啟發我們,解放并不能僅僅依靠對共時性結構的分析來完成,更重要的是依賴階級力量的成長,以及其背后所蘊含的暴力實力的增強。對此,馬克思直言:“暴力本身就是一種經濟力。”[20](861)對于福柯描繪的近代西方的禁閉與規訓等問題,馬克思也相應地指出:“被暴力剝奪了土地、被驅逐出來而變成了流浪者的農村居民,由于這些古怪的恐怖的法律,通過鞭打、烙印、酷刑,被迫習慣于雇傭勞動制度所必需的紀律。”[20]846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強制勞動的歷史性記錄和福柯分析實踐改變話語的論述,具有很強的同構性。同時,我們如果將福柯語境中的社會權力集團編織話語牢籠的行為,和馬克思語境中掌握經濟基礎的社會集團構筑上層建筑的行為,進行對比又能夠發現:二者的論述其實異曲同工——只不過馬克思的論述更宏觀,而福柯更微觀。
關于福柯的權力理論與馬克思的權力理論間的關系,學界一直存在兩種爭執不下的觀點。以萊姆克主編的《馬克思與福柯》中所收集的十篇代表性論文為代表觀點,主要強調二者間的差異:主要強調福柯的微觀剖析方法和馬克思的宏觀歸納方法間的區別。但是,在國內學界一直有學者致力于馬克思和福柯的同構性研究。特別是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在福柯的權力理論與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之間存在著深刻的關聯,體現為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諸問題與福柯權力理論的許多主題之間的互相滲透和印證”[21]。從總體上來說,馬克思的權力理論一般被認為是一種對“類型總體”和“全盤手段”的分析(“類型總體”也稱作“格局”,“全盤手段”也稱作封閉性之中的“關系媒介”),同時配套歷史演化動力的學說來輔助分析。簡而言之,馬克思意在指出權力格局的演化趨勢和未來走向,“權力是封閉性之中足夠程度的關系優勢……權力格局的更迭,伴隨著社會關系建構媒介的轉變”[22]。所以,從馬克思的權力分析來看,解放意味著必須解除掉總體社會關系之中的全盤性權力技術。以此邏輯,社會主義必須否定和摘除全盤性資本邏輯,也即否定掉人人、事事、物物都要把自己轉化為經濟價值的全盤強制。只有這樣,每個人才能在不迎合全盤權力技術的前提下,自由而全面地生存和發展。從這個角度看,馬克思的權力理論恰恰正是福柯權力理論的“總綱性先驅”。而福柯的諸多具體分析則正是對馬克思的“權力論總綱”的細致擴展。
此外,福柯還曾表達過對馬克思權力論的認同,只不過福柯強調,要找準馬克思分析的真正重點所在。福柯認為,權力的真正的重點不是在“階級”,而是在“斗爭”。“總是關注‘階級斗爭’的問題,可是對‘斗爭’,卻忽略了”[17](47)。這就是說,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重視權力場域中的力量對比以及由此產生的壓迫和沖突是把握權力的關鍵。所以,通過以上梳理可以看出,福柯在分析權力的戲劇化特征之時,關于權力斗爭的這部分內容確實“溢出”了結構主義論域。而馬克思所開辟的權力論傳統,目前看來仍是這一部分內容最切近的理論源頭。因此,“符號與權力的問題,在傳統的馬克思主義解釋框架之內,反而會得到更有力的解釋。”[23]
五、結語
戲劇性要素在何種程度上可以成為權力技術的組成部分,同時,權力又在何種情境下采取戲劇化姿態來表達,這是福柯的相關質疑。我們通過對福柯的這種解讀能夠看出,權力對敘事及符號的借用,在近代西方是別具特點的。同時,我們也能從福柯的語境里讀到一種謹慎。那就是說,面對西方近代傲慢的權力,烏托邦思維并不可取。因為,自馬克思以來,我們始終被提醒著,物質力量才是觀念系統的根基。揭示出這一點,對權力研究的總問題視域及方法論的選擇,均有很大啟發。
從具體理論焦點上來看,解讀福柯對某些權力的戲劇性特征的刻畫,可以拓寬研究福柯權力論的研究路徑。雖然福柯經常號稱他從尼采那里獲得靈感,即“福柯繼承尼采的譜系學,把譜系學運用到對西方社會歷史的微觀分析中”[24]。但是可以看到,對歷史進程中的物質力量關系的關注,恰恰體現了馬克思和福柯在權力論上的傳承關系。從這個角度來說,福柯對某些權力戲劇化特征的分析,為其權力理論奠定了一種發生學的分析基礎。
就西方的現代性演進而言,戲劇構想、符號系統等如何被確立且如何主導社會,這都不再屬于柏拉圖式的純主觀建構,而是屬于人類歷史的實踐問題。相對而言,“福柯的分析有很強的歷史情境性色彩,認為主體的出現及其對權力的運載,都是歷史性的。”[25]我們將此觀點對照馬克思總結的相關理論,“我們判斷這樣一個變革時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識為根據;相反,這個意識必須從物質生活的矛盾中,從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現存沖突中去解釋。”[26]
從現實層面來看,福柯的“瘋癲考古”包含著對解放的呼吁。“瘋人”的遭遇具有普遍性影射意義。在近代西方,眾多不能自主選擇生存話語權的歐美弱勢群體,都和“瘋人”是同構的。他們有可能是婦女、兒童,也可能是后殖民語境里的“他者”。但總之,如果不接受西方社會的“權力劇本”,則他們都是“瘋人”。
這一深刻的理論反思,對于當下的我們而言,具有深刻的現實啟發意義。在資本主義的霸權邏輯仍然彌散全球四處的今天,如何擺脫全球資本對地域個性的抹殺,如何不成為霸權話語中的“他者”,如何在跨文化交流的過程中書寫“美美與共”的崇高性敘事,從命運共同體的維度去書寫國際交往的政治美學,這都是發展中國家的人民面對“霸權劇本”時的當代要務。
[1] 柏拉圖. 柏拉圖全集: 第三卷[M]. 王曉朝, 譯.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PLATO. Collected editions of Plato: vol. 3[M]. Trans. Xiaochao W.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8.
[2] 阿爾都塞. 來日方長[M]. 蔡鴻賓, 譯.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ALTHUSSER L. L’avenir dure longtemps[M]. Trans. CAI Hongbin.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2.
[3] 弗洛伊德. 達·芬奇的童年回憶[M]. 車文博, 譯,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4. FREUD S. Da Vinci's childhood memories[M]. Trans. Wenbo C. Beijing: Kyushu Publishing House, 2014.
[4] OSIPOVA E D. Madness, creativity, and irrationality: The problem and its interpretation in the works of Foucault[J]. Rud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14(3): 54-63.
[5] BOUILLOUD J, DESLANDES G, MERCIER G. The leader as chief truth officer: The ethical responsibility of ‘managing the truth’ in organizations[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19, 157(1): 1-13.
[6] 福柯. 瘋癲與文明[M]. 劉北成, 楊遠嬰, 譯. 北京: 三聯書店, 2012. FOUCAULT M. Histoire de la folie à l’age classique[M]. Trans. LIU Beicheng, YANG Yuanying.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2.
[7] 福柯. 規訓與懲罰[M]. 劉北成, 等, 譯. 北京: 三聯書店, 2012. FOUCAULT M. Surveilier et punir[M]. Trans. LIU Beicheng.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2.
[8] ELDENS. Foucault and Shakespeare: Ceremony, theatre, politics[J]. The Southern Journal of Philosophy, 2017(55): 153-172.
[9] ZHOU W, WANG W. On the arbitrariness of linguistic sign: A brief commentary on De Saussure’s argument of arbitrariness[J]. Canadian Social Science, 2018, 14(9): 4-9.
[10] 福柯. 詞與物[M]. 莫偉民,譯,上海: 上海三聯書店, 2002: 1. FOUCAULT M. Les mots et les choses[M]. Trans. MO Weimin. Shanghai: Shanghai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2: 1.
[11] 克洛德·列維—施特勞斯. 野性的思維[M]. 李幼蒸, 譯.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6. LéVI-STRAUSS C, La pensèe sauvage[M]. Trans. LI Youzheng.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06.
[12] 讓·鮑德里亞. 象征交換與死亡[M]. 車槿山, 譯. 南京:譯林出版社, 2012. BAUDRILLARD J. L’échange symbolique et la mort[M]. Trans. CHE Jinshan. Nanjing: Yilin Press, 2012.
[13] OLSSEN M. Structuralism, post-structuralism, neo- liberalism: Assessing Foucault's legacy[J]. Journal of Education Policy, 2003, 18(2): 189-202.
[14] FOUCAULT M. The order of things[M]. New York: Vintage, 1994: 208.
[15] DERIDA J. The gift of death and literature in secret[M]. Trans. Wills 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 37.
[16] 福柯. 知識考古學[M]. 謝強, 馬月, 譯. 北京: 三聯書店, 2003: 215. FOUCAULT M. L’archéologie du savoir[M]. Trans. XUE Qiang, MA Yue.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3.
[17] 福柯. 權力的眼睛[M]. 嚴鋒, 譯.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FOUCAULT M. Dits et écrits[M]. Trans. YAN Feng.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7.
[18] 福柯. 性經驗史[M]. 佘碧平, 譯,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16-17. FOUCAULTM. 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M]. Trans. SHE Biping.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5: 16-17.
[19]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11. Marx &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1[M].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9: 11.
[20]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五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Marx &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5[M].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9.
[21] 張盾, 王雪. 福柯權力理論與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J].社會科學戰線, 2019(11): 20-27. ZHANG Dun, WANG Xue. Foucault's power theory and Marx's historical materialism[M]. Social Science Front, 2019(11): 20-27.
[22] 劉臨達. 權力的四重維度——馬克思的權力理論研究[J]. 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研究, 2018(6): 168-173. LIU Linda. The Four Dimensions of Power: A Study of Marx’s Theory of Power[J]. Studies on Marxist Theory, 2018, 4(6): 168-173.
[23] 劉臨達. 權力符號的存在條件——象征交換理論與總體呈獻理論的理解差異[J]. 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9, 25(4): 34-40. LIU Linda. The existence condition of power symbol——The difference between symbolic exchange theory and general presentation theory[J]. Journ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2019, 25(4): 34-40.
[24] 鄒益民. 譜系學: 尼采與福柯對主體哲學的批判[J]. 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9, 27(2): 97-107. ZOU Yimin. Genealogy: Nietzsche and Foucault's criticism of subjective philosophy[J]. Journal of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2019: 27(2): 97-107.
[25] 劉臨達. 權力主體: 在福柯和J.巴特勒之間[J]. 世界哲學, 2019(5): 22-30. LIU Linda. Power Subject: Between Foucault and Judith Butler[J]. World Philosophy, 2019(5): 22-30.
[26]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592. Marx &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2[M].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9: 592.
Foucault's criticism at the dimension of "drama" of western power and its theoretical tradition
LIU Linda
(School of Marxism,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In the wes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ramatic" dimension of power has a long history. By describing the relevant situation of western psychiatric hospitals since modern times, Foucault reveals and criticizes the "dramatic treatment" of mental patients in hospitals, including the harm of "setting roles and scripts" at will, thus opening up a new way to understanding the form of modern western domination. The discourse analysis of Foucault's criticism contains the methodological elements of Structuralism, and its historical analysis implies its inheritance relationship with Marx's power theory. Interpreting Foucault's criticism at the dimension of power drama not only helps to understand the important theoretical links of many western modernity problems, but also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people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including China, to deal with the contemporary "hegemonic script", such as how to write the sublime narrative that "goals of the self and of others can be unified" in the process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how to write the political aesthetics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mmunity of a shared future, and the like.
Foucault; the dramatic dimension of power; Structuralism; historical trends; Marx
10.11817/j.issn. 1672-3104. 2021.03.012
B152
A
1672-3104(2021)03-0131-10
2020-06-13;
2020-11-22
中央高校科研啟動項目“權力理論在前馬克思時代的西方范式”(202044002)
劉臨達,山東威海人,法學博士,中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主要研究方向:政治哲學基礎理論,聯系郵箱:weilaizhengzailai@163.com
[編輯: 游玉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