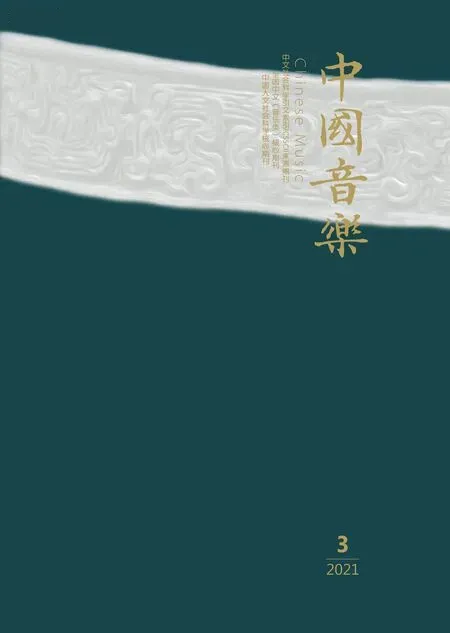西周“周樂”的文化基質(上)
○ 李方元
緒 言
有關西周的“周樂”,《詩經》《尚書》《左傳》和“三禮”等文獻的記載不少,據此自可管中窺豹,但若想深識,則需再做精研。歷史研究,總體觀照總有裨益,但基點仍離不開基本的史事。周初的三重史事——商周更代、姬周人當政和周公“制禮作樂”與西周“周樂”形成了三重的關聯。而需留意的是,此三事主角皆為“姬周”之人,這意味著理解西周“周樂”,“姬周”之人不可視之不見。
若此,言“商周更代”,便是說周革殷命,新朝繼起,歷史翻開又一頁,周朝與前商朝有了很大不同,這是從社會時間特殊蘊涵上說的。王國維曾就此發表過意見。他在《殷周制度論》中說:“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于殷、周之際。”①王國維著:《觀堂集林》卷一〇《殷周制度論》,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451;453頁。他是說,商周更代是中國歷史文化的一次根本轉折。言“姬周人當政”,是說隨姬周人開新,王朝更替,王朝主體族群亦隨之變更。自西周始,姬姓周人成為王朝“國族”,同時也成為“天下”的主導族群,這是說社會主體族群結構發生了變化。王國維所云更是一針見血,他指出:“殷、周間之大變革,自其表言之,不過一姓一家之興亡與都邑之移轉;自其里言之,則舊制度廢而新制度興,舊文化廢而新文化興。”②王國維著:《觀堂集林》卷一〇《殷周制度論》,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451;453頁。他想說的是,此時王朝更替的核心因素是族群,族群是那時制度興廢和文化傳遞的終極推手。言“周公制禮樂”,是說西周“周樂”是由攝政者周公姬旦為重建新王朝并實現其社會政治理想而做出的一項重大的制度努力,它為歷史轉折時期“周樂”的特定社會屬性定了調。作為周公成功的政治生涯的一部分,《尚書大傳》總結道:“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③伏勝撰,陳壽祺輯校:《尚書大傳》卷四《洛誥》,四部叢刊景清刻左海文集本。此處“制禮作樂”,是在周初王朝經過突發震蕩后開始走向穩定時所創設的一項政治措施,它既是周代“禮樂制度”的起點,也為西周“禮樂”注入了特定的社會內涵。可見,西周“周樂”的出現有時代政治、社會構成和文化歸屬等方面的深刻原因,而其中的“禮樂”架構則既是周初王朝制度革新的社會體現,也是姬周王朝社會和文化走向的最終定位和定性。按王國維氏所云,此即“舊制度廢而新制度興”的具體舉措,易言之即是西周政體中有關社會制度的重大歷史變革。在此之中,姬周人始終扮演著最為關鍵的角色,而西周“周樂”自然也就無法脫離開歷史的這一特定情境。
由此可以說,上述歷史事件在與整個王朝的社會互動中摶凝成“周樂”三重的特質,即時代性、族群性和制度性。也就是說,鑒于周朝的時代、族群和政治制度等社會基座的文化開新,西周“周樂”自然也同過去的商樂拉開了距離,而西周之初便是其開端,其基本的文化意涵也于此被大致框定。故可以如是說:西周“周樂”是以西周禮樂世界為中心和以姬周人音樂為主體的一種新興音樂。這樣的一種新興音樂,與它之前之后的音樂在其社會屬性和文化樣態方面的差別,即是本文關注的焦點。
一、周初姬周族群的己群認同
西周“周樂”研究,“時代”和“制度”備受關注,惟“族群”的因素長期無人問津,更無“姬周”名義下的文化考察和探究。本文的所做不同,擬從“姬周人”角度切入和考察,率先考察的是周初的一個重要社會現象——姬周人的己群認同。
“族群”現象,離不開族人及其認同。有關周初姬周人的“己群”認同,征諸載籍,有西土之人、詩樂記憶、周人尊夏和周人貶商等現象,頗值得重點關注。
1.西土之人。姬姓周人祖居中原以西,周初時多以“西土之人”自居,此事史籍所載不少。《尚書·牧誓》云:“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④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尚書正義》卷一一《牧誓》,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第182–183頁。《尚書·康誥》載:“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⑤阮元校刻:《尚書正義》卷一四《康誥》,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第203頁。又《逸周書·商誓解》謂:“昔在我西土,我其齊言,胥告商之百無罪,其維一夫。”⑥黃懷信、張懋镕、田旭東撰:《逸周書匯校集注》(修訂本)卷五《商誓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55頁。及《史記·周本紀》:“公季卒,子昌立,是為西伯。”⑦《史記》卷四《周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116頁。蔡模撰:《孟子集注》卷七《離婁上》“吾聞西伯善養老者”注云:“西伯,即文王也。紂命為西方諸侯之長,得專征伐,故稱西伯。”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200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在先周歷史上,姬周人有不少的徙居地,《詩》《尚書》《國語》《史記》等文獻都有記載,自母系先祖姜嫄至武王滅商前即有邰、戎狄地、豳、周、程、豐、鎬等地,這些居地無一例外皆在中原以“西”。“邰”,《詩經·大雅·生民》云:“誕后稷之穡……即有邰家室。”⑧阮元校刻:《毛詩正義》卷一七之一《大雅·生民》,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第530頁。《史記》張守節正義:“《括地志》云:‘故斄城一名武功城,在雍州武功縣西南二十二里,古邰國,后稷所封也。有后稷及姜嫄祠。’”⑨《史記》卷四《周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112;112–113;113頁。即今陜西武功縣。后來,先祖不窋“失其官而犇戎狄之間”,其居地按《史記》張守節正義引《括地志》所云:“不窋故城在慶州弘化縣南三里,即不窋在戎狄所居之城也。”⑩《史記》卷四《周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112;112–113;113頁。即今甘肅慶陽一帶。再后,公劉遷“豳”地,而其子慶節立國于“豳”,《史記》裴骃集解云:“徐廣曰:‘新平漆縣之東北有豳亭。’”張守節正義:“《括地志》云:‘豳州新平縣即漢漆縣,《詩》豳國,公劉所邑之地也。’”?《史記》卷四《周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112;112–113;113頁。即漢代扶風栒邑,今陜西旬邑縣西南。再往后,古公亶父率“私屬遂去豳,度漆、沮,踰梁山,止于岐下”,《史記》裴骃集解云:“徐廣曰:‘岐山在扶風美陽西北,其南有周原。’”?同注⑨,第114頁。即今陜西寶雞岐山縣。到了文王和武王,又遷都“豐”和“鎬”,皆今西安一帶。地理方位表明了周人先祖、先公、先王祖居之地皆中原(商朝核心區域)以西。姬周人勝殷后,以居地為分剖,自稱“西土之人”(與商人居地方位對舉),當離不開己群族性認同,“西土”之地理方位,便成為早期姬周族群凸顯自身最為鮮明的一種文化標識。在周初“天下”的坐標中,方域之地對應以天上之星宿,這種對應實有文化身份的區分和確認之意。故姬周人挑“方域”以明之,當為姬周“我群”認同的自我強化,用以區分和切割西土外之殷商等“他群”住民。地域表象背后,實族群意識使然。
2.詩樂記憶。“詩樂”“史詩”一類文化活動,歷來是族群辨識和己群認同的手段,古今無二。就《詩經》言,亦不乏大量的史詩性詩樂,如《商頌》中《那》《烈祖》《玄鳥》為商“史詩”,《大雅》《周頌》中則多姬周“史詩”。從內容看,這些“史詩”反映出商、周族群不同的生活和歷史,其文化的歸屬當列在商人或周人名下。這表明,“樂歌”確實是商、周族群用以維系其先祖記憶并達成其文化認同的有效載體。由此可知《商頌》即為商人歌樂,而《雅》《周頌》則為周人歌樂。下以“周樂”《大雅》三例示其大意。(1)《生民》云:“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即有邰家室。”《詩序》云:“尊祖也。后稷生于姜嫄,文、武之功起于后稷。”?同注⑧,第528、530頁。(2)《緜》云:“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詩序》云:“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阮元校刻:《毛詩正義》卷一六之二《大雅·緜》,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第509-510頁。(3)《文王》云:“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詩序》云:“文王受命作周也。”?阮元校刻:《毛詩正義》卷一六之一《大雅·文王》,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第502-504頁。這些姬周詩樂納入到西周“周樂”中,被子孫傳唱詠歌,后又結集于“詩文本”之中,終不斷亡。周人“詩樂”己族認同目的,就是讓姬周人子子孫孫長久記住其先祖們的艱辛創業史和歷史功績。這正是《禮記·檀弓》所云“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阮元校刻:《禮記正義》卷七《檀弓上》,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鄭玄注:“言其似禮樂之義。”第1281頁。之義。鄭玄甚至說此即“禮樂”之本義。?阮元校刻:《禮記正義》卷七《檀弓上》,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鄭玄注:“言其似禮樂之義。”第1281頁。這表明,“周樂”的核心價值反映了它與本族群的系連及族群文化使命的延續。故“詩樂記憶”背后,實族群意識和身份使然。
3.周人尊夏。周初周人尊夏,多自稱“夏人”,此非尋常。《周頌·時邁》中有載:“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阮元校刻:《毛詩正義》卷一九之二《周頌·時邁》,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第 589頁。《尚書·立政》亦云:“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阮元校刻:《尚書正義》卷一七《立政》,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第231頁。甚至《君奭》中見“有夏”“有周”并提:“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阮元校刻:《尚書正義》卷一六《君奭》,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第223–224頁。,等等。而且這種親“夏”之舉,還同周人斥“商”的做法形成對照。據文獻所載,在周人歷史記憶中,夏、周關系良好。《國語·周語上》載西周穆王時祭公謀父言:“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徐元誥撰:《國語集解》第一《周語上》(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3頁。又《史記·周本紀》云:“(棄)及為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棄為農師……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同注⑨。在周人的歷史記憶中,從堯至夏初是該族群最早的一段興盛歷史,周祖棄還親歷過夏禹治水,只是晚至夏太康之時,周人才隱沒于戎狄之地而遠離了主流社會。后在商代,周人的記憶是受制于商人。直至武王之世翦商立國后,商、周關系才根本逆轉,此后姬周人站到了歷史舞臺的中央。《尚書》中周人稱“周”為“夏”,或與他們早前的那段歷史有關。《康誥》云:“王若曰:‘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同注⑤。《立政》曰:“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同注?。這種夏、周互稱現象,為后來的學者如朱東潤、孫作云、葛志毅等人所注意。他們對此的解說,雖有血(姻)緣說、地緣說和政治說等不同,但多肯定夏、周二族存在某些特殊的關系。朱東潤氏看重周人之自稱,他在《詩三百篇探故》中說:“周部族與夏部族之血統關系,其中故不可盡考,然據周人所自言,則同為一部族。”?朱東潤著:《詩三百篇探故》,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65;67頁。他特別強調《周頌》中“時夏”(《時邁》)與“時周”(《般》)的對舉,稱此“為夏、周二名互稱之例”?朱東潤著:《詩三百篇探故》,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65;67頁。。孫作云氏則以為,西周王畿是夏人故地,周人居之;而夏、周又有通婚,故周初人常自稱夏人。?孫作云著:《說雅》,載《詩經與周代社會研究》,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6年,第332–342頁。而葛志毅以為,血緣說、地緣說有擬設推測、論之泛泛之嫌,其“周人稱夏”實多政治的考慮。?葛志毅著:《“周人尊夏”辨析》,《求是學刊》,1984年,第3期,第84–87頁。盡管學者具體的解說有不同,但相同的是并未否認夏人、周人的歷史聯系。其實,周人尊夏的原因不會是簡單或單一的,不僅可以有地緣、政治和姻緣的因素,亦不乏文化的因素等多重的歷史關聯。上古時代,人多遷徙而或有交集,不同族群或因遷徙為鄰,甚或居地上有所重疊,故因其地緣而姻緣或又有政治聯屬等情形亦非罕見,夏、周二族當類此。早在夏初,后稷即為禹臣,故夏、周人政治關系密切,《史記》稱“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可知周人步入黃帝系的“堯舜禹”集團始于唐堯之時。棄由堯“舉為農師”,舜時又“號為后稷”,并延續至夏初;后又有姻緣的關系,如文王娶有莘國夏人女子?《大雅·大明》:“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載文王娶太姒生武王之說。劉向撰:《列女傳》卷一《母儀傳·周室三母》云:“大姒者,文王之妃,武王之母,禹后有姒氏之女也。”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頁。“”,即“莘”。孫詒讓撰:《墨子閑詁》卷二《尚賢中》“伊摯,有莘氏女之私臣”引畢云:“莘,《漢書》作。”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58頁。等等。可見,周人“尊夏”原因當有多重。此外,文化方面的因素亦不可忽視。周初周人所稱之“夏”,即是用夏、周人可通的方言。揚雄《方言》稱:“秦晉之間,凡物壯大謂之嘏,或曰‘夏’。”釋詁云:“‘夏’大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物之壯大而愛偉之謂之‘夏’,周鄭之間謂之‘假’。”?錢繹撰集:《方言箋疏》卷一,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21、27頁。秦、晉,亦原夏之故土,而周初周人又復采夏、周二族都能聽懂的方音“夏”來作為己群之自稱,其中所反映出來的“夏”“周”關系,特別意味深長。今學人王力說:“其實,‘雅言’?筆者按:周人稱自己的宗周方言為“雅言”。阮元校刻:《論語注疏》卷七《述而》:“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何晏集解引鄭玄注云:“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后義全。”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第2482頁。就是‘夏言’。夏族最初在陜甘一帶。”?王力著:《漢語史稿》,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45頁。《康誥》將“我區夏”同“我西土”對舉,更凸顯夏、周二族關系的不同尋常。另據《逸周書·獻俘解》,武王克商后在獻俘祭典上,周“籥人”奏《大武》,亦奏《崇禹開生》。?黃懷信、張懋镕、田旭東撰:《逸周書匯校集注》(修訂本)卷四《世俘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28–429;428頁。劉師培指出:“‘崇禹’即夏禹,猶鯀稱崇伯也。‘開’即夏啟。《崇禹生開》當亦夏代樂舞。”?劉師培撰:《周書補正》卷二《世俘解第四十》,載《劉申叔遺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影印本,第744頁。在姬周族群建國的盛大禮典中,獻演“周樂”外的“夏樂”很不尋常,亦耐人尋味,至少可知這其中夏、周人關系的特殊一面,或可以說周人是諳熟夏文化的,亦愿接近和接受。《禮記·表記》中一段話即可佐證,其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后威,先賞而后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蠢而愚,喬而野,樸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禮,先罰而后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蔽。”?阮元校刻:《禮記正義》卷五四《表記》,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第1641–1642頁。對照此即知,在對待“鬼、神、人”的文化態度方面,周人都是近“夏”而遠“商”的。這表明,周人立國后在面對夏、商文化時,親近和選擇的多是前者。這在先秦文獻中不乏只例。如西周“周樂”多《九夏》之樂。陳旸和王應麟都以為《九夏》之名,夏代已有。陳旸《樂書·雅部·舞》云:“禹奏《九夏》而王道成。”?陳旸撰,張國強點校:《〈樂書〉點校》,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860頁。王應麟《玉海·音樂》云:“自禹立樂,名多以夏名,如《九夏》者。”?王應麟輯:《玉海》卷一〇六《音樂·周九夏》,揚州:廣陵書社,2003年,第1973頁。除此之外,《史記·周本紀》中還留有一段后稷“別姓姬氏”特殊的歷史記憶,此亦是姬周人想象中的有同夏人一樣的黃帝血緣:“周后稷,名棄。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為帝嚳元妃……及為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棄為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封棄于邰,號曰后稷,別姓姬氏。”?同注⑨,第111–112頁。“姓”,小徐本《說文·女部》云:“人所生也……因生以為姓。從女、生,生亦聲。”?徐鍇撰:《說文解字系傳》卷二四《女部》,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第247頁。鄭樵《通志·氏族》又云:“三代之前,姓氏分而為二,男子稱氏,婦人稱姓。”?鄭樵撰:《通志二十略》第一《氏族略》,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第1頁。可見,三代前之“氏”“姓”,跟男女性別有特殊的聯系,周祖棄得姓氏過程亦此。據《周本紀》:棄出生不言“姬”姓,成人后入帝堯集團,仍未言其姓,至舜時才“別姓姬氏”。司馬遷此記述(棄姜原所生,姜原帝嚳元妃)存二疑點:一、棄既為姜原所生,按三代之前“因生以為姓”(姓從母),當“姜”姓;二、姜原帝嚳元妃,嚳黃帝曾孫、玄囂孫。按《五帝本紀》,黃帝子玄囂姬姓,玄囂子蟜極(嚳父),“嚳祖本與黃帝同姬姓”?《史記》卷一《五帝本紀》司馬貞索隱,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9;46頁。,故棄本當“姬”姓。然《周本紀》未言棄生時何“姓”,只是到舜時才說賜其“別姓姬氏”。而此為“別姓”,非“正姓”;所云“姬氏”,亦非“姬姓”。此關乎三代前“姓”“氏”之別。太史公說棄“別姓姬氏”,或暗示棄原非“姬”姓。《禮記·大傳》云“系之以姓而弗別”鄭玄注“始祖為正姓,高祖為庶姓”?這里“始祖”“高祖”皆指男性祖先。阮元校刻:《儀禮》卷三〇《喪服》“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鄭玄注云:“始祖者,感神靈而生,若稷、契也。”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第1106頁。又《禮記》卷三二《喪服小記》“繼禰者為小宗。有五世而遷之宗,其繼高祖者也”鄭玄注:“小宗有四:或繼高祖,或繼曾祖,或繼祖,或繼禰,皆至五世則遷。”第1495頁。孔穎達疏云:“姓,正姓者,對氏族謂正姓也。”?阮元校刻:《禮記正義》卷三四《大傳》,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第1507頁。庶姓,即他姓非親者。《左傳·隱公十一年》“薛,庶姓也”杜預注:“庶姓,非周之同姓。”?阮元校刻:《春秋左傳正義》卷四《隱公十一年》,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第1735頁。又《詩經·伐木》“籩豆有踐,兄弟無遠”孔穎達疏:“庶姓,與王無親者。”?阮元校刻:《毛詩正義》卷九之三《小雅·伐木》,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第411–412頁。可見,“系之以姓”之部族內部,仍有“正庶”之分。“別姓”,或部族內再分建族姓。因之,舜時“別姓姬氏”意味著“姬”之姓族內部的再分。棄之“姬”,為“氏”非“姓”。按楊希枚“姓”“氏”有別說法,此或反映“姓族”“氏族”之別。?楊希枚:《論先秦姓族與氏族》,載《先秦文化史論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第197–210頁。以鄭樵說三代之前“男子稱氏,婦人稱姓”來理解,棄原為姜姓族群之男性首領,加入黃帝集團后,至舜時始“別姓姬氏”。至此棄進入姬姓集團,但稱“姬氏”,不稱“姬姓”。在整個“姬”之族性集團中,棄或只能是“氏族”,而非“姓族”,因為棄之“姓族”源頭為其母(姜原)之“姜”(“因生以為姓”)。促成棄姓氏轉變的關鍵在帝舜。他做了三件事:“封棄于邰;號曰后稷;別姓姬氏”。“封地”,即將原屬姜原國之邰易與其子?同注⑨,張守節正義云:“毛萇云:‘邰,姜螈國也,后稷所生。’”。,邰地歸屬關系變更。即“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杜預注云:“報之以土而命氏。”按孔穎達說是:“封之以國名,以為之氏。”?阮元校刻:《春秋左傳正義》卷四《隱公八年》,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第1733;1734頁。即“姓”與出生(母姓)有關,而“氏”則與“土”(封賜)有關。“名號”,舜時棄以“后稷”為號名世,為世人所知。而“別姓姬氏”,此舉最終意味著:“棄”所在族群之社會形態完成從母系到父系的轉換。自此,周“祖”(棄)因賜封而有其土,亦從“母系”轉從“父系”,并以“后稷”名號社會。此三事當基于棄加盟堯舜(黃帝嫡系)聯盟這一歷史事件。此處“姬氏”,似可理解為:舜或賜棄從其父(帝嚳)姓,即歸入“姬姓”血緣系統,從而脫離其母“姜姓”血緣系統。與此同時,為擺正同原黃帝“姬姓”系統的內部關系,故而棄只能“別姓”“姬氏”了。至此,棄之族群成為“姬姓”血緣集團中之一支——“姬氏”。此亦《周本紀》“棄為周,姓姬氏”裴骃集解引鄭玄《駁許慎〈五經異議〉》所云“姓者,所以統系百世,使不別也。氏者,所以別子孫之所出。故《世本》之篇,言姓則在上,言氏則在下也”?同注?,第46頁。之義。而孔穎達《左傳·隱公八年》“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疏認為“黃帝之后,別姓非一……后稷別姓姬,不是因黃帝姓也”?阮元校刻:《春秋左傳正義》卷四《隱公八年》,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第1733;1734頁。,同樣有此意思。司馬遷這里的“姬氏”之稱,也反映和彌合了三代“男子稱氏,婦人稱姓”的傳統。或可以認為,在舜之時,棄之族群以“別姓姬氏”而拉近了與黃帝一系的關系,也為靠近黃帝嫡親之姬姓“夏禹”多了層所謂的“血緣”關系。當然,“夏周”關系因資料闕佚瑣散,多為記憶之說,其歷史面目粗疏模糊,仍難識辨,至司馬遷《史記》亦此。不過,此中的蛛絲馬跡(如上述族群、地域、政治、文化等信息)不可輕易放過,它們于模糊中仍透出夏、周間的特殊聯系,于碎片中依稀可見史實之素地。“周人尊夏”背后,實周人與夏人剪不斷理還亂的關聯。
4.周人貶商。周初,與“周人尊夏”形成對照的,是周人貶商。武王伐紂后,姬周人竭力貶低商人。又因有三監之亂,周人對商人的警惕更是有增無減,進一步在政治、文化上同商人切割,分辨“我群”“他群”,擺脫其影響。這成為周初商、周關系的又一種寫照。對照《史記》中五帝、夏、商、周《本紀》文本,仍可見此意識之印記。在司馬遷相關敘事中,“五帝”“禹”之血脈同“商”“周”始祖之身世,出現了兩種相區別的“話語”模式:其一是“……父曰……”“……生……”“……之子(孫)”(包括兩個角度:“父”之角度或“子”之角度)。該敘事模式可稱之為“父子”模式。其“話語”模式。(見表1)

表1
據此可知,司馬遷講述的“五帝”(黃帝、顓頊、帝嚳、堯、舜)故事,從黃帝始,其血緣是父系的,并延續至“三代”之夏“禹”。
禹之后,《商本紀》《周本紀》繼續述說“商”“周”二祖。此時,司馬遷敘事出現了另一種話語模式:即“……生……”“……母曰……”“其母……”,此或可稱之為“母子”模式。(見表2)

表2
對照上二表,司馬遷講“五帝”,使用“父曰”一語,講帝嚳時溯其祖至黃帝,講帝舜時,也溯至黃帝子昌意,再對照夏禹看,司馬遷也一直追溯到元祖黃帝。然而在講商祖契及周祖棄時,其敘事中不見了“父曰”,卻出現“母曰”一語;同時,另“生”一語也源自“簡狄”或“姜原”之母系,而非“黃帝”“昌意”等父系了。在這里,司馬遷述說商、周之始祖,不同于“夏禹”或“五帝”,而別用了另一種話語模式——“母子”模式。
上述對周人的敘事(以及黃帝世系的整個敘述)或有周人歷史記憶的基礎(參見《大雅·生民》等),此處可留意兩點:其一,姬周人以為,血緣上周人跟商人一樣,屬“母子”系統,與“五帝”至“禹夏”一脈之“父子”系統不同。黃帝世系自黃帝始已是父系社會,而商、周族群至帝嚳時代仍處母系社會末期;其二,盡管司馬遷以“帝嚳之妃”將商、周二族扯上同黃帝一系的關系(或他信息來源就如此),但不僅時間上有疑點難以自洽,而其母系系統依舊無法回避。對此古人早有質疑之聲。司馬貞索隱引譙周云:“契生堯代,舜始舉之,必非嚳子。以其父微,故不著名。其母娀氏女,與宗婦三人浴于川,玄鳥遺卵,簡狄吞之,則簡狄非帝嚳次妃明也。”又引譙周以為:“‘棄,帝嚳之胄,其父亦不著’,與此記異也。”[51]《史記》卷三《殷本紀》,第91-92頁;《周本紀》卷四,第111頁。又,王逸《楚辭章句》不提帝嚳,而云:“姜嫄之生后稷,乃禋祀上帝于郊禖,而得其福。”[52]洪興祖撰:《楚辭補注·天問章句第三》,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112頁。可見,他們皆懷疑契、棄與帝嚳的關系。而司馬遷,于此不僅在血緣上閃爍其詞,更在姜原、簡狄為“嚳妃”和商、周二祖“非嚳出”二事上自相抵牾,難以圓通。至少,所謂的“感生”說是被商、周族人唱入了自己史詩的——《商頌》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53]阮元校刻:《毛詩正義》卷二〇之三《商頌·玄鳥》,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第622頁。,《魯頌》曰“赫赫姜嫄……是生后稷”[54]阮元校刻:《毛詩正義》卷二〇之二《魯頌·閟宮》,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第614頁。,但“嚳妃”說卻不見于族群記憶。這表明,倘若商、周二祖非嚳生難以更改,那么商人周人自然就非黃帝一系了。姬周人的糾結還不僅于此,還關涉商、周各自政權的合法性問題。商、周之際,權力更迭,但對周人來說血緣之合法性終究是一困擾。在姬周人眼中,商人,子姓,與黃帝一系關系并不明朗,而周人自己也一樣,雖有出母系(姜姓)之實,然畢竟還撈上個“別姓姬氏”的說法。由此,周人通過虞舜尤其是通過夏禹來拉近同黃帝一系的關系,以此從血緣上拉開與商人的距離,而使周王朝在血緣上具有合法性。此舉或乃姬周人政治考量之選項。可見,現實政治要求姬周人去重造一種歷史和重建一種歷史觀念,以重述族群自身的歷史和相關故事(亦包括夏、商)。《史記》敘事,或反映出一種歷史目的性,即周人得攀上黃帝這層關系(盡管或非直系)。或許這就出現了《史記》中姜原、簡狄與帝嚳間“元妃”“次妃”這層關系和又非“自嚳出”這種矛盾的記述,以及契和棄之歸屬于母系集團抑或父系集團這層不甚明朗的關系。更重要的是,要去完成姬周人尊夏、親夏而貶商的政治企求:即想說明盡管周人、商人血緣上同黃帝一系無關之事實,但又要放大周人“別姓姬氏”和歷史上同“夏”人的和睦關系以及血緣上與其有聯系的這層關系,以攀上黃帝之后嗣[55]王明珂《論攀附:近代炎黃子孫國族建構的古代基礎》一文,討論了黃帝作為華夏民族想象始祖和中國國族的歷史建構問題。文中他說:“黃帝出現在中國文獻記憶中,較可靠的時間大約是在戰國時期。西周金文中追美祖先,最多及于文王、武王;春秋時的齊國器叔尸鐘,才提到成湯、禹。戰國時齊國器,陳侯因咨簋,其中才出現‘高祖皇帝’之語。在成書于戰國至漢初的‘先秦文獻’中,黃帝逐漸廣泛被提及;其多元本質也在這些相關述事中出現、展開。起先,他在許多文獻中都是一古帝王,與伏羲、共工、神農、少皞等并舉,并未有各個氏族或部族共同祖先之意。然而到了漢初司馬遷寫《史記》時,黃帝已成為他心目中信史的第一個源始帝王,且為夏、商、周三代帝王家系的共同祖先了。”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3本3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發行,2002年,第587頁。。由此可知,“周人貶商”,亦實姬周我群意識及周初政治使然。
總起來說,周初姬周人的種種表現諸如西土之人、詩樂記憶、周人尊夏和周人貶商等,根本上說即是貶抑和排斥商人并強化己群認同,以及設法同黃帝一系相勾連的政治意圖。姬姓周人的“我群”意識及其如此歷史,當是理解西周“周樂”的一個基本前提。
二、從“三禮”禮樂資料看“周樂”
接下來考察的是有關西周“周樂”的歷史記述。周代典籍,“六經”地位顯要,“六經”中“禮”“樂”資料更是先秦社會重要現象的歷史記錄,而“禮”“樂”資料尤以“三禮”記錄更為集中[56]文本主以“三禮”的考察,而其他先秦文獻如《左傳》《國語》等中有關“周樂”的資料則大體不出“三禮”的范圍,故本文選擇以“三禮”中的“周樂”資料為重點研究對象。。盡管“三禮”成書或靠后,亦不及《左傳》等書時間坐標明晰,然其中或反倒可能隱含有西周的歷史信息[57]過常寶《制禮作樂與西周文獻的生成》以為:“《周禮》《儀禮》和《禮記》等,其文本的外在形態不能算是西周的,但其中部分內容,如儀式、理念、制度等,出現于或創始于西周時期,是西周制禮作樂的最為重要的成果。”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第124頁。,“樂名”或“詩樂”的記載更是如此。因此,本文再聚焦“三禮”中所載“樂名”和“引詩”,希望通過考察這宗“周樂”資料來揭示或被此前研究所忽略的一些歷史文化信息。下面是以書為單位對“三禮”中“周樂”的考察。
1.從《周禮》所載“樂名”看“周樂”
《周禮》一書,是制度角度的“禮樂”書寫,其中“周樂”的“樂名”可理解為曾作為“禮樂制度”的具體內容而施用于禮儀之中。《周禮》所載“周樂”樂名,可以周公“制禮作樂”為界分為前后兩組:一組是西周禮樂制度建立前已有的所謂“古樂”[58]此“古樂”借用《呂氏春秋·古樂》篇之語。該篇將《大武》歸入“古樂”之列。見陳奇猷校釋:《呂氏春秋校釋》,上海:學林出版社,1984年,第284-286頁。;一組是西周禮樂制度建立后姬周人用作為“禮樂”之樂。為簡明起見,茲列下表簡要示之。(見表3)

表3
前一組“周樂”為“六代之樂”,《周禮·大司樂》云:“以樂舞教國子:舞《云門》《大卷》《大咸》《大》《大夏》《大濩》《大武》。”鄭玄注云:“此周所存六代之樂。”又云:黃帝樂曰《云門》《大卷》。《大咸》,《咸池》,堯樂也。《大》,舜樂也。《大夏》,禹樂也。《大濩》,湯樂也。《大武》,武王樂也。[59]阮元校刻:《周禮注疏》卷二二《春官·大司樂》,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第787頁。這表明該組“周樂”基于歷時關聯和歷史積淀。其中《大武》最晚,見于周初。《逸周書·世俘解》有載:“籥人奏《武》。”[60]同注?,第428頁。陳逢衡《逸周書補注》云:“《武》,《大武》樂。”[61]陳逢衡撰:《逸周書補注》卷一〇《世俘解》,道光乙酉(1825)年修梅山館刊,中國書店影印本。該樂首見于武王伐紂后盛大獻俘祭祖儀式上。[62]李學勤認為,這次祭祀上帝、祖先的禮儀“《武》的演奏,可能即以此為初次”,即周朝之首演。見《〈世俘〉篇研究》,《史學月刊》,1988年,第2期,第6頁。依《呂氏春秋·古樂》所云,“六樂”為“古樂”,產生在周初周公“制禮作樂”之前[63]對此,古今有不同的看法,如《呂氏春秋》《今本竹書紀年》等說在此儀式之后。參見付林鵬著:《〈周頌·有瞽〉與周初樂制改革》,《古代文明》,2013年,第1期,第85–87頁。,后納入西周“禮樂制度”,成為“周樂”的組成部分。
后一組“周樂”包括了《九夏》和《騶虞》《貍首》《采薺》《采》《采蘩》以及《豳詩》《豳雅》《豳頌》凡十八部。(1)《九夏》,凡九部,《周禮·鐘師》云:“《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驁夏》。”鄭玄注云:“《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又引“杜子春云:‘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陔夏》,公出入奏《驁夏》。……《肆夏》《繁遏》《渠》,所謂《三夏》矣。’呂叔玉云:‘《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遏》,《執傹》也。《渠》,《思文》。”[64]阮元校刻:《周禮注疏》卷二四《春官·鐘師》,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第800頁。又,《儀禮·鄉飲酒禮》“乃合樂”鄭玄注云:“《大雅》《頌》為天子之樂”,賈公彥疏云:“《肆夏》《繁遏》《渠》之等是也。”[65]阮元校刻:《儀禮注疏》卷九《鄉飲酒禮》,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第986頁。阮元也認為:“《九夏》即在《頌》中。”又說:“所謂《夏》者,即《九夏》之義。”并引經書《周禮·大司樂》《禮記》之《文王世子》《內則》《仲尼燕居》《明堂位》《祭統》《樂記》等篇文例說明之。[66]阮元撰:《揅經室集·一集》卷一《釋頌》,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第20頁。據此,雖《九夏》樂之總體信息籍載闕佚,然據鄭、杜、呂、阮等學者所云,知《九夏》中之《三夏》皆《周頌》樂。(2)《騶虞》《貍首》《采薺》《采》《采蘩》。《樂師》云:“凡射,王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大夫以《采》為節,士以《采蘩》為節。”鄭玄注云:“《騶虞》《采》《采蘩》皆樂章名,在《國風·召南》。”[67]阮元校刻:《周禮注疏》卷二三《春官·樂師》,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第793頁。《鐘師》鄭司農注又云:“騶虞,神獸。”[68]阮元校刻:《周禮注疏》卷二四《春官·鐘師》,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第800頁。《墨子·三辯》認為:“周成王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騶虞》。”孫詒讓間詁亦云:“《詩·召南》有《騶虞》篇,蓋作于成王時。”[69]孫詒讓撰:《墨子間詁》卷一《三辯》,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第41–42頁。《貍首》,《儀禮·大射》鄭玄注云:“《貍首》,逸詩《曾孫》也。”[70]阮元校刻:《儀禮注疏》卷一八《大射》,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第1042頁。《漢書·司馬相如傳》顏師古注引郭璞曰:“《貍首》,逸《詩》篇名。”[71]班固撰:《漢書》卷五七上《司馬相如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574頁。另,《采薺》之樂,《樂師》注引鄭司農云:“《肆夏》《采薺》皆樂名,或曰皆逸《詩》。”[72]阮元校刻:《周禮注疏》卷二三《春官·樂師》,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第793頁。(3)《豳詩》《豳雅》《豳頌》。“豳”,地名,先周公劉遷居此地,其樂與周人有關。《籥章》說:《豳詩》用于“中春逆暑”“中秋迎寒”,《豳雅》用于“祈年于田祖”,以及《豳頌》用于“國祭蠟”之時。[73]阮元校刻:《周禮注疏》卷二四《春官·籥章》,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第801頁。
綜上可知,《周禮》中作為制度之“樂”有兩組,“六代樂舞”一組,包括自黃帝已降之先圣“古樂”,周《大武》樂列此中;另一組“周樂”,除《貍首》《采薺》為逸《詩》未曉來歷外,余皆姬周人之樂或與周人有關之樂。《九夏》,雖訓義不明,但其中的《三夏》知或為“周頌”一類。而《采》《采蘩》《騶虞》,皆《召南》樂歌。周、召之地,鄭玄《周南召南譜》云:“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今屬右扶風美陽縣。”孔穎達正義:“《孟子》云文王以百里而王,則周、召之地,共方百里,而皆名曰周,其召是周內之別名也。”[74]阮元校刻:《毛詩正義·周南召南譜》,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第264頁。鄭《譜》又云:文王典治南國,后作邑于豐,周、召成為了周公、召公采地,至武王伐紂定天下,六州者得二公之德尤純。[75]阮元校刻:《毛詩正義·周南召南譜》,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第264頁。可見,周南、召南是周、召以南連同“南國”江漢汝旁在內之地區,而二《南》樂歌即產生于這一區域,后又被姬周王公用于對該地區社會和文化的治理。而“豳樂”,則為周先公居地之樂。由此可知,此組“周樂”,皆同姬周人聯系密切(逸詩除外)。
2.從《儀禮》所載“樂名”看“周樂”
《儀禮》是儀式角度的“禮樂”記錄,重儀程與操演,為西周“禮儀”之實錄。《儀禮》十七篇中,有“周樂”樂名者四篇,為《鄉飲酒禮》《燕禮》《鄉射禮》和《大射儀》。此四篇所見“周樂”樂名二十有五,具體情形如下。(見表4)

表4
《儀禮》所見“周樂”有三類,多“詩樂”。一是見于《小雅》的十二篇,其中《鹿鳴》《四牡》《皇皇者華》《魚麗》《由庚》《南有嘉魚》六篇為“歌詩”,而《南陔》《白華》《華黍》《崇丘》《南山有臺》《由儀》六部為“笙詩”;二是見于《周南》的三篇:《關雎》《葛覃》《卷耳》,及見于《召南》的三篇:《鵲巢》《采蘩》《采》;三是另有《陔》《驁》《新宮》《勺》四樂,但不在“《詩》三百”內,或為當時“樂詩”。它們總體情況是:(1)《小雅》共十二篇。按鄭玄《小大雅詩譜》“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所云[77]阮元校刻:《儀禮注疏》卷九之一《小大雅譜》,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第401頁。,知當是姬周人“樂歌”。(2)《周南》和《召南》之六首。周、召二“南”之地,如上所述為岐山以南再向南輻射的南方地區,前文已提及與姬周人有特殊的聯系。(3)《陔》,即《陔夏》,《儀禮·鄉飲酒禮》鄭玄注云:“《陔》,《陔夏》也。”[78]阮元校刻:《儀禮注疏》卷一〇《鄉飲酒禮》,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第989頁。為《九夏》之一。(4)《驁》,即《驁夏》,亦《九夏》之一。《儀禮·大射》鄭玄注云:“《驁夏》亦樂章也,以鐘鼓奏之,其詩今亡。”[79]同注[70],第11044頁。《九夏》前文已有所及,或夏樂或周樂。(5)《新宮》,《儀禮·大射》“乃管《新宮》三終”鄭玄注云:“管,謂吹簜以播《新宮》之樂。其篇亡,其義未聞。”[80]阮元校刻:《儀禮注疏》卷一七《大射》,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第1034頁。又,《儀禮·燕禮》“下管《新宮》”鄭玄注云:“《新宮》,《小雅》逸篇也。”[81]阮元校刻:《儀禮注疏》卷一五《燕禮》,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第1025頁。或為《小雅》之樂。(6)《勺》,《周頌》樂。《儀禮·燕禮》“若舞,則《勺》”鄭玄注云:“《勺》,《頌》篇,告成《大武》之樂歌也。”[82]阮元校刻:《儀禮注疏》卷一五《燕禮》,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第1025頁。除此之外,還有《肆夏》,亦《九夏》之一;《騶虞》,逸《詩》,前文已考,此略。
總起來看,《儀禮》中所見“周樂”樂名,皆施用于儀式之樂。這些“樂名”包括有《小雅》之樂,二《南》之樂。它們或姬周人之樂,或因與姬周人有關而被姬周人使用之樂,后又錄在《風》詩中[83]其實自宋代始,人們對二《南》的性質便另有新說,視其為獨立的一類樂歌,而有別于其他的《風》詩。宋人蘇澈在《詩集傳》卷一三《鐘鼓》中始將《雅》《南》并立,各為一體,云:“《雅》,二雅也;《南》,二南也。”《續修四庫全書》,經部詩類,第5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20頁。王質《詩總聞》卷一上《南一》云:“南,樂歌名也。”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97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程大昌《考古編·詩論一》亦云:“蓋《南》《雅》《頌》,樂名也,若今樂曲之在某宮者也。”《詩論三》又云:“周之燕祭,自《云》《韶》等類兼采異代以外,其當代之樂,惟《南》《雅》《頌》三者,隨事配用……”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12頁。后清人顧炎武著(黃汝城集釋)《日知錄》卷三《四詩》中明確說:“《周南》《召南》,《南》也,非《風》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30頁。崔述《讀風偶識》卷一《通論二南》亦云:“《南》者,乃詩之一體。……蓋其體本起于南方,北人效之,故名以《南》。……自武王之世下逮東周,其詩而《雅》也,則列之于《雅》;《風》也,則列之于《風》;《南》也,則列之于《南》;如是而已。”北京:中華書局,叢書集成初編本,1985年,第12頁。可見,二《南》確有與一般《風》詩不同的特別之處。;另有逸詩,或也為《雅》《頌》篇什。此外,幾無他樂。
3.從《禮記》所載“樂名”看“周樂”
《禮記》所載,是從多個維度對“周禮”涵義的解說,包括釋“樂”在內。該書所見“周樂”樂名較前二書要多。筆者翻檢和通觀諸“樂名”后注意到兩種情況:一是直接記錄其“樂名”,二是摘引《詩》樂之章句。接下來先梳理前者,其總匯如下。(見表5)

表5
此表載“周樂”樂名24部(首),總體情形如下:
對照《周禮》《儀禮》知,《禮記》所載“周樂”樂名同于上二書者凡12部,即《咸池》《韶》《大夏》《大武》《清廟》《肆夏》《勺》《采薺》《采》《采繁》《騶虞》《貍首》。其中“六代樂舞”4部,闕黃帝《云門》和商《大濩》二樂;另有《周頌》3部:《清廟》《肆夏》(依呂叔玉說)《勺》;《召南》3部:《采》《采繁》《騶虞》;逸詩2部:《采薺》《貍首》(以上前文已考)。余12部(首)略考如后:
(1)《大章》,或《大卷》樂。《禮記·樂記》“《大章》,章之也”鄭玄注云:“堯樂名也,言堯德章明也,《周禮》闕之,或作《大卷》。”[84]阮元校刻:《禮記正義》卷三八《樂記》,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第1534頁。(2)《南風》,舜樂。《禮記·樂記》“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鄭玄注云:“夔欲舜與天下之君共此樂也。南風,長養之風也……夔,舜時典樂者也。”[85]阮元校刻:《禮記正義》卷三八《樂記》,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第1534頁。《尚書·舜典》曰:“夔,命汝典樂……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86]阮元校刻:《尚書正義》卷三《舜典》,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第131頁。(3)《武宿夜》,周初武王樂。《禮記·祭統》云:“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于祼,聲莫重于升歌,舞莫重于《武宿夜》,此周道也。”鄭玄注:“《武宿夜》,武曲名也。”孔穎達疏引皇侃曰:“師說《書》傳云:武王伐紂,至于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因名焉。”[87]阮元校刻:《禮記正義》卷四九《祭統》,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第1604頁。(4)《象》,其舞樂有二,“武王”之《象》舞和“文王”之《象》舞。[88]此說見賈海生著:《周公所制樂舞通考·象舞與酌舞》,載《周代禮樂文明實證》,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135–142頁。《文王世子》“下管《象》”鄭玄注云:“《象》,周武王伐紂之樂也。”[89]阮元校刻:《禮記正義》卷二〇《文王世子》,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第1410頁。又《明堂位》鄭玄注云:“《象》謂《周頌·武》也,以管播之。”[90]阮元校刻:《禮記正義》卷三一《明堂位》,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第1489頁。而《維清·詩序》“奏《象》舞也”陳奐傳疏謂:“《象》,文王樂,象文王之武功曰《象》。”[91]陳奐撰:《詩毛氏傳疏》卷二六《周頌·維清》,《續修四庫全書》,經部詩類,第70冊,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第396頁。(5)《宵雅》,“小雅”樂章。《禮記·學記》:“《宵雅》肄三,官其始也。”鄭玄注:“宵之言小也;肄,習也。習《小雅》之三,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92]阮元校刻:《禮記正義》卷三六《學記》,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第1522頁。(6)《雍》,《周頌》樂。《論語·八佾》云:“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馬融注云:“《雍》,《周頌·臣工》篇名。天子祭于宗廟,歌之以徹祭。”[93]阮元校刻:《論語注疏》卷三《八佾》,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第2465頁。(7)《振羽》,《周頌》樂。《禮記·仲尼燕居》“客出以《雍》,徹以《振羽》”鄭玄注:“《雍》《振羽》,皆樂章也。”孔穎達疏:“《振羽》即《振鷺》詩,亦樂章名也。”[94]阮元校刻:《禮記正義》卷五〇《仲尼燕居》,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第1614頁。又《周頌·振鷺》云:“振鷺于飛,于彼西雍。”孔穎達疏云:“美威儀之人臣而助祭王廟亦得其宜也。”[95]阮元校刻:《毛詩正義》卷一九之三《周頌·振鷺》,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第594頁。(8)《南》,南土之樂。《禮記·文王世子》“胥鼓《南》”鄭玄注:“《南》,南夷之樂也。胥掌以六樂之會,正舞位。旄人教夷樂,則以鼓節之。《詩》云:‘以《雅》以《南》,以籥不僭。’”[96]阮元校刻:《禮記正義》卷二〇《文王世子》,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第1405頁。(9)《昧》和(10)《任》,東夷之樂和南蠻之樂。《詩經·鼓鐘》毛傳云:“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南》。”[97]阮元校刻:《毛詩正義》卷一三之二《小雅·鐘鼓》,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第467頁。《孝經鉤命決》亦云:“東夷之樂曰《昧》,持矛助時生。南夷之樂曰《任》,持弓助時養。”[98]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輯:《緯書集成·孝經鉤命決》,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012頁。孔穎達疏《明堂位》云:“周公德廣,非唯用四代之樂,亦為蠻夷所歸,故賜奏蠻夷之樂于庭也。……蠻夷則唯與二方也。”[99]阮元校刻:《禮記正義》卷三一《明堂位》,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第1489頁。(11)《萬》和(12)《籥》,皆樂舞名。《禮記·檀弓下》載:“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100]阮元校刻:《禮記正義》卷一〇《檀弓下》,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第1310頁。春秋《三傳》亦載此事。舊注說《萬》是干舞,《籥》是籥舞。[101]阮元校刻:《春秋公羊傳注疏》卷一五《宣公八年》,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第2281頁。似釋之以形態。不過二舞另有一面,即:《萬》是商舞,《籥》則周舞。《萬》,甲文中已見,為商樂無疑[102]參見王維堤著:《萬舞考》,載《中華文史論叢》,1985年,第四輯,第179–194頁;陳致著:《“萬(萬)舞”與“庸奏”:殷人祭祀樂舞與〈詩〉中三頌》,載《中華文史論叢》,2008年,第九十二輯,第35–64頁。。在春秋戰國,用《萬》舞者僅魯、宋、楚、齊諸國[103]文獻中所載《萬》舞,僅見于侯國之域,如魯國“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左傳·隱公五年》),又“壬午,猶繹,《萬》入去《籥》”(《公羊傳·宣公八年》),又“將禘于襄公,《萬》者二人。其眾《萬》于季氏”(《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又楚國“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為館于其宮側而振《萬》焉”(《莊公二十八年》),又齊國“昔者齊康公興樂《萬》,《萬》人不可衣短褐,不可食糠糟”(《墨子·非樂上》);而《詩經》亦有三詩見《萬》舞:《邶風·簡兮》“簡兮簡兮,方將《萬》舞”“碩人俁俁,公庭萬舞”;《商頌·那》“庸鼓有斁,萬舞有奕”;《魯頌·閟宮》“萬舞洋洋,孝孫有慶”。又有商樂《桑林》,亦見于宋國“宋公享晉侯于楚丘,請以《桑林》”(《左傳·襄公十年》)。所有這些《萬》舞和商舞,全都見于原東土的商奄等地,而非在周王畿和周王室中。,原皆商土之地,而無關于王畿和王室“周禮”用樂。“籥”舞,則“周禮”之樂。據《周禮·籥師》“籥師,掌教國之舞羽龡籥”賈公彥疏:“此籥師掌文舞,故教羽籥。若武舞,則教干戚也。”[104]阮元校刻:《周禮注疏》卷二四《春官·籥師》,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第801頁。《禮記·文王世子》“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于東序”孔穎達疏云:“籥,笛也。籥聲出于中,冬則萬物藏于中。‘云羽籥,籥舞,象文也。’”[105]同注[89],第1405;1404頁。又“籥師學弋”鄭玄注云:“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106]同注[89],第1405;1404頁。而《小雅·賓之初筵》“籥舞笙鼓,樂既和奏”毛傳云:“秉籥而舞,與笙鼓相應。”[107]阮元校刻:《毛詩正義》卷一四之三《小雅·賓之初筵》,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第485頁。《小雅·鼓鐘》:“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108]阮元校刻:《毛詩正義》卷一三之二《小雅·鐘鼓》,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第467頁。同時,孔穎達還明確指出周王室籥師等樂官皆與《萬》舞無涉,在《邶風·簡兮序》疏中他稱:“《周禮》掌舞之官有舞師、籥師、旄人、韎師也。《舞師》云‘凡野舞,則皆教之’,不教國子。下傳曰‘教國子弟’,則非舞師也。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則不教《萬》舞。經言‘公庭《萬》舞’,則非籥師也。旄人、韎師皆教夷樂,非《萬》舞,又不教國子。”[109]阮元校刻:《毛詩正義》卷二之三《邶風·簡兮》,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第308頁。可見,《籥》舞周“學政”所用,王室設“籥師”掌教,為“國子”必備之樂,故《籥》舞當周舞無疑,而并無商舞《萬》,《萬》亦與國子無關。籥師不教《萬》舞,國子亦不習《萬》舞,則清楚說明周樂中無《萬》舞,而《萬》亦本非周樂。故可認為,上述魯國宣公“事大廟”而“《萬》入去《籥》”混用二舞,非意在形式,而在乎其政治象征。按周禮,卿(公子遂)死,宣公當不“繹”祭。然宣公做出兩個異常的舉動:一是“猶繹”;二是“《萬》入去《籥》”。《公羊傳》說此舉針對的是公子遂:“仲遂卒于垂。仲遂者何?公子遂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為貶?為弒子赤貶。”[110]同注 [101],第2280頁。這里一連問了三個“為什么”,魯國卿之死,被如此低調處理,使其銷聲匿跡,本已令人費解,然宣公卻繼以“繹祭”,還做出匪夷所思的“《萬》入去《籥》”之舉。這其中隱含了兩層意思:“遂死而繹”,貶其國卿地位并羞辱之,也是對其公子(國子)地位的否定;而“入《萬》去《籥》”,則去除其姬周符碼,從族屬上否定,暗示剝奪其姬周身份,將其剔除姬周族群之列(國子本不習《萬》舞商樂)。所以,《谷梁傳》顯白地說:“此公子也,其曰仲,何也?疏之也。何為疏之也?是不卒者也。不疏,則無用見其不卒也。”[111]阮元校刻:《春秋谷梁傳注疏》卷一二《宣公八年》,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第2413頁。“疏”,即疏離、洗滌、清除之義。孔子聞其事后對其非禮行為提出嚴厲的批評:“‘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112]同注 [100]。這也意味著,孔子明確表明周禮用商樂即是“非禮”之舉。我們知道,《公羊》《谷梁》二傳之可貴在于它們能闡發《春秋》的微言大義,而孔子也是從“復禮”的立場發聲的。由此可以說,《公羊》《谷梁》二傳從另一角度揭示了《萬》舞為商舞這一歷史的性質。
總體看,《禮記》所錄“周樂”樂名,亦“六樂”和“詩樂”兩類。“六樂”中不見《云門》《大濩》二舞,而另有《武宿夜》《象》《籥》《萬》4樂。“詩樂”則有《周頌》之《清廟》《肆夏》《勺》3部,《小雅》之《宵雅》1部,及《召南》之《采》《采繁》《騶虞》3部,余有逸詩之《采薺》《貍首》2部。由此可見,《禮記》所見“周樂”之樂名,亦主以姬周人之樂。此外,“六樂”獨無商樂《大濩》亦值得關注,而商樂《萬》則是以“非禮”的方式出現和提到的,當不在西周“禮樂制度”的“周樂”之列。
再看《禮記》引《詩》,所錄凡100見,包括風、雅、頌三體:引《風》詩23首(次),有周南、邶、鄘、衛、鄭、齊、秦、曹、豳九國風詩;引《雅》詩63首(次),有《小雅》27首(次),《大雅》36首(次);引《頌》詩10首(次):有《周頌》6首(次),《商頌》4首(次)。另有引逸詩4首。“引詩”所出《詩經》篇名和所出《禮記》篇目情形如下。(見表6)

表6
據上表,《禮記》“引詩”100首(次)。總體看,此“引詩”最多者為《雅》詩(《大雅》更多于《小雅》),其次《風》詩,再次《頌》詩,末為逸詩;見于《禮記》49篇中之15篇:《檀弓下》《禮運》《禮器》《大傳》《樂記》《祭義》《經解》《孔子閑居》《坊記》《中庸》《表記》《緇衣》《大學》《射義》《聘義》。“引詩”(首、次)最多之前5篇依次是:《緇衣》(22)、《表記》(18)、《中庸》(17)、《坊記》(14)和《大學》(12)。余諸篇引詩除《孔子閑居》(4)、《樂記》(3)、《祭義》(2)、《射義》(2)外,所剩6篇皆各1首。《禮記》所引“詩句”無“詩篇”名[113]作者按:上表所見“篇名”,只是筆者查實后為閱讀和研究方便所加,而個別地方不乏亦有異文的情形。,重在斷章取“義”[114]春秋時期,“詩樂”之“斷章取義”已是比較流行的一種現象了,如《左傳·襄公二十八年》就說:“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
對照《禮記》中的“樂名”與“引詩”,知這兩種涉樂資料“語境”有別。凡錄“樂名”者,通常伴有儀式用樂的情形,而“引詩”則不然。試觀前者文例:
《禮記·文王世子》:“天子視學,大昕鼓征,所以警眾也。眾至,然后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圣焉……始之養也。適東序……反,登歌《清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眾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115]同注[89]。
《祭統》:“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116]同注[87],第1607頁。
《仲尼燕居》:“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117]同注[94]。
此處“樂名”皆伴有儀式活動,也就是說,這些“樂名”體現的是“周樂”在具體儀式中使用的情況,皆以“禮儀”為中心。
而引《詩》情況有不同。引《詩》時的具體語境,基本與“禮典”或儀式無關。其所引“辭句”關注的是其現實隱喻而非“禮典”活動本身,且為“說理”之用,重“辭章”之“義理”。試觀以下用例:
《檀弓下》:“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報于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118]同注 [100],第1315頁。
《坊記》:“子云:‘利祿,先死者而后生者,則民不偝;先亡者而后存者,則民可以托。’《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以此坊民,民猶偝死而號無告。”[119]阮元校刻:《禮記正義》卷五一《坊記》,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第1619頁。
《中庸》:“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120]阮元校刻:《禮記正義》卷五二《中庸》,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第1627頁。
由此可知,引《詩》皆為“說理”之用,主要出現在無儀式背景的說理場合,以詩之“辭義”來增強其說理分量,故焦點不在儀式“音聲”,而在文辭之“義理”。《禮記》中,《緇衣》《表記》《中庸》《坊記》《大學》5篇“引詩”的總量高達全部“引詩”的八成,其典型句式是:“子曰-詩曰”,即孔子言說在先,引《詩》辭句在后,重“辭章-義理”義,而非“儀式-樂章”的禮儀本身。可見,“樂名”與“引詩”這兩種用樂的現象完全不同,分別對應于不同的“禮儀”活動,不可同日而語。“引詩”的出現,或當為周代“禮樂”儀典中“樂”“儀”分離后出現的一種“禮樂”現象。
需再提及的是,《禮記》中有“樂名”者13篇,有引《詩》者16篇,二者同見于一篇的情況不多,僅《禮器》《樂記》《射義》和《檀弓下》四篇,所涉“引詩”亦不多,僅7首。分析此四篇可知,前三篇“引詩”皆引《雅》詩和《頌》詩[121]具體為:《禮器》引《大雅·文王有聲》1首;《樂記》引《大雅》之《皇矣》《板》和《周頌·有瞽》3首;《射義》為《小雅·賓之初筵》1首(另有逸詩1首)。。《雅》詩和《頌》詩本“禮儀”之樂,而此時則已無關于儀式。如《禮器》:“禮,時為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詩》云:‘匪革其猶,聿追來孝。’(《大雅·文王有聲》)”[122]阮元校刻:《禮記正義》卷二三《禮器》,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第1431頁。又如《樂記》:“子夏對曰:……德音之謂樂。《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大雅·皇矣》)此之謂也。”[123]阮元校刻:《禮記正義》卷三九《樂記》,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第1540頁。而同時,此三篇所載“樂名”包括《夏》《武》(“六樂”類)和《采》《采繁》(“詩樂”類)[124]具體為:《禮器》之《肆夏》1部;《樂記》之《南風》《大章》《咸池》《韶》《夏》《武》《貍首》《騶虞》8部,以及《射義》之《騶虞》《貍首》《采》和《采繁》4部。。必須指出的是,盡管這些原本為儀式之用樂,但在此文本語境中則已遠離儀式操演,而重在義理了。如《禮器》:“一獻質,三獻文,五獻察,七獻神。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臘,四海九州之美味也……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重禮也。”[125]阮元校刻:《禮記正義》卷二四《禮器》,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第1442頁。又《射義》:“《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者,樂循法也;《采繁》者,樂不失職也。”[126]阮元校刻:《禮記正義》卷六二《射義》,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第1686、1687頁。另一篇《檀弓下》,所引《邶風·谷風》1首,直接為“子曰-詩曰”典型句式,更無儀式的語境。其云:“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127]同注 [100],第1315頁。由此可知,“樂名”、引《詩》同見一篇的這四篇,雖錄有“樂名”,但其實已無儀式語境,而同于引《詩》,皆強調其義,重在釋樂之意義了。從性質看,此四篇因無儀式性,故仍可劃歸于強調意義的引《詩》的這一類。除此四篇外,《禮記》其余有涉樂文字的各篇,或只錄“樂名”,或只有“引詩”,互不疊交;載錄“樂名”的9篇無“引詩”,“語境”同儀式有關;而載錄“引詩”的其他12篇則無“樂名”,語境亦與“儀式”無關,尤多“子曰-詩曰”之典型句式。可謂二者涇渭分明,似兩股道上跑的車,各行其道。“引詩”類中有“子曰”一語表明,其文所載樂事及其語境的時限范圍,最早也只能是在春秋中晚期。反過來,記錄“樂名”而無“子曰-詩曰”的篇章,所記樂事的時間或早于有“子曰-詩曰”的篇章,甚至可能反映的是西周時的狀況。上文提到的“樂名”、引《詩》同見一篇的這四篇,亦當為晚出之作,從與儀式無關的情況看,即是出自于“樂”“儀”分離后的“禮樂”現象。就此看,《禮記》文本中有關“周樂”的資料,仍然可視之為與儀式有關的“樂名”和與儀式無關的“引詩”這兩大類。
以此看來,《禮記》49篇的涉“樂”文字,其實隱含了“樂名”和“引詩”的兩種用樂系統,它們分別對應兩種意義上的“禮樂”活動,或亦聯系著前后兩個不同的“禮樂”歷史階段:前者依存于西周禮樂儀式的操演活動,而后者則為春秋已降“禮樂崩壞”以來出現的“樂-儀”分離且強調義理的說理活動。也可以認為:最晚在春秋早中期,西周“禮樂”出現了一種“樂”“儀”疏離的新情況以及相應的“以樂說理”的新的禮樂活動。其后,隨著孔子“刪詩”、教育和文化下移、“詩文本”流傳以及將“詩樂”用于教育活動等新起現象的出現,反過來它們又加速促成著“詩樂”與儀式的分離。尤其“詩文本”在儀式外的教育天地和諸侯國外交中被大量使用,則有了無“儀式”背景的“引詩”活動和以“儀式”為背景的用“樂”活動這兩種禮儀活動同時并存的歷史事實。而專講“義理”的無儀式之樂尤其是如“子曰-詩曰”這類經典的句式也被記錄在像今本《禮記》(《周禮》《儀禮》無)一類的歷史文獻的相關篇章中了。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