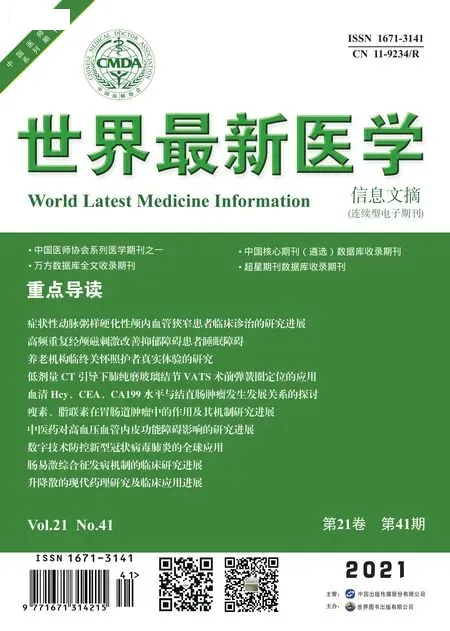新疆地區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獻腎移植總結
米克熱衣·艾孜買提,熱衣漢·西里甫,劉健,宋光魯,劉珍,帕合努爾·孜亞丁
(新疆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腎臟疾病中心,新疆 烏魯木齊 830054)
0 引言
2002年《腎臟病/透析的臨床實踐指南》中正式提出慢性腎臟病的定義,腎功能永久性喪失的狀態定義為第5個階段,即測量或計算的腎小球濾過率永久性低于15mL/min。在世界范圍內,由于人口老齡化和慢性非傳染性疾病(尤其是糖尿病和高血壓)的流行,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終末期腎衰竭患者數量都在快速增長。預測表明,到2030年,全球依靠透析治療的終末期腎病患者人數可能超過200萬[1]。國外數據顯示每年有4.1%的慢性腎臟病進展為終末期腎衰竭[2]。治療終末期腎衰竭最好手段是異體腎移植術[3],而開展移植受到器官不足的掣肘,故大力開展公民器官捐獻成為關鍵。英國2018年腎移植等待系統顯示,2009年等待患者7190,2010年下降至7183,而2018年更是下降至5011。這項調查顯示腎移植數量逐年增加,2017年至2018年腎移植器官捐獻占到66%,活體移植占到28%[4]。上述數據顯示公民死亡后器官捐獻成為解決器官短期的重要手段。
國外文獻報道,在心[5]、肺[6]、肝[7]移植中,種族匹配具有更好的結果。Locke等報道了黑人捐獻者(DBD供者),其黑人接受者移植物存活率更好,白種人接受后其移植物失敗的風險有所增加[8]。但Bhavini 等人報道種族匹配cox回歸模型中都沒有顯著差異,非白種人腎移植受者的預后較差[9]。國外文獻報道相互有所矛盾,且無目前暫無統一觀點。新疆是個多民族居住區,既往數據顯示新疆地區活體腎移植漢族與少數民族移植腎存活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10],但活體移植均為本民族間移植,不存在跨越種族間移植。因宗教信仰及生活習慣問題,目前新疆地區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獻者大部分均為漢族,故接受不同民族間腎臟移植是否存在種族群體之間的生物學差異,是否影響移植腎存活需要進一步探討。在我國器官捐獻移植是在2010年全面推廣的,我中心在2013年開展了新疆第一例器官捐獻移植,故本次研究回顧性收集2013年至2019年我中心器官捐獻移植臨床資料,了解新疆地區接受器官捐獻移植臨床數據,以及不同民族間腎移植是否存在差異,為今后臨床工作提供幫助。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新疆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2013年1月至2019年12月)接受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獻供腎移植患者,術前均簽署器官移植知情同意書,并在中國人體器官分配與共享計算機系統中登記。剔除1例行胰腺腎聯合移植,剔除1例少數民族接受少數民族器官捐獻。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獻腎移植患者供45例,其中19例為少數民族,26例為漢族;男性35例,女性10例。年齡14~59歲,平均(39.89±9.43)歲。44例為首次移植,二次腎移植1例。
捐獻者臨床資料:24例器官捐獻者均完成標準無償器官捐獻知情同意程序后施行供腎獲取,并在人體器官分配與共享計算機系上確認接收。28例為DCD,14例為DBD,3例為DBCD,年齡 8~63 歲,平均 (41.22±11.59)歲。
1.2 方法
需要收集受者術前臨床資料:①一般情況包括:性別、年齡、體重、血壓、術前透析時間;②實驗室指標:血紅蛋白、血白蛋白、血尿素氮、血肌酐、空腹血糖;③與供體匹配情況:淋巴毒試、HLA配型情況、PRA等;④器官捐獻者資料:死亡原因、性別、年齡等。術后并發癥隨訪:術后感染、急性排斥反應、移植腎功能延遲恢復等是否存在差異。Kaplan-Meier法比較兩組間人、腎生存情況;經SPSS 18.0統計軟件進行數據處理,P<0.05為差異有顯著性意義。
2 結果
2.1 術前一般資料
45例腎移植受者資料分析,隨訪時間在1至6年,少數民族組與漢族組患者術前一般情況比較,計量資料行均數比較;分類變量用卡方檢驗。差距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2.2 術后臨床資料分析
腎移植術后平均隨訪時間為44月(范圍8月至81月),圍手術期間無死亡,遠期隨訪中2例均因重癥肺部感染帶功死亡(少數民族與漢族各1例)。5例移植腎切除:1例出現超急性排斥反應術中移植腎切除(為漢族);3例因急性排斥反應行內科保守治療效果差,出現移植腎破裂后切除(少數民族1例、漢族2例);2例出現吻合口血管破裂出血,均行2次手術后再次吻合口破裂出血行移植腎切除。圍術期期間無患者死亡。
腎移植術后免疫:① 激素+ MMF +他克莫司(37例,少數民族為13例、漢族為24例);②激素+MMF+環孢素(4例,少數民族為3例、漢族為1例);2組間無統計學意義。腎移植術后發生排斥反應8例,發生率為17.7%,其中3例為少數民族,5例為漢族,無統計學意義。術中開放血流后出現1例超急性排斥反應(為漢族),術中移植腎摘除;1例發生加速性排斥反應(為漢族),病理結果提示:腎小球腫脹,腎小球囊腔狹窄,球內毛細血管局灶淤血,部分區域伴壞死,血栓形成,球囊內及周圍見少許中性粒細胞浸潤,間質及小管未見明顯異常。治療上給予即復寧(兔抗人胸腺細胞球蛋白) 5mg/kg/d,靜點5天,同時血漿置換,激素及丙種球蛋白靜點等處理后成功逆轉,移植腎功能恢復正常。3例移植腎內科保守治療無效,移植腎破裂,行移植腎切除(1例為少數民族,2例為漢族)。其余3例給予激素沖擊或聯合ATG靜點并調整免疫抑制劑等治療后逆轉。術后出現肺部感染8例,少數民族與漢族各4例,發生率為17.77%;泌尿道感染9例,6例為少數民族,3例為漢族發生率為20%;切口感染3例,2例為少數民族,1例為漢族,發生率為6.66%;腹腔內感染4例少數民族與漢族各2例,發生率為8.88%;2組間術后出現感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出現感染后給予抗生素,并根據情況調整免疫抑制劑后感染均被控制。腎移植術后發生移植腎功能延遲恢復9例,4例為少數民族,5例為漢族,發生率為20%,2組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見表2。

表1 兩組患者術前一般情況比較

表2 兩組之間術后情況比較
2.3 術后移植腎生存分析
采用Kaplan-Meier法分析少數民族組與漢族組間腎生存曲線無統計學意義(P=0.861)。1 年、3年移植人、腎生存率分別為98%、95%和82%、80%。接受器官捐獻腎移植術后腎功能存活患者隨訪平均血肌酐值及eGFR(MDRD公式)隨訪如圖1。

圖1 接受器官捐獻患者術后平均Scr及eGFR隨訪統計表
3 討論
Opelz 和 Terasaki 2位學者在1977年首次分開定義腎移植后人存活率、腎存活率,將2個結果獨立分析發現種族差異。這些作者表明雖然白種人和黑種人腎移植術后人存活率相似,但移植后3年腎移植存活率相差10% (黑人為25%,白人為35%,P<0.0001)[11]。在1983年美國阿拉巴馬大學伯明翰大學發表了黑人和白人移植腎存活率相差16%(黑人57%,白人73%P=0.002))[12]。1991年Kasiske等人在人、腎分開隨訪中發現移植腎存活有種族差異,范圍在7%至20%,但是人存活率無顯著差異[13]。2011年Keith發表了腎移植在供體種族配對分析,排斥反應以及慢性移植腎腎病是造成黑人移植腎失敗的原因,但是在腎移植后人死亡率(帶功死亡)在不同種族中無差異[14]。還有許多文獻顯示移植腎功喪失與種族有關,而黑人與高加索間的死亡率相似[15-16]。我國公民去世器官捐獻自 2010年開始大力開展,并且目前已經獲得了良好的效果[17-18]。新疆地區少數民族是由蒙古及高加索血統的混合[19],維吾爾族終末期腎衰竭患者與健康維吾爾族人群HLA基因多態性差異無統計學意義[20],但無少數民族與漢族HLA基因多態性對比研究。目前已有新疆地區不同民族間活體移植結果對比,但無跨越種族間移植結果報道。在新疆地區器官捐獻腎移植在我中心為首例開展,且占新疆地區器官捐獻腎移植的95%。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獻中漢族捐獻者23例,少數民族捐獻者1例,漢族捐獻者占絕大部分。考慮與新疆地區少數民族死亡后土葬,而漢族火葬,二者生活習慣及民族文化差異有關。通過術前一般臨床資料分析,少數民族HLA錯配率高于漢族,但無統計學異常。術前2組間一般情況比較均無統計學異常。
在本次研究中2組間術后并發癥也均不存在統計學差異。移植腎功能延遲恢復(DGF)暫無公認統一定義,本次研究中將術后1周內需要透析治療或術后1周血肌酐未下降至400umol/L以下定義為DGF。DGF主要潛在機制與缺血/再灌注損傷有關,不僅影響移植腎長期存活而且更易在術后前6個月出現急性排斥反應[21],DCD與DBD相比發生DGF可能性更大[22]。國內器官捐獻腎移植DGF發生率在6.6%至27%[23-24],本次研究中DGF發生率為20%,少數民族組與漢族組發生率相近,但相對于活體移植明顯偏高。
4 結論
在少數民族與漢族組間行移植腎生存分析顯示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考慮與術前一般情況及術后并發癥差異無統計學意義有關。本次研究數據收集均在我院完成,能獲得原始數據;且手術團隊、護理團隊一致。因此結果相對穩定劑可靠。在術前一般情況及手術條件一致情況下,研究顯示少數民族與漢族腎移植術后人存活率、腎存活率無統計學意義。偏倚與不足:為單中心回顧性分析,且例數偏少;由于例數偏少,影響兩組間生存因素無法比較;期望今后研究能擴大例數,并進行長期隨訪,為不同民族間腎移植提供臨床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