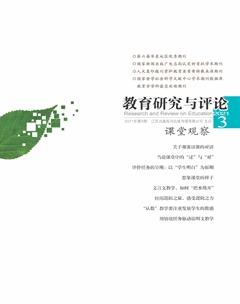于構思中見經典
儲雯
摘要:多元解讀在一定意義上成就了《溪鰻》的經典性。從文本的敘事策略角度展開分析:空白策略,敘述空白然而并不空洞,折射無限的可能;閑筆策略,閑筆頻出卻又不覺瑣碎,彰顯無盡的意蘊;縱橫策略,線索縱橫實則裹藏歷史,容納豐富的內涵。
關鍵詞:《溪鰻》;敘事策略;空白策略;閑筆策略;縱橫策略
20世紀80年代初的中國現當代文壇,各種思潮此起彼伏,創作空間大大擴展。與廣大創作者關注主題新穎不同,重返文壇的林斤瀾是“相對較多地考慮到表現方式的作家”,王蒙曾稱其為“一位有著獨特的藝術追求的短篇小說家”。
入選蘇教版高中語文選修教材《短篇小說選讀》的《溪鰻》是林斤瀾這一時期小說創作的高峰。小說講述的是一個外號為“溪鰻”的女子在新時期重新修建自己的店鋪,并請袁相舟為她的店鋪題匾的故事。敘述中,林斤瀾穿插了溪鰻在20世紀50—80年代之間的各種奇聞逸事:能治頭疼腦熱的神秘能力,與鎮長撲朔迷離的關系,一個突如其來的孩子,“割尾巴”運動縫隙中艱難支撐的店鋪……這些故事的敘述大多模糊不清,似是而非,往往讓人產生諸多困惑。但仔細思索,讀者又總能做出屬于自己的個性解讀。這種多元解讀在一定意義上成就了這篇小說的經典性。為什么會有這樣的效果呢?筆者在備課時嘗試從文本的敘事策略角度展開分析。
一、空白策略,折射無限的可能
林斤瀾曾在《論短篇小說》中說:“情節的線索是明顯的線索,最容易拴住人。但,也會把復雜的生活、變幻的心理、閃爍的感覺給拴死了。 有時候,寧肯打碎情節,切斷情節,淡化情節直到成心不要情節。”因此,他在創作《溪鰻》時有意識地在關鍵處中斷情節,刻意打破情節線索的連貫性。小說對溪鰻的身世及其相關的稀奇傳說,都只是一筆帶過。而袁相舟到縣城求學的幾年,溪鰻究竟有無生過孩子,小說結尾突然出現的那個七八歲的女孩子是誰,倒霉鎮長從在水產公司當副職到受驚嚇癱瘓在溪灘上的這段時間究竟發生了什么事情……這些最能吊起讀者胃口的蹊蹺之處,本該詳細鋪陳,林斤瀾卻反其道而行,刻意輕描淡寫,虛虛帶過,甚至不著一字,留下了無盡的空白。
關鍵情節中斷的同時,林斤瀾還將主人公的情感態度隱藏在云霧蒸騰的矮凳橋溪灘里。最能體現主人公情感態度的是她的心理描寫。但在整篇小說中,主人公溪鰻的心理狀態卻是完全隱匿的。面對鎮長的“非分之想”,溪鰻是心甘情愿還是被迫接受,或是借機尋求謀生的依托?鎮長癱瘓后,家人沒有管他,溪鰻為何會將鎮長接回家照顧?是出于知恩圖報,還是道德的同情,或是情感的延續?主人公心理描寫的隱匿切斷了讀者借著人物的心理變化去感知故事發展的可能性,人物的心理狀態完全寄托于讀者的聯想。
這些關鍵性情節的中斷與主人公情感的隱匿,使文本成為一個開放的、可活動的客體。情節不再是唯一的要素,讀者與小說人物也產生無盡的隔膜。有限的敘事空間因為空白而折射出無限的可能性。所有可能的情節與目的都要讀者自己補充,誘導著讀者在失落和困惑中運用自己的歷史、社會、倫理等各種閱讀經驗去思索小說空白背后的意味,從而使小說解讀走向多元化。
二、閑筆策略,彰顯無盡的意蘊
善用閑筆是林斤瀾小說創作的又一大特色。汪曾祺也曾在《林斤瀾的矮凳橋》中說過:“斤瀾常于無話處死乞白賴地說,說了許多閑篇,許多廢話;而到了有話(有事、有情節)的地方,三言兩語。”這體現了林斤瀾獨特的創作方式——“無話則長”。
《溪鰻》的主要故事情節應該發生在溪鰻和鎮長這兩個人物身上,但林斤瀾卻將大量筆墨用在情節之外。
閑筆之一是開頭的環境描寫。小說開頭,林斤瀾為讀者描繪了一幅小商品經濟蓬勃發展的畫面。在這幅畫面中,矮凳橋紐扣市場與密集的飲食店交錯在一起,字里行間都散發著煙火氣息。看似閑來之筆,細細想來,整條街上熱氣蒸騰的場景其實折射出改革開放之后小商品經濟的發展對矮凳橋日常生活的影響。矮凳橋從來不是一個與世隔絕的地方,多年來矮凳橋受到各種政治經濟風潮的影響,溪鰻也從來沒有置身其外。而在矮凳橋的紐扣市場被打開后,溪鰻的小酒家改建擴大、重新隆重地找人題匾不正是新時代背景下的應時之舉嗎?
閑筆之二是鰻魚的分類。林斤瀾在小說中為讀者詳細介紹了鰻魚的分類、鰻魚的外形與傳說,這些內容似乎與主情節沒什么關系。實際上,主人公“溪鰻”的外號就從此處得來。鰻魚 “仿佛蛇形”,有著“興風作浪的傳說”。將一個女子形容成鰻魚,自然不是出于好意。而后文中,鎮上人將溪鰻視為俊俏婀娜、具有妖氣的異類,剛好與前面看似閑筆的鰻魚種類描寫呼應。
閑筆之三是小說通過袁相舟的眼睛向讀者呈現了矮凳橋溪灘神秘朦朧的風情,并將種類豐富、色香味俱全的魚類小食一次次推送到讀者眼前。也正是在這個過程中,袁相舟詩興大發,聯想到白居易的《花非花》,吟出“鰻非鰻,魚非魚,來非來,去非去,今日春夢非春時,但愿朝云長相處”的詩句。這看似不經意間吟出的詩句實則應和了整篇小說迷霧般的氛圍,彰顯出“人非人,魚非魚”的無法言明的意蘊。
綜上而論,小說中的閑筆實則是林斤瀾有意為之。表面上看,這些閑筆云山霧罩,為讀者制造了各種閱讀阻礙;事實上,這些閑筆各有所指,或指向環境,或指向人物,或指向主題。在這種虛實錯位中,讀者反復咀嚼,讓小說走向經典。
三、縱橫策略,容納豐富的內涵
傳統小說喜用客觀時序反映生活實際,在清楚地將一個故事的來龍去脈按照時序呈現出來的同時,也將故事的敘事鏈直接暴露在讀者面前。林斤瀾在談到“短篇的心性”時說,短篇小說的取材“在生活的長河里汲取一個浪花一個斷面”,而這“斷面”也有縱橫之分:橫斷面反映典型生活的寬度;縱斷面呈現歷史的深度。
從時序上看,《溪鰻》寫女主人公溪鰻在政策放開、小店擴大經營后請袁相舟為她的小酒家取店名這個時間片段的故事,同時交織了溪鰻在過去三十年間錯綜復雜的人生糾葛。這種時空的交錯讓小說在短篇的格局里,容納極為豐富的內涵。溪鰻不是孤立的個體,而是歷史大潮流中的一朵浪花。在時間這條軸線上,林斤瀾進行“有限度的變形”,將時間進行自由剪切、拼接和組合,在歷時和共時中呈現出自己對這段歷史的思考。
溪鰻的幾個重要命運節點都與歷史浪潮緊密相連。一出生就被父母拋棄在溪灘,這其實正是20世紀30年代苦難的中國人民的命運寫照;作為“白點”的溪鰻魚食鋪子在“割資本主義尾巴”浪潮的縫隙中艱難維持,這與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密切相關;溪鰻與鎮長之間最原始與質樸的情感,因“文革”語境引人非議;溪鰻的“魚非魚小酒家”的擴張是在改革開放后小商品經濟政策的推動下進行的……幾個節點將溪鰻在困境中的本真自然、堅韌樂觀、有情有義展露無遺;但換個角度,面對歷史這只大手的操縱,溪鰻只是被動地、無奈地接受。小說結尾,出現一個同樣被拋棄在溪灘的小姑娘,這個與溪鰻有著相同命運起點的女孩將會怎樣成長,是否會延續溪鰻多舛的命運呢?歷史的鐘聲在此刻再次敲響,但此刻的時間已不再是當初,此刻的溪鰻也非故人。原本閉合的悲劇環在新時代終將被打破。溪鰻最后嚅嚅,說小女孩“趕上了好日子”。確實,時代發生巨變,溪鰻近30年來雖然容貌并未大變,可經歷歲月滄桑的她已不再是那個逆來順受的弱女子,從溪灘上抱回來的小女孩在溪鰻的照料下,未來也終將不同。
《溪鰻》敘述空白但并不空洞,閑筆頻出卻又不覺瑣碎,線索縱橫實則裹藏歷史;看似結構隨意,如同袁相舟微醺時的狀態,情思所到之處即是筆墨揮灑之時,實則是林斤瀾的“苦心經營”。《溪鰻》的經典性就在這獨特的構思中悄然顯現。
參考文獻:
[1] 汪政,曉華.無邊的文學[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
[2] 王蒙.王蒙文集(第七卷)[M].北京:華藝出版社,1993.
[3] 林斤瀾.論短篇小說[J].當代作家評論,2007(1).
[4] 汪曾祺.汪曾祺全集(四)[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
[5] 林斤瀾.十年矮凳[M].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2001.
[6] 林斤瀾.矮凳橋下的時光:林斤瀾散文經典[M].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2010.
[7] 程德培.小說家的世界[M].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