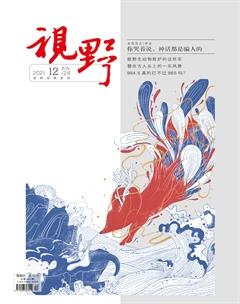從不想挖蟲草說起

時瀟含
我們一路上順著318國道行駛,20輛車的車隊浩浩蕩蕩,速度也不算快。用領隊的話說,就是天險早已變通途。然而,在我們這些長期在城市道路上循規蹈矩的人看來,崎嶇的山路、轟鳴的貨柜車、路邊懸崖上嶙峋的怪石,無一不張牙舞爪地向我們撲面而來。
我們的司機阿根是個沉默寡言的藏族人,只有在我們到了他家理塘的時候,他才開始侃侃而談。當然,在拉薩的兩頓大酒之后,我們也發現他的話還是很多的。
阿根說,現在正是藏民們開始上山挖蟲草的季節,只要看到山腳下停了車子,山上扎了帳篷,那就是挖蟲草的藏民們。
每年挖蟲草的時間并不長,也就短短的兩個月,可是藏民一年的大部分收入,靠的就是這兩個月的努力。
這些山頭,每個都被分給了不同的村子,山腳下有人看守,只有村民才能上山。資源好的村子,這兩個月一家能挖四五十萬的蟲草。然而大部分的村子一個人也就能挖個兩三萬塊錢的蟲草,所以有的家庭規模很大,畢竟一個人就代表了一個勞動力。
每到七八月份,那就是藏民們最富裕的時候,大家每天載歌載舞。聽到這里的時候,我不禁表示十分羨慕。一年只要工作兩個月,而且還是沒有本錢的買賣,這也太適合我這種懶人了。
阿根卻說作為藏民他覺得一點也不好,他說什么也不愿意他老婆和孩子去挖蟲草。他說他之前也去挖過一段時間蟲草,每天都要爬上五六千米的高山,一整天跪在地上,臉上被太陽曬到掉皮。有的時候一天也只能找到幾根大小不一的蟲草。
我們去帕隆藏布江的源頭任龍巴冰川的時候,冰川腳下藏族村莊里開車帶我們上去的小伙子,很驕傲地向我展示了他前一天用一天辛勞換來的十根蟲草,還給我看他抖音里拍的家里的七十多頭牦牛。他說現在的蟲草個頭不大,一根也就能賣三四十塊錢。
進冰川的時候,我們車隊被村長攔了下來,他說我們一定要坐著他們的車進去,因為這里的山上全是蟲草,怕我們的車橫沖直撞破壞了草場。
那條通往冰川的路高低起伏不斷,要不是緊緊地拉著馬韁繩都害怕會從馬背上翻下去。
替我牽著馬的小伙子一路上唉聲嘆氣,說一天到晚走這條路,循環往復走得他腳都痛了。
同行的人說,要是把這條路修好一點,那以后可以開車進來,不管是游客還是村民都更輕松。小伙子毫不猶豫地說:“那可不行,路修好了誰還來騎馬?”
我們聽了都笑了起來,夸贊他頭腦靈光。
這也是阿根覺得挖蟲草不好的原因。蟲草對于藏人,就像這條破爛的路對于這兩個村子的人一樣。他們只要守著現有的資源,每天都能分到數目并不大的錢,能維持他們的生活,卻也很艱苦。但是讓他們離開他們所擁有的東西,比如說修好這條道路,讓交通便利起來,其中所包含的變化和威脅,又是他們不愿意面對的。
阿根說挖蟲草是會上癮的,雖然又苦又累,但是錢來得快,來得毫無成本,對于許多除了放牧沒有別的收入來源的家庭來說,只要挖了一年蟲草,就年年都想挖,主要收入就依靠著它。而且挖蟲草的收入不菲,足夠讓他們活下去,那么他們也無須費心謀求別的出路了。
可是蟲草的資源在減少,各種關于人工蟲草的傳聞與日俱增,或者說有一天蟲草從神壇上跌落下來,價格不再高昂,那么這些家庭就別無生路了。
我們去然烏湖的路上,專門另辟蹊徑繞路經過了一個小村子。看到我們的車隊,村子里面沖出來了四個小孩子,很高興地朝我們跑過來。他們都拖著長長的鼻涕,他們要不就任由鼻涕流淌到衣服上,要不就用手把鼻涕在黑黑紅紅的小臉上抹勻、風干。
他們雖然不會說幾句漢話,但是大家都意會了他們是想找我們要吃的。我們靠著阿根和他們交流。阿根說他小時候和這些小孩子的區別也大不了多少,衣服穿得單薄又破舊,唯一的區別是他舅舅堅持他們一定要去讀書。
他爸爸聽說家里的孩子都要去讀書之后很生氣,問他們:“那山上的牛怎么辦?誰去放牧?”但是他舅舅堅持他們一定都要受教育,成績很差也沒有關系,倒數第一也沒有關系,就算考不上大學也沒有關系。受過教育和沒有受過教育就是不一樣的,能讀多少就讀多少,能多看一點就多看一點。
聽到這些話的時候,我心里又盤旋起一個疑問,我問阿根:“那男女受教育程度一樣嗎?”
阿根無奈地笑笑,說現在在家里女生還更受重視些,反正在他家里女兒想要什么就給什么,但是連好臉色都不會給兒子。
話雖如此,路上我們途徑了一個異常窮困的村子,那個村子里是一妻多夫制。經過的時候大家紛紛打趣要不就留在這里,讓幾個丈夫一起賺錢養著自己。但是其實,所謂的一妻多夫只是貧窮和不平等的產物。
許多家庭有好幾個男孩,不是每個人都娶得起妻子,就干脆一家兄弟一同娶一個,妻子要照顧家庭,還要生養后代。
越是對于這些貧窮的地方,教育越是唯一的出路,金錢對于他們來說,其實并不是真正能改變生活的東西。阿根說他有一個朋友,年紀也不過三十,大字不識,連名字都寫不清楚,但是家里有三四百頭牦牛。
要知道,一頭成年牦牛值兩萬塊錢,他那黑壓壓的一群牛可以說是一座金山。有一次他想去成都買一輛車,從家里拿了十幾萬現金帶在身上。從理塘到成都路程漫長又艱險,別人勸他把錢存進銀行,等到買車的時候再取出來就好了。
結果他把錢存進去了之后反而悶悶不樂,一路上坐立難安,擔心銀行會把錢拿走,再也不還給他。等買了車回到理塘之后,他又開始日復一日地放牛。他沒有對錢的概念,不知道放牛是為了什么,只知道他的父輩就是這樣日復一日地放牛的,所以他也要把這些牛這樣年復一年地放下去。
看著窗外倏忽而過的村莊,我問阿根,藏民們的生活看起來非常簡單,可以說維持最基本的自給自足問題不大,那么挖了蟲草、養了牦牛和綿羊之后,這些錢花到哪里去呢?
畢竟除了拉薩之外,大多數村子并沒有什么娛樂方式,看起來也沒有能花錢的地方。
他說對于大多數家庭來說,最大的開銷是看病。對于很多老人來說,總是覺得有什么病痛忍一忍、忍一忍就過去了,可是忍得久了,小病變成大病,最后人財兩空。
而且高原上的條件比平原艱苦,人的身體要承受很多風吹日曬和各種嚴苛的自然條件。
高原上的冷風,能吹進骨頭里。這里最常見的病是肺病。這與污染無關,與稀薄的空氣和極端的天氣有關。哪怕得了一場小感冒,在高原上都久久不能痊愈,只有去了成都才能完全恢復。
在大昭寺外面的八廓街,我們隨意地亂逛,看到了很多老人拿著轉經筒一同走來。我們一開始以為是那天有什么特殊的宗教集會,結果走了兩圈之后發現,街上的人一點都沒有減少,還是有那么多人拿著轉經筒繞著圈子。我們這才反應過來,原來他們是在繞行大昭寺。
我問阿根說,他們要在這里轉多久。我的原意是,他們每天幾點開始轉,轉到幾點回家工作或者休息。
阿根理解錯了我的意思。他說:“有的人轉了一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