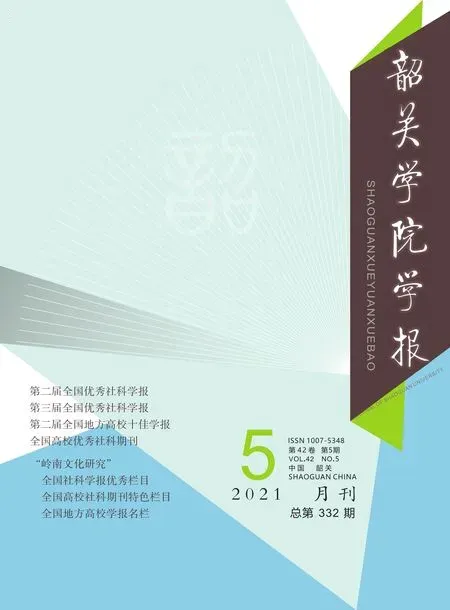《紅樓十二講》的情感教育旨趣與沉浸式閱讀
魏 國
(韶關學院 政法學院,廣東 韶關 512005)
《紅樓夢》作為我國四大名著之一,可謂家喻戶曉,紅學研究源流不斷,更由于影視傳媒廣泛提高了其知識傳播的有效性,形成了讀者加觀眾的疊加的擴展,并且早已進入大學人文學院的殿堂,歷久彌新,是東方文化對世界文化做出的卓越貢獻,就像西方對待莎士比亞的戲劇一樣,我們倡導對《紅樓夢》的閱讀是一個學習舉措,也是國學內容的一部分。在專業領域有紅學研究,而為了塑造人的全面性,應該在做情感人的意義上,普及這個通識教育。
一、契合通識課的情感目標
(一)情教旨趣
在教務處相關部門制定的申請表上,設有10多個模塊,一門通識課的申請是要進入模塊設定的,而《紅樓十二講》所屬模塊為語言與文化,作為通識課不需要自主添加了,這個定位是非常準確的。《紅樓夢》是漢語語言文學的驕傲,其經典性自不必言。《紅樓夢》原本卷末標有“情榜”,可見,作者就是要標榜情感[1]576。周汝昌先生認為曹雪芹當得起“創教”一說,是與釋迦牟尼、耶穌和穆罕默德一樣的人物[2]222。他認為這個教就是“情教”,曹雪芹自然被視為情教的教主了,這是非常有見地的[2]83。也就是說,《紅樓夢》是情感教育的極好讀本。應該說,《紅樓十二講》是跟著經典走的,在教師為這門通識課制定課程標準的過程中,就涉及三方面的目標設定,即知識、能力和情感。其中,情感目標的設定是值得一提的,可以稱之為“紅樓十二講”的情感三條:(1)培養學生理性內斂地動用自己的情感能力,節制情之濫觴;(2)培養學生精鶩八極、心游萬仞的自由馳騁能力,在思維、語言和外物之間想像,駕馭語言與外物通感的能力;(3)使學生樹立人文主義世界觀,與物換星移,人世流轉在一起,全面的世界觀既是科學的,又是人文的。情感三條是提綱挈領式的。
(二)預設閱讀
《紅樓十二講》以線下教學為主,然而,它預設具有《紅樓夢》情趣的共同體,建立微信群,這個情趣具體指向了閱讀,與時下的各種讀書會相當,側重閱讀與情感之間的因果,當強調《紅樓夢》是情教的《圣經》,是情感教育的極好讀本時,這還處于文本的靜態形式,而只有通過閱讀,才能進入文本的動態形式,建立《紅樓夢》情趣共同體及其學生個體與文本的互動關系。從廣義的閱讀上說,包括各種紙質版,電子版,有聲版和影視劇及其相關資料。關于“情感教育”,就教育學而言,業經形成了情感教育理論,比如:斯卡特金、羅杰斯和蘇霍姆林斯基都是這方面卓有建樹的理論家,相關理論可謂相當豐富。然而,在教師的領悟之中,這些理論并不高于人情練達這個源頭活水。對于情感教育的生成,從靜態形式來看,首先預設在文本之中,而從動態形式來看,是預設在閱讀之中的,預設閱讀是“紅樓十二講”的前提。由于當下的快餐文化,浮躁導致了淺閱讀、碎片化閱讀現象的存在。2019年的一項調查顯示,《紅樓夢》被網友稱為讀不下去的名著,王蒙先生感嘆:“連這點子累勁兒都沒有,那我們的精神生活就完蛋了。《紅樓夢》都讀不下去是讀書人的恥辱。”[3]通識課作為選修課,具有開放程度,文科的學生可選修,理工科的學生也可選修。如果大學生同學喜歡過《紅樓夢》,也有過一定的閱讀經驗,那么,還是有必要選修此通識課。即使以前沒有興趣,也可通過選修培養興趣。
二、專題化教學
《紅樓十二講》是以教學展開的,與預設閱讀相對接,教師進行教學設計。講,從教師發出,有一定的主導性,講什么取決于教師的理念,服膺情感教育的目標。那么,這個是否需要細化指標體系,以便執行可操作呢,其實是內蘊在專題之中的,這樣,專題化本身就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從前期教學成果來看,擴展到十二個專題,屬于人物論的范疇,而這個也是比較傳統的紅學領域,更能傳播和被受眾領略。這十二個專題的人物選取與專題擬定是同時進行的。就專題化教學而言,《紅樓十二講》追求的是專題化與人物論的結合,人物是專題的人物,而專題是人物的專題。其實也不過是講人物的一個方面,往往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為此,十二個人物專題都融入了這門通識課的課程標準之中,從中可以管中窺豹,見表1。

表1 “紅樓十二講”課程標準局部
以上有關教學內容的部分,有以下幾個問題值得思考。
(一)凡選即有代表性
如果我們承認《紅樓夢》是一部現實主義力作,那么,它的確增加了“人口”[4]。換句話說,可以納入《紅樓十二講》的紅樓人物太多了,“紅樓十二講”只講十二個人物。一是人物代表性的問題。其中,涉及的人物有核心大三角:寶玉、黛玉和寶釵,寶玉不用說,釵黛在金陵十二釵正冊之中,而外圍的湘云、李紈、鳳姐、可卿、巧姐、襲人、齡官、卍兒和小紅等九人,其中湘云、李紈、鳳姐、可卿和巧姐也在正冊之中,代表性當無疑議,而襲人是進入副冊的人物,剩下的齡官和小紅也因其鮮活的人物形象和個性傾向性而入選,卍兒因自身的特殊性而入選。另外,如果擴展十二釵為一百零八釵,齡官、小紅和卍兒也是榜上有名的人物[1]54-56。二是大關目(情節的安排和構思)的參照。就是說,大體上參照了《紅樓夢》第五回中的十二釵正、副、又副冊上的判詞以及《紅樓夢》曲中的判曲。一般認為,第五回是全書的大關目,情榜次之。而在專題中,除了可卿之外,都以選取人物名字標明。
(二)點上掘進
通過表1可知,《紅樓十二講》涉及的專題其實只講一個側面,一個片面。《紅樓十二講》專題是在筆者拙作《寶玉的愛物觀及其語境分析》[5]和《湘云論陰陽的文化心理詮釋》[6]基礎上擴展至十二個的。大部分是攻其一點,不及其余,可能相對含混一點的是卍兒,既是符號,又是人,然而,講民俗意義也是講人。寶釵的遮體現了其為人處事的特點,黛玉的檸檬精是說其性格之酸,李紈的鑰匙之問似乎在說她就是沒有再嫁的祥林嫂,而鳳姐起句也并非不會作詩,可卿尤物兼美,襲乃釵副,巧姐跟誰派對,齡官癡情到畫薔,小紅繞口奶奶令被調走了。總之,《紅樓十二講》仍是人物論。
(三)情感集結的過程
專題化是情感教育的載體,而情感教育是內蘊于專題化之中的。十二講對應的其實是十二個人,而在十二個專題中,還以講清寶玉、黛玉和寶釵這個大三角為核心,其他九人的加入基本上能滿足對《紅樓夢》的情感考察,而這十二個專題是關乎情感的,其中,巧姐旁及到鳳姐,而卍兒旁及到寶玉。之所以說基本上能滿足,是因為情感共性的存在,不僅指愛情,還在于影子說的存在,所謂“晴有林風,襲乃釵副”[7],那么,這個專題給襲人,就略去了晴雯,這也是壓縮的結果,還考慮到晴雯在愛物觀這個專題里也等于說到了。類似的以此類推。其次,用典型性來說明被講的都是典型,邏輯地,就會暗示不講的好像都不典型,顯然,這么認為是不準確的,然而,講的如果不典型還真不行,就是說,典型是必須的。個別專題標題明示的情感因素雖然沒那么多,比如:卍兒的民俗意義,但在實際的講解中,是少不了一個“情”字的,可以說,十二個專題是無情不立的。《紅樓十二講》是十二個人物在各自的情感方向上的集結,特別是,大部分表現為向寶玉這個核心的集結,是團團圍住的,除了自愛,釵黛云角逐自不必說,可襲紅介入,鳳若合符節,余者不論。或者是寶玉情不情所指涉的,比如:齡官就非常明顯,卍兒不甚明顯。然而,寶玉跟濫情人是有區別的,因而,要區別對待。而寶玉的愛物觀之所以列為第一個專題,是因為愛物觀承載著情之大略,起到了理統性情的規約意義,是情為自身之理的開展。
如果說,人物選取是分,情感集結就是合。在此分分合合之中,產生的量的規定恰恰是數字十二,也是推動著專題化的關鍵議程。周汝昌先生曾說《紅樓夢》整部書的十二乘九為結構法,贊嘆是結構奇跡[1]87。他著有《紅樓十二層》,王蒙先生也說到關于數字崇拜的情況,認為十二里有天機,有東方神秘主義,他有一篇的標題就是“ 12+12·女孩子與小尼姑”[8]。可以說,對十二這個數字的崇拜是成立的。
(四)慎用代入感
如今,流行一個詞叫代入感,是指讀者、觀眾或玩家“出現的”一種自己代替了小說、影視劇或游戲中人物而產生的身臨其境的感覺。《紅樓夢》是一部偉大的作品,其代入感是很強的。多年以后,當人們對87版《紅樓夢》電視劇一些演員的命運進行考察時,不禁感嘆,陳曉旭早年就覺得自己是黛玉,而張莉的命運也有些像寶釵,其他演員都有類似情緒。當然,演員不投入演戲也不是好演員,但代入感太強了,也拐帶了演員,有些再也接不了別的戲了。其實,閱讀《紅樓夢》文本毫不遜色于扮演角色產生入戲太深之感。開始,我們是以喜歡哪個紅樓人物被帶入,慢慢地,喜歡黛玉的就有黛玉型人格及情感模式,喜歡寶釵的就有寶釵型的,喜歡鳳姐的就有鳳姐型的人格及情感模式。同理,《紅樓十二講》在講的過程中,教師也會產生代入感。既然《紅樓夢》的“代入感”有某種必然性,也有一定的副作用,這就要求教師防范“代入感”,以便進入閱讀期待之中。原則上,應該把代入感的有無看作一個前提,如果學生沒有被代入感,那么,這個情感教育可能就是不成功的,相反,有了被“代入感”,這個情感教育基本上就是成功的,然而,又不能入戲太深,引起副作用。因此,教師提出一個慎用“代入感”標準,就像少林武僧,要能進得山門來,還要能打出山門去,這個標準就避免了情感教育走偏,“代入感”要用,但要慎用,教師端要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點,而學生要被提醒到這一點。那么,請對號入座,男生不要覺得自己就是寶玉,而女生不要覺得自己就是寶釵,或者是黛玉,或者是湘云,等等。如果學寶玉,就要區別對待,如果他平等待人,自然是好的,如果他在戀愛,要考慮怎么阻斷他變成暖男和中央空調,因為愛情是有排他性的;如果學黛玉,她多愁善感,怎么禁止她哭哭啼啼,這就是要把情感教育引導到陽光之中,而不是陰霾之中去。
三、沉浸式閱讀
如何將學生對接以及落實到課中呢?“紅樓十二講”不是文案,專題化教學就相當于一個小型講座,在課堂中,可能導讀和答問有伴讀性,就像一般家長能幫助做的一部分功課,然而,講和伴讀有不相容性,教師終究不是伴讀,講滿足聽,但也不意味著聽就容易,只要帶著耳朵來就行,當然,即使不讀,也有一個講聽機制在那里。然而,表面化了就遮蔽讀。從反饋來看,效果完全取決于閱讀落實到位,特別是課前和課后的預習,實際上,這是一個講聽(讀)機制,而聽和讀在學生身上互為表里,括號里的更為重要,不是略去聽,而是強調讀的重要性,于是,就變為講對應著讀,要形成講讀機制,而不是讀伴讀機制。在廣義上的閱讀中,《紅樓夢》文本具有優先性,可以稱之為狹義上的閱讀。對于《紅樓夢》文本,不通讀是不行的,讀一兩遍是不行的,一般來說,要沉浸式地閱讀。所謂沉浸式閱讀,是相對于淺閱讀或碎片化閱讀而言的,已經成為時尚的流行語,指陷在文字里難以自拔,讀起來暢快淋漓的感覺。而不沉浸式閱讀,就會浮光掠影,解不了其中味,達不到情感教育的目標。就是說,不但要有廣度,還要有深度。
這門通識課以落實學生閱讀為基礎,避免“地對空”現象。就某個專題而言,教師指定了章回,有些還是跨章回的,因為作者草蛇灰線,伏脈千里的文心筆意,這也要求沉浸式閱讀,教師主導著特點專題的方向和指定章回與跨章回合攏的機制。當然,能夠多讀就更好,然而,畢竟我們是通識課,要完成教學任務,聽講中不可以散漫無際,只能把握住一些重點區域。
(一)前八十回黃金區域
我們首先可能要接受前八十回與后四十回的概念,至于這個概念與一百二十回之間的論爭,孰是孰非,不在此討論,即使是一百二十回成立,即無續書之嫌,那么,我們仍然可以分出前八十回與后四十回來,這是一個基本的文本區劃。就前八十回而言,我們進行了黃金分割,產生的兩個黃金分割點剛好落在第三十一回和第五十回,相當于兩個大的高潮,那在第三十一回至第五十回之間,就仿佛在兩個高潮之間,又不存在明顯或拉長的低谷,而是高潮迭起的。這個區域是蔚為壯觀的,與前五十四回寫“盛”的看法大致吻合。不難發現,關于愛物觀的闡釋和陰陽之論恰好就出現在第三十一回中,這是一個巧合嗎?對于《紅樓夢》的宏觀結構,如果作者初步定在八十回左右,那么,就有可能產生與兩個黃金分割點大致吻合的文本書寫歷程。當講寶玉的愛物觀這個專題時,教師必然指定學生閱讀第三十一回,而講湘云論陰陽這個專題時,也必然指定學生再次閱讀第三十一回,但情節的發展不是剛好起止在這里,就需要以第三十一回為核心,讀前前后后的一些章回,這樣一來,雖然我們看重第三十一回至第五十回,但是不能排除回溯到第一回,或延伸至投鼠忌器寶玉瞞臟也未可知,特別是灰線伏千里。就明的來看,這個區域是個閉區間,而就暗的來看,又是一個開區間,即使落在第三十回至第五十二回之間,就是說,上限前移一至二,而下限后推一至二,都不影響對這個概念的理解,總之,大致上存在這么個區域。應該說,把這個區域劃分為重點,也許反映了我們的一般心理都是喜“盛”不喜“衰”的,這個可能是一個隱含的劃分標準。然而,對于《紅樓十二講》通識課來說,這個黃金區域的提出又是必要的,既對應著教學重點,也是沉浸式閱讀的需要;還因為大部分專題的內容都落在了這個區域里。針對十二個專題,具體地指定閱讀的章回如下,見表2。

表2 十二個專題與指定的章回
表中的章回,有指定的,有回溯的,也有延伸的,其中指定的章回是最集中體現專題的回目,專題一和四,已在前文交代,應該說,大部分專題的節點都好找,指定的確切性也高,而專題二、八和九相對難于找到。比如:專題二本應指定第8回,但其實指定第45回是因為金蘭契互剖金蘭語,釵黛關系有了冰釋前嫌的轉變,等于黛玉酸(多疑,尖酸)到極致處之后已走向反面,在寶釵面前做自我批評,但我們完全可以回溯到第8回,甚至更早,就是說,黛玉的檸檬精是彌散在更多回目之間的。專題八指定第36回,然后回溯至第21回,也可以指定第21回,然后延伸至第36回,這個完全沒問題。由于影子說是如影隨形的,而且,就第36回而言,繡鴛鴦夢兆絳云軒體現的恰是正身與影子的一個錯位,可見,影子是相對的。那一刻,寶釵坐在襲人坐過的位置上,接著繡起來,誰是誰的影子都說不清了。教師看重這個微妙,就指定了第36回,其實,影子說在細節上也是彌散的。專題九本應指定第41回,主要是考慮板巧戀的隱喻,即一般認為大姐兒的柚子與板兒的佛手互換,這個如同互換庚帖一樣,喝交杯酒一樣,這是關于婚姻設計的一個暗示。但我們還是指定了第42回,巧姐的名字是劉姥姥給取的,都說機緣巧合,那么,一個“巧”字做紅娘了,這也可以看做是婚姻設計的另一個暗示,就是說,從第42回回溯到第41回,也是可逆的,完全可以指定第41回,然后向第42回延伸。
(二)錄制音頻
那么,怎么布置學生對《紅樓夢》進行錄制音頻,以檢驗學生落實讀的情況。以2020年春季學期為例,首次選修的學生80人,這樣一來,就按照考勤登記表上的序號排列,一一對應,一個人錄制一回,正好可錄制前八十回,這對今后的“紅樓十二講”通識課來說,也是一個很好的教學個案。錄制音頻,沒有特意要求那么高標準,只要從頭至尾錄制下來就行了,當然,有些對自己要求高的學生,錄制的完全可以媲美評書演員,教師在引導學生做這個錄制的時候,讓他們參考了《紅樓夢》有聲版。錄制音頻雖然效果參差不齊,但這是一個良好的開端。為了避免替代錄制,教師通過語音通話對部分學生的聲音采樣,學生也理解了教師的意圖和設計,圓滿地完成了前八十回的錄制音頻工作,建立新文件夾保存,或把部分回目上傳到學習通云盤上。2020年春季學期,盡管受到新冠疫情影響,線上教學有某種嘗試性,可選修這門通識課的學生積極地配合,這是難能可貴的,由于他們出色的表現,首因效應明顯,可以進入教學循環模式之中了。教師每提到這個教學個案,并引以為傲。
四、情感教育的效果
當《紅樓十二講》作為通識課開設了一兩個學年之后,教學也會生成一些規律性的認知,揭示某種周期性。教學激發在講讀之間,就仿佛通過實驗組與對照組的比較得到的。那就是,不斷反復證明了,注重閱讀是對的,不管情感主線怎樣一以貫之,但情感教育總是寄托在閱讀上,像錄制音頻這種強化訓練就很好地推動了閱讀。
真正的教育是自我教育。結課后,教師的講告一段落了,預設閱讀是否成真?沉浸式閱讀是否持續?而情感教育終歸要依賴閱讀本身。借助《紅樓夢》文本,在抽象意義上,《紅樓十二講》的確是一種伴讀,而不是說教。所謂贈人玫瑰,手有余香。
對于讀來說,自主學習精神主導下,就是從要我讀到我要讀的轉變,可喜的是,已經有了自主學習行為。例如:坐在公交車上,打開《紅樓夢》文本的電子版來讀,還可以戴著耳塞聽有聲版。而事實上,經過一段時間的定向積累,訓練時數達到了量的規定,學生就能夠參與問答,文本的細節都耳熟能詳了,這個效果的取得是十分明顯的,形成了講讀良性的互動機制,開始循環起來。
引導閱讀是一種文化擔當的行為,這里,教師不能把抑郁的突然就轉變成陽光的,進而為此敷粉。顯然,這個也不切實際,情感是潛移默化的,而《紅樓十二講》作為通識課,僅僅是情感教育的一個入口。今后如果遇到了什么情感問題,還要看學生自己的修為,這就是結課寄語要講到的。然而,無論何時何地,都不要輕視閱讀《紅樓夢》。
五、有待改進的設想
結課后,教師通過回訪了解到《紅樓十二講》在專題化教學過程中,多少留下了一些小小的缺憾。
首先,比較常規的是,需要做一次情感問卷調查,以便在統計學意義上,把握每一個學生個體情感的發展狀況,不過,回訪基本滿足了這一點,因為情感不能停留在點上,而是一個過程,因而,需要的不是問卷,而是持續地關注和盡心地呵護。
其次,由于傳統文化的繼承性和解讀的需要,在講的過程中,個別地方沒有很好地清除掉封建糟粕,教師在此必須做出引導,由于沉浸式閱讀也會浸淫一些不良嗜好,這個必須克服。比如:錄制音頻中的淫詞浪語必須完全消除。
最后,文學與傳媒學院、音樂與舞蹈學院的學生擬議,在專題化教學之余,把一些專題改寫成劇本,舞臺戲劇化專題,讓學生演,但這個事有待去落實。教師愿意提供執導,因為這是一個很好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