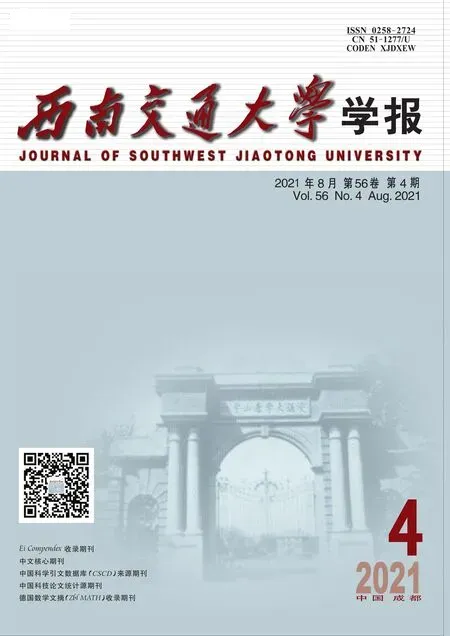八角樓鄉(xiāng)火后泥石流空間發(fā)育特征
楊 瀛 ,胡卸文 ,2,王 嚴(yán) ,金 濤 ,曹希超 ,韓 玫
(1.西南交通大學(xué)地球科學(xué)與環(huán)境工程學(xué)院,四川 成都 610031;2.西南交通大學(xué)高速鐵路運(yùn)營安全空間信息技術(shù)國家地方聯(lián)合工程試驗室,四川 成都 610031;3.西南交通大學(xué)數(shù)學(xué)學(xué)院,四川 成都 610031)
火后泥石流(post-fire debris flow)是指火燒跡地所發(fā)生的與林火有關(guān)的泥石流.Nyman 等[1]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2009 年2 月初澳大利亞維多利亞州大型山火過后,總共出現(xiàn)了319 處火后泥石流活動跡象,對2003 年—2009 年發(fā)生的16 次大規(guī)模地表侵蝕事件進(jìn)行了統(tǒng)計分析,發(fā)現(xiàn)有13 次為火后泥石流[2];Gartner等[3]對發(fā)生于美國火燒跡地的606 次地表侵蝕進(jìn)行了統(tǒng)計分析,發(fā)現(xiàn)只有216 次為泥石流,其余均為高含沙洪水.因此,并不是所有的火燒跡地都會發(fā)生泥石流,火后泥石流的發(fā)生是多個因素共同作用的結(jié)果.已有研究結(jié)果表明,影響火后泥石流形成的因素主要有地形地質(zhì)、林火烈度和降雨等.Gabt 等[4]研究發(fā)現(xiàn)美國蒙大拿州的火燒跡地泥石流的規(guī)模隨著坡面面積的增長呈指數(shù)倍增長;Cannon 等[5]發(fā)現(xiàn)由坡面徑流侵蝕引起的火后泥石流流域中,70%以上為沉積巖和變質(zhì)巖區(qū),而由淺表層滑坡引起的火后泥石流流域中,90%以上的為風(fēng)化花崗巖區(qū);Hyde 等[6]研究了美國蒙大拿州和愛達(dá)荷州的97 條火后泥石流溝后發(fā)現(xiàn),林火烈度越高,植被殘留越少,泥石流啟動所需的坡面面積和坡度閾值就越小;Kean 等[7]的研究表明,短時間強(qiáng)降雨對火后泥石流的規(guī)模影響很大,而總降雨量和坡面土壤的含水率則對其幾乎沒影響;Nyman 等[1]研究則表明干燥的火燒跡地更容易發(fā)生火后泥石流且規(guī)模更大.由此可見,影響火燒跡地火后泥石流空間發(fā)育特征的因素較多,而空間發(fā)育差異性及其影響因素的分析對火后泥石流的預(yù)測預(yù)報和防治具有重要的意義.據(jù)胡卸文等[8]初步統(tǒng)計,近年來川西南地區(qū)林火頻發(fā),由此引發(fā)了大量的火后泥石流,而目前國內(nèi)針對常規(guī)泥石流和震后泥石流研究較多(如文獻(xiàn)[9]),對火后泥石流的研究則比較少見,主要以綜述性研究(如文獻(xiàn)[8,10])和對其形成機(jī)理(如文獻(xiàn)[11-12])的研究為主,對其空間發(fā)育特征和影響因素的研究尚屬空白.本文以雅江縣八角樓鄉(xiāng)火后泥石流為研究對象,通過現(xiàn)場調(diào)查、室內(nèi)外試驗、遙感解譯等手段對其空間發(fā)育差異性特征和影響因素開展研究.
1 研究區(qū)地質(zhì)條件概況
研究區(qū)位于四川省雅江縣八角樓鄉(xiāng)扎日村境內(nèi),東經(jīng)101°13'56",北緯30°10'6",屬于雅礱江一級支流米西溝流域,為深切峽谷地貌,溝谷斷面呈V字形,谷底海拔約3 165 m,垂直落差約1 300 m,平均坡度在27°~37° 變化,局部較陡.區(qū)內(nèi)地層主要為第四系全新統(tǒng)沖洪積層(Q4al+pl)、泥石流堆積層(Q4sef),基巖為三疊系上統(tǒng)兩河口組地層(T3ln),主要以粉砂質(zhì)板巖為主(圖1).區(qū)內(nèi)無大型構(gòu)造及斷裂發(fā)育.研究區(qū)屬亞熱帶濕潤氣候區(qū),處于米西溝流域的暴雨集中區(qū),多年平均降雨量932.6 mm,具有明顯的干濕兩季,雨季一般為6 月—9 月,占全年總降雨量的90%以上,年平均氣溫11 ℃.

圖1 研究區(qū)火燒跡地及火后泥石流發(fā)育工程地質(zhì)平面Fig.1 Burnt area and geological development plane of post-fire debris flow
2 火后泥石流時空發(fā)育特征
2018 年2 月19 日,研究區(qū)發(fā)生了森林火災(zāi),過火面積39.5 km2,同年6 月—7 月,過火區(qū)域多溝多期次暴發(fā)了火后泥石流(圖1).通過現(xiàn)場訪問調(diào)查、搜集新聞、查看視頻資料等對2018 年火燒跡地泥石流暴發(fā)情況進(jìn)行了統(tǒng)計,結(jié)果見表1.從時間尺度看,6 月13 日,該火燒跡地有6 個小流域(流域面積 < 1 km2)率先暴發(fā)火后泥石流,至6 月24 日,這6 個小流域中有5 個再次發(fā)生泥石流,其余溝道只發(fā)生了高含沙洪水;5 d 后即6 月30 日,過火區(qū)域D2~D10 流域又相繼暴發(fā)火后泥石流;緊接著相隔4、7 d 后的7 月5 日、7 月12 日,過火區(qū)域D1~D10 流域又發(fā)生了兩次火后泥石流.由此可見,一次森林大火之后的火燒跡地,在集中降雨作用下,火后泥石流暴發(fā)相隔時間較短,暴發(fā)頻率很高.從空間尺度上看,F(xiàn)1、F2、F3 流域和與之相鄰的未過火的F4、F5 流域自始至終均以發(fā)生高含沙洪水為主,沒有泥石流活動的痕跡,而發(fā)生了火后泥石流的各流域,其暴發(fā)頻率也有一定的差異性.根據(jù)各流域暴發(fā)頻率,以暴發(fā)0 次和3 次為界限將火燒跡地各流域泥石流易發(fā)性分為不易發(fā)、易發(fā)和高易發(fā)三類,高易發(fā)流域有6 個(占比46.15%),易發(fā)流域有4 個(占比30.77%),不易發(fā)流域只有3 個(不含未過火的F4 和F5 流域).由此可見,火后泥石流發(fā)育的空間差異性明顯,并不是所有的過火區(qū)域都會發(fā)生火后泥石流,相對于較大流域、大流域,小流域易發(fā)性更強(qiáng).

表1 2018 年火燒跡地泥石流暴發(fā)情況統(tǒng)計Tab.1 Statistics of post-fire debris flow occurred in burnt area in 2018
3 火后泥石流發(fā)育影響因素
跟常規(guī)降雨型泥石流一樣,陡峻的地形、豐富的松散物源和降雨條件是形成火后泥石流的三個必備條件,其影響因素主要有地形地貌、地層巖性、地質(zhì)構(gòu)造、降雨條件以及人類活動等.而對于火后泥石流來講,除上述影響因素外,林火是其主要的影響因素之一.由于本文研究區(qū)范圍較小(39.5 km2),各流域地層巖性和地質(zhì)構(gòu)造均相差不多,區(qū)內(nèi)均為自然山坡,人類活動影響較小.因此影響研究區(qū)火后泥石流發(fā)育空間差異性形成的因素主要有林火、植被、地形和降雨,下面將從這四個方面逐一分析.
3.1 林火烈度
火烈度是評價林火燃燒程度的重要指標(biāo),對評估火后泥石流的發(fā)育具有重要意義.利用ENVI 5.3 軟件對林火前后(2018 年2 月11 日和2018 年3 月15日)的landsat 8 多光譜遙感影像(空間分辨率30 m)進(jìn)行處理,得出了火燒區(qū)歸一化差分燃燒指數(shù)(delta normalized burn ratio,dNBR)[13],結(jié)合林火發(fā)生一個月后現(xiàn)場調(diào)查的綜合植被燃燒指數(shù)(composite burn index,CBI)[14]確定各火烈度分級標(biāo)準(zhǔn),最終得出了各流域的火烈度分布(圖2)和各流域火燒區(qū)面積占比統(tǒng)計(圖3).

圖2 各流域火烈度分布Fig.2 Fire intensity distribution of basins

圖3 各流域火燒區(qū)面積占比分布Fig.3 Proportion of burned area in each basin
林火主要通過改變坡表土壤的物理力學(xué)性質(zhì)和水文地質(zhì)性質(zhì)來影響流域的抗侵蝕能力,從而直接影響火后泥石流的發(fā)育;而不同火烈度下土壤性質(zhì)的改變程度不同.
3.1.1 林火影響土壤物理力學(xué)性質(zhì)
坡表土壤的物理力學(xué)性質(zhì)是影響土壤抗侵蝕性的重要因素之一.林火產(chǎn)生的高溫對坡表土壤產(chǎn)生了烘焙效應(yīng),使得土壤的物理力學(xué)性質(zhì)發(fā)生了改變,進(jìn)而影響流域產(chǎn)流和產(chǎn)沙,對火后泥石流松散物源的形成和起動具有重要意義.
為研究林火對坡表土壤物理力學(xué)性質(zhì)的影響,按照《土工試驗方法標(biāo)準(zhǔn)》(GB/T 50123—1999)[15]中的相關(guān)規(guī)定,分別用環(huán)刀法、烘干法和比重瓶法依次測定了其天然密度、含水率和比重,并計算出了干密度和孔隙度,如表2 所示.

表2 火燒跡地坡表土壤物理性質(zhì)試驗結(jié)果Tab.2 Tested physical properties of soil on slope in study area
由表2 可知:林火引起土壤天然密度和含水率下降,而比重則幾乎不變.在重度、中度和輕度火燒下坡表土壤干密度相較于未火燒區(qū)分別下降了22.22%、18.75%和13.19%,而土壤孔隙度則相較于未火燒區(qū)分別上升了25.52%、23.31%和15.82%.由此可見林火顯著改變了土壤的物理性質(zhì).
對現(xiàn)場取的各火烈度區(qū)坡表的原狀土樣進(jìn)行直剪試驗,結(jié)果(圖4)顯示:在輕度、中度和重度火燒下,相較于未火燒區(qū),土壤內(nèi)摩擦角分別上升了2.07%、13.50%和24.24%,而內(nèi)聚力則分別下降了10.77%、35.14%和62.45%.由此可見,林火會引起坡表土壤的內(nèi)聚力大幅下降;雖然林火會使土壤的內(nèi)摩擦角有所增加,但是其變化幅度遠(yuǎn)小于內(nèi)聚力的相應(yīng)值.

圖4 各火烈度區(qū)土壤內(nèi)聚力和內(nèi)摩擦角Fig.4 Cohesion and internal friction of soil in areas with different fire intensities
綜上分析,在林火干擾下,坡表土壤干密度下降,同時孔隙度上升,內(nèi)聚力下降,使得土壤質(zhì)地變輕且較為松散,在降雨侵蝕下很容易被坡面徑流帶走,成為火后泥石流的物源.
3.1.2 林火影響土壤滲透特性
火燒引起土壤斥水性的增強(qiáng)是火燒跡地土壤最為顯著的水文特征改變之一[16].本次研究采用水滴入滲法測定土壤的斥水性,為保證試驗具有代表性,在4 個火烈度區(qū)采用隨機(jī)選點的方法,以1 cm 為深度間隔,依次測定不同深度范圍內(nèi)土壤的斥水性,直至斥水性消失.根據(jù)水滴入滲時間對土壤斥水強(qiáng)度進(jìn)行分級,分級標(biāo)準(zhǔn)參考Robichaud 等[17]的方法:當(dāng)水滴入滲時間小于5 s 為親水,5~60 s 為輕度斥水,60~180 s 為中度斥水,大于180 s 為嚴(yán)重斥水.最終統(tǒng)計得出各火烈度區(qū)不同深度處相應(yīng)斥水性強(qiáng)度的占比,如表3 所示.

表3 各火烈度區(qū)坡表不同深度處不同斥水土壤樣本含量占比Tab.3 Proportion of hydrophobic soil samples at different depths in areas with different fire intensities
由表3 可知:在坡表0 cm 處,未火燒區(qū)斥水性土壤占比為27.52%,而在輕度、中度和重度火燒區(qū),斥水性土壤占比依次增加至57.78%、70.21%和74.58%;隨著深度的增加,斥水性土壤占比大幅下降,到深度3 cm 處,火燒區(qū)斥水性土壤占比已經(jīng)和未火燒區(qū)相差無幾.由此可見,在坡表以下0~3 cm內(nèi),火燒會引起土壤的斥水性增強(qiáng).
土壤滲透性是影響降雨入滲的最直接因素.2018 年3 月對該火燒跡地土壤的滲透性進(jìn)行了現(xiàn)場測定,所用的儀器為美國Decagon 公司研發(fā)的微型圓盤入滲儀(mini disk infiltrometer).試驗結(jié)果為親水土壤、斥水土壤的滲透性分別為4.92×10-4、0.75×10-4cm/s,說明林火引起土壤斥水性增強(qiáng)會導(dǎo)致其滲透性下降,相對于親水性土壤,斥水性土壤的滲透性下降了84.76%.
土壤滲透試驗結(jié)果如圖5 所示.坡表0~2 cm深度范圍內(nèi),輕度、中度和重度火燒區(qū)土壤滲透系數(shù)依次為3.17 × 10-4、2.92 × 10-4cm/s 和2.17 × 10-4cm/s,相較于未火燒區(qū)依次下降了34.10%、39.29%和54.89%;在坡表以下2~4 cm 深度范圍內(nèi),輕度、中度和重度火燒區(qū)土壤滲透系數(shù)依次為2.97 × 10-4、2.40 × 10-4cm/s和1.21 × 10-4cm/s,相較于未火燒區(qū)依次下降了33.71%、46.43%和72.99%.由此可見林火會引起土壤斥水性增強(qiáng),從而導(dǎo)致土壤的滲透性大幅下降,這將勢必引起坡面產(chǎn)流量增多,從而為火后泥石流提供豐富的水源.

圖5 各火烈度區(qū)坡表不同深度處土壤滲透性Fig.5 Soil permeability at different depths in areas with different fire intensities

圖6 火燒區(qū)面積占比與泥石流暴發(fā)頻次的關(guān)系Fig.6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portion of burned area and frequency of post-fire debris flow
3.2 植被
植被覆蓋對泥石流的形成具有抑制作用,張穎等[18]的研究表明,林冠層和林下枯枝落葉層可以有效減少坡面徑流侵蝕和坡面松散物源的起動.為研究火燒跡地植被覆蓋率對火后泥石流發(fā)育空間差異性的影響,運(yùn)用ENVI 5.3 軟件處理2018 年6 月云量相對較少的landsat 8 遙感影像(空間分辨率30 m),計算其歸一化差分植被指數(shù)(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NDVI),并按式(1)計算得出各流域植被覆蓋率[19],如圖7 所示.林火對植被覆蓋率的影響如圖8 所示,隨著林火面積占比的增加,植被覆蓋率快速下降.

圖7 各流域6 月植被覆蓋率分布Fig.7 Distribution of vegetation coverage in each basin in June

圖8 火燒對流域植被覆蓋率的影響Fig.8 Forest fire effects on vegetation coverage in study area

式中:fg為植被覆蓋率;N為計算得出的歸一化差分植被指數(shù);Nmin、Nmax分別為最小和最大的歸一化差分植被指數(shù).
由圖7 可見,完全沒過火的F4、F5 流域植被覆蓋率較高,分別為62.07%和67.31%.而各火燒區(qū)不同流域植被恢復(fù)情況則有所不同.高易發(fā)泥石流流域中D2、D3、D10 流域植被覆蓋率較低,分別只有17.94%、17.82%和15.85%;D5、D7 和D9 流域植被覆蓋率則相對較高,分別為36.01%、37.74%和30.78%.易發(fā)泥石流流域中的D6 流域由于火燒程度較低,以中度和輕度火燒為主,因此其植被覆蓋率達(dá)到了46.88%,而D4 和D8 流域的則只有25.31%和19.48%;D1 流域只發(fā)生了兩次泥石流,而其植被覆蓋率只有23.22%.不易發(fā)泥石流流域中過火面積很小的F3 流域植被覆蓋率高達(dá)75.65%,只發(fā)生了高含沙洪水;F1 和F2 流域植被覆蓋率較低,分別為15.35%和21.23%,但是也只發(fā)生了高含沙洪水,沒有泥石流活動跡象.
經(jīng)統(tǒng)計分析,植被覆蓋率與泥石流暴發(fā)次數(shù)的斯皮爾曼相關(guān)系數(shù)為 -0.28,且相關(guān)性不顯著(P值大于0.05),通過上述分析也可以看出,植被覆蓋率對火后泥石流發(fā)育的空間差異性影響一般,但可以確定的是相較于未火燒區(qū),火燒區(qū)植被覆蓋率很低,發(fā)生火后泥石流的可能性相對較大.圖9 顯示當(dāng)植被覆蓋率大于約35%后,泥石流暴發(fā)頻次快速下降.

圖9 植被覆蓋率與火后泥石流暴發(fā)頻次的關(guān)系Fig.9 Relationship between vegetation coverage rate and frequency of post-fire debris flow
3.3 地形
陡峻的地形可以為火后泥石流的形成和流通提供必要的動能.通過運(yùn)用ArcGis 10.5 軟件處理30 m 精度的DEM 圖結(jié)合現(xiàn)場調(diào)查情況,得出了研究區(qū)各流域的基本地形參數(shù)如表4 所示.

表4 各流域基本地形參數(shù)Tab.4 Basic topographic parameters of each basin
地形因子及火后泥石流爆發(fā)頻次與流域面積的關(guān)系如圖10 所示.
主溝越長,發(fā)生泥石流時對松散沉積物的搬運(yùn)距離就越大,所需要的水動力條件也越大,因此主溝越長越不利于泥石流的形成.圖10(a)顯示,隨著流域面積的增加,主溝長度快速增加,而高易發(fā)火后泥石流流域主溝長度均較小.
之后,威特金又將肢解的尸塊加入了他的興趣清單,以其創(chuàng)造十七世紀(jì)佛蘭德靜物風(fēng)格影像——即使在更具容忍度的現(xiàn)代人看來,這種手法也令人難以置信——在美國,他的做法屢屢激怒地方律師與那些文化審查志愿者們。
主溝縱比降越大,泥石流流通時水動力條件越足,對沿途溝道的鏟刮和側(cè)蝕作用也越強(qiáng),越有利于泥石流的發(fā)育.圖10(b)顯示,隨著流域面積的增加,主溝縱比降快速降低,高易發(fā)火后泥石流流域主溝縱比降均很大.
溝道密度是指單位流域面積內(nèi)的溝道總長度,溝道密度越大,說明流域內(nèi)水系越發(fā)達(dá),將有利于坡面徑流和松散物源快速匯聚.由圖10(c)可見,隨著流域面積的增加,溝道密度快速降低,高易發(fā)火后泥石流流域溝道密度均很大.

圖10 地形因子及火后泥石流爆發(fā)頻次與流域面積的關(guān)系Fig.10 Relationship between terrain factors,post-fire debris flow frequency and basin area
由以上分析可見,研究區(qū)內(nèi)流域面積與各地形因子之間存在著相互制約的關(guān)系,流域面積越小,主溝越短,主溝縱比降越大,溝道密度也同時增大,地勢越陡峻,這些條件都非常有利于火后泥石流的形成.經(jīng)統(tǒng)計分析,流域面積與泥石流暴發(fā)次數(shù)的斯皮爾曼相關(guān)系數(shù)為 -0.77,且相關(guān)性顯著(P值小于0.05),表明流域面積對火后泥石流暴發(fā)頻率的影響也較強(qiáng);由圖10(d)可見,流域面積越小,泥石流暴發(fā)次數(shù)越多,高易發(fā)泥石流幾乎均發(fā)生在小流域(< 1 km2).
3.4 降雨
降雨是降雨型火后泥石流的重要組成部分.由于研究區(qū)距離最近的雨量監(jiān)測站較遠(yuǎn)(約10 km),其雨量監(jiān)測數(shù)據(jù)代表性較差,因此本文利用美國加州大學(xué)歐文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Irvine,UCI)水文氣象與遙感中心(CHRS)開發(fā)的實時全球高分辨率(0.04° × 0.04°)衛(wèi)星降水產(chǎn)品[20]獲取了研究區(qū)的降雨數(shù)據(jù)(詳見圖11),并用最近的雨量站監(jiān)測數(shù)據(jù)相互驗證,結(jié)果表明該數(shù)據(jù)產(chǎn)品精度相對較高,可以滿足本文的分析要求.

圖11 2018 年各次火后泥石流降雨過程Fig.11 Rainfall process of post-fire debris flows in 2018
根據(jù)降雨數(shù)據(jù),6 月13 日泥石流前期累計降雨量約10.67 mm,其激發(fā)雨強(qiáng)為9.83 mm/h;6 月24 日泥石流前期累計降雨量約8 mm,其激發(fā)雨強(qiáng)為8 mm/h;6 月30 日泥石流前期累計降雨量約66 mm,其激發(fā)雨強(qiáng)為18 mm/h;7 月5 日泥石流前期累計降雨量約24.51 mm,其激發(fā)雨強(qiáng)為41 mm/h;7 月12 日泥石流前期累計降雨量約19.66 mm,其激發(fā)雨強(qiáng)為15.33 mm/h.由此可見,除7 月5 日激發(fā)雨強(qiáng)較大外,其余4 次泥石流其激發(fā)雨強(qiáng)重復(fù)周期均小于5 a.且隨著火后泥石流的不斷發(fā)生,其激發(fā)雨強(qiáng)和前期累計降雨量有逐漸升高的趨勢.
3.5 綜合分析
6 月13 日過火區(qū)域只有D2、D3、D5、D7、D9、D10這6 個流域暴發(fā)了火后泥石流,根據(jù)降雨強(qiáng)度標(biāo)準(zhǔn),此次的火后泥石流激發(fā)雨強(qiáng)只達(dá)到了中雨級別,其前期累計降雨量也較低.從地形來看,這6 個流域均為小流域(< 1 km2),因此有利于快速匯流;從林火面積來看,D3、D9、D10 這3 個流域火燒區(qū)面積占比均達(dá)到了100%,D2、D5 和D7 流域分別為98.42%、95.85%和86.48%,因此火燒程度均較為嚴(yán)重;從植被恢復(fù)情況來看,這6 個流域6 月份植被覆蓋率均小于40%,尤其是D2、D3 和D10 流域只有17.94%、17.82%和15.85%,對火后泥石流形成的抑制程度較低.D6 流域其面積僅有0.31 km2,然而其過火面積占比較低(58.06%),且以中度和輕度火燒為主,植被覆蓋率也較高(46.88%),因此在此次降雨中也沒有形成火后泥石流.D1、D4、D8 流域火燒程度較高,植被覆蓋率也較低,然而其流域面積較大,因此受地形條件制約,水動力條件不足,在此次降雨中也沒有形成火后泥石流.
6 月24 日,其前期累計降雨量和激發(fā)雨強(qiáng)均較6 月13 日的小,6 月13 日發(fā)生了火后泥石流的6 個小流域中有5 個再次暴發(fā)了泥石流,D2 流域由于其主溝縱比降相對較小(370.61‰),主溝較長(2 km),而此次降雨雨強(qiáng)更小,導(dǎo)致水動力條件不足,沒有形成泥石流.
6 月30 日泥石流激發(fā)雨強(qiáng)為18 mm/h,此次 D2~D10 流域均發(fā)生了火后泥石流,D1 流域雖然火燒程度較高,植被覆蓋率也較低,但是由于其流域面積較大(是所有過火區(qū)域中最大的),因此受地形條件制約,沒有暴發(fā)泥石流.
7 月5 日泥石流激發(fā)雨強(qiáng)為41 mm/h,達(dá)到了特大暴雨級別,水動力條件很足,導(dǎo)致D1~D10 流域全部暴發(fā)了泥石流.7 月12 日泥石流前期累計降雨量和激發(fā)雨強(qiáng)較7 月5 日有所減小,但是D1~D10流域依然再次發(fā)生了泥石流,這可能是因為這些流域前期多次暴發(fā)泥石流,導(dǎo)致溝道下切嚴(yán)重,溝岸不斷塌滑形成了新的物源補(bǔ)給泥石流.
F1~F5 流域只發(fā)生了洪水.對于F1 和F2 來講,其燃燒程度較高,過火面積占比分別為73.68%和64.65%,植被覆蓋率也較低,分別為15.35%和21.23%,但是由于其流域面積較大,分別為4.13 km2和6.98 km2,因此沒有發(fā)生泥石流.
F3 流域過火區(qū)面積占比僅為8.35%,植被覆蓋率高達(dá)75.65%,流域面積也很大(5.15 km2),多重不利因素綜合作用下沒有發(fā)生泥石流.
F4 流域面積較小,僅有0.44 km2,然而該流域完全沒過火,植被覆蓋率較高(62.07%),所以也沒發(fā)生泥石流.F5 流域面積較大,為1.38 km2,與F4流域一樣,因為完全沒過火,植被覆蓋率高達(dá)67.31%,所以也沒有發(fā)生泥石流.
綜合上述分析可見,地形、林火、植被覆蓋率和降雨強(qiáng)度都對火后泥石流暴發(fā)有一定的影響,火后泥石流發(fā)育空間差異性的形成是這4 個影響因素綜合作用的結(jié)果,同時流域面積越小、林火面積占比越大的流域發(fā)生火后泥石流所需要的降雨閾值越小.流域面積、林火面積占比以及植被覆蓋率與火后泥石流暴發(fā)頻次的斯皮爾曼相關(guān)系數(shù)依次為 -0.77、0.78 和 -0.28,由此可推斷這三個因素對火后泥石流易發(fā)性影響的重要性排名為林火面積占比 > 流域面積 > 植被覆蓋率.
4 結(jié) 論
1)八角樓鄉(xiāng)火后泥石流具有易發(fā)群發(fā)的特點,且其發(fā)育存在空間差異性,并不是所有的過火區(qū)域都會發(fā)生火后泥石流,相對于較大流域,小流域(< 1 km2)暴發(fā)頻率更高.
2)各地形因子和流域面積之間存在一定的制約關(guān)系,流域面積越小,地形越陡峻,火后泥石流暴發(fā)頻率越高.
3)林火一方面通過高溫烘焙改變了坡表土壤的物理力學(xué)性質(zhì),使得土壤變得松散、抗侵蝕能力降低,同時還改變了坡表土壤的水文地質(zhì)性質(zhì)、使其斥水性增強(qiáng),滲透性降低,從而使得流域產(chǎn)流和產(chǎn)沙量激增,對火后泥石流的形成具有積極的促進(jìn)作用,火燒區(qū)面積占比越大,泥石流暴發(fā)頻率越高.
4)林火導(dǎo)致植被覆蓋率大幅下降,當(dāng)植被覆蓋率約小于35%時火后泥石流暴發(fā)頻率較高,大于此值后暴發(fā)頻率快速下降直至為0.
5)八角樓鄉(xiāng)火后泥石流發(fā)育空間差異性的形成是地形、林火、植被覆蓋率和降雨強(qiáng)度這4 個影響因素綜合作用的結(jié)果,各因素對火后泥石流易發(fā)性影響程度為林火面積占比 > 流域面積 > 植被覆蓋率,且流域面積越小、林火面積占比越大的流域發(fā)生火后泥石流的降雨閾值越小,且激發(fā)雨強(qiáng)有隨時間逐漸升高的趨勢.
致謝:成都理工大學(xué)地質(zhì)災(zāi)害防治與地質(zhì)環(huán)境保護(hù)國家重點實驗室開放式基金(SKLGP2018K011)資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