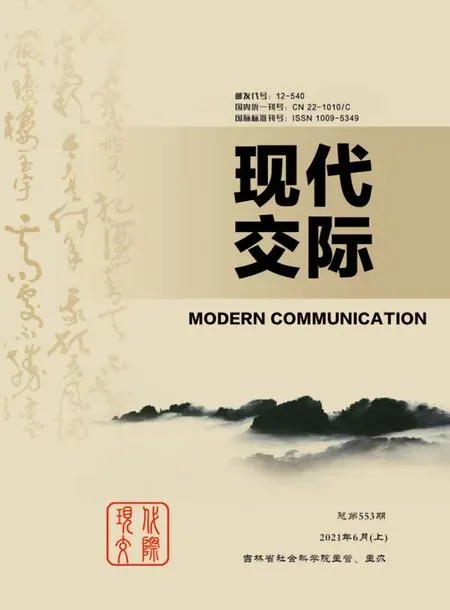《詩經》俄譯本中鳥意象的翻譯方法與翻譯效果
張勝男 楊 蕊
(哈爾濱理工大學外國語學院 黑龍江 哈爾濱 150000)
中國古代早期的文學典籍雖然不曾直接明確地提出“意象”這一概念,但關于意象問題的討論與表述卻有悠久的歷史,最早出現在《周易》和《莊子》這兩部著作中。本文通過研究阿布拉緬科俄譯版《詩經》中鳥類意象的翻譯,探討翻譯處理中國古代詩歌的方法,通過分析古代詩歌中“意象”翻譯的得失,觀察其翻譯效果如何。
一、“意象”翻譯的研究概述
所謂意象,是客觀物象經過創作主體自身的情感活動創造出來的一種藝術形象。《周易》借助卦爻變化所產生的象,來預示現實的禍福兇吉,是更注重“象”的著作。《莊子》一書更注重“意”,認為“言”的目的在得“意”,“言”作為說話的工具只是一種手段,而其目的是“意”。意象概念雖然在中國很早就有所涉及,但它開始走向成熟并引起廣泛注意是在較晚的明清時期。與我們現在所認知的“意象”概念相一致的看法到了明代大量出現。袁行霈學者在《中國詩歌藝術研究》一書中提到“意象是融入了主觀情意的客觀物象,或者是借助客觀物象表現出來的主觀情意”[1]。詩人們的共識是:意象是詩歌的靈魂,是詩歌表達感情的手段和媒介;因此解讀意象是詩歌的關鍵。
《詩經》中的動物意象比比皆是,很多學者對其出現的次數做過統計,但由于不同的種類劃分標準,其數字結果也有所差異。僅僅在篇名中,以動物名直接命名的就有42篇,而有動物名目出現的篇名多達167篇,這體現了動物意象在《詩經》中的重要性。[2]《詩經》動物意象的運用中,鳥意象占據很大一部分。不管是清代學者顧棟高的《毛詩類釋》、徐鼎的《毛詩名物圖說》,還是孫作云對《詩經》中動物意象的分類研究,盡管分類標準不同,但鳥類意象在動物意象中都是數量最多的意象。
中國人對飛鳥本身有著濃厚的感情。一些學者認為,鳥意象在《詩經》中被大量運用,是由于圖騰崇拜。[3]鳥圖騰崇拜在原始人的圖騰崇拜中是一種常見的現象,在古籍中也存在一些以鳥類為圖騰的氏族。勞動人民對鳥意象不斷進行加工、修飾,使《詩經》中鳥意象極其豐富。
二、В.П.Aбраменко 俄譯版《詩經》中鳥意象的翻譯方法與翻譯效果
在包含鳥類意象的詩歌中,有一大部分是與愛情婚姻有關的。中國古代雖是一夫多妻制,但人們對于美好愛情的向往也從未消減。鴛鴦、鵜鶘等鳥類,因為常年與配偶結伴出行,一雌一雄,往往作為愛情的象征出現在《詩經》中。
1.《周南·關雎》
《詩經》國風的開篇《周南·關雎》即取雎鳩聲音及形態來表現男子追求女子的相思之情。
原文: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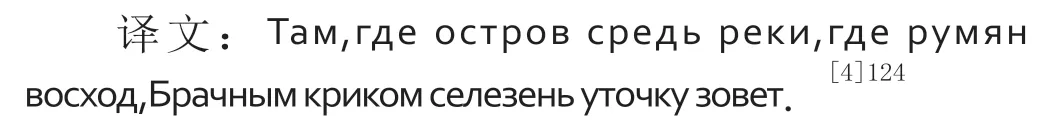
歷代為詩經作注的學者絕大部分都認為雎鳩即魚鷹。“關關”為鳥的和鳴聲。“雎鳩”這一意象在此句俄譯本中采用的翻譯方法是替換法,使用這種翻譯方法的情況通常是某種動物在俄羅斯并不存在,因此譯者會選擇一種俄羅斯人所熟悉的動物來代替原意象。譯者選擇替換原來的物象,以此保持原詩的意味。此手段易象存意,用目的語文化中的類似物象來代替原物象。在俄羅斯文化中,утка為母鴨,此處為女性的象征,селезень為公鴨,為男性的象征,兩者同時出現在民間詩歌中時是愛情伴侶的象征。這使得關雎這一意象在譯文中雖然沒有完整重現,但同樣給譯本讀者帶去了情感共鳴,讓讀者明白此句表示情侶之間的愛情。在大多數情況下,譯者替換原來的物象,采用以譯作讀者更為熟悉的取物象替換這一方法;這一方法雖很常見,但物象一旦被更換,原本的意象就或多或少地發生變化。易“象”時可以將原意象換成另一完全不同的意象,或是能夠找到目的語文化中的類似物象代替原物象。“雎鳩”這一意象的替換便屬于后者,此種方法使譯作讀者能夠把握到原作的某些寓意。盡管由于意象的系統差別,會導致翻譯作品中某些原“意”的流失,但在較大程度上保留了原作意思,使讀者對意象產生情感的共鳴,也算是較為成功的翻譯。
2.《小雅·鴛鴦》
在《詩經》中“鴛鴦”作為一種愛情的象征也常出現。鴛鴦在中國文化中一直是愛情鳥,民間更是流傳著“只羨鴛鴦不羨仙”的詩句來表現對美好愛情向往之情,寓意情侶相互陪伴,不離不棄。在《小雅·鴛鴦》篇就充分表現出了鴛鴦這一中國意象獨特的典型文化內涵。
原文:鴛鴦于飛,畢之羅之。

鴛鴦雌雄同居,相互依靠。俄譯本“鴛鴦”一詞在此處被翻譯為“Мандаринки-уточки”,即作為外來詞翻譯,此處采用的是文后注釋翻譯法,解釋此意象為愛情的象征。譯本中,此處鴛鴦意象僅保留了象本身,意被消亡,需要讀者結合文后注釋才能體會其意象的含義。《詩經》中的一些鳥的意象,文化淵源較為復雜,“象”和“意”之間的關系更松散,如果在譯文中直接呈現出來,譯文讀者不能從本國的文化角度體會其中的象征意義,因此一般用外來詞表示。如鴛鴦意象的翻譯,就很難使讀者懂得其寓意,這樣的翻譯雖然保留了原意象,但其寓意不復存在,存象失意,需要在文后對其進行額外注釋。
原文:鴛鴦在梁,戢其左翼。

在同一篇章中,“鴛鴦”一詞又被翻譯為селезень和утка,此處又采用了替換翻譯方法。此翻譯方法易象存意,讓讀者通過對公鴨和母鴨作為愛情眷侶的文化背景認識、體會原作品中作者想要表達的幸福婚姻生活。這兩個句子雖對“鴛鴦”一詞采用了不同的翻譯方法,但通過上下文及目標語的文化背景知識,相互呼應,向讀者傳遞出所追求美好愛情生活和婚姻生活的主觀要求和美好希望,達到了較好的翻譯效果。
3.《邶風·燕燕》
在中國古代文化中,燕子也承載著人們對婚姻和愛情的期望。一方面由于燕子雙飛的形象特征。燕子是自然界中一夫一妻制的代表動物,一對對燕子一起飛翔,呈現給人們美好的畫面,雙燕寄相思已經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象征;除此之外,燕子與春天的微妙關系,也引發人們對愛情的聯想。歷代的文人都喜歡在愛情作品中使用燕子這一意象,《詩經》也不例外,如《邶風·燕燕》。
原文: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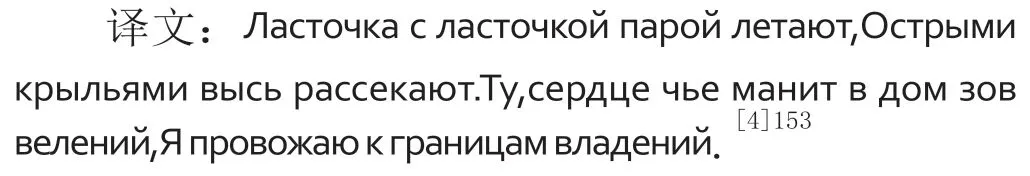
在這里“燕”被譯作為“Ласточка”,此處采用的是直譯法。對動物意象翻譯而言,用俄語中相對應的動物詞匯來表示這一意象,在這里“意”與“象”被和諧地再創造。在俄羅斯燕子這一意象雖與中國有所差異,但也隱含愛情之意,人們甚至用這一詞語作為對女人和孩子的昵稱。“моя ласточка”即“我親愛的,我的小燕子”,用來表示情侶家人之間的親密。這樣一來,燕子這一意象被和諧地再創造于譯作中。《詩經》中有一些篇節中鳥意象十分鮮明,寓意也較為明確。在翻譯中,我們往往容易把握此類意象。比如上文提到的例子,作者用雙飛的燕子體現對愛情的追求,翻譯時,其意和象均被保留下來,且兩者并未分離。譯文讀者比較容易在兩者之間建立關聯,存象存意,達到較好的翻譯效果。
4.《小雅·鶴鳴》
美刺觀念是一種關于詩歌社會功能的表現,最早起源于《毛詩序》對《詩經》的論述。所謂‘美’就是歌頌,‘刺’就是諷刺,作者對發生在身邊的事情有自己的看法,然后借助詩歌作品等文學載體,或贊揚,或批判,來抒發自己的感想。《詩經》中存在的大量鳥意象也具有承載這一社會功能的作用。
原文:鶴鳴于九皋,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

《詩經》中的鳥大多以正面形象出現,如“鶴”這一意象。“鶴”這一意象在古人眼中是良禽,是與神仙親近的神鳥,因而文人墨客都喜歡用鶴來贊美別人,指人擁有高潔美好的品德。此處的鶴也是用來指隱居的賢人,表現招賢納士的政治主張。俄語中“журавли”一詞有與漢語中象征意義相似的地方,它是指“上帝的鳥”,是神圣的鳥,人們對其懷有一種敬畏之情。此處的翻譯方法為直譯法,但在此處意象被淺化,雖然運用同一“象”,但“意”沒有被完整保留下來,失去了原文中用鶴來表示賢良之士的意。此時,譯者只在語義層面簡單翻譯了“象”,而忽視了譯文作品中的“意”發生的變化。對于譯文讀者來說,象和意之間的聯系就被分裂,動物意象被淺化或消除,達不到完美的翻譯效果,這是意象翻譯問題的主要問題之一。
5.《豳風·鴟鸮》
除了大部分以正面形象出現的鳥意象,《詩經》中同樣存在以反面形象存在的鳥,如貓頭鷹這一鳥意象。《詩經》中明確出現貓頭鷹意象的主要有四篇,并且這四篇中的貓頭鷹意象都為貶義,大都用來諷喻貪婪兇狠惡人的,如在直接以這一動物意象命名的《鴟鸮》中。
原文:鴟鸮鴟鸮,既取我子,無毀我室。

這是一首民間創作的寓言詩,也被很多學者認為是我國寓言詩的源頭。鴟鸮(貓頭鷹)在中國文化中被視為不祥之物,而在這里作為一種猛禽出現,表現出其兇狠、愛欺負弱小的特性。而“Сова”一詞在俄羅斯文化中通常是智慧賢明的代表。兩國文化背景完全不同,但聯系語境可以體現出貓頭鷹作為猛禽對其他弱小鳥類的欺凌。在翻譯過程中,譯者雖然保留了貓頭鷹這一意象,但這一意象背后的文化內涵被消除,僅把意象作為一種敘述描寫。在翻譯時類似一些意象常被翻譯成一組明喻,將其比喻或象征意義當成真實信息加以傳達,導致意象被消解而失去原詩的基本精神及內涵,存象而失意,這種情況下,意象只能通過語境及背景才能得到譯本讀者的理解。
三、結語
文學翻譯是翻譯工作的一個重要內容,翻譯我國的經典文學著作,尤其是傳統詩歌,是傳播我國文化的一個重要途徑。作為經典名著《詩經》有著重要的翻譯價值,而意象翻譯是詩歌翻譯的血脈,鳥意象是《詩經》動物意象中較為詳細和重要的意象群之一。譯者需要充分了解兩國文化背景知識,掌握意象翻譯的方法與技巧,擁有較高的知識素養,才能達到理想的翻譯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