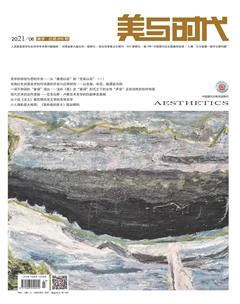電影敘事中“畫面隱含作者”與“源隱含作者”的異屬性修辭碰撞


摘? 要:畫面隱含作者傳遞的敘事和修辭信息一方面源于源隱含作者,另一方面源于其自身,將兩者從實際的電影敘事文本中分離開來,可以進一步分析兩者之間的修辭碰撞。其中異屬性元素層面可能發生邏輯碰撞:有議論修辭具體化過程中自我否定式的修辭碰撞;有影像具體化過程中抽象與具象的對立碰撞;還有影像與敘事及議論修辭的多元化對立碰撞。
關鍵詞:電影敘事;修辭碰撞;畫面隱含作者;源隱含作者;主體意識
基金項目:本文系2020年衡水學院校級課題“電影敘事中‘畫面隱含作者與‘源隱含作者的修辭碰撞研究”(2020SK27)研究成果。
所謂的影像表達是畫面隱含作者作為一種翻譯機制或想象機制,將源隱含作者的議論或選擇性的敘事影像化或實體化的過程。盡管這種想象機制的原材料來源于源隱含作者的信息,但由于源隱含作者的信息從未被具體為某種議論的聲音或活動的影像,不管它被描述得多么具體,它總是具有某種抽象性。就像我們讀小說時,難以確定敘述者到底是以怎樣的一種嗓音,也難以賦予小說中某個角色具體的臉一樣,因此畫面隱含作者的這種想象機制本身就有著極大的自我發揮的空間。它涉及的范圍很廣:有注意點的選擇,包含與構圖相關的視點的角度、高度,乃至畫框內外等選擇;有影像中一切元素明暗對比的選擇;有影像中聲音層次的大小分離;即便是前邊所論述的那種節奏的選擇似乎也是影像表達的一種;甚至還可以包括敘述者聲音以及人物形象的再構建等,看似與畫面隱含作者無關的因素。以上種種因素還沒有完全囊括影像表達作為畫面隱含作者的想象機制全部自主選擇性的產物,但這些自主選擇都可以以源隱含作者的信息為基礎而產生于源隱含作者的相反的修辭形象。對這種相反形象的選擇,體現了兩個意識主體在對待故事上的態度產生了分歧或對立。
一、自身的否定:議論修辭及其具體化之間的悖逆
非人格化敘述者在很多時候可以被看作是源隱含作者的形象,與故事中的人物形象一樣,與源隱含作者的敘述或修辭過程是最接近的。畫面隱含作者需要以其想象機制將語言話語下的兩種形象實體化為具體的聲音和具體活動著的人,也正是由于這種具體化導致畫面隱含作者與源隱含作者之間產生悖逆性的修辭行為。
一般情況下,在小說中一段話語聲稱要給我們講述一個故事或者闡述某種評價,讀者會以某種抽象的聲音形式想象這種講述或議論,但這種想象不會改變其本身的情感色彩,因為讀者沒有必要為這種想象賦予強加干涉的情感色彩,比如強行想象一個尖細、扭曲、乖張的聲音在講故事或發議論,這并無必要。但當這種想象屬于畫面隱含作者,本質上與小說的讀者不同,我們需要將其看作是二次創作信息的源頭,它得到源隱含作者信息的目的并不僅僅是翻譯,而是二次加工。因此,畫面隱含作者賦予源隱含作者代表的那個敘述者的聲音完全可以是尖細、扭曲、乖張的,而正是這種聲音形式導致這個聲音所代表的源隱含作者產生了不可信性。這種結果在小說敘事中是不可想象的,非人格化敘事往往代表隱含作者所限定的思想和規范,不同于人格化的敘述者,人格化敘述者的可信性可以通過其是否“為作品的思想規范(亦即隱含的作者的思想規范)辯護或接近這一準則行動”[1]來確定,但非人格化敘述者往往直接代表了那種思想規范,在小說中似乎永遠可信。由此,畫面隱含作者可以通過加工聲音,將源隱含作者具體化的聲音變得帶有某種不可信性,實際上是在畫面隱含作者的想象機制下,強行將一個代表源隱含作者聲音符號的能指與所指分裂開來,導致能指在指向所指的過程中又帶有自我否定性,而這種否定性與源隱含作者并無關系,它只來源于畫面隱含作者。因此,這種情形一旦發生,顯然是一種修辭意圖上的悖逆碰撞關系。
但是,在影像表達方面,畫面隱含作者與源隱含作者議論修辭的碰撞要想通過改變議論修辭的聲音來實現,還是困難的。因為這個聲音到底變成什么樣子才會使觀眾產生不可信性,實際上還存在一個標準問題,可能對于不同的觀眾來說,程度的不同會有不同程度的碰撞效果。但無論如何,這在探索兩個主體意識之間修辭意圖碰撞形式的過程中是值得嘗試的。
二、抽象與具象的對立:影像形象及其具體化之間的悖逆
影像形象的內容肯定是指向源隱含作者,它屬于故事內容的范疇,但小說式的敘事并不能使讀者產生具體形象,它們總帶有某種抽象性或模糊性。并且,這種模糊的形象符合小說的隱含作者給出的某些規定性概念,比如善良、美麗、雄偉、尖酸刻薄、猥瑣等。一旦引入畫面隱含作者的想象機制,人物形象是否與源隱含作者給予主體形象的規定性概念一致,便成為一個重要關注點。有一種特殊情況會導致影像形象與所謂的原著形象產生背離,即當觀眾對原著中所規定的某些人物形象的抽象概念比較熟悉,但看到電影文本展現出來的形象不符合此種標準時,便會認為這個具體的形象違背了預先設立的規范,顯得失真,進而產生抵觸情緒。盡管上述這種情況并不符合畫面隱含作者與源隱含作者之間的修辭上的碰撞,但在某種角度上是相通的,當影片中的形象與影片所傳達的概念不相符時,與觀眾打破的規范以及所產生的抵觸心理是相似的。影片《1942》是以大逃荒為故事背景,“饑餓”是此片的一個核心概念,并由此概念產生具有規定性的人物形象。但總的來說,該片不能令人滿意,影片中的人物面部過于豐滿,并不足以表現“極度饑餓”的狀態。
同理,以一種極度猥瑣的形象來具體化一個偉大的人物似乎不妥,但這正反映了畫面隱含作者與源隱含作者乃至大多數觀眾之間的分歧。這種分歧反映在電影敘事文本中就是兩個主體之間的修辭碰撞,這種碰撞甚至會延伸到畫面隱含作者與觀眾之間思想上的碰撞,而且這種碰撞很常見。我們經常會說“這個人物的形象跟影片的內容不相符”,盡管這種說法并沒有達到對兩種修辭意圖碰撞的總結,但足以表明這種碰撞經常存在。但是最終這種影像形象與源隱含作者預先規定的形象概念不相符到底會產生一種什么樣的效果,還應該和具體的故事情節相聯系,甚至會延伸到與之相關的現實史料。比如一部電影的源隱含作者的故事中存在一個正面人物,但這個正面人物與其他文本有著緊密的互文性關系,而在其他文本中,這個正面人物又是一個惡貫滿盈的反面人物。這樣,電影中該正面人物在畫面隱含作者的想象機制下具有一張尖酸刻薄的面孔也合情合理,這就表達了畫面隱含作者與源隱含作者之間對人物形象態度上的對峙。
三、多元化對立:影像形象與故事敘述及議論修辭之間的悖逆
在電影敘事文本中,畫面隱含作者代替讀者,接受了源隱含作者在敘述故事及自身的修辭評論中的態度,以模仿的方式傳達態度。傳達過程十分簡單:比如為展示了一個人物優秀品質的一面,竭盡全力地展示其優良的行動,這種選擇本身便是修辭;或者是一個聲音模仿源隱含作者,告訴觀眾“馬上要給大家講述的是一個惡貫滿盈的罪惡之徒的故事”,這種直接的修辭意圖是顯而易見的。但畫面隱含作者在對源隱含作者的修辭意圖表達的過程中,其修辭意圖選擇的空間是很大的,而選擇傳達出一種修辭態度。但我們往往認為這種態度應該與敘述的故事以及其中的議論修辭相適應,而不是將這種修辭與源隱含作者的敘述及議論修辭進行對比。
但影像形式選擇所帶來的修辭意圖與故事敘述或議論形成修辭碰撞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影像自身表達態度的方式是多元的,它可以通過多種媒介形成自身的修辭指向。構圖是畫面隱含作者形成修辭的一種重要形式,將畫面中的元素以獨有的形式置于畫框之中,這本身就是一種意圖性的選擇。構圖實際與一個敘事詞匯相關聯,即“注意點”,這是厄爾·邁納提出的一個概念,但他主要是想“引入人物的注意點和讀者的注意點的概念”[2]。在電影敘事文本中,注意點的選擇由畫面隱含作者的想象機制負責,用畫框、透視、虛化、高度、角度等形式模仿或取代了人物以及讀者注意點選擇的權利。敘事一旦進入某個聚焦領域,將那些成分展現出來便是畫面隱含作者的權利,而權利的實施則伴隨著意圖的出現,這種修辭與故事敘述及議論修辭便可以不一致。
畫框內容的選擇是一種顯見的態度取向。假如一部電影給我們講述一群上層社會人物的高雅生活,他們優雅的談吐并且伴隨一個非人格化的敘述者,在議論中表現對那種生活的向往。總之,從故事內容來看,這并不是一部帶有反諷意味的電影,但畫框卻不時將場景中最骯臟的角落展現出來,每一個人物都有一個凌亂的背景,這些都與電影敘述的故事以及敘述者的議論不相符,碰撞也由此產生。鏡頭高度的不同也表現出一種截然相反的態度,鏡頭俯拍主體,透視會導致主體身體變得不協調,可能含有蔑視或輕視之態;相反的形象則顯得更完滿,有仰視之態或者一種“謙和”的姿態;而平視則顯得平易近人,具有平等之態。小津安二郎的電影總是采用仰視的鏡頭,想來如果小津拍攝《盲山》,其態度上的悖逆可能會非常明顯。不僅是高度,角度以及明暗也能起到相似的作用,因此可以說,在表達態度方面,這種與敘事的注意點相關的構圖,可以通過多元途徑實現與故事敘述及議論修辭的碰撞。
四、結語
畫面隱含作者與源隱含作者之間之所以能形成修辭碰撞,根源就在于畫面隱含作者是一個與源隱含作者并立的文本主體意識。雖然其想象或翻譯機制傳遞的敘事及評價信息以源隱含作者的信息為基礎,但在對信息具體化的過程中也能形成自身獨有的表達和評價方式,這種獨有的修辭方式可以與源隱含作者的修辭意圖產生悖逆碰撞。總體來說,異屬性元素之間的修辭碰撞雖然是一種邏輯的碰撞,但因兩種意圖容易并置,其修辭碰撞的效果更為顯著。
參考文獻:
[1]布斯.小說修辭學[M].華明,胡曉蘇,周憲,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178.
[2]邁納.比較詩學[M].王宇根,宋偉杰,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270.
作者簡介:趙世佳,衡水學院中文系講師。研究方向:電影敘事。
編輯:雷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