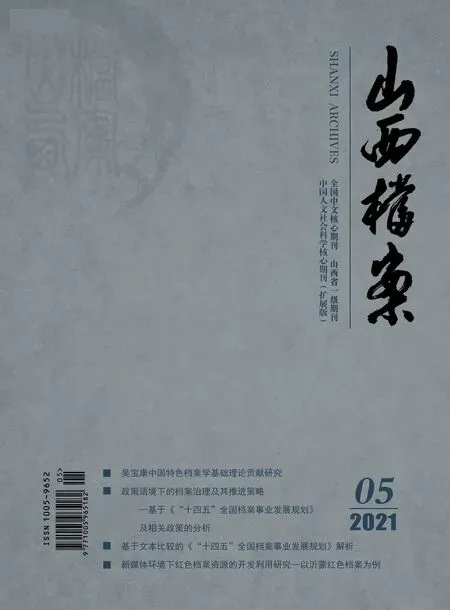數字記憶視角下紅色檔案資源開發模式構建探析*
徐海靜 姜惠丹
(黑龍江大學信息管理學院 哈爾濱 150000)
0 引言
檔案作為一種原始記錄,以不同的載體形式存儲著歷史過往中發生的人與事,它不僅使將前人的經驗教訓留存于后世,更使后人通過檔案記錄得以窺見趨于真實的歷史面貌。數字時代的到來,不僅更新了檔案載體的存在方式,也極大地延長了檔案“記憶”的應用年限。由于其使用的便捷性和傳播的廣泛性,“數字記憶”成為學者們研究的焦點。
紅色檔案資源是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真實歷史的記錄,展現了黨的奮斗不息的偉大精神內涵以及深厚的革命底蘊。2020年6月,新修訂的《檔案法》公布,增加了國家保護檔案的多種舉措,推進社會各主體有意識的形成檔案,積極開發利用檔案資源,為真實、全面地記錄新時代黨領導人民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進程貢獻力量[1]。作為弘揚紅色精神的重要傳承載體,紅色檔案資源不僅能夠促使公眾深入理解中華民族精神內涵,還能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提供現實支持。本文從數字記憶的視角對紅色檔案資源的開發模式進行梳理并提出優化策略,從而豐富紅色檔案資源開發的研究。
1 數字記憶理念與紅色檔案資源
1.1 數字記憶理念
20世紀末期,“記憶潮”的出現預示著記憶理念將呈席卷態勢而來,此后檔案學界也不斷涌現出檔案與社會記憶、城市記憶等理念相融現象,并不斷豐富檔案記憶觀[2]理論。信息時代的深入發展,推動著社會轉型與產業更新,使得網絡信息呈碎片式、無序化、海量化、增速快等特點,人們難以做到“精準存取”以及“方便調用”,因而馮惠玲教授提出要用“數字手段來構建數字時代的記憶。”[3]一方面對傳統介質上的文化記憶進行數字化,另一方面直接基于數字手段生產新記憶,“數字記憶”理念應運而生。2015年,馮惠玲教授在數字記憶國際論壇上,提出“讓歷史告訴未來”,最終構建一個充滿“愛與溫暖”的數字記憶[4]。可以肯定的是,數字記憶無論是從技術手段還是記憶載體,都順應了時代的發展,是對過往檔案記憶研究的豐富和擴展。
馮惠玲教授提出,數字記憶是數字形態的文化記憶,就是將特定對象的歷史文化信息以數字方式采集、組織、存儲和展示,在網絡空間承載、再現和傳播的記憶形態[5]。龍家慶、聶云霞學者則認為,數字記憶的研究不僅要考慮數字時代檔案傳播特點、保障記憶內容真實完整性、檔案記憶的建構活力,還應密切關注檔案服務的提供形式與場景塑造[6]。綜上能夠看出,數字記憶是以數字技術為手段,以特定文化記憶資源為挖掘對象,以內容真實性和檔案資源活態化為特點和目標。因而,在進行數字記憶項目過程中,要注意把握數字技術的應用以及文化記憶資源的處理,這對紅色檔案資源的開發利用提供了一定的指導方向和經驗支持。
1.2 紅色檔案資源概述
1.2.1 紅色檔案資源的定義
本文將紅色檔案定義為從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過程中,中國共產黨的機關、部門、組織以及個人在對敵斗爭、政治活動以及社會建設中形成的,具有保存價值的原始記錄。基于檔案資源的相關概念,紅色檔案資源包括三個方面:第一,紅色檔案工作與事業發展的對象,即紅色檔案本身;第二,紅色檔案工作與事業發展所需的由國家或社會提供的多種保護協調措施;第三,紅色檔案工作與事業發展作用于社會帶來的影響。而本文提到的紅色檔案資源是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改革、建設過程中形成的真實記錄,是能夠服務于人民群眾、推進全黨的建設、促進社會平穩發展以及宣揚樂觀積極情感的物質載體與精神載體的全部內容。
1.2.2 紅色檔案資源的種類
紅色檔案資源按照不同載體可以劃分為紙質檔案,如1936年由校長趙尚志、副校長李華堂等共同簽署發布的《東北抗日聯軍政治軍事學校臨時簡章草案》;口述檔案,如山東朐縣推出《紅色記憶·口述檔案》系列紀錄片;實物檔案,如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軍旗;石刻檔案,如烈士紀念碑等。
按照不同歷史階段可以劃分為兩部分:一部分可以歸為革命時期檔案,其生動地講述著中國共產黨領導各根據地人民參與革命斗爭、為中華民族謀未來的紅色篇章;另一部分可以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形成的各種文書與實物資料,包括口述史料、紀念革命活動記錄等檔案材料。
1.2.3 紅色檔案資源的現實價值
根據檔案的價值理論,檔案具有第一價值和第二價值。紅色檔案在對機關起作用的基礎上,更要對社會起作用,引領正確價值觀進而推動社會主義的建設。隨著紅色檔案利用范圍擴大,紅色檔案資源的形成與建設成為一個新的研究課題,因此認識并挖掘紅色檔案資源的現實價值是開發紅色檔案資源的必要前提。
開發紅色檔案資源有利于提高學生思想道德水平,實現教育價值。紅色檔案彰顯著前人不屈的意志和偉大的精神力量,在一代又一代的傳播和繼承的過程中形成深刻而鮮明的烙印。從教育對象來看,以在校學生和黨員為主。由于學生在成長過程中受主觀自我意識和外界客觀因素雙重影響,逐漸形成個體的價值觀和人生觀,就需要紅色檔案走入校園,通過開展紅色主題活動,組織參觀紅色展覽,播放相關視頻等形式豐富思想教育素材,創新傳播途徑,從而提高學生的信息接受程度。對黨員的思想政治教育也不容忽視,一方面需要黨員在制定和執行國家政策方針時走在隊伍前列,通過開展“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等主題黨會堅定黨員干部為人民服務的理念與防腐倡廉意識,保證黨員隊伍的純潔性。
開發紅色檔案資源有利于拓展新產業,創新收益渠道,實現經濟價值。結合黨和國家的政策舉措,逐步形成“紅色+”的旅游新趨勢。一方面將紅色檔案實物資源開辟為旅游景點,開放旅游路線吸引國內各年齡段游客,輔以紅色檔案周邊衍生品,作為旅游創收渠道之一;另一方面,將紅色檔案資源與虛擬交互等技術相結合,進行游客消費體驗,在產生經濟價值的基礎上,擴大紅色檔案資源的影響范圍,通過信息傳播新路徑宣揚紅色精神,進而促進紅色檔案資源的開發。
開發紅色檔案資源有利于傳承和保護紅色文化,實現文化價值。紅色檔案作為記載老一輩在革命時期付出的種種艱辛與努力的真實記錄,值得中華民族一代又一代青年銘記并傳承下去,努力建設祖國從而實現中華民族的騰飛。此外,紅色檔案資源要走入基層社區,通過舉辦靠近人民群眾生活方式的社區活動,發揮紅色文化凝聚作用和引領作用,由點及面的推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可見,紅色檔案資源的文化價值對于構建檔案記憶、城市記憶和社會記憶具有重要意義。
1.3 數字記憶應用于紅色檔案資源開發的適用性分析
1.3.1 拓展資源開發路徑
數字記憶應用于實踐項目數量大且類型多樣。按照地區來看,包括國家類記憶項目、地方記憶項目,按照事件屬性來看,包括文化現象記憶項目、重大事件記憶項目等,數字記憶深厚的實踐與理論內容就為紅色檔案資源開發路徑提供了新思路。將前沿的數字技術,如,機器學習、GIS地理可視化、VR/AR等技術,融入檔案記憶的“存取”與“展示”,使得紅色檔案資源開發路徑成為數字記憶視域下新的落腳點。
1.3.2 培養社會正向風氣與歷史責任感
紅色檔案資源具有多重利用價值,對社會公眾道德觀、價值觀以及思想教育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從社會群體來看,生長于信息時代的中青年群體逐漸成為社會主要群體,微博、微信、網頁等數字信息已成為他們不可缺少的獲取信息來源渠道,將數字記憶與紅色檔案資源相融合,不僅能夠提高公眾對于紅色檔案的認知程度與接受程度,也有助于肅清社會不良風氣,樹立公眾的正向價值取向,培養中華民族的歷史責任感與使命感。
2 紅色檔案資源開發模式實證分析
2.1 紅色檔案開發模式
數字記憶對紅色檔案資源的開發利用提供了新思路、新技術、新方法的理論支撐和指導,在深入挖掘紅色檔案資源的同時,提高社會公眾對檔案的認知程度。本文以對紅色檔案資源的開發主體為模式劃分依據,并通過對典型案例分析進行多角度對比,得出以下實踐分析矩陣,見表1。

表1 數字記憶視角下紅色檔案資源開發模式分析表
2.1.1 檔案部門主導模式
檔案部門主導模式是由國家檔案局等檔案行政管理機構對紅色檔案資源進行保護和開發的一種模式。2019年9月,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江西省檔案館用3D技術在線上開展了“紅旗漫卷江西——革命歷史檔案文獻展”,通過展示八一南昌起義、湘贛邊界秋收起義、井岡山斗爭等一系列黨的革命運動,宣揚偉大的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講好江西省改革發展的新故事[7]。2021年5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項目中國國家委員會在評定中國檔案文獻遺產名錄時,將中國工農紅軍長征檔案文獻與冼星海的《黃河大合唱》手稿編入名錄內[8],這是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和藝術財富,對研究中國革命史具有重大意義。
2.1.2 機構協同推進模式
機構協同推進模式是指社會公益機構或商業機構作為推進紅色檔案資源開發的一部分,參與到檔案資源管理工作流程中。2012年4月,中國記憶試點項目——東北抗日聯軍專題文獻資源建設啟動,國家圖書館中國記憶項目組搶救性的收集到各種珍貴手稿、日記、照片等文獻資料,以及對抗聯老戰士及其子女進行口述訪問,收集到約72小時的影音材料[9]。安陽紅旗渠精神的VR體驗館,每位游客借助VR的虛擬重建技術都能重歷紅旗渠修建情景,感受到以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為核心的紅旗渠精神[10]。隨著數字時代的深入發展,以“紅色+VR”、“紅色+5G”等為主題的旅游新業態紛紛崛起,在探尋老區發展的新路徑下,不斷提高社會機構的參與積極性。
2.1.3 學術組織推進模式
學術組織推進模式是指學術機構或學術組織從紅色檔案資源的歷史或社會意義角度進行資源開發利用的一種模式。如南京大學ARMapper團隊與南京利濟巷慰安所舊址陳列館合作開發“南京地區侵華日軍慰安所的AR故事地圖”項目,將慰安婦的個人創傷構建為公共記憶,利用GIS技術和AR技術,形成歷史學理論、社會學方法和新信息技術三合一的新構建模式,再現南京慰安所的舊址原貌以及其中發生的歷史事件[11],直觀的向公眾展示了日軍在侵華期間犯下的累累惡行。
2.1.4 公眾積極參與模式
公眾積極參與模式是指個體或社會群體以自發性組織的方式參與到紅色檔案資源傳承、紀念、開發的整個環節中。如中國人民解放軍原副總參謀長李天佑之子向解放軍檔案館捐贈了其父百余件珍貴檔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的女紅軍謝飛的親屬向省檔案館捐贈了謝飛的紅色革命檔案資料[12]。豐富檔案館館藏的同時,向世人展示了革命時期中巨大貢獻的佐證。
2.2 模式分析
深化領導主體間的跨界合作,擴大參與主體的組織范圍。從領導主體來看,對紅色檔案資源開發研究是以檔案部門為核心驅動力量,但如今社會呈多元化發展態勢,只憑借單一力量無法趨近最佳的社會效益和實踐效果,開發紅色檔案資源既離不開紀念館、圖書館等文化組織機構,也不能缺少以文獻為研究內容的高校、科研機構。一方面,開展主體間的協同合作有利于降低數字資源重復率,節約檔案部門前期投入的時間和財力;另一方面,可以避免對同一記憶項目惡性競爭,實現項目活動的最大效益。從參與主體來看,每種開發模式其參與主體不盡相同,但以數字記憶的目標范圍來看,社會的每一個體都是數字記憶的資料來源和受益目標,因而,如何提高公眾的參與數量和活躍程度以及增強公眾對紅色檔案的意識與共識,是紅色檔案資源后續開發利用的關鍵之處。
拓展紅色檔案資源來源途徑,采用數字技術推進成果展示。數字記憶事實上就是以公眾記憶為來源的,在進行紅色檔案資源開發過程中,四種模式的主體應從“自有資源開發”轉變為“自有+征集資源開發”的雙軌并行機制。從檔案部門和機構組織來看,不僅能夠補充原始資料,還能夠防止出現信息滯后、資源靜態化的情況;從公眾角度來看,一方面促進資源活態化,加強信息流通,實行以人為本的理念,另一方面提高公眾參與數字記憶項目的積極性,增強紅色檔案資源開發活動的互動與交融。此外,應采用前沿數字技術與項目成果相結合,除了使用網站平臺進行3D展示外,機器學習、GIS地理可視化、文本檢索和挖掘技術、VR/AR+5G等技術也能夠融入紅色檔案資源開發建設中,從而豐富項目成果展示方式。
網絡與現實渠道相結合,全方位實現聯通路徑。在這四種開發模式中,幾乎均實現了線上與線下渠道相結合,而公眾積極參與模式盡管以拍攝、紀念冊為主,但微信、微博等社交媒體的覆蓋下,存在采用虛擬渠道進行信息共享。因而,在信息時代飛速發展的當下,線上網絡這一渠道早已深入人們生活中,“虛擬+現實”空間的交叉路徑更有利于個體與群體組織的聯通。
3 數字記憶視角下紅色檔案開發模式的優化構建
3.1 資源層面:多途徑整合開發紅色檔案資源
從資源整合角度來看,紅色檔案資源的開發要利用數字技術手段組織整理現有檔案資源。在宏觀視角下,應探索搭建紅色檔案資源共享數據庫平臺,由檔案相關部門或機構建立統一數字平臺網站,按照紅色檔案主題、檔案類型等設立一級數據庫,在檔案類型下可以按照載體形式,分設紙質資料、照片、音像等二級數據庫平臺,在首頁鏈接各省市開展的利用紅色檔案活動,并實時更新,促進信息共享。各省市同時建立區域平臺,從而構建一個多省聯動的紅色檔案資源開發系統。
從資源開發視角來看,紅色檔案資源的開發要構建多種主題的紅色記憶項目。哈拉爾德·韋爾策就失憶與記憶提出,失憶常常是無意識的,記憶則需要“有意圖地與過去打交道”[13]。馮惠玲教授提出,數字時代的失憶癥要用數字手段救治[14]。以“前沿新技術+展覽新方式”相結合的數字記憶項目,一方面是基于公眾的動態化視覺需要,通過照片、影音、虛擬技術喚醒社會記憶是開發色檔案資源的新思路和發展方向;另一方面,貫徹了數字強國戰略發展目標,利用信息化和數字化樹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堅持文化自信。
3.2 協同層面:多主體合作構建以地域為專題的紅色檔案社會記憶工程
僅依托于單一主體推進一個成功的數字記憶項目可能性很低,必然會在某些領域存在短板,因而聯合多方力量合作構建數字記憶團隊才是正確開發方式。比如數字敦煌項目是由中國科學院計算機研究所、武漢大學和浙江大學聯合打造的敦煌莫高窟保護利用工程,因此,在構建紅色專題檔案數字記憶項目過程中,需要多個社會組織和機構聯合開發紅色檔案資源。
2021年中國共產黨已成立百年,各省市檔案局和檔案館都在進行紅色檔案宣傳活動。以傳統文獻資料進行展覽活動缺少持久的社會影響力,容易被人們忽略或遺忘,筆者認為各地檔案局和檔案館應與當地高校、學術組織開發具有地域特色的紅色檔案數字記憶項目,以線上成果展示為主,輔以線下展覽和學術會議,打破時間、空間的限制與隔閡,擴大參與主體以及提升社會效益。
3.3 技術層面:多樣化展示紅色歷史檔案的故事與文獻
信息技術的創新與突破,帶動了信息生產、信息傳播、信息規則等信息產業鏈的升級,基于數字采集、數字存儲、數字展示等前沿技術的應用[15],使得社會記憶所呈現為類型多樣的數字資源,如何做好紅色數字檔案的“存取”,講好紅色檔案故事,是當下關注的焦點問題。王兆鵬團隊利用GIS等數字人文技術編制唐宋文學地理圖示,提供了檔案開發的又一新思路。將GIS歷史地理可視化技術融入紅色歷史檔案的開發,生動而直觀地呈現中國共產黨革命征程與不同歷史階段的動向,在數字技術理論支持的基礎上,豐富紅色歷史檔案的開發路徑。
在檔案開發利用方面還要貼近人們生活,在利用社交媒體進行內容推送時,抓住社會關注的焦點問題,挖掘紅色檔案資源相關內容,從而提高社會關注。同時,可以用動畫短視頻、短篇漫畫的新形式展現紅色檔案中的故事,并定期做好意見征集與反饋,根據用戶的興趣與需求在合理范圍內調整紅色檔案資源的開發方式。
3.4 實踐層面: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紅色檔案文化數字旅游
為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文化需要,各地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紅色檔案文化旅游成為檔案開發途徑之一。紅色旅游的特點形式是產業式、鏈條式、集中式,將數字旅游與紅色文化融合,彌補了傳統紅色旅游的靜態性與單一性的不足。從國內實踐來看,南京市檔案館聯合博物館打造富有南京特色的紅色檔案文化品牌[16],但缺少與數字旅游相結合,其影響范圍有限。筆者認為,各地相關部門應以紅色檔案數字化資源為創意展示對象,以信息技術、日常運營、更新維護等方面為支撐,逐步實現紅色文化記憶的增值。
4 結語
數字記憶是對過往雜亂而破碎的文化記憶的一種重構,是對城市記憶、社會記憶的拓展與延伸,它為紅色檔案資源開發提供了新的理論支持。開發紅色檔案資源,不僅是對中華民族寶貴精神財富的傳承,更能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征程。當代人們的物質生活較為富足,對精神需求越來越多,且國民整體素質越來越高,對紅色檔案資源開發要求更為多樣,這就需要檔案工作者注重多層次、多角度、多領域的研究交叉學科與前沿技術,為紅色檔案資源的開發提供更廣闊的前景。由于數字記憶和紅色檔案資源的開發仍處于發展階段,還有許多問題有待于進一步研究,比如如何在數字記憶構建中將各地區紅色檔案資源進行聯合開發,怎樣促進紅色檔案與數字記憶融合的新模式,以及考慮紅色檔案與數字旅游新業態的可行性等,仍然是學者們未來研究的重要方向,也是探尋紅色檔案資源開發的新路徑與新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