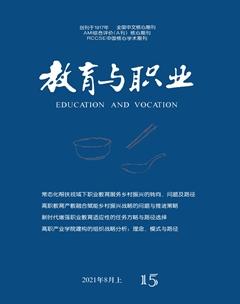職業教育第三方評價與內部評價實現主體認同的博弈分析及建議
劉瑩 胡婷 李文平
[摘要]近年來,第三方評價逐漸成為職業教育質量評價領域的重要工具,但職業教育辦學質量并沒有因為第三方評價的引進而得到明顯有效的提高。文章基于博弈論視角對此進行研究分析發現,第三方評價主體獲得內部評價主體認同不足的影響因素包括職業院校理性、教育行政管理部門信息集以及第三方評價機構的實力等。為此,建議第三方評價主體要注重內部提升、教育行政管理部門明確元治理的角色、加強頂層設計及職業院校改變傳統辦學觀念,增強第三方評價對職業教育發展的促進作用。
[關鍵詞]職業教育質量;第三方評價;主體認同
[作者簡介]劉瑩(1988- ),女,河南新鄉人,鄭州大學教育學院,講師,博士;胡婷(1997- ),女,湖北荊門人,鄭州大學教育學院在讀碩士;李文平(1988- ),男,河南遂平人,鄭州大學教育學院,講師,博士。(河南? 鄭州? 450001)
[基金項目]本文系2016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十三五”規劃教育學一般課題“青少年流動人口職業生涯教育現狀調查及提升機制研究”的階段性研究成果。(項目編號:BJA160065)
[中圖分類號]G717? ? [文獻標識碼]A? ? [文章編號]1004-3985(2021)15-0062-06
質量評價是教育評價的重要內容。隨著國家對職業教育的重視,職業教育第三方評價逐漸發展起來,學者們對此也給予了關注,但關于第三方評價的研究大都從宏觀層面進行探討,缺乏對第三方評價某一方面的微觀分析。特別是關于評價主體的研究,大多從第三方評價主體的分類與界定入手,或者從第三方評價主體整體構建等層面來分別提出對策,缺乏評價主體間關系的分析。評價主體作為評價機制中的利益相關者,具有能動性,其行為選擇關系到整個評價機制的運轉。同時,第三方評價作為外部評價的一種重要方式,與內部評價組成整個評價系統,如果內外部評價主體實現認同,則能在信息公開、評價結果認同上節約很多成本。因此,有必要對評價主體進行深入分析,從博弈論視角研究內部評價主體對第三方評價主體的認同問題。
一、職業教育第三方評價主體的構成及相關主體角色分析
職業教育第三方評價作為一項教育評價活動需要滿足社會和個人的需要,其評價主體應包括職業教育的需求者或是職業教育質量的利益相關者。基于此,本文結合職業教育的發展特征,對職業教育第三方評價主體以及相關主體在評價中的角色進行分析。
(一)第三方評價主體構成的界定
目前,關于職業教育第三方評價主體的選擇,學者們有不同的觀點。劉瑞芳從買方和賣方關系的角度,指出第三方評價機構是賣方,而職業院校、教育行政部門、企業則是買方,他們分別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劉曉敏將職業教育的評價主體分為校內評價和社會評價兩個層次,前者是由學校的教務教學部門牽頭,后者是由上級教育主管部門組織評價和企業間接評價;王永林等基于利益相關者視角,把政府、雇主、校企合作企業作為外部評估主體,而高職院校、學生屬于內部評估主體;李文霞認為高職高專教育教學評估要抓住“誰來評”這個關鍵環節,將教育評估分為內部評估和外部評估兩個層面,外部評價主體是政府部門,內部則由學生、同行教師、專家和管理者組成。顯然,不同學者基于不同視角對第三方評價主體構成的分析都有可取之處。基于此,筆者將市場化的第三方評價機構視為第三方評價主體,把職業院校、教育行政管理部門視為內部評價主體,并對兩個主體的認同情況進行一個博弈分析。
(二)相關主體在職業教育質量評價中的角色
當前,職業教育第三方評價機構主要是受政府的委托,根據要求完成評估任務,同時其作為參與主體在教育質量評估中也有利益訴求,即通過職業教育評估提高社會聲譽、為組織贏得市場份額,謀求發展空間。教育行政管理部門管理著整個教育質量,負責挑選和授權合適的第三方評價機構進行教育評價,但目前第三方評價完全市場化的條件還不成熟,授權不等于放權,就職業教育評價而言,“放管服”需要同時進行,任何環節落后都可能會影響整體效果。教育行政管理部門作為委托方,需要承擔起對代理方進行監督、元評價的責任。職業院校作為內部評價主體有兩種角色,一是作為與第三方評價機構這一外部主體相對的被評者,積極支持與配合評價,表達自己的訴求,不弄虛作假,同時監督第三方評價機構開展評價;二是相對第三方評價這一外部活動而言的自評者,要改變傳統的處于被動地位的觀念,做到外部檢查與自我審視結合,“以一種主人公的積極姿態主動投入到評估工作中去”①,發揮主觀能動性,接受第三方評價的同時進行自我評價,系統地整理、歸類、檢查各項數據,并將自擬的評估報告與外部評價結果相結合來為學校謀求發展資源,提升職業院校的辦學質量和職業教育的社會影響力。
二、基于博弈論建立模型
博弈論的基本假設為參與者均是理性的,每一個對弈者在采取行動時既考慮自身的利益和目的,也關注對手的行為,最終使效用最大化。理論上,這種理性參與者之間的合作難以輕易達成。但現實中,在博弈后選擇合作的情況是存在的。基于此,本文利用博弈論建立第三方評價機構與內部評價主體間的博弈模型,并分析其可能的博弈結果。
(一)第三方評價機構與職業院校的靜態博弈分析
第三方評價機構與職業院校在評估中都各有兩種選擇,即積極與否、認可與否。設Cs為職業院校投入的成本;Ct為第三方評價機構的投入;Rs為學校不認可第三方評價機構時獲得的收益;Rs為學校認可時獲得的收益。通常來說,學校認可第三方評價機構,更有利于發現學校的教育質量“洼地”,但由于教育改革具有漸進性,短期來看Rs
兩者的博弈會有四種可能的結果。一是雙方均配合;二是第三方評價機構不積極評價,由于Rt遠大于Rt,所以積極評價是第三方評價機構的上策選擇;三是職業院校不配合,由此得到的評價效用(Rt-Ct,Rs-Cs)也是較低的;四是雙方均不配合。
綜上,職業院校和第三方評價機構在博弈中均存在一個上策均衡,該博弈也存在唯一的納什均衡(積極評價、不認可)。但與策略(積極評價、認可)相比,這個選擇顯然達不到“帕累托最優”,存在所謂的“囚徒困境”。
(二)第三方評價機構與教育行政管理部門的靜態博弈分析
教育行政管理部門在博弈中有兩個選擇:一是信任第三方評價機構的專業性;二是不認可第三方評價機構,自主評估。教育行政管理部門自主評估所產生的成本為Ce,其認可第三方評價產生的費用為Cr,Ce>Cr。C1是教育行政管理部門投入的成本。
教育行政管理部門自主評估,評估效果為u1;其認可第三方評價機構,評估效果為u2。問題改進后預期產生的收益為y,得到的社會收益為s,s是u的增函數。教育行政管理部門自主評估,凈收益為ys(u1)-Ce-C1;改進效果不佳時,凈收益為-Ce-C1。其認可第三方評價機構,凈收益為ys(u2)-Cr-C1;效果不佳時,凈收益為-Cr-C1。
教育行政管理部門認可第三方評價機構,評價成功概率為p,失敗概率為1-p;其自主評估成功的概率為q,失敗的概率為1-q。在博弈中,教育行政管理部門自主評估的期望收益為E1=p[ys(u1)-Ce-C1]+(1-p)(-Ce-C1),其認可第三方評價機構的期望收益為E2=q[ys(u2)-Cr-C1]+(1-q)(-Cr-C1)。據此博弈結果有三種情況:E1=E2,E1
(三)不同規模第三方評價機構間的博弈分析
第三方評價機構對認真評價與消極評價的后果均有一個收益函數,內部博弈也就有四種結果。該博弈的納什均衡為規模大、運作能力強、成本和信息收集壓力不大的第三方評價機構,選擇認真評價;而規模較小、認證不足、資金也較為缺乏的第三方評價機構,會依賴前者去開辟市場,而自己等待受益,選擇消極評價。該策略顯然不是最優解,大量敷衍評價、評價效果差的第三方評價機構的存在顯然難以起到宣傳第三方評價機構的作用,導致其只有部分獲得內部評價主體的信任,難以獲得整體上的認可。
三、第三方評價主體得到內部評價主體認同的影響因素分析
通過第三方評價主體與內部評價主體間的博弈過程可以看到,第三方評價主體得到內部評價主體認同是一種雙向選擇,達成合作并非易事。職業院校、教育行政管理部門以及第三方評價機構在博弈中對可以達成認同的考量和懷疑都會影響最后的合作效果。
(一)職業院校方面
根據博弈論的預設,參與者都是“理性人”,即他所做的所有選擇都是使自身效用最大化。在第三方評價機構與職業院校的博弈中,職業院校作為一個獨立的“利益”實體也不例外。職業院校與第三方評價機構進行博弈的過程,就是職業院校對評估產生的成本與收益的理性考量。對職業院校辦學質量的評價關系到職業院校的聲譽,很可能會將學校內部不好的一面展示出來,進而影響生源和政府投資力度,威脅到學校的生存,學校自然不愿意接受第三方評價。另外,博弈中的收益顯示,“一旦某種行為的收益大于個體做出的犧牲,那么他將樂意做出這種犧牲,因為這是通過自我犧牲讓其他人從其行為受益,而他獲得了精神上的滿足感”②。受中國傳統文化和全能性政府管理模式的影響,職業院校在對待第三方評價上思想比較封閉,覺得第三方評價是完成政府強加的任務,實質還是政府評價,沒有建立起與自身的聯系,未能認識到第三方評價有利于自我檢視與自我完善,繼而推進職業教育變革與創新,缺乏長遠眼光,認為犧牲遠遠大于效用,致使內原動力缺乏,在與第三方評價機構的博弈中態度消極。
同時,博弈論認為參與者的理性取決于其掌握的信息,信息掌握不全會影響其行為。一是職業院校無法預估第三方評價結果,可能要將有限的政府投入花費到非計劃內事務上。因此,在缺乏限制或激勵的情況下,學校會本能地自我保護,出現“戒備”心理,不認可第三方評價主體。二是無法預測同行的行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職業院校不可避免地會受到“馬太效應”的影響,即強者越強、弱者越弱,導致一些愿意公開真實信息的院校在第一輪評估中處于劣勢,在資源分配上處于不利地位,陷入惡性循環;而一些存在數據造假的院校充分展示了自己的“優勢”,從而得到政府的關注,社會資源也會向其集中,便不愿配合第三方評價機構工作,真正意義上的合作認可也就不存在了。
(二)教育行政管理部門方面
教育行政管理部門雖通過授權和購買服務實現了第三方評價機構與自己管理上隸屬關系的脫離,但在第三方評價過程中,其還習慣于以指示規定的管理方式參與。處在博弈過程中的教育行政管理部門是理性的,購買第三方評價服務后如過多參與評價活動會加大管理服務成本,難以實現效用最大化,但又不能完全放手,因為職業教育第三方評價剛剛起步,實踐經驗缺乏,教育行政管理部門擔心出現評價秩序混亂。另外,博弈中的參與者都會有很多信息集,而每個信息集里有很多無法分辨的信息,“這些信息集刻畫的是其擁有的信息,而非其推斷出的結論”③。教育行政管理部門認為第三方評價效果是好是壞就在一個信息集內,但對第三方評價機構來說選擇認真還是敷衍卻是分屬不同的信息集。所以,教育行政管理部門的參與與否是影響其認同第三方評價主體的重要因素,既要防止過度參與,又要防止避嫌不參與。還有,現階段缺乏對教育行政管理部門參與人員合法身份的認定,沒有建立起對話協商機制,教育行政管理部門無法獲得深層次的信息,對評價結果的理解和利用存在困難,所以教育行政管理部門挑選第三方評價機構時顯得更加猶豫。
(三)第三方評價主體方面
當博弈是一種無限次重復的博弈時,“參與者能通過一次博弈產生的良好聲譽使其在其他博弈中也受益,這種利益可以看作是一輪策略所產生的收益的延期獲取”④。對于在之后重復博弈中兌現的獎勵看重程度不同會影響第三方評價機構開展第三方評價的態度和努力。一是對于未來教育行政管理部門提供更多的合作項目收益的認識不同,一些第三方評價機構通過認真開展評價來傳播好名聲爭取代理權,而其他一些機構由于心理原因和短期組織實際利益的影響,看不到未來第三方評價市場收益,對評價工作敷衍,由此產生的不良聲譽變成了懲罰,再次被教育行政管理部門選中的可能性降低。二是對之前與職業院校合作經歷創造的名聲在職業院校內部的影響力把握不夠,第三方評價機構在評價中留下的感受與印象被認為會影響職業院校根據合作經歷配合其工作的意愿。如果第三方評價機構在專業技術、自我管理、溝通協調和政策適應等方面有出色的誠意與實力,能為職業院校的生存發展提供建議與指導,職業院校自然會愿意配合工作,甚至在之后的評價活動中主動與第三方評價機構合作,第三方評價機構也可以獲得更多的發展空間,實現長期效用最大化。而目前第三方評價市場不太成熟,開放程度也有待提高,專業評估人才缺乏、數據庫建設基礎不足等導致了專業性受質疑。此外,雖然第三方評價機構通過政府購買服務和公開招標等形式獲得了評價主體的合法性,但實際上還是一種集“教練員、裁判員和運動員”于一體的主體。例如,某些承接教育評估的民間組織,其組織形式、領導結構、經費來源等都還帶有官辦色彩,一次不愉快的評價經歷可能就會讓職業院校認為這部分第三方評價機構發揮作用不明顯,難以提供實質性的幫助,這部分機構也就難以讓人信服和認可,合作也就難以再次產生或延續。
四、促進第三方評價主體獲得內部評價主體認同的建議
通過上述分析可知,影響博弈結果的關鍵還是參與者的理性與信息;同時,對手的實力和能力也會影響自己的理性選擇。因此,促進第三方評價主體獲得內部評價主體的認同可以從第三方評價主體自身、教育行政管理部門和職業院校入手。
(一)第三方評價主體要注重內部提升
第三方評價機構要加強自身能力建設,提高評價效能。第一,在信息公開、活動透明的同時,重視溝通協商,以達成評價認同。第二,注重輿情監督。“關注本組織的社會輿論動向”⑤,及時了解社會需求,明確組織發展情況,降低風險處理成本,時刻做到自律和自治,敬畏評價;及時收集被評價組織的意見和建議,完善與矯正評估信息,確保評價結論的客觀公正。第三,完善財務制度。第三方評價機構的資金會有多種來源,完善財務制度可保證良性運轉、降低腐敗風險,提高公信力。第四,完善工作制度,特別是內部管理制度的健全,提升依法依規投標、競標的實力。第五,強化社會服務精神。在完成政府委托評價任務的同時,要充分利用自身資源為職業院校提供“物超所值”的服務,為學校的改革發展提供建設性意見,構建良好的合作關系。第六,培養專家隊伍,完善激勵機制,吸引和留住人才。加強對評估人員的培訓,提高其外部適應力;加強與國外相關機構、協會和教育學會的交流合作,開闊視野,汲取經驗。
(二)教育行政管理部門要明確元治理的角色,加強頂層設計
教育行政管理部門和社會都是教育評價主體,只是在利益相關性上有些許差別。當前我國治理格局還未完全形成,在第三方評價過程中教育行政管理部門還是要發揮元治理的角色,發揮帶領引導作用,做到適當地“退出”。一是解釋作為委托方的真正需求、前期的相關政策和工作成果,說明對評價結果、內容和形式的期待,分析被評價對象的特點及評價時應注意的問題,指出評價的時間限制,對評價專家人選、評價標準、指標體系以及整體設計提出建議。二是尊重第三方評價主體的價值追求,努力營造其所需的市場化運行環境,按照市場的供求機制、價格機制、競爭機制來購買和使用第三方評價服務,培育市場主體。加快建立資格認證制度,制定第三方評價機構的資格認定程序,出臺相關的資質標準和人員準入標準,提升第三方評價機構的專業性。三是建立一種新的利益格局,解決職業院校的顧慮,發揮激勵相容的作用。例如,對一些主動積極參與第三方評價的學校給予激勵,幫助其改正存在的問題,給予人才、資金和政策上的支持,降低其后續自我完善的成本;對于明顯應付的學校給予負激勵,減少資源分配,激發其改革發展的動力。
(三)職業院校要改變傳統辦學觀念,提高“求生”能力
職業院校作為國家推行職業教育、提高公民素質的載體,公共性明顯。教育是最大的民生,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同是為了育人。因此,職業院校要明確自己的定位,正確行使權利和承擔義務。一是職業院校要了解自己是職業教育這一準公共物品的提供者,有責任接受投資者、消費者及社會組織的監督與評價。要積極配合第三方評價主體的工作,盡可能提供評價所需的信息,以獲得科學準確的評價,這對未來生源輸入、經費獲得影響較大。二是職業院校需逐步形成為社會辦教育的觀念。教育辦得好不好,最終還是得“消費者”說了算。第三方評價能補齊內部自我評價在時間、人力、技術等方面的短板,代表廣大“消費者”的評價偏好,能更專業地發現和解決問題。三是職業院校要改變依賴政府資源供給的生存觀念,學會自謀出路,拓展所需發展資源的來源,減輕辦學壓力。例如,與企業協商,在學校自建的實驗實訓基地為企業培訓技術人才,同時企業需支付部分培養成本;依靠自身影響力,爭取國際機構、有識之士等社會資助;通過經營學校資產,獲得經營收入。
[注釋]
①王永林,王戰軍.論高等職業教育評估主體的構成[J].職業技術教育,2011(25):58.
②④劉小山,唐曉嘉.基于囚徒困境博弈的理性、信息與合作分析[J].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22,26.
③(美)拉斯穆森.博弈與信息:博弈論概論[M].韓松,張倩偉,龐立永,等,譯.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54.
⑤徐雙敏,崔丹丹.社會組織第三方評估主體及其能力建設[J].晉陽學刊,2018(5):110.
[參考文獻]
[1]崔月琴,龔小碟.支持性評估與社會組織治理轉型——基于第三方評估機構的實踐研究[J].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17(4):55-60.
[2]郭小聰.政府經濟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
[3]黃承國,肖山.“管辦評分離”改革中的高等職業教育第三方評估優化[J].中國成人教育,2019(14):26-28.
[4]蔣麗君,何楊勇.高職教育第三方評價的局限、問題和對策[J].黑龍江高教研究,2017(9):99-102.
[5]鞠錫田.政府參與第三方教育評估:現實路徑、理性思考與應然走向——基于對s省的實證考察[J].當代教育科學,2019(7):69.
[6]劉瑞芳.論職業教育第三方評價機制的構建與實施[J].職業教育研究,2017(3):16-20.
[7]劉曉敏.高等職業教育評價的現狀、問題及對策研究[J].職業技術教育,2005(07):20-23.
[8]李棟,蔣軍利,唐曉嘉. 基于名聲機制的重復囚徒困境合作博弈分析[J].計算機科學,2013(4):240-243.
[9]李文霞.試論高職院校教育教學評估主體的缺失與對策[J].黑龍江高教研究,2008(09):139-141.
[10]黎明.公共管理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11](德)賴因哈德·施托克曼.非營業機構的評估與質量改進:效果導向質量管理之基礎[M].唐以志,景艷燕,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
[12]王晶晶.民間第三方教育評估機構公信力的構建[J].教育評價研究,2016(1):45-49.
[13]王啟龍,湯霓.委托代理理論視野下職業教育第三方評價:潛在風險、行為博弈與應對策略[J].職教通訊,2020(2):1-9.
[14]王晶晶.基礎教育第三方評估中的學校角色[J].教學與管理,2019(22):20-21.
[15]王璐,王世赟,尤錚.國際視野下第三方教育評價機構的規范、認證與行業自律行為研究[J].現代教育管理,2020(5):36-45.
[16]徐紅勤,崔靖宇,潘瑞雪.職業教育多元化社會評價機制實施條件和配套改革研究[J].現代教育管理,2019(2):108-112.
[17]楊彩菊,周志剛.第四代評價理論對高等職業教育評價的啟迪與思考[J].中國職業技術教育,2012(30):70-86.
[18]AUMANN R J. War and peace[J].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2006(46):17075-17078.
[19]VAN BENTHEM J. Rational dynamics and epistemic logic in games[J].International game theory review,2007(1):13-45.